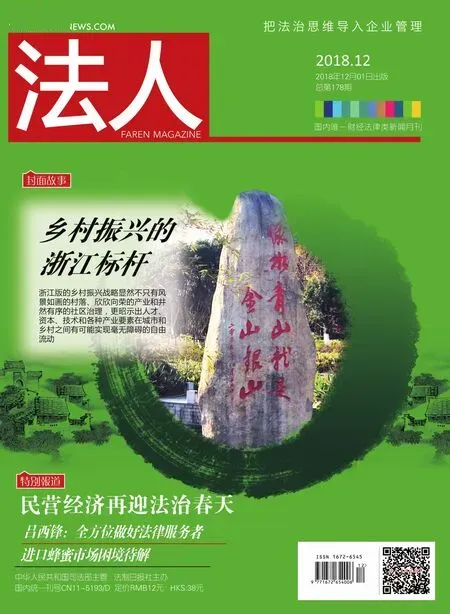乡村振兴的浙江标杆
文 《法人》记者 阮加文
浙江版的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只有风景如画的村落、欣欣向荣的产业和井然有序的社区治理,更昭示出人才、资本、技术和各种产业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可能实现毫无障碍的自由流动

平日里几乎不看电视的刘世伟这一天傍晚却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他就想听听央视新闻节目对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解读。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在刘世伟看来,这个旨在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纲领,将不只是让那些正在凋敝的村庄和再也回不去的年轻人又一次走到聚光灯下,也会使人获得不一样的眼光重新审视每年都被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
刘世伟在大学里学的是农科,2005年大学毕业后在浙江省一个农业研究机构工作,从此与纷繁复杂的农村问题结下不解之缘。也就是在这一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一个被毛竹包围的小山村余村做出科学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论断当时就吸引了在浙西山水之间长大的刘世伟,只是他不可能想到,这一后来被总结为“两山”理论的思想不仅给浙江成千上万的村庄带来令人赞叹的巨变,也为13年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宏伟蓝图。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同比增长9.1%,是全国13432元的1.86倍,连续1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在位于太湖之畔的湖州市,2017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甚至保持在1.73∶1,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迄今为止,浙江全省已创建美丽乡村先进县58个,示范县12个,一大批“脏乱差”的村庄变得“水清、路平、灯明、村美”,不计其数的村庄面貌已焕然一新。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高歌猛进、飞速增长的经济似乎天然限制了人们对中国乡村未来的想象力,社会一直在鼓励繁荣的城市反哺落后的乡村、发达的工业反哺停滞不前的农业,这种思维甚至被设计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路径。然而,浙江乡村振兴的成功实践却证明,如何振兴乡村还存在另一种更令人信服的逻辑。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的话说,要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乡村的大振兴,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谋好新篇。既要遵循乡村振兴规律,又要勇于打破常规,突出规划先行、突出融合发展、突出系统推进、突出共建共享,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发动农民积极参与进来,加快形成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根据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专家秦诗立的解读,浙江乡村振兴在理念和路径选择上首先是城乡融合、一体共赢;核心和重心在于进一步提升和增进乡村的魅力,使其不仅自身要成为美好生活的盛放地、大观园,而且要争取成为城市产业、人居、金融、技术、文化等的外溢地、安放处,并可实现城乡之间的无障碍、无门槛自由流动与共享。
“事实上,城乡割裂到城乡融合会贯穿乡村振兴战略的始终。”刘世伟认为,深化城乡配套综合改革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持续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早在2014年,浙江就开始了“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改革实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是农民最重要的三项权利,浙江省当前将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基础性工作将权利量化到人(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权随人走”“带权进城”的具体办法,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城镇化”。同时,还进行了深化“三位一体”、农村产权制度以及农村金融等一系列改革;在美丽乡村建设上,浙江最新探索的“抱团飞地”模式也已卓有成效,所谓“抱团飞地”就是将贫困村、薄弱村用地指标集约打包和城郊用地指标进行置换,从而挖掘潜在的资源禀赋和乡村价值。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浙江相对成熟与高效的市场体系,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也为乡村领域的建设、服务和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市场资源。浙江的村级自治、协商民主等自治领域,则发挥了在基层动员、农民引导、矛盾调处等方面的作用,使得乡村社区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优势得到了展现,乡村集体的一致性行动得以实现。
显而易见,浙江版的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只有风景如画的村落、欣欣向荣的产业和井然有序的社区治理,更昭示出人才、资本、技术和各种产业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可能实现毫无障碍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