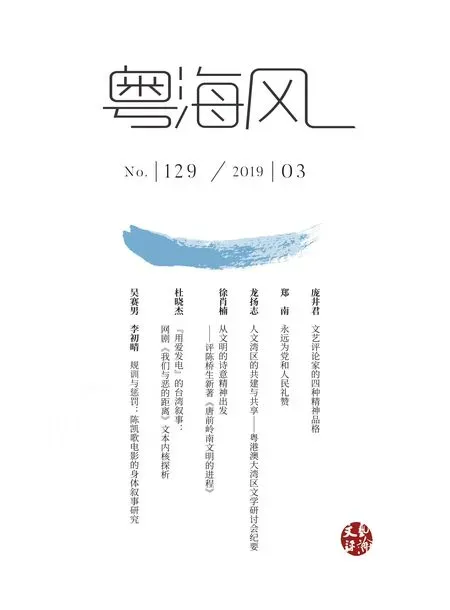规训与惩罚:陈凯歌电影的身体叙事研究
文/吴赛男 李初晴
不同于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的肆意张扬、感性极致,田壮壮的诗意和理想主义,陈凯歌早期电影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哲理性的探索和质询。他从小熟读古典文学、历史和诗歌,对于艺术的激情既来自理性的思考,却也有诗性的抒发。陈凯歌执导下的镜头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沉重。他善用宏大叙事和结构的精巧来表现心中的电影理想和自己的人文追寻,这也造就出他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型作者电影风格。
对于陈凯歌电影中对身体叙事和父权思维的探讨,既源于时代大环境对第五代导演的思维塑造,更受到个人成长经历与家庭关系的影响。在陈凯歌的成长经历中,他与父亲陈怀皑之间存在复杂感情,也让他对于经历过的特定时代(“文革”阶段)产生了一定逆反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创作。
在这场政治灾难中,他主动揭发和批判自己的父亲,让自己的心灵一并蒙上了时代和家庭的双重阴影。因此,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思索中,他执着于在电影中探讨忠诚与背叛、狂热与仇恨的关系,这也成为他电影创作的核心动机。能够看到,陈凯歌对于时代赋予的那些无形的权力压迫与反抗的认识,很多是从自己的青年困境和现实成长中汲取和形成的。而陈凯歌对于其电影中对身体叙事的表现,则也来源于此。他回忆父亲被打倒时期,从身体向心灵的压迫和不快。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因此,他对身体政治的理解随暴力行为带来的快感而形成,肌肤的接触和身体的伤痕成为最明显的权力印记。
一、第五代导演对身体叙事的呈现
陈凯歌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后,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与第五代同仁一起,开创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开创性的繁荣局面。因此,陈凯歌电影中对于身体叙事体系的形成和呈现,也是将个人因素深深揉进时代中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乱无疑是最大的时代背景。这也形成整个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五代导演对于时代的集体印象。对于亲历过去而带来的不认同和反叛,对于最高意识形态的思考,能够透过自身的男性视角和历史伤痕对身体政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在第五代导演中出现的父亲形象大多是消极和备受质疑的,在越过了“十七年电影”的门槛后,他们意欲树立起来一个新的文化形象。因此,不管是《红高粱》中大家族的父亲,还是《黄土地》中女主角翠巧的父亲,都在客观地陈述之外存在一定的负面色彩。而这种男权社会中大家族族长式的角色,不论是其作为实施权利的一方还是被报复的一方,其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粗暴而直接地对身体的惩罚和规训来表现。身体,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被呈现为一切权力施加的交汇点,并最终通过视觉影像语言展现在大荧幕面前,成为一种传递时代价值观的大众文化。然而,另一方面,第五代导演仍旧未能彻底摆脱男权思维的局限,这尤其反映在其对女性角色的整体性塑造中。女性身体在镜头前的展现仍然被赋予太多性别的联想,这直接导致灵魂、思想层面的独立人格和话语权被掩盖过去或因不做全面而立体的赘述,导致其始终作为一个性别符号,活在男性主宰的权力体系之下。即使是在陈凯歌意欲借此为女性发声的电影《搜索》中,也未能完全展现女性身份对自我成长的正面影响,更不用提在《荆轲刺秦王》 《和你在一起》《赵氏孤儿》等影片中,对作为支线剧情中女性角色的塑造。
作为第五代导演中一名卓越的艺术贡献者,陈凯歌执导电影以男性视角,表现出极具个性的独立与反叛,通过对电影中性别角色的思考与架构,呈现出身体叙事下的文化观与人生观。而米歇尔·福柯作为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文化理论学家,所提出的身份叙事理论为其学术成果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在电影上的表现,则更多以围绕福柯权力观中对身体的规训、性别角色的生成等手段来进行分析。
在此,笔者将着重以福柯的身体叙事研究,对陈凯歌电影中英雄叙事的身体政治、女扮男装的文化建构与母亲形象的建构三个角度,分析其电影中如何对身体叙事进行呈现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味。
二、《荆轲刺秦王》中的双重英雄塑造
陈凯歌执导的历史类电影中,有一些带有极强作者电影色彩的重在描摹宏大叙事下的英雄潜伏复仇、谋反帝王等情节的电影。例如,新世纪前的《荆轲刺秦王》,以及近几年来的《赵氏孤儿》《妖猫传》等。此类电影往往从导演塑造的英雄观切入,在情节的展开上展现身体上的规训。尤其是在帝王叙事电影中,身体的背叛与服从更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
电影《荆轲刺秦王》在几代版本中原本以荆轲刺杀秦王的行刺场面为叙事主体,但是电影在前面埋伏下看似冗长的背景介绍及情节铺垫。电影中塑造的两个英雄或枭雄角色——被刺者秦始皇与刺杀者荆轲——在使命的召唤后完成自我救赎与放逐。电影的历史叙述空间定在尔虞我诈、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封建时代残酷的身体规训与惩罚在电影中得到较为平实的演绎。
在荆轲被监狱吏施用酷刑时,镜头一幕幕扫过被鲜血浸染的石块,随着身体前后的摇摆,头不断接近石块,这时屏幕外的观众心中的恐惧感也随之层层加重。画面中,荆轲却缄口不言,从容就义,一个不屈的非典型英雄形象在这种身体的威胁中被树立起来。观众对于杀手荆轲的感情是复杂而沉重的,荆轲肉体上的皈依未了唤醒了人们对正义的渴望,但是杀人营生时的残暴也时时让剧中的荆轲陷入身份的困惑与悔恨。在他被高渐离的医术挖去血痂时,镜头在极度疼痛发出的嘶吼间转换到了盲女自杀的画面,通过快速的镜头切换,身体的苦痛与内心的冲击被有力地纠缠在一起。能够看到,剧中塑造的英雄观是多面而立体的,在施暴与被施暴之间,荆轲的内心状态发生转变——如果说之前他只有生存欲求的话,那么此时他的情欲与善念也在滋生。
而另一个令人敬畏的历史形象——秦始皇在电影中也被呈以病态人格的创造,这或许成为多数观影者诟病的主要缘由。例如,电影中,嫪毐与嬴政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一场身体的较量与驯服间草草收场。嬴政一把抱起嫪毐将其放在两个城楼之间架起的木板上,嫪毐以懦弱和迎合取得嬴政信任,嬴政自大而狂妄的形象也进一步得到诠释。影片中,同样涉及的身体规训还有秦国残酷而细分的刑法。例如,黥刑通过在脸上烫字作为降服的符号。这种身份的归降是在肉体的受罪中展开的,同时它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转变为另一国家的阶下囚的转变,它使得暴力权力上升为一个符号权力,以给人震慑而威严。影片里,赵女在自己身上施加这种刑罚希望骗取燕丹的信任,避免战争,实际上就是在表明身体在权力惩罚下已经沦为一个符号。
正如福柯在话语权力理论中认为的那样,身体作为一种话语,其本身带有权力的烙印:“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因此,身体不仅是权力的规训对象,同时它也生产权力。”[1]福柯认为,社会所有的历史悲喜剧都是围绕身体而展开的,身体被精心地规划,是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在控制它,生产它,并且“历史摧毁了身体”[2]。电影中,秦始皇始终被统一六国成就大业的历史使命所束缚和禁锢,这种禁锢直接受困于他的身体。他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历史中的一个关联物,是权力的承载体。作为个人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身体主动的控制权,只能听命于历史的召唤,并最终造成了人格的异化。
在另一部电影《赵氏孤儿》中,肉体本身就以作为权力的传承物而存在。赵氏孤儿的幸存在家族的恩怨情仇中,变成了一把利刃,被迫卷入到一场政治的争斗中,最终将尖刀刺入仇敌的胸膛。根据福柯的观点,“肉体只有在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3]在这部影片中,也完全践行了福柯的这一观点。一方面,肉体作为生命的存在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又化身为另一种力量的留存,成为两股力量对峙的基本载体。赵氏孤儿被程婴在自己的阴谋中训练、培养,但是同时孩子又陷入到另一种培养体制中,这一幕在屠岸贾和程婴让孩子跳下屋檐的情节中明确展现。影片中,程婴真正的儿子程勃和赵氏孤儿虽然同为婴儿,但生下来就被身份、等级所约束,成为互相代替但完全对立的两方。
在改编视角上,相比原著《赵氏孤儿》而言,电影将屠岸贾弑君的情节和程妻一角加入,并将剧情修改为韩厥放孤后未自杀,同时换掉了屠岸贾的死法。这使得整个电影的叙事主体和逻辑随之改变,韩厥肉体上的保留成为后面剧情的一个推动力。程妻的加入也更合乎让人物在强烈的情感矛盾中走向最后的结局。影片中以不同手法回放的屠岸贾摔死真正的程勃的镜头。叙事镜头、剪影不断交叉在事件的叙述和回忆当中,成为具有强烈视觉刺激的暗示。而这一剧情则是完全建立在视觉影像本体的基础上,对肉身做出的惩罚。肉身的惩罚被电影画面不断放大,对画面内外的观众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
三、男扮女装的角色扮演和身体认同
男性与女性身份性别上的自然属性,以生理形象上的区别最为显著。陈凯歌电影中涉及的男扮女装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历史视阈中导演对于时代与人性的反思意识。因此,本章通过性别角色在中国戏曲文化中的伦理观与宦官角色在朝野中的身体角色两个方面,来分析男扮女装背后的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色彩。
陈凯歌电影中男扮女装的剧情引入,主要以《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两部影片展开。而这两部影片则全部以中国传统戏曲为文化背景,在历史的回眸中,赋予其现实意味。陈凯歌巧妙地将男扮女装的性别关系引入到电影艺术的诉说中,借助男扮旦角和“戏中戏”的手法,使得对时代和人性的悲剧建构在荒诞离奇的性别角色之上,让人更觉悲哀沉痛。电影《霸王别姬》中的男主角程蝶衣在现实中“本是男儿郎”,但是在戏中却变成“女娇娥”,在戏班师傅强行纠正程蝶衣的台词的一场戏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一句戏词经常被蝶衣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随后师傅随手拿起烟斗捅进小豆子嘴里,不断搅动。这一富有性意味的行为将程蝶衣的性别角色逐渐从身体上的被侵犯内化为心灵上被迫的自我认同。
相对于女扮男装而言,男扮女装似乎更容易抹上一层悲剧阴影。在东方文化的训诫中,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区别也被当作一种伦理特征加以诠释,女扮男装的历史故事与民间演义大多被赋予勇猛善战的巾帼英雄角色,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然而自有阶级分化和暴力压迫以来,由于女性一直以来的依附地位,被赋予女性特征的男性则大多意味着屈辱和被服从的身份地位。这一点可在古代律法上寻获一二——我国在殷商时代就实现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做法。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
而我国传统的戏曲文化中男扮女旦的传统,则原本就是缘于旧时妇女地位的低下。尽管女伶演戏在元明舞台上曾一度活跃(尤其是元代),但到了清代,随着礼教意识强化,许多梨园成为清一色男演员的天下。“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旋奉严旨禁止。”[4]由此,可以看到,影片中男扮女装不仅是性别关系的转换,同时又是我国文化伦理与社会地位的展示。在电影中,男儿身的程蝶衣扮成旦角后,进入到虞姬的角色中,并不断代入角色的感情。在女性身份的新的时空中,程蝶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而在现实里他却处在无依无靠的境地。这种由于性别转换带来的痛苦,使他最终无法自拔,人性的凄凉又多添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另一方面,戏曲情节构建的虚拟空间可以看作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5]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物的换装是完全明了的,它不像花木兰替父从军中现实的参军,而是一种虚构情节的演绎。在戏曲空间中,演者和观者全部清楚台上戏子性别角色的状况,因此不存在掩饰、暗藏或猜测身份辨识的层面。但是,在接下来展开的爱恨纠葛中,男主角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发生了错乱。这种认知混乱导致男扮女装下的程蝶衣心境和情感的内部转变。由此,男扮女装在剧中的含义由身份角色的表面转换,演变成了自我性别认知的转换。而这种双重转换是在中国戏曲表演中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引起的,再落入历史和时代不可逆转的悲剧中去,在人性、性别、时空的转换中将文化与历史的思辨推向深处。
相比之下,《梅兰芳》中的男扮女装叙事则与现实层面的关联较弱。在历史向现实的投射中,电影主要集中以男儿身的梅兰芳对两位知己和爱人的感情作为叙事主体,对性别角色的转换导致的内心冲突与情感不做主线叙述。这也让整部片子的历史深度和时代隐喻逊色了一些。
在陈凯歌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角色——嫪毐。在电影《荆轲刺秦王》中,嫪毐作为一名伪宦官私通赵太后,后又谋反嬴政,揭示嬴政身世,落得车裂之刑而死。嫪毐的伪宦官身份虽然不能完全算作男扮女装,但是需要扮出女性的生理特征。电影将嫪毐作为逆子的形象进行重新书写,突出他作为普通人与赵太后的情愫历程。在阴柔的宦官角色和穿上盔甲意图谋反的军官角色的对比中,一个为成大业,野心勃勃,但蛰伏数年最终失败的历史人物形象也被塑造起来。这种男扮宦官的非典型“性别转变”,除了给处于历史中的人物带来一丝吊诡和阴谋论的气息,也同时加重了人们对宦官在我国历史中的政治地位和其所使用的权力手段等的刻板印象。再如,这种宦官角色还出现在陈凯歌最新的一部电影《妖猫传》中,其中被称为“千古宦官第一人”的高力士一角,更让人们对与宦官的性别意识与其历史视阈下的参政身份的敌视和不齿。《妖猫传》再现了太监高力士为唐太宗在虚构出的极乐之宴上脱靴的情景。尤其是在这两部影片中,均将特写镜头对准宦官的狡黠与诡异的笑容。对于观众而言,这是对人物的负面形象的一种暗示。
在身体性别的转换中,“功成名就”的太监形象似乎始终行走在正邪边缘上。在性别外型转变的同时,其心理意识也随之变为扭曲与狭隘的一面,能够明显区分于女扮男装后英气潇洒的歌颂式正面形象。由此窥见,我国传统观念建构下对于男扮女装认同上的文化隔离,以及在两性问题上生理性别意识的根深蒂固。
四、多重能指的女性身份
女性身体相比男性而言,更具柔弱、敏感的生理属性,同时也更容易沦为一个性别符号,含有更加复杂的意味。在福柯的观点中,身体由话语组成,构成了日常生活与权力体系间的关联。福柯认为对身体的控制和意识只有对身体施加权力才能获得。“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志,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
较为明显的一部女性主义影片《搜索》,则主要以女性为言说对象,围绕性别身份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伦理道德进行现代性讨论。作为其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影片,《搜索》用影像语言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将网络暴力、炒作新闻等话题串联起来,道尽女性角色在社会现实中的悲哀与无奈。
影片中,女主人公叶兰秋本来是一个公司白领,但是因突然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不久于人世,而陷入沉重的打击之中,没想到意外卷入一场网络暴力事件。在这个网络空间中,叶兰秋从一个仅与社会具有亲属联系、朋友联系等常规社会关系的普通人,被放大为一个不知廉耻的符号化人物。她被迫走在千万人面前,成为被不知名的陌生人孤立的绝望女性。虽然她曾对这个所谓的道德社会与男权社会发起抵抗,但最终迎来注定走向死亡,并溺死在群体性指责的漩涡中。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及监狱惩罚时,指出“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都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
这种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的观点被运用于大多数电影之中。在电影《搜索》里,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种手法的运用。电影中,女主角叶兰秋始终受限于自身的生理角色。她半裸出浴的出场镜头首先强化了自身的女性性征,后面的被诬陷为小三等污名化身份,又全部基于女性这一生理角色在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在这部电影中被拉到了完全对立的两方,甚至是互相抵抗的两个极端中。同时,导演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女性的受辱和反抗无效中加大戏剧冲突的张力,激发人们对于女性主义和性别意识的思考。
电影中特别强调了媒介带来的性别化,这种性别化最终演变为了性别暴力。新闻媒体的报道使得叶兰秋的女性形象与美貌勾引、诱惑等负面行为所关联,并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另外一个女性角色陈若兮则承担起更多传统男性角色在社会中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职责,工作狂、职场御姐等标签被贴上,但是同时她又是为男朋友做饭的温柔主妇形象。陈凯歌意欲在此构筑起一个全能而多面的女性形象。像他自己所坦言的那样,他希望在这一角色中表现对旧有男权秩序的某种反叛和挑战,树立起对女性身份的认可和新的权威。
在陈凯歌的电影中,女性角色众多,但大多是以依附品的地位存在,群像描写则多以男性为主。虽然不占有重要篇幅,但是女性在电影中制造的意义不可忽视,例如《荆轲刺秦王》中的赵女和赵姬,她们作为情人和母亲各自拥有心中所爱,形象饱满。虽然必须以依附性的姿态存在于时代的战乱和家族的纷争中,但仍然渴望支配身体的自由和爱的渴求。在电影《赵氏孤儿》中,庄姬和程婴妻的母亲色彩则更为浓重,女性自身的母性和对后代的延续功能,使女性在片子中更容易成为一个生育符号,而不具有较完全的个人性格展现和价值拓展。
在陈凯歌的电影中,还有一些具有鲜明女性性征的角色,如《霸王别姬》中的菊仙,《荆轲刺秦王》中的赵女,《妖猫传》中的杨玉环,《道士下山》中的药店老板娘。她们或为妓女,或为皇帝的情人,或为出轨的荡妇,在女性的外表下,始终依附于掌握主体话语权的男性而存在。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性始终是被规训的符号。她们被各种职业、身份、地位所包装,但唯一指向性则为女性受害的身体。在陈凯歌的大多数电影中,女性的肉体一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是权力施加在身体上的政治,是肉体政治学的一种显著表现。
这一点在《荆轲刺秦王》中赵女自愿受到黥刑中也得到明显体现。赵女作为嬴政的青梅竹马,身上寄托着君王的特殊感情。嬴政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黥刑这个权力标记作用的残酷性。而在情人身上,当赵女脸上烫的伤口赤裸裸地向嬴政展示出来时,这个雄心勃勃的君主让步了。很显然,嬴政并没有想把这种暴力权压迫在赵女身上,但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禁锢她的肉体,使她失去归家的自由。这两种权力的施加方法虽然发生了偏移,但不管怎样,仍旧以高位者、男权者的意志为转移,赵女的身体已然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注释
[1]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65-5066页.
[5]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