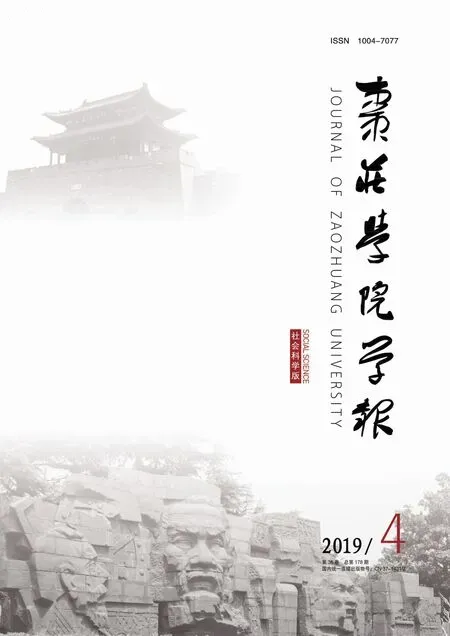论张溥的骈文批评及其文论史意义
杨志君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张溥(1602~1641)是古代第一大文人社团复社的领袖,后来又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可谓晚明极为得势的风云人物。其诗文创作皆可观,《七录斋集》为其代表作,在当时影响甚大。友人陈子龙在《七录斋集序》中说:“夫天如之文章,天下莫不知其能。”[1](P338)《明史·文苑传序》将张溥与钱谦益、艾南英、陈子龙并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矮,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2](P4883)由此可见张溥在明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张溥除了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批评家。他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并于各集前撰写题辞。这些题辞,可视为张溥对汉魏六朝诗文的批评材料。学术界对张溥的文学创作以及诗歌批评、散文批评皆有较充分的论述,①但对张溥的骈文批评,却鲜有论及。而张溥对汉魏六朝作家文集的题辞中,多次谈及自己对骈文的看法,从中可提炼出其骈文理论,本文拟对此作一阐发。
一、“中情深者,为言益工”
骈文讲究对仗、藻饰,语言华丽,以文采见长。张溥对骈文的文辞华美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原叙》中说:“两京风雅,光并日月,一字获留,寿且亿万。魏虽改元,承流未远。晋赏清微,宋矜新巧。南齐雅丽擅长,萧梁英华迈俗。总言其概: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风骨,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人但厌陈季之浮薄而毁颜谢,恶周随之骈衍而罪徐庾,此数家者,斯文具在,岂肯为后人受过哉?”[3](P2)可见,张溥对两汉的赋、魏晋诗文及齐梁骈文,皆有肯定,并为以骈文见长的徐陵、庾信受到批评而辩护,认为追求文采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过程。更何况,这段文字本身就是以骈偶的形式写的,更见出其对骈俪的肯定。不过,从其评江左名流“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可窥见其置“质”于“文”前,也就是在文质关系上,“质”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
在张溥的语境里,“质”指的就是情感。他在《王詹事集》题辞中写道:“昭明哀策,中朝嗟赏,然辞丽寡哀,风人致短。东汉以来,文尚声华,渐爽情实,诔死之篇,应诏公庭,尤矜组练。即颜延年哀宋元后,谢玄晖哀齐敬后,一代名作,皆文过其质,何怪后生学步者哉。”[3](P308)张溥这里指出王筠为昭明太子写的《哀策文》,虽然文辞华丽,但缺乏哀情,故少“风人之旨”。可见在张溥看来,真情实感是第一位的,文辞华美是第二位的。而他对于东汉以来的追求声律藻缋而缺少真情实感是不满的,甚至批评颜延年《宋文皇后哀策文》、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虽是名作,却“文过其质”,也就是虽有文采,却缺乏真情实感,那也是不可取的。可见,“质”指的就是真情实感,“文”就是文采;“质”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在《沈侍中集》题辞中,他又说:“劝进三表,长声慷慨,绝近刘越石,陈情辛宛,又有李令伯风。至《为陈太傅让表》,义正辞壮,即阮嗣宗上晋王笺,曷加焉。恭子隽才,雅慕忠孝,冒危履险,情深指哀,过殷墟而箕子涕,睹风木而吾丘泣,所处然也。”[3](P337)张溥认为沈炯的《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三表“长声慷慨”,与刘琨的《劝进表》相仿;其《请归养表》委婉而辛酸,有李密《陈情表》之风;其《为陈太傅让表》“义正辞壮”,可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牋》相媲美。在此基础上,张溥进一步指出沈炯的骈文“情深指哀”,哀婉感人,突出的便是沈炯文章情感深挚的特点。
在《江醴陵集》题辞中,张溥评价江淹道:“身历三朝,辞该众体,恨别二赋,音制一变。长短篇章,能写胸臆,即为文字,亦诗骚之意居多。余每私论江、任二子,纵横骈偶,不受羁靮……而晚际江左,驰逐华采,卓尔不群,诚有未尽。”[3](P279)张溥指出江淹《恨赋》《别赋》在音韵上的变化,及其继承诗骚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他认为江淹、任昉的骈文不受对偶、声律的限制,能够纵横捭阖,写其胸臆。他还批评江左文士追逐文采,虽然亦“卓尔不群”,但缺少江淹的“纵横”及“胸臆”,故认为“诚有未尽”。张溥认为骈文的写作要“能写胸臆”,应该“纵横骈偶”,无疑还是以情感作为文辞之根本。而在《庾开府集》题辞中更是直接评价庾信的骈文是“辞生于情”,并以之作为庾文独优的地方,更可见其对情感的极度重视。
不过,张溥不仅批评骈文持“辞生于情”的观点,在批评散文乃至诗歌时,皆以情感深挚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其在《谢宣城集》题辞中说:“集中文字,亦惟文学辞笺,西府赠诗,两篇独绝,盖中情深者为言益工也。”[3](P251)张溥推重谢朓的诗歌《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与骈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情深”。在《夏侯常侍集》题辞中又云:“《周诗》上续《白华》,志犹束晢《补亡》,安仁诵之,亦赋《家风》,友朋具尔。殆文以情生乎?”[3](P121)张溥对夏侯湛的《周诗》,及潘岳读该作后所赋之《家风》,并为推崇,并提出“文以情生”的观点,可见张溥是把情深作为骈文与诗歌共同的标准。而在《刘伯宗稿序》中,张溥评应社诸子之散文:“序应社诸子之文,则气动辞数,思常有余。盖亦性情之系,不可类托者也。”[4](P136)可见,张溥认为散文也应该“辞生于情”。
张溥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批评观念。张溥的骈文创作虽然不多,但少数几篇骈文却是“辞生于情”的体现,如《赠大理卿制》,虽是代作,篇幅不长,却具有抒情小赋的特点,周钟眉评道:“四六之文,贵议论,贵丰骨,非徒华美也。天如诸作,仅以酬应而声律清和,字句香洁,其思长,其骨古,便为韵言开辟,才真不可测也。”[1](P531)所谓“丰骨”,所谓“思长”,指的便是篇中的情思绵长,表达了皇帝对大理卿祖父的深切怀念,及对大理卿的勉励之情。而张溥的散文创作,更体现了“情深”的特点。如《王慎五稿序》先叙述未见王慎五前,对其已神交已久;再叙与王慎五之见面,及两人默契相得之乐。行文自然,对友人的深挚情感溢于文字之间。正如周钟所评:“他人之为文,文而已。天如之为文,无非情也。情弥长则文弥曲矣。”[1](P401)《刘公子像赞》周钟眉评:“语不多,而情已甚。”[1](P520)《礼质序》眉评云“奋谈著作,不觉情至”。[1](P381)而其名篇《五人墓碑记》,更是慷慨激昂地歌颂了生于编伍之间的五位烈士,对他们“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读来让人神旺。
二、“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
张溥认为情感是文辞的根本,而深挚的情感用恰当的文辞表现出来,便会有一种“生气”。他在《庾开府集》题辞中说:“(庾信)文与孝穆敌体,辞生于情,气余于彩,乃其独优。”[3](P365)这里指出庾信骈文的特点是“辞生于情,气余于彩”——文辞是从情感中生发出来的,是刘勰所说“为情而造文”;文气溢出于文采,也就是说他的骈文不只是追求文采,还具有文气之充沛,文意之畅通,并认为这是庾信骈文优于其他人骈文的地方,可见其对骈文的文气是十分重视的。
张溥认为有“生气”的骈文便是“俊物”。他在《徐仆射集》题辞中又说:“余读其《劝进元帝表》,与代贞阳侯数书,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至羁旅篇牍,亲朋报章,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代马越鸟,能不悽然?然夫三代以前,文无声偶,八音自谐,司马子长所谓铿锵鼓舞也。浸淫六季,制句切响,千英万杰,莫能跳脱,所可自异者,死生气别耳。历观骈体,前有江任,后有徐庾,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他家学步寿陵,菁华先竭,犹责细腰以善舞,余窃忧其饿死也。玉台一序,与九锡并美,天上石麟,青睛慧相,亦何所不可哉?”[3](P333)张溥这里指出徐陵的《劝进元帝表》《在北齐与杨仆射书》《与宗室书》《与梁太尉王僧辩》等骈文,是感慨兴亡、声泪并发之作,所以有“生气”,而徐陵同时代人(除了江淹、任昉、庾信)的骈文只知道学步寿陵,缺乏真情实感,故无“生气”,因而不能称为“俊物”。
张溥有时把骈文的“生气”称为“逸气”“壮气”。他在《任彦升集》题辞中说:“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齿,生意尽矣。居今之世,为今之言,违时抗往,则声华不立,投俗取妍,则尔雅中绝,求其俪体行文,无伤逸气者,江文通、任彦升,庶几近之。”[3](P293)可见张溥反对掇拾古人之辞以追求辞采,认为这样会丧尽“生意”,也就是缺少生气。他反对违时抗往、投俗取妍,认为骈文既要有声华之美,又要具备雅正之格,同时还不能伤“逸气”,也就是要有飘逸之气。而骈文不伤“逸气”的作者,在张溥眼中只有江淹、任昉两个人。他在《王宁朔集》题辞中又说:“齐世祖禊饮芳林,使王元长为《曲水诗序》,有名当世,北使钦瞩,拟于相如《封禅》。梁昭明登之《文选》,玄黄金石,斐然盈篇,即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其焜燿一时,亦有由也。”[3](P284)张溥指出王融的《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即便语多骈俪,但“壮气不没”,所以它才能在当时十分显耀。可见他认为好的骈文应有“壮气”。
张溥不仅认为骈文要有文气,认为散文乃至诗歌都要有文气。他在《冯曲阳集》题辞中说:“其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叙、官录、说策五十篇,遗逸者多,即今所传,慷慨论列,可谓长于春秋。夫西京之文,降而东京,整齐褥密,生气渐少。敬通(即冯衍)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起扬眉抵几,呼天饮酒。”[3](P37)张溥赞扬冯衍之文直抒胸臆,具慷慨之气,善于属词比事。他对东汉之文有所不满,认为东汉之文虽然文辞更缛丽,但缺少“生气”。可见张溥认为不管是骈文还是散文,都不能缺少“生气”。他在《挚太常集》题辞中又说:“东堂策对,其平生致身之文,中少壮气,沿为卑响,靡靡之句,效者益贫。”[3](P150)张溥指出挚虞策对之文,缺少“壮气”,徒有文采,以致于格调贫弱,可见其心目中“壮气”比文采更重要。他在《孔少府集》题辞中还说:“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耶?”[3](P57)张溥认为东汉文章都过于拘密,只有孔融的诗文富有豪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可见,在张溥眼里,诗歌与文章一样,都是不能缺少文气的。
张溥甚至把“气”与人的性格联系起来,认为“气”是人的一种宝贵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盛气”之人,方能写出有“生气”之文。他在《徐复生稿序》一文中说:“天下深巨之事,非有气者莫为也,况文字乎?吾友复生,士之颠然盛气者也。其为文周折规矩,行安节和,读之有《采齐》《肆夏》之思焉。……夫人所贵乎气者,非其动之谓也。……今之文人弗模弗范者有之矣,类非能特立者也,窥其中索然而干,则亦无有而已矣。使治气焉,必无是患。……复生之文,廓乎远翔,上扰云气,徘徊数处,不离其本,惟其治气者善也,治气者无衡气焉,是以大全其说,又在庄子之言鹏鸟也。”[4](P344)他认为只有有“盛气”的人才能完成“深巨之事”,才能写出好文章,而徐复生乃“士之颠然盛气者”,所以他的文章就如大鹏展翅,直穿云霄,具有一种飘逸恢廓之美。由人格到文章的风格,这体现的是一种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张溥的文章也是富有“生气”的。周钟在《七录斋集序》中这样评价张溥之文:“至其援笔为文,气高风逸,……体含自然之华,动有烟云之气,诚文家之乐事,间代之逸才矣。”[5](P252~253)指出了张溥的文章“气高风逸”,有“烟云之气”。陈子龙在《七录斋集序》也说:“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彼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1](P338~339)指出张溥的文章“逸不逾道”,即具有“逸气”,但又没有偏离儒家仁义之道。张采褒扬张溥之文云:“古文之难,难于音节,其一种亢壮顿挫激昂生气,惟韩欧能之,今仅见天如耳。”[4](P127)指出张溥的古文有亢壮顿挫激昂生气。这些评价大体上是符合张溥文章实际的。
三、张溥骈文批评的意义
张溥对骈文华美的文辞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踵事增华符合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相比于文采,他更重视的是情感的深挚及表现于文章中的“生气”。
“辞生于情,气余于彩”,这种观点其来有自。战国时期屈原提出“发愤以抒情”(《九章》)的看法,西汉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的观点。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亦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6](P212)这里的“辩丽本于情性”,意思跟“辞生于情”几乎等同。刘勰又说,“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6](P214)“繁采寡情,味之必厌”。[6](P216)指出情感是文辞的根本,不能一味追求文采而寡情忽真,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中唐时期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北宋时期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命题,而明代前期薛瑄也有类似的表述:“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词》、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7](P648)再加上李梦阳的“情真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以及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将明代文学重情理论推向高峰,故重情之说成为晚明文人的普遍主张。[8]可见张溥的“辞生于情”远绍屈原,近承李梦阳诸子。
张溥对“文气”的重视,亦有渊源。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浩然之气”,不过它主要指的是一种道德修养,尚未用到文学批评中。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看法,把“气”分为清气与浊气两种,认为它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力强而致”;还指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9](P113)表明曹丕已经自觉地运用“气”来品评当时的诗文了。而齐梁时的刘勰也多次提到“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说:“气有刚柔。”[6](P189)《声律》篇又说:“声含宫商,肇自血气。”[6](P222)在刘勰看来,“气”或“血气”,是人天生的气质,它的刚柔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刚柔。《才略》篇云“孔融气盛于为笔”[6](P318),“阮籍使气以命诗”,[6](P321)《明诗》篇评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6](P31)表明刘勰也把作家气质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丽辞》篇又云:“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6](P238)他认为,运用骈偶,贵有奇气异采,如果词句平庸,会让人昏昏欲睡。这些表明刘勰已经自觉地运用“气”这个概念来批评诗文。唐代韩愈针对古文的创作提出“气盛言宜”,侧重也是作家的道德修养,但他把气与文勾连了起来。张溥的“气余于彩”或“以生气见高”,应是吸取了上述文论家的观点,并把它自觉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
可以说,“辞生于情,气余于彩”的观点并非张溥的原创,张溥的贡献就是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具体的骈文批评当中,而之前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骈文这一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际,鼎盛于齐梁之间,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及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古文运动,骈文渐趋衰落。到了元明,骈文一度陷入低谷。杨旭辉说:“从唐宋直到明末,骈文既没有出现经典作家,也没有经典的名作传世作品。”[10](P24)台湾学者张仁青的《中国骈文发展史》从先秦写到清代,两宋之后便直接跳到清代,元明两代的骈文未立章节,仅于第九章《清代骈文之复兴时期》第一节《缀语》的首段略加说明。骈文创作在明代处于低谷,骈文批评自然也难以兴盛起来,只有王志坚的《四六法海》、蒋一葵的《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隽》,以及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值得一提。而前两部著作在骈文方面的价值,学界已有关注,但对后者中所包含的骈文批评,学界却有所忽视。比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其对张溥的论述着重于其“宗经复古”,认为张溥编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体现了其“兴复古学”的主张,指出“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是其品题百三家集的标准,“‘吐华含实’,故不废齐梁;‘先质后文’,则尤重汉魏”[11](P575)。该著把张溥归入应社、复社一派,对其评价道:“这一派以通经学古为宗,重视人品学问的修养,重视事功,故政治色彩也最浓,而文学观点则不甚鲜明。”[11](P567)对张溥的骈文批评没有展开论述。从其评语“文学观点则不甚鲜明”来看,可以说该著对张溥的骈文批评基本是忽视的。
在古代文论史上,“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后来便形成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文以载道”是古文的重要命题,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直到新文化运动对其展开猛烈的抨击,这一命题便不大提及。而“文气”这个范畴,针对的对象主要还是古文。张溥把诗学领域的核心范畴“情”与古文领域的重要范畴“气”运用到骈文批评中,并把它们作为评价骈文的核心标准,这对历来只重视骈文的对偶、声律、藻饰、用典等形式而忽视其内容,是一种纠偏。虽然张溥最重视的是质实的汉魏诗文,但他对重文辞的六朝骈文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六朝的骈文进行具体的评析,还在自己的创作中骈散兼融——这从前引《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原叙》一段文字就可见一斑了,这其实与清代中期的“骈散合一”论是相通的。
更重要的是,张溥的“气余于彩”的观点,在骈文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虽然提出骈文需要有奇气,但他并未把“气”运用到具体的骈文批评中。在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上,第一个自觉地运用“气”来评价骈文作品的,当属张溥。骈文最初被称为“四六”,到宋代才有专门的骈文批评著作,以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为代表。《四六话》中也运用了“气”这个概念,如《四六话·序》云:“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12](P942)又说:“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凡此之类,皆以气胜与语胜也。”[12](P951)从文中的语境来看,王铚笔下的“气”主要是指彰显庙堂气象森严的“朝廷气象”,而不是“文气”。而谢伋的《四六谈麈》中几乎没有“气”的概念。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主要是谈论辞章技巧,属于“辞章之论”,还没有对于文气的自觉关注。这正如莫道才所说:“总的来看,从宋代《四六话》《四六谈麈》开始有正式的四六话后,骈文文论的核心话题是骈偶句法,基本停留在具体的骈句的点评和讨论上,或者偶尔涉及章法的话题,偶尔提到‘气’但并没有进入理论层面。”[13](P121)莫道才认为“气”进入理论层面,是从清初蒋士铨的《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开始的[14],这其实忽略了张溥这位骈文“气”论的先驱。
清代关于骈文的“气”论文献非常多。蒋士铨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总论中说,“气静机圆、词匀色称是作四六要诀,今之作者气不断则嚣,机不方则促,词非过重则过轻,色非过滞则过艳”“四六不可无才,然虑其为才累;四六不可无气,然虑其为气使;四六不可无雕琢,然虑其为雕琢所役;四六不可无藻丽,然虑其为藻丽所晦”。[15]蒋士铨把“气静机圆”作为四六的要诀,并提出“四六不可无气”,已经从理论上指出“气”对骈文的重要性了。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亦说:“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16](P597)李兆洛在《骈体文钞·自序》中也说:“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途,可以知文焉。”[17](P629)阮元在为孙梅《四六丛话》写的《后序》中褒扬欧、苏、王、宋:“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18](P3)类似的文献不胜枚举,这里只是列其要者而已。到了晚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提出了“潜气内转”说,这是对骈文“气”论的总结与升华。
综上所述,张溥的骈文批评对传统文论有所承继,其把情感置于第一位,又重视骈文的“生气”,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以往(主要是宋代)过于重视骈文形式技巧的弊端。张溥重视质实的汉魏诗文,但对六朝的骈文并不偏废,对骈文作品加以具体的评析,多有肯定,且把骈偶运用到自己的骈文批评及文学创作中,显示其骈散并存的开阔胸襟。而其把“气”这个概念自觉地运用到骈文批评中,更是开创了骈文的“气”论,成为清代骈文“气”论的先声,其意义不容低估。
注释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莫真宝.张溥文学思想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陆岩军.张溥研究[D].复旦大学,2008.陆岩军.论张溥的散文观[J].兰州学刊,2015,(5).陆岩军.论张溥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