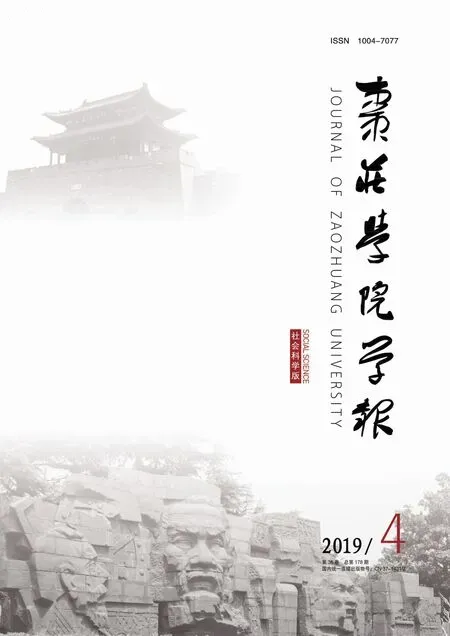情怀涵养与价值觉悟:中国当代休闲美学价值论初探
张耀天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价值是哲学的范畴,意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审美价值是在审美过程中,审美对象(客体)对审美主体(主体)所产生的意义。审美价值不同于其经济价值、人伦价值,后两者一般都有相对完整的价值评判标准,审美价值则不然。除了在普适价值评判上,审美强调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外,审美价值更强调个体性、多元化,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对美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对同一个审美客体进行美的关照,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价值,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中体认的“情怀”,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词汇,原因在于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更强调于个人精神世界的建构;也不否定“价值”的内涵,它在认同“价值”中主体、客体结构的同时,更强调情感意识、社会意识,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古代人文情怀的具体表征。
当代休闲美学话语中的“情怀”,在承认审美价值范畴的同时,强调在休闲体验中感受到个体命运、社会责任、宇宙大流的情感与念怀,以“情怀”作为个人主观精神世界领域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体的自由意志[1](P11)。
一、情怀的缘起:当代休闲美学的“各正性命”
中国当代休闲美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在休闲生活纳入到普罗大众生活场景的具体语境下,以传统美学的分析结构和相关范畴作为探索休闲审美的学科支持,将休闲生活提升到哲学思辨和美学审美并进行学理批判的新学科。既然当代休闲美学的学科底色是哲学,也就意味着休闲美学是关乎人的哲学、也是关乎价值的哲学,要明确当代休闲美学的“审美价值”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
再回到现实生活的场景中来,“休闲”已经是一个生活的常态,从经济学意义上的“休闲产业”到生活场景的“休闲行为”,再到中国古代以来文化上对“闲情雅致”的追求。“休闲”的意涵是多层次的、丰富的,既反映了当前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反映了“富而后教”“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当代休闲美学的价值发现问题,既是学科价值的本质之意,也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潘立勇较早地指出了中国当代休闲美学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缺陷问题,机遇在于社会现实场景提供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素材,休闲生活可以作为美学发展的新突破,同时也可以成为创新哲学体系和话语模式的新尝试[2](P16)。同时也应该从中国哲学的精神中汲取如“乐生”“玩物适情”“各得其分”等精神元素。当代休闲美学的审美价值,不同于抽象形式的审美价值,也不同于被泛化的“生活美学”,而是在认同大众审美权力的前提下,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下,多元、包容地承认不同审美的意义:既承认休闲生活具有达人之道的审美价值,是“顶天立地”的学问,也要承认休闲生活是普罗大众实现个体德性,实现“明心见性”的审美路径;既是通过休闲实现生命歇息、进而探寻生命真谛、寻求真善美的主要形式,也是在休闲活动中一刻轻松、享受明月清风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体系中的“价值”一词,尽管抽象地概括了休闲审美的意义,但却不能如“情怀”二字充分囊括休闲审美多重层次的内涵。
西方物质主义对精神世界的侵袭,往往导致两个极端的思考结果:或是虚无主义的游戏人间,或是消费主义的“娱乐至死”。法国自由主义土壤上诞生的虚无主义,是以构建一个强大的个体性精神世界,来对抗外在的物质世界,并试图用革命化的、彻底性的否定思维,以标榜“虚无”来抵抗外在世界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更容易诞生和物质世界“和解”的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势头在意识形态领域泛滥。究其根源在于,传统哲学所构建的价值体系的力量,已无力对抗新的历史时代。“要么死扛、要么投降”,成为西方哲学两个极端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而把“休闲”纳入到美学思考的领域,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休闲”填充了生活场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本体论的关怀和价值论的体贴;另一方面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层面,“休闲”开拓了传统美学的新领域,实现了传统美学从“身心之学”到“试听之学”从“书斋美学”到“人间美学”的双重转换。
周易《乾》卦之《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其中讲到了“各正性命”,既可以理解为不同生活层面的人,都拥有平等的审美权力,在自己的生活场景中借助于休闲生活实现审美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通过休闲审美价值,实现对生命本体的体贴、对生命源流的赞叹。休闲不仅是在寻求快乐,也是在快乐中“乐生”、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休闲美学的价值呈现,与传统美学的抽象性不同,它更强调借助于融入性的生活践履而体验超越性的审美,并以“情怀”的形式呈现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形上与生活的和谐。情怀,是中国哲学对美学范畴的重要贡献,它既肯定了西方语境下的审美价值,也赋予了审美价值更为丰富的内涵,把人的情感架构、理性思维、生命感受和使命追求都融入到休闲审美历程中。
“各正性命”,是在当下现实的生活场景中,以生活的休闲、生命的歇息进入到形上的空灵状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是中国哲学的本体关怀,也是感受宇宙生命奥秘的大美渊源,是休闲美学的形上学依据;“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意指文明润化、润物无声,有宋儒所谓“月印万川”之意,人人都能体会美的本体、美的存在,但所秉承的美之心得却截然不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若是感知到本体的空明,实现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性,既是儒家所谓的“颜回之乐”“曾子之乐”,也是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天地境界”,消弥了知识对宇宙生化体验的屏障,“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无我,是不需要努力底”[3](P698)。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则指感受了天地壮美的人,自觉地把对宇宙认知的成果、融化为生命的情怀,“各正性命”,把个体生命与美的生命融合,在当下的生活中寻找追求真、善、美的动力。也如黑格尔所讲审美的力量,人总要把对象化的美带入到个体生活中来,并按照审美价值认知自我、塑造自我,“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衬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4](P38)。 “各正性命”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美学的土壤上,承认每个人的情怀涵养和审美价值,消解现实世界中人被职业、阶层、环境、境遇等“隔离”的现状,最大程度地承认人的审美本能,即承认人在休闲生活中,明确“人成为人”的目的和意义,通过休闲审美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各正性命”是休闲审美价值的觉醒:物质主义泛滥压缩了精神世界的空间,异化、物化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现实世界不会因个人认知的改变而“境随心造”,只能选择与世界智慧地圆融、理性地和解,才能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经验世界的觉悟。休闲审美所确立的价值方向,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以“情怀”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人成为人”的心灵自觉,在现实世界也以休闲实践的方式,摸索出一条可以让人生喘息、生命休息的“和解之道”。
二、情怀的重塑:当代休闲美学的“寓志以闲”
情怀,是西方美学理论体系下“审美价值”的中国话语表述。情怀,不仅是从概念上要呈现和表征审美价值的定义,更要完成在当代休闲美学体系下对个体精神世界的“重构”:首先,它意味着在当下生命紧张的状态下,人通过休闲实践而“收拾”个体精神世界的方案。通过个人修养、认知能力、觉悟水平等,以“情怀”的形式,整体地表征审美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情怀”本身富含道德情感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建立与世界关联的过程中,以同情悲悯、推己及人、仁人爱物的长者之风,规范个人德性与行为。并把这种情怀,泛化为休闲审美历程中的个体审美意志。第三,“情怀”在当下物质主义泛滥的背景,逐渐演化为一种生命个体不断反思、和解与外界世界沟通的审美力量,彰显出审美价值的能动能力。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国哲学文化,强调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生命关联”,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其最高使命是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境界中,充分体现天地宇宙的生命精神”[5](P38)。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寄情”“移情”的文化传统,借助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抒发情感、表达心智。周朝就强调“乐教”,以音乐之理而行教化之道,文人雅致也多以琴韵派遣时光。“文士以琴消解闲暇,在琴声雅韵中自娱、自乐、自适、自得。孔子、颜回、庄子、屈原、宋玉皆以琴为修身养性之物,借以抒发高洁之心志。孔子无论清居于陋室,抑或受困于陈蔡,然操琴弦歌之声不绝。左琴右书是古代文人寄托情怀和表达处世态度的重要载体”[6](P11)。闲情逸致,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智慧,既在休闲文化中寻求进步的能量,也能借助休闲、实现生命的歇息,更能在文化氛围中寻觅内心的宁静、感受“生生”的力量。
“寓志以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体现,也是当下人实现与物质世界“和解”、保持内心安静、寻求人生精进的能量源泉。当下人生命体验的完整性,被现实的职业、阶层、环境、背景等所“分割”“异化”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人的生活被呈现为碎片化、解题化的状态,加之强大物质力量的压迫,人的主观感受已经很难真实地、内在地把握生命本质。“由于世界的机械化必然使其主体、即人本身一同机械化”[7](P16)。人在现实的职业场景中,逐渐被对象化、客体化。物化的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物化,既否定了人的生命本质,也迫使人不得不面对一个被自己的文明所塑造一个庞大“怪胎”。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一种紧张、冲突的对峙状态,人与世界的对峙、与他人的对峙,以及人与自我的对峙。休闲审美所带来的“情怀”感受,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范畴体系,这个范畴本身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它既有几千年来承受中国文化浸淫、且已“实证”地展示文化魅力的基础,也有在当下发挥新生价值、重塑个人精神世界的“应然”之理。情怀在当下休闲审美体系中,被赋予了更为“沉重”的历史使命。
首先,通过情怀的审美价值呈现,表达人的生命意义感受。休闲过程是人的本体呈现的历程,而休闲审美价值所凝聚的“情怀”则呈现出完整的人格、圆满的心理。进入到休闲状态的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本质并以“乐生”的态度,积极融入世界、享受劳动成果,借助于“情怀”消融了“异化”所带来的人的“碎片化”,并丰富了马尔库塞笔下的“单面人”的生命状态,如潘立勇所言“休闲是人成为人的过程”。情怀既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生命维度的展示,也是审美价值的体系、休闲愉悦的呈现。
其次,通过情怀的审美价值呈现,内化人的生命价值诉求。世界领域内较早系统提出休闲学和休闲美学的西方学者约翰·凯利认为,如果说劳动是一个人职业生命的主题,那么休闲则是人的一生之中一个持久且重要的舞台[8](P90)。借助于休闲活动和休闲体验,在当下物质主义泛滥的语境下,促成个体生命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融合、和谐个体道德与“生生之德”的和谐,寻求“保利太和”的情感抒发,是当代休闲美学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情怀”范畴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通过情怀的审美价值呈现,和谐人的“生生之易”大流。休闲审美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在于,将休闲行为视为生命的本能行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休闲实践的过程中把情怀作为生命感受和审美价值,去呈现主体和客体的生命圆融之道。当代休闲美学面临着传统美学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美学以人的自然生命审美为研究对象,传统社会状态的人,并没有面临今天如此巨大的“异化”力量。物质力量被技术力量持续催化、发酵,在实现生活便捷化的同时,也阻断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人的主观感受,越来越多地被物质主义“裹挟”,并逐渐丧失了回复自然生命状态的权力。中国传统文化讲“生生”,不仅强调个体的生命、也重视“同生”“共生”的原则,并集中地展示为底色为“仁”的精神世界。“仁”道推己及人,进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沟通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审美价值体系:从周易“生生之德”出发,伦理道德上体现“仁”、社会法制体现为“仁”的类推结构(“推己及人”)、生命情怀上体现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天地之德”呈现审美价值的“上传下达”。脱胎于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智慧的当代休闲美学,更是坚守了生命哲学审美的原则,克服“异化”、拒斥“物化”,以“寓志以闲”来恢复人的天性,探索自由、超越的心灵之路。
三、情怀的意涵:当代休闲美学的“闲情之志”
闲情之觅,无碍于志。以孔子为例,孔子的文化形象,“不仅精通人道,而且洞彻天道,是一个实现了融天、地、人为一体,具有天地情怀与境界的圣人”[9](P19)。儒家为底蕴的中国古代精神世界,将儒家的使命意识、道家的隐逸追求和佛家的超越诉求等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富含生命感的中国审美价值体验。在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休闲既不是放浪形骸,也不是玩物丧志,而是借助于休闲实践进入到休闲审美的境地,建立一个生命个体与宇宙生命、情感个体和历史责任交融的“情怀”表征。情怀既是审美成果,也是审美价值,集中反映情感诉求的同时,也实现人在休闲实践中胸襟抒怀、智慧成熟、境界提升、心性空灵的审美感受。
在当前的休闲生活、旅游生活,并不是单纯的在自然风景或人文景观中的行走,而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熏陶:自然界或人文景观所内涵的精神元素,借助于休闲实践而转化为影响人情绪、心理的精神力量,再通过人的其它社会实践而形成积极的社会能量。在休闲实践中,审美价值不同于“商品价值”或其它价值,而是内化为涵养人、成就人的力量,并集中地以“情怀”的形式呈现。“情怀”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互动,休闲实践的形成情怀的基础,审美客体所蕴含的精神要素、内化为审美主体的感受,审美主体为审美客体“凭添”上个体精神的要素,内心所关照的世界展示为自己所“观听”的世界。
休闲的核心是“闲”,休闲的审美价值呈现为“情怀”,是在休闲实践中所感受的“深度生存”价值。中国当代休闲美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形成了以“情怀”为审美价值的范畴,从根本上建立了区别于西方纯粹语言逻辑意义上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由此而建设的中国当代休闲美学,完全不同于西方美学所导向的、侧重于形式美学的“观听之学”,建立了审美主体主导、身心一体的“身心之学”。休闲美学的审美价值集中呈现为“情怀”范畴,既感受到本体的生命关怀,也深度表达了个体的精神诉求。当代休闲美学的审美价值,集中地呈现为“情怀”,并且“打通”了现实生活到审美生活的三个路径:
一是借助审美价值的“情怀”呈现,实现从“现实生活”到“超越生活”的转换。当代休闲美学对休闲生活的态度,是实现审美的“双向化”,即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休闲审美赋予了“现实生活”以审美的意涵,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逍遥、坐忘、心斋等范畴,把西方哲学的自由、解放、超越等范畴,嵌入到当代休闲美学的体系中,给日常的休闲生活充盈了哲学的意味和智慧的意涵。休闲是个体生命最本质、最真切的表达,在休闲放松的状态下,人才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人生问题、探索生命真谛。情怀则集中地体现了休闲审美的价值,把个体化的审美成果,展示为超越现实的永恒价值,既体现了传统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也表达了休闲状态下人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转换。
二是借助于审美价值的“情怀”呈现,实现从“生命羁绊”到“生命自由”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认为,物质主义对人最大的伤害在于,它所创造的“文化消费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文化的商品化意味着,它必须满足生产者的利益最大化,这让生产者把文化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现代工业成了艺术作品的现实基础,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工具理性侵入了超功利的艺术领域”[10](P413)。按照阿多诺的说法,即使人在当下文化生活中所接受的文化产品,也是商品化的结果,简单形式的文化产品消费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审美。休闲审美的体验,是一种生命自由、“心适物闲”的状态:有了“情怀”审美价值的导引,既明确了审美的“功利主义”倾向,也把审美历程实现了超功利性的去向。从这个角度出发,休闲审美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双面体,一方面它只有拒绝功利主义,才能实现情怀审美价值,同时它也是实现了最大的功利主义,在休闲审美的过程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最大自由,摆脱了现实生命羁绊,实现了审美层面的精神自由。
三是借助于审美价值的“情怀”呈现,实现了从“超验场景”到“生活场景”的转换。中国传统美学所强调的审美价值,具有一定的超验性,强调“天人合一”的空灵、虚实结合的澄明,借助于对现实的超越、对形上本体的诉求,进而构建重精神、轻物质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种审美价值对当代休闲美学“情怀”构建的益处在于,它赋予了当下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意义,并把传统美学资源中的本体“觉解”演化成今天抵抗物质主义侵袭的“精神武器”。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审美价值中的“超验场景”,使“身心之学”的美学更加形上、更加抽象。当代休闲美学的“情怀”价值,是把休闲生活中人的主体性通过审美权力和审美价值综合实现,休闲实践成为人与世界沟通的“介质”,把“生活场景”中的休闲实践提升到“超验场景”的心理感受,也把“超验场景”的抽象审美,落实到现实的休闲实践中来。
“情怀”和“境界”一样,都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富有深厚的话语底蕴和文化内涵,既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贡献,也是传统美学对当代休闲美学的启发。“情怀”集中地体现了休闲审美实践中的审美价值,把抽象化的审美价值以理性情感、感受怀思的形式进行表达,把生命体验借助于休闲活动“放置”到生活场景中来,既赋予了休闲活动以哲学的意义,也使美学中的审美价值问题更具有生活的想象力,在关照生命本体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人生的真实状态。从历史时代的语境出发,“情怀”范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对整个美学研究范式西化趋势的“反哺”,从中国话语体系中提取了“情怀”、化解了西方美学审美结构对中国美学的冲击,回应了构建中国哲学话语的时代主题。从当代休闲美学的学科出发,“情怀”消解了传统审美价值“心物二元”的对立,把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碰撞所产生的精神性成果统一起来,进而达到了“心适物闲”的状态,既实现了哲学之美、也实现了生活之美,体会到“生生之流”的壮美,融入到“乐生”的休闲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