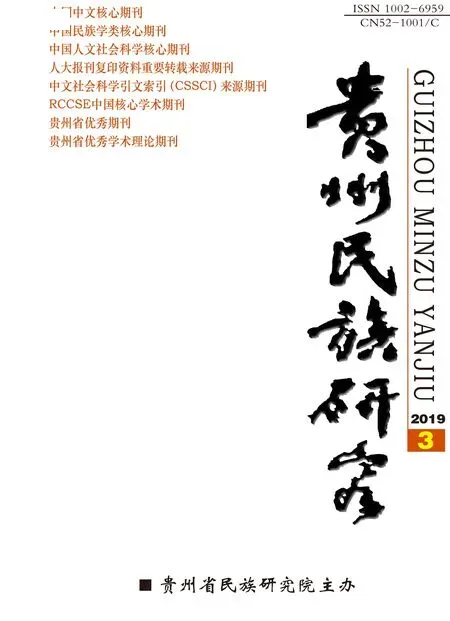论西湖小说“于祠祈梦”现象的民族文化渊源与交融
代智敏 胡海义
(1.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西湖小说”是绝无仅有的以地域命名的小说。明代崇祯年间,湖海士以“西湖说”来指代杭州人周清原的小说《西湖二集》。[1]清顺治年间,著名史学家谈迁正式提出完整的“西湖小说”概念。[2]从宋代至清末,出现了如西湖义士、西湖野臣、西湖渔隐主人等数十位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家。还有大量小说以西湖命名的小说集,如《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新西湖佳话》等,蔚为大观,生生不息。但在谈迁之后,西湖小说罕被提及。近些年来,学界开始关注西湖小说。[3]本文依据古代小说热衷书写西湖的现象,将西湖小说界定为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以西湖为重要的故事场景的小说。
一、独树一帜:西湖小说及其“于祠祈梦”现象
西湖小说以浓郁的地域色彩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其中的“于祠祈梦”现象尤其令人瞩目。于祠就是位于西湖畔三台山麓的于谦祠。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杭州府钱塘县人(今属杭州市),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临危受命,整饬兵备,勇破瓦剌,保卫北京。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冤杀,葬于杭州西湖西岸的三台山,被后人誉为“西湖三杰”之一。作为杭州的乡贤,不仅于谦本人的故事被西湖小说津津乐道,而且还有大量讲述四方百姓去于谦祠庙祈梦求福,尤其是科举考生求取功名的故事情节。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于祠祈梦”的故事数量众多。如《西湖佳话·三台梦迹》以“梦”命名,正文讲述5 个梦境,所附《于祠祈梦显应事迹》收录32则祈梦故事,描述42个梦境,全篇共写了47个梦境。《于少保萃忠传》也讲述了大量的祈梦故事,尤其是第六十九、七十回集中收录的三十二则于祠祈梦灵验故事。另如《无声戏》第九回《变女为儿菩萨巧》与《湖堧杂记》也讲述一些有关“于祠祈梦”的故事。
其二,“于祠祈梦”或于谦祈梦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枢纽与关键,构成全篇的主旨与灵魂。如《无声戏》第九回《变女为儿菩萨巧》的头回就紧扣举子祈梦、于谦托梦与道士解梦的“三部曲”来展开故事情节。《西湖佳话·三台梦迹》正文先后写了五个梦境,其中有于谦因其父得吉梦而生,长嫂因关公托梦问前程而笑骂口头禅“天杀”,预示了于谦的悲惨结局,可谓因梦生,因梦死。“故于公一生信梦,自成神后,亦以梦兆示人”[4],照应题目,点明主旨。《于少保萃忠传》与《于少保萃忠全传》中,于谦托梦给儿子,要求借目去找皇帝申诉冤情,并告知自己将被天帝任命为都城隍。此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情节。
总之,在西湖小说中,“于祠祈梦”是一种值得瞩目与深入探讨的现象。
二、氐羌传说:“于祠祈梦”风俗的民族文化渊源
杭州乃人文渊薮,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那么“于祠祈梦”风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笔者发现首次记载“于祠祈梦”风俗的史志,是成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万历钱塘县志》,其云:“四方人祈梦者,以七宝山、三台山为九鲤湖。因试事祈者尤多。盖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谦都城隍也。”[5]此前成于万历七年(1579年)的《万历杭州府志》,还有嘉靖年间的杭州人田汝成所编纂的《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都未提及“于祠祈梦”。而根据乾隆十年(1745年)所立《重修于忠肃公祠碑》记载,于谦是在清代被朝廷封为都城隍[6]。那么《万历钱塘县志》的说法出自何处?笔者考证发现,最早宣称于谦是都城隍的是一部西湖小说《于少保萃忠传》,第五十一回讲述被杀害的于谦托梦给远谪途中的儿子于冕说:“当日诉于天,蒙上帝怜吾忠义勤劳,着吾为京都城隍。”[7]而且,其第六十九、七十回又集中收录了三十二则“于祠祈梦”灵验故事,予以佐证。这是“于祠祈梦”的发端。《于少保萃忠传》虚构于谦被封为都城隍而善于托梦示人,进而形成三台山“于祠祈梦”的风俗,其实是模仿同在西湖畔盛行的吴山梓潼神庙祈梦的风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真德秀会试于行都,祈梦于吴山梓潼庙……是夜得吉梦,其年果及第。”[8]梓潼庙是祭祀梓潼神的庙祠,梓潼神又被称为文昌梓潼帝君,是梓潼神和文昌神的合称,有时又被简称梓潼帝君或文昌帝君。此神并非杭州本土神,而是来自蜀地的流寓神。著名民族史学家与考古学王家祐先生认为:“供奉文昌之根源,似有一极古雷神地方的供奉,起于四川北部蛮族之间。”[9]确切地说,文昌梓潼神应该源于四川的氐羌文化。
(一)梓潼的氐羌文化渊源。梓潼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县(今属绵阳市),这里曾是氐族与羌族的聚居区。氐与羌都属于西戎,错居杂处,所以被视为同源,常被连用或并称,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宋代丁度等编《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梓潼是羌氐故地,据《汉书·地理志》载,益州广汉郡,领县十三,梓潼居首,为郡治所在,所辖甸氐、刚氐、阴平三道,都是氐人的集中居住区。东汉末年,氐人杨腾率部迁至仇池(今属甘肃省西和县),先后以仇池、葭芦、武兴、阴平为中心,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与阴平国。李祖桓《仇池国志》载:“梁天监五年正月壬申,魏军攻克武兴,俘杨绍先,改武兴为益州……东益州领武兴、仇池、盘头、广长、广业、梓潼、洛从郡。”梓潼被划入氐人区域的管理。白翠琴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中经过考证认为,仇池国的疆域曾包括四川梓潼等地[10]。可见,梓潼具有非常深厚的氐羌文化渊源。
(二)梓潼神的现实原型的氐羌关系。梓潼神的主要现实原型是张亚子,“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嶲人,因报母之仇,徙居是山,屡著灵异”[11]。《清河内传》载梓潼神张亚子“后西晋末,降生于越之西、嶲之南两郡之间,是时丁未年”[12]。现存梓潼神碑文《紫府飞霞洞记》亦称:“吾旧生越嶲间……越嶲遂沦。呜呼!吾将安归?”[13]越嶲属于西南夷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越嶲郡,地处川西,是越嶲羌(又称牦牛羌)的主要居住地。可见张亚子是氐羌后裔。他对羌人政权立有大功,据《十六国春秋·后秦录》载,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羌人姚苌在梓潼七曲山,“见一神人谓之曰:‘君早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苌请其姓氏,曰:‘张亚子也。’言讫不见。”姚苌建立后秦后在此立庙纪念。
(三)“善板祠”的氐羌特色。《华阳国志》卷二载:“梓潼县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14]“恶子”又作“亚子”,即张亚子。祭祀张亚子的梓潼庙为什么被称为善板祠?王家祐考证认为:“‘善板’二字可能为‘青氐’之误。或‘羌氐、羌神之讹’;或者“雷氐”之讹。”[15]黄枝生则认为板屋是氐羌人的居所,善板祠由此而来[16]。《毛传》曰:“西戎板屋。”《南齐书·氐传》载:“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室土墙。”《紫府飞霞洞记》称张亚子的居室,“其俗多营窟板屋而息”。氐羌人所居多靠近山林茂密地区,木材非常丰富,板屋是十分普遍的。
(四)张亚子成神的氐羌宗教文化因素。张亚子成神尤其是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梓潼神,道教起了很大作用。前文所引《清河内传》《紫府飞霞洞记》,还有《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等诸多收入正统《道藏》及《藏外道书》的典籍,对张亚子成为科举神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些道教典籍大多是刘安胜等属于天师道的蜀中道士所作。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与氐羌文化非常密切。著名历史学家向达认为天师道的“三官”(天、地、水)信仰来自氐羌,前秦苻坚(氐)、后秦姚苌(羌)、南中南诏(乌蛮、白蛮属氐羌)皆有此种影响。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道陵所修之“道”,不外是“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17]。蒙文通也认为:“天师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汉末西南民族向北迁徙,賨人、氐人北入汉中及汉水上游,五斗米道亦于此时入汉中。”[18]
综上所述,梓潼神的起源、发展与传播都离不开氐羌文化的深刻影响。没有氐羌文化的滋养,就不可能诞生梓潼神,“于祠祈梦”也就是无源之流,无从谈起。
三、梓潼东传: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于祠祈梦”现象的兴起
梓潼神大庙所在的七曲山位于北宋四川举子赴汴京省试的古金马道上,他们们因此顺路拜神助考,但这一风俗限于蜀地少数民族地区。到了南宋,梓潼神的影响逐渐从氐羌文化圈扩大到汉文化占主导的地区,尤其是东传到杭州,影响倍增,成了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最终孕育出“于祠祈梦”的风俗。梓潼神信仰东传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一是江浙士子赴蜀耳闻目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李知几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几。是举过省。”[19]李知几是四川资州人,浙江人陆游有过入蜀经历,可见江浙士人对四川举子祈梦梓潼神而灵验成真已经颇感兴趣。
二是蜀中举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宋南渡后,有祠在吴山之巅,盖蜀士赴举者所创也”[20]。“靖康之变”后,政治中心与科举中心南移杭州,梓潼神祠庙随着蜀地举子而来,扎根于杭州吴山,据南宋吴自牧记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21]各地举子纷纷前往杭州吴山梓潼神庙祭拜、祈梦,蔚然成风。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景定五年(1264年)三月二十九日,宋理宗下旨:“朕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生为孝子,殁为明神。信矣!神文圣武安福忠仁王夙着孝行,炳灵西蜀,御患救灾,七曲名山闻天下,而士之发策决科者皆归焉。有孝有德,徽号允昭。邦人有请,宜复其旧,衹承修命,大庇吾人。可依旧封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22]梓潼神被朝廷封王,并明确了“士之发策决科者皆归焉”的科举神职责。该神后来又得到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屡次敕封,最终奠定了国家科举神的地位。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在杭州祈梦梓潼神的科举风俗中又衍生出“于祠祈梦”现象,这是氐汉文化进一步交融的产物。杭州乃科举胜地,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自(明)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里巷诗书,户不绝声”[23]。据统计,在明清时期,杭州诞生了1039位进士,居于全国各大州府城市首位[24]。然而,明清科举以八股文作为最重要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又称制义、时文、经义、制艺等,极端讲究形式主义,正如章学诚所说:“时文体卑而法密。”[25]考生必须恪守十分严密繁琐的功令格式。他们要想脱颖而出,需要从小全身心地投入八股文训练。这无疑是一种极其痛苦不堪的身心煎熬,给举子们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心理阴影,所谓“磨难天下才人,无如八股一道”[26]。
杭州应举风气浓厚,高手如云,竞争极为激烈。杭州人袁枚说:“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27]抱有极端功利心的举子在祈祷神灵时,希望出现一位精通八股文的科举神来帮助解脱困境。但身为蜀地氐人的梓潼神张亚子本无科举功名,更与八股文无缘。于是,源自氐羌文化的梓潼神信仰结合新的八股取士因素,精通八股文的杭州本土进士于谦登上了科举神坛。
于谦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及第,其八股文成就颇高,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俞长城是清代非常著名的八股文选家,他在《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中将于谦的八股文冠于明文之首,《于廷益稿》卷首题识云:“至其文,英风劲节,跃露楮间,杀机已见,亦不必怨群小也。夫文山有忠肃之志而功不克成,忠肃有文山之功而志不见谅,皆千古遗恨;然而,立德立言,允文允武,旷世合辙,余故以文山殿宋,以忠肃冠明,比而录之,谅九原亦为称快尔。”[28]俞长城将文天祥视为宋文的终结,将于谦奉为明代八股文的开创者,认为于谦“时文独成家”,“以忠肃冠明”。清代著名文学家王步青也赞扬于谦的八股文体大思精,光焰万丈,以此制义开宗,不在班马欧韩之下,即他们都认为于谦的八股文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于谦的八股文成就高超,入选明清时期多种八股文选本,是考生模仿的圭臬。他们希望这位爱国英雄也能在八股文写作上给予神助。因此,“于祠祈梦”应运而生,逐渐兴起。
总之,西湖小说中的“于祠祈梦”现象源于四川氐羌民族文化中的梓潼神信仰,是氐羌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
——梓潼县文学创作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