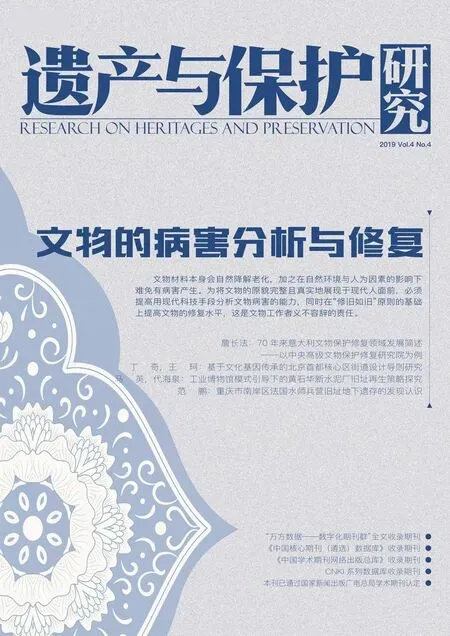重庆市南岸区法国水师兵营旧址地下遗存的发现认识
范 鹏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 400013)
2013年6月,南岸区文物管理所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重庆市南岸区法国水师兵营旧址修缮方案》[1]。在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后,于2016年启动了对地面文物的修缮工作。2017年3月16日,在修缮施工对中庭区(指主楼、副楼、耳房环伺围合成的平台区)的地面清理工作中,发现有砖筑的地下遗迹。重庆市文物局委派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进行了现场实地踏查,确认该地下遗存位于法国水师兵营旧址保护范围之内,在报清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开展了清理工作。
1 法国水师兵营旧址概况
1.1 基本情况
法国水师兵营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谦泰路142号。地处长江东岸的滨江路与谦泰路交汇处,与朝天门、江北嘴遥相对应,现存分布范围西至南滨路,北到谦泰路,东、南为“长嘉汇”住宅小区。现占地面积653 m2,总建筑面积2 339 m2。地理坐标为东经106°34'49.5"、北纬29°34'56.0"。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历史沿革
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把重庆列为通商口岸[2]。1894年,法国官员到达重庆,考察设立领馆事项;1896年2月,清政府与法国政府议定,允许法国在渝设立领事馆,1896年3月26日,法国正式成立驻重庆总领事馆。
1902年,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波特尔的命令,法国海军军官虎尔斯特率领法国测量队抵达重庆,并开始修建水师兵营。“法国水师兵营”原为大清北洋水师营务处,修建经费10万法郎由印度支那总督杜梅尔捐款,兵营重建由“奥利”号舰长休斯特.南希负责,于1903年竣工。法国水师兵营又称“奥当军营”,为法国海军军官士兵提供了居住的营房、修理军舰机械的车间、储备生活物资的仓库和后勤物资的补给站。当时,法国扮演着长江航道上的水上警察的角色,法国水师兵营也担负着法国在长江中上游实际控制站的作用。
1940年法国战败于德国,国民政府承认了法国新成立的傀儡政府维希政府。1941年,因原维希政府驻渝领事馆遭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同意其迁至奥当军营办公。1943年,国民政府承认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自由法国),并断绝与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奥当军营所有权转归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自由法国)驻重庆大使馆,但只保留一个无线电联络部、两名操作人员,法国大使馆主体迁回其原所在地渝中区领事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房屋管理部门接收并管理了奥当军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重庆粮油机械厂、面粉厂和重庆粮油加工厂使用。2002年,南岸区人民政府出面将奥当军营最后一个使用单位重庆粮油加工厂迁出。2003年4月,南岸区房产管理局、南岸区文物管理所和重庆裕佳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对饱受岁月摧残的法国水师兵营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在修缮后将其改为商业用途。
1.3 地面建筑及环境的现状与变迁
1.3.1 地面建筑现状
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现存建筑为一整组带有回廊和内廷的围合式庭院建筑[3]。现存地表由4部分建筑构成,包括主楼、副楼、耳房和牌楼(图1)。
主楼为2层回廊式,采用砖石木混建结构,木构梁架与内外墙共同承重,其地上2层、半地下1层,外加顶部坡屋顶阁楼,层高较高,建筑高度约为12.4 m,建筑面积约为662 m2,主楼平面约为方形,附有3面围合的外廊。
副楼为3层折廊式,采用砖石木混建结构,其地上2层、半地下1层,外加顶部坡屋顶阁楼,层高较高,建筑高度约为12.0 m,建筑面积约为753 m2,沿庭院内部设有一圈外走廊,平面呈L形。
耳房上部2层采用砖混结构,顶层坡屋顶采用砖木结构,建筑高度约为10.4 m,建筑面积约为250 m2,耳房平面呈长方形,沿外立面辟有一平台,并可以直接通过庭院进入耳房一层。
牌楼为两柱一间三重檐,采用砖石混合结构,面宽6.9 m,高为9.4 m。
1.3.2 历次改建与变迁
据已有资料,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经历了数次改建、加减、修缮等活动,周边文物环境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903—1949年,原主体建筑依照山势建立,选建在高阔的台地之处,可俯视长江,与长江江面形成高差十几米,对江面的情况一览无遗。这一时期,建筑区除主楼、副楼、耳房与牌楼外,至少应包含主楼北部的平台、主楼西侧的圆形平台、梯步自牌楼向外延伸至圆形平台、从圆形平台的中部以阶梯下至江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00年,粮油机械加工厂使用期间,谦泰路向南延伸,在水师兵营外修建了沿江公路,拆除了主楼西侧的圆形平台,占据了主楼北侧的平台区域。
2002年,南滨路由南向北延伸修建。出于防洪需要,南滨路抬高了地基,地表与牌楼大门几乎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在同年的修缮工作中,为耳房加建一层。为了加强主楼、副楼和耳房的联系,又在主楼与副楼的3层加建了连廊,副楼与耳房在2层与3层分别加建了连廊。
2009年起,周边出现大规模的拆迁活动,东部、南部逐步建设为现代住宅小区。
2 考古工作概况及主要发现
为确保暴露的地下遗存得到有效保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了由考古发掘、古建筑保护、现场文保、摄影、航拍以及测量测绘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工作队,于2017年3月20日启动了抢救性发掘,至4月10日基本完成田野工作。共布设10 m×10 m探方1个、5 m×5 m探方1个、2.5 m×10 m探沟1个,合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150 m2,先后发现并清理了地窖1座(J1)、水池4座(C1~C4)、房址2座(F1、F2)、灰坑1座(H1),这一批遗存的时代从清末延续至民国时期,填补了地下遗存考古发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的文化内涵(图2)。
2.1 地窖(J1)
系先开挖长方形土圹,在土圹内构筑本体。土圹长8.27 m、宽3.05 m,方向约170°。平面呈长方形,长6.9 m、宽2.4 m、高3.35 m。拱顶,以灰砖双重横向起券,券顶内、外面皆施一层白灰。四壁以条石错缝平砌,厚0.24 m。条石不甚规整、大小不一,之间以白灰砂浆黏结。四壁下部四周覆一层水泥,底部水平,表面覆灰白色砂浆(图3)。前部顶上开方形出口,四周以条石包边,因施工破坏已残,残长0.85 m、宽0.75 m。出口下见有嵌于前壁石墙上的铁质回形爬梯,现可见有梯步6个,从分布上看,中间有2步缺失。J1窖室内的前部、中部各见有砖砌方柱1个,二者间距3.5 m。顶部与券顶相接,方柱下以方石作为基础。左后部券顶上存在一小型圆孔,圆孔正下方的窖室底部为一圆坑。前部左侧壁可见有方孔与C2相连接,方孔内为竖向的铁栅栏。
以上遗存虽都在J1内,但并非完全是共时关系,根据清理情况,可将J1内的遗迹现象分属为早到晚3个阶段:①J1土圹及建筑本体,以及前壁爬梯、顶部方形入口;②四壁下部敷设的水泥,左壁前部与C2相通的方孔,券顶后部的圆孔,圆孔正下方的窖室底部的圆坑;③窖室的两座砖柱。
2.2 水池(C1~C4)
水池共有4座。C3和C4残损严重,在此不做介绍。
C1:土圹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方形,以灰砖砌筑“37”墙,砖缝以灰色砂浆黏结。墙体残,上部已不存,残存4~5层砖。水池内部四角及南、北两墙体中部砌筑有砖柱共6座。底部水平,表面施灰色水泥。宽2 m、残高0.25 m。
C2:系先开挖长方形土圹,在土圹内构筑本体。土圹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J1,被F1叠压。土圹为长方形,本体平面呈“凸”字形(图4),以灰砖梅花丁砌筑“24”墙,砖缝以砂浆黏结,墙体残,上部已不存,方向270°,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中间以拱门相通。拱门底部高于水池底部,宽0.64 m、高0.84 m。前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 m、宽0.64 m、深1.7 m,距底部两侧壁上可见有砖砌突出,砖砌突出下部可见有较多的鹅卵石、细沙等(图5)。前部前端底部正中可见有竖向铁条构筑的铁栅栏,与J1内部相通,宽0.48 m、高0.28 m。后部平面呈方形,底部水平,边长2 m、深1.7 m。
2.3 房址(F1、F2)
房址共2座。F2残损严重,在此不做介绍。
F1,现存7座磉墩,其中6座形成面阔2间,进深1间的柱网结构,间宽3.4~4.5 m、进深5.5 m。磉墩平面基本为方形,边长0.75~0.9 m,厚约0.4 m。由长方形条石以灰浆黏结,分上、下2层。
3 遗存的时代与功能
3.1 F1的时代
在前述的3组遗存中,均缺少明确的年代证据。因此,可根据法国水师兵营的一批老照片初步推断F1的时代。据搜集的关于法国水师兵营的老照片(图6),可以看到中庭内已有至少1座房屋,为传统中式普通建筑,“人”字顶,与水师兵营相比修建得相对简陋,就其朝向来看,很有可能即为本次所发掘的F1。照片的拍摄时代不详,从江面行使的蒸汽轮船来看,其时代可能在民国期间。从结构上看,该建筑较高,顶部已与副楼高度相近,至少应是个2层楼的建筑,特别是其地处法国水师兵营中庭核心位置,普通民众即无财力也无能力修筑。因此,这一建筑最大可能为法国人在此增筑。
笔者注意到,在关于位于渝中区法国领事馆的沿革记述中曾经提及:1940年,为躲避日机轰炸,法国领事馆曾迁至水师兵营办公。领事馆虽为外交机构,但在战争期间也有保护与收容本国侨民的职责。因此,F1应是这一时期为满足大量人口居住而临时增建的建筑,其时代应在1940年后不久。
3.2 J1与C2的关系与功能推测
C2是一座“凸”字形的遗迹,有几点现象值得注意:①C2与J1以铁质栅栏相通,这种设计应是用于流通液体;②C2分为前、后两部分,中间以拱门相通;③C2前部底部有大量的鹅卵石和细沙等。
根据以上3点可推测:C2的后、前部很有可能分别为沉淀(消毒)池、过滤池,过滤后的水通过铁质栅栏流入J1内,J1则为经过净化后的储水池。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J1右侧的顶部发现了圆形孔洞1处,孔洞正下方的窖室底部存在一个直径约50 cm的圆坑,这些应当均与当时取水密切相关。因此,C2应是一处过滤、净化水源的设施。
J1的时代早于C2。从观察来看,J2作为C2的蓄水池,应是在修建C2时进行了功能上的改造。特别是J1前段顶部留有开口并以条石包边,开口下在前壁上设置直达底部的爬梯,这种设计更多是为了满足一种经常性的进出。因此,笔者认为J1在最初更加可能是一座地下储藏室。值得注意的是,J1前壁爬梯损毁了2步,而未加修补,原损毁处与J1窖室内四壁下部一样均敷上了一层水泥,这说明爬梯与水泥是一种早晚关系。水泥的应在J1已经使用较长时间后敷设,鉴于C2表面均敷设水泥,这个时间应当就是在修建C2时,J1已在此时改建为与C2相通的蓄水池。
4 结束语
于文物保护、服务于文化建设的大局上的独特作用。通过发掘工作获取了一批重要的地下遗存,特别是以实物为载体,印证了法国水师兵营的修建以及法国领事馆搬迁等历史事件,进一步丰富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有助于加强和深化目前关于该遗址的学术研究。此外,法国水师兵营旧址即将对外开放展示利用,通过考古工作,挖掘出一批具有良好展示价值的地下遗存,该遗址将成为重庆主城为数不多的既具备地面遗存,又具备地下遗存展示素材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法国水师兵营旧址是重庆地区较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其整体欧洲中世纪城堡建筑之风格具有显著而强烈的时代特征,折射出了重庆近代开埠时期的历史风貌。本次考古发现该遗址的地下遗存与现存地面文物建筑共同构建了具有时间感、空间感的展示平台,可采纳如覆罩露明的展出方式,与重庆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相结合,进行保护、展示与利用,具有独特的展示价值。此外,本次工作以事实证明了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必要性,建议在地面文物保护规划、修缮设计等工作中,应主动吸纳考古的参与,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致谢:发掘工作和本文的撰写均得到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邹后曦研究馆员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