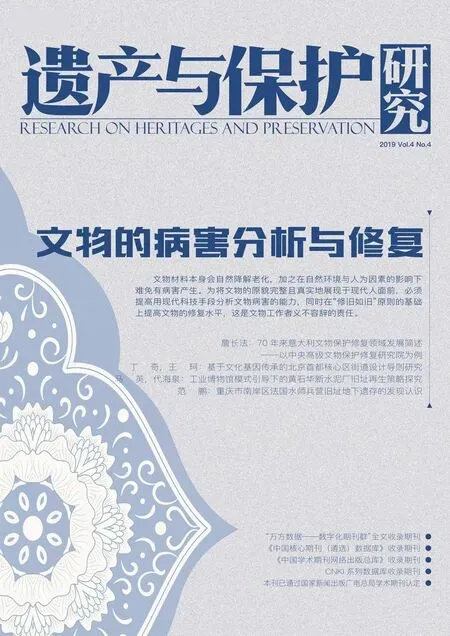“长安(敦煌)-泉州文化线路”初探
——以福建石狮琼林、南安杏埔“燉煌衍派”洪氏家族为例
陈宇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27)
“文化线路”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圣地亚哥线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8年10月4日,在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正式通过《关于文化路线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后,“文化线路”可谓正式成为了一项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不同人群在一定空间(线性或非线性)上产生的具有目的性的流动交往行为,继而在产生了跨文化碰撞与整合作用的同时,于有形和无形遗产基础上,以文化传播或文化涵化的显形或者隐形的路径为线索,形成的具有一定类型特征的文化意象的遗产保护、城乡规划的视角”[1]。
“长安(敦煌)-泉州文化线路”是笔者根据“文化线路”之概念,在研究文化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迁移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众所周知,汉唐时期的文化重心以长安"为中心,随后开始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由于种种原因,长安的辉煌早已不在,只能通过今天西安的些许碎片去探寻昔日盛况;而敦煌则因丝绸之路的衰落和20世纪的考古发现,在今天仍然向世人展示着盛唐之辉煌。故在“长安”后补充以“敦煌”,正是基于“通过敦煌看长安”的想法。
“燉煌衍派”是笔者在跟随导师郑长铃②郑长铃,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闽江学者,硕、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在闽南田野考察时的意外“发现”,因其恰巧又是“燉煌”移民,遂以其为例,初探“长安(敦煌)-泉州文化线路”。
1 初探“燉煌衍派”
衍派,是记录氏族姓氏发源地或血脉渊源的一种方式,与其字面意相似,就是指从某一地域迁徙至此、繁衍至今的家族或派系。“衍派”与“传芳”相似,是闽南地区姓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一般以丁号(匾额)的形式,镶嵌在闽南人家或祖厝、祠堂的门楹上(图1),如“颍川衍派”“济阳衍派”“开闽传芳”等,是历史上的“闽南人”从中原迁徙至此后,留存并延用至今的重要移民文化符号之一。
“燉煌衍派”就是指从敦煌迁至闽地的洪氏家族,但让人不解的是:洪氏家族在丁号中使用的“燉”并非如今敦煌的“敦”。带着疑问,2018年6月16日,笔者在导师的带领下,前往泉州初访“燉煌衍派”洪氏家族。
泉州的“燉煌衍派”洪氏家族主要分布在泉州多个下辖的县市中,晋江、石狮、南安等地的村镇均有聚居。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名为“六桂堂”的组织,该组织以洪氏为主导、凝聚着洪、江、翁、方、龚、汪6个氏族,为“燉煌衍派”的研究提供了些许线索。
据洪氏族人介绍:洪氏先祖从敦煌跋山涉水来闽避乱,为保后世安全,便将六子分别改姓为洪、江、翁、方、龚、汪,故有“燉煌衍派,六桂传芳”之说法。但笔者认为该说法相关史料说法不一,值得商榷。如方煜东在《慈溪六桂堂文化探析》中提到:“六桂堂源起的历史要追溯至唐末五代,在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年间,在福建兴化县,有一个翁乾度,官拜郎中(应仕闽国),娶妻陈氏,生六子。因当时闽王朝内乱,公元945年,闽国被吴越国和南唐夹攻而亡,在亡国之际,由于翁氏是当时朝廷显官家族(乾度堂叔翁承赞是当时闽国宰相),翁乾度携眷归隐莆田竹啸庄,同时,怕被灭族而将六子改为六姓,依次为洪、江、翁、方、龚、汪六姓”[2]。类似的还有方氏某位先祖生六子而得名“六桂”的版本,在此不逐一列举。
但无论故事的主角如何变化,无论哪一家是六桂之“源”,故事中6兄弟分得6个姓氏的故事情节却是一致的。这是否意味着洪、江、翁、方、龚、汪6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虽然他们未必是同一时期从同一地点迁移至闽地③除洪氏丁号为“燉煌衍派”之外,其他5个姓氏均为其他丁号。,但也许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或者同样的目标,以至于他们的子孙在千百年后依然还能团结在一起,共同祭祀“六桂”先祖。
2 再访泉州——田野考察“燉煌衍派”
2018年12月21日,笔者随吕锤宽④吕锤宽,絃管(南音)专家,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教授。教授、高德祥⑤高德祥,敦煌学专家,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教授,再次前往福建泉州进行关于“燉煌衍派”的田野考察。早在2016年,高教授就曾匆访南安杏埔“燉煌衍派”,并提出了泉州絃管(南音)⑥据吕锤宽教授:絃管、南音、南管,既是局内与局外,又是社会环境的现象。从泉州所在地的政府层面,“泉州南音”属现阶段官方或学术界的用法,另基于普世的观点,该词汇又无涵盖性;“絃管”则作为历史性与局内人通用的乐种名称。故下文中除特殊情况外,均用“絃管”,不再逐一说明。与敦煌唐代时期流行的讲唱文学有一定联系的推论。
有了之前的初探,这次的田野考察可谓是“有备而去”。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和现实情况,选取石狮湖滨琼林社区(林边村)⑦湖滨琼林社区(林边村),以下简称“琼林”。和南安杏埔村作为考察点。
2.1 石狮琼林洪氏宗祠
选择琼林是因为事先联系到了洪世键⑧洪世键,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团长,这里是他的老家。在洪团长的带领下,笔者一行拜访了石狮琼林大小两座洪氏宗祠。
较小的洪氏宗祠是一座闽南红砖厝(图2),来此祭拜的都是五服之内的亲属。因为规模较小,除祠堂门楹上的“燉煌衍派”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只是当时正值冬至,陆续有族人来祭祀。祠堂门前挂着一对正面写着“洪”、背面写着“燉煌衍派”的灯笼;供桌上摆满了各种供品,这些供品不全是手工制作的花供,也掺杂有一些带塑料包装的现成品,笔者看来,这是宗族文化在当下的“再创造”。
较大的洪氏宗祠是全村所有洪氏族人祭拜先祖的大祠堂(图3)。祠堂内除一副“祥光普照敦煌传万代 瑞气回环固始颂千秋”⑨福建省石狮市湖滨琼林社区(林边村)洪氏宗祠楹联。的楹联外,并无其他记有历史信息的楹联、匾额或碑记,所幸洪氏族人为笔者一行请下了他们的族谱。
《琼林洪氏族谱》中也没有记载洪氏如何从敦煌迁至此,只是载有:“始祖缨斋公,相传由廿四都龙窟⑩龙窟,即今石狮市洪窟村。乡西公派下二房霞庵房分居于我林边乡,是为我琼林开基始祖”⑪石狮琼林洪氏:《琼林洪氏宗谱》。。但是,现存族谱是近些年根据台湾琼林族裔的民国版族谱重新修缮的,故内容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当笔者向村民询问“燉煌衍派”事宜的时候,村民表示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用“燉”,只是祖辈上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他们也就一直沿用了。
2.2 南安杏埔洪氏宗祠
南安杏埔村与石狮琼林十分相似——村中无论是新楼还是古厝,家家户户的门户上也都写着“燉煌衍派”的字样,毫无疑问,这里的洪氏与琼林同源。村中一座村庙倒是与闽南其他地方颇有些不同,庙中奉祀的是闽南很少供奉的包公,或许这与该村洪氏家族暗含联系。杏埔洪氏宗祠在外形上与琼林的有些相似,都是典型的闽南祠堂(图4);但不同的是,祠堂内部的楹联、匾额和碑记中写有大量历史信息。祠堂正中挂有“武荣正堂”字样的匾额(图5),梁柱的楹联分别写道:
“唐载我祖氏姓首开敦煌郡 宋志吾宗科第宏冠武荣州”。“源溯河南光州固始敦煌胤裔洪氏宗嗣荟蔚成望族 祖官赵宗大理评事瓜瓞绵衍武荣世胄浩气贯长虹”、“唐昭衍纬郡号敦煌赞万枝一脉 固始溯源分流武荣传百子千孙”、“英林世系标名族承先启后 武荣分流蔚大宗桂馥兰馨”、“堂构尊严昭奕代祖功宗德 孙枝蕃衍承万年春祀秋尝”⑫福建省南安市大霞镇杏埔村洪氏宗祠楹联。。
嵌在祠堂墙壁上的《建祠碑记》载:
“伏惟我祖于唐统绍敦煌一派,自豫光州固始入闽,初居泉郡,三徙英林家焉,垂千余春秋,迄今三十七代,其间仕宦明贤蔚起,英豪俊杰辈出,忠孝廉节,文武兼资,不胜枚举。故有礼仪望族之盛称。迨至赵宗二世评事濬公开基武荣,人杰地灵,宗支蕃衍,兰馨桂馥,誉闻遐迩。淳化年间三世义公,嗣科登仕,知武荣州牧,簪缨炳赫,诗礼传家,可谓显且贵矣。时至南宋末,吾宗九世祖天鸾公自武荣移居王塘,乃继承孝友遗风,奋发图强,自此王塘杏埔昉焉。继后,九峰山下,三名潭畔,枝繁叶茂,人文鼎盛,英贤鹊起,勋绩辉煌,德业光耀,世人瞩目”⑬福建省南安市大霞镇杏埔村洪氏宗祠《洪氏宗祠重建碑记》。。
2.3 田野思考
“武荣”“燉煌”“固始”……这些地名似乎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一条“燉煌衍派”迁徙的路线。
2.3.1 关于“武荣”
杏埔洪氏宗祠《建祠碑记》中的“武荣”就是如今南安市丰州镇。现如今,这里似乎已经看不到太多古城的影子,只是镇口矗立的“武荣”牌坊,还有“武荣街”在向后人述说这里昔日的繁华(图6)。虽然这里几乎看不到写有“燉煌衍派”的人家,但是按照武荣慈济宫、甘泉桥、丰州书院、南邑城隍庙等古迹的位置,可以推测出当年洪氏祖厝大致的位置,现如今已改建为一幢5层小楼。
民国版《南安县志》记载:“武德五年析南安县置丰州县为州治,贞观九年省丰州入泉州,嗣圣间析置武荣州县仍为州治,久视元年于南安县十五里置武荣州即今泉州府治,景云二年以武荣州为泉州仍今泉州府治南安属焉,开元六年析南安东南地置晋江县又析西南地置大同场析西北地置桃源场析西二乡置小溪场”[3]。
南安在梁、陈时期叫“南安郡地”,隋代叫“南安县地”,唐代叫“丰州”或“武荣州”,从五代至清朝的1 000年里,一直都被叫作“南安县”。所以,“武荣”一词是该地唐代的名称,而杏埔洪氏宗祠中用的“武荣”一词,是否意味着这支“燉煌衍派”就是在唐代从敦煌跋山涉水先迁至武荣、再移居杏埔呢?
2.3.2 关于“燉煌”
早在汉代,无论是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中的“敦煌郡”,还是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时的“敦,大也;煌,盛也。”“敦”字均无火字旁。
到了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敦煌县条目中,不仅用‘大’和‘盛’解释敦煌,还自作聪明地将‘敦’字改为火字旁,以示其盛明”[4]。才开始出现了带火字旁的“燉”,这一点,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体现。
如《旧唐书》卷四十,志第二十,地理三记载:“燉煌,汉郡县名。月氐戎之地,秦、汉之际来属。汉武开西域,分酒泉置燉煌郡及县。周改燉煌为鸣沙县,去县界山名。隋复为燉煌。武德三年,置瓜州,取春秋‘祖吾离于瓜州’之义。五年,改为西沙州。皆治于三危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县七里”[5]。
此外,高德祥教授通过多年来对大量资料和元典的研究,断定“燉”出现在汉代以后。而泉州“燉煌衍派”洪氏家族将“燉”沿用至今,也许正是希望后世可以铭记当初离开故土时的点点滴滴。另据前文有关“武荣”的考证,当年洪氏先祖离开敦煌的时间很可能在唐代。
2.3.3 关于“燉煌衍派”迁徙的猜测
杏埔洪氏宗祠《重建碑记》还提到:洪氏先祖从敦煌到泉州移民的过程中,途经了河南光州固始。光州固始是“闽王”王审知的老家,能和闽王成为“老乡”或是有关联自然是荣耀至极之事,故笔者认为后人在建祠作记之时,难免会有基于该观念而附会杜撰的可能。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华健在《丝绸之路》中提到: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由若干节点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路线,或者说更像是一个“网络”[6]。所以,尽管无法准确断定当初洪氏族人从敦煌到泉州都途径了哪些“中转站”,但人口迁移的线路就像米华健提到的“丝绸之路”一样——绝非一条!但为简化研究对象,一般只选取其中一条有代表性的线路进行研究。
“关于移民的原因,其最主要的研究框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迁出地向迁入地的人口流动,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7]“推力一般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因素,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8]。“拉力主要表现在有较多的谋生机会和发展机会”。
在那个安土重迁的时代,7 000多里(1里=500 m)路的大迁徙背后一定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犯了重罪,被迫举家迁往泉地;也许是一路追随“闽王”或“开漳圣王”的脚步,前去泉地寻求美好而安逸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当时西北战乱频繁或连年饥荒,一路逃荒,走走停停,最终选择在泉地落脚;也许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为了谋生,他们朝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跋山涉水,最终抵达泉地。
洪氏家族从敦煌迁至泉州的原因暂且不做决断,但正是许许多多诸如洪氏家族这样的族群,从长安、从中原、敦煌、丝绸之路沿线重镇举家迁至闽地,才有了随之而被带来并被不断“再创造”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表现形式等“中原文化”。
3 敦煌求索——探寻中原文化东移南迁
除泉州外,笔者也曾前往甘肃敦煌田野考察,寻找“燉煌衍派”的蛛丝马迹。
3.1 再考“燉煌”
敦煌莫高窟,一直以开凿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规模大、内容丰富闻名遐迩。除了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外,也留下了大量史料。如开凿于初唐时期的220窟,在其甬道北壁的《翟奉达兄弟二人供养像》中,就写有“亡兄燉煌□□翟温子一心供養”字样(图7)。同样是这个洞窟,在其甬道南壁的晚唐时期题字中,也写有“燉煌郡”的字样(图8)。
高德祥教授介绍,他查阅了从北魏一直到宋的敦煌壁画题记,其中写有“敦(燉)煌”字样的共11处,唐代的题记中均为“燉”。此外,高教授还提到,在敦煌出土的汉简中,所写均为“敦煌”。
3.2 丝竹相和,执拍者歌
前文提到了诸如“燉煌衍派”洪氏这样的氏族,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也带去了被不断“再创造”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表现形式,泉州絃管就是其中之一。
絃管,至今在闽南地区依然深受欢迎,其使用的乐器无论是形制还是演奏方式等,均与敦煌乐舞壁画接近(图9、图10)。与此同时,絃管所使用的“工乂谱”,也与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敦煌琵琶谱”颇为相似。所以,也就有了高德祥教授提出的泉州絃管与敦煌唐代时期流行的讲唱文学有一定联系的推论。
“演奏南管音乐的固有乐器,概括地指有南管音乐以来即存用的乐器,且属于南管音乐所独用,计有拍、琵琶、二弦、洞箫、三弦。这些同名的乐器虽也能见于其他乐种,形制则彼此不同,且使用于南管的上述5件乐器,除了三弦之外,都保存了唐代的乐器形制特征,换言之,上述5件乐器已属于南管音乐所独用,并不见用于今存的其他乐种或剧种”[9]。
除此之外,泉州开元寺甘露戒台上手持乐器的“妙音神鸟”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为佛和菩萨演奏妙音的“迦陵频伽”颇有相似之处。所以,“燉煌衍派”的扑朔迷离更是让人好奇两地之间的微妙联系。
4 结束语
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时期的靖康之乱造成了大量北方人南迁;“开漳圣王”陈元光、“开闽圣王”王审知开漳兴闽,为闽地输入了大量中原移民。
中原移民向东南沿海地区迁徙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古时交通工具并不发达,遥远的距离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随着迁徙族群一路上走走停停,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表现形式也随之与当地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不断流变,并被“再创造”。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无论对中原移民的南迁,还是对文化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迁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大运河的贯通加速了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进程”[10]。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又再次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南下”寻求美好生活。
“燉煌衍派”洪氏家族只是中原向东南移民大潮中的一支,但也正是其一直沿用的“燉”字,为当前研究文化重心东移南迁提供了新的线索。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