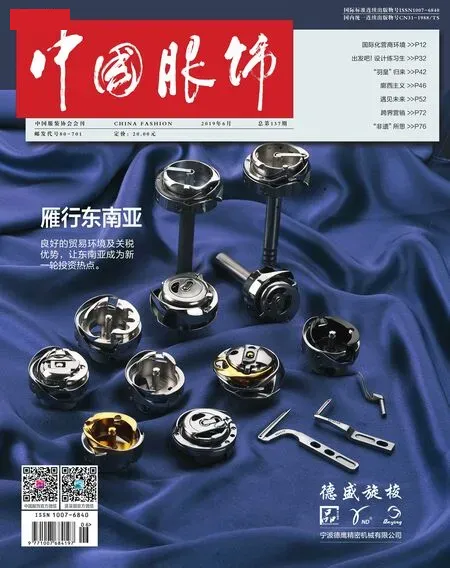科技向善
文|陈禹安
在“善恶义利”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日,IT巨头腾讯在自己的企业愿景及使命中增加了一项“科技向善”。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The World in 2019》杂志上撰文(后被《财经》杂志翻译刊载)写道:“我们能不能通过科技缓解人们的苦楚,帮助有需要的人群?”
这一系列举措表面,以腾讯为代表的IT行业,在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赢利甚丰后,终于有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来直面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了。
不过,“科技向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IT企业将各种前沿技术应用于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如果是这个小范畴,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展开探讨。因为公益慈善事业本身就具备了“善”的属性,科技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助力于扩大其规模,降低其成本,提高其效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IT企业所具备的更为本质的商业属性,却有可能与“向善”的导向形成“义利之争”的冲突。
“善”可以说是全体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无论什么国家,什么种族,基本上都会把对“善”的追求作为一项底线原则。而对“利”的追求则是商业组织绕不过去的基本属性。商业追求目标顾客的最大化,也即是在更大的那个最大公约数中异中求同—在相异的人群中求最大的“同”,以便转化为最大数量的目标顾客。
这是两个不同的最大公约数。企业有没有可能在“向善”上同时满足这两个最大公约数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比如说,滴滴打车的初心是“让出行更美好”,乍一看,这自然是符合“科技向善”的,但细究一下,滴滴打车是在让谁的出行更美好?显然是那些下载了“滴滴”App,且使用熟练的用户。马云曾经吐槽,滴滴打车让他的老母亲打不到出租车了,因为老年人不会使用“滴滴打车”。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最大公约数之内的顾客的“善”,就是对最大公约数之外的人的“不善”?
更进一步,再来考量一下“善”的具体标准及内涵,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期,善的标准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此时此地的善,在彼时彼地可能会被视为不善。对于当下全人类的善,也有可能是对未来人类的不善。这就会埋下冲突的隐患。
1.2.3 RTCA增殖实验 RTCA(Real Time Cellular Analysis)中文名为实时细胞分析技术。可实现实时、动态的对细胞进行定量分析,可用于追踪细胞增殖、迁移和浸润。本实验采用xCELLigence RTCA DP(model:3×16)仪器,实验开始前RTCA机器整体置于5%CO2 37℃细胞培养箱内,待RTCA机器温度与培养箱内一致方可开始实验。
再从商业逐利的本质来看,只要存在外部的市场竞争,只要有内部的KPI考核,向善就很难持之以恒,善的底线就可能被突破。
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向善的问题已经跳出了科技本身,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向善的问题。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新科技才出现的。
1981年,福特公司生产的一辆Pinto汽车在行驶爆炸,导致车上小孩被严重烧伤。调查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这款汽车的油箱设计存在瑕疵,可能导致行驶中发生火灾。但经过评估,公司认为全部召回该款汽车加以修复的成本高达1亿美元,而汽车着火致人死亡最高赔偿20万美元。按照发生事故的概率推测,赔偿金额将远低于召回成本,据此,福特公司决定不采取召回措施。
波音公司最新款737 Max 8机型,在接连发生了两起惨烈空难后,初步的调查显示:该机型增加了一项自动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当飞行中出现机头仰角过高时,该系统就会自动将机头拉低,以稳定飞行状态。这本不是坏事,但波音公司为了逐利而采取的功能模块化销售策略,对于没有购买这一功能模块的客户,不提供说明及操作培训,从而导致飞行员根本不知道飞机具备这项功能,以及当这项功能自动运行后如何手动取消等必要的技能。
上述这两个例子,都是商业组织“以利害义”的负面典型。这两个例子和技术还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很多情形下,哪怕和技术无关,也会出现“以利害义”的不善案例。
据法国媒体报道,零售巨头亚马逊将包括全新厨房设备、电视、书籍和尿布等在内的数百万件销售不出去的新商品,直接倾倒在了垃圾填埋场或焚烧掉。
当商家的产品在亚马逊卖不出去的时候,亚马逊会向他们收取每平方米22英镑的仓储费,6个月后则会飙升到430英镑,一年后高达860英镑。一位供应商则表示,亚马逊向他的公司收取每件17英镑的退货费,而销毁这些商品只需0.13英镑。供应商表示,当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付钱给亚马逊销毁这些产品。
如果单纯从利益角度看,直接销毁滞销商品,对于亚马逊和供应商都更经济。但从商业向善的角度看,这些产品本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
可见,即便是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方式,未必对整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利。商业向善,应该追求的是“你好我好环境好”。亚马逊显然背离了商业向善。
再来看看谷歌的故事。
谷歌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不作恶”的公司行为准则。但在2018年4月5日更新的行为准则页面上,谷歌却拿掉了“不作恶”这条准则。其背景是谷歌参与了五角大楼的 Maven项目。Maven项目的正式说法是“加速国防部整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意在通过AI技术来处理无人机所拍摄的视频内容,在其中识别出车辆等38类物体,以此减轻分析人员的负担。据披露,Maven项目中开发的技术,已被用到了美国同ISIS的战斗中。
这个项目引发了谷歌员工基于“不作恶”准则的担忧。不少激进派员工愤而离职,另有数千员工对公司高层发起请愿,要求中止与军方合作。公司最后回应,保证这项技术“不会操作或飞行无人驾驶飞机”“不会用来发射武器”,然而这并不能让员工安心。
谷歌拿掉“不作恶”,并不代表着要开始作恶了。这实际上是其在“善”和“利”的两个最大公约数之间的一种妥协。
谷歌将“不作恶”改为了“做正确的事”。但争议在于:什么是“正确的事”?是依据“善”的标准的“正确”,还是依据“利”的标准的“正确”呢?这依然是一场没有明确答案且永无止境的博弈。
谷歌员工拥有自己的关于善恶义利的独立判断,而这个判断往往和公司的判断并不一致。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谷歌的员工并没有坐视不顾,埋头挣自己的工资,而是选择离开或抗议。
同样的反应模式也会出现在顾客身上。比如,当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被列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候选人名单后,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网民们因为对于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导致的一系列负面事件的严重不满而纷纷对李彦宏候选工程院院士提出抗议。这充分表明,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互联网网名已经摆脱了“多元无知效应”的束缚而拥有了自己清晰的判断。
所谓“多元无知效应”,是指当环境及形势不明朗,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法作出自己的确定性判断,从而更有可能接受并参照别人的行为行事。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与社会规则趋同。
互联网初兴之际,人们出于对技术及其带来的对生活的冲击性影响的陌生感、迷茫感和恐惧感,往往无所适从,只能听任各种技术应用对于自身的各种“虐菜”,表现出怯懦屈从和盲目模仿的行为特征。
但是,随着网民的心智进化到了觉醒的阶段,基于人类基本法则的“善恶”判断恢复正常,互联网企业利用新技术作恶渔利或者先作恶再洗白的盈利路径将不会被消费者漠视、容忍,更不会继续被动接受。
所以,放眼未来,科技向善将不再是企业锦上添花的升华之举,而是必不可少的生存原则。但是,基于“善恶义利”的两个最大公约数始终是一个悖论。只有那些能够顺利破解这个悖论,在“善恶义利”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企业,才有可能在未来取得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