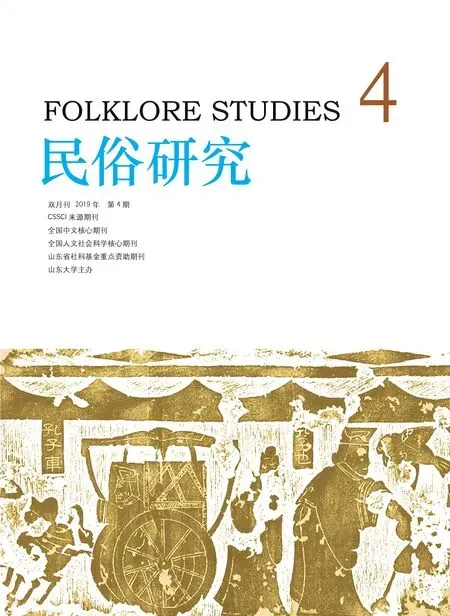昆仑文化意义的递变
钟宗宪
一、前 言
对于“昆仑”一词的来源,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和方法,但是大抵都是以训诂的方式从字词原义去推估,似乎难有定见。“昆仑”与“崑崙”二词,所指涉的意义有别,从“崑崙”专指山名与造字学理来看,“崑崙”应该是后起之词,属于具体的地理山名或山系名,基本上没有超越性的概念。
目前所见文献,最早且明确的“昆仑”说法出自《山海经》。[注]本文引用《山海经》原文及相关注语,俱出自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今《尚书·禹贡》曾提及“崑崙”,历来注家咸认为位处西戎之地。关于《禹贡》一文的撰作年代,众说纷纭,而《史记·夏本纪》亦引有相关内容,或可视为与《山海经》共时的著作,但是内容并未对“崑崙”做出具体说明。《山海经》作为昆仑记录的最早载体,其成书历程犹有争议,而各卷所载的昆仑也多有参差。以“昆仑”一词于《山海经》进行检索,散见于《西次三经》《北山首经》《海外南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分布方位可区分为东南和西北两种“昆仑”。其中,《海内东经》以昆仑虚为地标,既有流沙,又杂有大夏、月支等历史上具体的西域国名,应该如郝懿行、袁珂所言,此段文字是由《海内西经》内错简而来,该移入“流沙出钟山”节后。《海外南经》所记“岐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的情况应该也类似,或者至多只是单纯的地理名词,与《淮南子·地形》“崑崙、华丘在其东南方,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桃、甘樝、甘华,百果所生”[注]本文引用《淮南子》原文,俱出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说法雷同。所以,位处西北而分别记载于《山海经》其他各经的昆仑,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昆仑。
从甲骨文的相关资料来看,殷商文化已有四方神、四方风的观念。丁山认为:“殷商文化时代四方风名,确含有四时节令的意义;其四方神名,则全是天空上的岁次……”[注]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95页。殷商文化与姬周以降的所谓东夷文化[注]广义东夷的说法,如《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或者再细分为九夷,如《后汉书·东夷列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所处地理位置有不少重叠,且关系密切;传说中的夏史,也与东方民族互动频仍。虽然目前还不容易具体掌握其神话内容,但是若以周人所传的《尚书》《左传》《国语》《山海经》等书为基础,似乎可以推测:即使周人继承了四方神、四方风的观念,如《山海经·大荒经》所载,同时保留了类似“岁次”、四季的原初内涵,则已然将殷商或东夷崇拜的上帝或神祇转化为天体名与帝王名。
例如《左传》关于东夷郯国称祖于少昊的记载,是历来学者经常注意到的材料。若整理《左传》的内容,有以下数则可以规模出大要:
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昭公八年)
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昭公十年)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昭公十七年)[注]本文引用《春秋》《左传》原文,俱出自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新兴书局,1979年,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
其中,昭公十年、昭公十七年的“颛顼之虚”,应该是天文中的星占语词[注]杜预注:“颛顼之虚,谓玄枵。”《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韦昭注:“天鼋,次名,一曰玄枵。”又说:“天鼋,即玄枵,齐之分野。”韦昭注:《国语》,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47页。又,《汉书·地理志上》:“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虚。”汉代所认定的颛顼之虚,当指濮阳。王先谦注:《汉书补注》,艺文印书馆,1971年,第698页左上。《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预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这是继承汉代的说法。,“大辰之虚”“大皞之虚”“祝融之虚”也是如此;所谓的“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卫,颛顼之虚也”,指的是星占之中的分野观念[注]关于分野说的问题,可参考泷川龟太郎的批评,见[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洪氏出版社,1983年,第486-487页。或参考白川静《中国神话》,王孝廉译,长安出版社,1983年,第169-176页。。《昭公八年》载“陈,颛顼之族也”,以及《昭公十七年》所提到的宋、卫、陈、郑,分别为大辰[注]大辰即心宿大火星。《公羊传·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之虚、颛顼之虚、大皞(昊)之虚、祝融之虚,形成一种特殊的对应关系。若以殷商故地、宋都商丘为中央核心,那么包括鲁、郯、卫、陈、郑等国,皆在其周围。那么此一区域所构成的传说圈,很可能就是承袭自殷商旧说,其区域与九夷的活动区域重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有一则记载: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重为句芒,属春、木、东;该为蓐收,属秋、金、西;修、熙为玄冥,属冬、水、北。虽然独缺南方[注]从《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山系走向观之,《南山经》由西而东的横向叙述,水系走向则独缺南海,明显是对于南方的一种观念上的断绝。,但是不难看出这是方帝、五行的雏形。若将战国后期如《吕氏春秋》所形成的五方、五帝、五神、五色与四季整体系统来进行比对,则此一传说圈的方位观念原来很可能是上、下、东、西的立体四方,与四方风、四方神的平面四方不同。如右两图:一图为“平面系统”的四方分布;另一图为“垂直系统”,其上为帝俊,其下为颛顼,其东为太昊,其西为少昊。其间的转化过程与周人立国翦商有关,也与姬姓、姜姓两族的关系密切,于是在周人帝系的构成中,关于殷商主神帝俊的纪录也就在古籍中消失,基本上只保留在《山海经·大荒经》与最末卷的《海内经》。颛顼、太昊、少昊,则并入取代帝俊为上帝的黄帝系谱。
因此,在中国神话语境中的所谓“西方”,对应于中原以西的地理方位,之所以会成为周代以后上帝所在的圣域,尤其是西方昆仑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周人承袭殷商文化的信仰观念,并因为建国于西陲,而逐渐形成的神话系统。
二、《山海经》的“昆仑”
周秦时期记载“昆仑”最早、最详细的是《山海经》。
从神话体系的角度来看《山海经》书中的“昆仑”,基本有三个范围:
(一)帝与百神所在之处,即西北的昆仑之丘、昆仑之虚,是为小昆仑。
(二)环昆仑之诸山间,为各职司神分居之处,即如《西次三经》所载,是为大昆仑。[注]后世托名东方朔所著的《十洲记》,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载有:“崑崙,一号曰崑崚,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地方一万里,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回绕匝。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崑崙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是王母宫,王母告周穆王云:山去咸阳三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山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故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崑崙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其中所谓的“四角大山,实昆崙之支辅”,即是出自大昆仑的观念。引自张君房《云笈七签》卷26《十洲三岛》,自由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398页。
(三)与帝的各种活动相关之处,是为泛昆仑。[注]《海外南经》有在岐舌国东的昆仑虚,毕沅认为“崑崙者,高山皆得名之”,则《山海经》各高山都可以称为“昆仑”,于此暂不取。语见毕沅校注《山海经图说》(又名《绘图山海经新校正》),新兴书局,1958年影印,第105页。但是如《中山经·中次三经》:“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和山,其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苍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山之阳,出入有光。泰逢神动天地气也。”此二则仍属于昆仑体系。
在《山海经·西山经》的《西次三经》中,以昆仑之丘为核心的昆仑群山,是建构昆仑神话体系最主要的大昆仑范围。以《西次三经》记载“昆仑之丘”前后较为明显的各条为例: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无水。
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
《山海经》屡称“帝俊”“帝颛顼”“帝舜”“炎帝”“帝尧”“帝喾”等,或如昆仑的长留之山有白帝少昊,尚且还有“群帝”之说,例如《大荒北经》有“群帝因是以为台”[注]《海外北经》称为“众帝之台”。、《中次十经》有“騩山,帝也”、《中次一十一经》则有“禾山,帝也”等与祭祀有关的记载,那么《山海经》各卷所提到的“帝”,显然不是专称。
《西次三经》的“帝”,应该是原指帝俊,而非黄帝。从《山海经》来看,黄帝只是群帝之一,峚山只是黄帝活动区域之一,黄帝并不必然是昆仑之丘的“帝”。但是《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庄子·天地》“黄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以及《西次三经》西王母所居处的玉山西方有“轩辕之丘”,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女,因号轩辕丘”,郝懿行案语:“《大戴礼·帝系篇》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史记·五帝纪》同《淮南·墬形训》云:‘轩辕丘在西方。’高诱注云:‘轩辕,黄帝有天下之号即此也。’”[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78-79页。综合上述部分列举数据来看,或者应当如袁珂所说的一样,“帝”指的就是“黄帝”,反映的是黄帝地位在战国以后不断提升的意义。[注]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书中解释《山海经》里面的“帝”,除了少数别有专指之外,大多以黄帝来解释。
昆仑之丘是上帝在人间的都城。其情景或如《海内西经》所说的:“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注]《海内西经》的功能在于对《西山经》进行补充性的说明,着重于昆仑内部的空间叙述,而没有关于分司之神的记载。而《大荒西经》说昆仑之丘是“此山万物尽有”: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黒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輙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西方确实是《山海经》的乐园所在。除前引昆仑乐土外,还有《海外西经》的“诸夭之野”[注]《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闲,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与此相类。《海内西经》:“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毕沅本在本句后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之文,文下有郭璞注:“离骚曰:‘绝都广野而直指号。’”郝懿行:“楚词九叹云:‘绝都广以直指兮。’郭引此句,于都广下衍野字,又作直指号,号即兮字之讹也。王逸注引此经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经文,今脱去之,而误入郭注也。因知‘素女所出也’五字王逸注虽未引,亦必为经文无疑矣。素女者,徐锴说文系传云:‘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黄帝悲,乃分之为二十五弦。’今案黄帝史记封禅书作太帝,风俗通亦云:‘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云云,然则素女盖古之神女,出此野中也。又郭注天下之中当为天地之中。”若都广之野在天地之中,依《海内西经》所示又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是“百神之所在”,则都广之野为圣地。在《山海经》全书中,神境乐园不止一个。:
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昆仑之丘在《大荒西经》里,似乎成为西王母穴居之处,但是对照《西次三经》所载,西王母不是昆仑之丘的主神,其地位应该与英招、陆吾、长乘等相类似,“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的形象,略同于蠃母之山的长乘,“其神状如人而犳尾”。西王母原本是“帝”之佐臣,“司天之厉及五残”。
至于《西次三经》黄帝与白帝少昊的方位与从属关系,如果黄帝不是昆仑之丘的“帝”,峚山、长留之山各在昆仑之丘东、西两方,那么黄帝与少昊皆为群帝之一,或皆为“帝”之属臣。但是如果黄帝确是昆仑之丘的“帝”,为昆仑神话体系中的主神,则黄帝与白帝少昊的方位与从属关系,可能还是与方帝观念的逐渐形成有关。
所谓的方帝,或谓“五方帝”“五方神”“五帝”,是指东、南、西、北、中央五个方位之统领上帝,代表着一个结构完整的空间观念和宇宙观,而以中为尊。但是“方帝”体系的成形,是否在战国以前,则各说不一,各有所见。方帝神话中的西方之帝少皞其色为白的传说,似乎在东、西周之际已经出现。《西次三经》中的黄帝,即使是主神,位置也未必居中。不过,“主司反景”的白帝少昊确实在西方,居于泑山的蓐收[注]蓐收是昆仑神话体系中的刑杀之神。更在长留之山以西。然而《南山经》既没有炎帝的记载,《北山经》《东山经》同样没有颛顼、太昊,推测《西次三经》的记载乃代表方帝系统在战国中晚期逐渐形成的过渡阶段。
《大荒经》也有方帝系统观念存在。如前文,少昊、颛顼原来都在中原的东方,但是在方帝系统中,少昊是西方的白帝而职掌秋季;颛顼是北方的黑帝而职掌冬季。以此解释《大荒东经》说的“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就可以理解为秋冬两季相接的秋末冬初,所以称之为“少昊孺帝颛顼”;“弃其琴瑟”则是冬季寒缩内敛、不张扬的表征,而颛顼的原始意义就是寒缩内敛。[注]《说文解字》:“颛,头颛颛谨貌,从页端声。”“顼,头顼顼谨貌,从页玉声。”颛顼,这两个字似乎不曾单独出现过,所谓“头颛颛”“头顼顼”,似乎是颛顼之名在表现一种谨慎严实的态度,《说文解字》顼字下段玉裁注引《白虎通》说:“冬,其帝颛顼。颛顼者,寒缩也。”即内敛而不外显的样子。两条俱见钟宗宪编《新添古音说文解字注》(许慎撰,段玉裁注,洪叶文化,1998年,第423页)。“其帝颛顼。颛顼者,寒缩也”,语在《五行》。见陈奂《白虎通疏证》(上)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第181页。方帝神话系统中,少昊之国在西方而不在东方,“东海之外大壑”是东、西方可以环状相连的关键。“大壑”一词,此为《山海经》中仅见,应该和《列子·汤问篇》所说的“大壑”“归墟”相同。《列子·汤问篇》载“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减焉”[注]本文引用《列子》原文,俱出自杨伯峻《列子集释》,华正书局,1987年,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指的是海外之海,也就是最终的尽头。
《山海经》书中“大荒”的意思,都是抽象的海外之海与海外之间的地方,或许接近于海上沙洲的意义。[注]海神所居之处皆在大荒之中,而称“海之渚”。《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猇。黄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猇处东海,是惟海神。”《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大荒东经》有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东极、离瞀、猗天苏门、壑明俊疾等山为“日月所出”之山;《大荒西经》有方山、丰沮玉门、龙山、月山、鏖鏊巨、常阳之山、大荒之山等山为“日月所入”之山。[注]刘宗迪认为:“《大荒经》既然是古人‘观象授时’的产物,就应该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其整体结构和其中要素的意义。”刘宗迪基本认为《大荒经》是观察太阳出没方位来确定季节和月份的天文历法志,而且出自东方;少昊、颛顼皆在东方。语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6页。大荒西的日月所入到大荒东的日月所出之间,就是大壑的所在,也因此日月出没得以循环。《大荒南经》《大荒北经》没有日月出没的记载,而皆有海水入的说法[注]《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也可说明海外之海的意义。
少昊之国在西方,那么颛顼之国是何处?《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由这段记载,颛顼之国应在北方。颛顼葬于“东北海之外”,合于冬末春初的概念,与“少昊孺帝颛顼”相配,正是季节轮替的神话说法。[注]《山海经·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山之南曰阳,冬季北方的颛顼葬于山之南,亦合于此条之说。
在《山海经》中,不可忽视的是“昆仑”在《西山经》,而《西山经》起自于华山(华山之首)。换言之,即使《山海经》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五藏山经》应该出自东周;而“昆仑”是周人所信仰的圣域,并成为西方的神山,也应无疑义。
三、“昆仑”成为“仙乡”
王孝廉《绝地天通——崑崙神话主题解说》[注]据文前小序,该文的写作动机是在肯定苏雪林于1945年发表《崑崙之谜》一文的贡献之外,另提出与崑崙神话(仙乡乐园神话)有关的“绝地天通”(失乐园神话)的神话类型。文见王孝廉《中国神话世界》(上编),洪叶文化,2006年,附录二,第357-371页。一文认为“昆仑”之所以为“仙乡”的原因,大概可归纳成以下四点:
(一)能成为“仙乡”,乃因此地具有神明聚居之处的性质——“帝之下都”(《山海经·西山经》)、“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海内西经》)。而所谓的“仙乡”,实即涉及“仙”的概念[注]“仙”是人或物透过修行的方式、藉由时间的累积或是藉由其他外力:包括法宝、圣果之类的影响,成为具有特殊力量的英雄或人物。仙话往往表现下列特质:(1)能够法术变化;(2)具备飞升能力,如:从人境到仙境;(3)向往不死或死生齐一;(4)追求现世性、功利性的满足。,或者在此地者能因修炼而得长生、不老不死,或者此地即有满足各种世俗欲望的条件,因此“仙乡”又与“他界”相连,而与“我界”相对。
(二)孕有各种奇异之动植物。所谓奇异,或乃自然界物种某特征(包含外表与习性)之扩大、重复,或乃不同物种特征之合成。而这些奇异之物,实多具有描述此奇异的人类的心理寄托。
(三)人类踏进“昆仑地界”,上“凉风之山”,则能不死;上“悬圃”,则得呼风唤雨的神通;再上至天,也就到了“太帝之居”,人类乃能化为神(《淮南子·地形篇》)。于是,藉由登升“昆仑”以转换身处之地,即可不死、得异能、甚至化神,呈现出一种由人而灵而神的登仙飞升概念。这也是昆仑神话世界与仙乡产生联系的原因之一。
传统典籍对于“仙乡”的记载,尤其是东方蓬莱系统中的仙乡,较早且较详尽的典籍为《列子》。[注]具体以“求仙”为名目的蓬莱叙事,多出自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孝武本纪》与《封禅书》等处,如《孝武本纪》:“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如果视《列子》全书为一个整体,书中比较显见的神话空间记载大致集中在《汤问篇》:
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
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蹔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阨,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
西北方位是天体的归处。对于“归墟”的说明则包括了关于东海上五座仙岛由来的神话,也是神话与仙话合流的一个例子:“五山”是海上的五座岛屿,其上有许多花果,人食之“不老不死”,包括所谓“仙圣之种”云云,说的显然是“仙境”,不纯然是一则神话国度的叙述;但是对于归墟、上帝“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的叙述,则是空间神话。[注]“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即四方或八方之极可以与天界相连相通于归墟;“海”为无底之渊,为归墟,或其他天地之外的“他界”,是地之极。“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则“地”是由水族之物所支撑,也是地之所以能够浮载万物的原因。这是说明天、地、海三者关系的空间神话。至于龙伯巨人被上帝惩罚,以及“僬侥国”“诤人”,乃至于“鲲”“鹏”等等记载,都是与神族物种或殊方异物有关的神话。
《列子》书中类似归墟五山这样神话、仙话合流的仙乡国度,还有《周穆王篇》提到的“古莽之国”“阜落之国”和《汤问篇》中的“终北”之国,分别在西极之南隅、东极之北隅和滨北海之北,都属于相对于“我界”的“他界”想象。[注]《周穆王篇》所谓的“中央之国”即为“我界”空间。其中,终北之国尤其具有乐土的意义。同样有乐土性质的他界国度,书中另有《黄帝篇》中的“华胥氏之国”和“列姑射山”[注]也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射姑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然所谓“神人”者,张湛注曰:“凝寂故称神人。”实与《庄子·逍遥游》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相同。另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21-322页有关于“列姑射”之各条说明,以及王先谦《庄子集解》[(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页有关于“藐姑射之山”之说明。。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或犹可及之;华胥氏之国则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因此“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黄帝只能昼寝梦游而往。从“华胥氏之国”的例子来看,显然“梦”是空间与时间的延展,是现实与虚幻的混同。
《周穆王篇》提及“崑崙”(昆仑)凡2次,其中有“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西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之语,可知西方崑崙之丘近于日入所在,其上有黄帝之宫、瑶池,瑶池为西王母所居之所。《周穆王篇》一开始就为圣性的西方布局,从“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到化人带领周穆王神游“化人之宫”,而有以下的描述:
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王俯而视之,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
周穆王因神游“化人之宫”的点化所以西行,其实“化人之宫”也就是崑崙之丘的复制与浓缩,只是“化人”“化人之宫”的仙话性质更为强烈。
从《列子》神话的内容来看,原本世界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然而在女娲修补之后,却又遭到共工的破坏,造成现在世界“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情况。换言之,天地的形成是经过“残缺→修补→破坏→定型”的程序进行。但是《列子》全书有明显而清晰的天地四方观念:青天、黄泉、八方、八极、八荒、四海、四荒、四极、归墟、八纮、九野、北极、西极、东北极、终北之北等等名词,来阐明天地四方上下的空间概念。
例如《仲尼篇》:“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汤问篇》:“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黄帝》:“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汤问》:“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八纮是大地的极限,九野则是天的中央和八方;天上除了有日月星辰之外,还有天汉银河。

从《列子》空间神话的内容来看,以《汤问篇》对于“共工怒触不周山”的记载和“归墟”的描述,天地的构造应当如“篷形”[注]中国神话对于天地之间结构关系的叙述,各个时期皆不相同。大致上是由“混沌”关系而到“球状”关系(神人相混),再到“篷形”关系(包括以天柱支撑),再到“三维”关系(绝地天通)。本图所谓“海”,即指“归墟”,实为海外之海。,也就是“天圆地方”的天盖地载观念:四方或八方之极可以与天界相连相通,由天柱如不周山顶天;地浮于海,由水族之物所支撑。如右图所示。
在归墟、东海仙岛的说明中,出现了“西极”与“北极”两个地方。在《列子》书中,“西极”另出现了两次,都是在《周穆王篇》:“西极之国有化人来。”“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似乎都并未有比较特殊的涵义。“北极”则仅出现于《汤问篇》,未出现在其他篇中。
《汤问篇》所说的“帝恐流于西极”,似乎赋予“西极”负面的意义。五山原位于渤海之上,而归墟乃在渤海之东的无底深谷,其幽深不可测之境地,即使八纮九野及天汉之水流注不止,仍是无增无减。依此情状,五山终究会有掉入归墟之时,那么本则应是“帝恐流于东极”,而非西极。但是依全文来看,流于北极或四极较为合理。[注]关于这一问题,前人注疏有可参考者。俞樾注曰:“‘西极’字亦疑有误。五山随波上下往还,安知其必流于西极也?下文云‘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可证其不必西流矣。‘西极’似当作‘四极’。”杨伯峻亦同意此说。
《列子》关于西方的记载,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他界、梦境之地。除具体地名之外,多在表现特殊的时间观念:认为梦境是另一种时间的存在表现。例如《周穆王篇》:“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而《黄帝篇》所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则颇有“以梦中所为者实”的意味,梦境也因此可以跨越他、我两界之间。
其二,帝神的居处。如《周穆王篇》“观黄帝之宫”,“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注]《列子》的西王母形象类似《穆天子传》,而较不同于《山海经》。
其三,殊方之人。包括《黄帝篇》有处于乐土中的“华胥氏之国”民,《周穆王篇》有来自“西极之国”的化人,献白鹄之血给周穆王的“巨搜氏”,以梦中所为者实的“古莽之国”民等。
《列子》中的方位结构,是以中央为主轴,向东、西两方的北面延伸,正南、东南方几乎没有任何着墨,如下图:
图中的标示位置,在《列子》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如下:
1.华胥氏之国——《黄帝篇》:“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
2.不周之山——《汤问篇》:“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作为天柱的不周山,也是人神往来交通的途径之一,若是以不周山折断之后,“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特性来看,不周山当位于西北方。
3.巨搜氏之国——《周穆王篇》:“驰驱千里,至于巨搜氏之国。”巨搜即渠搜,西戎国之一,原分布在黄河上游、甘肃西北部,后遂逐渐东迁。
4.崑崙、赤水、瑶池、黄帝之宫——《周穆王篇》:“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
5.古莽之国——《周穆王篇》:“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为首见于《列子》的虚构国名。
6.隅谷——《汤问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隅谷是神话中极西日落之地,也作“虞渊”“羽渊”。
7.仪渠——《汤问篇》:“秦之西有仪渠之国。”仪渠亦作“义渠”,为西戎国之一。
8.西戎——《汤问篇》:“周穆王大征西戎。”
9.弇山——《汤问篇》:“管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

从上述整理不难发现,《列子》对于西方的认知,除了现实的西戎民族之外,其文化意义与《山海经》《庄子》《穆天子传》皆颇有雷同之处,而特殊之处是增添了梦、幻的想象空间;与《山海经》的较大差异是沃之野式的仙乡乐土在北方的“终北之国”。
单从神话角度来看,《列子》确实出现一些特殊的神话材料。如《汤问篇》将“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两则本来可以不相关的神话,连结在一起;甚至“女娲补天”的部分将“练五色石以补其阙”与“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合为一事,而没有其他因果关系的说明,则在《列子》之前的神话叙述为何?此问题更值得思考、深究。
因此,《列子》神话体系的构成存在着前体系,是可以肯定的。顾颉刚曾经认为:
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崑崙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崑崙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注]详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如果东、西两大仙乡神话系统的说法成立,那么“崑崙”两次出现在《周穆王篇》,“蓬莱”仅见于《汤问篇》一次,显然这两篇各保留或引用了东、西两大系统的一部分。倘与《山海经》相比,则《山海经》记“昆仑”者多,记“蓬莱”者甚少,内容也颇有与《列子》参差之处。若是再与《淮南子》相比,《淮南子》有“崑崙”而不见“蓬莱”。中国神话的保存不必记载于同一个叙述文本,也不必全部统属于一个神话体系,但是在这些看似片段、散乱的话语之前,《列子》这本书遗留下相当宝贵的线索,需要后人加以复原,而《列子》也应当被视为重要的神话经典来看待。
顾颉刚认为崑崙神话由西传东,才逐渐形成蓬莱神话系统。这样的推断固然还有讨论空间,不过也反映出中国神话,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属于大陆型,而非海洋型的性质。西方“昆仑文化”与东方“蓬莱文化”互涉与共融的现象,汉代典籍、画像都提供了一些线索。虽然不容易确定汉代出现许多“三山平顶”的图像,是否与“昆仑”或“蓬莱”仙乡系统有关。如汉代画像“三山平顶”多坐有西王母或东王公,学者认为即为“昆仑”图像[注]如山东沂南汉墓墓门立柱画像,《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山东画像石》提到的“山字形的瓶状高几”,信立祥即认为西侧有西王母者是“昆仑山三峰”,东侧有东王公者是“仙山”。见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山东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9页;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甚至认为是受到“蓬莱”三岛说法的影响所致[注]如高莉芬认为沂南汉墓立柱所刻三山,应即“蓬莱三山”。详见高莉芬《垂直与水平:汉代画像石中的神山图像》,刊载于《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11月第23期增刊“文学与神话特刊”。。但是从《淮南子·地形篇》开始形成的“三成(层)昆仑”之说,确实是文化昆仑意义转变的关键。
四、地理崑崙的认知

(第一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崑崙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崑崙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第二段)河水出崑崙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第三段)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其中,第一段继续深化《山海经》的西方昆仑形象,较为特殊的是“掘崑崙虚以下地”,表现出崑崙的崇高。第二段则直指“河水出崑崙东北陬”。第三段将昆仑山之上分为三层:昆仑之丘→凉风之山→悬圃→太帝之居。第三段除了具有“昆仑”仙乡化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呼应《山海经》:建木是众帝所自上下,而居天地之中。汉代对于“昆仑”的想象与认知,可能因此而展开两个比较明显的倾向:
(一)“昆仑”的位置在文化意识里由西方而居中,其地位更加崇高;
(二)对于真实地理的崑崙山位置展开探寻,并以黄河河源为定向。
《淮南子》的“昆仑”始终在西方或偏西之处,但是相较于《山海经》,却已经出现趋中的现象。《时则篇》: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山海经》的《西山经》之首是华山,即中央、西方的交界处是华山。但是在《时则篇》的五方观念中,中央、西方的交界处已成为昆仑:由西方往中央靠近。直接将“昆仑”定位于中央,最早的文献是纬书,而对于“昆仑”的叙述最多的是《河图括地象》[注]又称《河图括地象图》《括地图》《括象图》。本书的成书年代虽多有争议,但是多数学者仍认为出自汉代。。其内容主要有:
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
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而赫然。
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昆仑在西北,其高一万一千里,上有琼玉之树。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员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之,与天地同休息。
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东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偏域也。
既言“地中央曰昆仑”,又说“昆仑在西北”,可见《河图括地象》之类纬书成书争议之一斑,何况书中多杂有类似《史记·孟荀列传》所记的邹衍“大九州岛”“小九州岛”的地理观,以及《吕氏春秋·有始览》与《淮南子·天文篇》关于“九野”“九天”的说法。其中,九天之说明显是以“九天”合于“小九州岛”,也就是《淮南子·地形篇》所提的九个方位: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秭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凡此,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记录者的立论视角不同。但是以昆仑为地之中央的观念,影响甚为深远,一直到十七世纪李氏朝鲜出现的“天下图”,图中仍称崑崙山为“天地心”。[注]今存最早的版本是李灿所藏的《天下总图》(1684年)。另有一图作于十七世纪末,是尹炯斗所藏之《天下图》。经比对,两图的构图类似,大抵以《山海经》所载为依据,明显的差异只有在《天下总图》的“西域诸国”和“蕃胡十二国”的部分,详列了许多国名。
从《淮南子》到《河图括地象》,相较于《山海经》对昆仑的认识方式,显然更试图将他界的昆仑与我界相衔接。这不仅是神话到仙话之间的观念演变,同时也是文化昆仑与地理崑崙相混合,呈现若即若离、既分且合、既合且分的分水岭,而东汉到魏晋之间可能是关键的时代。
《史记·大宛列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注][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洪氏出版社,1983年,第1306-1312页。本文引用《史记》原文、张守节《史记正义》俱出自此,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这段文字说明直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仍不知道昆仑、西王母究竟具体在西域的哪个地方,地理昆仑是汉武帝依据“古图书”的记载判断,以张骞所认定的黄河河源所在,将之命名为昆仑山。此一创举,首度将他界的昆仑明确地落实到我界的地域来。但是司马迁记录这段文字时的态度,显然是半信半疑的。所以司马迁在《大宛列传》的传末赞语说: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河水出自崑崙之说,起自于《山海经·西山经》的记载,《淮南子·地形篇》之后各书皆继承此说。殊不论张骞对于河源地点的认定是否正确,影响所及,如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司马相如列传》引《大人赋》“西望崑崙”下所言:
张云:“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括地志》云:“昆仑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后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明矣。”
在西方之中的地理崑崙位置也就因此大致确定下来。南北朝以后,或者受到《史记·大宛列传》的影响,或者是周穆王故事的流传,致使崑崙山、瑶池、西王母等文化单元产生连动性的变化,使地理崑崙的地点出现不同看法,则可以用类似“地望”的角度视之,成为另一种形态的文化昆仑单元。[注]如《穆天子传》《列子》,甚至笔记小说之类,都将崑崙山、瑶池、西王母视为地理方面的共体认知。所以当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设安西四镇,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到龟兹,任原本是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于是地理崑崙也随之产生了另一种说法。
河源的探究是文化昆仑落实到地理崑崙的一条思路。另有一条主要思路与西域交通、佛教传播密切相关。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注]王嘉:《拾遗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2页。高山出自海中,或即为陆地出自海上,历来多有此类看法。所谓“对七星之下”的思维方式,也见于纬书。[注]如《河图括地象》:“河导昆仑山,名地首,上为权势星,一曲也;东流千里至规期山,名地契,上为距楼星,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积石山,名地肩,上为别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陇首间,抵龙门,名地根,上为营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陇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为卷舌星,五曲也;东流贯砥柱,触阏流山,名地喉,上为枢星,以运教,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东至雒会,名地神,上为记星,七曲也;东流至大岯山,名地肱,上为辅星,八曲也;东流过洚水,千里至大陆,名地腹,上为虚星,九曲也。”《拾遗记》最具意义的看法是“崑崙山者,西方曰须弥山”,认为佛教的圣山须弥山即是崑崙山。这样的看法固然与文化昆仑的内涵密切相关,也与昆仑由西趋中而为地之中央的崇高地位有关,但是直接对应须弥山,似乎不是单纯的相互形容、相互比拟,而是一种认定。
《拾遗记》的说法并非孤例。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于“崑崙墟在西北”下注:“三成为崑崙丘。《崑崙说》曰:崑崙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可与《淮南子》参照。于“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下,郦道元注:
《禹本纪》与此同。高诱称河出崑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按《山海经》,自崑崙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余里。又按《穆天子传》,天子自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崑崙之墟,诸仙居之。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绵褫,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末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注]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5页。本文引用《水经注》原文、注文俱出自此,后文不再另行标注出处。
所谓“数说不同”,亦可印证关于地理崑崙的位置,甚至河源,都只是大致确定在西方,而众说仍旧纷纭。重要的是在说“河水”处,经文有“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一句,郦道元注:
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崑崙,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雷公也。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

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
竺法维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
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图调传》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崑崙山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传》亦知阿耨达山是崑崙山。释云:赖得调《传》,豁然为解,乃宣为《西域图》,以语法汰,法汰以常见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释云:复书曰:按《穆天子传》,穆王于崑崙侧、瑶池上觞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涧,万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调言?子今见泰《传》,非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后,乃知崑崙山为无热丘,何云乃胡国外乎?
郦道元不厌其烦地引用佛家之语为注文,显然是被当时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各种说法所困扰,而多次强调路途遥远,难以亲临考察。然而即使如此,郦道元还是抱持客观中肯的态度,注文提到:“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又,“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阗二水之限,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郦道元虽然未必相信佛家之语,但是以征实的史家注语而予以记录。其中所反映的现象是:佛教经典的中土化策略,以及对于文化昆仑的运用和意义方面的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教传播的推广与深化,“昆仑”或“崑崙”的意义又似乎另有发展。宋代《太平广记》收录唐代裴铏《传奇》中的名篇《崑崙奴》,多数学者认为“崑崙”是唐朝人对印度半岛与南洋群岛的泛称。其实前文引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就已经可以看出两点重要迹象:其一,凡经由西域抵达的地方,都属于“西方”,都与昆仑、崑崙山有关;其二,“天竺”在西方,而不是今天所认知的南亚或东南亚。东晋高僧法显所说的“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则或可证明当时中华文化传播、东西方交流的情况。这应该都与通西域、走丝路的发展,以及佛教东传的路径有关。
另外,郦道元《水经注·温水》的注文还引用《林邑记》,提到两条资料:“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弥之征林邑,阳迈出婚不在,奋威将军阮谦之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已过四会,未入寿泠,三日三夜无顿止处,凝海直岸,遇风大败。阳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谦之遭风,余数船舰,夜于寿泠浦里相遇,闇中大战,谦之手射阳迈柁工,船败纵横,崑崙单舸,接得阳迈。”又引《林邑记》:“汉置九郡,儋耳与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亵露,不以为羞。暑亵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然则儋耳即离耳也。”林邑国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其船只被称为“崑崙单舸”;当地人“以黑为美”,应该是“占人”,属于广义的马来人。《晋书·后妃传下·孝武文李太后传》:“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崑崙。”[注]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81页。《旧唐书·南蛮传·林邑》也提及“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崑崙”[注]劉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0页。。所以唐人小说《崑崙奴》记载:
时家中有崑崙磨勒,……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发如旧耳。
其中的崑崙奴磨勒,应该就可以理解为南亚人或东南亚人。[注]今越南东南方有昆仑群岛,距胡志明市120海里,由十六座小岛组成,可能出于华人命名。而磨勒的武艺高强,十余年后容发如旧,颇有神仙异人的形象,即是对于西方他界想象的具体结果,一如《列子》中的“化人”。唐人认为西南有地理崑崙,当时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
《括地志》云:“又阿傉达山亦名建末达山,亦名昆仑山。恒河出其南吐师子口,经天竺入达山。妫水今名为浒海,出于昆仑西北隅吐马口,经安息、大夏国入西海。黄河出东北隅吐牛口,东北流经滥泽,潜出大积石山,至华山北,东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万里。此谓大昆仑,肃州谓小昆仑也。《禹本纪》云:‘河出昆仑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
以至于宋代将唐代位于西南的“南雄关”,即宋代广南西路所属,易名为“崑崙关”。[注]南雄关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建关城,命名为崑崙关。因关隘名称为“崑崙”,所以直至今日,当地人仍称关隘所在的台地为“崑崙山”。民间流传有狄青“三鼓夺崑崙”的故事,出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狄青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崑崙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燕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崑崙矣。’”见于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1939年,发生抗日著名战役的桂南会战“崑崙关战役”,即在此地。若以佛教传播的路径区分,陆路的部分属于西北崑崙;海路的部分,则是西南崑崙之说的主要原因。
五、结 语
现代学者在推论“昆仑”或“西王母”,多由卜辞的“东母”“西母”为开端,实际上对于“东母”“西母”的解释还有一些讨论空间。从目前对于殷商时期的活动区域来看,即使对于西方有所想象,也应该不至于以汉代所知的西域之地为圣域。
《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注]陈奂:《诗毛氏传疏》,中国书店,1984年,中册诗二十三,第36页。周人以蕞尔小邦,能够战而克商,因而利用殷商所信仰的上帝,说明上帝的天命是可以更改的,商人因为失德,不再为帝命所眷顾,帝命乃转而西向,周人遂得以统治天下。其反映的是“中商”与“西周”。
随着周人势力由西往东的发展,以及世界观的开阔,周人一方面继承殷商的神话与信仰,并形成更大的空间分布;一方面到了东周以后逐渐出现五方、九州岛等等的空间认知,而西方也因天体东西走向,东方为海所断绝的缘故,西方遂以“昆仑”为主体,表现于《山海经》,构成文化昆仑的神话体系基础。而《山海经》中仅《海内北经》出现“蓬莱山在海中”的记载,很难判断当时的具体内容。“昆仑”之所以成为仙乡,《淮南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后有纬书如《河图括地象》之类的观念继承与深化,包括昆仑居中的说法。所以,“昆仑”一词自始至终都有与我界不同的“他界”意义。《穆天子传》《列子》的相关说法,则是通过我界与他界的特殊联系,显现出对于昆仑、西方的想象和理解。
张骞打破了汉人对于西域的迷思,却又因佛教的东传使“西方”又沾染了神秘的色彩。在我界与他界之间,由文化昆仑逐渐递转为地理崑崙。若从真实地理的角度考察,则有“黄河河源”和“域外接壤”两种不同的思路。以黄河河源为崑崙所在,一直到清代的官方立场都是如此。较为特殊的是佛教东传、中土化的过程中,崑崙山成为天竺佛国位置的参考坐标,甚至将崑崙山视之为佛教圣山的须弥山、阿耨达太山。也因此在“域外接壤”的思路中,西北崑崙之外多出了西南崑崙之说。西南崑崙的出现与佛教传播的路线有关,致使西北昆仑的圣性与他界的意义转嫁为西南,而有地理上视南洋诸国为昆仑的说法。
综观而论,昆仑文化确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单元。其经由历代不同时期的意义演变,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昆仑面貌。唯一不变的是,对于中原本位而言,“昆仑”始终是关于“他界”与“异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