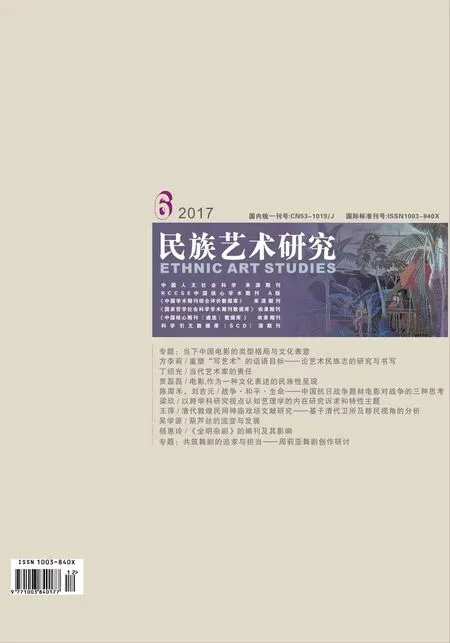汉画像的空间叙事:问题及论域
温德朝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创造和传承文明的重要途径。叙事的历史悠远,自人类诞生至今,先后经历了口传、结绳、刻锲、图像、文字、多媒体等不同叙事方式的嬗变。可以说,我们对叙事探索的脚步从未止息。叙事的媒材广泛,声音、手势、绘画、小说、戏剧、影视……但凡我们能够看到或想到的事物,均可成为叙事的媒介。罗兰·巴特曾说:“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1)[法]罗兰·巴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张寅德选编 :《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从深层上讲,叙事即通过讲故事或类似于讲故事的观念传达来抗拒遗忘,在始源上统一于时间和空间两种“先验的形式”,二者彼此不能离开对方而单独存在。但囿于讲故事的因果性、连续性、链条性特征,人们在筛选叙事媒介时更青睐优于表现时间的文字文本,而忽视或遮蔽了偏重表现空间的图画文本。随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空间转向”的到来,人们重新认识到叙事学领域不仅存在处于显性和中心的时间叙事传统,还存在处于隐性和边缘的空间叙事传统,积极推动重构叙事格局以还原其真实性和丰富性。汉画像作为典型的偏重空间叙事的礼仪美术,是汉人对死后身体的安置和“另一世界”的构想,在相对固定的图像程式中生产着汉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此,我们尝试以汉画像为观照对象,以国际流行的空间叙事理论为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汉画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追溯话题源流,厘定基本论域。
一、汉画像空间叙事的话题缘起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统一、稳固、进步的启蒙大叙事越来越受到质疑,断裂、偶然、即时的反启蒙小叙事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意味着后现代哲学迎来了“时间的碎片化”和“空间的时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认为,后现代社会极度压缩时间、扩张空间,“互联网+”、地球村的出现使人类的空间感知、空间体验、空间把握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后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是一种空间化生存。福柯也曾断言,后现代或许是空间的纪元。“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2)[法]米歇尔·福柯 :《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 :《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他从知识谱系和权力控制的关系来分析空间问题,对照“乌托邦”发现了“异托邦”这一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空间”。巴什拉提出了“想象力的现象学”,他的《空间的诗学》从知觉现象学和象征隐喻功能出发,分析了家屋、抽屉、巢穴、贝壳、角落、圆形等幸福空间的原型意象。这些内部空间或场所,以心理体验的形式悬置了时间,存在的意义在想象力中不断被发现、补充、丰富。如果说巴什拉的研究偏向家宅内部空间意象分析的话,那么,大卫·哈维、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寻求建构更加开放的空间体系,拓展了空间叙事的社会政治维度。苏贾陆续出版了“空间三部曲”,他在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认为“第三空间”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既包含二者又超越二者。他特别关注空间建构中的阶级、性别、种族等权力关系,试图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推动建构一个无限开放的具有颠覆力量的空间。我们知道,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方法论,受哲学空间转向和空间思想的影响,叙事学领域的空间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在文艺叙事领域,最早关注空间问题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他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首次提出并论述了“空间形式”。他认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中的时间因素。”(3)[美]约瑟夫·弗兰克等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小说,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倒置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截断了叙述的时间流,具有空间化特征。弗兰克从两方面阐释了他的“空间形式”理论,从创作主体上说,作者往往通过意象(暗示、象征、短语)并置、主题重复、章节交替、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在同一时间展开不同层次上的行动和情节,从而结成一个叙事整体;从接受主体上说,读者必须在整体上认知和接受一部空间形式的小说,在与整体联系中去理解不同的空间意义单元。弗兰克的这篇原创性作品激发了人们的思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以詹姆斯·M.柯蒂斯、戴维·米切尔森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空间形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小说对时间和顺序的摒弃、对空间和结构的偏爱,为现代小说批评创造了新的理论范式。以菲利普·拉弗、罗伯特·魏门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空间形式”存在对历史和时间否定的嫌疑,削弱了思考的深度,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面对理论界的不同声音,弗兰克最终在《空间形式:对批评者的回答》一文中作出了回应。他坚持认为,一是“空间形式”是现代小说独有的现象,现代小说需要空间地去理解;二是强调“空间形式”,并非要将空间和时间割裂或摒弃时间,而是要建立一种空间的文学分析框架。弗兰克之后,文学叙事与空间理论在碰撞交融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内容层面的空间,一方面“关注小说对现实空间的表征,以及小说中建构的地方与空间。”另一方面“关注小说叙事中空间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4)方英 :《小说空间叙事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国内空间叙事研究是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张世君把《红楼梦》叙事的空间类型划分为实体的场景空间、虚化的香气空间、虚拟的梦幻空间,深入考察了“门”的叙事功能、香气的空间定势与韵调、梦幻对现实空间的颠覆作用等。龙迪勇《空间叙事学》指出,小说、戏剧等偏重时间维度的叙事文本,存在着时间的空间化问题;绘画、雕塑等偏重空间维度的叙事文本,存在着空间的时间化问题;电影、电视等时空兼重的叙事文本,存在着在空间中获得新的阐释活力的问题。他在全面考察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图像文本的跨媒介空间叙事、历史文本的跨学科空间叙事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叙事理论构架。方英《小说空间叙事论》认为,所谓叙事的“空间化”,是指以空间秩序和空间逻辑来统辖作品,其中“关系性”和“建构性”是其核心。表达层面的空间化强调小说叙事的块状化、立体化、非线性发展,通过并置、碎片、迷宫等艺术手法,在不同叙事元素之间形成空间性关联。内容层面的空间化强调小说虚构世界中空间的凸显,这些空间具有图像性和视觉性,隐含着物理、心理、社会、文化等不同的审美功能。孟君在《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中,深入论述了中国当代电影中城市、小城镇、乡村三类叙事空间中蕴涵的丰富表意内涵、美学因素和社会学价值,初步建立起中国电影空间叙事的研究体系。此外,还有一些成果对空间叙事理论在具体作品中的实践运用做了分析。
以上,我们不惜花大量篇幅来追溯空间叙事的历史源流,从中可以充分认识到:一是空间存在和空间问题是当前国际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流行观点及未来趋势,席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无视空间向度紧迫性的任何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其结果就是导致对一个故事的性质的过分简单化。”(5)[美]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页。二是空间叙事的理论适用性、渗透力非常强,具有跨学科、跨媒介的特性。“在可以直接体验到的真实生活空间和由符号组成的概念化的想象空间之间,包括诗歌、小说、电影、绘画、建筑在内的空间文本是还原物质空间和理解社会空间的重要介质。”(6)孟君 :《中国当代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页。一个有创造力的画家,“总是能以图像这么一种空间性媒介来达到叙述事件、表现时间的目的,而这也正是我们‘空间叙事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7)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03页。同时,我们在艺术史研究中亦发现,与偏重听觉与时间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古典文化在对视觉和空间的探索上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视觉性的“象”思维、图像思维。中国古代叙事文本中的章回小说、庭院建筑、古典园林、叙事性图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性特征。从汉语词源学上看,叙事也带有很强的空间色彩。古汉语中,“叙”通“序”和“绪”。“顺序,绪也,古或假序为之。”《说文解字》释“序”曰:“序,东西墙也,从广。”“广,因厂为屋也。”“序”的原意为房屋间的隔墙,即指向空间。《说文解字》释“绪”曰:“绪,丝耑也,从系。”(8)[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442、126页。段玉裁注释说,剥茧抽丝以“绪”为端引,凡事得“绪”方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以,空间叙事,即是研究空间的次序和故事的头绪。基于此,我们认为:第一,汉画像作为偏重空间维度的叙事文本,对其研究应紧跟国际理论热潮和重回中国古典叙事传统,不能漠视或淡化画像艺术的空间叙事探索。第二,以空间理论为指导,广泛借鉴小说、电影等领域的空间叙事研究成果,深入系统地开展汉画像的空间叙事研究,是紧迫、必要且可行的,或潜藏着范式创新的可能。这是我们尝试深入开展汉画像空间叙事研究的文化背景和意义之所在。
二、汉画像空间问题的研究现状
汉画像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等各类图像资料,是图绘世界的浓缩的“绣像汉代史”。秦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大一统,当其时外来文化尚未传入中国或东汉末佛教文化刚入中土尚未激起多大反响,故而汉画像是最能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原生艺术形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全国共发现或发掘汉画像石(砖)墓200余座,出土汉画像石(砖)超过10000块,出版汉画像图录、专著200余部,发表汉画像考古发掘报告、论文2000余篇。汉画像研究先后经历了金石学、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四种学术范式,(9)朱存明 :《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学者们重点围绕汉画像的地域分布、历史断代、艺术风格、图像考释、宗教信仰、文化功能、美学精神等展开了深入探讨。但直到近年,汉画像的空间问题才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是美术史的“空间转向”与汉画像的“位置意义”。墓葬艺术的空间整体性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当我们以单个石刻画像或拓片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其在墓葬空间中的位置安排和相互间的配置关系就无形中消弭了。美国学者费慰梅在复原武梁祠建筑原型时特别指出,应特别注重汉画像空间布局的“位置意义”。美国学者巫鸿是美术史研究“空间转向”的先行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他在早期研究中使用了不少与“空间”有关的概念和词汇,如礼仪美术中的“阈界”、绘画图像中的“女性空间”、视觉文化和公共仪式中的“政治空间”、汉画像中的“位置意义”、墓葬布置中的“层累”、绘画和雕刻中的“正反构图”等。2018年出版的《“空间”的美术史》是他对上述研究的统整和深化。他指出,“空间”在传统美术史写作中经常出现,但没有像“图像”和“形式”那样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积极倡导以“空间”为核心的描述和解释框架。他从图像分析中发展出三个空间概念:一是“视觉空间”,即绘画再现中对空间的表现和感知。二是“图像空间”,即图像中的空间表意结构。三是“位置空间”,即画家通过画面构图来决定绘画和观看的逻辑,形式和意义在这里混合叠加。“空间分析”的美术史研究意义在于,空间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图像、雕塑、器物和建筑这些美术史材料的传统类别划分”“可以帮助我们将注视点从孤立地图像和作品(works)转移到图像间和作品间的关系上”“可以帮助我们连接和综合艺术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前者为艺术品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后者为艺术品产生和展示的条件和环境”。(10)[美]巫鸿 :《“空间”的美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巫鸿还在《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等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墓葬具有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特征,并从整体上阐释了武梁祠画像的图像配置和文化意义。此外,崔雪冬的《图像与空间——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与建筑关系研究》,在墓葬礼仪空间整体环境中考察了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图像、形制分布、组织形式。
二是汉画像的图像叙述形式与配置规律。从叙事的意义上讲,汉墓是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汉画像是汉墓这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画像依托墓葬建筑空间存在,遵循约定俗成的礼仪化图像程式,以独特的图像语言和图像呈现,为逝者的灵魂营建一座体象天地的宇宙寓所。李立《汉画像的叙述》在考证释读图像的基础上,采用传统考据学与现代大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认真总结了汉画叙事的图像模块配置规律。他认为,在汉代墓葬成熟的室墓建构模式中,形成了为逝者构拟“彼岸世界”的主题叙述形式。墓葬内部空间设计及随葬品的置放形式,在叙事意义上构成了“彼岸世界”的“实体叙述”。汉画像正是借助“虚拟叙述”的形式,从物质和精神的不同维度对这种“实体叙述”给予补充、拓展和完善。另外,画像的叙述往往是观念的表现而非事件的再现,其图像的编排与连接,依靠的是观念的展示而非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链条。美国学者孟久丽在《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中完整勾勒了中国古典文献与叙述性图画的关系史,认为武梁祠中名臣雅士、贤淑女性的题材及艺术表现手法,集中展现了前佛教(佛教盛行之前)叙事性绘画的审美特征。唐琪《沂南汉墓——东汉图画艺术中的叙事和仪式》结合案例探讨了图像叙事、葬礼仪式、空间方位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墓室空间通过图像的遴选和配置实现了叙事性话语的传达。
三是汉画像的空间构图与时间转化艺术。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空间文本向时间文本的转化。以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图像要想达到叙事的目的,必须重建或恢复故事的上下文语境,接通事件的因果序列和时间流。李征宇的《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考论》《顷刻与并置:汉画叙事探赜》认为,汉画像具有“取诸经史”“语图互文”的叙事特征,而把握“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展开构图和并置重要场景与事件,是其最主要的两种构图方式。李彦锋《论汉代绘画与决定性倾间的选择》认为,历史故事类画像的刻绘是通过选择决定性顷间来实现的,对事件发展过程中关键动态的把握至关重要。以荆轲刺秦王画像为例,高明的画工并没有选择故事的开端或结局,而是非常巧妙地选择图穷匕见、荆轲行刺、秦王环柱走的顷间进行刻画,进而将图像“定格”于顶点之前的高点,包蕴了整个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曹建国、张洁《石头上的叙事解码——从汉画“完璧归赵”看图像叙事》一文认为,汉画像的图像叙述依历史文本而存在,需要在图像与文献典籍的互文对比中进行观照,才能把这些仿拟现实的图像故事还原成叙事代码。画像叙事结构充满张力,总是试图寻觅突破有限空间框架束缚和制约的可能,努力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时间和形象的流动。朱浒根据图像逻辑层次,将胡汉战争图的叙事分为两类。一类以“狩猎—出行—战斗—献俘”的时间进展场景为序构图;一类通过“桥”“楼阙”“山包”等将画面分割为若干意义迥异的空间,在不同空间中构建各自的情景。上述成果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关注类型化图像的讨论,缺乏对其整体视野的观照。
汉民族有两条叙史传统,一条是文字的,一条是图像的。我们在仔细盘点、检视现有成果中发现,传统叙事研究往往将汉画图像与墓葬整体空间布局割裂开来,遮蔽、隐匿或破坏了汉画像存在的空间原境。且关注视觉层面的构图空间较多,主要是雕刻技法、构图比例、画面视角、色彩线条等方面的探讨;关注作为汉代社会生产图像空间的较少,对图像所寄寓的汉人的宇宙认知、丧葬观念、精神信仰、道德镜鉴、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等挖掘不够;过于关注作为物的存在属性的物理空间,尚未建立起以空间为核心的描述和解释框架,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总而言之,“空间”不是汉画像的辅助元素,而是根本的叙事元素和表意元素。“空间”蕴含着思想价值和文化符码,空间叙事研究是对汉画像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汉画像空间叙事的基本论域
空间不仅是物质和形式的存在,也是容纳社会关系演变的器具。在汉画像的各种叙事元素中,画像空间是还原物质空间和理解社会空间的重要介质。我们认为,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考察汉画像艺术,主要是把它作为物理空间、图像空间、美学空间来进行分析,深入探究汉画叙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文化内涵和美学精神,即画像文本如何以及为何呈现汉代社会。巫鸿在《东亚墓葬艺术反思: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提案》一文中总结说,墓葬艺术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侧重于丧礼和埋葬过程研究,另一种侧重于墓葬内部空间性的研究。显然,汉画像的空间叙事研究属于后者,即“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墓葬设计、装饰和陈设中隐含的逻辑和理念,阐释这些人造物和图像所折射出的社会关系、历史和记忆、宇宙观、宗教信仰等更深层面的问题。”(11)[美]巫鸿 :《时空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6页。汉画像的空间叙事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论域展开。
一是汉画像叙事的空间思维。战国末年“礼崩乐坏”,诸侯僭越礼制的事件时有发生,传统礼制开始松动。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魂魄、生死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祖灵祭祀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在祭祀的内容、形式、对象等各个方面。传统上以宗庙“尸祭”为主的祖灵祭祀渐趋式微,在墓地上向逝者个灵祭祀的坟墓祭祀开始兴起。配合着祭礼的变化,注重与外界隔绝的密闭型竖穴椁墓显现出“开通”意识,先后在椁内间隔板上开设方孔、装饰门框、设置模造门扉,最终在西汉初年定型为由羡道、玄门构造、祭祀空间、埋葬空间等组成的开通型室墓。黄晓芬将其概括为汉墓形制嬗变的“三阶段说”,即从“椁内开通”到“向外界开通”再到“祭祀空间的确立”。(12)黄晓芬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0-72页。葬者,藏也。秦汉之际汉墓形制变化是以魂魄思想嬗变为动力的。先秦人认为,人死阴阳两隔,墓以藏魂,通过密闭的墓葬间隔,让生死两界互不干扰。秦汉人在升仙思想的驱动下创造出了一个介于天界和人世之间的神仙世界。他们认为,人由魂、魄二气聚合而成,气聚而生,气散而亡。人死之后,魂气归天升仙,魄气归地变鬼,但魂可自由往返于天地之间,随时返回墓穴、人间接受宗亲献祭。为便于墓祭的实施、灵魂的出入,迫切需要开通的、扩大的墓葬空间,这也为汉画像产生、繁荣创造了条件。整体来看,一个独立的墓葬空间就是一个缩微的宇宙。汉人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仿生建造地下宅第,在墓室、祠堂、棺椁画像上创作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宇宙象征图式。巫鸿通过对武氏祠画像的图像志考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规律。“这座小小祠堂能够使我们形象化地理解东汉美术展现出的宇宙观。其画像的三个部分——屋顶、山墙和墙壁恰恰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13)[美]巫鸿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2页。可见,成熟期汉画像的空间方位配置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阴阳五行思维逻辑展开的。其中,墓室、棺椁画像以墓主为叙述中心,祠堂画像以祭拜者为叙述中心,四方图像围绕中心辐辏配置,以此与中心产生种种联系和发挥“幽墓既美,鬼神既宁”的功能。在出土画像中,山东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题记、宋山祠堂画像石题记等,均有明确的指向性记载。
二是汉画像叙事的空间类型。汉画像是一种墓葬礼仪和装饰性图像,几乎所有画像在讲述生死故事、定格动作造型、建构主体形象、推动情节展开等方面,都有相对稳定的表现程式。从画像创作主体看,有死者生前预先设计的,有家人朋友代为设计的,有画工依据流行粉本格套制作的。从叙事空间类型看,可分为神圣化空间、公共性空间和私人性空间。神圣化空间是汉人对躯体魂魄的安置,是关于“死后要到哪里去”的审美想象。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雷神、风伯、羽人,以及大量出现的祥瑞图谶符码,蕴含着汉人永生、长生、超生的美好愿望。汉代社会普遍弥漫着升仙思想,人们对仙界充满了向往,千方百计追求升仙。《乐府古诗·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天华,揽芝蒦赤幢。”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体现。洛阳西汉卜千秋墓顶壁画,描绘了男性墓主乘神龙、女性墓主御仙凤,二人经由持节方士的引导和各种天界神物的协助,“超越大限”、飘然升仙的情景。人物乘龙御凤是灵魂升天的象征,《楚辞》描绘了诸多“驾飞龙、历天堂”的场景,传说黄帝也是乘龙升仙的。墓主乘龙御凤升仙的画面,暗含着生命在不同时空中转化的过程,空间转换带动了时间延续,完成了故事的讲述。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和朱地彩绘四重木棺,也通过虚拟象征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诠释了驱鬼辟邪、引魂升天的过程。公共性空间是汉代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孟久丽《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认为,中国古代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统治阶层,常常从历史典故、文学作品、时事政治中选取一些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题材,并通过制作、使用、褒奖这类主题的绘画来规训社会群体和操控社会秩序。汉画像中的高祖斩蛇图、泗水捞鼎图、胡汉战争图等,宣扬了汉王朝代秦而立的正统与皇权,确立了宾服四夷的中心与威势;明君图、忠臣图、贤士图、孝子图、烈女图等,具有鲜明的道德指向、礼仪规范、礼仪规训功能;农耕图、射猎图、市井图、庖厨图、宴饮图、乐舞图等,集中描绘了汉代日常生活图景和汉人恋生乐生的积极心态,是汉人的日常生活叙事。私人性空间是对墓主个人经历、个性偏好的叙述。徐州贾汪青山泉一号汉墓曾出土一幅“缉盗荣归图”,该图画面展开长达8米,详细记录了由审讯囚犯、押解囚徒、村口迎接三个场景组成的完整故事。据推测,墓主身份可能为官秩四百石的县尉。根据汉代“捕盗律”规定,捕盗有功者可加官晋爵,可能墓主生前因此得到表彰升迁,特别将这一显耀经历镌刻在墓室中。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就对墓主从“举孝廉”“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时”“繁阳令”“雁门长史”“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宦经历进行了长卷式的精彩叙述。汉画像的叙事空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在题材内容上出现了神话、现实和历史三种图景相互交融的特征”。(14)徐文菲 :《略论汉代绘画与两汉哲学思想》,《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比如,私人性空间对墓主道德功业的标榜,正是公共性空间对个体规训的希冀和结果,而此二者又是顺利跻身神圣化空间的前提。
三是汉画像的空间叙事意象。汉画像构图中的一些空间意象,是空间叙事的分节点,它们分中有联、联中有分,具有空间分割与叙事离合、空间衔接与叙事贯通、空间转换与叙事栖止的功能。画像中数量众多的门(阙)、桥、山图像,或具有实指功能,以物理实体形式推动画面自动转换和叙事自然转折;或具有象征功能,往往象征着天门、奈何桥、昆仑山系(蓬莱山系),它们是通往天界、仙界、人界、鬼界的显著标识,推动升仙叙事逻辑展开,从而形成整齐连贯的宇宙象征图式。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西壁画像第四层有一幅榜题“胡王”的“胡汉战争图”,画面右侧层峦叠嶂,大批胡兵隐觅其间。作为物理存在的山峦,在叙事空间上自然分割了东方与西方、汉军与胡虏、胜利与失败、文明与野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T形帛画的天门图像,跨越画面构图纵横两个部分。其中,横向部分象征天界,人首蛇身的大神烛龙居中,右上方是荷载金乌的太阳、翼龙和挂着八个小圆日的扶桑树,左上方是由盛装女子擎托的新月、蟾蜍和玉兔,此外还绘有两神兽牵拉悬铎。纵向部分上部象征人间,刻一华盖和一大鸟,华盖下是拄杖缓行的老妇人侧面像,两侍者前方跪迎,三婢女随从其后。正是因为有了天门的存在,人神两界才得以贯通,门外俗界、门内仙境,并置的空间重新续接了一度被斩断的时间流、故事流。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山东苍山元嘉元年汉墓画像均绘有车马行进在桥梁上的图像,桥梁上方榜题“渭桥”或“卫桥”(“卫”通“渭”),这正是漫漫升仙征程中跨越人间和黄泉的空间标志。苍山汉墓还刻有题记注释,“上卫桥,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簿,亭长、骑佐、胡使弩。下有深水多渔者,从儿刺舟渡诸母。”(15)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据史料记载,渭水是汉代著名的地理标识,从西汉皇都长安城以北流过,北岸的都城和皇陵以此为界分割开来。汉初帝陵大多选址渭水以北,然后在渭水上建桥联通都城和陵寝。当皇帝去世发丧时,文武百官和宫廷卫队护卫着死者从桥上通过,渭桥因此成了通往死后空间的必由之路。用分节概念来考察汉画像空间叙事的衔接与转换,旨在明确叙事场景内外交替、过渡的临界处有明确的标识,在叙事进程中充当了不同场景间转换的分节符。
四是汉画像的空间叙事艺术。尽管叙事统一于时空两个坐标轴,但不同媒材在表现时空上确实有偏差。莱辛通过对不同媒材塑造拉奥孔形象的分析,提出了“诗画异质”说,进而断言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是空间艺术、以诗为代表的文学是时间艺术。陆机对比丹青与雅颂之界限曰:“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16)俞建华 :《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然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说,上古书画同体而未分,圣人仰观俯察、比类取象,为表意故有书,为赋形故有画。又认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17)[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确实,就叙事艺术发展史来看,人类或出于创造性冲动,或出于创新性追求,常常突破单一媒材的限制,不同媒材经常超越自身表现性能而挺进另一种媒材领域。汉画像介于建筑、雕塑、绘画之间,又“取诸经史”“语图互文”,具有鲜明的“出位之思”和跨媒介叙事的艺术特征。画像构图空间先后经历了从固定格套到突破格套、从单一视角到混合视角、从平面叠加到斜边错位的嬗变过程。画像作者往往利用观者谙熟文本故事和图像格套,通过顷刻式叙事、纲要式叙事(并置)、循环式叙事(连环画)等,来调动观者的想象力,从而达到将空间时间化并延展时间、满足审美期待视野的叙事目的。这一过程,即是“利用‘错觉’或‘期待视野’而诉诸观者的反应;利用其他图像来组成图像系列,从而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事件流。”(18)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页。武氏祠画像的叙事技巧极其高超,有单幅图像通过顷刻或并置来叙述某一特定历史事件,从而形成简单的叙事单元,如孔子见老子、豫让刺赵襄子、秋胡戏妻等;有多幅图像连贯叙述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从而形成的复杂叙事单元,如荆轲刺秦王等;有上述以历史时间为序的不同叙事单元并置形成的叙事模块,如古帝王圣贤序列、忠义勇士序列、节烈妇女序列等;有若干叙事模块并置形成的叙事整体,即图像版《史记》。从汉画像的故事来源来说,有图像模仿文本、图像文本互仿等不同类型,不同时代、区域、工匠创作的汉画像,对“具有包孕性”的顷刻和故事情节片段的选择并不相同,即图像叙事常常僭越或溢出文本叙事,但这并不影响观者正常接受。
统而论之,我们倡导开展汉画像的空间叙事研究,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积淀,也有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推动;既有文学与影视空间叙事研究的借鉴,也有前辈学人的探索启示。但是在学术研究范式创新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恪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原则。一是应注意解决好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理解空间历来是个哲学难题,以发源、流行于西方现代的空间叙事理论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汉画像艺术,要特别注意理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问题,找准话语结合点和阐释的限度。二是应注意解决好研究的交叉性问题。如何以美术史研究“空间分析”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阐释清楚汉画像空间叙事的问题和论域,全面把握汉人关于死后世界的意义言说和生命理想,需要坚持文献资料、画像榜题、图像格套“三位一体”,以及较强的美术考古、图像阐释和理论思辨能力。三是应注意解决好学科的汇通性问题。空间叙事理论在现代小说、影视文学研究方面展现了独特的理论优势和话语活力,如何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来深化汉画像研究,既要找准普遍共性,又不能忽视个性特色。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将当今国际艺术学界流行的空间叙事理论与最具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形态之一的汉画像研究相对接,在辨析源流和厘定论域的基础上,把汉画像研究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