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的防洪效益是无可替代的
谷宝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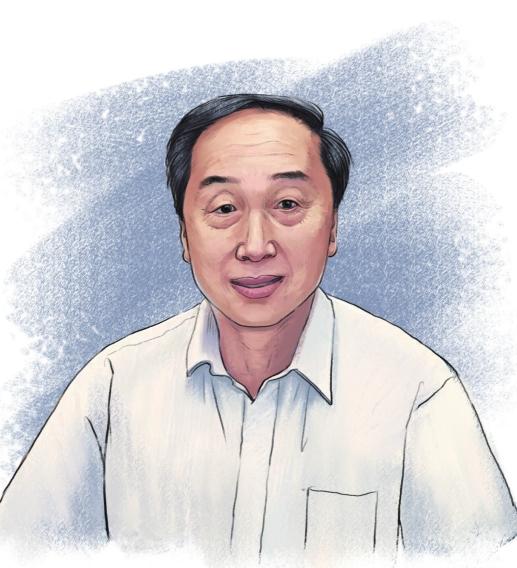
“自宜昌以上……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19年,孙中山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首次提出了在长江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工程的设想。
在一次演讲中,他兴奋地说“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
100年后的今天,孙中山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
但外界对三峡大坝工程的关心和疑问从未停止,近来有关“三峡大坝变形”的谣言,也惹得舆论一度纷乱。
三峡大坝的功能和实效究竟如何?是否还存在没有明言的隐忧?
带着这些社会关心的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86岁的陆佑楣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电力部原副部长、中国三峡集团首任总经理、中国大坝委员会原主席。
集学者、工程师、管理者、经营者于一身,他的名字已与三峡工程联系在了一起。
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不会变
南风窗: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防洪。但有人认为,三峡是为发电而建的,修建三峡的人是看重它的发电功能和经济利益。
陆佑楣:三峡同时存在多方面的效益,防洪、发电、航运,乃至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防洪。
之所以讲防洪效益最關键,是因为它是最无可替代的,发电可以有火电、核电,但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什么其他措施能拦蓄这么多的水量呢?
洪水的本质是人和水争夺陆地面积,人要有空间来生存和生产,水要空间来容纳自身,这就会起冲突。
一种办法是分洪,20世纪50年代修建了荆江分洪区,相当于洪水来临时牺牲一些农田来保护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每启用一次就要把40万百姓安置在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一平方公里2万多人,这是多么拥挤的生存空间!而且分洪一次也必将恶化环境、毁坏作物、诱发多种疫情,这是多么大的人间灾难!
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上千里长的荆江大堤再加高加固,但显然经济上代价更大,技术上也很困难,当时论证认为并不合理,所以只能靠水库来容纳。从三峡工程建成多年来的运行效果看,它能控制荆江河段洪水来量的95%以上,控制武汉以上洪水来量的2/3左右。
截至2018年底,累计拦洪运用47次,总蓄洪量1440亿立方米,有效拦蓄了上游洪水,干流堤防没有发生一处重大险情,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三峡的防洪效益是无可替代的。
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三峡发电的效益也不能简单说成是“经济利益”,水电本身不消耗水、不污染水,同相同数量的火电相比,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三峡电站历年累计发电量相当于替代燃烧原煤5.9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亿吨、二氧化硫排放1180万吨、氮氧化合物排放437万吨,对减小气候变化压力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它的发电功能也有生态效益的内容。
南风窗:当年孙中山提出设想时似乎更看重发电和航运效益,而不是防洪。
陆佑楣:孙中山确实是考虑要发电、要改善航运,后来国民党在重庆时请美国专家萨凡奇去实地考察过,国民党是希望用三峡的电力生产化肥,用利润来偿还美国的借款。
把防洪任务放在首位的是中国共产党。刚建国那几年,长江连年发大水,我当时在南京的河海大学(当时叫华东水利学院)读书,师生们下课也要到大堤上扛沙袋,防止江堤决口。
1954年那场大洪水夺去了3万多人的生命,1800多万人受灾,320万公顷耕地受淹。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想法,之后历届领导人继承了这样的理念,并把它变成了现实。
今后三峡的任务还是把防洪放在首位,这不会变,也不能变。
争议的问题中有些客观存在,有些则违背科学常识
南风窗:有网友收集了报道三峡的新闻题目,先说“三峡可以抵抗万年一遇的洪水”,后来又说是“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仿佛三峡的防洪能力变来变去,三峡的防洪能力下降了。
陆佑楣:之所以有这种报道上的混乱,主要是因为水利专业术语,如果用日常语言描述,就会太笼统,出现概念混淆。关于三峡工程“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描述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即“救人”的能力,另一个维度是三峡工程自身的防洪能力,即“自助”的能力。
第一个维度防洪功能,即指的是三峡工程保证下游防洪安全的防洪控制能力,即帮助下游防洪的能力。当遇到不大于“百年一遇”(洪峰流量超过 83700m3/s)的洪水,三峡工程可控制枝城站最大流量不超过每秒56700m3/ s,不启用分洪工程,沙市水位可不超过44.5米,荆江河段可安全行洪。这也就是常说的“三峡工程的建成,使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当遇到“千年一遇”(洪峰流量超过98800m3/s)的洪水,经三峡水库调蓄,通过枝城的相应流量不超过每秒80000m3/s,配合荆江分洪工程和其他分蓄洪措施的运用,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从而可避免荆江南北两岸的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地区发生毁灭性灾难。
之所以讲防洪效益最关键,是因为它是最无可替代的,发电可以有火电、核电,但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什么其他措施能拦蓄这么多的水量呢?
第二个维度防洪能力,则是对于三峡大坝本体而言。三峡大坝建设的防洪标准是按照“千年一遇”设计、“万年一遇”加10%校核,即当峰值为98800m3/s的“千年一遇”洪水来临时,三峡大坝本身仍能正常运行,大坝各项工程、设施不受影响,可以照常发电;当遇到峰值流量为113000m3/s的“万年一遇”洪水再加10%时,三峡大坝主体建筑物不会遭到破坏,三峡大坝仍然是安全的,只是个别功能如发电、通航可能要暂停。
理清以上概念我们就能明白,三峡工程不存在所谓“防洪能力下降”的问题。
但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觉得有了三峡,整个长江流域就高枕无忧了。毕竟洞庭湖、鄱阳湖和汉江都在三峡的下游联通长江,如果这些支流的上游发生暴雨,还是可能引发洪涝。
所以支流也要建立自己的防洪体系—堤防、水库等等,城乡建筑的防洪标准也要提高,要修得坚固些。三峡是长江防洪体系的关键工程,但不是全部。
南风窗:三峡同时具备防洪和发电效益。要防洪,就不宜把水位蓄到太高,以免洪水无处存蓄;要发电,水位越高效益就越大。有媒体报道称三峡为了提高发电效益,运行的水位比较高,这是否会占用三峡的防洪库容,降低防洪能力?
陆佑楣:两种效益的权衡,就要在调度上下功夫,把防洪调度和兴利调度结合起来。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气象预报的精度,并把它利用好。
如果能够积累大量的降雨量数据,并用先进技术进行整合分析,通过降雨量来安排调控量,就可以作出相对有利的调度方案。
当然现在三峡的上游有了向家坝、溪洛渡这些水库,如果天气预报精度进一步提高,可以在中下游大雨来临之前,由上游水库提前向三峡水库放水,同时三峡也提前向下游放水,以此保证三峡防洪库容。
南风窗:有人担心,由于上游来沙量减少,三峡之水太清了,这会加剧下游的河道冲刷,使下游河槽變深,影响下游的河势。
陆佑楣:关于下游河床深切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它有一些好处:河道深切之后,水位下降,行洪能力更强;其次,水更深了,对通航有好处;此外,它延缓了洞庭湖萎缩的进程。
根据河流动力学原理,河床在冲刷到一定程度后会达到冲淤平衡,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不会无限下切。
南风窗:长江中有些岛屿是泥沙堆积形成的,有人说清水冲刷会使这些岛屿的泥沙被冲走,造成地貌变化,即“淘沙”现象。
陆佑楣:上海崇明岛就是长江的泥沙堆积而成,三峡蓄水之后改变了江水的泥沙含量,可能对崇明岛会产生一些影响,可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来加固,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南风窗:还有人担心,三峡库区蓄水后,水体流动速度减慢,自净能力下降,可能导致污染不能及时排出,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大,甚至会引发有害藻类蔓延滋长,即“水华”现象。
陆佑楣:水体污染问题的源头和要害在陆地上,不在工程本身。几千年来沿江两岸的百姓都向长江排污,三峡开工以来国家采取了很多的宣传和控制的措施,如果各种配套措施落到实处,是有可能减少对水体排污的总量的。
关于“水华”的问题,长江每年通过大坝的水量达4500亿立方米,而三峡的总库容仅393亿立方米,水库的水体不断地更替,平均每年更替十多次,水质富营养化程度是有限的,水华现象是可控的。
对于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社会公众关心的比较多,有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部分可以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加以解决。
当然也有一些就很荒谬了,比如诱发汶川地震、引发大范围极端天气现象、还有最近谷歌地图搞出的“变形事件”,这些就违背科学常识了。
南风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峡现在成了“航运瓶颈”,是这样吗?
陆佑楣:个别媒体紧盯着三峡的一些所谓的问题,拍照片、写文章,可千百年来荆江两岸洪水肆虐、百姓遭殃的惨状,没有太多影像和文字资料留存下来。如果大处着眼,权衡利害,那么对三峡的很多质疑就会不攻自破。
对于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社会公众关心的比较多,有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部分可以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加以解决。
把三峡说成是“航运瓶颈”,这完全没有比较三峡工程建设前后航运能力孰大孰小。
原来峡谷里河道窄、水流湍急,还有险滩礁石,好多都是木船在航行,要靠人力来拉纤,即使后来有了汽船,拉纤不常见了,但夜间还是很难航行,吨位也小。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航道可以24小时通航,船闸通航能力达到 1 亿吨,是建坝前的5.6倍。
船舶的拥堵现象恰恰是因为水运成本大大降低,同时重庆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太多船只穿梭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的结果,怎么能说是三峡工程造成了航运的瓶颈呢?
以人为本,改造自然
南风窗:三峡确实改变了自然本来的样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陆佑楣:认为三峡改变了自然,就是违背自然规律,这种观念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人改变的就是不好的,人不改变就是好的、原生态的。我不赞同!
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自然界也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被塑造的。三叶虫、恐龙,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留下了痕迹,那么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本身又何尝不是自然界漫长的演化变迁历史的一部分?
难道说洪水滔天、一片泽国的景象就是好的,只因为它是“原生态”的面貌?
要尊重人类的发展权利,发挥人类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能力,当然也要注重永续发展,尊重子孙后代的发展权利,这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矛盾的。
我非常欣赏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伯聪教授的一句话,他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改成“我创造故我在”。人不仅是思想活动的主体,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应当积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所以我说,我们也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三峡工程、认识中国的水利工程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