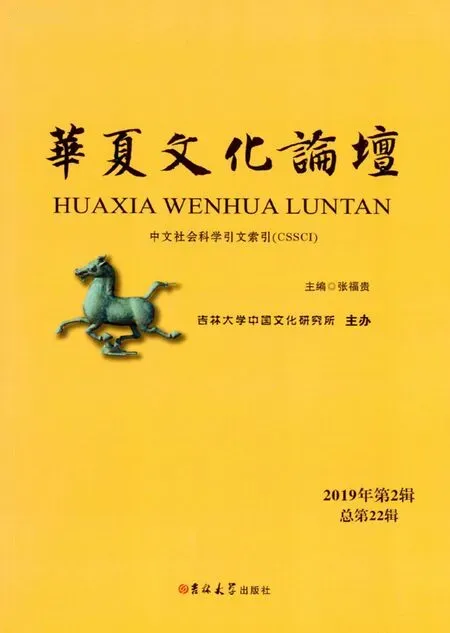晚清中日文人汉诗酬赠研究
——以广府文人与日人汉诗交游为中心
张奕琳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中日文人汉诗酬赠大为兴盛,参与其中的有不少广府文人。较之明治维新以前,此时的汉诗酬赠不仅数量增加、文学交流层次提升,且形式更为丰富、互动性增强,场域亦从中、日扩展至欧美。日人从江户时代追慕汉土,到明治维新以汉诗作为建构亚洲精神统治之利器,双方在酬赠中不再是文化主导与被主导的心态。中日文人汉诗酬赠的繁盛,是基于双方“同文同种”的心理认同,以及中日士大夫对传统文学评价取向、对士大夫趣味、对文学与事功并重的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标举。同时,也体现了日人的“兴亚”政治主张以及中国文人振兴国运的渴求。
诗歌酬赠既是文学创作形式,亦是人际交往方式,其兴盛、发展往往受交游活动影响。晚清(1840-1912)以降,国人与海外交往频繁,与日人交游者尤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同洲同文,尤足为我所取资借镜”,且“俗近而情洽,地迩而费省”,成为国人考察、学习之优选。除驻日使节外,还有大量清朝官员或普通读书人赴日考察、留学。与日人交游的文人群体、尤其是旅日官员中,有不少广府人士。梁启超曾言:“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学界对晚清驻外官员籍贯有所考察,认为因粤地民风早开、同乡相荐之故,驻外领事以粤籍为主体。广州府乘地理环境之便,得风气之先,其籍文人不少与日人有文字因缘,如被学界誉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广东南海人罗森(?-1900)。汉诗作为中日同文之体,又便于速就,且带文人雅趣,故成为双方建立联系、沟通感情最常用的文学载体,酬赠之风随之而兴。这类酬赠之作,虽良莠不齐,然颇可以见得中日文人或同或异的文学取向、文化心态、政治立场以及其时的社会思潮。本文以刘学询、黄璟、陈慕曾、关赓麟、金保权、许炳榛、潘飞声等广府籍文人与日人汉诗交游为例,考察双方汉诗酬赠的方式、内容及寄寓的诗家情怀、政治意味,以见晚清中日文人心态、文化交流之一斑。
一、世运更迭下的汉诗酬赠与文化心态
明治维新(始于1868)以前,尚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日人追步中土、矩矱汉唐。其时学者武川幸顺曾言:“(吾邦)礼乐政刑,无一而不资诸汉唐以为损益者,而其明经文章之选,亦惟无一而非金马玉堂之则也。故公卿大夫翕然皆用心于诗赋论颂,而若和歌,则其绪余也耳。”其时,士大夫所治学问为汉学,文学上亦以汉诗文为尚,能与中土诗家交往唱酬,被视为莫大的荣幸。然因德川幕府闭关锁国,交通遂绝,除间有来华或得遇个别赴日中国人者,与中土诗家交游并非易事,故一有机会,便紧抓不放。汉学家木下彪(1902-1999)状此风气云:“崇华之文人们,对能来长崎的清人紧捉不放,与之笔谈往复,请其正诗文、向其求书画,又请托商船以诗赠予彼乡之人,冀其赐和。更有甚者,还以与漂流到近海的清人会晤为荣。”近年学界有关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有关注《陈林诗集》者。这是一本潮州渔民因飓风漂流至仙台,获救后与仙台儒者志村五城等人汉诗唱和的诗集。时人岩垣彦明誉此举为奇事:“得诗友于异域,晨夕相唱读,可不谓之一大奇乎?”于此时风,木下彪讥之为卑陋可笑,然从另一角度看,亦可想见其时中日文学交流之贫乏,以及日人对与中国人诗赋交游的向往。
时风如此,故罗森日本之行大受欢迎。罗森以翻译官身份,于1854年随美国舰队赴日商议通商事宜。他是“1840年以后近代第一位赴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日本游记《日本日记》的作者”。罗森并非官身,名不显于时,考其流传下来的诗作,亦不见佳,在日却倍受追捧。据其日记所载,日人“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馀柄”。此外还有不少日人录诗见示。在日人记载美国舰队此行的日记中,录罗森诗若干,甚至还称其为“诗文之达者,亦书法之美笔也”。江户中后期兰学兴盛,日人对西方科学文化有所了解。加之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满清治下的中国已然夷狄化,中国中心论逐渐瓦解。但从罗森与日人的酬赠中,可见“慕华”与“攘夷”仍是明治维新前的主流文化心态。日人关研次赠罗森诗有“和议皆安仰赖君”句,对其翻译之功大加赞赏。但同时,日人又认为罗森习西语乃舍良取莠。罗森赋有七律一首赠日人明笃,抒发“乘风破浪平生愿”之抱负,便是回应明笃的疑问:“子乃中国之士,何归 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其时,大多日人对西方文明尚处于排斥态度,认为西人“唯利是趣,唯奇是趣,骎骎乎至于忘忠孝廉耻”,反而鼓励罗森游历四海以传播儒家之道,“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世运更迭,明治维新后,中日文人汉诗酬赠境况为之一变,与前大有不同者,一是双方文学交游十分兴盛,酬赠之诗家人数、作品数量大增。龟山云平为刊于1884年、清人致水越成章诗文集《翰墨因缘》作序,其言:“今者万国交际……吾友水越畊南在神户仅数年,而与清国诸士以文字交者,二十有五家。”水越成章在非首府的神户,数年已交有二十五位中国文人,较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木下彪指出,自1871年日清建交后,“自然而然地打开了两邦人士的文字之交,诗酒之会屡屡在东京举行”,并认为此时乃交游最盛之际:“其最盛之时,从明治十一年至二十七年的日清战争止,此后中断不振。”此语尚有可斟酌之处。清日建交之初,何如璋、黎庶昌等驻日公使掀起了中日文人燕集、唱和的热潮。甲午(1894)战败后,国人急于寻求变革方案,故赴日考察者大增,足迹遍布日本各大城市。他们寓日时,仍与日人酬赠不绝,只不过较之建交初期前所未有之盛,显得更为日常而已。以广府文人为例,甲午后赴日考察者,有香山人刘学询(1855-1935,一说1860-1936,1899年赴日考察商务)、南海人黄璟(1841-1924,1902年赴日考察农务)、南海人关赓麟(1880-1962,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番禺人金保权(生卒年不详,1904年赴日视察)、番禺人许炳榛(生卒年不详,1904年赴日考察商务、1905年再次赴日考察矿务)等等。他们均与日人有所酬赠,作品多载录于各自诗文集中,亦有编为唱和集者,如黄璟将其在日唱和之诗编为《东瀛唱和录》。
其次,因酬赠双方多为显宦、学者,文学交流层次有所提升。与日人酬赠的广府文人,多是工于诗文者,如黄璟诗画皆精,关赓麟更是稊园诗社的主持人。黄璟赴日前得知日方已“嘱能诗画者相会”,清人所接洽者,不仅为其时盛流,且有较好的汉文学素养,更有不少诗坛名宿。如与黄璟、刘学询等人酬赠最密的,有永井禾原(1852-1913)、永坂石埭(1845-1924)、森槐南(1863-1911)和长冈护美(1842-1906)。永井禾原学诗于诗坛大家森春涛、大沼枕山,与田中梦山创立诗社剪烛会。叶德辉称其“诗心括中土,才名轰旧京”,姚文藻更誉其诗“取径盛唐,措词沈雄,寓意深稳”。永坂石埭师从鹫津毅堂及森春涛,创立诗社一半儿会。森槐南为森春涛之子,幼承家学,创办杂志《新诗综》,重开星社,乃明治汉诗三大家之一,其诗风被认为是“基于唐诗,杂之以吴梅村之苍凉、王渔洋之神韵、清陈碧城、郭频伽之艳丽,形成了独自之风格”。长冈护美诗作颇丰,其诗得黄吟梅“风调深佳”、“风致极肖唐解元”之评。双方互致唱酬,虽不至逞才使气,但亦非罗森与日人酬唱般随意,基本用依韵、次韵的形式。此外还有诸多文字游戏,如黄璟赴永井禾原之约,“分韵得麻字”;长冈护美约许炳榛“后夕至其寓园联句志别”等等。酬赠之作颇有可诵者,如永井禾原《刘问刍观察邀饮绮席,不期晤黄小宋观察有赠,次韵酬之》一诗:“休言霜雪上吟须,满座名花酒百壶。超海壮游留爪印,添香多恨入诗图。年来勋业志终遂,世有公评名岂沽。尚有风情难掷得,明时未可隐江湖。”用“名花”、“酒百壶”、“添香”、“风情”等词紧扣绮席唱和,中间两联推许了黄璟颇为自得的《益壮图记》,更不忘颂扬其事功,语带洒脱,旨趣立意均有佳处。
其中又有深于诗者,还进一步点评酬赠之作的诗风、诗法。如番禺人潘飞声(1858-1934)论诗标举情韵,尝云:“诗至齐梁,别为艳体,如无情韵,即不能谓之诗。”其赞誉小野长愿、森春涛等唱和《梅影》一题之佳句曰:“皆有情韵,有思致”。又评永井禾原“诗境幽远高浑”。名诗家菊池三溪对众广府文人与水越成章酬赠的诗作,从风格、用典、笔法等各方面均有点评,如赞香山人郑文程《读畊南先生〈秋思〉诗,次韵,即希教正》诗“措词清脆,绝无一点尘涤气”;论番禺人冯昭炜《题畊南先生〈薇山摘葩集〉》诗用“正而葩”一词,是“用韩文成语,有力”;评陈慕曾(原籍浙江嘉兴,迁广东广州府,捕属客籍)《偕畊南偶集柳原花月楼,席间为小妓春尾题扇》诗笔法“前半正叙,后半侧笔,一正一侧,作法极佳”。
再次,汉诗酬赠形式更为丰富、互动性增强。如前所述,江户时期,日人以诗见示,希冀汉土人士能赐和。如罗森与日人唱酬,是处于被请教者地位的。他并未主动出示诗作,多是日人录诗见示或请其题词。明治以降,中日汉诗交游形式大为丰富,不仅是一般的录诗请和、临别赠诗,还有官方宴会唱和、私人雅集题咏、作品题词、节日赠答、日常以诗问讯、观赏书画题赠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虽亦有日人请求指点诗文之举,但请教与被请教的高下之分逐渐减少,互动成分增多。从以下两点可见:一是酬赠场合多为宴饮、雅集。如刘学询赴永井禾原宴,席上唱和,“酬酢甚欢”。日人还喜欢雅集于当地名胜,以享兰亭修禊之乐。如东京不忍池,考诸刘学询等旅日文人日记,多有在此地雅集者。不忍池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一名小西湖,称为东京胜地”,风光颇与杭州西湖类。刘学询赞曰:“四面荷花,一堤杨柳,夕阳初下,雨送秋来,风景殊胜”。在此间雅集,甚得文人西湖雅事之韵味。有些宴集还是由非地主方的清人主动发起,如冯昭炜曾于中秋邀饮众日本友人,其致函水越成章,言语切切:“明日是月圆秋夜,日前在府时,曾约鹏万翁,邀阁下及尊夫人等于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后,光临伊宅,共话知交。……如值公暇,乞践前约,是感不已。”正如许炳榛席上听铃木充杉“对酒当歌,春雨一曲”,感叹“足怡我情矣”一般,雅集场合诗赋佐兴,不同于以诗见教,更多是士大夫趣味所在。
二是中国文人不仅是被动和作,还经常主动赠诗,亦有乞请日人和作者。如黄璟自上渡轮始,诗兴大发,不仅赋诗以录见闻,还主动赠诗予日本船长野田启太郎和楠原正三。黄璟既感激野田的照顾,又与其笔谈甚欢,有互赠照片、团扇之谊,其赠诗有:“握手主人翁,笔谈黄海中。相逢情意合,何必语言通。饮食投吾好,姿容相尔丰(以小照见贻)。赠之以团扇,霁月合光风。”到日后,黄璟亦多次在日人宴会中主动赋诗相赠。又如郑文程《余与廖内翰枢仙、冯副理相如、水越先生畊南,诗酒流连,相交最契。感三君子之忘年降德,喜而有赠,乞赐和章》诗,有“琴无知己音难奏,诗有同心兴不孤。独恨唱酬添我累,枯肠搜尽渐清癯”句,虽则搜索枯肠为赋诗,但仍将嘤鸣会文视为知己乐事,希望得到友人和作。对于相交甚笃者,汉诗还成为展现朋友间雅趣、情感的工具,如黄璟访永井禾原不遇而留诗,陈慕曾赠水越成章以《问病诗》等。这些酬赠方式,已无涉文学地位之高下了,双方在互动中自得其趣。
此外,汉诗酬赠场域有所扩大。广府文人与日人汉诗酬赠,多发生在日本,亦有部分在广府,如新宁人黄景棠(1870-?)在《倚剑楼诗草》中,载有其为旅粤日人赠别的诗作。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赴欧美者渐多,酬赠场域亦扩大至东亚以外。如潘飞声寓德时,与日人金井雄、井上哲、石黑忠悳等有所酬赠。客居欧美,双方“笃同洲之谊”,更能感受到东亚汉文化圈的归属感。另外,还有酬赠双方未曾谋面,仅以朋友作为中介的神交。如番禺人杨永衍(1814-1893?)所辑的唱和集《草色联吟》录有金井雄诗,二人未曾谋面,全因潘飞声而神交。又广府著名诗家李长荣(1813-1877)与众日人交,除了八户顺叔外,其余关义臣、铃木鲁、小野湖山等均是笔友。李长荣将与日人唱和之作辑为《海东唱酬集》,未定稿而遽卒,后由森春涛校订于日本出版。是集所载录之日人,均未与李长荣面,多是因铃木鲁见示《海东唱酬集》后唱和的。
中日汉诗酬赠的新变,既是交通开放的客观结果,亦反映了双方文化心态上的变化。明治时代,以西方文化为优、东方文化为劣的“脱亚”思潮盛行。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著名的《脱亚论》,认为中国“不识改进之道”,但日本“国民精神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移转于西方文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甲午战争的胜利,日人民族自信心大增,大部分日人即便不是如“脱亚论”那样极端否定东方文化,但也认为,较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中国尚处于落后的文明。如高锐一为冈千仞的中国游记《沪上日记》作序所言:“夫汉土大国也,而中世以后,政纲渐弛,士大夫不知域外大势一变……天爵此游,与彼土士大夫周旋,使彼知九州岛之表,六经之外,固不乏人物,则彼必有所瞿然以反,惕然以警。”此时,日人已不复罗森时代的“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了,反而认为能为清人师,心理上自然不甘居清人之下。此外,汉诗经千余年之发展,兼之国粹主义盛行、汉文训读体的推广等社会原因,在明治时代达至发展高峰,名家辈出。汉学家大町桂月便指出,本应呈衰败之势的汉诗,此时“反而兴盛起来,且变得更为纯熟”,并感叹“自汉籍传入两千年,汉诗创作技巧的发展,尚未有如明治时代这样的”。此时日本文人汉文学水平较高,兼之视野开阔,部分学者还以西方学术方法治传统文学,如笹川临风、森槐南等人的中国戏曲研究。这些都使日人面对纯正的汉土文化继承者时,带有文化自信。日人摆脱了“慕华”的文化被指导者心理,而于中国文人而言,处于以学习日本为尚的风气下,也转换了文化教导者的心态,双方更为平等地进行汉诗酬赠。
在文化心态转变的同时,因一直以来的汉文化熏陶,同文同种的意识仍植根于日人心中。源桂阁在石川鸿斋与清人唱和集《芝山一笑》序中,便提及这种文化心理上的亲近。他对比了自己结交的西洋人和中国人,认为与中国人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盖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于是能“谈笑戏谑,以至彼我相忘,所谓倾盖如故者非耶”。中国文人于此亦有同感,潘飞声在录日本友人诗时,适逢永井禾原造访,“即以案上稿示之,彼此叹为文字之感,心气相通有如此巧合者”。汉文化倾向与“同文同种”的心理认同,是中日文人汉诗酬赠兴盛的文化基础。
二、汉诗酬赠与对传统的坚守
中日文人汉诗酬赠因世运更迭而呈现出新变,但另一方面,在酬赠中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学评价取向及酬赠者对传统士大夫行为模式的仿效、对士大夫理想人格的赞赏,就不仅是基于“同文同种”的心理认同了,更彰显了两国文人在西学主流思潮中坚守传统文化、文学的价值取向。
1.传统文学的评价取向
在中日文人的平等交游中,还是存在着以传统文学素养为价值取向的轩轾之别。汉文学对于非母语的日人而言,不易掌握,大部分人汉诗水平并不高。他们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对于清人的汉学水平,仍存在着倾慕心态。如冈千仞在与中国文人笔谈时,便会问及日人之诗“中中华矩度否”、“不知仆辈下手学文自何地”?又如菊池三溪评郑文程《敬题水越先生〈薇山摘葩集〉》(二首)云:“二诗清名家本色,邦人百方模仿不能望其后尘。”此语固然有应酬成分,但亦可见日人认为要达至中国诗家之境界并非易事。同为《沪上日记》作序的另一位汉学家高桥刚便追溯中日唱酬之历史,认为:“吉备真备、安倍仲麻吕诸人,辞藻彬彬,与彼土人士倡和歌咏,至今使人钦羡,为艺苑美谈矣。”感叹如今有交通之便,然“学士大夫亦以审外情为先务,争讲西学”,“而汉土实与我为比邻同文之邦,而未闻有学士大夫一游其地者”。对于能与正统汉文学传承者诗赋交游,日人还是颇为推崇的。随同黄璟赴日的王瑚便状其时日人对黄璟的追捧云:“彼邦士大夫皆以得接丰采为欢,乞诗书画者,日不暇给。并梓其《东瀛倡和录》,争相传诵。”中国文人亦然,在传统文学领域,难免流露出一定的心理优势。如关赓麟在日记中载录三省堂书店主人冈正一以诗见示并求订之事,曰:“东人赋诗,体格绝卑,与相酬和亦不得不敛才就范。”此语下,载有自己的和作两首:“传语惟凭尺楮通,雅人佳趣古今同。日长最好消岑寂,身在千岩万树中。”“东南大陆古文通,况乃神灵统系同。寄话此邦人士道,风潮今注太洋中。”二诗用语浅近,为应酬漫笔,确是其“敛才就范”之作。即使是与众日本诗家交好的黄璟,在描述自己赠诗予日人时,亦颇为自矜。如其载录在茨城县赴宴时即席赋诗事,云:“(二十二日)合座亦鼓掌致礼,各以扇乞书新诗,即席应之,各和诗见示。二十三日,昨晚主人陆续来访,复对客书十馀扇,以应所乞。”字里行间,文化上位者的心态隐隐可见。
其时中日文人的汉诗交游,多伴随着传统作品互赠、题词的习惯。如黄璟访森槐南时,森槐南“以其《浩荡诗程》《新诗综》并所刊《中国嘉道六家绝句》见赠”。又潘飞声常与日人互赠诗作并题词,其获赠永井禾原与森槐南等人的唱和集《檀栾集》后,和作《日本永井禾原君(久)过访,并赠〈檀栾集〉,即次集中第一会韵奉酬》,有“一卷《檀栾》识素心”句。永井对此评价大为欣喜,答以《访潘兰史香海冠南楼,兰史次〈檀栾集〉中余诗韵以赠,叠韵答之》,称之为“文章海外有知音”。潘飞声以其《海山词》赠予日人,金井雄、井上哲均有题词。两人诗中有“歌舞欧西眼易青,冶游休说似浮萍”、“洋琴试按衷情曲,帘外蛮花解笑听”、“爱向海山题艳曲,细腰人拜杜樊川”等句,道出了《海山词》书写异域风物之特色和绮艳词风。考之双方题词,乞请者还是多为日人。其时日人颇以他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对自己作品点评为荣。冈千仞《东旋诗纪》得沈文荧、黄遵宪提点,大感荣幸:“二君中土名流,今幸得亲接提撕,真希世之遇也。”并将二人评语附注诗集中。更有甚者,如内田诚还特意将俞樾《东瀛诗选》和陈鸿诰《日本同人诗选》所选的小野湖山诗辑为一卷,命曰《清人俞陈二家精选湖山楼诗》。黄遵宪对日人这种风气有所批评:“既各持其说,无以相胜,则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在此时风下,广府文人也多有为日人诗集题词者,语多褒扬之意。如冯昭炜、郑文程均为水越成章诗集《薇山摘葩》题词,有“新诗字字露英华,东海名流自一家”、“不与时流工獭祭,独张旗鼓继山阳”等句,称赞水越承继江户名宿赖山阳,诗风能自成一家。此外,陈慕曾也曾为水越《赞州游草》题词,黄璟、金保权等人亦有为长冈护美的诗集题词。
正如幸田露伴视汉文学为领悟一切文学之根基那样:“我邦人若不能领会中国诗味,那就等于对我邦和歌、俳谐等一切文学都不能领会,亦即对世界文学也无一人能够领会。”日人对汉学大家的仰慕,对请清人题词、点评的风尚,可见其时不少日本文人仍视传统文学素养为名士人格构成的重要因素。
2.士大夫趣味的标举
汉诗酬赠双方虽是一时遇合,亦有志趣相投,既而交往不绝者。如潘飞声在德国结识了男爵石黑忠悳,石黑“工书能诗,貌古情挚”,临别赋诗赠潘飞声,有“不怀故乡先怀君”句,此后二十年“犹时时约余游东西京”,并寄赠作品、照片,潘飞声颇感其多情。又如许炳榛二次赴日,长冈护美“坚约一见,以慰数月积思”。此语虽有夸张、应酬成分,但从不少酬赠之作可知,双方确是心有灵犀,故而成为知交的。汉诗酬赠的背后,体现了双方对旧式士大夫情怀、审美趣味的认可。曹丕《与吴质书》云:“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汉魏六朝赠答诗和公宴诗的勃兴,诗歌交际、娱乐功能得以发展,以诗娱情与以诗言志一样,成为士大夫所标举的诗学理念。已倾襟结交的中日文人,延续了士大夫修禊燕饮、诗酒赓和等以诗会友的行为模式。如潘飞声与井上哲“最称莫逆”,唱酬之作颇多。潘飞声《现华客馆喜遇井上君迪赋赠》(二首)有“我交东海多良友,文采风流似子稀”句,对井上诗才十分推许,认为“清新可诵”。井上哲亦将唱和之举比之元白,和作有“促膝联唫元白诗”句。又陈慕曾与水越成章交好,其《寄畊南》“好句君同赵倚楼”句下,自注云:“君有‘暗澹荷香风度水,参差松影月侵楼’之句,予每爱诵之。”其《结交行·即赠水越畊南》一诗,用公孙弘以脱粟饭待友而见疑,翟公罢官门可罗雀的典故,感叹“富贵相忘贫贱弃”的“人情翻覆”;用汉范式、张劭的鸡黍之交比喻双方是“丈夫结讬贵如斯,白首依然抱明义”的“人生知己”。陈慕曾还写有《问病诗》四首赠水越,其三便调侃曰:“君之病固多,却不在肢体。文章忌太好,君必求满美。处世忌太真,君必见根柢。”这些均可见其对朋友才情与品性的认可。故临别时陈慕曾颇为不舍,致水越之函其情依依:“更不知此后足下与群公琴歌酒赋时,犹念及一狂奴阿雨否。”水越也将陈慕曾等好友称之为“忘形之契者”,更提到因是如此知交,“故日用应酬,音书问讯,其往来所积,尺牍诗章颇多”,这正是他编集《翰墨因缘》之因。
除日常以诗会友外,文人们还喜欢有意无意间,重现传统文学作品的经典主题,欲以自身成就一段文坛佳话。以常见的“寻人不遇”诗为例,这类诗作因作者心境不同而立意各异。黄璟某日访永井禾原不遇,“留诗一首:‘看竹何须见主人,花花草草各精神。园中更有乔松在,我与盘桓意已亲。’”此诗一反访友不遇的遗憾,看到友人所栽草木,便是一大收获,又何须非要遇人?后两句化用陶渊明《归去来辞》“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句,既表达了在永井家园林中悠然自得、流连不已的心情,又将两人喻为高逸隐士,颇有雪夜访戴的洒脱,带有一种精神上的自足。永井亦深具会心,归家后即和答一首,题为《黄小宋观察过访,余偶不在家,观察留诗去,依韵答寄》,诗云:“未见先知如故人,梅花风格竹精神。吾归君已留诗去,文字之交淡最亲。”此诗虽逊于黄诗,但抓住了黄诗君子之交不需亲面的立意,成就了一段唱和雅事。永井对此事颇为自得,两年后在《题黄小宋观察〈益壮图记〉后》(四首)中,有“小阁来青留影在,花花草草入君诗”句,自注云:“君来游时,过敝庐留影,且惠诗有‘花花草草各精神’句。”可见其视此次唱和为一大故事,念念不忘。
永井禾原与黄璟、刘学询交好。黄、刘归国后,永井来华,双方“文字有交依旧好”(永井禾原《增子固中丞招宴于西湖刘庄。刘庄,吾友刘问刍观察别业,丁家山水行居也。酒间赋此赠中丞兼呈观察》),继续唱咏无虚。永井深谙名士交游之风流,某次访友,看见黄璟题画诗,欣然和作《上海客次访严小舫观察,观察见示〈春江意钓图〉,卷中有吾友黄小宋依胡华亭韵诗,余亦效之》,又成一图咏雅事。其又有《严、刘、谢、黄、辛、叶诸君子邀饮加藤泰园及同游诸人于松柏园,园有小湖泛舟。余将放棹,失脚落水。主宾拍掌大笑,作此解嘲》一诗,中间二联为:“太白江心曾掬月,知章水底好贪眠。奇踪莫笑拟双美,逸兴敢言追两仙。”“奇踪”句下自注云:“去年此园有宴集,朱湘娥、花小宝林误落池中,传为逸事。”他用杜甫《饮中八仙歌》典,将圈中逸事比之八仙贪杯典故,欲通过酬唱传播文人佳话,成就诗末句所言的“名园佳话有诗传”。由上可见,中日文人酬赠,有着士大夫“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的志趣与情怀。
雅集、访友、题词、编集……中日文人延续了文人士大夫案牍之暇、诗酒赓和的各式酬赠活动。王瑚为黄璟寓日唱和集《东瀛唱和录》作序,点出了对这种合诗才与事功于一身的士大夫形象的赞许:
欧阳永叔云:“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向谓此非极论也。及读韩退之《荆潭诗序》亦云:“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而裴、杨二公皆以致身通显,能文章、工诗辞,终断以“材全而能鉅”,以此见苟得于天者独全而其能固不测也。……知交中莫不谓观察之材全能鉅,天将以补人之不足也。
序中所谓《荆潭诗序》,即韩愈为裴均、杨凭《荆潭唱和诗》所作之序。韩愈在序中虽然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但针对诗集作者,便言裴、杨二公是:“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颂扬了作者身居高位仍不废辞章,非穷而后工,而是“材全而能鉅”。王瑚举例裴、杨二公,是吻合黄璟与酬唱日人身份的。其时酬唱者,大多是官身,既有政治抱负,亦有文学情怀。他们在汉诗交游中,深谙此中三昧,推许的也是双方的抱负与才情。如陈慕曾在为水越成章花红竹翠居题诗的诗序中,先说水越“幼负雄心,长怀壮志,学优而仕,以道得民”,再言其“更复志慕词章,性耽吟咏”,塑造了事功与文学兼擅这种传统士大夫所标举的理想人格。
中日文人酬赠中,对传统文学素养、士大夫审美情趣、理想人格的标举,其背后是逆西学时流而动的一部分文人对传统文化的贵尚与坚守。森槐南、永坂石埭等人,是酬赠的常客,亦是随鸥吟社的成员。随鸥吟社是大久保湘南为了挽回汉诗坛日渐衰落的颓势而创立的。森槐南在其与永坂石埭、永井禾原等人的唱和集《檀栾集》序中言:“壶觞雅洁,啸咏风流,曲尽唱予和汝之乐,席上诗篇往往流传人间,遐迩想慕”。日人所“遐迩想慕”的,不仅是诗酒风流,更是逐渐式微的传统士大夫趣味与情怀。其时不少汉诗家就主张要熟习汉诗,甚至反对新奇诗风,提倡“排斥淫哇以兴作大雅”。汉土文人亦然,郑文程《病中读畊南先生胶漆砚诗次韵》一诗便心有戚戚焉地感叹道:“西学方张汉学微,典刑变乱速祸机。落落儒徒扶一脉,砚乎舍此将焉归。”潘飞声为姚文栋编校日人为姚践行之诗集《归省赠言录》,并作跋云:
然日本为我同文之国,敦诗说礼,向不乏人。自政治更变,崇尚西学,宜其举国趋之若鹜矣。而二三耿介独立之士,犹抱持风雅,播诵辞章。且知诗之原本于忠孝而乐道,其性情之正者,盖人伦教化,久行域外,断非异学所能淆乱。
潘飞声视酬赠为“耿介独立之士”逆时流而行之举,有助于传扬诗教正风俗、化人伦之用,认为传统文学、传统士大夫的理想情怀是“断非异学所能淆乱”的。“抱持风雅”的汉诗酬赠,带有诗家伤感时势、维持旧学的意味。
三、汉诗酬赠与“兴亚”思潮
在“维新”之时,标举传统文学、涵泳于士大夫趣味,日人对汉诗、汉学的复兴意图,不仅是文人志趣,更与其时的“兴亚”思潮有关。如前所述,明治时代日本脱亚入欧思潮盛行,但也有部分日人看到欧化的弊端,提出重新认识东亚文化的价值,主张亚洲团结以对抗欧美。这种“兴亚”的亚洲主义与“脱亚”论一起,成为近代日本思想史上互相交织的两大思潮。持亚洲主义论者思想背景颇为复杂,流派众多,具体主张不一,但核心均是东亚同人种国家应相互提携、共同“兴亚”。至于中国在中日同盟中的地位,则随着流派、时期的不同而异。学界有关亚洲主义的研究颇丰,兹不细述。值得注意的是,日人对汉文化的推崇,无关“慕华”,而是“尊日”。此时日人已视汉学为日本民族的学问,汉诗也并非作为中国文化的投影出现,而是日人涵养民族精神、构建亚洲精神统治力之器具。如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在1891年发表的《真善美日本人》中指出,汉字可视为日本民族之文字,日本已对中国文明十分了解,将其向全世界传播,是极易为之事。桑兵在论及近代日本新汉语词汇的推广时,提到:“在重建东亚文化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故此,作为“同文同源”的汉学、汉文学,不仅成为日人对抗西学、振兴东亚文化之利器,还是确立日本在东亚精神统治地位的工具。
广府文人与日人的交游中,长冈护美与多数人均有酬赠,如黄璟多次与长冈唱酬,又金保权在其旅日诗集《东游诗记》中,录有与长冈酬赠之作五首,四首为赠诗,一首为赴长冈宴的即席和作。金保权以官员身份赴日,不可能没接触其他日人,但诗集所录与其汉诗酬赠之日人,仅长冈一位。其中“晤长冈护美子爵”之诗云:“此行不负破长风,得见樱花复见公。一点丹心何处认,天边遥指早暾红。”颇有示好之意。其“长冈子爵以《云海诗钞》见贻”一诗,有“一笑春生四座中,异乡相见道相同”句,这种道,不仅是文学之道,更语涉长冈主张“兴亚”的政治立场。长冈护美先后任兴亚会会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此二会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团体。东亚同文会十分重视两国士大夫之交往,认为“两国士大夫,则为中流砥柱,须相交以诚,讲明大道,以助上律下,同底盛强也”。长冈护美热衷于结交中国官员,诗集《云海诗钞》收录了大量与中国官员、文人酬唱之作,其行为亦是基于兴亚团体立场的。他在东亚同文会翻译出版的《刘张变法奏议》序中提及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交游,颂扬了清朝士大夫日渐顾全大局,使日清得以亲厚、交流得以增多,更推崇日清之间便是古人所谓的辅车唇齿。其以诗赠别刘学询,有“图经著就绥边略,携得嘉谋献禁闱”句,不仅切合刘赴日考察事,亦未尝没有希望刘归国后能为日清提携论张目之意。除长冈护美外,其时唱酬的日本政坛、文界者,多与东亚同文会有关系,黄璟某次赴永坂石埭诸诗人之宴,即席赠诗,便直言“喜联东亚同文会,来结西园雅集缘”。
面对持“兴亚”主张的日人,清廷官员亦投桃报李。在酬唱中一方面表示赴日收获匪浅,如黄璟赴茨城视察农学,席上赋诗,称赞日本“漫道农桑新法好,天时水利在人谋”;另一方面亦附和“兴亚”主张,如黄璟和长冈护美诗,推许长冈“君思东亚疮痍复”。又赠永坂石埭诗,言“一笑相逢证夙因,同文国似齿依唇”,呼应了长冈“辅车唇齿”之说。且不论场面上的酬赠之作,从清人的私人著述中,亦可见对中日提携论的赞同。如许炳榛寓日时与长冈护美酬赠不绝,其在日记中称赞长冈“于中国情事洞若观火,故谈及国政外交,殷勤忠告,诱导我国,不遗余力。彼之与我并列亚洲,同文同种,唇亡齿寒,子爵能知之,亦有心人哉”。某次许炳榛席上和答长冈赠诗,中有“东亚邦交唇齿笃,枯肠三涤勉陈辞”、“同文为我迷津指,异地如君毕世知”等句。他在日记中载录此事后,言双方“诗歌赠答,怡怡如也”。《论语·子路》云:“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怡怡如也”一词,很可能是许炳榛对东亚同文会所提倡的两国士大夫以诚相交的肯定,甚至认为中日提携乃士大夫应行之道。非官身的文人,也有不少对“兴亚”论持有兴趣,如潘飞声便撰有《兴亚会序》,提出亚洲各国应“如手足,如兄弟,一心戮力,各修国政,共捍外难”。
同时,中国人对日清提携下中国地位如何,也是有所疑虑的。桑兵认为,其时中国对日清同盟的态度也并非十分信任:
由于甲午战争的阴影和日本对华的进逼态势,即使在相信同文同种、同盟提携之际,中方人士对于日本与中国结盟的善意也将信将疑,更多的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希望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基本。
某些唱和诗作,隐晦地表达了中日双方微妙的政治立场。如刘学询与日人的某次雅集中,永井禾原席中赋诗,有“大国由来德照邻,交情偏觉辅车亲”句,虽写出了中日辅车唇齿之情,但德化广被的“大国”,到底是以汉文化熏陶日本的中国,还是帮助中国学习新法的日本,指涉就颇为模糊了。同在此场雅集中,刘学询与森槐南有一组唱和诗,前三联均是“结欢自仗同文谊”、“同洲今日更相亲”这类颂扬中日情谊之语,唯尾联颇有深意。森诗尾联为:“一笑楼兰夸电速,看朱成碧漫相猜”,刘学询和诗的尾联为:“传杯拼醉葡萄酒,一任弓蛇影误猜”。此外,黄璟和立花小一郎韵,也有“变齐变鲁终归道,同轨同文两不猜”句。特意点出“漫相猜”、“误猜”、“两不猜”,自是在当时有猜疑、反对的声音,故在应酬场合上作一表态。可知,日清同盟论之下,亦非一片和谐。但无论如何,正如上文桑兵所言,大多中国人是希望学习日本新法,在日本的帮助下“增强自身实力”,以振兴国运的。黄璟在返程船上观日出,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感而赋诗,尾联“曙曦自是扶桑始,华夏今将万象征”,便道尽了士大夫这种抱负与寄望。
四、结语
巩本栋在论唱和诗词时指出:“尽管唱和双方各自的情况多有差别,然而当其构成唱和之时,双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遭际,各自的生活体验、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等,或此或彼,总有相同、相近之处”。晚清中日文人的文字因缘,不仅在于场面应酬之需,更带有“同文同种”的心理倾向和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取尚。同时,也寄寓了中国文人对取法日本、振兴国运的渴求。正如刘学询赠永坂石埭诗所言:“移家为爱诗人宅,济世应同良相心”,中日文人酬赠的形式与内容,都与传统士大夫对文学与事功并重的人生理想并无二致。只不过对于尚未如日本经历彻底变革的汉土人士,这种汉诗酬赠的士大夫趣味尚是一种行为习惯。他们可能未预料到,不久的将来,清遗民与旧式文人们,诗文唱和赓续不绝,藉此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而日本的汉文学进入大正、昭和之后,更为式微,尤其自明治诗坛名宿去世后,汉诗坛再难重现辉煌,其时的汉学家大力呼吁写作汉诗、复兴汉学。如此看来,晚清时中日文人以酬赠来“抱持风雅”,亦可算是后来人追慕前代的唱首。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