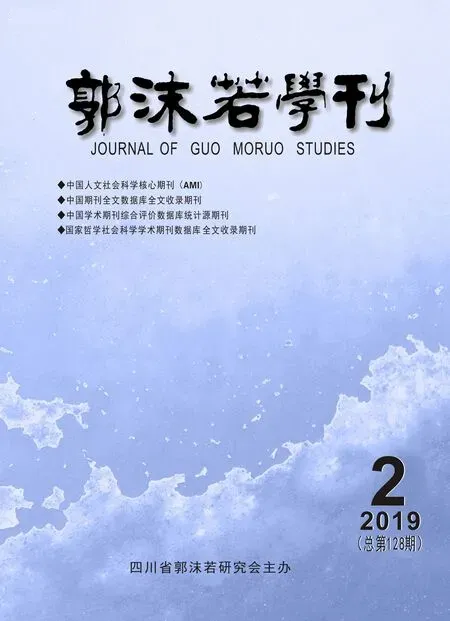试论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贡献
董仕衍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70)
曾彦修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变化轨迹时,认为使自己思想觉悟的关键人物是郭沫若、鲁迅、茅盾,他直言不讳:“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而且他相信,这种情况应该是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界的普遍现象:“说当时的青年,抗战前受了多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影响,太夸大了,其实看不到。但很多人,都读过郭老、鲁迅的书。”由此可见,当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时,除了关注知名理论家的传播活动之外,现代作家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在众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做出贡献作家当中,郭沫若以其深厚的哲学素养与对理论问题的批判性思辨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
郭沫若曾借孔子之口讽刺当时的国内理论界:“我听说要谈你的主义,用不着你的书呢。只消多读几本东西洋的杂志就行了。”这样的嘲讽并非无的放矢,纵观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成果,几乎全部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大部头、成体系的理论著作,这与早期散碎翻译、译述国外报刊杂志上的介绍性、评论性文章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沫若翻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便是日本政治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于河上肇,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统计,仅1919至1922年之间,被翻译成中文的河上肇的作品已经有:《贫乏物语》《マルクスの〈资本论〉》《共同生活と寄生生活》《妇女问题漫谈》《マルクスの社会主义の理论的体系》《思索の必要と研究の态度》《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观》《劳动と资本》《社会主义の进化》《利己主义と利他主义》《资本家的思想の一例》《マルクスの唯物史观に关すゐ一考察》《同盟怠业の道德的批判に就て》《资本论に见はれたゐ唯物史观》《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脑味噌の问题》(G.R.Kirkpatrick原著)《共产者宣言に见はれたゐ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と唯物史观》(恩格斯原著)《社会主义の未来国》(J.Borchardt原著)《断片》《次の日の问答》《マルクスの理想及び其の实现の过程》《マルクス主义に谓ふ所の过渡期につぃて》《唯物史观问答——唯物史观と露西亚革命》等几十种,而且重要的专著类作品往往都不止一个译本。就郭沫若本人而言,他在留日期间便读过河上肇自己创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便是由刊发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文章编纂而成,虽然零星散读的结果是“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也足以说明郭氏在译书之前,已经对河上肇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郭氏很早便与孤军社的陈慎侯、何公敢等人有交往,更加大了他较早接触河上肇思想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郭沫若之所以能够被河上肇的思想所吸引,并多次强调《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折点,是因为郭氏早期思想中的均富、利他主义等内容与河上肇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具体到《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本书,自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译完以后,其出版情况为:初版本为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年成都嘉陵书店翻印,1951年经吴泽炎校改后再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题目为“关于资本主义的若干之考察”,主要内容为讲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会使资本集中进而生产停滞,爆发社会危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内容,涉及的理论要点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再生产及其周期性、剩余价值论等。同时在这一部分河上肇还反驳了其论敌东京商科大学教授、经济学权威福田德三的相关观点。这一部分在全书所占的篇幅最大。中篇题目为“社会组织与个人之生活”,主要内容为对雇佣劳动制、劳动异化、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与义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生活等问题进行分析。下篇题为“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之考察”,这是全书最具思辨性的部分,也是对于当时中国现实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本篇的第一章重点介绍《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及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等问题;在第二章中,河上肇首先提出他认为马恩的思想当中存在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是以“沉着的进化主义者”面貌出现的,而到了《共产党宣言》,马恩却变成“狂热的革命主义者”了。(所谓“沉着的进化主义者”,即“历史决定论者”。)在区分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之后,河上肇引用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以及马恩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作的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马恩后来对自己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对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判断进行了修正。基于此观点,河上肇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公式,进一步分析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最终会使生产力减退,即使成功也会蜕变为单纯的政治革命,进而指出当时的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整体来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本书的逻辑与体例是严谨、完整的,材料方面也十分扎实,引用了大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马恩原著,做到了用材料说话。观点方面,以政治的标准来评判,其中关于“和平革命”以及超越阶段的“政治革命”的观点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如果仅以学术的标准来看待,河上肇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对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特别是马列原著的那个时代,这本材料详实、详引各种原著原文同时又涉及劳动价值论、人的异化、社会革命理论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显得意义尤为重大。郭沫若后来将此书认定为“偏重学究式的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骨干——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是有失公允的,这本书虽然重点在于强调生产力水平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但这恰恰是忠于原典、谨慎选取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能够有力地纠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原著材料不足、主观发挥有余的毛病。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怎样来改造世界,更差不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句评价虽然属实,但明显超越了当时具体的时代语境,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半还是倾向于其唯物主义一端的,郭沫若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列宁,这一点在当时恐怕也并非共识,要求20世纪20年代初的学者河上肇(而非从事实践的政治家)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显然过于苛刻了。
在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郭沫若便开始直接翻译马恩原著。这里体现了郭沫若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个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传播史当中,早期的传播者,特别是文艺界出身的译者翻译的多是来自日本、欧美的二手文献,关注的重点也更加偏重俄国革命与列宁,而郭沫若则少见地在翻译过一部河上肇作品之后便直接跳过日本与苏俄,直抵马克思,而且翻译的都还是马恩原著中较为难解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著作。
郭沫若翻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930年4月,由左联编辑、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文艺讲座》(第一册)书后广告中,便预告了郭沫若署名易坎人译的卡尔马克斯著《经济学批判》,这说明此书大致翻译完成应该是在此前后。1930年5月,郭沫若将译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命名为《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讲座社编辑、光华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在文后的《译者附白》中,郭沫若称此译文的完成时间为“第一百一十二次的马克思生日”,即1930年5月5日,并告知读者此译文依据的底本为考茨基(Karl Kautzky)整理的1922年德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考译本为N.I.Stone的英译本、猪俉津南雄的日译本以及河上肇与宫川实二的日文合译本。在这篇附白中,郭沫若特地交代了马克思在正式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为何弃置此导言,郭氏认为马克思放弃事先预设结论的大纲并要求读者同自己一样“由个别的升到一般”,体现了“马克思研究学问的态度和诱导后进的精神”。通过辨析“从个别到一般”与从“一般到个别”的区别,郭沫若将此《导言》比作旅行时的地图,一方面说明了《导言》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可以起到的提纲挈领的作用(郭氏《经济学方法论》的命名正体现了这一作用),另一方面也提醒读者要从实践当中获得具体的经验体会,点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郭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于1931年12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郭沫若为初版本写的序言已佚,此书印行量极大,1946年10月群益出版社再版印行1000册,截止到1951年4月群益出版社第六版时,总印量已达到13500册,据说在郭流亡期间该书还被北平的书店冠之以“李季”之名印行,足可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发行量,大概如郭沫若在1947年2月为群益出版社出的《沫若译文集之四》版《批判》写的序言中所说:“所谓‘唯物史观的公式’是包含在原序(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笔者注)里面的。”这部译作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确实能够为没有读过《资本论》的读者快速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提供很大帮助。
之后,郭沫若又翻译了马恩原著当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按照郭沫若的自述和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一般认识,郭译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的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Engels Archiv)第一卷(MEGA1)德文原版进行翻译的。近期有学者通过研究郭译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译注、术语、误译指出,郭沫若主要是依据栉田民蔵与森户辰男1930年日译本译出,仅在必要时参考了德文版,并据此确定郭氏着手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间当在1930年5月以后(此前有学者依据郭沫若在1947年为群益出版社再版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写的序,推定此书翻译于1927年,结合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中的回忆判断,此书应该是在作者流亡日本期间翻译的)。郭译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本书的翻译虽然完成较早,但“因为时局关系”直到1938年才得以出版,1947年再版,其后分别于1949年4月、1950年7月、1950年9月出版发行二、三、四版。1960年译自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卷翻译出版以前,郭译本一直是国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通行版本。从内容上看,郭译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书作《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第一章,并非全译(全书德文原版直到1932年才公开发表)。从译者弁言可以看出,郭沫若翻译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为缺乏马列著作可读的中国读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并非采取“学究式”的理论研究立场,故而为了使读者得到更好的阅读感受,梁赞诺夫原版中的“有些无关宏旨的废字、废句以及脚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某些字句的批注、修改,均被省去,郭沫若认为“这种校勘学上的功夫非就原稿本身去研究是无甚意义的”。
众所周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的译介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艺界成为时髦语言的当时,对于廓清何谓“唯物史观”、批驳错误理解与庸俗化用法,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除此之外,此文对于理解郭沫若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实践”问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亦有极大帮助,因为此文的结尾便是那句十分著名的、可被革命者树为座右铭的“哲学者们只曾把世界作种种解释目前是归结到要改革世界”(据郭译本1938年版)。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唯物史观正式创立的标志,正是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详尽批判,使之前浮于云端的思想世界来到人间,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经典论断便是出自郭沫若翻译了的“费尔巴哈”章中,郭氏的译法为:“不是意识规定生活,反是生活规定意识。”
1936年2月15日,郭沫若又完成了《神圣家族》节译,将其节译部分命名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由日本质文社于同年5月25日出版,1947年3月由群益出版社更名为《艺术的真实》再版。比起《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的节译更加不完整,因为郭沫若依据的原本便是刊登在日本Nauka社的《理论季刊》第一辑上,根据P.Schiller和M.A.Riefsitz从《神圣家族》中摘取内容写出的《马昂艺术论体系之拔萃》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三手文献了。郭仅仅是对照了阿多拉次克版《马恩全集》的德文原版进行了文字翻译,而内容选取则完全依据日本杂志上刊登的那篇文章。具体来看,《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主要是摘取了《神圣家族》第五章“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八章“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由于文献来源于《马昂艺术论体系之拔萃》,所以《神圣家族》中原本的小节标题基本上都被弃置不用,而换上了同文艺问题有关的标题,例如从原书第五章第三节“‘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节选出的小部分内容被编为新的第三节“思辨的文艺批评之畸形的一例”、第四节“苏泽里加大师之舞蹈观”,原书第五章第六节“‘斑鸠’(丽果莱特)”的最后一段被编为新的第五节“布尔乔治的典型之理想化”,原书第八章第一节“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连同第八章第二节“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玛丽花”中的(b)部分被编成新的第六节“文学中的典型及新的社会关系歪曲之实例”,原书第八章第三节“揭露法纪的秘密”的(b)部分被编成新的第七节“布尔乔治浪漫主义文学之肯定的典型之暴露”。经过对原书内容的如此摘录并分节命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已经基本上全然变成了一本文学批评类著作,而且此书选取内容至多只有《神圣家族》原书内容的十分之一,通过阅读此书不可能窥见以鸿篇巨制形态出现的哲学著作《神圣家族》之全貌。尽管如此,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的“译后记”中还专门提到了郭沫若翻译的这本书,并指出《全集》本的翻译还参考了郭氏的译文。
另外,《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的第一节,即全书中统御以下各文学批评章节的哲学性纲领部分,还被单独拿出来冠以《黑格尔式的思辨之秘密》的题目,发表在《质文》杂志1936年五、六期合刊上。
以上就是郭沫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理论著作,虽然说他译书的最直接动机是为了换取稿费(《资本论》的全译计划就因为未能得到出版商的支持而遗憾流产),但郭氏对经典理论的翻译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理论的译介传播同他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形成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郭沫若同茅盾、鲁迅等作家不同,他们基本是将译介传播的重点放在文艺领域与现实政治需要,有的放矢、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呈现出“短平快”的特点,而郭沫若明显有着更大的雄心,他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思想体系,从而进行一种整体性哲学建构,而不是将自己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在某一领域的具体应用。无论是《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毋庸提计划中的《资本论》,都体现出郭沫若希冀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最新思想成果的宏图远志,恐怕也正是因为持有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社会科学整体性视野,此后他才能够在文艺、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均游刃有余、有所建树,才能够在前人“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
二、通过政论与文学作品传播
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前,郭沫若的思想与创作情况可以用他自己捕捉到的一个生活场景来形容,那就是“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尽管许多作品中都或多或少透露着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并且提到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以及阶级斗争等革命术语,但在哲学层面还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第一篇较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政论文章是写于1923年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这篇文章与其这一时期写的其它文章(如《艺术家与革命家》等)相比,观点存在较大不同,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将其作为“五卅”前“革命文学”“潜在萌芽和滋长”的证据。具体来说,《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这篇文章从外部世界开始分析,是因为政治破产、武人专横、政客蠢动、资本压迫,这些客观世界当中先在的严峻状况是提倡文学新运动的原因,文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革新外部世界(“五四”文学革命因未能改变资产阶级的根性,所以是失败的),而不再是以文艺本身或是以个体人生为关注焦点的艺术、革命一元论。这篇文章通过“向外求”的方式将实践的重点完全放在外部世界的改善,虽然没有具体介绍某种理论观点,但这种“向外求”的分析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大特征——客体优先,这种分析方式在文艺出身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当中并不多见。
类似这样的客体优先的分析方式在郭沫若自己20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撰写的文章中也很不寻常,除了这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之外,还有写于1923年10月的《太戈儿来华的我见》。这篇文章比起《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唯物史观的理论见解更成熟,表述也更直接。初看起来,此文延续了《论中德文化书》的观点,即借泰戈尔访华这一事件,批判静观、出世的印度文化,但《论中德文化书》仍旧是一种文化立场,是基于文化类型学的对比分析而得出结论,对于马列主义的称颂也是从其反抗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进而恢复科学的价值中立这一角度。而《太戈儿来华的我见》已然放弃文化本位,走向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与人的主体相联系的文艺同作为客体的“经济制度改革”相比,已经处于一种没那么重要的从属地位。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以外,郭沫若写的评论文章里较早从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写于1924年六月的《盲肠炎与资本主义》。郭沫若在1947年为群益版《盲肠炎》写的《〈盲肠炎〉题记》中写道:“1924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对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是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1924年整体上在郭沫若思想转型过程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暂且不论,但将《盲肠炎与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单独拿出来看,其写作时间正是郭沫若刚刚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应当正是他对于从这本书里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以及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更替等内容十分熟悉并且感叹佩服的一个时期,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对《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摘要论述及评议回应。其中将资本主义比作盲肠,认为它对社会毫无用处,只会不断榨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自身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最终因生产无计划和无序竞争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论述,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简要概述,用盲肠炎作比,更加有助于读者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质疑河上肇理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文章结尾处,在以宗教天国可从人间地上建立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论据以后,作者话锋一转,写道:“有人或会以为这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但是这种人并不是不欢迎这种地上乐园,他们是欢迎过度而生出了这样的杞忧,在飞行机尚未发明之前,人谁信二十世纪中有人会在天空中翱翔呢?”河上肇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反复多次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发挥出容纳的其全部生产力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所谓“唯物史观公式”以证明超越阶段的社会革命不会成功这一观点,郭沫若在文章结尾写的“杞人忧天”的人,显然是指河上肇及其理论追随者。
写于1925年12月的《新国家的创造》,是另一篇郭沫若早期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为了同国家主义者论争,重点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其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大段德文原文与中文翻译。众所周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这一部分内容,茅盾早在1921年便翻译过来并发表在《共产党》杂志上。目前找不到证据证明郭沫若此前阅读过《国家与革命》,但根据其在多篇文章中对列宁表达的高度赞誉可以推论,他对于列宁的国家观应该不会陌生。《新国家的创造》一文中,郭沫若没有直接引用列宁,而是使用了国内流传最广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这或许为了进一步嘲讽“不读书好求甚解”的国家主义者。尽管如此,郭沫若的逻辑却同列宁对“考茨基主义者”等机会主义者们的批判是一致的,他指出马克思说的“工人无祖国”并非是工人不要祖国,而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工人是不掌握国家机器的,并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工人是无祖国的。本来没有的东西,人不能从工人们取去(就是他根本不否认国家)。无产阶级只要先求政治的支配权,把自己提高到国民的阶级,自己来组织成一个国家,这虽然决不是有产阶级者所说的国家,但仍然是国家的。”这就非常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指向了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郭沫若称之为“新式的国家”,这便进一步同《国家与革命》的主旨联通起来了。
有趣的是,在郭沫若此文发表以后,得到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李芾甘(巴金),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评洪水八期郭沫若之〈新国家的创造〉》,直接引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称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另一方面则是孤军社郭心崧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来证明马克思是否定国家的。然而无论是考茨基的观点还是对《反杜林论》的错误、歪曲理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是详细批驳过的,特别是郭心崧的文章中还特意提到了《国家与革命》,却也不曾回应列宁,似乎是对列宁此书只闻其名而全未读过的样子。此两人对郭沫若的批判,达到的效果仅仅在于证明郭氏的观点同列宁竟是惊人一致,郭沫若原本没必要再做《卖淫妇的饶舌》从德语翻译的角度证明郭心崧曲解恩格斯,只需拿出《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的现成结论即可。
除了上面这两篇文章之外,郭沫若在同国家主义者论争过程中发表的多篇文章以及针对“五卅”运动写的评论当中,都能够看到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由于郭沫若反对以论文形式直接“搬运”观点,而更热衷于直接翻译大部头的经典原著,所以他的政论文章多是针对中国具体问题加入了自己的观点与阐释,很少原封不动地转述马列,故暂不讨论这些文章。
除了政论,郭沫若还善于用文学作品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而且他在作品中宣传理论还并非是像茅盾那样通过长篇小说普及一种历史观与哲学方法论,而是用诗歌、日记等篇幅更短小、内容更直接的形式来表达具体观点,带有较强的说理意味。
诗歌方面,主要体现在1928年初郭在养病期间作的《恢复》集中所收录的诗歌。虽然《前茅》被郭沫若在序诗中称为“革命时代的前茅”,但很明显,该集中收录的作品表现出的还仅仅是一种泛化的浪漫主义革命情绪,是缺乏任何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作内容支撑的,比如《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只是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绪;《上海的清晨》《励失业的友人》只是传达了对穷苦人的人道主义感情以及传统士人的仇富与清高;《太阳没了》也仅仅是用华丽的文学技法表达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哀时古调》如作者自己所述缺乏阶级视角……难怪作者在刚编完此集不久便认为“这个集子并不高妙”。而《恢复》中有几首作品,抛开艺术价值不论,至少在观点的传达方面,已经不同于《前茅》的花拳绣腿与横冲直撞,而是一招一式有了真实内涵,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以及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用诗的语言进行表述传播。比如《述怀》与《诗的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不仅从经济基础出发对当时的中国作了一个极简单的阶级分析,而且还指出了革命的具体实现途径——“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同前一首《对话》比起来,不仅加入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而且顺便批判了国家主义者的观点,深刻地指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他们在经济侵略之下的矛盾性——“不做走狗,便做猪羊”,最后还点明了以工农为主体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希望;《电车复了工》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赞颂与继续召唤,阶级出身不是通往天堂的门票,无产者的解放从来要靠自己,虽然“但我想在这样高压的政策之下,/工人们也断不会能够得到甚么满足”,但工友们的英勇斗争与坚强意志依然值得歌颂,“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
写完《恢复》以后,郭沫若又紧接着在同一个抄本上记了一个多月的日记,这些日记在1933被编成《离沪之前》发表。《离沪之前》日记当中同样有大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是其阅读某本马列经典之后得到的最初感性体会,因此带有更强的真实性与个人性,对于理解其个人的思想转变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1月16日读过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之后分析了宗教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中影响较大的原因,并得出结论“反宗教运动应隶属于阶级斗争之下”。1月17日的日记里,原文记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谓“唯物史观公式”一段的中文译文。1月29日的日记中将工人出身的魏特林与蒲鲁东同非工人出身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对比,由此提出了知识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此外还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的形式进行了对比。2月8日的日记中称“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Bier-Bauch(啤酒肚子)。”这是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流行的哲学观点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的体现。
上述作品是从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例子,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所作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将经典理论结合中国问题进行的具体应用之中。
三、取得的传播效果
胡愈之以记者特有的敏锐,往往对于许多人和事有着十分精准独特的评价,比如他曾经如此评价郭沫若:“如果说鲁迅对革命文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沫若同志是有及其广泛的影响的。”确实,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革命文化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单一的领域,他的影响真可当得起“广泛”二字。而且这种广泛性,不只是体现在他所跨的学科领域之广,同时也是在说受他影响的人的数量之多。郭沫若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效果,充分体现在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与评价之中。
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在讲过郭沫若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之后,还专门谈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和介绍等方面”也有重要建树。
同为作家的茅盾,在对郭沫若的一生进行总结评价时,特意提到:“一九二七年后革命文学的论战,给当时的作家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这说明在茅盾看来,虽然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早于郭沫若,但真正使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文艺具体问题并在作家当中取得广泛影响的还是郭沫若,他自己的贡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较早阶段中一般性地引入理论,而更为具体精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通过郭沫若的理论建构和“革命文学”论争,才普及到作家群体当中的。
周扬对郭沫若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效果评价更高,他认为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引导他们走向革命。”这一评价并不过分,因为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作的贡献,体现在理论输入和方法建构两个方面,理论输入方面,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法建构方面,他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具体应用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去,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同时,他著名文学家的身份又极大地扩展了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力,因此,“在千万知识青年中播下火种”云云,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对郭沫若传播行为产生效果的客观评判。
夏衍在谈到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所做的工作时,并不认为他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在甲骨文、青铜器、线装书的故纸堆里闭门过了十年“书斋生活”,他同样看到了郭沫若这十年理论工作所产生的实际传播效果。具体来说,夏衍认为郭沫若“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仅和国内的革命斗争有经常的联系,同时还团结和培育了许多留日革命青年。”兼具文艺家和革命者身份的夏衍,看问题时往往不会孤立静止地看,而是联系实践,即他并不仅仅根据郭沫若翻译、写作了哪些书、搞了哪些研究来对其进行一种“学术评价”,而是要看这些书、这些研究在青年受众当中所取得的实际传播效果。
作为稍晚一辈的作家,艾芜现身说法,讲了郭沫若的政论文章以及经典著作翻译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艾芜说:“郭沫若同志还指引我们从文艺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的《共产与共管》、《马克思进文庙》等等文章,又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人突破了文艺这个圈子,引起更新更美好的憧憬。”艾芜的话可以说为前面列举的几个评价给出了具体的注脚,周扬、夏衍等人讲的受郭沫若传播行为影响的“千万青年”之中,就包括艾芜。郭沫若传播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是具体的,而不是泛泛而谈的。
云南作家陆万美在谈到郭沫若对青年时代的自己产生的影响时,提到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我的童年》,一部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认为,《我的童年》“使我学习到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切现实生活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然看不懂,但也听许多“专攻历史的朋友”说这是“必须经常阅读的、以马列主义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教科书”。这里,陆万美强调的是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建设在青年当中产生的传播效果。
经济学家许涤新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当中起到的作用,指出郭沫若“不但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当头一棒,而且推动了当时向往光明的青年们,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我就是郭老这一部著作的热心读者之一。”同样属于现身说法,介绍了郭沫若的方法论建构在自己学习成长与方向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郭沫若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历史,还曾引起过鲁迅的关注。许广平曾经告诉历史学家侯外庐,“鲁迅看了郭老的古史考证,金文甲骨文研究,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这就是说,郭沫若的方法,不仅在后学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连鲁迅这样的思想文化巨匠也被其所吸引。由此可见,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传播,不仅是泽被后世,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得到了承认。
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实际上已经不能算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原封不动的输入了,而是其在学习、掌握了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之后,自觉应用在中国具体问题上产生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的贡献,除了译介经典理论,以及自己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外,还体现为他自己在理论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换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郭沫若这个人物的出现,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有效传播的一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