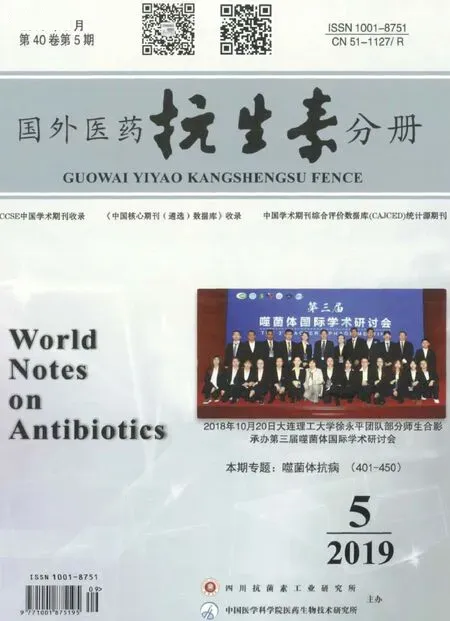上世纪50年代中国噬菌体研究成就回顾及思索
丛聪,魏炳栋,袁玉玉,李晓宇,4,5,王丽丽,4,5,李纪彬,徐永平,4,5,*
(1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4;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分院, 吉林公主岭 136100;3 大连赛姆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辽宁大连 116620;4 动物性食品安全保障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辽宁大连 116600;5 辽宁省大连赛姆噬菌体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00)
1 前言
自从发现细菌后,人们普遍认为细菌是一种最小的生物。而自从俄国学者依万诺夫斯基于1892年发现了病毒以后,人类了解到还有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存在。1898年,俄国学者加玛列发现在许多细菌中都寄生着一种比细菌还小的极小微生物,它可以溶解细菌,这也是噬菌体(Bacteriophage,简称phage)发现的起点。直到1915年,人们观察到了噬菌斑后才正式开始了解噬菌体这种生物。1917年,Felix d'Herelle率先从拉丁语字源中提取出“噬菌体”这一词的概念,其中文解释是“吞食细菌”。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重视噬菌体,他们普遍认为噬菌体对于传染病的医疗是没有效果的,而前苏联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成功的,也具有较丰富的经验。20世纪期间,人类已发现了40多种有噬菌体的细菌,如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伤寒沙门菌(Salmonella typhi)、肠炎沙门菌(Salmonella enteritidis)、耶尔森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prazmowski)和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sp.),以及被海内外学者研究颇多的痢疾/志贺杆菌(Shigella Castellani)[1]等。
自1940年起,随着抗生素产业的兴起,特别是磺胺类药品的畅销,在欧洲流行的噬菌体制剂被排挤,以致后来趋于退出市场。但同时期,因为长时间的封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百姓若是生病却买不起进口的药物,甚至有钱也几乎买不到磺胺类等抗生素的消炎药,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土办法来治病——寻找细菌的天敌。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学家在前苏联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噬菌体及其制剂,并用其防治细菌性疾病,例如痢疾杆菌(痢疾性腹泻)[2]和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烧伤)等。曾有五个前苏联研究所生产过噬菌体制剂,但却只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和霍乱弧菌等少数几类细菌,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所(原大连大学附属卫生研究所,简称大连所)是我国最早开创痢疾噬菌体制剂生产的机构,用于痢疾的防治。由于口服液体混合制剂服用剂量较大,成品又全为培养物,其味道和口感不佳,群众不太乐于接受这种噬菌体制剂[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连所的研究人员动身赶往上海奶粉制品厂采用喷雾干燥法成功制备出了噬菌体粉剂,并相应做出各项检定报告和总结,达到了中国噬菌体制剂研究成就的高峰。不料在将粉剂制成胶囊之前,全所人员奉命迁往成都与成都新所合并,不久后新所撤销了噬菌体室(曾称为法基室,音同phage室),自此痢疾噬菌体粉剂产品在我国消失,而主要的研究人员也被分散到其他科室或被调往外地,如温江专区防疫站[3]。这个阶段的摸索为中国噬菌体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奠基,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后来因为前苏联的撤资以及国内科研环境不理想,致使我国研究工作日渐没落,研究进展缓慢,可悲可叹。
为了了解上世纪50年代我国噬菌体及应用的研究成就,本文首次总结和归纳了这一时期中国噬菌体的研究工作,回顾历史并思索当年的不足,简要分析当时的成就对如今噬菌体工作所奠定的基础,对噬菌体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的追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50年代中国噬菌体研究工作
现如今,中国50年代初关于噬菌体研究的文献已极为罕见,纸质版本多为孤本,主要是从国外翻译文献中学习并开展相应的工作,从1953年起电子版存档才逐渐被保存于网络。1953年,程子明[4]描述:“噬菌体好像是一种吞噬细菌的物体,其实它并不吞噬细菌而是使细菌溶解。噬菌体分布很广,大凡有细菌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噬菌体,尤其在动物粪便中及一些脊椎动物肠内存在更多。”
1955年,郭成周等[5]从晚期战伤伤员(负伤后的1~3年,经多次手术和长期药物治疗未愈的)处采集6类感染标本,并用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科K.P1号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噬菌体对鉴定出的金黄色和白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均做了噬菌作用的观察,结果发现噬菌体(效价为108CFU/mL)对金黄色和白色葡萄球菌均有溶菌作用,分别为75 %和54 %;类似的结果也体现在铜绿假单胞菌的噬菌实验中,用产绿脓素的铜绿假单胞菌增殖的噬菌体也能适用于仅产荧光素的铜绿假单胞菌上,但不能适合于铜绿假单胞菌的全部菌株,噬菌效果分别为54 %和84 %[5];这两个实验说明两种噬菌体都不能完全适合于两类细菌的全部菌株。
1959年,吴连元和张伯翊[6]研究了肉类加工厂中的猪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他们发现猪的炭疽病大部分是由于摄取了含有炭疽芽孢的饲料和污水等,从而由猪口腔进入而感染,然而急性、败血型的猪炭疽病较为少见,原因是猪对炭疽杆菌有天然的抵抗力,并且还在健康猪的血液中发现有噬菌体的存在,故猪炭疽病的发生多限于局部性的慢性型。
2.1 噬菌体与痢疾杆菌
国内关于痢疾噬菌体研究的文献约占50年代噬菌体文献的60 %。1955年,大连所的司穉东[2]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痢疾噬菌体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噬菌体预防不同于一般的自动免疫或被动免疫。服用噬菌体预防传染病,主要是应用噬菌体的生物特性,即噬菌体对病原菌的裂解作用(即使病原菌发生变异,当然有的也可以引起某些免疫因子的增强),而消减了病原菌(或改变了它的毒力),达到人类预防的目的。因此这种作用,并不是像服用或注射菌苗(如口服菌苗及注射用菌苗)、疫苗及类毒素,而使身体产生抗体的自动免疫现象;也不是像注射含有抗体的免疫血清的被动免疫现象。使用噬菌体预防应明确这一点。”同年,司穉东[7]采取口服噬菌体的方法治疗痢疾患者,结果发现在服用噬菌体后的患者的脓血粘液便中,不论在其滤液或悬液中,全部都能检测出噬菌体。他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分离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和乙型副伤寒杆菌(Bacterium paratyphosum b)噬菌体,并发现噬菌体较耐热,加热至58 ℃处理30 min后依然能够检测出噬菌体(表1)[8]。另外,司穉东[9]发现口服痢疾噬菌体的健康人的粪便中能够持续检出痢疾噬菌体,时间跨度为3 d~15 d,并且在尿液、乳液(以及被哺乳婴儿的粪便)和唾液中均能检出,说明噬菌体被消化道吸收后可随血液等循环至肾脏、乳腺和唾腺内并随之排出;次年,他在小白鼠的实验中也证明了该结论,注射福氏痢疾杆菌(Flexner's dysentery bacillus)与志贺杆菌混合的多价痢疾噬菌体后,噬菌体可在小白鼠的脑、血液、肝、肾、肺、肠和脾中存留很长时间(在脾脏中至少可长达37 d),但在粪便中未检出噬菌体[10]。因此,噬菌体通过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可到达肠道、肝、脾、肾、肺、脑、血液、乳腺和唾腺等处,并且能够停留一段时间。
1956年,何明达[11]对某团驻地步兵爆发的流行性痢疾进行研究(图1),试用了痢疾杆菌的志贺和福氏多价混合噬菌体(大连所1954年出品)进行治疗,并结合各项卫生预防措施有效控制了痢疾的季节性流行。
但在1958年之前,国内外关于痢疾噬菌体应用于痢疾预防上的实验研究有过不同的报告,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痢疾噬菌体并无预防痢疾的功效。1957年7月~10月,张挺和郑丕志[12]使用大连所出品的痢疾杆菌多价噬菌体(志贺和福氏)对无锡在驻部队1543人进行了噬菌体实验,并连续服用了14次噬菌体制剂(服用11次后仍有痢疾发生),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痢疾发病率分别为1.23 %与1.29 %,他们认为所服用的5种批号的噬菌体对散在性痢疾缺乏应有的预防效果,效果不佳。本文作者认为之所以没有显著性差异的结果可能与地域性的不同有关,应考虑到噬菌体特异性较强的特点,而不应归咎于噬菌体制剂本身的无效性。
1959年,赵树壁等[13]在做痢疾细菌学检查的同时进行了噬菌体的分离工作,自北京流行菌样中分离制备痢疾多价噬菌体以供临床试用,并企图观察噬菌体在急性和恢复期病人中出现的百分率与培养阳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从221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5例痢疾噬菌体,噬菌体的分离与细菌培养及病程上的关系表明培养阴性病例及恢复期病愈除了由于药物因素外,还可能由于噬菌体的作用;当年北京流行主要为福氏和宋内痢疾杆菌(Shigella sonnei),因此只制备了二价混合噬菌体制剂供临床试用,但由于和临床未能密切联系且未能继续供应噬菌体,因此无法获得确切的疗效资料[13]。

表1 司穉东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离痢疾、伤寒和乙型副伤寒噬菌体[8]
1959年,王德旺等[14]对驻渝部队3055人进行了粪便菌调查以及非典型痢疾杆菌的噬菌体可溶性研究,结果表明,检出的27株非典型福氏痢疾杆菌中有19株可被噬菌体所裂解,占70.37 %,可见非典型福氏痢疾杆菌与噬菌体存在较密切的关系,并且非典型痢疾杆菌带菌者仍应作为痢疾杆菌带菌者处理。
上世纪50年代末,痢疾噬菌体制剂一直是我国防治细菌性痢疾的唯一正式生产的生物制品,投入使用后应用于全国各地,在预防和治疗细菌性痢疾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在我国学术界却对痢疾噬菌体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理论上来说,用噬菌体治疗和预防细菌性痢疾是最理想的药物,并且方法简便、无抗药性,容易被人接受。但需要注意噬菌体的裂解效价、裂解范围、服用方法和次数等等条件,业界之所以褒贬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噬菌体的性能,噬菌体特异性较强,并受环境、生产和使用方法的影响而效果各异。1959年,郑韦明[15]对噬菌体用于预防细菌性痢疾及治疗等发表了一些个人的看法,阐述了我国在生产和使用痢疾噬菌体时存在的问题,并对噬菌体工作的研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2.2 噬菌体与发酵产业
我国早期对噬菌体的研究也有一部分集中在如何预防、消除或杀灭噬菌体等方向,医疗领域主要以抗噬菌体血清为主导[16,17],生产领域主要以发酵工业为主导,而噬菌体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发酵罐中的产品质量,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18]。自从我国链霉素的发酵生产遭到放线噬菌体的侵蚀以后,研究人员除了积极选育抗噬菌体的菌株以保证生产能继续进行外,又展开了一系列对放线噬菌体本身的研究[18]。

图1 何明达使用噬菌体制剂对某团驻地步兵爆发的流行性痢疾进行研究[11]
1957年,许文思等[18]为了防止链霉菌在发酵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受放线菌噬菌体的侵蚀而开始研究抗噬菌体的方法(再生的抗性菌X4),并对分离出来的灰色链霉菌(Streptomyces griseus)噬菌体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发现噬菌体是在菌丝繁殖时才能繁殖;同时,他发现噬菌体原液在4 ℃条件下保存7 d后浓度会降低24 %左右,而用冷冻干燥法处理并保存在真空安瓿瓶中的噬菌体,2年后效价未见降低,这说明链霉菌噬菌体在冷冻干燥环境下能保存很长时间[18]。
寄生链霉菌对其噬菌体非常敏感,在培养皿中不易产生再生性菌落;即使在液体培养情况下,链霉菌的菌丝体经溶解后,在一星期内亦不能产生再生性的菌丝体[19]。1958年,徐尚志等[19]对放线噬菌体进行了精制和提纯试验,从灰色链霉菌530的发酵培养液中分离出噬菌体530-P,噬菌体含量可达到1010~1011个/mL,他们不断摸索培养条件,并对提纯的噬菌体性能做了研究。放线噬菌体培养液经过过滤、硫酸铵盐析、胰蛋白酶消化后,再用流水透析法去盐,最后以冷冻干燥法得到白色棉絮状无定形物,回收率为60.8 %。精制品经过分析,得到每个放线噬菌体重量为1.15×10-12mg,含氮量为2.8×10-13mg,即噬菌体含氮量为19.0 %(图2),这说明噬菌体是由核蛋白质构成的[19]。
2.3 噬菌体型别分类
积累了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噬菌体后,我国学者又着手于研究噬菌体及其宿主的分类。噬菌体型别分类的依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含有Vi抗原菌株的分型法,另一类是对仅含有O抗原菌株的分型法[20]。一般来说,前者的结果简明而确实,如伤寒杆菌的噬菌体型别由一株噬菌体的作用而决定,有临界溶解现象者即定为该型;但后一方法则靠数株噬菌体的共同作用,以不同的反应模式为标准而定型。1958年,徐镖秀等[20]在国内率先研究了福氏痢疾杆菌噬菌体的分型研究工作,他用5株噬菌体对355株武汉市流行的菌株进行试验,出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和不同的反应模式,重复试验多次后反应模式及噬菌斑无变化,并且在抗噬菌体血清中和实验中证明了这5株噬菌体在血清学上是不相同的。因此,噬菌体分型对于某些细菌在追溯传染源上有一定的帮助。

图2 徐尚志测定了不同温度和pH对放线噬菌体的活力影响[19]
2.4 噬菌体与抗生素联用
随着科研领域的扩展,有关化学治疗剂及噬菌体对病原菌协同作用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上世纪50年代,细菌性痢疾仍为国内常见的传染病之一,且多由福氏痢疾杆菌所引起,磺胺类药物仍作为当时治疗细菌性痢疾的常用药物,由于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尝尝会引起用法不当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给痢疾疾病的治疗带来种种困难。抗生素与痢疾噬菌体配合作用于痢疾杆菌时,可能由于痢疾杆菌的生理学性状有所改变而易被裂解或抑制,也可能协同作用的一方面增强了另一方面的活动能力或抑菌力,而能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1924年-1950年,在氯霉素应用和普及之前,人们对伤寒患者的治疗除了使用一般的保守疗法以外,也有国外学者主张采用噬菌体治疗。1948年-1958年,国内外医疗学者均认为氯霉素是治疗伤寒的特效药,不论在病的哪一期、病情的严重程度如何,均能使患者迅速退热,中毒症状显著减轻或消失,血液细菌培养也很快转为阴性,但是这种情况也具有20 %~25 %的复发率[21]。若盲目加大剂量或延长疗程可以降低其复发率,但由此也可能引起造血系统的损害。
1958年,李萍等[22]率先研究了痢疾杆菌噬菌体及磺胺噻唑对痢疾杆菌的协同抑菌作用,结果表明,二者相互配合后,噬菌体的溶菌力及磺胺噻唑的抑菌力皆有所增高,并能明显抑制再生菌的生长;磺胺噻唑的浓度越高则协同作用越强,但差别并不显著;噬菌体的稀释度越高则其协同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抑菌效果的强弱可因菌株而异。同时,她发现协同抑菌作用对耐药性菌株同样能发挥作用,并能抑制耐药性菌株的再生长,但暂时没有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22]。她认为抗生素的化学性质及其本身的抑菌机理不同于噬菌体,因此二者协同作用的机制机理值得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959年,彭仁玲[21,23]研究了氯霉素和噬菌体ty2(由大连所提供)对伤寒杆菌的协同抑菌作用,结果表明,氯霉素在各种不同浓度下对伤寒噬菌体的活性没有不良影响;加入多价噬菌体后,氯霉素的剂量可降低至0.1~0.3 μmol/L(即原剂量的1/15~1/20),若可在临床上配合氯霉素治疗,效果更为理想;加入噬菌体3~6 h后再加入氯霉素的治疗效果更佳,因为噬菌体在4 h左右已将大部分细菌裂解,此时再加入氯霉素可将剩余的细菌抑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并且不论同时或先后加入氯霉素和噬菌体,其抑菌能力均较单独使用任何一种物质的效果更好[21,23]。
2.5 噬菌体的性质及应用
我国学者在研究噬菌体的初期,已从国外文献中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噬菌体都是有尾部的;噬菌体可在固体培养基上产生噬菌体的集落—“噬斑”(即噬菌斑);溶菌后还有细菌不被溶解并能继续繁殖——“再生菌”(即抗性细菌);噬菌体只能溶解活菌,不能溶解死菌;一种噬菌体只能对某一种细菌的某一型有作用,对其他型的细菌不起作用,可用来区分细菌的种别或类型——特异性;噬菌体还有抗原性,注入动物体内可产生特异的抗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学者已经了解到了噬菌体的这些特性,并且开始将噬菌体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比如治疗由多种细菌混合感染的炎症,或不同时期细菌反复感染的炎症。
在5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对噬菌体性质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对毒力弱的噬菌体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敏感细菌的一部分细胞,在毒力弱的噬菌体的作用下不被裂解而形成所谓赋裂解性(lysogenic)细胞—也即如今所说的含有溶原性噬菌体的细菌。当时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噬菌体以所谓“前噬菌体”(prophage)的形式存在于细菌细胞内,并随着细胞的分裂而传给下一代,且不影响细菌细胞的繁殖。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如X射线、紫外线照射或某些化学物质的作用),使“前噬菌体”与细菌之间的平衡破坏时,则“前噬菌体”转变成活动性噬菌体(即裂解性噬菌体),而细菌细胞也随之裂解。部分细菌的某些生物学特性可以通过毒力弱的噬菌体的作用传给另一个菌株,此种现象被称为“传递”(transduction),为了阐明该现象的本质与机制,1959年,李焕娄[24]对鼠伤寒沙门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毒力不同的4种噬菌体的生物学性质进行了比较及研究,结果表明,在抗噬菌体血清交叉中和实验、敏感细菌细胞的吸附率、单循环繁殖实验(即一步生长曲线)、温度以及紫外线照射等实验中,属于同一血清学组的噬菌体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而毒力不同的噬菌体在各方面与其他组皆有明显的差别。
噬菌体在实际应用上,特别是广泛地应用于预防措施时,常常需要结合大量的实验来验证,否则所能达到的期望会缺乏应有的效果。噬菌体对于细菌学诊断临床诊断流行病学以及预防治疗上都有应用价值,学者们还进行了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及外伤治疗的实践,分别为:
(1)分类细菌:比如已发现伤寒杆菌有23种噬菌体,可将伤寒杆菌分成23型;大肠埃希菌用噬菌体可以分出7型等,但用血清学的方法不能分出这些型;
(2)某些细菌的鉴定:如检查鼠疫患者的血液、痰液时,除应用了一系列的涂片、培养和凝集反应外,最后可以用噬菌体试验来确定是否是鼠疫杆菌,也即将噬菌体放入鼠疫杆菌培养基内是否能看到溶菌现象;
(3)流行病学上的应用:如在伤寒流行病区域可以用噬菌体来鉴别带菌者所携带伤寒杆菌的类型,这样可以帮助了解某些区域伤寒流行情况;
对于“供给侧改革”,经济学人在报道中将这一术语与里根时期的供应经济策略相提并论,并将二者进行了对比。该报道中包含了两则概念隐喻——“经济问题是疾病”和“经济改革是旅程”。在例1中,在“经济问题是疾病”概念隐喻中,该报道承认中国的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经济弊病对应于人罹患疾病(例1),重大改革对应于真正的大手术(例2),刺激经济对应于暂时用药物刺激病人缓解痛苦。在“经济改革是旅程”概念隐喻中,政策的改变对应于旅程路线或方向的改变(例3),路线和方向的改变或可以使旅程更加顺利。上述表达一方面体现了外媒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体现了外媒对“供给侧改革”并不看好。
(4)某些传染病的预防:如霍乱杆菌、痢疾杆菌等都可以用噬菌体做为疫苗来注射,起到预防的功效;
(5)某些传染病的治疗:如伤寒、疮疖、气性坏疽和小儿夏季肠炎等疾病,这些都可以用噬菌体来治疗;
(6)研究病毒的生物性质:如病毒的变种问题,以及细菌、病毒和噬菌体的关系等;
(7)医学治疗:我国最早一则著名的噬菌体治疗案例至今被人们广为称赞。1958年,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余 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抢救大面积钢水烧伤的邱财康(全国著名劳模、钢铁工人),在此期间,邱财康的大腿发生严重的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病情持续恶化,余 用自制的噬菌体控制了铜绿假单胞菌的繁殖,在创造治疗重度烧伤病人的奇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5]。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此案例拍摄电影《春满人间》,由桑弧执导,白杨等人主演,主要讲述钢铁工人丁大刚奋不顾身抢救一炉钢水而被烫伤,在抢救过程中丁大刚的右腿被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病情急剧恶化。微生物学夏教授和医院党委书记方群主张尝试培养噬菌体、消灭铜绿假单胞菌的新医疗法,尽力保全丁大刚的肢体,最终在各界支援下,治疗所需要的噬菌体终于扩增出来,丁大刚的右腿保住了,痊愈后他又重返到了炼钢岗位继续奉献。
3 大连所痢疾噬菌体制剂的成就
当年在大连所生产噬菌体制剂时,不论在生产规模、生产技术或是人力上的特点可归纳为3点:培养液量大、装备条件落后和工作人员劳动负荷较强[3]。原因是由于液体培养物需用大瓶(5 L-10 L)装载、经接种培养后混入大罐,用超大型除菌滤过器过滤后,再用500 mL瓶子进行人工分装。所幸原大连所备有一台老式大型多层板式除菌滤过器(当时国内仅此一台)和Seitz大型滤板为大量液体制剂的生产解决了问题[3]。这些大瓶培养物和大罐从培养室里搬进搬出全靠职工人力相互传递,因此噬菌体室是当时大连所人员最多、最耗人力的生产室。令人欣慰的是,痢疾噬菌体这一产品为当时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部队,以及安徽省在建的好几个大型水库工人的痢疾预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
司穉东及其同事们在大连所工作期间为痢疾噬箘体的生产和科研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主要业绩如下[3]:
(1)在临床治疗和预防应用方面,他们发现只要噬菌体型别与感染菌型一致则必然会有效果,即便当不知道型别时使用也具有一定的预防效果;
(2)噬菌体的治疗效果优于磺胺类药品(那时青霉素还未上市,仅有磺胺嘧啶和磺胺胍);
(3)在用小动物作基础理论探究时,无论口服或注射均可在各个器官或组织内检出噬菌体,只是数目分布各不相同(但注射后未能在动物肠道内检出噬菌体),这表明噬菌体口服法可方便用于防治疾病;
(4)他们对伤寒、乙型副伤寒和鼠疫杆菌噬菌体做了分离和研究;
(5)他们就噬菌体用于临床诊断和菌群分型工作做了初期的摸索研究;
(6)大连所并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后,成都所在20世纪50年代与英国合作在我国建立了唯一一家“金葡菌专业实验室”,在21世纪前后已分离到5型共计23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但后期因人员调动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4 50年代我国在生产和使用噬菌体制剂时存在的问题
我国研究痢疾噬菌体的工作实际上是在解放后才开始的,1949年大连所在前苏联专家歌洛毕兹的帮助下开始生产痢疾噬菌体,随后几年相继有产品制出,并在全国各地广泛使用,由于当时限于经验不足,痢疾噬菌体制剂生产与实际结合地不够,因此在生产和使用上存在诸多问题:
(1)型别不全:1949年-1957年初生产的噬菌体是志贺和福氏2a两种噬菌体的混合制剂,1957年3月开始改为志贺、福氏、宋内和舒密次等四种噬菌体的混合制剂。但根据1957年各地痢疾杆菌分型资料来看,各地流行的菌株类型及占比各不相同,因此治疗效果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当时大连所并没有生产福氏1b噬菌体,以后虽在生产中选用了福氏1b噬菌体,但效价很低,不能达到法规生产的要求,同时福氏Ⅲ型噬菌体也没有加入混合制剂当中,因此生产出的多价噬菌体制剂对福氏菌株的裂解范围较窄;
(2)未及时更新:在规程内规定每年生产用的地方菌种必须占有25 %,并适时更换,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当时能够成产噬菌体的只有大连所一家,直到1958年武汉所才开始试验生产。由于对各地菌型的分布调查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在生产时并没有按地区需要加入对应的菌种,因此无法提供出理想又高效的噬菌体制剂;
(3)口味不佳:噬菌体制剂的气味和口味并不好,还向其中加入了石炭酸作为防腐剂,石炭酸有酚味,群众们形容其为马尿味,并且在使用时没有按规定方法服用,而是将苏打水和噬菌体混合服用;
(4)未能连续服用:大连所的痢疾噬菌体制剂对预防痢疾杆菌是有显著效果的,在一定的时间内,预防组的发病率比对照组降低了2~5倍;当用于预防痢疾时,该制剂应连续地每隔5 d~7 d服用一次,若超过时限则会使预防能力减退,特别是在痢疾流行期间必须连续服用;服用时应先服用苏打水中和胃酸,给噬菌体造成有利环境而不被胃酸杀灭,在5 min~7 min后再服用噬菌体制剂,而不能将二者混合在一起服用;在使用噬菌体制剂之前应先进行噬菌体与当地流行菌型的裂解实验。
由此看来,当年我国在生产和使用噬菌体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使噬菌体在防治痢疾工作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学者们盲目地否定噬菌体制剂的效果也是不恰当的。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随后几年痢疾噬菌体在防治痢疾方面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用噬菌体治疗细菌性痢疾的效果也是可以被肯定的:单独使用噬菌体制剂比单独使用磺胺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更好,并且噬菌体可以治疗抗药性(包括抗生素和中药)痢疾患者;噬菌体制剂既可采用口服法又可采用灌肠法,后者的效果更显著;服用噬菌体制剂后几乎不会出现不良反应,在复查中也几乎没有复发患者。
因此,噬菌体制剂效果不好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未能正确了解噬菌体的性能,并且没有正确地使用噬菌体,因而会得到相反的效果。事实上,噬菌体预防痢疾疾病不但有科学理论依据,还在当时痢疾流行的情况下可作为最佳的预防手段。某些研究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不同结论的噬菌体制剂效果的文章,其实验设计方面的评价,发表后给我国医务工作者带来了一定影响,甚至武汉所生产噬菌体的研究者也不能明确指明噬菌体制剂的效果。所幸,我党和卫生部均高度重视噬菌体治疗的工作,于1957年责成大连所、卫生部生物制品鉴定所和内蒙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等单位,于内蒙萨县进行了两年的痢疾噬菌体流行病学效果观察,在最终递交的材料里可以看出用痢疾噬菌体预防细菌性痢疾是一个重要方向。1957年,郑韦明[15]在内蒙萨县做了2897人噬菌体治疗效果调查,采用口服多价痢疾噬菌体制剂,细菌菌型均在多价噬菌体裂解范围之内,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
5 50年代末中国噬菌体研究的发展方向
经过几年的摸索与探究,研究者们发现细菌的型别和噬菌体的数量(也即裂解效价)是取得细菌性疾病治疗效果的两个重要因素[3],并总结出了此阶段的经验教训,奠定了未来的研究方向:(1)应选择并研究裂解面广、溶菌力强、裂解速度快的噬菌体,这是保证噬菌体具有有效的预防效果的措施之一。事实证明,效果弱的噬菌体在预防价值上利用率不大,因此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大力研究并选择强裂解性噬菌体种液投入生产,同时对噬菌体制剂的质量监督也应加强采用和研究新的鉴定方法,以使其质量得到保证;(2)生产多价或单价噬菌体制剂必须符合地方流行菌型,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材料证明不对型的噬菌体不会获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生产和鉴定部门必须与使用部门进行密切协作,掌握地方流行菌型才能够发挥噬菌体应有的作用。
6 小结与思索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研究学者们还并不了解噬菌体为什么能够溶解细菌这个问题的机制和机理,有些人认为噬菌体有酶(又称酵素)的作用因此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前苏联生物学家波什杨认为:“噬菌体不是寄生于细菌的独立的微生物,更不是非生物,而是细菌形成细胞前一阶段的有生物微粒,是细菌为了适应环境而转变的一种能通过滤菌器的过渡形态。”
十年转瞬即逝,人们对噬菌体从最初懵懂阶段突飞猛进跨越到对其性质及应用的研究,若非受到了当时科研环境的影响,我国关于噬菌体制剂的探索可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因此我国的科学研究在未来一定有更好的发展,对于噬菌体的研究,未来一定会与格鲁吉亚的发展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