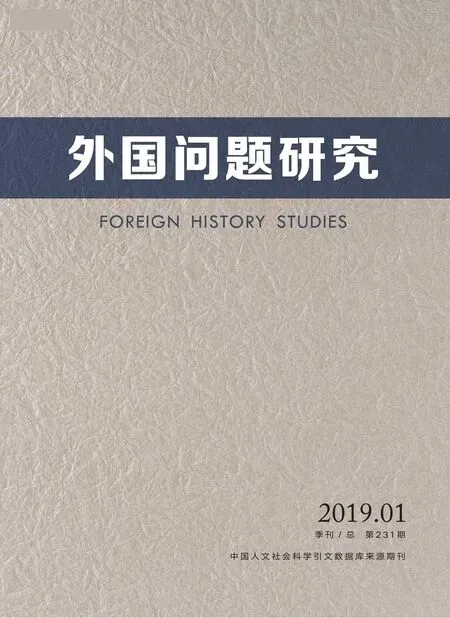“儒学日本化”与“日本儒教”之间——与吴震教授商榷
张崑将
(台湾师范大学 东亚学系,台湾 台北 106)
笔者在过去一次的朱子学研讨会中,看到一篇讨论有关日本《教育勅语》的论文,当时作者研究的是中国朱子学,对日本儒学的研究不是很清楚,只看到某学者引用《教育勅语》中有关“忠”“孝”等的儒家相关用语,便断然称朱子学缔造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由此看到儒家对日本近代的影响力。作者的原意是为了阐扬儒家在近代日本仍然有其生命力与影响力,故举了这样的例子。当时,笔者提醒他,你所谓的“儒家”是经过被日本化的儒家,且是皇国主义体制下的御用儒家,不是孔孟学或朱子学的儒家,应该区分清楚。以上的插曲,事实上涉及“儒教日本化”的课题,迄今为止,一些研究儒学的学者,由于比较缺乏东亚的视野,对于近代儒教被日本化一无所知,导致以讹传讹的情况还真是不少。吴震教授2015年出版《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以下简称“吴书”),正可澄清这类的误解。[注]吴震:《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为行文方便,以下均简称“吴书”。
吴书前言即点出儒学日本化的现实脉络关怀,故在本书开宗明义的摘要中即点出:
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的“原型”致力于探索“日本性”,便与此问题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吴书,第2页)
由此可知,本书关心两大问题,其一是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来迄今有关“儒学日本化”的发展过程,由此企图呈现“日本原型”或“日本性”的关键课题;其二是关心儒学日本化的同时,也关心当今“西学中国化”的问题,因为“西学中国化”也面临目前中国恢复传统国学的过程中如何吸收与转化“西学”的课题,吴书几乎在全书各章的结尾部分都表达这个关怀课题。
既然讨论到“儒学日本化”与“西学中国化”的相关课题,也许我们可以比较明治维新后的30年与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迄今将近30年的历史发展比较。如所周知,中国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以不到30年的时间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彷若当年的明治维新后三十年(1870年代—1900年代)发展的改革富强阶段。日本在这三十年发展期间,于1890年推出《教育勅语》,强调“忠孝一体”的国体观,并透过“祭、政、教”三合一的体制推动“国家神道”,禁止所有宗教,“国家神道”成为超越所有宗教的宗教,并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于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强化大日本帝国的万世一系的天皇主权说,又经1905年日俄战争中崭露头角,日本国势如日中天,遂一步步投入帝国主义行列,一发不可收拾。当是时,日本知识分子面对如日中天的国势,许多人本是人权论者纷纷转向国权论者或进化论者,一些本是儒家普世信仰者也转向拥抱帝国正当性者,更有本是基督教信仰者也转向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那个大时代与大环境里,日本人开始注意“日本人的天职”,从“日本人中的日本”逐渐升华到“亚细亚中的日本”乃至“世界中的日本”,思考要在亚细亚中或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是要以“亚细亚盟主”的膨胀姿态来对待其他亚洲国家,或是摆脱帝国主义心态,诚心以济弱扶倾的心态帮忙亚细亚诸国等观点来认知日本国的天职,事实证明日本人选择了前者,迄今这个议题仍然困惑着日本人。在那个大时代与大环境里,不论是旧有的中国儒教思想,或是趋新的西方思想,都高度地像快餐一样被吸收、排斥、消化并转出“一致性”帝国需要的产品。
以上是吴书所涉及的“儒教日本化”主题的时代背景。如今中国也走过三十年,其国势与经济之盛,与当年明治维新的发展何其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外貌富强相似的背景下,却有着内在体质的根本差异,在日本涉及“日本性”或“原型”的问题,在中国则是否也关乎“中国性”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我想吴书最终也想解开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一、“儒学日本化”的华人研究概述
吴书共分七章,作者虽无分类,笔者约归为四部分,其一是有关“儒教日本化”言说出现的背景说明,其二是与“儒教日本化”言说至关重要的思想冲击与响应,诸如“近代化”与“日本化”(第二章)、“日本道德论”与“国民道德论”(第三章),以及“近代超克论”与“道德生命论”(第四章);其三是考察战前至当代学界对“儒教日本化”的思考与争论,特别以丸山真男为主轴(第五章),并扩及其他当代重要学者相关的论述(第六章);其四是由儒教日本化回到思考“中国化”的当代问题(第七章)。以上四部分架构堪称完整,次第分明,亦照顾到从战前到战后的时间序列,在各章最后往往又透露作者“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的用意,即常常“由日本化想到中国化”的当代关怀。就笔者所知,本书是目前华语学界直接探讨“儒教日本化”最为完整且详细的研究专书,对有心想了解“日本化”“日本特色”“日本精神”或“日本式思维”等学界同好,此书有画龙点睛的参考作用;同时本书也对当前中国上下积极恢复传统儒学或国学的现况,亦有殷鉴与启迪的作用。
本书若单独观赏,无法凸显其特色,但若与当代华人诸多重要的日本儒学研究专著相较,或可更能看出本书的特色与贡献。揆诸华人学界对日本儒学的研究开宗者当推朱谦之在1962年即出版《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撇开书中有关唯心与唯物及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朱谦之当年针对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及阳明学派,在最后总结时,点出“儒学日本化”的问题,他说:“这两种哲学传入日本,均不得不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结合,最后变成反动的思想体系之一,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注]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85页。本书有最新版本,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朱谦之这个观察耐人寻味,点出认识近世儒学与近代儒学的不可分割性,笔者过去曾撰文日本江户时代神儒兼摄学者有“神儒合一”与“神儒一其揆”的两种神儒习合调和方式,这类学者在江户时代为数真的不少。[注]张崑将:《日本德川时代神儒兼摄学者对“神道”“儒道”的解释特色》,《台大文史哲学报》2003年第58期。迈入近代,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事实也证明,神主儒辅的扮演角色依然换汤不换药。可见当我们探讨近代的“儒学日本化”的课题时,难与前近代的德川儒学日本化断为两橛,关于这个问题,在本文第二节另有详述。
继早期朱谦之投入日本研究的代表者是王家骅,他于1988年也曾出版《日中儒学の比較》一书,在最后一章提到“日本儒学的特质”,提出以下六项特质:1.疏于抽象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思考;2.重视感觉经验的认识论;3.富于感情色彩的伦理观;4.“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5.强调灵活对应现实;6.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注]王家驊:《日中儒学の比較》,東京:六興出版,1988年,第339—352頁。此书在1994年台湾即有中译本《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但少数部分章节有调整。王家骅以上六点的归纳对于考察“儒学日本化”有抽丝剥茧的作用,同时也都不是切割近代与前近代儒学的观察,实可补充吴书未能涉及“前近代”儒学日本化的现象观察。
讨论儒学日本化课题,近年来韩东育的两本姊妹力作相当重要,2009年出版的《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与2016年出版的《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去中心化”之行动过程》,[注]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去中心化”之行动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二书系韩东育周游于东亚区域之中,不仅融贯中日文献,贯穿中日古今时空,扣紧日本的“去中心化”之主轴,提出许多合理的疑问并抽丝剥茧,或周游于中国、日本的神话书,或与丸山真男对话,或质疑福泽谕吉之论点,或探索从“请封”到“自封”的华夷秩序变化过程,融贯中日及古今,鲜明地呈现日本从“请封”(由夷变华)到“自封”(自立华夷秩序)的“去中心化”到“自中心化”之过程,一一加以响应解答。毫无疑问,从书名便可浓浓地嗅出“儒学日本化”甚至“脱儒化”与“自中心化”的过程,亦可为吴书厘清“儒学日本化”的前近代历史轨迹与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关系。
总之,几乎所有有关华人讨论到日本儒学的相关著作时,难免都会碰触到“儒学日本化”的课题,但都倾向针对某一人物或学派,或集中在江户儒学,或是将日本纳入“儒教文化圈”来讨论儒学日本化的特色等等,比较缺乏直接将“儒学日本化”做一个完整的课题,并集中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来的“儒学日本化”现象,做一比较完整的分析,对于日本近世儒学迈入近代的“儒学日本化”的重大转折,吴书给出明确的概念史考察,与前面诸代表作品可交相辉映。
二、“儒教日本化”与“日本儒教”区隔的问题
笔者十多年前到日本做短期研究时,也曾与江户时期教育史研究者讨论到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当时我一直使用“儒学的日本化”或“日本化的儒学”,日本教授当面订正我,应该使用“日本儒学”,当下触发我深入思考“儒学的日本化”与“日本儒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何在?前者总还是有母体的“儒学”渊源,寻求“转变”“转化”,比较无法凸显“日本主体”。“日本儒学”则是一个“完整主体”概念,主体是“日本”,它不需要再执着于“转化”或“转变”,就是一个“完整主体”概念的日本儒学,就如同我们说“中国儒学”或“朝鲜儒学”一样,这个“完整主体”概念本身有独立于母体渊源的中国儒学,取得与之平等主体的地位。虽然不免心中仍存有疑问,但在日本知识人心中,当谈到儒学时,他浮现的概念,往往是不同于中国儒学,而是已经融入日本风土的儒学,成为日本主体的一部分。儒学日本化的“化”字还是会牵涉有母体的“儒学”渊源,较难凸显日本主体,而“日本儒学”此一概念的主体是日本,儒学成为日本本有的东西,刻意反客为主,比“化”还更强调主体性,它与“中国儒学”“朝鲜儒学”一样具有平等的主体性功能。
但是,吴书在第一章一开头便对“儒教日本化”与“日本儒教”的差别进行区隔,[注]在日本学界一般使用“儒教”一词,并非指的具有西方“宗教”意义的儒学,而是作为“教化”与“教学”功能体制下的儒学,本文及吴书所称的“儒教”是指这类“儒教”的意涵。但少部分涉及儒学具有祭祀、祭神的功用时,“儒教”也带有神圣性祭祀的宗教意涵。并言“日本儒教”之说法“不常见”,因为使用“日本儒教”会给人一种印象:“似有一贯通整个古今日本历史的‘日本儒教’之实体。”作者使用“实体”一语,依笔者揣测是指“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主导整个国家的政策与意识形态之运作,因为作者接着说明此书偶尔会出现使用“日本儒教”,但它是在以下的脉络下使用:
本文仅在儒教“日本化”这一宽泛意义上,使用“日本儒教”,具体指17世纪以降的近世日本,以及1868年至1945年的近代日本,至于中世以前及近代以后,儒教在日本社会文化中是否占据核心地位,在我看来是颇为可疑的,特别是把当代日本社会说成是“儒家资本主义”或将日本文化归属“儒家文化圈”,则完全是一种想象而已,若在当今“东亚儒学”研究中,仍把日本视作“儒教国家”则应慎之再慎。(吴书,第7页)
上述作者企图切割“儒教日本化”与“日本儒教”,并赞同丸山真男否认日本是属于“儒教文化圈”,乍见之下,言之成理,细论下去,恐未尽然。诚然儒教在日本17世纪以前无法与佛教文化在日本相比拟,也在17世纪以后虽然经过幕府将军大力提倡,但儒教也只能与当时德川上下社会热衷的佛教、神道教鼎足而三,也就是没有如朝鲜、中国居于核心的地位。但是,近代诸多使用“日本儒教”的学者,完全也认知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并不能否定有一“日本儒教”的存在。何以言之?以下论之。
首先,以是否占据“核心地位”就否定“日本儒教”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这样的说法,如同儒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极端式微,受到佛教、道教的双重夹击,所以这一时期没有“中国儒学”;或如说“佛教”在中国的明代不是核心地位,所以明代一朝没有“中国佛教”。我也许再用一个比喻,台湾有许多民间信仰如关公、妈祖信仰来自于中国,他们都不是国家、政府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显然有“台湾妈祖”“台湾关公”的信仰一直影响着庶民百姓的精神生活,迄今亦然。当然“台湾妈祖”“台湾关公”一定涉及“妈祖台湾化”与“关公台湾化”的课题,就如同“日本儒教”一定涉及“儒教日本化”的课题。
其次,使用“日本儒教”的学者,不仅在近代有诸多学者使用,甚至在江户时代已有学者使用“我邦儒学”“我邦儒林”,[注]“我邦儒学”见山田慥斎出版的《闇斎先生年谱》(1838年刊),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巻3,東京:鳳出版,1971年,第15頁。“我邦儒林”见长野豊山:《松陰快談》之《儒林雑纂》,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巻14,東京:鳳出版,1971年,第8頁。比作者举出明治维新后第一个使用“儒教日本化”的德富苏峰还更早(吴书,7—8页),即使当代许多学者的著作,也都自然使用“日本儒教”或“江户儒教”。[注]山下龍二:《儒教と日本》,東京:研文社,2001年。吴书中也提到的中村春作的《江戶儒教と近代の“知”》,東京:ぺりかん,2002年。我以下举战前岩桥遵成有一代表作《日本儒教概说》,出版于1925年的昭和时期。此书将“日本儒教”分为四期:第一期儒教传来至平安期,第二期镰仓至德川期,第三期德川时代儒学全盛时期,第四期明治维新至现代期。在绪论中标题为“日本儒教的意义及价值”,一开始即引用《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岩桥氏特别注意到“下袭水土”,意谓儒教进入到日本后,注意到与日本国不同的历史、国体与地理环境的风土,经过独特的“日本化”后,成为适应日本的“日本儒教”。岩桥遵成以下更说得很具体:
我邦先哲以坚定十分的国民性自觉,咀嚼此外来的思想,取其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真实体得孔孟之教旨,以能融合我国体之本义,阐明一个独立的教义,此即日本儒教本来之面目。换言之,所谓日本儒教,以我日本固有之精神,解释孔孟之教义。[注]岩橋遵成:《日本儒教概説》,東京:寶文館,1925年,第3頁。
可见,在其专著中并没有企图说儒教在日本具有核心地位。显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儒教”说法,在国体论的氛围下,呈现上述所引“所谓日本儒教,以我日本固有之精神,解释孔孟之教义”之特色。换言之,儒教在日本是扮演辅助“日本固有之精神”而被使用,此就其工具性意义而言;另外则是任何外来思想,即使像孔孟的教义(乃至佛教、西方思想),也需要用“日本固有精神”加以解释,成为符合日本国民性的东西,此涉及“转化”的课题,而笔者认为吴书所谓“儒学日本化”是偏属于这个层面的问题。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厘清,战前日本学者用“日本儒教”此一概念,一是就“儒学当成辅助性工具作用”而言,一是就“儒学日本化”而说,但在吴书刻意切割“日本儒教”与“儒学日本化”的关系,则会遗漏“儒学作为工具性”的课题。并且,事实上吴书在第一章讲述明治维新以后一开始举出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1893年出版)一书及武内义雄(1886—1966)的《日本の儒教》强调“儒教日本化”的课题时,仔细窥其内涵,事实上都在表达笔者上述“日本儒教”的双重内涵,既有儒学工具性意义,又有以“日本固有之精神,解释孔孟之教义”的儒学日本化之意义。这也证明何以武内义雄用的书名是《日本の儒教》,书中并常用“日本儒教”一词,虽然“日本儒教”词语受到当代学者子安宣邦的严厉批判,但不能否定“日本儒教”一词是作为明治维新十九年(1886)后恢复汉学作为“皇国道德”的工具之内涵与事实,若光讲“儒教日本化”,会有遗漏“工具化”这项事实,因此“日本儒教”之用语反而比较精准,实没有必要切割。就如同吴书在最后一章表达所谓“日本儒教史”有两种解读的可能:一是“在日本的儒教史”,另一是“日本儒教的历史”(吴书,第123页),前者是通贯的日本儒教史,后者是以明治维新以后强调“国民道德论”的狭隘的“日本儒教”。
因此,若就“儒学当成辅助性工具作用”而言,当我们谈“日本儒教”这个课题时,实不应切断其“前近代”的因子,也就是说儒教传入日本,经过“去脉络化”后,又加以“再脉络化”,所形成的“日本儒教”特色,经过抽丝剥茧后,我们将也会发现有其同构型,可见探讨“日本儒教”的近代性,也不能与“前近代”割离。下面以最具有日本儒教特色的古学派之儒学特色分析为例,来说明儒教被“工具性作用”的一样思维方法论,这个“工具性作用”普遍呈现在德川儒学的现象中,被以“实学”或学者所称的“功效伦理学”而展现其“日本儒教”之特色。我们以德川时代古学派的王霸论与管仲论为例说明之。
笔者过去曾考察德川古学派的“管仲是否仁者”的争议,就其“道德与事功”或“内圣与外王”的偏重而言,管仲论在德川儒者的论辩中,有渐细密化的趋势,孟子的管仲论,在德川儒学界不是遭转化(如伊藤东涯、松村九山)即是遭批驳(如徂徕学派),一致反对宋儒朱子所持管仲虽有“仁人之功”但并不是“仁人”之论。不论是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均推尊管仲为仁者,笔者称仁斋之学为“轻内圣而重外王”,徂徕之学为“去内圣而尊外王”,所以仁斋主张“管仲之仁”=“圣人之仁”,甚赞管仲安民济世之功;徂徕则持“贵能贱德”之说,称管仲何止“器小”,实为“大器”。基本上,仁斋虽秉持孟子之论,但其称许管仲之功,与孟子之论有歧出;徂徕专取事功,对于上项孟子对于管仲的态度,皆持否定态度,尤其对于孟子不尊君的立场,更引起德川儒者争辩的导火线。[注]有关管仲论在德川儒者的详细论辩,详参拙著:《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第5章。由德川儒者大部分儒者肯认管仲论的思维看来,如孟子、朱子这样坚守“管仲非仁者”之论,往往遭受扭曲与批判,黄俊杰教授称日本儒者这种判断“仁政”与“仁者”时,所采取的是“功效伦理学”远过于“存心伦理学”的立场,[注]黄俊杰:《从东亚视域论德川日本儒者的伦理学立场》,《思想史视野中的东亚》,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79—100页。他们所重视的是“功利伦理”(utilitarian ethic)而不是“道义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注]黄俊杰教授采取的是李明辉教授的定义:“功效伦理学主张: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之最后判准在于该行为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后果;反之,存心伦理学则坚持:我们判定一个行为之道德意义时所根据的主要判准,并非该行为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是行为主体之存心。”见李明辉:《孟子王霸之辨重探》,收入氏著:《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47页。并指出这种“功效伦理学”皆与东亚近世实学思潮之发展密不可分。
我们从以上德川儒者对管仲论所带有的“功效伦理学”的前近代思维之特色,再一一去推论如多有肯定“唐太宗论”“许衡论”的事功之论,而对于“汤武革命论”一致以“放伐”而不敢以“革命”,甚至在幕末水户学严厉批判孟子的君臣相对关系论革命论。如此,我们不难连结到何以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这种“功效伦理学”的儒学工具性思维,不仅持续发酵,甚至蔚为主流,也很容易与西方帝国主义乃至西方的进化论接轨的主因。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1890(明治23)年颁布的《教育勅语》是凸显“忠孝一体”的国家工具伦理思维,以存心伦理学的儒家孔孟最重要核心的“仁学”之道竟退位给“忠孝”道德,这种儒教日本化的“工具性”或“功效伦理”思维,早在前近代的日本儒教发展史中可以追寻到轨迹。
一言以蔽之,笔者想表达的是,吴书书中所言近代有关“儒教日本化”已包含在“日本儒教”的言说当中,“日本儒教”本身已相当强调其主体性,重点已不是转不转化的问题,也不是以“儒学”为主体问题,“日本儒教”的使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本身就迥异于“中国儒学”或“朝鲜儒学”,而在明治维新到战前的学者使用“日本儒教”往往与皇国道德结合而超越了“中国儒学”。但在战后迄今的当代学者所使用的“日本儒教”则是一种以思想史的发生历程,阐述曾在日本各时代受儒教影响的政治与伦理、养成教育的历史。
三、翻转“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关系的前近代追溯
本节拟对吴书在讨论日本道德论议题时,涉及“国民道德”或“国体论”,颠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维课题,提出以下两点补充意见,其一是作者没有提到进化论在当时盛行的时代背景,其二是这种逆转普遍与特殊的思维其实江户儒学就一直存在着。
吴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似乎遗漏了一个学说背景问题,就是进化论在19世纪帝国主义的流行,诸多学者习惯在道德论述与国民性精神结合的过程中,渗入了进化论,亦即当时藉由升华“生物学演化论”,从“人种的进化论”[注]“人种的进化论”中最有名的事件是1903在大阪所爆发的“学术人类馆事件”,该事件背景是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往往借着举办博览会,强化其帝国的优越感,从而藉此展现日本人种的优越性。所谓“学术人类馆事件”是1903年于大阪举行劝业博览会,以学术之名,在馆内陈列北海道爱奴族、台湾原住民、琉球、朝鲜、支那(中国)、印度、爪哇等七种“土人”,首先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清政府进行交涉,同意取消“支那人”的陈列,接着韩国公使也抗议,不久也取消韩国人的陈列。虽然“支那人”的陈列被取消,但在馆内依然出现穿着传统中国服装的台湾缠足女性,仍然引起抗议。关于此一事件,研究颇多,事情脉络之分析可参考厳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第三章《“人類館”現象と“遊就館”体験》,第99—150頁。另从帝国可参李正亮《帝国、殖民与展示:以1903年日本劝业博览会“学术人类馆事件”为例》一文中从日本人类学家坪井正五郎“民族混合论”的进化论角度,分析此事件的帝国殖民权力结构之关系,刊于《博物馆学季刊》20(2),2006年,第31—46页。导入“精神进化论”,由此连结到日本国体精神的天皇体制,是世界最独一无二的体制,进而推尊日本国民是最优秀的民族,这种思维的种种,都可看到进化论的轨迹。当时,不论是尊皇论者,乃至自由民权论者,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到禅学家忽滑谷快天(1867—1934)的《禅学批判论》(1905年出版)乃至基督教神学者海老名弹正(1856—1937)所著《勝利の福音》(1903年出版),都受到这波进化论色彩的影响。以下即以上述两位宗教家的精神进化论为例。
忽滑谷快天在1905年出版的《禅学批判论》中有一节专讲禅学的伦理时,标题称为《与进化的“伦理说”和“完全说”的一致》,总结其论:
人类以其发生以来着实地进步向上,且从鱼介走兽至人类的进步阶级过程中,都是在其物质性向上之同时,也是道德性精神的向上。又从蛮愚到贤明的进步阶级过程中,也都是精神性的道德向上。如此,天地自然的目的,由此无限的进步向上,而使之成为愈愈益益完美的展开。吾人本具天真的道德向上之力,与天地之大目的契合而益益进步,故吾人改订进化的伦理说而可使之完全一致。正确的说,我想应用进化论于完全说(按:即禅学之论的完美理论),始可与禅之伦理一致。[注]忽滑谷快天:《禪學批判論》,東京:鴻盟社,1905年,第141頁。
上述论点,不可轻易看过,表面上快天所承认的“进化论”,并不是作为物质、功利的进化论,而是作为促进精神性道德向上的进化论。质言之,物质的进化论是“不完全”的,需要“完全的”禅学补强其不节制而流于功利、物质的缺陷或弱点。但是,“进化论”不论是“物质的、功利的”或是“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如果没有厘清它的精神进化论与国家政权强调的“精神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则这层暧昧关系都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帮凶。类似快天这样主张“精神向上”的进化论者,在当时基督教界里,我们也不难找到相似者,如知名的海老名弹正在1903年出版的一本《勝利の福音》,其中不乏进化论之说:
吾人自觉有二千六百年的历史之日本民族,值此能在精神上一大进化之际,率先可为其先驱的是吾党基督教的团体。我党之基础,存有二千六百年间祖先之衷心,此衷心以天地为主宰,能在指导人类的神灵之翼下取暖,如今卵若能破壳而出,即可为新日本的内在生命(inner life),而在帝国中形成新帝国,此不用多言亦明也。[注]海老名弾正:《勝利の福音》,東京:新人社,1903年,第3—4頁。
上述海老名氏之论充满着“文明进化”论,只是他把“物质进化”改成“精神进化”而已,却又充满对帝国日本的期许。[注]海老名弾正:《基督教新論》,東京:警醒社書店,1918年。一书也有不少进化论观点,例如在一篇《人格不灭论》如是说:“人格是万物进化的最高产物……若见此进化的经历,则万物的奋斗努力是所不及想象的,经历着或者是优胜劣败,或者是适种生存的历程,迈向最高而不断进化着。如此,最终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呢?乃人格也。吾等之人格是作为宇宙的最高产物,断无可疑之余地。有人格才明白万物进化的经历与理法。人格是宇宙的光明,无之则宇宙无光明。人格无疑是万物的灵长,仔细思索进化的理法,宇宙保存优秀之物而舍去劣恶之物。宇宙不就是在保存其所产生的最优等的人格吗?若信进化的理法无误,则人格之保存无疑。”(第102—103页)上述之论,可窥海老氏即使论“人格”依然不脱其进化论色彩。可见进化论的思想也深深打动当时日本的基督教与佛教信仰者,他们一致都否定“物质进化”而强调“精神进化”,但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他们所主张的“精神进化”与以天皇至上论为基础而强调国体论的“精神进化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性。如所周知,至高上帝的普世精神与佛陀的超越种界、国界之菩提精神,无论如何与国体论的特殊精神大异其趣,更不用谈与其宗教核心论旨相违的“精神进化”,而佛教者如忽滑谷快天、基督教者如海老名弹正等大谈“精神进化”,纵然披着宗教外衣,但不免令人联想其“精神进化”理论,不过是为当时风靡的国体论做嫁。
职是之故,我们若将进化论风潮,回到“日本儒教”或“儒教日本化”的讨论主轴上,就可明白“日本儒教”正是对“中国儒教”进行“进化”手术,乃因“中国儒教”的固陋迂阔,无法迎合新时代,但“日本儒教”完全可以符合时代、且顺应日本国民精神,所以“日本儒教”对“儒教”做了起死回生的进化转生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著作都凸显这种思维。
吴书在第三章中论及《日本道德论到国民道德论》,提到近代日本推动“国民道德论”的两个关键人物,其一是井上哲次郎,另一是西晋一郎,二者是师生关系。前者如所周知是《教育勅语》的衍义者,1910年出版《国民道德概论》,将“国体论”与“道德论”整合一体;后者西晋一郎(1873—1943)是井上的弟子,比起井上更是激进的国体论的推动者。笔者这里关心的是吴书中分析这位翻转“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的知识能手之分析:
在他(按:西晋一郎)的道德研究中,有中日文化比较的视野,他通过比较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他认为日本“国体”是普遍的(但其道德又是特殊的),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国体”则是“特殊国体”而缺乏普遍性;一是他认为中国有关“天”的思想始终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故而是“非实在的”,由此中国并没有真正确立君主绝对性,这也是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因。……通过这种“认识论颠覆”,由此引出的结论:真正能使“普遍化”的宋学付诸“实际”,并作为“国民道德”而得以“土著化”的只有日本,从而形成“我日本之国体”,这才是儒教完成“日本化”的真实体现。可见,正式在日本“国体论”“国民道德论”以及日本儒教的重构过程,儒教面临着“再日本化”,而此次的“再日本化”其实是对江户儒学的严重扭曲,成了宣扬“日本国民精神文化”的符号。值得关注的是,儒教与日本精神互相连动,其结果实现了日本普遍而中国特殊这一国体论意义上的认识论翻转,其目的在于借“日本儒教”以重建日本国体。在这里,所谓“儒教”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中国儒教,而是经过日本国家“实体”转化的作为日本精神—甚至直接就是亚洲价值之代表的所谓“日本儒教”。(吴书,第52—53页)
以上西晋一郎的“日本儒教”论堪可为当时国体论的代表。作者分析西晋一郎如何用日本特殊的“国体”严重扭曲或中国儒教甚至江户儒教,形成其独特的“日本儒教”,而这种“日本儒教”带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颠覆了以下有关“普遍”/“特殊”的认识论:
1.日本国体的普遍性/中国国体的特殊论。
2.日本确立了君主绝对性(等于普遍性)/中国君主相对性(等于特殊性)。
3.日本实体“天”的普遍论(天皇制)/中国抽象“天”的特殊论。
以上西晋一郎对“普遍/特殊”的颠覆性,笔者要补充的是,这种思维倾向其实并不是从明治维新才有,在江户初期抱有日本主体性强烈的山鹿素行(1622—1685)、山崎闇斋(1619—1682)到幕末的吉田松阴(1830—1859)、水户学都有过这种“颠覆”或“逆转”中国儒学的情形。因此,当我们在谈“儒学日本化”这样的课题,绝不是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的产物,贸然切割会看不清其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故应追溯“前近代”与“近代”的连续性关系,因为甚至这些儒者的论点与著作都成为明治维新以后强调“日本国体”的继承来源。
例如江户初期的山鹿素行一部《中朝事实》,在明治时期成为军界、政界的显学,这是一本以“日本为第一主义”的著作,在各章各卷的开始皆冠以“皇统”的标记,该书著作主旨,更十足透露日本是卓越万邦的思想,如常被引用的以下话语:
“愚生中华(案:指日本)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案:指中国)之经典,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抑妙奇乎,将尚异乎。夫中国(案: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注]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廣瀬豊編:《山鹿素行全集》巻13,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第225頁。
素行这种视日本水土是“卓尔万邦”之思想,可说是山鹿兵学的共识。以上引文也可说是“普遍”与“特殊”的翻转解释,将本是以中国“经典”或“水土”为中心、为普遍依循的标准,翻转为应以日本“经典”(指《记》《纪》神话经典)或“水土”为中心、为普遍的依准,日本文物与武德都是“可比天壤”的普遍性,笔者称此为“以特殊凌驾普遍的普遍性”。继承山鹿素行这种普遍性思维的是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其名著《讲孟余话》所表达也正是这种思维,过去笔者曾分析过这部作品如何逆转“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思维特色如下:[注]拙著:《吉田松阴〈讲孟余话〉的诠释特质与其批判》,《汉学研究》2009年第27卷第1期。
1.视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具有绝对的普遍性,鄙视中国“汤武革命”的相对君道特殊书性,却不问汤武革命背后基于仁义的“王道”普遍性;
2.视日本超越血缘意义的“孝”所具有的普遍性,批判孟子基于血缘原则的“一本”思想并不具普遍性;
3.以自己时空性取代经典与作者的时空性,以一种“错置经典主体性”的现象来解读《孟子》,亦即《孟子》已不是中国儒家的《孟子》,而是换成日本主体的《孟子》,这种经典主体性的错置,实也是一种对经典普遍性义理的颠覆。
其实不只是松阴如此解读经典,明治维新以后,几乎许多解释中国儒家经典的学者都可找到像吉田松阴站在日本国体论上来逆转儒家经典,阳明学也罢,朱子学也好,一个个都成了“日本阳明学”或“日本朱子学”,这都可在井上哲次郎所编纂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6年)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看到这种诠释特色。因此,笔者还是强调,讨论“儒学日本化”这个课题,不可能切割前近代的思想关连,在前近代的日本儒学发展氛围下,“以特殊凌驾普遍的普遍性”的思维特色已经是散在日本各藩的小树苗,明治维新以后的时空环境则是加速让这些小树苗成长茁壮为一棵大树,并蔚为森林。
其次,与翻转“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关系的文化特色,也与吴书在第六章《“近代超克论”与“道德生命力”》分析息息相关。在此先说明近代超克论的背景。
稍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们,都可强烈感受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鼎盛之际,多少知识分子因此而“转向”,放弃了自己普遍主义的立场,例如加藤弘之(1836—1916),在幕末时代由攘夷论者转向开国论者,明治后他也可以从民权论者转向到进化论者;再如福泽谕吉也是从一个天赋人权的平等论者,转向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拥护者,甚至有些知名的基督教徒(如海老名弹正)、佛教徒也都修正了自己普世价值理念的宗教信仰,不得不拥抱特殊国家主义的侵略论,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支持对他国的不义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的“近代超克论”下的知识分子,大讲诸多哲学概念与世界理想之建构,许多知识分子在权威压力下不是被动就是主动地向趋向帝国主义的国家权威输诚与转向。
“近代超克论”是在上述战争气氛凝重的背景产生,希望超越代表近代西方的诸多价值(如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让日本成为代表亚洲新秩序、新价值之中心,必须先从每个日本国民道德心的改造开始,整合“日本精神”。吴书提到近代超克论常出现“道德的エネルギ”的词語,据京都学派的解读,这种“道德的エネルギ”是历史的推动能力、民族的生命力,而且是“建设大东亚之活动的原动力”(吴书,第69—70页)。吴书点出“道德的エネルギ”系受19世纪德国兰克史学的“Moralische Energie”一词概念影响,并指出Moralische Energie一词开始被京都学派翻译成为“道义生命力”或“道德能量”(道德的エネルギ),而吴书则一概译为“道德生命力”。总之,“道德的エネルギ”是近代超克论中的重要思想,也代表着西学日本化的重要课题,吴书更谓之为“京都学派座谈会的一个最核心的观念”(吴书,第76页)。
只是,笔者相当疑惑为何吴书坚持要将京都学派“道义生命力”翻译成“道德生命力”。若笔者没有误读,吴书是从德语脉络直翻成“中文脉络”,但既然要讨论西学日本化或儒教日本化,应该尊重日语脉络的“道义”内涵,因“道义”在日本语脉上更符合日本过去武士集团的君臣义理之脉络,也比较能贴切表达一个“道义力量”构成的集体性国家和社会团体之必要。以下深论之。
笔者认为“道义”一词实来源于日本武士伦理的“义理”。江户时代名著《叶隐》的作者山本常朝回忆他的主君的话说:“没有比义理更为深奥的了。”还说:“即使堂兄弟死了也不会流泪,但是一听到五十年或百年前的故事,只要有关于义理,眼泪就会掉下来。”[注]山本常朝:《葉隠聞書》巻3,《記佐賀藩藩主》第1条,第152頁。“义理”两个字可以说是日本封建武士的特殊词汇,至于什么是“义理”?武士礼仪学者伊势贞丈﹙1717—1784﹚区分为“主人之义理”与“家臣之义理”,在日本近世武家义理中相当有名,他说:
君臣之法,君为主人之事,臣是家臣之事。主人把赐扶持之米与金,自然当作“恩”,家臣尽力奉公,受恩而悦,此“主人之义理”也。家臣也将尽力奉公,自然当作“恩”,从主人所仰给扶持之米与金,受恩而无忝,思为主人舍一命,此“家臣之义理”也。[注]伊勢貞丈:《貞丈家訓》,有馬祐政編:《武士道家訓集》,東京:博文館,1906年,第90—91頁。
如是主人以“施恩”为义理,让家臣经济毫无负担,这是作为主人应该作的义理,家臣在此主人的义理下,欣然受恩。至于家臣以“受恩”为义理,但为无忝于主人的赐恩,在必要情形下为主人舍一命,这是作为家臣的义理。换言之,主人与家臣均是由一个“恩”意识而结合,若无此“恩”意识,义理亦无从而生。而这种“恩”意识也是建立在封建武士集团的特殊文化的基础,具有“代代世袭”的性格,例如室鸠巢在《赤穗义人录》中载大石良雄(1659—1703)劝其年仅十五岁的儿子一同赴义时提到的观念:“人道莫大于义,义莫重于君臣,汝父受国恩至厚,义当为先君死。汝虽未仕于国,亲受君禄,然其生长于家,有衣食之裕,有仆隶之徒,自享奉养之安,优游岁月之间,汝之私国恩也,亦已大矣。”[注]室鸠巢:《赤穗义人录》,《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第361頁。实则大石良雄自其曾祖父即代代为赤穗藩的家老,良雄之子在出生之前即享有主君之“恩”,因此对其子而言,为主君尽义理是先天的道德义务。
因此,武士的根本义理是由“恩”意识而来,个人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公”﹙施恩者﹚而存在的。在这种义理下常将个人主体的独立意识斩断而全力奉公,这是一种“立公次私”“报公恩以成私”的思维。这是中国“义”的价值理念,在日本武士道德意识下的一个特殊转型。换言之,儒家所谈之“义”带有强烈的个人内在超越的主体性而言(如孟子所定义的“羞恶之心”),然而武道之“义”则有强制斩断内在超越内涵,从而依循一个以外在主君为最高的伦理判准。
由此可窥,吴书坚持要将京都学派“道义生命力”翻译成“道德生命力”,也许照顾了中文脉络,却失去了日语脉络,所得恐不偿其所失。何以言之?上述对封建“各藩主君”绝对尽忠的“特殊义理”,正是明治维新以后提倡国体论者,拿来转化到对“天皇”进行“忠孝一体”思维的“普遍义理”,亦即从特殊的“封建臣民”转化到普遍的“国家臣民”,“义理”看似一样,但已有多元松散的“特殊”与单一固化为“普遍”之别,这中间扮演着结合“多”与“一”的关键,还是与“万世一系”这种以神性血缘且具超越时空的“天皇体制”息息相关,如同丸山真男所说“日本国家成了伦理的实体,独占了所有价值内容的决定权。”[注]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64年,第14—15頁。
四、丸山真男原型论的补充及其对“儒学”的晚期态度
吴书讨论有关“儒教日本化”与“近代化”课题时,几乎每章都提到丸山真男的论点,也引用了不少丸山弟子如平石直昭与渡边浩的修正观点,可见丸山论旨有关儒学日本化的厘清对本书的重要性。兹将书中呈现丸山论旨的相关重点,整理如下:
1.赞成丸山否定“儒教文化圈”的说法。(吴书,第7页)
2.批判丸山晚期研究仍坚持德川儒教是一种“体制意识形态”的观点,过于强调“近代化”视角,而缺乏“日本化”视角。(吴书,第89—90页)
3.从丸山的“原型—古层”论中涉及如何重新发现日本文化传统的问题,厘清丸山有关儒教日本化的课题。吴书点出丸山的态度是:“日本化”是一种“文化接触”的过程,其前提是“古层—原型”,“日本化”必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实施改造、修正和接受的必然结果。而儒教日本化过程中的实际状态也正表明日本文化“原型”与儒教思想以及日本体制思想“互相作用”的结果而已。(吴书,第98—99页)
4.用19世纪德国史学家罗伊森(1808—1884)的史学理论针砭丸山原型论的局限。吴书介绍罗伊森指出史学研究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可以在历史事件中寻找到一个“确切的、绝对的源头、事情的本质。”由此批评丸山的“原型论”。(吴书,第103页)
5.对丸山追溯日本的过去原型的立场有所澄清,认为是“认识过去正是为了克服过去而改变现在”,也就是“为现在而过去”,并认为丸山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吴书,第105页)
吴书对丸山命题,均持之有故,也言之成理。只是,对于丸山的“原型—古层论”,笔者有两点补充,而这两点又与吴书关切的“儒学日本化”至关重要。
其一是丸山的“原型—古层论”追溯日本“源流”之际常不出日本的问题,韩东育对此有精辟的厘清与考证,在其新著《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中的序章《关于日本“古道”之夏商来源说》一文中,指出丸山真男在探索日本“原型”时,只要涉及与中国古代之关系,往往事涉敏感从而“停滞”或避之不谈。[注]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79—125页。但韩东育每每在丸山论旨下,几乎把丸山《讲义录》及《丸山集》读到精透,并加以整理进行睿见的评论,积极找出丸山所“说不出”的中国之源流,一一抽丝剥茧,厘清古代中日关系的源流,如“日本古道”与“夏商古道”之关系。如丸山真男的“日本原型论”之论不出日本,而韩书乃使之出日本而远溯中国殷商时代“原型”之“原”,将之重现其“原”,故乃能将丸山未能言明在“日本原型论”的根源上,与中国古代之关系串联起其渊源关系等等,大概只有中国学者会去做这种探索日本之源来自于中国“古道”的厘清工作,故能发人所未发。
笔者认为这种探源到中国古道的工作,与“儒教日本化”这样的课题当然息息相关,儒教日本化或“日本儒教”关注的是“如何与中国来源切割”的问题,而且这种切割随着明治维新国力的增强,一开始切割的很“不自然”,最后变成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导致本应是很自然要去追溯“如何与中国的根源关系”,竟变成“绝响”。但造成这种“绝响”是有很多的禁忌或压力氛围导致的结果,丸山这样杰出的思想史家,算是日本学界少数有睿见而敢于挖掘出日本的“原型”,并极力批判这种切断“普遍主义”而保留“特殊主义”的“原型”。
其二是丸山晚年对“儒教”的重新评估问题,在此我想补充丸山晚年的关门弟子区建英的观点来说明之。区建英在2016年发表《丸山真男与福泽谕吉思想中的“独立自尊”与“他者感觉”》一文中提到丸山对福泽的继承有两大关键思想—“独立自尊”与“他者感觉”,这两者看起来富有西方近代思想内涵中,同时也潜藏着丰厚的儒学价值观。因此,区建英提到即便像福泽谕吉表现看似与儒教决裂的启蒙思想家,所要批判的矛头,事实上是御用儒家而不是周公孔子的原始儒家,在日本脉络则是被德川政权利用的儒家。区建英指出:
儒教即便曾经服务于德川封建体制,也对封建等级关系起过支持作用,但儒教本身并不是作为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而诞生的。而且,福泽所批判的儒教也不一定等同于中国的儒教。实际上,日本在引进儒教时已对之进行了脉络性转换,特别是朱子学的“天理”思想,在适应德川社会的过程中失去了超越的、抽象的哲学含义,而三纲五常则被套用于日本的上下尊卑秩序,并被直接赋予了自然秩序的性格。丸山没有意识到儒学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因而也忽视了儒教的正面价值。不过,丸山也注意到福泽所说的话:“我辈一味排斥儒教主义的原因,绝不是因为认为其主义有害,周公孔子之教提倡忠孝仁义之道,不仅没有一点可非难,而且作为社会人道的标准是应该敬重的。”之所以排斥之,是因为现在的儒教已“改变了原来的本性,达到了腐败的极点。”而且,丸山还注意到福泽在分析“权力的偏重”时,指出那不是德川时代特有的,而是日本古来就有的陋习,那就意味着在儒教渗透于日本之前就有。
以上区建英所指出福泽与丸山对儒教的批判,扭转了过去许多学者仅注目于二者的儒教批判,却未能区隔出“批判儒教主义”≠“批判儒教本身”或是“批判日本儒教”≠“批判中国儒教”这个隐微而未被注意的面向,笔者姑且称之为“重新发现儒学原貌”,注意起“儒学原貌”的独立自尊资源(如人性论与人权论可以互相发明),与日本“古层”有脉络性转换儒教成为扼杀自主人格的日本传统因素。[注]区建英:《丸山真男与福泽谕吉思想中的“独立自尊”与“他者感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6年第13卷第1期(总第25期)。
由此,区建英注意到丸山晚期对儒教的改变态度,指出丸山真男对江户儒学与中国儒学的盲点,在于认定来自中国的朱子学阻碍日本社会进步的封建意识形态,未免缺乏对中国以及韩国儒学的内在理解,因而也缺乏了对日本儒学的内在理解。如所周知,丸山在战后反省了自己受西洋的“亚洲停滞论”影响,认为中国是停滞的,但日本虽落后而并不停滞,后来又反省了自己没有把中国的朱子学与日本的朱子学区别开来,也受到丸山自己弟子渡边浩的批判。[注]区建英:《丸山真男与福泽谕吉思想中的“独立自尊”与“他者感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6年第13卷第1期(总第25期)。他们指出丸山过度地美化了徂徕学的“主体制作”的近代性格,从而对于斩断了“公共”之“理”的普世追求的徂徕学失去了批判的力道,而对儒学在江户时代因徂徕学而逐渐崩溃,最后由强调国学的“皇国”优越性取而代之。[注]相关论点可参见渡边浩原:《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特别是第三章《日本的儒学与国学的心性》,第138—144页。区建英借着此文,有一想表达的重点是丸山晚年对徂徕学的过度高估及欠缺对儒学内部的深刻理解而进行重估,而这是丸山透过重新检视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论”而得来的反省。很遗憾,丸山晚年没有直接写出对儒学内部较为同情理解的研究,因此一般研究者也只能停留于早期“丸山论旨”或“丸山批判”的视野,但由于其优秀弟子渡边浩等也进行着“批判丸山”的继承态度,使得我们更能掌握“后丸山”学者们更为深刻的儒学日本化的文化立场。
结语:儒学日本化已经“中断”了吗?
吴书曾引用丸山弟子渡边浩所言儒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西洋化”而不断“自杀”的过程。[注]渡边浩的原文如下:“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也就是儒学教养最为渗透的时期,在这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眼里,常常认为同时代的西洋是实现了儒学的最基本价值‘仁’与‘公’的社会。……使得后来,儒学诸理念渐渐被西洋思想吸收,相对地迅速地失去了作为独自体系的思想生命。也就是说,至少在日本,儒学在引进起源于西洋的‘近代’的过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正因如此而导致了自杀。”参见氏著:《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196—197頁。悲观者往往认为,日本儒教经过“近代化”过程被“西洋化”,但同时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包装,使得战后儒学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好像“自杀已死”。但笔者不太能同意这个“自杀”用语,因儒学在明治初期得到人权论者的拥护并嫁接西方的“主体自由”“民权”与“公共性”价值,证明儒学是可以顺利地“近代化”,但扼杀这个“儒学近代化”正是明治维新政府本身,换言之,儒学真正的致命伤者,不是自己,也不是“西学”,而是被明治权威主义“他杀”了。因此,与其说“自杀”,不如说是“他杀”,而这个“他杀”者,正是日本“国民道德论”或“国体论”的鼓吹者,刻意强调儒学的“忠孝”道德,遗漏了儒学最重要且具有普遍价值理念的“仁学”精神,脉络性转换了“儒学真貌”,推出“假貌的儒学”而加以渲染,为国家主义背书,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相较于近代儒学在日本“被他杀”的过程,近代中国儒学的命运反而比较像是“自杀”。五四反传统的“民主”“自由”与“科学”标语,完全看不到儒学可以西学化的轨迹,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转为五四时代的“全盘西化”,再转为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被“自杀”的很彻底。
但是,不论是“自杀”或“他杀”,儒学依然在日中两国“他杀未遂”与“自杀未成”,否则难以说明目前日本民间与知识人仍有儒学学习的传统,而中国如今竟然可以“国学复兴”。因此,笔者不太能认同吴书中言及儒学日本化在当今日本经已经中断的问题,吴书如是更表达“XX中国化”的问题:
至于“日本化”在当今日本是否依然处于进行式当中,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儒学日本化在当今日本已经中断,这是毋庸置疑之事实。至于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探究。相比之下,“中国化”则完全不同,尽管以前有“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但是当今中国社会还处在进行状态中的西学“中国化”或许将是一个长远的实践过程。(吴书,第119—120页)
有关儒教日本化在当今是否已经中断,或是作者在最后一章表达“已经走完了‘日本化’的进程,变成了‘历史化’的知识对象”的“死亡”现象。(吴书,第121页)当然,作者所谓的“死亡”指的是儒学只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非认同儒学价值的“知识”与“价值”两分的情况。尽管也有不少学者这样认为(如作者引用的渡边浩、黑住真等),但笔者认为还是不能贸然这样判断,而这样的判断往往来自于知识人仅在知识领域或材料所看到文化传播现况,未能关注民间儒学活泼的情况。因为笔者曾经参加过日本民间的《论语》读书会,也考察过企业界、实业界如何活用孔子的《论语》,如皆木和义出版的《稲盛和夫の论語》及渡边美树的《使う!论語》及棒球名教练的野村克也出版的《野村の實踐论語》(2010),还有依附在寺庙而以孩童为主的《论语》授业、《论语》讲义会、《论语》学会及《论语》普及会等。以上都有百年前1916年涩泽荣一出版的《论语与算盘》之一贯传承,将《论语》不只当作知识,而是当作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准则。[注]《论语》在当今日本企业界的实用与流行,可参拙著:《日本企业界的〈论语〉经营学》,《鹅湖学志》2014年第53期。但学者往往轻忽这种儒家经典在民间的活力与应用。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吴书比较偏向引用东京大学丸山真男系统下的儒教观察,若能将注意力放在九州岛大学冈田武彦系统下对儒教的积极认识,恐怕也不会贸然就判定儒教已经在日本“历史化”的话语。
其次,不能贸然判断儒学日本化已在日本“中断”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我们讨论儒教日本化的课题时,须从长远的历史消化过程中(吸收、排斥、转化)来观察,而这种观察将发现也往往不能脱离“中国因素”。意即当中国国力强时,相对的传输到周边国家的文化力也强,周边国家往往也主动吸收中国文化。而当中国国力气弱游丝时,也波及到中国文化传输至周边国家的强弱状态,甚至周边国家的文化也能逆输至中国,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吸收明治维新以后富强的日本文化。因此,现在看起来儒教日本化表面上是“中断”,但应没有“绝断”,确切来说是“藕断丝连”。换言之,作者提到目前中国复兴国学、儒学的过程中,其背景是自19世纪中叶清末民初以来,经五四反传统文化到文化大革命的民族文化挫折,如今随着国力上扬,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许多“中断”的文化也开始恢复,昔日有极端的“全盘西化”,今日亦有“全盘中化”的主张,“西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也在紧锣密鼓中不断地变化当中。周边国家如何面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强大波浪,也往往不是政治力所能局限,东亚民间展现的共通文化力量,其可能发挥的能量也不容小觑。[注]例如在民间甚有活力的书院文化,在日本、韩国及台湾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民间书院传承着儒家文化的种子,甚至民间宗教的儒释道,也充满吸收儒家经典内涵成为其教义,落实并内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日用之间,这种儒家在民间文化的共通现象实不容小看。笔者想要表达的是,“儒教日本化”往往与“XX中国化”不能分裂为两个问题看待,也无法简单用短时期如一两百年时间的视野去评估,两者往往密切相关且需长时间的观察,因为“XX中国化”不能逃于曾经挺立千年来主流的儒家文化,其文化底蕴早已深耕,虽经破坏、摧折,但仍保留一股元气,随时蓄势待发。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