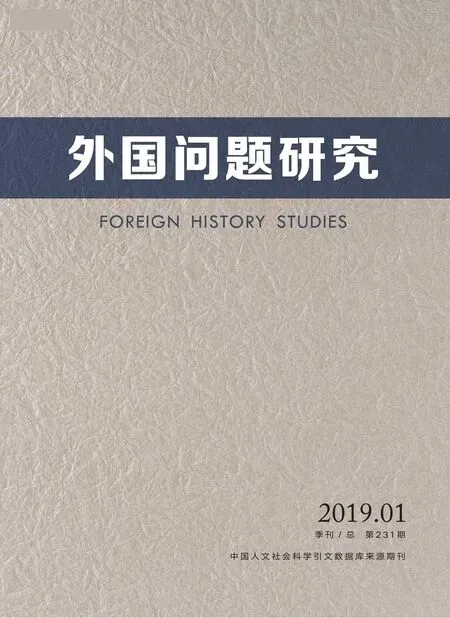越南考古学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理解与消解——读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
王明兵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俵宽司所著的《脱殖民地主义的越南考古学——超越“越南模式”“中国模式”》[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東京:風響社,2014年。是一本极富魅力的著作,曾获得第一届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松下正治纪念学术奖(2013年9月)和第13届东南亚史学会学术研究奖(2015年12月)这两项大奖,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注]参见吉田泰幸:《書評·俵寛司著『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考古学研究(62)》2015年第1期;山形眞理子:《新刊書紹介·俵寛司著『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東南アジア学会 編:《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46)》,2017年,第88—92頁;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年。该著不仅对铜鼓、东山文化和汉系墓葬考古进行了精深而细腻的整理与研究,还对自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中国与越南之间关于考古历史认识中的“越南模式”与“中国模式”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问题解析及其理论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
在越南研究领域,何谓“越南模式”、何谓“中国模式”,因所处时间与空间之异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和内容,但二者的共通特质乃是一种“中心取向(Centered Approach)”或“中心模式(Centered Model)”。概言之,“中国模式”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本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影响,将越南附属于中国内部、作为中国的翻版甚至是中国的一部分或“地方史”去对待;“越南模式”则是以越南为出发点,主张越南的独立自主与民族文化的自发生成,强调越南本土文化特性以及所具有东南亚“多元性”特征。显而易见,这两种认知模式与话语方式,均非纯“学术性”话语,而是或隐或现地透露出“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然而,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能否被超越呢?这也即是作者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去试图理清并解决的核心问题。
关于越南历史分期问题,在历史学领域和考古学领域甚至是同一个学科内部的不同学者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此为常态。就考古学领域而言,同为考古学者的俵宽司与西村昌也对越南古史的分期理解就不尽相同。[注]西村从考古“实物”与历史史籍的角度,以公元前1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将越南史分为史前期与历史时期。以公元前1世纪中叶为分水岭,主要是基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之后在越南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中国系物质文化”占据主导,而且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史籍最早对“越南”历史具有记载;而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东山文化”具有相当的本土特色。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按照考古学时代划分,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至10世纪是越南的古代。参见:西村昌也:《ベトナムの考古·古代学》,東京:同成社,2011年,第141頁。俵氏将越南的“古代”定位在从公元前29世纪被视为越南初期王朝的“鸿庞纪”至10世纪自主建国及“大瞿越”的形成。[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東京:風響社,2014年,第17頁。以此算来,则越南“古代”可长达4000年。事实上,在这4000年的越南“古史”中,越南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足1000年,而最早对其记载的又是“中国”的史籍(比如《尚书》《礼记》《楚辞》《淮南子》等)。因最早记载它的史籍是“中国”的,故在“越南”看来,“中国”史籍或中国人的越南史研究,则难免不充斥着一种“中国模式”。越南最早的史书可溯及到黎文休的《大越史记》(1271年)和范公著的《大越史记续编》(1455年),不过一般认为越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史书乃是黎圣宗时期吴士连主编、于后黎朝正和18年(1697年)正式刊行的《大越史记全书》。由于《大越史记全书》乃是由越南学者独立完成,所以该书就成为“越南史”书写的“越南模式”之嚆矢与典范。而问题是该书的编纂与出版均晚于记载越南历史的中国史籍,所以难免会有“层累”史观的建构特色,其可信度自然不免大打折扣。其中,争议最大的则是视为越南古史起源或越南初始王朝的“鸿庞纪”建元问题。[注]参见叶少飞、田志勇:《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2期。在该问题上,中越史书均缺乏详细的记载,而“雒龙君”又是神话传说,以致各国学者即便是越南学者之间也争议不断。从史料学的批判原则来看,除非确有越南本土的考古证据或传承脉络,那么早于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两千年的中国史籍无疑仍是最为可靠的文献资料,而且当时的交趾(越南)也仍是古代早期“中国”的一部分。随着越南考古学的发展,越南“本土”考古实物越来越多的出现,对于早期“越南”历史因资料不足而无法得以解释的部分,考古学的“实物”证据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近代越南史是一部遭受法国统治的殖民史,所以近代以降的越南考古学乃是在法国“东方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关于越南历史形成的“东山”文化遗迹的发掘、整理以及最初的研究,也是由法国远东博古学院的帕若(Pajot)和阳士(Janse)完成的,其争议也最早发生在法国学者马司帛洛与鄂卢梭之间。由于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主要是陶瓷、青铜器以及汉型墓葬,加之对越南早期历史的记载主要是中国史籍且越南历史上存在过长达千年“北属”于中国之历史事实,所以法国学者所持守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越南就是缩微版的“中国”。细究发现,法国在这一现代“东方学”学术认知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种文明优劣高下的“东方主义”歧视及“殖民征服”的“正当性”言说,即古代越南接受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统治,那么现在越南受文明程度较高的“法国”的统治,也是“合理”的。因为对于越南来说,中国和法国均是“外来者”,而且是能够给越南带来“进步”的“外来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时期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国”。易言之,在越南的发展历程中,法国殖民统治无异于是“古代中国”文明在近代以降的历史延伸。既然越南可以接受一个长达千年的“中国”统治,那么何以就不能接受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法国”的支配呢?
越南在历经抗法抗美斗争的“胜利”后,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之建立。越南抗战胜利的“正义性”,既是现代越南民族国家的实现方式,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越南延续历史与改写历史的“传统”。作为一项体现民族“抗争”精神的“传统”,在历史中的呈现形式主要表现为雄王建国、二征夫人起义、丁部领建元、李常杰抗宋、陈朝的三次抗元以及黎利抗明等与北方“中国”的抗争。经过抗争,越南最终实现了独立。只不过,自李·陈朝到阮朝,越南的文教制度、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基本上都“中国化”了,形成了一个越南式的“小中华”。但不管怎样,最终在民族或国家独立意义上则“越南”仍是“越南”。尤其是1945年越南独立以后,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越南“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话语模式的这一言说方式,也深入学术内部,即呈现出的“民族史观”支配下的“越南模式”,对以铜鼓为代表的东山文化的“越南式”强调,乃是最明显的实例。[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8頁。
“东山文化”,虽然出现在越南的清化省东山社并因此而得名,但它的形成、出现以及对其的研究和争论,已经不单单是越南一家之事,而是“中国”“法国”“越南”三方要素皆涉其中,且在民族、国家以及超越国族的“东方主义”多重话语的解读之下,历史、学术与政治又相互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但问题总要解决,还原事实,理清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无疑是最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二、铜鼓问题
铜鼓被视为东南亚典型文化之代表,它以近代越南清化出土的东山文化遗迹而得名,但它的分布甚为广泛,截至目前为止,除菲律宾外,在东南亚其余地区均有发现。而且在中国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也有与越南东山文化同期的铜鼓的发现和传承,中国早期史籍《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等对其也多有记载。在1980年代,围绕铜鼓的起源、年代、地域问题,中越学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但受政治因素与民族情绪所困,迄今为止该问题仍陷于“中国”还是“越南”这样一种非此即彼、二者只能择其一的两难选择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也即是作者试图重新确定铜鼓编年与传播路径,试图复原铜鼓历史的真实存在状况的意愿所在。
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对越南东山铜鼓的四期分法及年代的研究,仍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研究成果。但黑格尔的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藏于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以及后续在法国和中国收集到的一些藏品,而现在所知的各式铜鼓已达2000余个,则以黑格尔所据的铜鼓数量之低,其代表性与分类依据自然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在黑格尔对铜鼓四式的分类中,争议最大的则是黑格尔Ⅰ式铜鼓所产生的诸问题。因黑格尔Ⅰ式被确定为年代最早,上限于公元前4—3世纪,但不明出处。直至1924年帕若在越南清化麻河右岸东山遗迹进行考古发掘时,才发现了黑格尔Ⅰ式铜鼓。以此才确定了铜鼓是东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东山文化时期也即是越南的青铜期时代。由于这一时期尚处在汉朝的征服之前,所以也可表明早期越南是有一套独立的文化系统存在的。1937年奥地利学者海涅·革尔登(Heine-Geldern)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东山文化乃是东欧黑海沿岸民族迁移的结果。对此,高本汉(Karlgren)批评道:中国青铜文化起源甚早,东山文化为何不可能是中国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呢?[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96頁。
在20世纪上半期的铜鼓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所依据的资料都极为有限。在东山文化遗址展开的最大规模考古与发掘虽然早在1935—1939年就完成,但考古报告却是在1958年阳士到美国后才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而且有部分被毁坏或遗失。[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96頁。中国方面在1955—1960年先后四次对云南石寨山文化遗址进行了挖掘,也首次发掘到了黑格尔Ⅰ式铜鼓。随之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出土了铜鼓,不过以黑格尔Ⅱ式和黑格尔Ⅲ式居多。此后,因中越关系恶化,1980年之后中越两国学者因铜鼓起源之争,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重新确定铜鼓的年代问题,俵氏将目前蒐集到的2000余铜鼓资料,汇集起来重新进行分析。由于黑格尔Ⅱ式和黑格尔Ⅲ占据绝大多数,所以其主要是对争议最大的黑格尔Ⅰ式进行分析。即便较少的黑格尔Ⅰ式铜鼓,也达到了215个。其中,144个发掘于越南,数量超过在中国发掘的铜鼓数量。鉴于此种情况,俵氏最终在图像清晰且报告较为详尽的365个个案中择取早期及黑格尔Ⅰ期的铜鼓,并将其中的265个案例,依据型式、属性、文样等重新分类加以分析,对其具体的观察点则集中在鼓面部、头部、胴部、脚部、耳部、端部、内壁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连接部分。[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105頁。作者经过细致整理和缜密分析,在黑格尔铜鼓编年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其年代划分,将其分成了6期:前Ⅰ期——公元4—3世纪、Ⅰ期—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前叶、Ⅱ期—公元前2世纪前叶至后叶、Ⅲ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半、Ⅳ期—公元1世纪后半至公元3世纪、Ⅴ期——公元3—4世纪以后。[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168頁。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变化:早期及黑格尔Ⅰ式期,云南地区和越南红河、麻河三角洲地区乃是铜鼓起源的两极或两大中心区域;但在Ⅰ—Ⅱ期,云南地区的铜鼓发生变化并趋于消失,而越南红河、麻河三角洲地带的铜鼓则继续发展,由大陆区向岛屿区传播而扩大;在Ⅲ—Ⅳ期,分布地域有所收缩,仅限于越南北部;在Ⅳ—Ⅴ期,其范围向越南西北和广西地带扩大,出现了铜鼓多中心化的趋向。这一情况也即意味着“古式铜鼓时代”的终结。[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177—178頁。
三、东山文化的复原
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东山文化遗址的考古是由考古学家阳士主持发掘的。他先后对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第一次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第二次是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第三次是1939年几乎整年。根据阳士的记述可知,早在他发掘之前,一些法国文物收藏家就曾在清化地区收买过铜鼓及墓葬出土物;在他主持发掘和整理的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文物被赠送给法国殖民官吏、遭遇偷盗、考古拍摄照片被毁、收集到的文物管理混乱等不良情况。[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190頁。直到1950年代阳士移居美国之后,他才陆续将东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整理出版。但由于时隔较长,一些已经遗失和散落的考古记录也无法得以弥补。尽管1980年代中国学界依据石寨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鼓,极力主张中国青铜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以及铜鼓石寨山文化起源说,但其在论述上基本都忽视甚至是无视阳士的东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东山文化遗迹的发掘工作,自1924年至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调查与发掘。1924—1930年,帕若最先进行了长达6年的调查和挖掘,但他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无详细的报告留存下来,所以其详情不得而知。但依据一些简单笔记和遗物账单可知,在其6年的持续发掘中,分2个工作区进行作业,大量的土器、陶器、青铜农具、青铜武器、青铜乐器等总共有523件出土,主要是青铜器物,尚无铁器类出现。[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12頁。阳士是在1935—1939年分3次对其进行了发掘作业。由于阳士的三次考古工作有较为详尽的考古记录和报告,所以从其记录和报告中可知他所发掘的遗迹地点与遗构中的出土文物。据其报告记载,在几次出土的文物中东山系青铜器占据多数。铜矛、铜剑、铜斧等武器或农具类较多,而铜壶、铜鼓型、铜铃等遗物较少,而且出现了特征较为明显的石制或玉制类的耳环、手环等佩戴品;另外则是土器和陶器制品。其中,还出现了具有东山系特征的台壶、甕、高杯等物品与具有汉系特征的印文甕、小壶等遗物。东山文化最有有名的邵洋(Thieu Duong)遗址则是由越南考古工作者完成的。1959年12月和1960年5月越南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其进行了两次预备调查;1960年11月末至1961年12月—1962年3月、1965年先后两次次正式实施考古挖掘。发掘报告显示,邵洋遗址的东山文化延续时间较长,从东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汉代设置郡县初期,墓葬类型不仅有东山系墓,而且出现了汉系墓。这一事实表明公元前后乃是东山文化与汉文化的一个并存期。[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40頁。
东山文化的时间断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处于青铜器晚期,后期已有铁器出现。俵氏综合帕若和阳士的考古调查,对铜鼓年代、东山文化发展阶段与实际年代进行了比对后确定了大致的一个铜鼓文化期:铜鼓Ⅰ期——东山文化前期——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前叶、铜鼓Ⅱ期——东山文化前期—后期——公元前2世纪前叶至后叶、铜鼓Ⅲ期—东山文化后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前半。[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52頁。在从东山文化前期到后期的东山墓葬群中,铜鼓、青铜乐器、青铜容器作为附葬品大量出现,但青铜武器、青铜农具逐渐减少。如果把这一情况与石寨山系文化、广西普陀屯铜鼓墓作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越南北部和广西、云南的情况有着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向。而这一变化,或反映出了东山系文化与汉系文化并存融合进而前者被后者所“驱逐”的一种文化冲突情形。[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65頁。
四、越南的汉化
在东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的汉系墓葬存在。这一情况,最早有案可查的是1896年法国海军曾在河内近郊发现过汉系墓。不过,对汉系墓的系统性调查则始于1916年由时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的亨利·帕尔芒捷(Henri Parmentier)带队对越南北部的汉系墓葬进行过初步的考古调查工作。1917年、1918年、1919年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均有关于汉墓的调查成果发表。虽在1920—1930年初,清化的汉墓被帕若和克莱芒·于埃(Clemant Huet)等文物收藏家所盗挖,但真正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则是由阳士主持进行的。[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70—271頁。需要说明的是自1959年开始,越南考古工作对清化地区的汉系墓也展开过发掘调查,1960年代末及其后亦有不少的调查发掘工作,但受政治与出版所限,越南考古学家的研究报告很难被外国学者所利用,故在学界的影响极为有限。自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对汉系墓,尤其是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的汉系墓的发掘调查和研究报告,数量非常多,发现的墓葬已经超过2万座。尽管岭南地方与越南北部的早期历史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以一种地域或某种历史情形去推测另一区域的历史态势难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故而也无法完全用岭南地区的汉墓去比对或硬性推测越南北部的汉系墓情况。[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275頁。但基于公元前后共同隶属于南越国和交趾郡管辖这一历史事实,故而在同一历史体系参照下的比较认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阳士对东山汉系墓的调查和挖掘工作,主要集中在1939年进行的第三次作业。依据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考古民族学博物馆和胡志明市越南历史博物馆所藏阳士第三次调查资料及后续调查资料可知,他主要对Man Thon墓群、Ngoc Am墓群、Bim Son墓群、Phu Coc墓群、Lien Huong墓群、Vuc Trung墓群、Tam Tho墓群进行作业,共发掘21座墓,其中16座墓出土遗物最多的是陶器,绝大多数是壶类和甕类,而钵、碗、皿类、陶制明器比较少;青铜器、铁器、玉制品、石制品等除了Man Thon1—A墓之外,其他墓葬出土较少。这与阳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北宁和清化挖掘的墓葬比起来,器种和数量相对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三次发掘以小型墓葬居多,而且破坏和盗挖情况非常严重。[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314頁。
通过对汉系墓陪葬陶器、铜钱、铜器等实际年代的比对计算,越南汉系墓大致可分为六个发展时期:ⅢA期—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前半、ⅢB期—公元前1世纪后半至公元1世纪初期、ⅢC期—公元前1世纪前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ⅣA期—公元前1世纪后叶至公元2世纪中叶、ⅣB期—公元前2世纪后叶至公元3世纪(前叶—中叶)、Ⅴ期—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334頁。在华南地区的汉墓系统中,公元1世纪前叶到中叶乃是木棺墓向砖室墓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大致即是王莽时期。这一转变与越南北部的变化情况较为一致,即是公元前111年南越灭亡后的发生情形。这一现象也标着东山文化的终结。[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336頁。
麻河流域的邵洋遗迹和玉勒遗址的土圹/木棺墓,是砖室墓出现之前的汉系类型墓,大致处于南越灭亡前后到西汉后期。从其遗构、埋葬方式、布局等特点来看,既与广东南越汉系墓相似,又有一些不同点。最大的不同之处则是“室”的有无。[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342頁。这一差别的原因则可能与广东南越系汉墓受到楚系墓与秦汉系墓的影响有关,而越南清化地区或许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注]俵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第344頁。公元1时期前后至3世纪出土的汉系墓则以砖室墓为主,阳士第3次在麻河流域调查发掘的主要是砖室墓。从其主体部分的形态和规模、内部设施的变化、出土砖的分析可知,越南汉系墓中的“后藏椁”“后藏室”的特点较为鲜明,这一情况在华南汉系墓中基本上没有发现。何以会有这样的特点呢?对此尚无清楚的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越南汉系墓的构造确实是与中国的汉系墓有一些差异的。
俵氏在该著中,以铜鼓为轴,通过对东山文化与越南汉系墓的综合分析,加以与云南石寨山文化和岭南地区的汉系墓的比对,清晰地重构了越南北部从东山文化到汉代郡县时期“内部”之越与“外部”之汉的文化变迁、融合甚至是冲突、衰退、消亡的起伏与演变情况。他以考古调查、尤其考古实物来消泯掺杂于学术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政治话语、复原历史面貌的这一工作无疑是成功的。毋庸置疑,“民族主义”政治话语的“中国模式”“越南模式”均应值得警惕,彼此之间简单而鲁莽的“否定”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