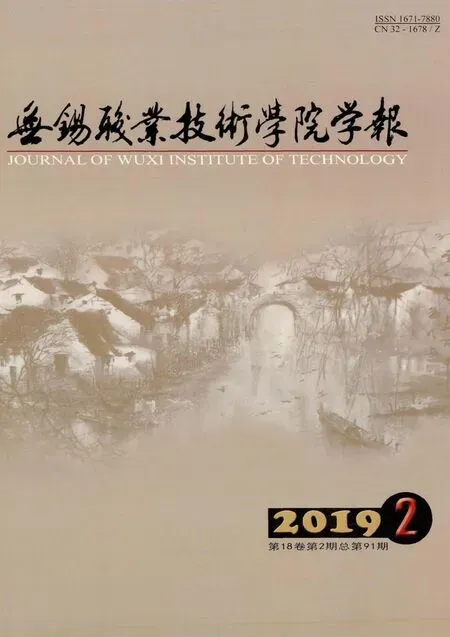试论汪曾祺早期小说中人物的内在叙事
岑梦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创作方式受到文坛的注目。他早期的小说中常常忽视故事发生的情节以及故事情节之间的连贯性,事件发生的前后关联等。他经常采用的手法是让小说中的主人公站到小说叙述的层面,由小说主人公的思绪引导着作品的发展,主人公的思绪思考到当下就描写当下的故事,联想到过去就描写过去发生过的种种。因此,在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作者不太注意故事情节之间的连贯性,甚至有些作品模糊了故事情节,转向小说人物内在性的叙述。这样寻着小说人物内在意识的叙述方式,又使他小说笔下的人物都是形象化、象征化、符号化的,甚至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没有确定的姓名,或者用人称代词“我”“他(她)”代替,如《钓》中的主人公“我”、《春天》中的主人公“我”、《猎猎》中的主人公“他”等,汪曾祺早期小说中的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用人称代词“我”“他(她)”来代替的;或者用中国农村典型的命名方式给人物起一个小名儿,小女孩儿的名字后跟个“子”,小男孩则在名字后加个“哥儿”,如《翠子》中的“翠子”,《悒郁》中的“银子”,《春天》中的“玉哥儿”“春哥儿”“英子”等;或者用人物的外貌来给人物起名,最为典型的是《寒夜》中守夜的一群人,“老爹,二疙瘩,大炮,蛤蟆,海里蹦”,“这几位,不必去请教,看一眼便知道谁是谁,甚么名字属于甚么主人。”[1]17以及用人物的职业给他们命名的,如《灯下》中的药材店里的陈相公称“学徒”,陶先生和苏先生是“同事”身份,称他们为“先生”,而总管药店大小事务的是“管事”,于是就有了“卢管事”。
汪曾祺早期小说中的人物似乎被作者赋予重大使命,通过他们能够展现出作者更加复杂的内心感受。
1 中国人共识情感抒写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大多是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创作的,那时的他经历着与过去在江苏高邮截然不同的生活,独身一人远离家乡,加之他那段艰苦的求学经历、病痛的折磨,处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下,他那种浓厚的思乡、恋乡之情也随之迸发出来,所以作者由自身的经历引发联想创作到文学作品中使小说中的人物也带有这种情感。作者在营构小说时总是让他笔下的人物的思想情绪在一瞬间转移到童年、往事的追忆中。如小说《钓》中的主人公“为怕携归无端的烦忧(梦乡的可怜土产),不敢去寻访枕上的湖山”[1]3。开篇就奠定了小说主人公思乡的苦闷,他试图消解这种浓浓的思乡之情,但却还是在有意无意间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自己的童年趣事。
汪曾祺的恋乡不止于此,作者还善于用人们共同的情感来进行叙写,这些情感都是中国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感态度,“乡愁”就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主题。作者在他的小说中引入这样的主题更能将读者带入作者试图构造的情感世界中。如《钓》中用于表现人们归家急切心情的,“昨晚一定下过牛毛雨,看绵软的土径上,清晰的画出一个个脚印,一个守着油灯的盼待,拉快了这些脚步,脚掌的部分那么深,而脚跟的部分却如此清浅,而且两个脚印的距离很长,想见归家时的急切了。你可没有要紧事,不必追迹这些脚印,尽管慢点儿。”[1]4通过归家时的脚印来引发出思家恋乡之情体现了作者的别出心裁,最后一句的自嘲更加凸显出主人公落寞的心境。在这样的气氛渲染之下更能够感受到主人公思家恋乡的心情,也能够让读者领会到主人公孤身一人在外的落寞与孤寂。
展示主人公乡愁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自己童年美好记忆的书写。小说《春天》则是一篇更为典型的怀念儿时伙伴、怀念故乡生活的作品了。作者为了让小说更具有真实感,让小说的叙述者回到儿时的那个身份:春哥儿,以小朋友的视角来讲述童年在春天发生的故事。而“风筝”在小说中似乎又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主人公由现在看到的蓝天,联想到故乡的天空,又由天空想到风筝,想到自己童年与小伙伴儿们在田野上自由自在放风筝的场景。“风筝”就像是中介,一头牵引着“我”,另一头则是令“我”难以忘怀的记忆。
《猎猎》中的这段描写也能够让读者在顷刻间迸发出与小说主人一样的情感,甚至让读者感同身受。“——而他,仍以固定的姿势坐着,一任与夜同时生长的秋风在他疏疏的散发间吹出欲绝的尖音:两手抱膝,竹竿如一个人入睡的孩子,欹倚在他的左肩;头微前仰,像是瞩望着辽远的,辽远的地方。”[1]39作者的这段描写看似平常却在无意间给人一种萧瑟感,落寞的主人公静默地坐在秋风中,无人相伴只有“问路”依靠在他的肩头,这样的一幅画面怎能不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的寂寞与苦闷呢?汪曾祺就是拥有这样一种能力,用寥寥几笔就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主人公的真实感受,并且把读者也带入主人公那时的心境中。
汪曾祺在渲染这些人物复杂意识的时候往往采用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描写来烘托。汪曾祺用特殊的环境来营造出与主人公心境相对应的氛围,这样的一种氛围不仅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小说主人公复杂的心情,而且也能够使读者透过文本感受到小说主人公的心情。汪曾祺笔下的环境描写是与众不同的,是以作者本人为典型的。这是与汪曾祺的家庭文化教育有关联的。汪曾祺从小受祖父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封建私塾教育的教导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加之父亲对他书画等艺术上的影响,使汪曾祺身上又带上了文人的风雅。在这种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之下,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不知不觉间就带有了一些中国味道。因此,这种典型性的环境描写感觉上像是加上了中国古典水墨画的意境美,又有中国文人士大夫那种别致的附庸风雅,给人一种冲淡平和的力量,再加上作者想要通过小说主人公衍生出来的苦闷、寂寥,整体上就是一种淡淡的孤寂感,但是这种“淡”又不是能够让人轻易化解的,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持久的落寞感。如小说《钓》中主人公所营造的氛围,“打开旧卷,一片虞美人的轻瓣静睡在书页上。旧日的娇红已成了凝血的暗紫,边沿更镌了一圈恹恹的深黑。不像打开锈锢的记忆的键,掘出葬了的断梦,遂又悄然掩起。”“烟卷一分分的短了,珍惜的吐出最后一圈,掷了残蒂。一星红火,在灰烬里挣脱最后的呼吸。打开烟盒,已经空了,不禁怅然。”[1]3小说主人公这样稀松平常的吸烟动作在悄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他此刻异常烦闷的心情,可是文人那种独有的自持内敛又使他的情绪不轻易外露,只能通过这些小动作表现出来。
2 个体生存的困境
在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中不仅能看到中国传统的情感意识,还能够看到他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影子。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那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如果说阿左林和纪德等给予汪曾祺的主要是艺术风格和感觉方式上的启发,那么萨特和加缪给予他的则主要是思想上的启发”[2]。汪曾祺开始思考人的生存困境,存在的意义,并且渐渐地将它们引入小说的创作中。
汪曾祺在探索这个困惑时,他思考到了那些生存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们。小说《寒夜》与《灯下》,这两篇可以说是有相似之处的。两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凡人物,并且都描绘了一幅人物群像图,不论是在冬天雪夜的牛棚中还是在小城中一个小小的药材店中,里面的人物都是各有千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作者选取这两个时刻也有作者的深意,寒冬雪夜守夜人本就疲惫万分,但他们学会苦中作乐,以起哄年青人的亲事为乐;而傍晚的药材铺则是劳作了一天,人们休息、谈天、玩闹的好去处,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围在一起讲城里的闲话琐事,这都是平常百姓最爱的乐趣。在这热闹场面的背后也隐含着作者的深意。守夜人取笑年轻人的亲事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现在面临生存困境的转移,在这样寒冷的冬夜守夜纯属无奈,是受生活的压迫。在这种无聊单调的工作中,他们只能以乡下人自认为最热闹的男女情爱来消解。
小说《灯下》则隐含更多生存困境,如职场中上下级的严格区分,且不用说在大城市怎么样,在这小小的药材铺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对社会变化难以适应的困境,这一点在陆二先生的身上能够体现出来。他曾经作为蒙馆先生,早已习惯本本分分地用毛笔写字,按照俗例每天到一个学生家吃饭,周而复始。但是现在“世界变了”,店面招牌上都是些花花绿绿的像画一样的美术字,他感到蒙馆的教育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体现在虾二爷身上的则是更为现实的难以满足口腹之欲的困境,虾二爷是药材铺店主的本家,每天傍晚到饭点就来店里吃饭,但是他却没有命令开饭的权利。这就是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这从侧面也能看出汪曾祺早年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感悟。
汪曾祺笔下人物的生存困境许多都是人的无奈之举,人自身对生活的难以把控。小说《翠子》的主人公翠子就是一个生活在由父母、雇主决定中,不能把控自己命运的女孩儿。她的到来、离开都是由家中的长辈决定的,她到年纪该成婚了,于是在她父母与雇主的协商下找个日子就把她接走了。翠子面对这样不合理的事件能够做的也只是满心留恋,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流泪告别。《复仇》中的复仇者走上复仇之路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是母亲从小到大在他耳边一再的叮咛,是中国传统观念中为父报仇的思维在主导着他的复仇信念。他甚至找寻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一生不是由他自己来把控的,他是一个被复仇化了的形象的人。小说《猎猎》的主人公,他的职业是随着轮船事业的兴衰而存在的。他曾经是在轮船上帮助漂泊异乡的人消解寂寞的说书人,但随着社会变化,轮船事业衰落,自然他也失去了这唯一的职业。他对自己的人生不能把握,他最后只能独自在岸边暗自神伤,由自己的思绪带领他飘到自己所认为的“光辉岁月”。
笔者在研读汪曾祺这类早期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他总是偏爱将小说主人公放置在一种孤独、冷寂的环境中,尤其他喜爱“黑夜”“黄昏”这类意象,这类意象自古代以来就暗示着萧条、沉寂与落寞。作者将它们引入对人生命运、生存困境难以把握的小说中,更能够体现这类人的苦恼、困惑。如《复仇》中的主人公在傍晚时分留宿寺庙,又在漆黑的夜晚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舞剑消愁,“山门外有一片平地,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夜已深,星很少,但是有夜的光,夜的本身的光,也够照出他的剑花朵朵,他收住最后一着,很踌躇满志,一点轻狂围住他的周身,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一些断草飞起来,落在他的襟上。和着溺爱与珍惜,在丁丁的声息中,他小心地把剑插入鞘里。”[1]30
黑夜以及寺庙的不寻常让复仇者的心绪不宁,他回想起往事的种种因缘,回想自己复仇的艰辛与苦恼,让他这样一个孤身在外的异乡客更显落寞与孤寂,而能够使他暂时得以慰藉的就是伴随着他的那把剑,这样的存在对复仇者来说是何其不幸。提到“黄昏”已经让人感到寂寞了,但是再联想到黄昏时孤身一人的场景是该多么寂寥呀!
小说《猎猎》的开篇汪曾祺就渲染了这样一个场景,“将暝的夕阳,把他的‘问路’在背河的土阶上折成一段段屈曲的影子,又一段段让它们伸直,引他慢步越过堤面,坐到临水的石级旁的土墩上,背向着长堤风尘中疏落的脚印;当牧羊人在空际振一声长鞭,驱饱食的羊群归去,一行雁字没入白头的芦丛的时候。”[1]39更甚的是汪曾祺将主人公回想过往的时间定为秋日的黄昏,“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感受在作者的只言片语间更加浓厚了。夜色渐浓,主人公身上那种寂寥感也在随之加深,“现在,暮色从烟水间合起,教人猛一转念,大为惊愕:怎么,天已经黑了!甚么时候开始的呢?像从终日相守的人底面上偶然发现一道衰老的皱纹一样,几乎是不能置信的,然而的确已经黑了,你看湖上已落了两点明灭的红光(是寒星?渔火?),而且幽冥的钟声已经颤抖在渐浓的寒气里了。”[1]39
从这段文字中不仅能够看出小说主人公难以消散的落寞与哀愁,而且能够激起读者的想象,似乎回到了“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歌意境中。黄昏傍晚的确是人们思绪发散的最好时刻,在黄昏朦胧的意境中,总是能够让人联想到种种往事,尤其是对出门在外的旅行人来说。正如小说《待车》中讲述的那样,“将晚的车上堆积的影子太多了,是的,将晚的车上堆积的烟灰太多了。风和太阳把两边的树绿尽向车上倾泼,弄得车里车外淋淋漓漓。因此,车拼着命跑。可不是,表的声息都弱了。如落花,表的声息积满一室,又飘着,上上下下,如柳絮呢。”[1]67当小说主人公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下,怎能不发出苦闷、寂寥之感呢。同时,这也表现了汪曾祺孤身一人在云南昆明求学的痛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质问。
3 现代人情爱的体验
汪曾祺早期小说书写的都是那一类普通人,在他们身上除了体现出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外,在自己的情感体验上也有自己的苦闷。笔者发现作者总是喜欢将男女的初恋体验写入小说中。或许是因为初恋那种隐秘,不能为外人知晓的特性。汪曾祺将它置于男女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中是特别恰当的。如小说《待车》就是主人公在待车室回忆与恋人的种种过往,甚至当主人公情绪中情爱的波动大于亲情时,他可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刻,只为追求心上的“那一种极美的花”。小说《春天》也是在回忆主人公童年美好记忆中,穿插自己内心懵懵懂懂的情感体验。为了心爱的女孩儿英子,对其父亲表示尊重不叫他“老败爹”。想在英子面前展现自己放风筝的技术,与玉哥儿引发了一场战争,最终因为英子的责怪,感觉自己在她面前丢了面子,没有受到英子的疼爱,而以一种他自认为“最恶毒”的方式“离间”英子与玉哥儿的关系。从这个细节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小孩子幼稚的情感体验,但是却很真实。
如果说《待车》和《春天》都是主人公对过去情感体验的一种回忆,那么《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描写的就是主人公在路途上的“艳遇”。作者别出心裁地由女人的一双手(手套)写起,由这双手(手套)联想到主人公“我”上幼稚园时遇到的老师。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主人公儿时上课的场景,似乎也能够与汪曾祺自身的童年经历联系起来。或许是这样的情感体验在起作用,主人公对待船上的女人显得更加亲近,两人共同攀谈着共有的话题:绘画。但是主人公在谈话过程中依旧忘不了那双引起他注意的手,因此在后文的叙写中,主人公将自己的思绪引向对那双手的描写:
“你看,你的左手就比右手红些,因为她受暖的时间长些。你的体温从你的戒指上慢慢消失了。李长吉说‘腰围白玉冷’,你的戒指一会儿就显得硬得多!”“我用手掩住眼睛。我的手上感到百倍与那只猫的柔润,像一只招凉的猫,一点轻轻的抖,她的手。” “她的手”就是带给我情爱体验的暗号,把“我”的那颗动荡不安的心越发搅动的波澜迭起。作者随着描写的“波——,岂有此理,一只小小的船安这么大一个汽笛。随着人声喧沸,脚步忽乱。”[1]125-129这看似在写船靠岸人们争先恐后下船的场景,实则反映出主人公复杂的心境,巨大的汽笛声打破了自己的陷入情爱中的甜蜜感受,破坏了自己与女人的带有情愫的氛围,同时又暗示自己的爱情似乎走到尽头,下船后这种情感将会慢慢消散,在这样一种思绪的体验下,主人公的内心是格外复杂混乱的,有喜又有悲。
汪曾祺不仅擅长于将类似与自己的主人公“我”的情感体验加入小说中,而且他还能够将一些小女孩儿们的情感体验写到小说中。这一方面,笔者能够看到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一种师承关系。小说《悒郁》展现给读者们的就是一个对爱情、初恋充满了憧憬的小女孩儿。汪曾祺用秋天成熟的稻穗来暗示少女银子的成熟。处于少女怀春期的银子充满着对恋人的美好想象,想要跑到更远的地方,想象着自由。而银子内心上奔跑的那匹马既把她那颗少女心“得得得……”搅得一团糟,而且也放飞了她的小心思,她轻声低唱代表少女成熟的民歌,同时又在恍恍惚惚间听到有人接唱露骨的情歌,银子表面上呵斥露骨的情歌“狗嘴里说人话,不像人”,其实她也在憧憬着情歌中的情爱。
《悒郁》这篇小说作者营造的环境氛围也特别适合女孩子遐想,“时近黄昏,夕阳在西天烧起篝火,地面一切都薄薄地镀了一层金。在卷发似的常青树梢上勾勒起一道金边,蓬松松的,静静的。”[1]13银子在秋天黄昏朦胧的时刻,在这样暖色调的气氛中才能够无忧无虑地幻想,想着自己梦中的恋人,畅想自己美好的爱情。小说最后银子感觉受欺负,她的哭,其实也是在暗示她情感体验的不真实,银子期待着美好的爱情,同时又埋怨情爱的不来临。
小说《河上》描写的也是少女朦胧的情愫。不同的是小说《悒郁》是以主人公银子展开的对于恋爱期待的情感体验,而《河上》则是以小说写作者的视角来展现三儿的情感。从这一角度看,如果说银子是怀揣着情爱想象,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表现的话,那么《河上》中三儿的情感则是通过与城里少爷的对话或是行动上的对抗中看出来的。三儿调皮地抗拒少爷介入乡下生活,嫌弃他笨手笨脚地跟她们下田劳作,乡下最好的吃食也满足不了少爷的“城里胃”。可是,正当三儿抱怨着城里少爷 “乡下生活他甚么也干不好,就学会了唱歌!”时,少爷突然提出要借船上城去,这可一下子将三儿敏感的少女情怀波动了。三儿拒绝借船的表现实则是她的害怕,担心少爷上城就不再回来,但是矛盾的三儿最后又亲自送少爷上城。在划船上城的过程中,从三儿与少爷之间的对抗中可以看出三儿复杂的情感。三儿这种奇怪的表现不仅能让少爷感受到她的情愫,而且也能让读者在一瞬间明明白白。虽然小说全篇都没有用很明显的字词来表现少爷与三儿的情爱,但是在作者隐晦的言辞中却能感受得一清二楚。三儿的那种心口不一的表现,少爷故意逗弄三儿的行为正是最典型的处于暧昧期男女们的表现方式。
汪曾祺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独白,同时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作者在采用此手法构造小说上的不同。或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过去的某段经历,或是脑子中记忆的闪回没有什么常规的逻辑可言,或者是由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带领着故事的发展。从这些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带有汪曾祺本人的情感与生活经历,他们意识闪回的片段都带有作者故乡的特色,或者小说主人公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那段经历有相似之处,并且这类小说的主人公身上都带有读书人的痕迹,甚至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古代文人郁郁不得志的影子,如他们消解寂寞的方式是钓鱼、读书、放风筝,他们不在意这样事情的结果反而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寻找乐趣。
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中除了这样一类有特色的人物外,还有一类是他经常接触的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汪曾祺善于把他们日常的生活状况、乐趣写到小说中,如《寒夜》《灯下》就是描写这样一类人。这样的两类人在汪曾祺早期小说中经常能够读到,但是汪曾祺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提笔创作时却将自己的经历都投注到描写那些普通平凡的底层人民身上,的确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