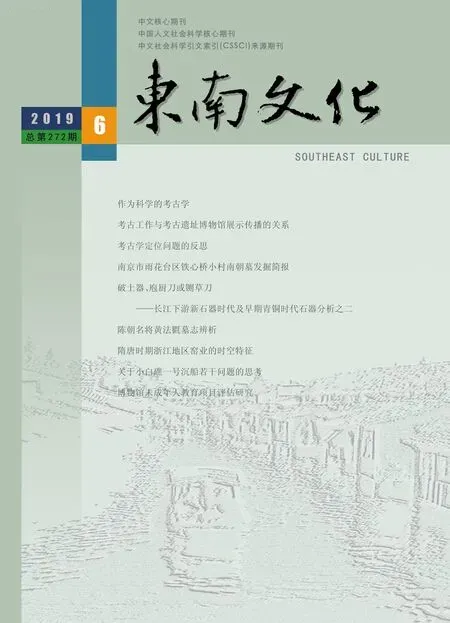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
淮北市文物局
内容提要:2019年,安徽省淮北市文物部门清理出两座汉代石祠C1、C2。C1保存完整,呈“凸”字形结构,前室后龛,内部刻满画像。经研究,这是第一例经考古发现、且配置构件完整无缺的汉代小祠堂。其独特的平面布局,抱鼓石形建筑风格,在全国皆是首次发现,填补了汉代祠堂研究的空白。
2019年元月,淮北市文物局根据群众报告线索,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淮北大唐发电厂西侧的洪山南坡粉煤灰池水沟内发现几块露出的汉代画像石(图一)。由于位置处在电厂储灰场,较为偏僻,且环境复杂,为保证所发现汉代画像石安全,随即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工作。清理出两座汉代祠堂,其中一座保存完整,一座前期遭到破坏,仅存几块祠堂构件。两座祠堂(分别编号为C1和C2)相邻较近,建造于朝向东南的山坡处,因遭受泥石淤积,掩埋于表土下,幸存至今(彩插一︰1、2)。两个祠堂北部所依的小山当地称作洪山,因此将该祠堂定名为“洪山汉代画像石祠”。现将两座祠堂分别介绍如下。
一、1号祠堂
C1朝向南,方向185°。其构造为前室后龛,呈“凸”字形结构,前室铺地基石高于后龛铺地基石。整个祠堂东西宽1.62、南北进深1.52米。前室内宽1.25、进深0.79、高0.78米;后龛内宽0.79、进深0.505、高0.515米(图二)。
C1基本保持建造时的形状,但是左侧因地基沉陷而向东倾斜,导致前盖顶石受力不均,中间断裂,塌落在前室,前室2块抱鼓石稍有错位。前室左右壁石基础用碎石作底,后龛3块壁石则直接建立在基石之上。因受场地限制,仅对C1后侧及东侧局部区域进行了钻探,发现有封土和砖室墓存在。C1的外壁粗糙,凸凹不平,没有人工加工痕迹,因此判断祠堂除朝向南侧一面外,其他的三面皆应掩埋在封土中。C1两侧有间断用粗糙山石垒砌的石墙,应是早期被破坏的墓垣。由于墓垣破坏严重,没有对墓垣进行清理发掘,根据墓垣走向判断,墓垣应呈长方形,祠堂则大致位于南部墓垣的中间位置。
C1由9块青石组成,依次为前室盖顶石1块,前室左右侧壁石2块,后龛盖顶石1块,左右侧壁石2块,后壁石1块,前室基石1块,后龛基石1块。其中刻有画像的石头7块,画像共11幅。分别描述如下。
石1,祠堂前室盖顶石。长方形,长20、宽53、高28.5厘米。中间已断裂为两截,上侧仿刻瓦脊和连檐瓦当,内侧刻有两个浅槽,其尺寸正好与两块抱鼓石上部的方柱嵌合。画像朝向外侧,中间刻画羊头,羊头两侧刻画了两条鱼,鱼的两侧分别刻画青龙、白虎(图三︰1;彩插一︰3)。
石2,前室左侧壁石。抱鼓石形,下宽上窄,下部略呈弧形,向上逐步收窄为矩形的柱子。高90、宽79、厚26厘米。该石正立面和内侧壁分别刻有画像。正面画像上刻龟和翼虎。内侧壁画像题材为“狩猎图”,自上而下分别刻画一人肩扛猎叉疾步前行,一只猴子受惊攀援至大树上,两只猎犬飞奔追赶猎物,一匹马儿立在树下(图三︰2、3;彩插三︰1)。
石3,前室右侧壁石。形制与石2一致,高90、宽69、厚26.5厘米。正面和内侧壁分别刻有画像,正面画像上刻蹶张武士和翼龙,内侧壁自上而下分别刻画伏羲女娲束长发、相向而立,一羽人持插有鱼儿的短杆,逗引一只仙鹤,最下端为车马出行画像(图三︰4、5;彩插三︰2)。
石4,后龛盖顶石。长方形,长138、宽57.5、厚28.5厘米。朝向外侧的一面刻有画像,刻画西王母、羽人、青鸟、九尾狐、羽人、东王公(图四︰1;彩插一︰4)。
石5,后龛左侧壁石。正方形,长51、宽51.8、厚24.5厘米。正面和内侧壁分别刻有画像。正面刻画铺首衔环、柿蒂纹、水波纹(图四︰2)。内侧壁上格刻画“建鼓舞”,二人双手执桴击建鼓,建鼓上有二层幢,饰羽葆和华盖,一个羽人和猴子攀援其上;下格刻画宴饮图,两人跽坐于酒樽前,手持耳杯畅饮,似在欣赏歌舞,两侧各有一人持剑守护(图四︰3;彩插二︰1)。
石6,后龛右侧壁石。正方形,长51、宽51.8、厚24.5厘米。正面和内侧壁分别刻有画像。正面刻画铺首衔环、柿蒂纹、水波纹(图四︰4)。内侧壁刻画楼阁、六博、杂耍题材,画面正中两人在楼阁内对弈六博棋局,下格刻画杂耍场景,中间的人在作跳丸表演,旁观三人似做击掌状。楼阁右侧一仆人肩着毕网(笼或篮)站立,左侧一仆人持剑守卫,望楼内刻画弓弩,应象征守卫瞭望之用。屋脊处两只猴子攀援其上,正中站立一只异兽(图四︰5;彩插二︰2)。
石7,后龛后壁石。长方形,长 107、宽53、厚16厘米。刻画楼阁宴饮题材,表现内容较为宏大,刻画人物9人,动物9个,建筑3组。楼阁中间刻画两人饮酒正酣,楼阁两侧各有一人倚栏而坐。楼下一人手举炙肉拾阶而上,一人从壶中倒酒,两个妇人似在烹煮肉羹,一条狗儿闻香垂涎观看。楼阁之上刻画羽人饲凤、青鸟、猴子等祥瑞景象。两侧阙楼上层各倒置一弓弩,阙下置盾和戈,应象征守卫之用;阙楼顶上各站立一只鸠鸟(图四︰6;彩插二︰3)。
石8,前室地基石。长方形,长 124、宽77、厚16厘米。临近后龛室左侧位置雕凿出一只耳杯(图五;彩插三︰3)。基石横向铺置于前室,略高于后龛室基石,两块抱鼓石左右紧挨而立。
石9,后龛地基石。长方形,长 129、宽65、厚14厘米。略低于前室,左、右及后侧边缘皆刻有规整的浅槽,方便摆放左、右及后壁石(图五;彩插三︰4)。
二、2号祠堂
C2早期遭到破坏,其建造形制和布局与C1相同,为前室后龛布局。原址仅存祠堂基石2块,左侧抱鼓石1块,残缺一半的前盖顶石1块(图六)。距C2东南约3米处发现1块后龛盖顶石,应是早期C2被拆除时所弃置。C2朝向正东,有墓垣间断与C1相连,之间相距不到2米,应与C1墓主人同属于一个家族。C2东西残宽1.48、南北残长1.31米。前室内宽1.25、进深0.7、高0.84米。后龛内宽0.8、进深0.5、高0.515米,内部空间尺寸与C1基本相同。
C2由5块青石组成。其中刻有画像的3块,画像共4幅。分别描述如下。
石1,前室盖顶石,倒塌于祠堂前侧。长方形,部分残缺,长172、宽82、高30.5厘米。上侧仿刻瓦脊和连檐瓦当,内侧刻有浅槽。画像朝向外侧,刻有羊头、鱼画像(图七︰1)。
石2,前室左侧壁石。抱鼓石形,高93、宽84.5、厚24厘米。该石正面和内侧壁分别刻有画像。正面画像上刻蹶张武士和翼虎(图七︰2)。内侧壁画像题材为“车马出行图”,上刻一武士肩着长钺、牵一猎犬疾行,下面则刻画车马出行的场景(图七︰3;彩插三︰5)。
石3,后龛盖顶石。该石发现于C1、C2正前方约3米多处,应是早期C2被拆除后弃置。该石长方形,长147、宽68、厚42厘米。朝向外侧的一面刻有画像,刻画题材与C1后龛盖顶石基本相同,从左至右依次为西王母、羽人、玉兔捣药、青鸟、九尾狐、龙马、羽人、东王公(图七︰4)。
石4,前室地基石。长方形,长125、宽70、厚15厘米。临近后龛室左右两侧位置雕凿了两只耳杯(图六)。基石横向铺置于前室,略高于后龛室基石。
石5,后龛地基石。长方形,长141、宽65、厚15厘米。略低于前室,左、右及后侧边缘皆刻有规整的浅槽,方便摆放左、右及后壁石(图六)。
三、结语
洪山汉代画像石祠C1内部最宽处1.52、最高处0.78米,占地约1.48平方米;C2残宽1.48、高0.84米,占地约1.4平方米。可见两座祠堂体量不大,形制矮小,应属于山东嘉祥宋山1号小祠堂类型[1]。洪山汉代画像石祠由前后盖顶石、左右两块抱鼓石形壁石、后龛左右侧壁石、后壁石以及两块基石组成,其前室后龛的建筑布局要比山东宋山1号小祠堂复杂许多,是一种新的汉代祠堂建筑形制(图八)。尤其是前室的两块抱鼓石形制独特,使祠堂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别致,更具有装饰艺术效果。洪山汉代画像石祠两座祠堂画像风格一致,采用阴线刻与剔地较浅的浅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技法,是阴线刻技法向浅浮雕技法迈进的时期,刻画技法、刻画题材与徐州汉王乡“永平四年”(61年)小祠堂有相近之处[2],因此建造年代应不早于东汉中期。相关研究认为,这类祠堂的营建者一般为小官吏或中小地主[3]。
汉代祠堂是对地下墓葬中死者进行祭祀的地面建筑,其四壁皆刻画精美的画像,宋代时就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历经千年沧桑变化后,现存完整的祠堂极为罕见。根据蒋英炬、杨爱国著《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汉代祠堂建筑仅发现于皖北、苏北和山东地区。多年来,这一区域虽然不断有汉代祠堂资料的公布,但是除了山东长青孝堂山祠堂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汉代祠堂[4],其他发现的祠堂基本残毁,倾圮成零散的构件。像洪山汉代画像石祠这类小祠堂,所用石材形体不大且较规整,并刻有图像,很容易被后人拆除并再利用,故在此之前,尚无完整的汉代小祠堂见诸于考古报告。因此,洪山汉代画像石祠应是第一例经考古发现、且配置构件完整无缺的汉代小祠堂。
经研究,目前所知的汉代石质结构祠堂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的小祠堂,洪山汉代画像石祠也可归于这一范畴;第二种为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第三种为双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第四种为双开间悬山顶后壁有龛的祠堂[5]。但洪山汉代画像石祠的发现又可以证明,除去以上四种汉代祠堂建筑类型,在皖北还存在一种形制独特的汉代祠堂,这就是抱鼓石形汉代祠堂。抱鼓石形汉代祠堂大多发现于皖北淮北市、萧县以及苏北等区域,尤其是淮北市,在20世纪80年代迄今基本建设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这类祠堂构件[6]。这种祠堂一经发现,就引起广泛关注,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朱永德《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祠堂》、刘辉《汉画新释》对这种祠堂都曾进行分析研究[7]。由于一直缺乏详实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人们对这种祠堂的建造形制和布局始终莫衷一是。洪山汉代画像石祠的发现,证实了这种祠堂的存在,展示了这种祠堂建造形制和布局,明确了祠堂内画像的基本刻画题材和配置方向,为人们更好地研究这种祠堂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C1、C2相邻而建,虽祠堂朝向不同,但其墓垣共用。从祠堂建造形制以及画像刻画风格来看,祠堂应是同一批工匠在一个时期而为,因此C1、C2应是同一家族墓地中不同墓葬单独建设的祠堂。笔者认为,祠堂前室基石上雕凿耳杯,其功能是为祭祀墓主服务;后龛功能应是用于摆放墓主的神位,类似安徽宿县褚兰汉墓祠堂内镌刻的“胡元壬墓碑”[8],只不过“胡元壬墓碑”是镌刻在祠堂的后壁石上,而洪山汉代画像石祠后龛内则可能是摆放物件,其材质可能为石质或木质,因其可被随意移动,早期即已丢弃或毁坏。
总之,洪山汉代画像石祠的发现,使我们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汉代墓上祠堂建筑形制、画像石配置等考古资料。尤其是C1建筑构件完整,其独特的前室后龛布局,抱鼓石形建筑风格,在全国皆是首次发现,填补了汉代祠堂研究的空白,其学术研究价值非常重要,是难得可贵的汉代文化瑰宝。
[1]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2]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文物》1990年第9期。
[3]刘尊志:《江苏徐州东沿村出土东汉祠堂画像石浅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
[4]同[1],第83页。
[5]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6]朱永德、解华顶、姜海洲:《淮北汉代画像石图录》,黄山书社2016年,第161—213页。
[7]a.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63—66页;b.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c.朱永德:《皖北“抱鼓石”形汉代画像祠堂》,《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8年,第485页;d.刘辉:《汉画新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310页。
[8]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