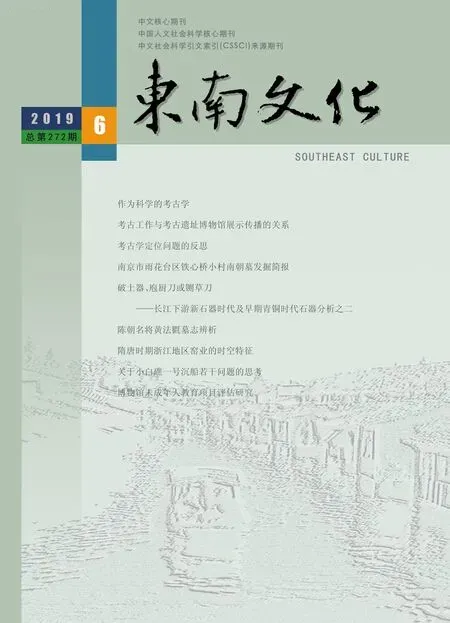明代南京钦天监副贝琳家族墓发掘简报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内容提要:2015年4-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南京市江宁区南京南站南侧、宏运大道北侧清理了14座明代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金、银、铜和砖质文物。家族墓群呈“品”字形有序排列。位于墓群东部的墓葬M32出土了墓志,墓主为南京钦天监副贝琳。该家族墓的发现,为研究南京地区明代地方人文历史、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实物材料。
2015年4—6月,为配合南京南站站东片区地块的出让,受南京市文广新局委托,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现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位于江宁区南京南站南侧、宏运大道北侧的一处墓地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图一)。该墓地位于艾村北部的一处土岗上。本次发掘共清理明代墓葬14座,分四排七组,呈“品”字形排列(图二;彩插九︰1)。东部的两座墓葬(M31、M32)位于南北向一条状黑土带范围内,东西两侧各被一褐土带所围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范围其西部南北两侧分三排整齐排列着其余12座墓葬。从墓葬排列方式来看,推测应为一家族墓地。14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表一)。南北两侧分布的12座墓葬形制简单,出土遗物少。而东部的两座墓葬(M31、M32)墓葬形制特殊,分别呈半圆形、圆形,营建方式颇为讲究,且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墓主身份明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M31、M32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M31、M32位于墓群东部中心位置,M31北部被一晚期墓葬(编号M17)打破,南部打破M32。
1.M31
M31开口于现代耕土层下,竖穴土坑墓,方向90°(图三)。墓葬开口呈半圆形,下部呈长方形。构筑时先下挖一个深约0.54米的半圆形土坑,长径3.2、短径1.76米。然后在半圆形土坑底部中央开挖一个长2.24、宽0.74、深2米的长方形墓坑。墓底放置一棺,木棺已腐朽,根据朽痕,推测长1.8、宽0.46、内高0.44米。清理中,棺内可见少许褐色漆皮,疑为棺板上漆皮脱落所致。棺内骨架不存,仅在棺内东部见牙齿两颗,棺内有铁钉数枚。
2.M32
M32开口于现代耕土层下,竖穴土坑浇浆墓,方向100°(图四)。墓葬开口呈圆形,下部呈长方形。距圆形墓圹西约1.25米处,有一长1、宽0.82、深0.76米的长方形土坑,坑内近东壁处竖立一合石墓志。M32构筑时,先下挖一直径为3.3米的圆形土坑,然后在距墓葬开口0.44米处,圆形土坑底部中央开挖一长2.76、宽1.4、深1.88米的长方形墓坑,距墓葬开口约1.2米处,用三合土浆浇筑墓圹,四壁浇浆厚约0.13—0.22米。将木棺及椁下葬之后,以三合土浆填充于棺椁之间(彩插九︰2),并在椁板上方浇筑一层厚约0.18米的三合土浆,与墓圹持平(彩插九︰3)。然后在三合土浆上覆一层厚约0.1米的草木灰,其上填黄褐色土,厚约0.6米。在黄褐色土上部再浇筑一层厚约0.05米的三合土浆,其上用草木灰覆盖(彩插九︰4),直至与圆形土坑底部持平,最后以灰褐色土及碎石回填,并进行了多次夯筑。
M32为一棺两椁。椁板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均已腐朽不存,仅存少量木屑、铁钉、漆皮等。木棺保存较好,内长1.84、内宽0.5,内高0.5-0.6米。棺盖板、侧板、挡板、底板皆用整木制成。棺盖板四角因棺钉的缘故残损严重,中部保存尚好,最厚处厚0.06米。两侧侧板及挡板均厚0.02米。东部挡板内壁残留少量朱红色漆痕。棺盖板、侧板、挡板外均未见漆痕。棺底板通长1.84、宽0.7、厚0.04米,内壁髹朱红色漆。棺内上层为青膏泥,厚0.4米,下层为灰色泥沙,厚0.1米。随葬品大部分出土于灰色泥沙层中。墓主骨骼保存差,仅见少量未腐朽的骨殖残留。棺底板下为生土台,略高于四周。

表一//墓葬发现概况一览表
二、出土器物
两座墓葬出土器物质地有金、银、铜、石、砖等,以M32出土遗物较多。现以单个墓葬为单位,将出土器物分别介绍如下。
1.M31出土器物
共出土各类器物3件(组),质地包括金、银、铜等。其中金、银器出土于头骨附近,铜钱散落于棺底各处。
金币 3枚。保存完整,形制一致,均为方孔圜形钱,平缘,正面穿外以阴弧线分成四等分。M31︰1,正面弧线内刻有“大吉大利”四个字,直径1.7厘米,重1.2克(图五︰1)。M31︰2,正面弧线内刻有“正德壬申”四个字,直径1.65厘米,重1.2克(图五︰2)。M31︰3,正面弧线内刻有“天下太平”四个字,直径1.65厘米,重1.1克(图五︰3;彩插一〇︰3)。
银簪 1件。M31︰4,素面。圆锥形,前端尖细,末端粗,平顶。长12.2、粗端直径0.45厘米,重5.3克(图五︰4)。
铜钱 37枚。M31︰5,散落于棺内。开元通宝37枚,其中7枚残,1枚漫漶不清。直径2.3~2.55厘米(图六)。
2.M32出土器物
共出土各类器物8件(组),质地包括铜、银、石、砖等。其中铜、银器出土于棺内中部,墓志出土于墓葬西部方形土圹内,地契砖出土于墓室东部、内外椁之间。现将出土器物详述如下。
铜组佩 共16件。出土时,穿系的线已腐朽,铜饰件散乱,现存钩1、珩2、瑀2、鱼形铜片4、花2、冲牙2、滴3及料珠若干颗。
铜钩 1件。M32︰9,钩身下方有一圆孔与铜珩相连,上方弯曲呈钩形,系挂腰间。通长5.5厘米(图七︰1;彩插一〇︰1左)。
铜珩 2件。形制、大小相同。翘角云头形,下有五穿孔。保存状况不好,下端五穿孔部分均有残缺。M32︰10,长3.9、宽7厘米(图七︰2;彩插一〇︰1中)。
铜瑀 2件。形制、大小相同。长方形,上下各有均匀间隔的三穿孔。M32︰12,长3.6厘米,宽3.3厘米(图七︰3;彩插一〇︰1右)。
鱼形铜片 4件。形制、大小相同。鱼形,上下各有一穿孔。M32︰14,长4.9厘米(图七︰4;彩插一〇︰1右)。
铜花 2件。形制、大小相同。上下皆成云头形,上下各有三穿孔,左、右各有一穿孔。M32︰18,长4、宽5.8厘米(图七︰5;彩插一〇︰2左)。
铜冲牙 2件。形制、大小相同。上部为云头形,下部为弧形。云头部中央有一穿孔。M32︰20,长4.8、宽5.8厘米(图七︰6;彩插一〇︰2右)。
铜滴 3件。锥形,上端有一穿孔。M32︰22,高1.5厘米(图七︰7;彩插一〇︰2中)。
另出土蓝色料珠(M32︰8)若干颗。
参考各地区出土的组佩资料,将出土铜组佩复原如下。
按可穿系铜佩计算,可分两组。最上方为铜钩;铜钩下方有一珩;珩下有五组穿孔,中间三组穿料珠与长方形瑀相连,两侧穿料珠与瑀两侧的鱼形饰件相连;瑀下与一云头形铜花相连;铜花中部下接一冲牙,冲牙两侧各有一铜滴(图八)。此外,根据文献记载及其他出土资料来看,冲牙两侧还应各有一坠饰,该墓佩饰保存欠完整,惜未发现。
银耳挖 1件。M32︰3,勺头扁圆弯曲成钩形,柄细长,末端锥形。长9、直径0.05~0.3厘米,重3.2克(图七︰8)。
银冥币 3枚。两枚保存完整,一枚残缺一角。形制一致,均为方孔圜形钱,平缘(彩插一〇︰4)。M32︰5,正面刻“长命富贵”(图九︰1)。直径1.5、孔径0.2厘米。重0.9克。M32︰6,正面刻“金玉满堂”(图九︰2)。直径1.5、孔径0.2厘米。重0.7克。M32︰7,正面刻“长生不老”(图九︰3)。直径1.5、孔径0.2厘米。重0.6克。
铜钱 33枚。M32︰4,散落于棺内(图一〇)。淳化元宝1枚,直径2.5厘米。至道元宝3枚,直径2.4厘米。咸平元宝3枚,直径2.5厘米。景德元宝4枚(1枚残),直径2.4~2.5厘米。祥符元宝2枚,直径2.4厘米。祥符通宝2枚,直径2.5厘米。天禧通宝1枚,直径2.4厘米。另有17枚,无法辨识。
砖 1件。M32︰2,方形,长宽均为33.5、厚3.5厘米。其上可见零星朱砂痕,无法识读,疑为地契砖。
带扣残件 1件。M32︰25,铜质,残甚,不可修复。仅存扣板部分,扁平圆角方形。残长3.5、宽1.8、厚0.6厘米。
墓志 一合。M32︰1,石质,完整。由志盖、志石两部分组成。长宽均为62厘米,志盖厚8厘米,志石厚7.5厘米。志盖,框内阴刻篆书“南京钦天监副贝公墓”9字铭文(图一一)。志石正面阴刻楷书志文共32行,满行36字,共计950字(图一二)。录文如下:
南京钦天监监副贝公墓志铭
赐进士及第、嘉议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同修/国史兼经筵讲官,/晋陵王㒜撰文。/赐进士正议大夫、资治尹、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淳安胡拱辰书丹。/赐进士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前都察院副都御史、奉/敕巡抚福建、河南,江浦张瑄篆盖。/贝公讳琳,字宗器,号竹溪拙叟。其始祖立本,河北人,仕江南李氏,为常州刺史,赐锦衣鱼/袋。宋开宝八年,吴越王钱俶据常州,执刺史,流之定海。虽颠沛中,犹服旧赐锦衣,时人以/锦贝呼之。孙孟博,在明道中举,直言,累官浙东转运使。继是亦代有显者,故定海称世胄,/以贝氏为巨擘焉。洪武初,祖可恒谪隶戎籍,来居金陵,生二子,长永阜,公考也。公自少才/敏出伦,尝学举业且有成,曰:是仅足以荣吾身也。又去学象数于司历何公,辞其母,从何/至北京,乃尽得其奥旨,遂被荐充天文生,例除戎籍,公喜曰:斯可以庇吾宗矣。正统间,从/昌平侯杨公,征北虏,至独石而捷。景泰庚午,从征云中,深入至贺兰山。壬申,又从征两广。/皆以其术占候佐军行有功,授钦天监漏刻博士。天顺初,玄象示警,/英庙召见,便殿奏对称旨,赐白金文绮,寻升五官灵台郎。三载给/敕命,赠永阜如其官,母鲍氏封太孺人。成化戊子,因灾异上言,其略曰:大君者,万民之父母;/天地者,大君之父母。天心仁爱人君,时出灾异,以谴告之,人君修德以格天心,则灾变为/祥,凶化为吉。高宗因雉升鼎耳,修德正事,终克嘉靖殷邦。宣王遇旱魃为虐,侧身修行,卒/能中兴周室。遂条陈弭灾图治六事,其言多有可采。庚寅,升监副。壬辰,改南监。时与弟珙/南北异处者,几三十年矣。至是复同居,以旧居湫隘,更作新第于武定桥西。明年,第中产/嘉瓜骈头并蒂,大夫以为雍睦之应,作诗美之。公为人负气敢言,人有善,称不绝口,有/过,面折之不讳;有仕而被诬者,力为辩理;去官者馆之而资其归。其所为仗义事,皆历历/可数。然其心未尝责报,不沽恩,不咎背已,此其识量抑又有过人者也。其所刊校有回回/历、台历、百中经诸书行世。公自戊戌感风疾,至壬寅九月三日属纩,凡屏居不事事者阅/五寒暑,而于弟者,未尝忘欢,于子未尝失教,吁!亦贤矣。初娶同邑盤嶴乐氏,赠孺人;继娶金/台刘氏,封孺人。三子,翱、翔、云翔,侧室陈氏出。五女,长适南京刑部尚书江浦张公子纺,今/为应天府学生;次适盛奎子昌;次许聘大理寺副戴君子愈;次受常春子绅聘;次尚幼。珙/卜以卒后十月二十五日,葬江宁县新亭乡艾家原。遂奉刑部主事伊君德载所为事状,介/予同年友扬州都运欧公宗德来请铭,予素与公交,嘉珙之能弟,而又重欧公之笃友谊也。/故不辞,为墓 铭曰,/日官居卿代天工,巫咸甘石世所宗。象占景测谁精通,寥寥千载兹惟公。出参戎律入献/忠,匪从授时成岁功。灵台有历垂无躬,公名与之为始终。
东吴朱铧勒石
三、结语
(一)墓葬年代与营建过程
本次清理的贝氏家族墓共计14座。主墓贝琳夫妇墓(M31、M32)均出土有相关纪年材料。M32(贝琳墓)出土墓志记载贝琳卒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M31紧邻M32北侧,出土了银簪等随葬品,结合墓葬位置及出土物,M31应是贝琳妻之墓,该墓出土了“正德壬申”金币,据此判断,其年代为正德七年(1512年)。其余12座家族墓整齐排列于主墓西侧,部分墓葬出土有少量遗物。其中,紧邻贝琳夫妇墓的M2、M20均出土“万历通宝”,西侧家族墓的年代均当不早于万历时期。
据以上墓葬年代判断,再结合墓葬排列方式,此家族墓地的营建应经历了先后两阶段。贝琳夫妇墓营建时间较早,于正德年间完成入葬。其墓坑选址也相对特殊,位于南北向的一条早期形成的黑土带[1]范围内,四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余12座家族墓位于主墓西侧,大部分位于黑土带范围以外,以中部一平坦空地为中心,于南北两侧整齐排列。其营建时间较晚,年代不早于万历时期,与主墓年代相差至少60年。《地理新书校理》卷十四《阡陌顷亩》条“三灵七分擘四十九穴图”:“凡葬,不立三灵七分四十九穴,名曰暗葬,凶,亡魂不宁……正中一分名曰地心明堂,祭神之所。”[2]又,《地理新书校理》卷十四《祭坛位置》条“明堂祭坛法”:“葬必置明堂,祭后土诸神,则亡魂安。”[3]贝琳夫妇墓西侧,这 12 座墓所围成的这块空地,与《地理新书校理》中所述十分符合,故推测为明堂,是坟丘前举行墓祭的场所。
(二)墓主身份与家族世系
主墓M32出土一合石质墓志,清楚记载墓主身份及主要经历。墓主贝琳是明代著名天文学家,曾任明代南京钦天监副,其著作《回回历》(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时改书名为《七政推步》)为研究伊斯兰历法的重要资料。贝琳生年不详,卒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葬于江宁艾家原。清代路鸿休《帝里明代人文略》载:“……琳,字宗器,号曰竹溪拙叟。生宣德己酉……”[4],可知贝琳生于宣德四年(1429年)。由此可知,贝琳去世时,享年53岁。
贝琳墓中出土了一组铜组佩。组佩是明代流行的饰物。《大明会典》卷六十一冠服二“文武官冠服”条:“珮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5]。《明史·舆服志》对文武官朝服亦有清楚记载,规定文武四品官员以下“佩药玉”[6]。墓主贝琳为钦天监副,官品在五品以下,其墓中出土佩饰以蓝色料珠串联,与文献所载相符。
有关贝氏族人概况,以清人路鸿休所撰《帝里明代人文略》[7](以下简称“《帝》”)中贝氏一族的材料最为详尽。路鸿休曾为康熙年间续修的贝氏家谱作序,《帝》一书中对于贝氏一族的材料便来源于此次续修的家谱。该书中对贝琳及贝氏子孙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包括祖可恒、父永阜、贝琳、琳弟贝珙及后世子孙贝仁、贝豳、贝尚质、贝元祯、贝守仕等人的传记。此书所载谱系虽有缺失,但仍是目前对于贝氏家族最原始、最全面的记录。此外,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有贝琳弟贝珙[8]、贝珙妻毛孺人[9]的墓志,为了解贝琳子孙两代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参照《帝》一书所载及贝琳、贝珙夫妇墓志等材料,可将贝氏家族世系表大致还原(图一三)。
(三)相关推断
路鸿休在《帝》一书中,将贝琳一族归为金陵天文世家时称:“监副琳以天文起家,之后,次鹏、次岳、次仁、次豳、次尚质、次元祯,凡历七代而以天文家与国同终。”[10]但据贝珙夫妇墓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贝珙墓志中明确记载,贝珙“弃儒而就商”,其长子贝鹏“干蠱,克世其业”,子承父业;其孙贝山、贝岳、贝岱、贝嵓[11]“皆治《周易》”。由此可见,贝琳后的贝鹏、贝岳两代人并未从事天文事业。《帝》一书将此父子加入序列,或许只是为了保证天文世家谱系的完整。据现有资料来看,贝琳后人中,能确定习天文者始于贝仁(1495-1564年),之后有其子孙贝豳(1522-1604年)、贝尚质(1556-1615年)。由于谱系缺失等原因,路鸿休在为续修的贝氏家谱作序时,发现贝琳子孙两代信息缺失,无法确定贝仁与先人贝琳之间的世系关系,只能通过年龄大致推测贝仁为贝琳的曾孙辈。
对照考古发掘情况,贝琳夫妇墓西侧的12座家族墓,年代不早于万历时期,与贝琳夫妇入葬时间间隔至少六十年。根据时间判断,这批墓的主人不太可能是贝琳的子孙辈,可能是入葬于万历年间或更晚的贝氏后人。贝琳去世后的百余年间,贝氏子孙以贝琳墓为中心,营建了一处排列有序的家族墓地。值得一提的是,与营建家族墓年代相当的万历年间,贝氏子孙贝元祯(1582-1652年)请金陵大家焦竑为其曾祖贝仁、祖父贝豳、父亲贝尚质作传,介绍三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此举或许是为树立贝氏“家本天文”的形象。由此看来,营建家族墓地与请焦竑立传,这两件事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都可视为是一种认祖归宗的行为,希望以天文来凝聚家族合力。因此推测,家族墓地营建和为先人立传,属同一批贝氏后人规划完成的两件家族大事。
(四)发掘意义
本次发掘的贝琳墓,墓葬平面外圆内方,形制奇特。墓葬建在一黑土带内,葬地选择也显示出与众不同。墓主贝琳身份明确,曾任南京钦天监副,是一位天文学家。古代科技史研究中,不乏对贝琳《七政推步》等天文历法方面的著述,然而并未对贝琳其人展开充分研究。本次发现的墓志内详实,与历史文献互相补充,对于研究贝琳及家族史具有重大意义。贝琳家族墓整体布局相完整,历经百年最终形成,为研究明代家族墓南京明代地方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此外,琳墓出土一组较为完整的铜组佩,为研究明代服制度增添了实物材料。
[1]M31、M32在建造时,打破了南北向的一条带状黑土,该黑土带延伸至M31东侧,西侧延伸至高压电线杆处。现存长28、宽6.5、厚0.3米。解剖该黑土带发现,其中出土早期陶片、六朝砖块,未见其他遗物,该黑土层形成年代应远早于贝琳墓营建时期。黑土层底部呈自然堆积状,不见人为修整痕迹,应属自然形成。
[2]北宋·王洙等编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7-418页。
[3]同[2],第418—419页。
[4]清·路鸿休辑:《帝里明代人文略》卷十一《宗系可考》,江庆柏《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四册,广陵书社2011年,第155页。
[5]《大明会典》卷六十一《文武官冠服》,明万历刊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第1054页。
[6]《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4-1635页。
[7]同[4],第149-184页。
[8]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南京卷》上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9]同[8],第228页。
[10]同[4],第182页。
[11]有关贝珙孙辈的记载,贝珙与其妻墓志有差异。贝珙墓志中孙辈为“贝山、贝岳、贝岱、贝嵓”,而贝珙妻墓志中所载孙辈为“贝山、贝岳、贝岱、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