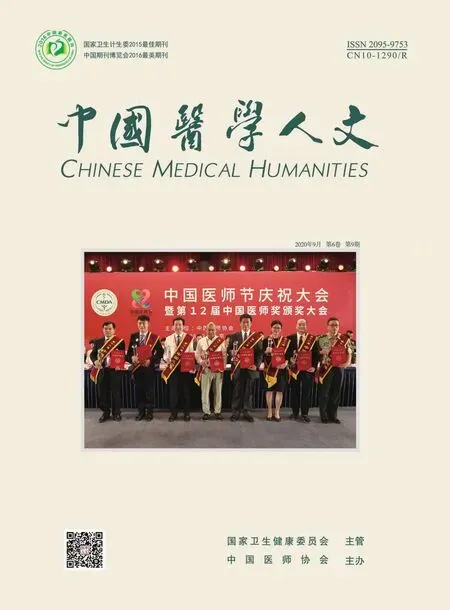谁愿放手
文/刘姿君 陈安乔 马 萍
那天下午,我们在社工部办公室里忙碌着,键盘声和电话声夹杂在一起。忽然听到一阵时轻时重的敲门声,我便走上前把门打开。
门外站着的是两个男青年,他们背着行李,低垂着头,看起来有点疲惫。见我开门,穿黑色T恤的男青年说:“你好,我们是医生推荐过来的,说是有基金可以申请给小孩治病。”他们的神情有些犹豫,好像对自己此时做的事情充满怀疑。
我请他们进来,让他们先把行李卸下,坐在沙发上喝口水休息一会,再拿起笔记本记录他们的述说。穿黑色T恤的男青年姓高,是哥哥,同行的是他弟弟,都是广东普宁人。兄弟俩这次来广州是为了带哥哥高先生出生不久的女儿治病。高先生二十多岁,在服装厂打工,妻子在家带孩子。患病的女儿是高先生的第三个孩子,养孩子不容易,全家人就靠高先生一个人赚钱养活。
“上个星期在家里给她喂奶,她吃不进去,全吐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的身体变成紫黑色的,我和她妈妈都吓死了……”高先生有点着急,说话有些结巴。“我们当晚把小孩送到普宁的医院,在ICU住了10天院,但是一直没好,那里的医生说他们做不了手术,要来广州才行。”
家庭经济本来已经有些困难,小女儿还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畸形,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尽快判断高先生的女儿是否符合基金会申请的条件,我让他们把疾病诊断证明拿出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房间隔缺损、心包积液、呼吸衰竭……”复杂的诊断占据近半张纸的位置,特别显眼。孩子刚出生不久,又是术前,诊断也在爱佑基金会资助的范围,初步判断可以申请救助,我开始联系基金会。高先生对我说了声:“拜托了”,目光流露出无助和期待。面前这位只比我大两岁的高先生,我不知道能帮他多少,但我觉得作为社工,要保持专业,要尽力提供帮助。
按照安排,第二天上午九点,医生要跟高先生谈话,向他解释检查结果和手术方案,并告知所需费用。高先生很紧张,一是不知道女儿的病情到什么地步,二是怕自己没有能力支付手术治疗费。“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去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吧。”我感觉高先生面对女儿的病情一时难以接受,思绪也有些混乱,我希望能陪伴他们一起倾听医生的方案和建议,在他们没能听清楚或下不了决定时给他们一些思路。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心外小儿科门口。与我一同前往的除了高先生,还有他的弟弟、小姨。一家人很焦急,小姨不停安慰高先生,让他不要害怕。科室门口人很多,走动有点困难,他们都是等着医生叫名字进去谈话的家属。空气慢慢变得闷热混浊,大家的汗水也被蒸发出来,家属们越发有些待不住了。等待间,我感觉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回过头看见高先生给我递了一瓶水,“刘社工辛苦了,这么早来都没有喝一口水,拿着吧。”比起解渴,等到医生是更重要的事情,我的脑海里还在思索着等会儿要着重留意哪些内容,如果高先生承受不了医生说的话我要如何应对等等。我将水递回给他,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广州看医生特别折腾,手头资金也已经很拮据。
“高XX家属!”将近十点钟,护士终于呼唤我们,可以跟医生面谈了。当时高先生正坐在楼道里,眉头紧锁似乎在思考什么,我过去拍拍他提醒应该进病区了,高先生急切又慌乱。我们挤过人群,从半开的门进入科室,看见医生时,他正埋头翻阅病历,桌上摆放着一个立体的心脏模型。“怎么这么多人进来?一个家属就够了。”平时谈方案一般是一两个家属,但这一次来了四个人,“我是医务社工,这次跟高先生一起过来听手术方案是想给他多一些支持,后面我们也会链接一些资源给他。”医生理解我们的来由,就没再多说什么,很快进入术前谈话。“这个孩子的心脏病比其他人复杂很多,手术难度高,风险很大,这次手术主要是将……”听到这里,高先生已经紧紧抿住嘴唇,手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我边用笔记录医生所说,边轻轻拍高先生的背表示陪伴和安慰。“手术的结果分三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手术成功,看后续孩子的恢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孩子恢复不好,可能面临第二次手术;最坏的情况是孩子下不了手术台……你们至少要准备十万,这个手术才能做,后面预估还需要多少,现在还没办法确定,要不要做这个手术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小姨已经趴在桌上掩面哭泣,高先生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我将纸巾分别递给他们,然后问医生:“多久要给您答复?”医生说:“明天早上八点半前来办公室给我答复,这个孩子不能拖,要尽快决定。”
我扶着小姨,我们缓缓走出办公室,好像肩膀扛了一块巨石一样。我让他们回到社工部,坐下来平静心情,让高先生把孩子的情况转告给妻子,大家一起商量。
傍晚,小姨告诉我他们还没决定好,风险又高,如果凑不齐钱可能不做手术了。作为社工,我只能帮助他们分析两个选择带来的后果,但不能帮他们做决定。这个夜晚对高先生一家来说一定是纠结、煎熬、不能入睡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决定要给孩子做手术,不管要花多少钱,结果怎么样,都可以承担。高先生的语气很坚定。我尊重他的选择,也为他感到高兴。
手术到来的那天清晨,高先生把女儿送到手术室门口,医生表示一定会尽力。然后高先生到社工部找我,我陪他们一起到爱佑基金会递交申请材料,三天后审核结果出来了,高先生的女儿获得了5万元的资助。手术也非常成功,医生告诉我们过程顺利,孩子身体情况稳定,已经转入新生儿科,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一个月过去了,高先生的女儿身体逐渐恢复,他们可以办理出院了。我陪同高先生去科室找医生开出院的相关证明,大家心里的一块大石终于放了下来。这段时间,我和高先生以及他的家人们相互关心、相互鼓励,高先生一家挺过了最难的时刻。
高先生和家人收拾行李回家前,特意买了些水果送到科室和社工部,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助他们我也十分感恩,在这期间我也获得了成长,医护人员对能治疗好小宝宝也感到很高兴。
临下班前,高先生一家要坐车回家了,回家前又特意把女儿抱到我们办公室,分享喜悦,合影留念。孩子皮肤幼嫩白皙,正熟睡着,高先生脸上的愁容早已褪去,洋溢着幸福。“你看,她长得多好!你抱抱她。”小姨把孩子抱到我面前,但我不太会抱孩子,没敢接手。“宝贝,这是姐姐,她一直在帮你的,谢谢姐姐!”此刻,办公室这一角透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灿烂,我们都特别欣慰。
高先生说,来广州就医很不容易,虽然有家人陪伴,但过程也很辛苦,在省医遇见社工,在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感受到以往就医经历中从来没有过的安心。
后记
高先生作为患者家属,面对疾病,心里不免紧张焦虑。异地就医,人生地不熟,各种不确定性更容易让人毫无安全感。加上家庭经济困难,面对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这更是他难以承受之重。那时候的他,不仅急需医疗资源救助,更需要精神支持和就医辅导。医院工作繁忙而紧张,医护人员很难面面俱到,这时候,医务社工就是患者家属可以倾诉和依靠的人,是与他们并肩对抗困难的人,是让他们感到温暖、给予他们力量的人。
帮助患者是医务社工应该做的,更是医务社工愿意做的,使他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也是社工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