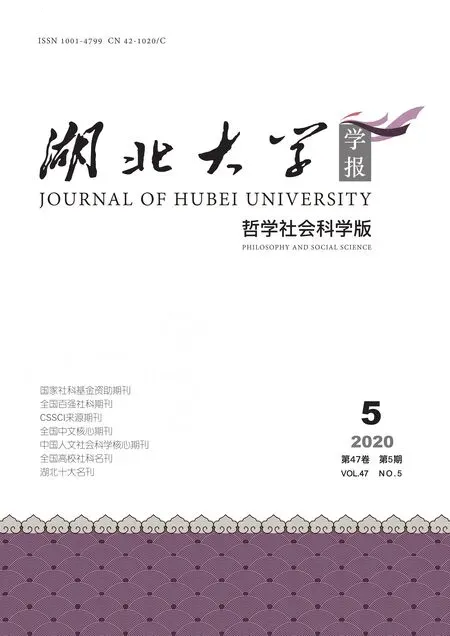王阳明六经“删述”说发微
——兼论文化生态的净化
王胜军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王阳明与徐爱讨论“文中子(王通)拟经”和“五经皆史”的对话,并非单纯指向经史之辨。这段对话出现于《徐爱录》的文末,有对前面关于“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探讨的进一步说明和申辩之意注在之前与徐爱的讨论中,王阳明认为理不在心外,只要心纯是天理,就自然能发乎到具体行为,如有诚孝之心即自会思量父母的“寒”、“热”,进而关注“温”、“凊”等外部经验知识,并将这种从心到物的自然流行总结为“知行合一”。并且,阳明发现徐爱之所以认识不到心即理,与朱子“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成说“之蔽久矣”有关。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5页。,并将这一探讨推及到社会领域中文化生态的净化注“文化生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将文化置于环境中去考察其生成、发展与变异。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145页。。这段对话,实际上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知识体系以及将经验知识奉为真理的逻辑进行批判。在北宋儒学从中衰到复兴之际,由于缺乏良好的礼仪环境和文化学术环境以及师友传承,自我体认天理成为重建儒学的重要方式,到南宋朱子由之建立起一个与传统经学时代不同的庞大精密的新知识体系,并被不断诠释和解说,当其被奉为真理时,又形成了对自我体认天理即良知自觉的一种反向压抑。朱子学以外在事物和经验世界为起点和依据,而王阳明的良知学却是建立在内心的先验基础之上。对王阳明而言,儒学经典并非与真理等同,而只能作为体认天理的产物,即作为在特定时间应对特定事件的历史记录而存在。面对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外求定理的逻辑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言说,王阳明认为应当如孔子删述六经一样,荡涤其中所谓的“异端”、“曲学”、“邪说”,优化良知发用环境、净化文化生态。因此,六经“删述”说实际上是王阳明良知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的补益性思考。
应该说,对王阳明“删述”意识进行关注极为重要,而进一步探讨诸问题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删述”说与良知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更为重要和必要注目前论及王阳明六经“删述”意识的研究主要有蒋国保、阎秀芝《王阳明经学思想散论》(《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和汪学群《王阳明心学与经学的互释》(《哲学动态》2020年第1期)。前者梳理了王阳明的经学观和解经方法,尤其重点解析了《五经臆说》;后者从经学即心学的学术史角度简略论及王阳明有关“删述”的诸观点及“删述”的社会文化意义。总体来看,两文尚未深入分析六经“删述”与王阳明良知学诸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亦未进一步将这种逻辑关系与文化生态净化关联论述。。 故本文再次考察王阳明与徐爱关于“文中子拟经”和“五经皆史”等对话,探求王阳明“删述”意识与良知学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分析这种内在逻辑关联对文化生态净化的意义。
一、“焚书”与“删述”:私意与良知对文化生态的不同导向
长期以来,在儒家的历史叙事中,秦始皇都是以“暴君”形象出现的,其罪状之一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直接造成了“六艺从此缺焉”的儒家经典传承的断裂,以及后续今、古文等许多争议[注]尽管对此也不乏有学者提出异议,但是作为一场“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参见王子今:《“焚书坑儒”再议》,《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第11版)。而就王阳明与徐爱的问答来看,也是认定“焚书”对传统经典断裂负有主要责任。。王阳明在《传习录》与徐爱讨论“文中子拟经”时对“始皇焚书”有一个惊人的评价: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
王阳明在这里将秦始皇焚书与孔子删述六经对举,自然是出于警策,旨在为“删述”打上着重号,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然而所谓“暗合”,则又当是指二者在文化生态建构和净化潜在意指上的一致性。
纵观先秦诸子的言说,建构和净化文化生态向来是一个重要方向,诸如孔子“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墨子“尚同”(《墨子·尚同》)、孟子“息邪说、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庄子“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儒效》)、韩非“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韩非子·忠孝》)等等,只是内容所指和达成方式不同而已。
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将结束学术纷争、建立文化秩序完全寄托于王权政治的暴力介入,导致这场绵延二百余年的大论战以“焚书”来结局[注]章太炎认为秦始皇焚书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参见《秦献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3页),这对传统说法的冲击很大,但是有学者认为其证据《韩非子·和氏》一篇为伪(参见姚能海、张鸿雁:《商鞅“燔诗书”辩》,《光明日报》1987年2月4日,第3版),不排除《韩非子》为文化专制寻找依据而捏造寓言的可能。。李斯主张焚书的理由是“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其实就是在担扰文化秩序的混乱会危及政权稳定。从李斯所主张的焚书措施来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注]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第六》,《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仍然保留有博士官所职之《诗》《书》,并非是简单的反智主义,而是要消除异己的学说,以吏为师,掌握文化学术领域的话语权。
孔子删述六经与秦始皇焚书相比,表现为更为纯粹的文化行为。所谓“删述”,指对古代文献进行删汰、编次(述而不作)。关于孔子是否曾经删述六经,质疑者向来亦不为少,如郑众等汉代古文学者,而确信孔子有删述行为的汉代今文学者更倾向于其中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比如《鲁诗》学者说孔子编排了《诗经》的篇次,实际上是为了在《诗经》中挖掘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内涵[注]赵茂林:《孔子“删诗”说的来源与产生背景》,《孔子研究》2018年第5期。。由此可见,孔子删述六经本质上属于文化行为,亦带有社会教化和文化生态净化的潜在意指。秦火之后,由于文献凋零,汉儒将孔子“删述”更多理解为经典的“编次”而并不强调“删汰”,在此基础上求助于王权以禁绝百家并进之道,进而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有着比较强烈的政治色彩。
降及唐宋,在反对两汉经学、重视自我体认的理学语境中,对“删述”的关注激进到“焚书”的程度。韩愈在《原道》这篇拉开新儒学重建序幕的文章中,就指出要对佛、老等所谓的异端之学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措施。之后,许衡、吴海、陈献章都有类似的“焚书”之说[注]前贤对此已有关注,罗立刚强调许衡的焚书说基于他的陆学倾向(参见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庞光华、周飙将陈献章的焚书主张归结为儒学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合作(参见庞光华、周飙:《从学术史论陈白沙的焚书说》,《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日本井上进认为许衡、吴海的焚书说是宋代以降理学讲求修身、反对知识主义的结果(参见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并且,朱子等还认为“异端”对文化生态的污染将导致文化本身的厄运,在他看来,“始皇焚书”式的权力干预学术自由乃是时人“好为异论”的结果,如其所论:“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6页。郝经则推而广之:
仲尼氏没,本散而末分,源远而流别。文晦于理而文于辞,作之者工于辞而悖于理。故庄、列以之文虚无,仪、秦以之文狙诈,申、韩以之文惨黩,屈、宋以之文怨怼,卒致吕政焚书之厄。[注]郝经:《文说送孟驾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秦雪清点校、张儒审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
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王阳明“繁文乱天下”说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王阳明的“删述”说一定程度继承了前代关于知识言说会影响人心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秩序的传统观念。对王阳明而言,良知并非杂乱无章或纵情恣意,它本身就是天理,有天叙天秩,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注]王守仁:《博约说》,《王阳明全集》,第266页。。因此,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描绘的理想国就是“人无异见,家无异习”,而学术纷争和文化秩序的混乱,则被他比喻为“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6页。。所以王阳明对举“焚书”与“删述”如前人一样,认为儒家理想国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生态的条理化、有序化,而非任由各种言说滋生传播。
王阳明的“删述”说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是在良知学的范畴之中基于“良知”与“私意”的对立而展开的。在阳明心学中,心之所发是意,意之本体是知,意之所在是物,因此,只要是意之所在,如事亲、治民、读书、听讼等都可以被视作一物[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47页。,意决定着事物的秩序[注]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扩而言之,意形成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就决定着伦理、政治、教育、法律等人类社会的运行内容。当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其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未必合于天理。意要由明觉的良知来监督、判断和引导,不循于天理即为私意,私意状态就不是本体之知,即不是对真理的终极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良知的监督、判断和引导作用反映在个人和内心就是消除杂念、人欲,而当杂念、人欲即私意社会化并形成知识体系之后,良知仍然有必要去甄别和消除其有害部分,从而形成对语言文字的“删述”,进而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才有可能进入善治之境。
这样,王阳明的“删述”说在良知学的视域中就表现出与从秦始皇以降到朱子、郝经等人的鲜明不同。首先,就目的而言,私意不合天理,是欲望的投射,如“始皇焚书”即由私意而发,是为万世一系的皇权统治,建立的是一套由荀子外铄而有的“人为秩序”[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将善治的根本放到外在制度的精密设计和严格推行上。王阳明则认为“孔子删述”是“志在明道”,道不是一家、一人之私,乃是天下之公,是与有意为之相对的“廓然大公”的一种工夫境界,他指出“公”与“意”的关系:“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30页。可以看到,王阳明最终是要建构起人的内在心灵秩序,由此而主张删述,既与秦始皇以私意追求权力控制文化的模式不同,亦与朱子以“思索安排”去树立外部知识权威体系的方向相反[注]阳明多次批评“思索安排”,认为这是“私智”所致,以之对比说明良知发用流行的自然、浑成,如其诗“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王守仁:《次谦之韵》,《王阳明全集》,第785页)。。
其次,就手段和方法而言,秦始皇使用王权暴力来焚书坑儒,对儒家经典并无敬畏,而在王阳明看来,更根本的还在于“私意”从学术角度会导致儒家经典知识体系的变异,或者将“先王之近似者”作为“猎取声利”的工具,或者希高慕外,将之变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纷纷籍籍,群起确立自己的学术权威以相争竞[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5页。,朱子向外求取知识的逻辑最可能导致这种危险。王阳明论“删述”显然不是在知识学中打转,而是要回到本心良知中去[注]只有陈献章《道学传序》中对记诵词章之学与心性之学的区别与王阳明较为接近(参见陈献章:《陈献章集(上)》,孙海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不过陈献章没有完全抛弃向外求取知识的思路(参见黄明同:《陈献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王阳明从良知学入手,旨在对颠倒良知与知识关系、以追求外在知识为依归的著述之学及其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诉诸伦理实践中反己以求内心之理、师友夹持和“知行合一”的良知自觉。
再次,就性质而言,“始皇焚书”是政治意义上的,秦始皇所关心的“异论”是各种言说与他的政令相合与否,是否有反抗其统治的意图。朱子等人关注的“异论”有强烈的知识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考察各种言说是否合于经典文义,从“自我体认”这一点上朱子大大有别于汉儒的注疏传统,如对《大学》的整理就是新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它既经建构起来,自身又成为一个不可质疑的权威,遂导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社会文化生态。王阳明的良知学则质疑经典文字与真理的关系,徐爱《传习录序》就集中探讨这一问题,在王阳明看来,真理其实只是“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注]徐爱:《传习录序》,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567页。,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神圣言说,只有良知才是主宰,而朱子到经典文本中去格物,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5页。,即亦未尝不带有“私意”。
最后,就前提来看,良知的引导是以内心的天理为出发点,私意看似由自我而来,其实只是欲望对外在事物如色、名、利的迎合和追逐,良知本身内在有一套天理秩序,“删述”在良知的引导下合于儒家的道德价值标准,可以不断接近儒家的理想国之门。私意却是知行本体的隔断者[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4页。,要“删述”经典自然无条理可言。所以,“删述”的出发点不从良知来,善治就无由达成,“删述”亦将失去其意义。
二、“习染”与“剥落”:良知视角下“著述”与“删述”的关系
王阳明对举“始皇焚书”与“孔子删述”,否定了朱子所批判的隋儒王通的“拟经之失”,并指出“天下所以不治”、不能“敦本尚实、反朴还淳”等等,从社会文化到人性的败坏,“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从王阳明与徐爱的对话来看,所谓“著述”就是指解经的注疏式作品[注]由徐爱“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可知“著述”所指,乃是揣摩前人文字的解经之作,包括汉儒尤其是朱子的解经之作,与现代意义的著述不尽相同,反而“拟经”是基于自己心得的创作,如仿《论语》而成的《中说》即是。,即从六经语言文字中去寻求天理的一种认知、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以“著述”为载体的言说体系和文化环境由于外逐而偏离了内在心体,既不能“明道”,又会遮蔽人心,激发人欲。这样,只有揭开“著述”建构的知识权威的云翳,良知才能如白日般放射光芒,“删述”因之成为一种必要。
至少从汉代起,儒学中的知识主义传统就一直占据主流,宋代理学兴起,既是迎接佛老心性建构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经学即“俗儒记诵词章之习”的一个反动。宋代以来,学者们不仅意图建构心性形态的儒学,又努力兼容原有的知识主义传统。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一般意义的知识被界定为见闻之知,是“耳目有受”的经验性知识,是人心即非本体之心的知觉活动;还有另一种德性之知,是“大其心”、“尽心”的穷神知化,是道心即本体之心的明觉活动。虽然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自张载就曾加以区分,然而,这两种“知”不免存在着鸿沟。朱子完成了二者的统一,即将见闻之知作为德性之知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开辟了经由格物理来明本心的格物致知之路,后来王阳明格竹子之理的问题实际也由于此[注]向世陵:《闻见与德性——朱子、阳明“知”论辨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说“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对比《朱子语类》中“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工夫到,然后脱然贯通”[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519页。一句,可以清晰看到见闻之知就是对具体事物之理的揭示,“具体是万,普遍是一,对一的把握必须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认识逐渐积累来实现”[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对朱子而言,所谓“格物”主要在圣贤由其经验知识形成的语言文字之中,六经就是这种经验知识的最高结晶和准衡,并由之衍生出以“著述”为载体的诠释体系。
王阳明却认为良知之外别无知识,任何见闻之知即从外在事物中体认出来的“天理”其实都只是对真理的有限认识,都不免有偏见[注]关于王阳明“名言”对“道”的遮蔽可参见杨国荣的论述:“在经验知识的领域,名言所达的,常常是对象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及于此往往蔽于彼。”(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18页),即便六经也不过是得鱼之筌、醪尽之糟粕[注]王守仁:《五经臆说序》,《王阳明全集》,第876页。,只是特定时代的言说,况且古人更是难以真正揭示出来。当陆澄问“著述”是否有乱正学时,王阳明回答说:
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1-12页。
对阳明而言,心即理,外在事物无定理,见闻之知的起点和依据不是本心,而是外在的经验性知识,因此见闻之知就不是对世界的终极认知,六经等经典就是这样一种间接性的经验知识。当后人在揣摩圣贤经典留下的非终极认知的语言文字时,可能还有私意杂入其中,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将其奉为真理自是偏见。
王阳明不仅断然否定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二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而且认为由经验知识形成的意见(偏见)还可能会对良知造成遮蔽(对其明觉而言)的消极影响。早在龙场,王阳明就发现“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只患闻见不多。良知闻见益多,覆蔽益重。反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注]王守仁:《传习录拾遗五十一条》,《王阳明全集》,第1172页。。因为抛开对内心的省察而去热烈追求见闻之知,只会诱发人的私欲,“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1页。,而心被私欲遮隔之后,知就已失去其本体[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4页。,从而形成意见(偏见)。
由经验性知识构成的“著述”式的知识言说体系,没有良知起用,就会夹杂着偏见和私意,成为笼罩在个人本心上空的云翳,并广泛波及教育、学术、文化、风俗等方面,以文本和教条崇拜为特征的文化生态形成“习染”。朱子虽不否认“人欲之蔽”[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习染),却认为恶的品质具有先天根据,乃是本善之性堕入到气质之中,被薰染得不好了[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432页。,气禀本身有善恶(正气、戾气),还是运势甚至寿、夭的依据[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80页。,由于其乃先天禀受,极难改变,因此,在朱子看来,孟子将恶仅归诸后天“陷溺”是论性不论气,不算完备[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465-1466页。。王阳明虽不否认禀气清明与物欲牵蔽之间有关,即气质清明便可以少物欲之牵蔽[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69页。,却并不倾向于认为气质本身有善、恶。在他看来,气质清浊、厚薄、强弱只是在应对外物蔽染时会起到一定作用而已,气质之偏生而有之,并不影响成圣成贤(圣贤彼此气质亦各有不同),相反还是成圣成贤的重要依托,如王阳明所谓:
人生初时,善原是同的。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习于恶则为刚恶;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习于恶则为柔恶,便日相远了。[注]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23页。
所以,王阳明才对弟子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注]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04页。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更多将气禀看作是才气大小,如他的“精金喻”所论。
在王阳明看来,“习染”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性的,故而良知之达成亦绝非个人之事,必须还要从社会教化中着手整顿束缚个人的不良文化学术环境,以集体的方式获得解放,如他所论“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只有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个我之病狂才能“脱然以愈”[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81页。。
对外逐见闻之知而造成的遮蔽和习染,王阳明提出与象山类似的“剥落”功夫,即剥落经验知识对心本体的遮蔽,他大声疾呼:“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8页。他还用必须伐去大树才能种植嘉谷作比喻加以说明[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1页。。在王阳明看来,只有批判“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的“义外”逻辑,不再将外物作为思考的起点,才能廓清由经验知识形成的私欲牵蔽,即“习染”,由外逐转向内省,从而为良知发用创造更好的环境。
“剥落”工夫是就个人而言,对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就是“删述”,因为“习染”已然形成一种以“著述”为载体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并以正统之名在传播。“删述”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重整已然变异的儒学价值世界。在王阳明看来,朱子本人就是“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8页。。朱子从六经的语言文字中去寻求天理的认知、解释世界的方式,建构出一套以“著述”为形式与载体的话语权威和认知逻辑,即“著述”之学在本质上就是以见闻之知为本,而以良知为末。经典只是得鱼之筌、醪尽之糟粕,与良知的本末次序不能颠倒,良知是规矩尺度,经典及其知识文本是方圆[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0页。。在相反的逻辑之下,以“著述”来求圣学和真理,将沦之为霸术,原因就在于知识偏见会遮蔽良知,没有良知自觉,就不会有天理呈现,自然是霸术流行。千百年来,即便是有志之士亦卒无以改,原因在于“风气习染之所成,学术教化之所积”[注]王守仁:《重修浙江贡院记》,《王阳明全集》,第903页。,“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注]王守仁:《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王阳明全集》,第958页。,现有的儒学知识体系及其建构逻辑对学者而言既是遮蔽又是束缚,加之常人气质之软弱易塑,很难冲破既有的知识罗网,必须借助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来祛魅或解蔽。
王阳明虽讲“习染”,却与荀子将外在环境作为人性的决定因素是绝不相同的,“习染”只是如浮云蔽日而已,蔽既易,解蔽亦不难,“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注]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1页。所以,良知虽然从百死千难中来,但是相对于朱子要“即凡天下之物”的知识学路径,也是极简易之学。解蔽的动力依然来自于每个人的良知自觉,而非外铄的知识或秩序,为良知解蔽就不可能以知识灌输、法令严禁的方式来达成,相反,只有“剥落”由人欲、私意而成的知识性偏见才会为良知自觉营造宽松的文化生态。因此,具有“有减无增”的文化性质的“删述”是一条可行之路,它将不断地剥落个人心灵可能要承受的千百年来学术和文化的重负,终使良知轻盈起舞。良知既为主宰,其明觉之力发为监督、判断和引导,就可以酬酢万变、从容自在地运转见闻之知,即朱子学奉为真理的经验知识,达成其发用流行。
三、“示法”与“杜奸”:“拟经”式“删述”的文化生态净化原则
“删述”就是由破除“习染”这一逻辑思路而来,要以良知来引导经验知识,而不是从经验知识包括经典文字中去认取天理。王阳明以六经为史旨在说明“明善恶,示训戒”的导向,因此,文献典籍编纂要遵循“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0页。的原则[注]与汉儒不尽相同,王阳明认为《春秋》义例并非出于孔子,孔子只是就“鲁史旧文”删繁就简、述而不作(笔其旧、削其繁),不是增改原有文本,而是对原文进行选取和削减,“存迹示法”、“削事杜奸”就是其“删述”的原则。,突出良知对经验知识的引导以及预防经验知识对良知的遮蔽,扩之到社会中,这也就是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生态净化原则。
“拟经”是王阳明“删述”的基本方式,即通过文献简择、编次来突出圣人之学的价值和原则以“存迹示法”,与“焚书”的消极意识相反,它具有积极的建构倾向,带有教化色彩。由朱子的评论来看,王通“拟经”的内容是“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以《七制》《命》《议》之属以续《书》”、“取曹、刘、沈、谢等人诗作以续《诗》”[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256页。等,《中说》则以王通与弟子问答为主体以续《论语》。“著述”是对原有文献的解释,是增不是减,而“拟经”是从芜杂的文献中选取部分精华,即有减无增。朱子曾嘲讽王通的“拟经”“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佐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256页。,而王阳明高度肯定王通,并阐述“拟经”的意义: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
由“断不能去”可以看出,王阳明也不认为“始皇焚书”式的暴力手段会有效果,而是主张通过文献整理的方式,表彰正学以改造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正进邪退的文化生态结构,将六经系统、拟六经系统之外的文献及其意识形态渐次淘汰出学术界和历史舞台。在王阳明看来,“孔子删述”就是一个文化生态净化的过程,比如孔子赞《易》之后“纷纷之说尽废”,删《诗》之后“一切淫哇逸荡之词”始废[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
拟六经系统类文献与六经一样都具有“史”的特征,都是时人由良知而发形成的具有时效性的历史产物,是为了“明道”,而非道之化身。朱子批评“拟经”之作无法与六经相比[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256页。,王阳明却认为“拟经”是历史上由良知明觉产生的实践性文献,可以达到“因时致治”的目的(反之,王阳明认为《三坟》虽有意义却已失去其时效性,故孔子删之)[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9页。,它胜于后儒对六经加以解释的、从知识文本解读出来的散发着复古味道的言说,是以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纵论明堂、辟雍、封禅等典制都非达成致治之本[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2-53页。。究其根本,真理的认知不是从外在经验知识构成的儒学经典而来,而是从生命体认和实践应对而来,所以,王阳明讲“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4页。,即真知来自于良知自觉。章学诚论“六经皆史”,批判“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李春伶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页。,将典籍转向事物人伦日用,实堪为一注脚;不过,对道的认知从根本上还是要依托良知的明觉,余者皆为外在,如事父之理不在父亲身上而在自己心中[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页。。因此,六经及拟六经文献更多具有功能性意义而非终极真理意义,只是对特定时代文化的总结、批判、引导和启示。王阳明并不认同汉儒断简残篇式的复古以及朱子学对遥远的古代文本进行支离破碎的体认,而是意图以良知不断建构起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这样,从汉儒的注疏之学到朱子的注经方式在王阳明“五经皆史”的论断下都走下终极真理的神坛,而冉冉升起的则是不假外求的良知主宰。由于王阳明的“删述”说强调经典文献的时效性,所以拟六经系统就既有新经典的形成,亦有旧经典的退出或者说旧经典真理指示意义的消退,即又表现为新陈代谢的特征。
排除在六经及拟六经系统之外并将渐次淘汰的言说,即所谓解经的“著述”,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是展示了阴谋诡计等犯罪细节和过程,作为恶的“习染”会遮蔽良知、对社会教化产生消极影响。对此,徐爱质疑说“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页。。实际上,徐爱的思路仍是程朱式的,即认为定理在外在事物中。对此,王阳明回答说:
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8-9页。
在王阳明看来,《春秋》原文中弑君、伐国中的“弑”、“伐”已是定罪,已然可以警醒人心、生发良知(存戒),就应该削减“纵人欲、灭天理”之事以防止在叙事过程中将恶表现出来形成遮蔽,因为义理在心而非在外在之事。可以看出,王阳明主张汉儒解《春秋》的义例褒贬说,不同之处是从内在良知而非外在行为出发,而朱子批判说“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注]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147页。曾亦的《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比较详细论及此问题。实际上,朱子早已发《春秋》为史之论,只是试图要从史实之中去寻找义理,这与阳明“五经皆史”说名同实异。朱子曾对弟子讲“《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89页。,所以,尽管“郑伯克段于鄢”是描写兄弟相残之事,朱子却说“兄弟之事”、“人伦尽在”[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160页。,未曾关注阴谋诡计对读者的消极影响,亦即外物对私欲诱发的可能。而《左传》之类在王阳明看来,却是“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9页。。王阳明还由此批判传世《诗经》文本,在他看来,淫溢之词既无法在郊庙、乡党等严肃的公共场合进行演奏,也不能“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所以现存郑、卫之诗等乃是由于可以迎合人的低级趣味,而在秦火之后被窜入以凑“三百”之数的,绝非旧本[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0页。。这与朱子虽然批判郑、卫之诗,却又认为孔子保留下来是为“惩创人之逸志”[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539页。(即使读者有所愧耻并引以为戒)之说有本质之别。
到此,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谓的“反经叛理”不仅仅是指解经的“著述”,甚至还包括传世六经自身的文本。传统上从汉儒到朱子都是围绕如何理解经典的字义、文义而来,由此形成了传播上千年之久的注疏之学,而王阳明显然有陆象山“六经注我”的独特建构意识和个我体认的特征。早在撰述《五经臆说》时,王阳明的“得鱼忘筌”说就已经质疑传统经典文本与真理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心之是非亦即良知才是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良知与经典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删述”之所以能明道,一方面是可以更加突出圣人之学的价值和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因人用药”教法的表现。正德七年(1512),储柴墟将所撰《刘生墓志》寄赠,王阳明认为志中所记刘父侧室事“有伤忠厚”,主张删去为佳,并指出“子于父过,谏而过激,不可以为几;称子之美,而发其父之阴私,不可以为训”[注]王守仁:《答储柴墟》,《王阳明全集》,第811页。。嘉靖六年(1527)即王阳明去世前一年,钱德洪请刻其《文录》,王阳明却认为“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注]钱德洪:《年谱三》,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304页。,而且还打算既著一书之后,将自己讲学的其他“零碎文字都烧了,免致累人”[注]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577页。。钱德洪后来回忆说,自己乐于面炙,从不笔之于书,后来看到传出的记录稿,觉得其生动性、亲切感比之面炙时“歉然常见不足”,这恰好可以印证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之教中的“减法”也许或胜于考索书册的“增法”。
当然,从“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来看,圣学之兴不可能不依托言说,与佛、老一味排斥言语文字不同,言语文字在良知发用中自有其意义。在王阳明生前,诸如古本《大学》、古本《中庸》以及《朱子晚年定论》、《象山文集》、《传习录》、《文录》等其实都已有刊布流传,尤其是他将古本《大学》、古本《中庸》等派人送到朱子讲学的大本营白鹿洞书院中,就有就正朱子之意。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是其良知学建立的文本依据,是其眼中的“正学”,程朱整理本《大学》就只能是所谓的“著述”了。由此来看,在王阳明良知学的起用之下,以古本《大学》等为代表,新一代的拟六经的文献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形成。这样,就以良知为动力中心形成了心学特有的文献生成模式。
四、余论
中晚明是一个知识繁荣、思想剧变的时代,据学者考察,在弘治、正德间,一批儒家眼中“混杂着异端邪说的书也堂而皇之地得以出版”,诸如《韩非子》、《管子》等等,甚至终宋之世三百余年都未被刊刻的《墨子》也在嘉靖中期面世[注]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46页。。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六经“删述”说未尝不无其现实关照。“删述”说就根本而论是要“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注]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0页。,因此,明代中后期肯定欲望的思想狂飙,至少不能说是王阳明讲学的初衷,相反,王阳明却用“病革临绝”[注]王守仁:《答储柴墟》,《王阳明全集》,第814页。来形容其生活的时代。实质上,王阳明是在忧心“纯粹之价值中立之知识论破坏了价值论之根基”[注]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匡钊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亦即语言文字并不是真理化身,而只是工具(见闻莫非良知之用),只有良知才可以手执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权杖。
对朱子等人而言,知识却非中立,而是具有价值论意义的。入清之后,考据学继承这一理念,知识文献主义兴起,以小学明大道,六经以及围绕其而形成的“著述”文字又占据了绝对的优先地位。像《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浩如烟海的经学注疏就繁衍出来。从王阳明“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56页。到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中晚明之后的中国文化生态经历了一个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显然与王阳明的思考完全相反。王阳明的六经“删述”是要对传统注疏之学作减法,而清代考据学却是要对六经作加法,从此语言文字又重登终极真理的宝座。因此,批判阳明学与王阳明,是知识文献主义兴起的一个必然选择,良知学反而成了被“删述”的对象。
对王阳明而言,经验知识既携带有遮蔽性因素,在良知发用流行之际,其本质又是中性的、工具性的,因此良知学视域下的知识彼此之间的争竞并不激烈,比如王阳明就曾讲“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注]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4-115页。。在江西剿匪和宁王之乱中,王阳明屡用诈谋,这种张仪、苏秦式的知识在良知的观照下也具有了某种正面的意义。相反,当知识具有价值论意义时,不同的理论、观念、逻辑、认知要判定是非、争夺正统,就难免关系紧张、产生冲突,其兼融性可能更差,所以才有韩愈要焚佛老之书的主张。纵观王阳明的言说,对所谓的“异端”往往要宽容许多,比如他用三间厅堂之喻,认为在良知发用时,“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注]钱德洪:《年谱三》,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89页。。由于良知学的支撑,王阳明主张的“删述”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事业,是以孔子为符号的,是文治,不是暴力,尽管它包含有社会教化的潜在意指。
当然,事实上良知却又常为见闻所蔽,这样,为了良知发用,就又不能不对如“百戏之场”的言说世界加以区分、判断、引导,包括“删述”,必须建立起一套套与时俱进的拟六经的知识系统。良知之手对文化生态的改造绝非政治暴力追求表面上的威服和形式上的划一,相对于外铄式的霸术,良知不是揠苗助长,而是因循事物之性,加以培拥、灌溉、扶植以及删锄[注]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王阳明全集》,第239页。,依据天理自然生长出来的禾苗绝对是千姿百态(“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注]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2页。),依良知妙手而建构起的文化生态亦将同样如此。因此,王阳明所谓的六经“删述”是以表彰正学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仅仅一味对异论进行剿杀,以中医为喻就是它虽曰去病,其实是以扶正为本。与政治暴力相比,这个净化过程将是缓慢的,由于“习染”积之太久,故要“渐次改化”[注]王守仁:《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王阳明全集》,第635页。。
应该说,王阳明的六经“删述”说一直在力图将孔子与后儒相区分,将六经本身与注疏相区分,将“删述”理解为一种良知发用流行的行为,以之来对抗、揭示和纠偏朱子学知识主义的偏差甚或倒置;它将朱、陆之争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化,是王阳明对于良知与见闻之知关系的一个侧面的生动说明,是良知学从本体论、工夫论走向学术界和社会文化界的一种有力拓展;它说明良知发用不仅是个我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终极目的是实现儒家的三代之治。“删述”说展现了王阳明良知学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总之,对于文化生态的净化来说,发明“良知之学”是“本”,是主要的救治之方,“删述”为其辅助,是“末”,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只有本末相养、内外交互,才能达成良知在社会文化中的流行不息。相对于经典的固定和程式,良知发用流行是一个非封闭的、动态的结构,是一个不断净化和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个我的社会性走向。时值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重建、复兴的关口,大力提倡传统经典包括阐释、宣传经典文本,即进行学术创造是必要的、迫切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提和基础;反过来,是否应该明辨良知与经典的本末关系,是否有必要审视语言文字构成的文化生态可能附带遮蔽良知的消极因素,以及依据良知学建立起一套套千姿百态、不断更新的拟六经的知识文本体系以提升中国传统学术的时代感和应对性,似亦有必要纳入到这一进程中,与前者相辅以成。如此等等,皆有待于方家之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