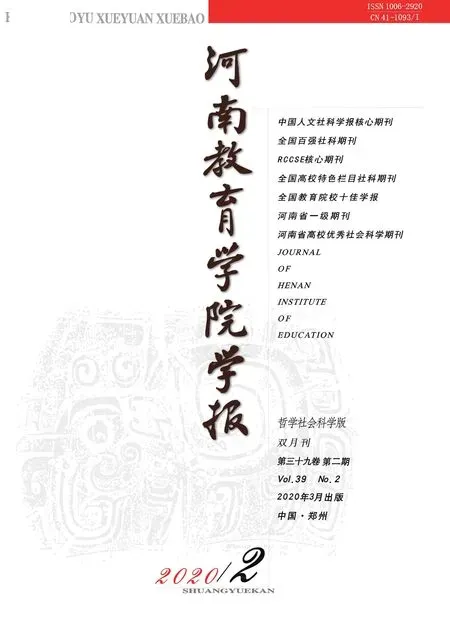宋代禅宗美学及其艺术向度
——读《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
贺志朴
在汉语文化圈中,对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禅宗与中国文化、禅宗美学思想的历史、禅宗与中国画论等。这些都是对禅宗的哲学、文化以及它和画论关系的研究。就禅画来说,有关于禅画本身、禅画的意味,以及著名禅画的个案如“泼墨仙人图”“牧牛图”的研究。这些研究的角度或是禅宗文化,或是禅宗美学,或是禅宗与画论,或是禅画个案,它们丰富、翔实而富有启发性。在此基础上,刘桂荣的《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一书另辟蹊径,选取宋代的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为研究对象,从断代史的维度把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提供了一个把握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的新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宋代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同时,又较为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禅宗美学在宋代文化艺术中的意义以及禅画艺术的意蕴。
一、对宋代禅宗和禅画的追溯和审辨
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它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关联的网络之中。梳理清楚研究对象的关联网络是明确其文化特质、定位其文化身份的必要条件,也是《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一书自觉使用的研究方法。
其一,从历时性的维度看,菩提达摩作为禅宗初祖的地位在宋代进一步确立并得到尊崇和弘扬。中国禅宗在晚唐五代时期形成“五家七宗”,到两宋时期流布甚广。在朝廷支持、文人参与的情况下,两宋时期禅宗经典大量地翻译和刊行。宋代的《景德传灯录》中的《菩提达摩传》综合前代有关菩提达摩的多种历史资料和传说,明晰了达摩的身世地位,为宋代禅宗思想、公案故事和绘画图像确定了依据。随着公案的流行出现了大量《语录》《灯录》,文人士大夫中弥漫着参禅之风。基于禅宗在宋代的发展以及禅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提升,《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选择“在两宋”的禅宗美学作为研究对象。
就禅画源流而言,唐代诗人王维参禅悟理、书画精妙,被后人推为南宗山水画之祖和禅画之祖。王维之后,晚唐至五代时期,禅月大师贯休的《十六罗汉像》是禅画中人物画的新图景。《十六罗汉像》画法高古脱俗,衣纹平行排叠,存唐画“二李”遗风。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评价该画“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态。”[1]107延迁至两宋时期,伴随着禅宗的兴盛和广泛传播,禅画的题材就从以表达禅宗思想为主旨的佛像、观音像、罗汉像、高僧图、牧牛图等,拓宽至表达个人禅悟禅趣的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瓜果蔬菜、梅兰竹菊,这一变迁显示了禅宗精神向禅画艺术,宗教意义向艺术情趣的演进。
其二,从共时性的维度看,宋代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存在于宋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和这一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也构成了禅宗内化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中介环节。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栖心禅寂、热衷禅修,他们和禅僧谈禅论道,倡斗机锋,自修证悟。哲学家陆九渊谙熟禅宗典籍,和禅僧诗达畅游,彰显禅宗自作主宰之气魄。朱熹论及本心、心之主宰、心之功夫等问题,他的“心之本”“主人翁”思想和禅宗自心自性的思想一脉相通。文学家欧阳修从禅宗中了悟生死。苏轼在感怀人生如梦、参透生命幻相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某家思想,涵纳孔儒、老庄和禅宗的“无念”“心无所住”等思想讲“自得道”。他们的思想与创作使禅宗精神渗透到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之中,为禅画艺术的生成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和文化背景。
其三,建基于宋代的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中国,它传播到日本后,对日本的禅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的学者释宗演和其学生铃木大拙等人把它传播到美国,影响了20 世纪美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把研究对象放在当代国际化的视野中来看待,研究它和当代艺术的关联。比如在先锋音乐的实验中,深受禅宗影响的美国艺术家凯奇要使声音成为声音自身。他的音乐作品中出现噪音,意图是转换人的视角,让噪音显现自身、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又如,艺术家杜尚不拘泥于任何权威和限定,用狂禅者的自在游戏创立了艺术世界,在作品中展示了一个自在的、陌生化的图像,揭开了世界的诸种遮蔽,如拂拭尘镜、如拨云见日。这就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中实现了禅宗美学和当代艺术的贯通。
二、禅宗美学和禅画的审美形式
禅宗美学属于哲学,禅画属于艺术。该书以宋代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为题,显示了哲学和艺术对话的意图。禅画概念的核心层面是禅意的表达和悟解。因此,禅画的内在规定性及其所呈现出来的艺术表象可以理解为“禅意”。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类禅画画家,一是融通禅宗思想的禅僧群体,他们在绘画中自觉地表述禅宗思想;二是非禅僧文人画家,他们的作品蕴涵有浓浓的禅意或禅趣,如苏轼、米芾、梁楷、马远等人。这也决定了禅画的两个维度:一是直接表达禅宗理念的绘画作品:“以表达禅宗思想为主旨进行创作,或以修禅为主的绘画作品”[2]6,这是借视觉化的形式对禅宗理念进行图解。二是突破了“直接表达理念”的禅画作品,把理念融入意象之中,把宗教信仰变成人生的艺术化体验,并以此丰富和扩展禅宗的理念,比如雪景图、寒林图、古木怪石、米氏云山等。这些禅画是“以表达个人禅悟、禅趣,或作品具有禅意、禅境的绘画作品,如惠崇、巨然、牧溪、玉涧等人的水墨山水、花鸟梅竹等,以及石恪、梁楷、马远等人的人物图。”[2]6这种划分的逻辑很清晰。前一维度的禅画更多地是指证理念。在后一维度,禅化为文士阶层的精神资粮。历史地看,禅画艺术是两个维度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对话、彼此圆融的结果。
以禅宗美学和绘画批评理念为基点,《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结合禅画作品提炼出了宋代禅画艺术的审美形式,即:“简”“远”“虚”“淡”“妙悟”。李泽厚在评论南宋马远、夏圭等人的绘画时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马远的山水小幅里,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来辽阔无垠而心旷神怡。”[3]177-178这种简略的水墨画风,盛行于南宋。画作不执著于“有”,直抵气韵之生动、大自然无限之意趣。禅画的“简”是禅宗思想中“无”的体现。比如,大慧宗杲言明禅宗“无”之宗旨,在于破除是非思量、分别之心;黄龙慧南强调参禅者要“一念常寂”,达到“自然无心”之境界,从而超越任何拘辖。苏轼把“简”叫做“无心”,“无心”会自然地导向艺术的简远和疏淡,这就和禅画审美形式的另一个概念“虚”有了内在的逻辑关联。如果说佛教主张的我法皆空、世相空幻、生命无常包含了把人生导向悲观的可能性,那么,禅画的“虚”在凸显幻化、空无的禅意的同时,让人体验无限的生命意蕴。在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中,云是澹荡虚化的,山影在有无之间,画面一片迷蒙,涵蕴了无限生机;在牧溪的《渔村夕照》和《远浦归帆》中,“虚”的画面使人感受朦胧之美,让画家和读者在“虚”中安放生命,感受天地宇宙,领悟万物的幻化变迁。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远”的绘画思想,并依此作为标准来品评画作。“三远”之中郭熙推崇“平远”之境,因为平远的意味是“冲淡”,不像“高远”“深远”那样给人的心灵造成动荡起伏。平远“冲融而缥缥缈缈”[4]639,能够在冲融绵渺中实现心灵的腾挪远顾,从日常、功利的此岸世界解脱出来去安顿性灵、建构生命的意义。“远”是真如呈现的过程,它借助想象发现生命的真实,这就和禅画审美的另一形式“淡”有了内在的逻辑关联。“淡”源于道家“无”的哲学,经过魏晋玄学的浸润,和禅宗美学的“三无”(无念、无住、无相)思想结合在一起。随着宋代禅宗思想的文人化,“淡”成为文人阶层的审美追求。欧阳修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5]1976欧阳修表达了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种气象是艺术神韵生发的前提条件。苏轼倡导萧散简远、疏淡平易,这是一种繁华之后的宁静,呈现生命、自然拙朴、至美纯真,蕴涵着浓浓的禅意,让人获得性灵的安适平和,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心理诉求。
禅宗绘画艺术的审美形式侧重于客观。这是禅宗美学向禅画艺术进展的理论成果。当然,禅画审美形式的目的不在于形式本身,而是要超越形式、最终趋归于“无”形式,达至禅意的表达与领悟。这就引出“妙悟”概念。“妙悟”作为审美直觉侧重于主观,是实现宋代禅画艺术旨归的重要方式,标明了禅宗美学和禅画艺术共同的精神实质。
三、以禅宗之心呈现禅画艺术
语言是思想的现实,明晰的语言表征了清晰的思想。学术语言的第一要则是简明准确,这也是禅宗精神。《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不是把读者带入语言丛林、向读者呈现一座高深莫测的语言迷宫,而是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了自然朴素之美。这一语言风格似乎和禅宗的精神相契合,禅宗之心是“无心”“平常心”,无事于心、无心于事,以本来面目呈现生存的世界。此书对禅宗美学和禅画的呈现简略淡逸、禅意盎然,极具韵味。
其一,对直接表达禅宗理念的禅画的语言呈现。《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认为,直接表达禅宗理念的绘画作品,有两种表达方式,或是把禅意融入浑茫无限的宇宙,或是让禅意显现于自性之中。南宋画家梁楷绘有《出山释迦图》,描绘释迦牟尼得道后从雪山走出、度己度人,佛祖的面部削瘦凝重、表情沉静坚毅,作为绘画元素的雪山、枯树和红色的袈裟,既是时间的言说、雪山苦修的生命经历的表达,又超越个体的当下性,以幽深无垠的雪山、混沌的天地表征强烈的宇宙感,以此展露巨大的宗教力量。两宋的《牧牛图》发展到后来,禅修意味弱化、“无念为宗”等禅意凸显,一牧牛、一牧童,世间即出世间,画面更加生活化和世俗化,但禅趣与诗意却更加浓郁。“田间水边柳荫下,自在安闲萧然中,可闲坐横笛牛静卧,可骑牛归家乳牛随,有牧童的天然彰显,有牛儿的自性呈露。”[2]344这是“我”和“物”的不沾不滞、自足其性和圆融无碍。
在禅宗看来,本心自足圆成、清净明澈,犹如光遍虚空的月亮。本心容易受到欲望遮蔽,如月在云中。这就需要荡涤云翳、显露本真。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就以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这一理念:“月光清淡朦胧,山云虚幻优柔,画境空灵淡远,意味悠长……只有一抹清云、一片烟峦自在澹荡,清明了世界,融化了心性。”[2]214寥寥数语、描写传神却禅意盎然。禅宗亦常用牛比喻自性,廓庵禅师《十牛图》,以寻牛起,以人牛俱忘做结,最终牛不存在、牧童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幻化成一片虚渺的风景,指证了禅画的精神境界。《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以语言本身呈现出浓郁的禅意,实现了语言和禅意之美的贯通。
其二,对禅家山水画作的语言呈现。宋代山水画的代表性作品,如米友仁的云山图,法常的潇湘八景,玉涧的庐山图,马远、夏圭的山水图等,在物象中显露出浓浓的禅意,其山水是禅家的山水。
从自然性来说,雪很快就会融化,是须臾之物,其梦幻飘忽如禅宗之“本来无一物”的性空所示。同时,雪融化之后归于天地,又表达了当下永恒、即刻千古的意蕴。雪的洁白和清寒也韵味丰盈,因此,雪景成为宋代禅画的重要题材,画家们用它创造一片静寂的天地。马远的《雪景图》四段,空阔的画面上是淡远的山影、迷蒙的云水、洁白的积雪,表达生命的轻歌和性灵的曼舞。梁楷的《雪栈行骑图》有苍茫的虚空、淡淡的雪痕,把骑驴赶路的人淹没在漫天雪景中,昭示了一种有限人生和无垠宇宙的情思。在画中,“我”面对“宇宙”时,不是彷徨不安,而是就在“宇宙”之中,我和无限的自然风景融合为一。
禅宗要荡涤妄念、去除攀缘、呈现本明的纯真生命状态,荒寒的画境与这种诉求十分契合。在李成的《寒鸦图》、范宽的《寒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郭熙的《寒林图》《寒鸦秋水图》等画作中,天地之间的风景萧疏野逸、清净冷寂,其间没有欲念的骚动和对无穷的追逐,只有心的清静、明洁和洒脱,呈现着禅宗的超越精神。缥缈的微云、栖居的寒鸦、萧瑟的芦苇、冷寂的孤月、幽深的寒林、远尘的古寺……构成了一个蕴涵着禅宗精神的意象群,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了禅的精神世界。
世间生命常有困惑之感,常徘徊于意义和无意义之间。感受时光飞逝、浮萍飘零,感受世流挣扎、雪泥鸿爪,破除执念、回归本真,超越有限、拾得自在,是禅的精神所在。禅宗和禅画就是要通过显现自性、安顿人们饱经沧桑的惊魂,使生命廓如太虚、无所挂碍。《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意图弥合精神和肉体、现世和来世、有限和无限的分裂,实现生命此在的朗照洞明和“诗意栖居”。作者以优美的语言标举禅宗精神,探求创作者之心性,揭示接受者之领悟,也见证了禅宗美学和道家哲学、儒家哲学的相通相融,从而在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生命交融中彰显禅画之魅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学术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以自己的学识和研究对象对话的过程。作者以《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为载体,和禅宗、禅画相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悟解生命真谛、把握宇宙流行。因其明白的语言、富有洞见的禅意,在阅读中,我们便不自觉地跟随作者进入这场历史和精神的对话中,去感怀生命的情味,理解禅宗的精神,妙悟禅画的真谛。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在禅宗的语境中,在禅修者、画家、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中融通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