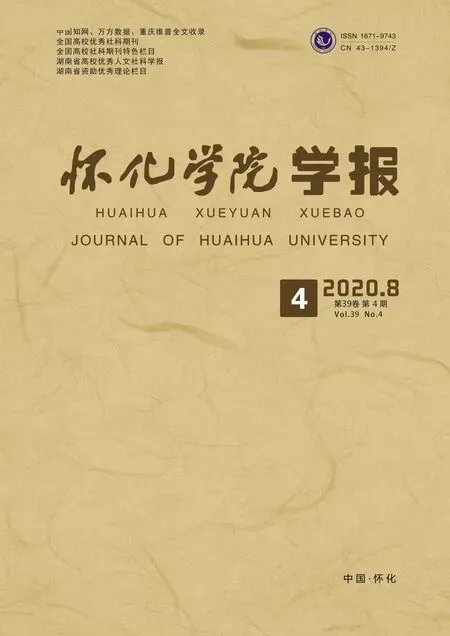魂归笙鼓地:贵州清水江苗族“焚巾” 丧祭仪式调查
曾雪飞
(贵州大学音乐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清水江流域为中国苗族聚集区。根据苗族古歌,该区域苗族大多从河流的下游迁入:“先祖住在欧振郎,水波潋滟与天连,大地平坦如晒席,像盖粮仓的地坪。窄处窄得像马圈,陡处陡得像锅沿,鸟多巢窠容不下,人多地窄住不了,火坑挨火坑烧饭,脚板挨脚板舂碓,盖房拥挤像蜂窝,挤挤撞撞破锅罐,汽盆甑子都压烂,我们商量迁西方,西迁才有好吃穿。”[1]463-464相传,清水江流域苗族先民从榕江古州一带经过剑河县 “松党故”①,分支迁居清水江沿岸各村寨。
清水江苗族丧葬仪式不同于川黔滇、湘西方言区的苗族,最具有特色的是丧葬仪式中所演唱的《焚巾曲》。“焚巾曲”,苗语 “hxak peed qub”,hxak,为 “歌”;peed,为 “烧”;qub,为 “巾”;直译即焚巾曲。有的苗寨也称 “焚绳曲”“赞娘歌”“带路歌” 等。“焚巾曲” 是根据巫师念诵祭歌时焚烧头巾、腰带等而命名。清水江流域丧祭仪式中的“焚巾祭” 核心在于叙述逝者的一生,并最终将逝者灵魂送归祖居之 “笙鼓地”。“焚巾祭” 是个体人生的终极仪式,也是对逝者的一种最高祭典;同时,“笙鼓地” 的描述,表达了苗族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一、“焚巾祭” 仪式过程
“焚巾祭” 在仪式功能上,主要是为了安排逝者的亡魂。清水江苗族认为人有三魂,死后就会分离:一个魂留守在家屋,为祖灵;一个魂与坟墓同在,守在坟上;一个魂在野外,寻找食物。
出现丧亡,清水江苗族忌讳说 “死”,多以 “靠下” (khod), 或者“ 变龙去了” (jangn vangb mongl) 来指代,有的村寨也称 “走客”。一般非正常死亡,如婴儿夭折者,用杉木皮裹尸土葬,不行葬礼。亲友一般自提一壶酒到丧家安慰。成人非正常死亡者,必须火化。
(一) 落气与报丧
老人病危,通知兄弟姐妹及亲友见最后一面,若是女性,则必须通报舅爷家。临终前,亲属将其移到堂屋火塘边长凳上,脚踩稻谷断气。老人刚断气时,亲人会为其烧落气钱,包好纸钱灰烬。孝子把铜钱丢在取饮用水的井中(意为向龙神购买清洁之水),在井边插一根青竹,这根青竹上有用麻线捆绑的白纸,并用水桶装些水回家为逝者擦洗。告知亡魂,擦洗干净,穿新衣服,就可到天上跳芦笙,踩木鼓。请寨老划十二片竹条,编成竹架,置于堂屋左边。为死者穿丧服(女性需新百褶裙),衣服为一、三、五等单数,忌讳双数。男性寿衣不能有花纹,女性则必须是绣衣。寿衣一般在生前准备好,只有鞋子必须死后制作。鞋底上用碳灰画九个圈,代表多子多孙。
死后第二天,请两青壮年带柴刀等铁器,到亲属家报丧。报丧者不能进他人的家屋,问路只能在路旁和屋外,沿路不能摔倒,否则认为丢魂在此。报丧后需喝或者吃些亲属家的水和食物,表明完成了通知任务。
(二) 随礼与抢客
参加丧祭的亲属一般在逝者入土前一天赶到,一般亲属送白布、米、鸡鸭等。丧祭结束后,孝家需回礼给客人。
本家族均具有义务提供帮助,协助办理丧祭。本家族成员进行分工:男性准备丧祭仪式、参与守灵等,女性主要负责饭菜。在礼物方面,一般赠送糯米与酒,有的还要挑一担柴。因为丧事是不可预料之事,孝家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本家族出人出力,提供米酒等招待客人是应尽之义务。
舅爷家、女婿家最重要。逝者咽气,女婿家需第一时间把殉葬物 “垫尸布” 送到孝家,以便入殓。女儿需在老人临死前去看望,去世后也要去看望一次,直到逝者上山下葬那天,女儿才正式送礼,礼物主要有公鸡、稻谷、猪、被子之类。女儿还需将一小袋糯米饭放入棺材,并送给逝者银元,谓之买路钱。女婿家送的礼相对多些,一般需要送一头猪,白酒若干,有的还请人吹唢呐。女婿家回去时,孝家也需回礼,女婿家送来的猪宰杀祭祀后,留一条猪腿给女婿家带回,以招待女婿家帮忙的家族兄弟。
舅爷家礼物有稻谷、酒、被子等,银钱为亲属中最多的。台江县一带苗族还必须请舅家坐专桌,派人专门陪酒。舅家在席间与孝家边吃边争论,吃剩的酒肉直接带回家。舅爷家回去时,孝家专门砍一块带猪尾巴的猪腿和一把杀猪刀、一壶酒送给舅家。在送到岔路口时,打三个草标,倒三大碗酒祭祀亡灵。如果舅家愿意继续与孝家保持关系,便收下猪腿和酒,用杀猪刀将猪尾巴砍断,送给孝家,表示留下亲根,姑舅常来往,老亲戚永远延续。否则,视为断交。
媳妇娘家也需送礼。客人到后,走进灵堂烧纸钱(只能由男性负责),并行礼。下葬之前,准备好酒肉,参加葬礼的亲属进门时需喝酒,送 “酒钱”。客人将带来的孝被盖在逝者身上,捆碎银在逝者白布袋上,并告知这点碎银是给您老人家买水喝的,老人家要喝东边的水,西边的水是生者喝的,同时由女儿嘱咐逝者:回东方祖居地的路上,要买清水喝,不能喝浑水,这样才能安全抵达笙鼓地。
逝者埋葬后,或者复山晚上,亲友到孝家 “抢客”。抢客时,由每一组客来说明为何要抢某公或某奶(逝者) 去他家走客。苗语称 “Tod hmid lacb”,直译为 “复寻生前的脚印”。最后由寨老评判,判断哪组客理由更充分,就允许亡魂到某家做客。最后,通过大家评论,确定亡魂最先跟随哪一门的亲戚去走客并且确定走客的顺序。送魂和走客后,孝家备酒邀请兄弟姐妹房族相聚,感谢众人协助办理丧祭仪式,共饮团圆酒。出嫁女儿必须带回一只鸡、一壶酒、一篮糯米饭等礼物给健在的老人,并把带来的糯米饭分给大家吃。
(三) 梨屋与守灵
清水江高坡一带苗族在丧葬仪式中有 “犁屋” 习俗:从前,死者亲属头捆丝麻,腰束稻草以示哀悼,现在其子孙及近亲晚辈头包白布帕,以示哀悼。入棺那天,高丘地区兴 “犁屋”。犁屋前,家属把死者生前用过的睡席剪一块下来,制成一个 “斗”,斗上盛谷糠和瓦碴子,插上九炷香,再将事先炒焦的菜籽、稻子、棉花籽少许放入 “糠斗” 上。然后把“糠斗” 移于筛中,筛内放半熟的猪头和全鸡、全鸭各一只,蛋一个,然后把筛子置于堂屋中央。其旁放九块蚌片,蚌片内斟上酒。这一切摆好后,一个年高德劭者,用犁从火炕中间犁出犁田状来,犁到堂屋,对死者说:“菜、谷、棉、银你都有了,你在生有吃有用,此去阴间也如此。在生,你同家人是一家,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以后,是好是歹你不要过问自家人和客人了。如果你要问,除非炒焦的菜种能发芽。” 这些话刚讲完,就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将生苞谷籽撒出堂屋去,其他人随即将尸体抬出堂屋,置于屋檐外棺材内。犁出死者家大门后,还要去死者房族家犁屋,但堂屋中央筛子的蚌片杯只摆三个或七个。菜籽、稻子等物均是孝家炒好分给的,不够部分可以自炒,猪头、鸡、鸭可免,但仍要蛋一个。犁完房族屋后,犁收回放在孝家门边。筛中的食物均拿到路头或路头的仓脚吃掉,筛中那些非食品即在路头烧掉[1]236-237。
守灵。入殓既毕,即用斗盛一斗谷子放在灵柩(或殓床) 之前作插香用,在灵柩上或殓床边,放有一把十余棵的稻心草,表示替亡人驱逐蚊、蝇之用。亡人入殓后,请好命人把插香用的一斗米拿到水边,让稻米顺河流而下,意为人与稻米都顺着河流回到东方祖先之处。
(四) 下葬与填土
亡人如系中年以上的,守灵的妇女常在夜间三更以后唱丧歌(苗语意为 “哭丧”)。丧歌很长,善歌者常终夜不辍,通宵不尽。内容主要是叙述亡人的经历和大家的悲伤,最后安慰亡人不要想念家人等。其中一部分是以前长篇说理词——“贾” 的一部分。歌唱者一面唱,一面手持稻心草把,在尸体或灵柩上从头到脚轻轻掠过。丧歌曲词与别的歌种不同,悲哀凄恻,带哭带唱。当唱到悲伤的时候,常常泣不成声。夜深时,孝家准备大量糯米饭,分给在场的人每人一团作夜宵,苗语意为 “深夜之饭”。但这种称呼,只能在办丧事时用,平时的夜宵是不能如是称呼的[2]254。守夜期间,需防止猫,苗人认为猫会侵害死者的身体和灵魂,有的地方认为猫在死者旁边跳,死者会变成 “老变婆”。
找地理先生根据逝者死亡日期推算下葬日子,如果犯煞需请鬼师化解。如果一直难以选定日子,也要送棺材上山,但不下葬,用竹棍支撑棺材,上面覆盖杂草,直到入土。有的停棺时间长达一年,甚至三年。有的逝者时辰犯大恶,还需拉人陪死,为免灾,用一只小鸡或小猪代替人,打制简易棺材随逝者一同埋葬。
逝者尸体抬出大门置于棺材期间,必须打黑伞遮盖住逝者的脸,以免见到阳光(苗人认为人的灵魂与阳光关系密切,如果死者看见阳光会以为自己没死)。
清早下葬,由地理先生相地,并烧香祭祀后才可动土。准备出殡时,鬼师手提公鸡祭祀,摔死公鸡后给老人吃。出殡时,由孝子负责,女性因阴气重需避开。剑河县一带苗族由长子穿草鞋戴斗笠扛牛刀(牛刀是用来开路,不允许其他鬼魂挡路),带糯米饭、酒、肉等食物在下葬时祭奠,其次跟随次子、三子等。女性不能上山,棺材上山后,妇女去逝者房间,将其生前的衣服、被子等拿到上山所经之路边烧毁。
赶嘎嗒,苗语为 “ganx ghad dab”,其中 “ganx” 汉意为 “堆上去”,“ghad dab” 为 “土”,直译就是“添土”。老人死后第一年清明前做 “赶嘎嗒”,子孙带白公鸡给逝去的祖先 “暖家”。巫师在祭祀 “嘎嗒” 同时,也祭 “白虎” 并招龙,让龙神保佑子孙发财发富。第三年后子孙们再次祭奠,称 “沙嘎嗒”(“沙” 汉意为最后一次),即最后一次 “赶嘎嗒”,表示丧祭仪式最终完成。赶嘎嗒选择在宜动土之日。赶嘎嗒主要围绕 “啊嘎嗒” 仪式。相传,嘎嗒为掌管建筑的神,嘎嗒有三个分身,住不同的地方:一个掌管坟墓修建,一个掌管桥凳修建,一个掌管房子修建。嘎嗒耳朵背,请神时需大喊三声。赶嘎嗒属于丧祭仪式的一部分,请负责坟墓修建的嘎嗒神来稳住坟墓的砖土。
丧祭期间禁忌较多,如盐巴说 “甜石头” 之类。其中未出嫁的姑娘不参加丧祭,一般到外寨回避,直到丧祭结束后才回家。孝家忌讳狗肉、鱼虾等食物,不能理发、洗澡,更不能夜宿他家。
二、 《焚巾曲》 的内容演述
演唱《焚巾曲》 是焚巾祭仪式中的重要环节,但只能在逝者埋葬的当天夜里由巫师演唱,目的在于送亡魂沿祖先迁徙的路,一步步回到祖居地的东方老家,再送其灵魂到蝴蝶妈妈和始祖 “央公” 的天上去。 《焚巾曲》 内容庞大,包括苗族始祖来源、支系迁徙以及人的一生,如出生、成长、游方、结婚、生育、劳动等。
演唱前,孝家准备长桌(枫木),摆在堂屋中间,桌子上面,摆煮熟的鸡鸭各一只(头反背在背上,各插一双筷子在鸡鸭背上),三个酒杯,一个木升子,桌子下面放置一个笆篓,装一些稻谷、白布(稻谷、白布最后给巫师),一个木制脸盆,装些清水,盖白布巾。歌唱结束时,焚白布巾于木盆内。
开始唱歌前,孝家宾主聚集在堂屋,围着桌子坐一圈。家族长老主持歌场,按孝家的老亲、新亲等各亲属顺序,逐门点名呼唤,请其演唱《焚巾曲》。被点名者均客气推托,愿出钱请巫师唱。于是,各人掏钱放在桌子上的木升里。最后主持歌场的长老正式请巫师演唱。焚巾曲演唱结束后,主持者将笆篓口上的白布系在巫师手臂上,并将笆篓内的稻谷送给巫师,将客人的买歌钱分送给所有听众[3]。
《焚巾曲》 叙述人的一生,直到死亡后,亡魂走向 “笙鼓地”:
1. 缘由。 《焚巾曲》 属于巫师所演唱的指路经,首先由巫师介绍 “焚巾曲” 的来由:来悼念老人,大家都掏钱,买歌我们唱,带老人上路。走天上蝴蝶妈妈家。去招金银粮,去招金银来。去招金银来,保哥有饭吃,保妹有衣穿,你富我也富,主人和客人,人人都发财。……唱哪样歌好?唱首焚巾歌,唱首古老歌,唱首赞娘歌,我唱你们听:山岭是主人,个人是过客。生命较短暂,创业给后生,绣花给妹穿。等到夜晚到,抬脚去月亮寨,去跟祖先住,不会转回来。
2. 人类起源。 《焚巾曲》 演唱从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开始。清水江苗族在古歌中喜欢追根溯源:馄饨那岁月,朦胧的岁月,蝶妈生老人,生老祖央公。 《焚巾曲》 也唱蝴蝶妈妈与十二个蛋的古歌:从前远古时,最早的年头,枫树长坝场,枫树枝叶茂,叶子盖坝子。地方宽坝场平,款场如天上,如同天无边,地方宽无垠。看一眼很远,再看也很远,三看也很远。流水没有路,地方无村寨。啄木鸟东来,来啄枫树干,才生出蝶妈,生出祖先妈。别人生孩子,妈妈亲怀蛋,生蛋在家里,生了一场天,生了两场天。生出十二个,十二个黑蛋,妈生妈不管,妈生妈不抱。让鹡宇来抱。鹡宇迈步来,落脚在窝里,抱蛋成一时,又抱两时候。到时孵出来,圆蛋出雷公,飞到天上去。花蛋出猴子,出个花脸虎,爬到山坡去。长蛋成水龙,水龙身体长,进入深水潭,一去不回来。第二个蛋生黄牛,宽角的水牛,在山冲吃草,老是吃不饱。第三个蛋出野猪,生山湾的山羊,啃芭茅草当粮。最小蛋生央,生腊开辟地方,开寨大伙住,姑娘才出嫁,后生才成家。
3. 人的一生。叙述人类从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宰鸭来贺小,一伙妈来一批,取名才好叫,取名送妮妹,取名送哥哥,消息传舅爹,舅妈缝背带。……三岁会走路,用火灰造田,提三脚架做鼓,那坝场跳芦笙,葵花杆做碓,学妈妈舂米。……十岁哥大了,十岁妹大了,哥大成后生,妹大成姑娘。十岁会寻对象,跟后生开脚去,跟后生游方远。一夜九个寨,十夜九路游,十夜九地方玩。……活久年岁大,年高妈变老,人老容貌衰,衰老实难看,不愿留人间,要往天上还。上天去修德,跟祖先坐在天,去住央公寨。
4. 死亡。清水江苗族认为山林是主,人是客。万物均有起源,并是永恒的。山林常在,但人生无常,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是大自然的过客。 《焚巾曲》 :“Ghab vangx dios dail xiut,Dail naix dios dail khait”,汉意为 “那梁是个主,个人是个客”,也就是说,山梁等是永恒存在的主人,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人只是山梁的客人。人的死亡不可抗拒,生死有命,人类只有顺应自然:五倍子树知,确定人季节,哪个来主宰,捉到妈季节。央爸来时候,定妈的季节,逃也逃不脱,推命推不掉。野猫寨脚叫,以往叫别人,这次叫到妈,叫到妈要走。娘死儿孙盖脸,众崽捏眼合。姑娘灶边哭,半夜不停息。
5. 笙鼓地。苗族《焚巾曲》 主体内容在于为亡魂指路,从生活之现实世界走向祖先迁徙之路,沿着祖先 “溯河西迁” 的反方向,回归祖居地,最后升入天堂,与苗族始祖央公永住 “笙鼓地”:妈辞别骨骸,妈辞别水塘,妈挑银和财,妈开步游脚。……榕江好地方,坝子自空好,河水浪来打,村寨不成地方,妈妈踏步走,抬脚上高坡。……妈回到家乡,回到水浑的东方,走到浑水边,走到先人场坝。先人地方很富,祖居地在远方,是央公出生地方,是妈妈出生地方。……妈爬到天光,爬到踩鼓场,跟央公成寨,跟祖先在天。……老人到天上,老人大声喊,喊月亮妈妈,喊天上的月亮。月亮妈听到了,为老人开门,开门让进屋,老人陪阿妈,跟月亮在天上,一去不回来。
6. 歌尾。 《焚巾曲》 有歌头和歌尾,歌头在于介绍此歌的缘起与价值,最后结束时,巫师必须将众人带回阳间现实世界。众人送亡魂走向 “笙鼓地”,但现实生活的人必须回归原有生活与秩序。由此, 《焚巾曲》 歌尾在于 “回归”:得你的工钱,一笆篓稻谷。我教你上路,来唱这首歌。我唱这首歌,唱了我不要,我送你上天,送到我回转。我回到家来,种庄稼有吃,绣花衣有穿。我送你到家,我转回我家屋,我活百把岁。我活百把代,能过千次宗鼓节,越活越发财。我送你到家,你不得回来,你变成宝浓,一个来家里,受香火敬供;一个守坟地,看你的骸骨;一个去野外,在路边找吃。
对于众人来说,灵魂也需回到阳间现实世界,《焚巾曲》 是送亡魂之 “哀歌”,需牢牢拴住,永留人间:捆歌系住了,拴住哥儿魂,拴住妮妹魂,不让随妈走,跟随去天上。捆歌系住了,拴住姑娘魂,拴住哥郎魂,不让歌跟阿爹走,跟随阿爹上天去。捆歌系住了,系在泥田里,拴在金银上,不许歌随阿妈去,不让歌随妈去天上。捆歌系住了,拴在门和仓,拴住牢牢的,不让歌随阿妈走,留下歌来我们唱。
三、魂归笙鼓地:苗族生活的社会理想
罗伯特·赫尔兹认为对于集体意识来说,死亡在通常情况下是将死者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实现他从可见的生者世界向不可见的死者世界过渡。个人的每一次提升都意味着他获得了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转换的途径:如死亡是一种排斥,而再生则是一种重新整合[4]65。许烺光从灵魂观看到葬礼之社会功能:葬礼也是为了保证死者的灵魂在去灵魂世界的途中一路平安,保证灵魂在灵魂世界里能平安无恙[5]138。林耀华则从现实社会的功能来思考丧祭:在死亡所带来的危机打破了生活的常规之后,丧典仪式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重新建立起人们之间共同的感情。举丧的人家与吊唁的客人们借此重新加强了旧有的关系[6]126。
苗族认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清水江苗族普遍存在 “过阴” 习俗,即鬼师能 “走阴间”,通过一定仪式,灵魂进入 “笙鼓地” 看望逝者亡魂。有人生病,也请鬼师过阴侦查,寻找是什么鬼作祟。过阴仪式需糯米、布条、香纸钱、清水、芭茅草等,以及一位 “通事” 协助。鬼师之所以可以过阴,在于鬼师有许多亡魂附在其身上,称 “阴崽”。过阴时,由阴崽去侦查鬼怪。苗族认为糯米为阴崽带路,糯米要病人自家的糯米;布条带鬼与阴崽见面,布条必须从病人身上扯下来。鬼师过阴后,通事配合鬼师进行仪式。最后,通事拔掉香和芭茅,鬼师跳回阳间。
苗族灵魂观将人世阳间与灵魂阴间视为二元空间:人类在阳间具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而灵魂阴间则是吹芦笙、踩木鼓的 “笙鼓地”。“笙鼓地”,这是清水江流域苗族对于死后世界的描述。“笙鼓之地”,苗语 “Dangx gix dangx niel”,苗族认为,死后世界是与祖先一起,大家共同娱乐,“吹芦笙,踩木鼓”,不用劳累,没有病痛,天天过节,生活美满。民国时期陈国钧《生苗的丧俗》 记载:“据生苗说:人死了三天,家人们须至墓前敬供,供品为牛肝或猪肝及鱼、酒、糯米饭等,意思让亡魂吃饱,好赴一个地方去住,那地方生苗语叫Sen u (生有),在一片大坡之上,亡魂在那里还是继续人世时一样的生活,天天吹芦笙,踩歌堂作乐。”[7]262据调查,在巫师唱诵《焚巾曲》 时,将白布焚烧,在火光中最后显现亡魂赐予子孙的牛、鸡等财富。清水江苗族之所以将美好世界界定为 “笙鼓地”,一方面是因为苗族具有祖先崇拜,亡魂需要回归祖居地,且在苗族史诗记忆中,东方老家本来就是富饶美丽之地;另一方面是因为苗族对 “芦笙”“木鼓” 的喜爱与崇拜,笙鼓不仅是娱乐的歌舞乐器,也是沟通人神的媒介。
清代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关注到清水江苗族对 “笙鼓” 的喜爱:“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族类甚众,习俗各异。衣服皆尚黑男女俱跣足,陟岗峦,履荆棘,其捷如猿猴。性悍好斗,头插白翎,出入必带镖枪、药弩、环刀。自雍正十三年剿后,凶性已改。孟春,各寨择地为笙场。跳月不拘老幼。以竹为笙,笙长尺余,能吹歌者吹之,跳舞为欢。人死,则生前所私者以色锦系竹竿插于坟前,男女祭拜也。” 该条丧祭礼与苗族自由恋爱婚制有关。刘锋认为,随着远古自由婚恋成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和姑舅表婚的盛行,青年男女婚恋成家越来越受到舅家的干预而不得自主,因而只能将青年男女之间的自主情爱寄托于死后的未来,返回到祖宗地去圆生前的恋爱梦。真正相爱的男女在对方死时用色锦系在杆上插于坟前,其用意是寄托生前未了恋情[8]72。
“芦笙” 与 “木鼓” 均是清水江苗族的乐器,男女青年节日相聚 “游方” 时,往往 “吹芦笙,踩木鼓”。苗寨聚落空间内,有专门为男女青年交往娱乐准备的 “芦笙场”“踩鼓场”。男子吹芦笙,姑娘随芦笙木鼓节奏起舞。雷山、凯里一带过苗年期间,每天中午以后,各村寨男女穿盛装到芦笙场。吹芦笙以男青年为主,轮流交换吹芦笙,不能使场上笙音中断,跳芦笙踩木鼓者以青年女性为主。芦笙曲最正统的叫铜鼓调,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曲调和跳法是 “讨花带” (Gix jangl hlat),为吹芦笙青年以“讨花带” 芦笙曲调向所爱慕的姑娘吹奏,笙曲意译:窈窕的表妹哟,美丽的姑娘,你绣的花带哟叫人心花怒放!把它送给我吧,把它系在我的芦笙上。如果你有心哟,我俩便成双;芦笙来做媒哟,花带连着你我的心房[9]88。
“木鼓” 不仅作为清水江苗族的乐器,更是血缘家族组织的象征。清水江苗族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就是 “鼓社”,每十三年一次的 “鼓藏节” 的实质内涵就是 “鼓社祭”。同一鼓社严禁通婚,历史上有“破鼓开亲” 的传说,这一传说反映了苗族古代社会所进行的婚姻改革。他们认为,祖先之灵居于木鼓之中,只有在重大节日,如苗年,或者鼓藏节时才能敲响木鼓。“踩木鼓” 也是苗族在节日中重要的娱乐活动,其含义与 “吹芦笙” 相同。
因此 “笙鼓地” 是苗族特定时间和场域的一种表述。当老人说死后去 “笙鼓之地” 时,表达的是一种死后的理想社会图景。而这种理想社会图景的想象,也蕴含了苗族社会丰富的男女情感内容,即恋爱自由和婚姻不自由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悲剧,从而产生对真正自由恋爱的憧憬。苗族谚语有云,“妈妈只给我游方,妈妈不许我成双”。一方面,苗族社会普遍存在男女自由恋爱的游方体制;另一方面,苗族社会具有严格的婚姻制度,尤其是 “舅霸姑婚”,即姑妈之女须嫁给舅家。黔东南规模庞大的十二路酒歌《开亲歌》,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改革姑舅表婚的婚姻制度。
可以自由婚恋,但在婚姻上难以获得自由的青年男女,遭遇了各种悲剧。有的压制自己的情感,听从阿妈之言,嫁到舅家,也有的坚决抵制,进行私奔:“我俩逃走吧!顺河逃走呢,或向高山爬,上山逃走呵。怕爹带狗追,哥带铁链拿,逃不出呀!顺河逃走好,河水淹脚印,茅草遮我身。午夜就逃走,那时妈不知。” 有的甚至殉情:
妈妈羨慕哟别人的高楼和大厦,爸爸贪图哟人家的白银亮花花,硬逼着我哟去出嫁。那个男人哟一副黄鼠狼的嘴脸,身子瘦得哟像只蚂蚱的骨架架,实在不中我的意,我怎能嫁给他呀!可是婚期哟却已订在来年哪,到时赶我哟跨进那个鬼人家,我不气死哟怕也要愁煞。花衣再好哟我也无心绣,饭食再美哟我都咽不下。上坡干活哟无力挥锄把,收工回家哟沉吟求妈妈:相爱的人哟我才嫁,不看银钱哟有多大。这门亲事哟不作罢,宁肯老死哟也不嫁。
……
我生我长哟不逢好时光,爹妈强迫哟匹配丑夫郎。女儿命苦哟不值银一两,越想越惨哟悲断肠。命运好苦哟横顺无出路,心儿一横哟带上根绳索,悄悄跑去哟密林老山坡,高高吊在哟一棵坚韧树。蓬头散发哟任随风吹乱,两腿直直哟长长吊下来。村坊寨邻哟吼叫轰轰传,等到爹妈哟惊慌跑拢来,可怜的女儿哟气已断,三魂分离哟剩下躯壳,身子空壳哟冷僵尸一个。
……
女儿尸骨哟要埋山坳上,不要埋在大路水井旁。抬儿上山哟要过水井边,井边大路哟阿郎常过往。我和阿郎哟前世的鸳鸯,我还等他哟过来叙衷肠。别人过路哟漠然望一望,阿郎走来哟凄凄对我讲:你的花镯哟还在我手上,你是爱我哟还是将我忘。日日夜夜哟我都把你想,谁知道你哟吊绳把命丧!你是一个哟坚贞的姑娘,请你起来哟和我去成双![10]167-180
因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真正的自由恋爱难以实现,因此只能把自由恋爱的憧憬,投于死后的“笙鼓之地”,所以《开亲歌》 中又唱道:
小妹先去哟苗家高坡地,蝌蚪坳上哟游水等着你。小妹蹲在蝌蚪哟井边,喝着清水哟解渴与充饥。我等阿郎哟等一年也等,一年不来哟等两年也等,一直等到哟阿郎来时,我们两个哟死后做夫妻。我俩抬头哟望见天上,天上铜鼓哟咚咚响双音,嗡嗡吹奏哟尽是好芦笙。天上过节哟人多闹沉沉,人人都会哟踩鼓跳芦笙。我们两个哟手牵手前进,夫妻双双哟进入笙鼓坪。阿郎吹的哟芦笙最好听,我踩鼓点哟舞步最轻盈。阿郎看我哟眼睛笑眯眯,我瞧阿郎哟脸上喜盈盈。我们两人哟相亲又相爱,恩爱夫妻哟形影不相离。美好日子哟说也说不完,生离死别哟前世的霉运,从今以后哟万代不离分②。
四、结语
清水江苗族认为死后世界即是自由婚恋的世界,“人人踩鼓跳芦笙”“夫妻双双进入笙鼓坪”。他们对 “笙鼓之地” 理想社会的向往,源于苗族现实生活中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在生的世界不能与情人在一起,只能盼望在死后的灵魂世界能如愿。
注释:
①“松”汉意为“坳”,“党”为“地坪”,“故”为集中议事。
②1982 年台江县革夷公社杨鱼长、姜阿觉演唱.姜柏记录.姜柏、燕宝译.参见魏龄编:贵州情歌选第2 集苗族游方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