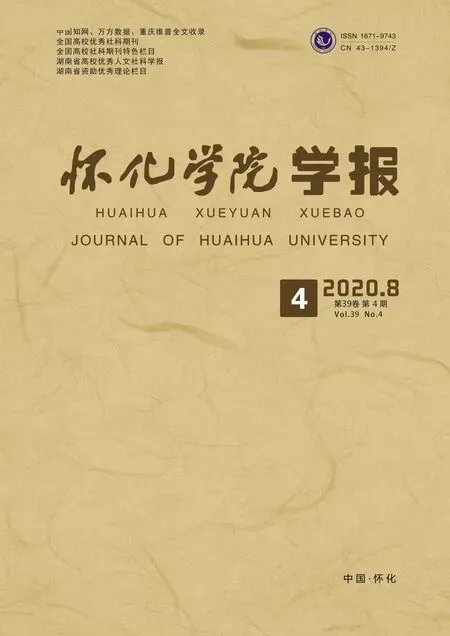“法脉” 说与明末清初制义文风
李文韬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200433)
时运交移,文章代变,有明三百余年,制义文章风格多变。在这期间,伴随着明代制义的发展变化,明人对于制义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也揣摩得愈加深刻,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颇具理论性的制义指导书籍,也诞生了诸多批评术语,使得制义文论的理论化程度更趋精密。在明人的分析、批评与阐释中,“法脉” 是一个广泛存在于制义文论中的批评术语,该说自明季开始流行,这既与明代中叶以降文法著作增多的客观事实有关,又与明季制义颓敝的整体生态状况相关。前者表明 “法脉” 作为一种关乎制义写作的文章技法,其诞生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与明代文章学的整体演进有关;后者则是 “法脉” 说价值指向意义的重要来源,文论家赋予 “法脉” 说以价值评判意味,从而呼应社会需求。
“法脉” 说自明季开始流行,随后亦为清初制义文论家所沿用,在清初制义文风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前的制义研究来看,大多数论者还是从断代的角度出发,对明清制义风格的变迁作客观的阐释。制义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头场,科考又是帝制王朝意志的体现,制义发展史与政治史密切相关,这无疑是正确而自足的。基于此,明末制义无疑属于明代制义的范畴,而清初制义则从属于清代制义。然而,回归到明末清初制义的实际发展中,可以发现,制义发展自身的连续性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中断。明末清初时人对制义的思索,始终围绕着如何继承先正法脉、如何写作制义正体这一核心命题,由此而展开批判和写作。明季开始被广为沿用的 “法脉” 说,直到清初,其影响依旧不减。因此,从断代角度对明、清制义发展分而述之,未免忽视了明末清初制义发展的连续性,从而也忽略了制义自身的演进。以 “法脉” 的内涵来把握明清之际制义文风的转变,能深刻地看出明季制义与其他各朝制义的不同,能发现明末清初制义文论家对制义轨范的种种思考,更能揭示出明末清初制义文风转变的内因。
一、释 “法脉”
“法脉” 既包含了文章技法的意义,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标准。前者是该词的应有之义,后者则是批评家有意赋予的产物。前者是文章学中文论术语自然而然的汇流,论者不过是因袭前人的共识;后者则是制义文论家的创见,文论家们的主观判断为该词增添了新的内涵。
明初洪武年间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制义属于头场考试,考官、考生均极其重视,这也促使制义文论比隶属于科举后两场考试中的论、策等文论更为发达,其中的理论性也更为突出。具体到其中,伴随历科的开设,明代文论家也在积极建构制义文论,从传统文论中寻求可嫁接使用的文论资源,进而提出诸多与制义相关的批评术语,“法脉” 便是其中的典型。从语词形式来看,“法脉” 一词是由 “法”“脉” 二字组合而来,由于 “法”“脉” 二字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文论意义,当两个单独的文论术语合并成为一个词时,其原有的文论意义也被整合进来。
不妨以 “脉” 字而论。明初洪武间,曾鼎就提出:“学文切不可学怪语,且先明白正大,务要十句百句,只如一句贯串意脉。”[1]曾氏谈到的 “一句贯串意脉”,自然是要求全文中心思想须得统一,不可散漫。同时期苏伯衡亦谈到:“抑扬以达其辞,反复以致其意,血脉之流通,首尾之照应,则善矣。”[2]他同样认为文章写作不可枝蔓,炼辞以达意,文章血脉才得以畅达。年代稍晚的吴讷亦认可文章思想须要一以贯之的观点,指出:“作文须要血脉贯穿。”[3]以上三人生活在成化、弘治之前,该阶段制义文论尚少。事实上,直到成、弘两朝之后,关于举业的论述才逐渐增多。其原因在于,制义虽然创制于明初,但直到成化、弘治之时,其文体才逐渐定型[4,5]。基于此共识,制义写作者在写文章技法上寻求进一步的突破,制义文论家也有意识地进行文章技法层面的阐释。
正如乾隆时陶元藻指出:“明自守溪为之先,荆川继之而法脉已备,然犹未尽其变也。”[5]陶氏明确地指出成、弘时期是制义初具文法的时代。成、弘之后,关于制义写作技法的讨论增多,制义文论渐趋发达,“法”“脉” 二字也自然而然地从传统文论进入制义文论中。例如,正德年间杨慎曾评价制义:“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6]万历时汤宾尹认为:“题中亦有脉理,亦有来龙。”[7]董其昌更是援引堪舆学说来释“脉”:“吾尝谓成、弘大家,与王、唐诸公辈,假令今日而在,必不为当日之文。第其一种真血脉,如堪舆家所为正龙,有不随时受变者,其奇取之于机,其正取之于情,其实取之于事,其藻取之于辞。”[8]从制义文论的角度来进一步看,当 “脉” 被整合进 “法脉” 中时,其原初内涵亦被 “法脉” 所吸收。清初惠周惕曾说:“先辈论文既曰法,又曰脉。脉者何?生气也。人有脉而后荣卫有所灌输,地有脉而后山水有所凝结。”[9]该段论述对 “法脉” 中 “脉” 的阐释与传统文论中 “脉” 字的含义并无二致。李光地亦指出:“文字词气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眼人多不讲,其斗凑成文者,即有一段好处必不能通篇自圆其说,文中有一两句似无甚关系,却是他为文眼目,说话虽多,终须归到发明此句上,这是传下来的一点法脉。”[10]榕村亦是着眼于 “法脉”,对文章的主旨问题有所发明。文论材料颇多,以上兹援引五例,已能看出制义文论中的“脉” 是从一般性的文论术语处所挪用。当该字被整合进 “法脉” 一词时,其在传统文论层面的意义并未发生变异,均是表明文章主旨须一脉贯穿,不可枝蔓,最终使得全文充满生气。
“法脉” 中 “法” 依然与传统文论中的 “法” 密切相关。我国传统文论中由 “法” 字衍生出的章法、句法、字法等概念,也被制义文论家深度改造并加以使用,使之更适用于应试色彩浓厚的制义写作中,如赵吉士谈及制义时曾言:“所谓法者,规矩准绳之谓,而巧即寓乎其中……总之要活法,不要死法。法不一法,而实有一定之法,夫是之谓真法。”[11]该段论述实则沿袭了传统文论、诗论中关于“法” 的解释,这种法指的是一定之矩矱,同时也包含着充足的变动空间。总的来看,由于在传统文论中,“法”“脉” 二字本就具备着文章技法层面的含义,因而,当 “法”“脉” 在制义文论家手中被有意识地进行合流时,该种意义也被整合进 “法脉” 之中。
从历时的角度进行概念梳理时,我们探讨 “法脉” 的词义来源能充分解释 “法脉” 在文章技法层面的含义,但促使 “法脉” 的内在趋向复杂化的却是价值评判内涵的赋予。文论家结合明季制义文风的整体生态状况,由制义文风而反思文章技法,从而跳脱出文章技法的范围,转而探讨文章技法的价值。此时,“法脉” 的文章技法意味就被削弱甚至剥离,凸显出来的是价值指向的内涵。
关于 “法脉” 的价值评判,王夫之当为较早的探索者,他曾指出:
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特世所谓 “成、弘法脉” 者。法非法,脉非脉耳,夫谓之法者,如一王所制刑政之章,使人奉之,奉法者必有所受。吏受法于时王,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豫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12]。
细绎此节,王夫之其实是站在超越制义文法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他并未完全否定制义中的 “法脉”,而是要求学者从题目中寻求作文 “法脉” 之本原。稍后的陈龙正亦持有同样的看法:
谓以法脉成大家,何其隔与!于三者间得焉,于法脉合焉、离焉,亦足以不朽。无自得而斤斤法脉,法脉何物哉?文生于题,故符旨先之;文贵有用,故裨世道终之;总以自得为本,一自得而两者具在其中矣[13]。
陈龙正于文章开篇明确指出,制义为阐释经义之文,所谓 “经义之必传有三:一曰符圣贤之旨,二曰自得,三曰有裨于世道人心”。陈氏以这三点作为判断 “法脉” 价值的核心要素,认为明季制义局限于文章技法,距离因题立法、因题制义的先正制义相去甚远。
结合王、陈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二人实则是针对此时制义文风颓敝的状况进行议论。明季制义文法著作多若井喷,士子重文法而忽视经义原典,又重文法而刻意求新、求奇,以至于背离典雅纯粹的先正制义。如明季徐世溥指出:“万历季年,学者方厌苦拘牵法脉陋习,吾党兄弟乃力为古学以振之,天下翕然向风焉。”[14]此亦是明季制义文风不振的例证。
文章技法作为提高文章表现力的一条辅助途径,其正面价值无疑值得肯定。但只有与制义正体相联系,才能出奇而不离于正。例如,明季郑鄤指出:“夫法脉不善用则方而不圆。”[15]与此同时,左培亦点明:
元品,皆由浅入深,由宾及主,运局正大而不纤奇,议论浑成而无劈积,寓宽局于庄严,寄精味于淡漠,如众人争望高山而趋,我先登以览胜,彼喘而我定,如元气胚胎于亥,而四时生意浑然具备,识得此种法脉,便王、唐、汤、许,可与齐驱方轨[16]。
两人对 “法脉” 中的技法层面意义均持肯定态度。同时,也认为它具备一定的价值指向,指向以前朝大家制义为楷模的制义范式。该种认可的态度也存在于清人的论述中,例如,清初吕留良谈道:
陈大士先生文,人但惊其纵,不知其法脉细静处,是为老作家。凡一字人其手,必有两义,文即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有义,不犯合掌架屋之病,义虽多,局虽碎,而章法首尾有体,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气呵成,转转见妙,此皆古文正法[17]。
吕留良深入剖析了前明制义大家陈际泰的文章,虽然陈际泰凭借 “以古文为时文” 而知名,但吕氏依旧认为其制义颇具 “法脉”,由 “法脉” 体现出制义理想模型,无疑值得考生积极学习。
“法脉” 一词由具体的文学批评术语上升为一种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由于论者通过 “法脉” 建立起前辈与后人对制义的认同关系,进而塑造出制义正统的传承性。例如,康熙时陆陇其表示:“或疑将书中字面反复串插,此万历中年以来所谓法脉也。其法盛于宣城汤霍林,其弊也丝绪繁而大义鲜,不畅发题理,而专究题字。”[18]赵国麟评价清初韩菼制义时也指出:“文势忽起忽落,具离奇夭矫之观,而法脉又复丝毫不乱,真杰构也。”[19]“先生文稿,衣被天下三十余年,起衰振靡,允当首推。然究其所造,以配启、祯大家则有余,若追溯嘉、隆以前法脉,则会墨二义之外,指不再屈矣。”[19]论者通过认定后人制义继承前辈制义 “法脉” 的方式,使得后人制义得以比附前辈大家,其制义之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取其法,承其脉,在陆、赵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法脉” 二字既指向了制义写作的标准,更上升成为价值层面的象征。
总体来看,制义论者针对明季制义的庸陋貌袭之文,认为单纯研习文章技法不足以拯救此时趋于极端自由化的制义写作倾向。在此基础之上,应当学习先正法脉,前朝大家制义应当成为研习重点。“法脉” 发生了从文章技法论到价值指向论的转变,实则是从强调文章技法的 “文章法脉”,转移到强调价值指向的 “先正法脉”。
二、“天、崇” 无 “法脉”
明季制义文风与前朝的区别极大。截取明季该阶段来看,天、崇两朝制义文风颇具特点,如清初王步青谈到:“论明文者,于成、弘、正、嘉言理,隆、万言法,天、崇以才。”[20]康熙时华希闵则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他说:“高者谈成、弘,次者摹隆、万,独于启、祯诸家或以才情有余、理法未足而抑之。”[21]天、崇两朝制义以才而闻名,但较之前朝先正制义的理法充沛,则略显不足;如果从明代制义的整体发展来看,天、崇两朝制义与前朝先正制义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其整体风格是未能笃守规矩,出奇而未能守正。
具体来看,明末清初陈瑚说道:
洪、永、成、弘之间,皆以明理为主,而一篇之中,首尾正反虚实,莫不有法。正、嘉以降,小变其格,然不出绳墨之外。隆、万之末,文风颓敝,士习荒谬,叛违传注,溃决规矩[22]。
“隆、万之末” 也就是天、崇之始,陈氏点明,自洪武到万历,制义文其实皆有 “一定之法”。然而,天、崇制义的整体表现却是对前人定法进行猛烈的冲击。清初王介锡也对天、崇制义的文风进行抨击,他指出:“至天启、崇祯,去今不远,或子或史,奇正间出,而终流于杂。”[23]理学名臣陆陇其更是慨然感叹:“自明季以来,为文者亦可谓鬼怪百出矣。非反求之先正,何以正人心而作士气乎?先正之文,非濂、洛、关、闽之言勿敢言。”[18]稍后的纪昀也有高屋建瓴的论述:
成、弘、正、嘉之理法,真理法也。流而空疏庸陋、钞写讲章,则为伪。隆、万之机局,真机局也。流而纤仄吊轨、穿插斗巧,则为伪。天、崇之才学,真才学也。流而驰骋横议,亻面规破矩以为才,则才为伪;流而剽窃钞袭,饣豆饣丁凑合以为学,则学亦伪[24]。
撇开纪昀所谈的 “制义之伪” 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成、弘、正、嘉以制义理法出名,隆、万以制义机局闻名,二者皆有一定规律可循。天、崇则以显露才学而著称,因而此时制义中出现了杂用子、史的现象,更产生了崇尚骈文书写的 “云间派” 制义。这些都促使制义失去了 “一定之法”,也使得先正制义渐渐失去了其典范地位。以上三人的批评极为猛烈,他们均认为天、崇制义向着极端自由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不仅背弃了前人的制义正统,更违背了制义创制的初衷。
正是由于明季制义整体文风 “专于纵恣发越,而蕴蓄停涵之意少”[25],因而从 “法脉” 角度来看天启、崇祯两朝制义时,论者并不认为天启、崇祯两朝具备 “法脉” 特征,在此存在着评价的真空。论者将 “法脉” 比附于成化、弘治乃至万历朝,唯独撇开天启、崇祯两朝,其根本原因在于天、崇两朝的制义各立门户,唯才是骋,制义中却缺少了先正 “法脉”。而明季制义文论家将先正 “法脉” 拈出,其目的是强调其典范作用,更借此来针砭当时的颓敝文风。
在理论化的实际处理过程中,文论家将 “法脉” 与明朝相结合,使得其价值指向更为清晰,如 “成、弘法脉”“正、嘉遗法”“庆、历家法”“隆、万家法” 等。这些术语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风的变化有时候并不与帝王改元平行,流行的文风有时会跨越数个朝代;二是强调前朝制义作为正统的合法性。这些术语的诞生,均指向文论家心中一种理想的制义形态,也强调了制义正统的传承性。通过强调制义正统的传承性,更能将明制义的发展进行脉络化的清晰处理,为后人建构出制义典范。
首先来看 “成、弘法脉”。除却王夫之所谈到的“成、弘法脉”,该条术语还有一个变体——“成、弘家法”。康熙时陈鹏年谈道:“括帖于今日洵称极盛,亦极变矣。海内有心之士间亦喜谈成、弘家法,而先民矩矱,惜未能翕然复也……拟裒辑先正小题文,加之选择,以理淳脉正者为归。”[26]从陈氏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成、弘制义在清初人们心目中依然地位很高。同时,在陈氏心中,“成、弘法脉” 也是“理淳脉正” 的代名词。
其次看 “正、嘉遗法”。是说出自李兆洛,他谈道:“(吴耶谿) 为制艺文高雅,得正、嘉遗法。”[27]从此文前后来看,李氏是从古文角度来评价当时文。众所周知,正、嘉之时,制义文坛兴起 “以古文为时文” 之风,在行文中追求骈散结合,语言醇雅畅达。虽然此时行文规范有所变化,但依旧不离成、弘绳墨。又如方苞评点方舟制义时指出:“无首尾,无过渡,无承接,而细按之,乃循题位置,不失分寸。盖于正、嘉前辈法度之外,能自开一途径者。”[28]方苞也是从古文立场出发进行了高度评价,“正、嘉前辈法度” 所指向的便是明正、嘉时的制义轨范。
最后再看 “庆、历家法”。清初黄中坚指出:
余维帖括一道日新月异,而小题家之变态为尤甚。要其机法巧妙,至庆、历诸公而无以加矣……然余所望于汝者,初不欲汝仅至于是而已也,尚其亟自振拔焉,使人谓汝文实有庆、历家法,此则无负于余之心也夫[29]。
黄氏于该序文中盛赞庆、历家法,认为制义中的 “章法、股法、句法、字法以及提掇串插之巧,离合轻重之宜” 皆由庆、历家法所体现。事实上,该种论调在清初屡见不鲜,如清初黄越在编纂制义选集时,认为 “庆、历间文字股法细”,随后进一步指出其取舍倾向,他说道:“合庆、历法者存什之七八,近启、祯才气而不诡于庆、历法度者存什之二三。”[30]结合其选文数量,能看出黄越推崇隆、万制义更甚于启、祯制义。复次,康、雍间陆奎勋在盛赞他人时说道:“时艺能以庆、历法度行启、祯之才情。”[31]其言下之意,自然是以 “法度” 为第一义。学界一般认为隆、万时期,制义凭借文章技法而出名,行文更趋细密,文辞也更优美,正如王筠《教童子法》 中谈道:“法莫巧于隆、万。”[32]制义之法到隆、万之时达到鼎盛。因此,“庆、历家法” 的提出,一是要求学者重视制义中的章法、句法等,衷之以理,御之以法;二是也将隆庆、万历间制义视为学习之典范,当 “庆、历家法” 作为一种理论用语而提出时,就已经表明了论者对隆、万制义价值的肯定。
制义发展到明季,其写作朝着极端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先正法脉则未能深加接受并运用,因而导致明季制义整体上呈现出偏离正轨的状况,也使得文论家无法用 “法脉” 来合理地解释天、崇制义。当我们意识到,在当时文论家眼中,如何继承先正法脉、如何写作制义正体是他们思考的核心命题时,便能更好地把握此时文论家对明季制义的定位。明季制义文论家将先正 “法脉” 拈出,其目的不是解释天、崇制义的风格,而是强调前朝先正制义的典范作用,意图借此来打破当时的颓敝文风。
清初,“法脉” 则成为了建构清初制义文风的重要依据。清初制义文风的建构,既肯定、吸收了天、崇制义的部分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对明季制义进行了反思。例如清人极力推崇明季金声、陈际泰等大家,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制义大家能够拨乱反正,肯定了先正法脉的价值,将前朝大家制义作为学习的典范。
三、承接先正法脉:清初制义文风的建构逻辑
朝代改朔,新朝大都将前朝视为殷鉴。制义亦如此,清初树立开国法度,力矫此弊。从清初的制义评价体系来看,中央司衡与引领制义文风的民间文派,在制义持论中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双方均认为,从制义的文风角度来看,需要将清初与明季作切割。强烈的切割意识,既反映出清人对于改朔后文运的期待,也折射出清人对明季制义尚奇使才文风的不满。由于切割意识的存在,我们看到了清初与明季制义文风的极大不同。结合时人的论述,我们对二者的反差能有更为直观的了解。如康熙时杨绳武指出:
成、弘之文纯以理胜,而制格炼局法已具备,实为有明一代风气所由开。后人以朴率当之者,谬也。正、嘉而下,巨公林立,皆恪守成、弘之规,扩而张之。隆、万季年,稍变革矣。然其格律严整,针线绵密,又皆因题立制,并非率意穿插……启、祯之际,才人辈出,各自名家……国初诸公,文皆雄浑深厚,与启、祯相表里,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33]。
杨氏认为清初制义文风是在推倒明季积弊的基础上确立的,其文风的主要特点是 “雄浑深厚”,这种评论与明清人们对明代成、弘、正、嘉朝的制义评价是相近的。又如乾隆时郑虎文谈及制义时说道:“必取衷先正,以王、唐正其体,以震川茂其气,以思泉厚其力,而后濬巧于隆、万,搜奇于天、崇,升华于国初。”[34]郑氏也视王鏊、唐顺之等人的制义为制义正体,天、崇时制义则强调才情,文章趋于“奇” 而不趋于 “正”,明季制义文风直到清初时才得以改善。
清朝矫正天、崇以来的制义文风,是制义发展的必然之举。清初制义文风之所以与明季有很大不同,是因为在文风的建构过程中,对 “法脉” 的思考始终是在场的,也即 “法脉” 是清初制义写作、清初制义文风建立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明季与清初制义其实是似断裂而非断裂。从整体来看,明末清初的制义发展始终围绕着如何继承先正法脉、如何写作制义正体这一核心命题而变化。更细致地看,从制义发展的内在联系中来把握清初制义文风的因应变化时,可以发现:从 “法脉” 角度来看明季制义文风,明季文论家欲借 “法脉” 说来打破当时的颓敝文风;从 “法脉” 角度来看清初制义文风,清初论者则视 “法脉” 为制义写作的重要标准,从而主动继承先正法脉。同时,也正是从 “法脉” 的角度来看清初制义文风时,我们能更好地整体理解清初制义的不同风格。
清初制义名家众多,其中也不乏章金牧等尚奇使才的名家。如何把握清初制义的整体性文风?我们认为,一是审视代表性作家制义的特点,二是探查知名地域性制义文派之间的共通性。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主流也有浪花,如果将目光过多地放在浪花上,就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探求清初制义文风的整体性特征也是如此,从主流作家、作品中探求共通性,能使我们比较清晰地把握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探讨清初代表性作家的制义,以康熙年间俞长城的论述最为突出,他谈道:
文运之升,其体从正;文运之降,其体从偏。天顺以前,淳朴未开。成、弘、正、嘉四朝虽疏散浩瀚、离奇简淡,境各不同,无不归于正面。降而隆、万,正者什七,侧者什三。降而启、祯,正者什三,侧者什七。此有明一代之升降也。国初自己丑以来,返朴还淳。至于壬辰,名家林立[35]。
“侧” 者,奇也。该种论述流行于六朝,多指轻艳柔靡的文风。俞长城于该题解中指出有明制义文风以成、弘、正、嘉四朝为正,隆、万虽然崇尚机法,但符合制义轨范的正体依旧占据大多数。天、崇则愈变愈奇,远离正途,直到清朝顺治己丑(1649 年) 才返朴还淳。俞氏还指出:“己丑以来,上有名臣,下有巨儒,相为协赞,敛华就实,黜靡崇雅,才归于法,辞约于理。故数科之文,典则醇粹,有弘、正之风。”[36]在此,俞氏认为清初制义的特征是具备法、理,这也符合前明成、弘、正、嘉朝的制义特征。俞氏进一步将清初制义文风比附于前朝先正,这反映出他对制义正统之传承性的强调。
再进一步看,俞氏所说 “国初自己丑以来,返朴还淳”,实则指向以熊伯龙为代表的清初制义大家。在《题熊钟陵稿》 中,他谈道:“至于己丑,主司既执先正法律衡天下士。名公硕儒,起而应之。钟陵先生,较著者也。”“往时选家评论本朝传文,首推钟陵间及克猷,己丑以前勿道也。” 熊伯龙与其同乡刘子壮并列为清初制义之首,这样的看法实则为清人共识。如钱振伦也谈道:“国初文家虽难确指何人第一,而纪文达以熊、刘、李、韩为大家,自是定评。”[37]可见熊伯龙、刘子壮、李光地、韩菼等人在清初制义的地位是世人所公认的。正如江国霖所说:
本朝初,屏除天、崇险诡之习,而出以浑雄博大,蔚然见开国规模,如熊次侯、刘克猷、张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后益轨于正,而李厚庵、韩慕庐为之宗[38]。
清初最具代表性的制义大家非熊、刘、李、韩四人莫属,熊、刘制义被称作 “开国元音”,韩菼制义在清初影响深远,“天下从风”。如上文所指出,四人之文一扫明季积习,力求返归制义正体,其思想倾向无疑透露出浓厚的 “法脉” 意识。
同时,目光转向同时期的较为闻名的制义文派,虽然声誉未必能及上述四人,但从制义写作层面而论其实是并堪骖靳。清初文派虽多,实则以宜兴储氏、金坛王氏、桐城方氏最为显名,如李中简所说:“国朝一门文章,首推宜兴储氏,次金坛王氏。诸储以气格胜,诸王以法律胜,相唱若喁于然。又桐城三方氏之濶卓,皆同怀济美,骈枝交萼于制作之林。”[39]又如陈兆仑所说:“江左论文推三家,长洲韩氏与金坛王氏、宜兴储氏并列,类以文章通显。”[40]再如金武祥所谈论:“制艺兴而能文之彦恒钟于一族,以宜兴储氏、金坛王氏、桐城方氏为盛。”[41]三家的影响不落于李光地、韩菼等人之后,甚至到乾隆中期,翁方纲督学江西时,依旧有惋惜学者不能体会 “宜兴储氏以经术为文,而金坛王氏尽举看题窾郤”[42]之叹。
宜兴储氏由储氏家族以及宜兴地区其他文人组成,以储欣、储大文、储在文、储雄文等人为代表。对于宜兴储氏,当今学者已予以关注[43],其制义持论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当使时文、古文相济;二是认为要以先正为师法对象,制义应当 “原本儒书为真理,实恪宗先正真法脉”[44]。所谓的 “法脉”,从文章技法论的角度来看,便是要追求 “理精法密,词炼气昌”;从价值层面来看,则是指向以前明成、弘、正、嘉诸位制义名家为代表的制义正体。
金坛王氏以王汝骧、王步青为代表。王汝骧于制义推崇前明大家,曾辑有《明文治》。正如李中简所言 “诸王以法律胜”。翁方纲亦指出:“金坛王氏并以时艺名家,耘渠最善,其晚年续稿更有进。其法密而气醇,宜有以发其微妙之诣。”[45]断语简洁而中肯,点明了王汝骧个人制义的鲜明特色。王步青的制义推崇 “理”“法”“才”,他谈道:“论明文者,于成、弘、正、嘉言理,隆、万言法,天、崇以才,夫是三者,合之则美,离之则伤。”[20]他认为天、崇两朝依然有可效法之处,但就其文集、制义选集来看,其持论是具有偏向性的。王步青的制义更推崇古雅,谈及清初制义,他认为 “必义法为度,曲昭文体,以古雅为宗”,其对清初制义的定位,明显是要求上接前明成、弘、正、嘉四朝先正。其个人创作亦是如此,如储大文指出:“简而有法,汉阶之文之谓也。”[46]王氏对法的强调更甚于才,这也是清初制义家 “廓清摧陷” 意识的展现。
桐城方氏以方舟、方苞为代表,就制义而言,方舟不如方苞闻名。首先,如戴名世所说:“灵皋(方苞) 客游四方,其文多流传人间。百川(方舟)闭户穷居,深自晦匿,鲜有见其文者。”[47]其次,方舟年岁不永,方苞中年时奉旨修撰《钦定四书文》,故而后者影响更大。对于两人制义的特点,戴名世指出:“灵皋之文,雄浑奇杰,使千人皆废;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隽永深秀。” 两人制义虽然各有特色,但深入方氏兄弟为学历程来看,两人幼习古文,深谙古文之道,其制义亦是灌注了古文气韵,两人制义可从有明正、嘉两朝制义处找寻到历史渊源。如现代学者谈到方苞制义时指出:“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时文,颇有古文矩度,融化经籍子史,大多言有来历,一以经义为归,看似平淡,其实丰蕴,是时文的标准样本(正体)。”[48]方氏兄弟制义有所根源,两人承接起 “正、嘉遗法”,其制义师法对象正是明代正、嘉时的制义正体。总体来看,以上三家的制义风格或有不同,但在创作态度上都一致推崇先正法脉,其制义也表现出了与明季制义截然不同的风貌。
考察清初制义知名作家以及代表性文派,可以发现清初制义文风较之明季有极大不同。深入制义本身的发展逻辑,可以发现,对先正法脉的推重是促使文风转变的关键。“屏除天、崇之习”,推崇先正法脉,已经成为当时的群体性追求。清人对于先正大家的崇尚,对于制义正体的推崇,其实反映出“法脉” 作为一种重要价值判断,在清初制义文风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长时段的制义发展角度来看,明季制义过于强调才情,这使得制义文体本应具备的 “法脉” 特征被削弱,与前朝大家制义的联系也被削弱,致使明季制义出奇有余,守正不足。伴随着对明季制义文风的反思以及对如何继承先正法脉、如何写作制义正体这一核心命题的思考,清初无论官方、民间,均对先正制义持以推重的态度,试图重寻制义的“法脉” 特征,促使清初制义文风一返于正。通过对清初制义的代表性作家、文派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央司衡、地方性文派、民间选政等多方的合力之下,对先正法脉的价值推重也转化为实际的制义创作,最终使得清初制义文风表现出了与明季截然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