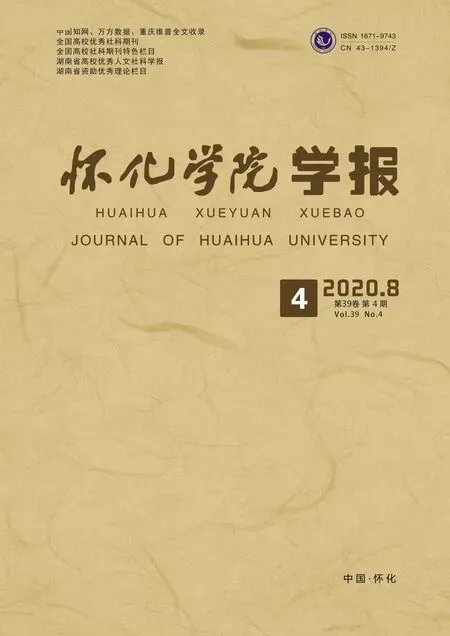从《上海的萤火虫》 看武田泰淳的上海体验
李庆保
(1.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 北京100083; 2.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合肥230036)
武田泰淳(1912—1976) 是一位具有特殊中国因缘的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他一生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中国经历。其中,1944 年6 月至1946 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武田泰淳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创作了大量的中国题材作品,日本战败前后的上海成了他众多作品的舞台。本文主要借助作家晚年的回忆性质作品《上海的萤火虫》,对他的战时上海体验进行梳理和解读,探讨多元交织的上海意象下,参与国策文化事业的经历给作家带来的内省与思考。
一、武田泰淳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武田泰淳,曾在1937 年11 月至1939 年9 月以一名侵华日军辎重兵的身份辗转于华中战场。从战场回国后,武田泰淳一直想再去一次中国。1944 年年初,北京和上海两地都向他发来了邀请。北京那边是土方定一①所就职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文化局。而介绍他去上海中日文化协会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仁小野忍②,具体接洽的是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林广吉③。收到了中日文化协会发来的说明月薪、身份等待遇的电报后,武田泰淳便决定去上海。1944 年5 月,他辞去了日本出版会文化局海外课的工作,准备去上海的行程。
当时,民间人士出国已经很困难,加上武田泰淳有参加左翼活动的前科,还在受监视中,得到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通过在大东亚省供职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仁增田涉④的斡旋,经过多方交涉,终于获得了以扬子江社特派员身份前往上海的出国许可。时隔六年多,武田泰淳再次在黄浦江登陆,开启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体验。
武田泰淳晚年的自传性质作品《上海的萤火虫》记录了他的这一段上海生活经历。 《上海的萤火虫》于1976 年2 月至9 月在杂志《海》 上连载,同年12 月,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单行本。全文由 “上海的萤火虫” (2 月号)、“出汗的墙壁” (4 月号)、“旋转的房间” (5 月号)、“后门” (6 月号)、“杂种” (7 月号)、“废园” (8 月号)、“歌” (9月号) 等七章构成。因为武田泰淳的离世,在剩下最后一回时连载中断。
武田泰淳以上海为舞台的作品数量不少,但是比较完整地反映他的上海体验,并且展现了日本当局在上海的所谓文化交流活动情形的,则是这部《上海的萤火虫》。遗憾的是,由于连载中断,作品只记录了到1945 年6 月为止的经历,自那之后至1946 年2 月回国之前的一段体验只能通过其他作品去解读了。但是,通过作品中对他在 “东方文化协会” (即中日文化协会) 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描写,基本可以窥见他的上海时代的中国体验。
二、上海体验与中日文化协会
从1944 年6 月至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武田泰淳就职于中日文化协会的上海分会。所谓中日文化协会,是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于1940 年7 月设立的附日文化机构,总会设在南京,在上海、广州、武汉、杭州等汪政权的势力范围设有分会或支会,理事长和常务理事由汪政府的要人担任。武田泰淳所任职的是位于上海的分会。根据分会的规程,上海分会是以 “协助南京总会,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在两国朝野感情融洽的同时,发扬东洋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的目的”⑤为宗旨[1]14,具体活动涉及文学、艺术、出版等方面。
中日文化协会明显具有日本的国策推进机构的性质,但是,当时聚集在上海分会的日本职员对当局的文化政策的态度却未必是完全倒向国策一边的。日本学者木田隆文在《上海1944—1945 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 注释》 一书的前言中指出:
不如说,那里是一个像泰淳那样的从国内闭塞的言论环境中逃出来的人、利用国策机构的便利来满足自身的文化欲求的人、或是借文化政策之名,实际是被这种远离正处在战争中的国内的享乐气氛所吸引而来的那些人的集合体,是一个通过各种活动互相争斗的日中文化的大坩埚[1]3-4。
确实,我们从《上海的萤火虫》 中也可以感受得到,中日双方的所谓文化工作者带着各自的目的来到被称为战争中的 “孤岛” 的上海,通过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各种所谓文化交流活动,享受着国际都市特有的自由氛围。林广吉对上海分会的评价是,不但与 “将当今日本所拥有的,业已达到并且还要超过世界级水准的崇高的日本文化无条件地引入中国” 这一日方当初的意图相距甚远,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 “杂乱无章的网罗”,“两国的文化上的理解一步都没有前进”[1]14-15。
当时在上海的很多机构里都有原左翼人士,光上海分会内部,除武田泰淳自己外,常务理事林广吉、会计处长横田正雄、小说家石上玄一郎⑥等都有过左翼经历。武田泰淳就是在这个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一直工作到日本战败。他当时担任协会所属的东方文化编译馆的出版部主任,负责汉译日语书籍的出版事务。
三、从《上海的萤火虫》 看武田泰淳的上海体验
1944 年6 月9 日,冒着鱼雷攻击的危险,迂回行驶了近十天,武田泰淳所乘坐的船终于抵达了黄浦江码头。1937 年11 月,武田泰淳曾作为一名士兵驻扎在上海南市中山医院的卫生材料厂,现在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再次来到上海这座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最大的城市,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都市风貌:
穿过外白渡桥,沿河耸立着一排庄严的建筑物。欧式风格的银行、商社、机关大楼、报社、酒店等都挺起胸膛,并肩整齐地排列着,像城墙一样迎面吹着河风。那就是所谓的外滩。……本来是来到了中国,却感觉进入了另一个异国的街道[1]14。
选择中国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希望尽量多地接触中国文化的武田泰淳,看到这样的上海,未免有点遗憾吧。
上海分会的事务所设在原法租界亚尔培路的一栋三层花园别墅里(现陕西南路30 号衡山马勒别墅饭店),这是日军占领租界后从一位英国籍犹太富商手里强行接收的 “敌产”。事务所在三楼,一楼和二楼是 “日华俱乐部”。当时上海分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林广吉,陶晶孙任分会总干事,小说家石上玄一郎也在同一事务所,从事舞蹈、音乐等艺术方面的交流工作。
刚刚登陆上海的武田泰淳,“一点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总觉得那里一定有一种与日本国内不一样的自由”[1]10,而且,“在林荫道下走过时,我感到被一种在东京从未体味过的静谧所包围”[1]19。
这就是武田泰淳刚到上海时的感受。对于有过“转向” 经历的他来说,比起思想、言论控制越来越严格的国内,对上海的 “自由” 的期待是很自然的事。在日本国内,从1944 年春开始,战局迅速变得紧张,本土空袭也更加激烈,而且加强了粮食统制。与这样的国内情况相比,上海的 “正宗的、松软的、油放得足足的炒面,给我一种解放感”[1]10。
在这样久违的 “解放感” 与 “满腹感” 中,武田泰淳开始了他的上海体验。
关于武田泰淳再次来上海的原因,埴谷雄高编的武田泰淳年谱中称他是 “带有逃避征兵的意味前往上海,就职于中日文化协会”[2]600。但是,武田泰淳在《上海的萤火虫》 中是这样说的:“总之,只要居住在上海的话,好像就不会有突然收到征兵令的情况。当然,我并不是为了逃避征兵而来到上海的。”[1]43武田泰淳对逃避征兵的说法予以了否定。
如前所述,大桥毅彦等编的《上海1944—1945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 注释》 中称武田泰淳是为了逃避日本国内闭塞的言论状况而来到上海的。《上海的萤火虫》 中提到他在出发前的送别会上放声演唱了一首名为《看,降落伞!》 的歌,说 “那一定是因为长久的愿望实现的喜悦和心情激动所致”[1]42。另外,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些表述:
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我来说,来到中国人中间和他们一起生活是再高兴不过了。并且希望时间能够长一些[1]42-43。
我准备尽量在这不长的时间之内,吃一吃上海人所吃的东西,走一走他们所走的地方,看一看所有能看到的东西,融入到上海的喧嚣当中[1]43。
必须尽可能地与上海的中国人交往,触摸他们心灵的深处[1]63。
这些都是一个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的真实想法,也间接说明了武田泰淳来中国的目的。以上文字也涉及他所关心的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他曾经在战场上所写的《土民的表情》 和《有关中国文化的一封信》 中都提到过文化研究的问题,在《上海的萤火虫》 中再次论及:
但凡中国人,不问男女,我都想认识。要了解中国,总之,就是从这种简单的事情开始。光是出入于大学那昏暗的研究室或严肃的研究所的书库,是感受不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情感的。东京大学的教授和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作为学者,我是信得过的。但是,在他们讲课或做研究的同时,在另一个地方,事态正在向前发展。他们孤独地埋头于研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一定会取得了不起的成果吧。不过我想,仅仅如此的话会很无聊[1]163。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武田泰淳对于中国研究的方法的思考是不同于传统的,主张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实地调查来进行中国研究。这是他从战场回国后一直想再来中国的主要原因。加上日本国内越来越严酷的言论环境,共同促使他再次来到了中国。
当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开始出现战败的迹象,不管左翼右翼,作家文人们都被动员起来。在中日文化协会周围就有不少是脱离左翼的人士。“日本文学报国会”“国际文化振兴会” 等机构不断派来 “文化使节”,进行所谓中日文化交流。很多日本的作家、画家、作曲家以及歌手等避开危险的海上路线而绕道北方来到上海。每当这时,武田泰淳就得充当服务生来接待这些来客,比起翻译书籍的出版工作,更多时间是在忙于接待工作。从《上海的萤火虫》 的叙述来看,光是接待的文学家就有佐藤俊子、漥川鹤次郎、小林秀雄、高见顺、长与善郎、火野苇平等。
他总是和石上玄一郎一起,将来客领到餐馆饭店,招待他们吃上海菜,喝中国酒,有时还会陪他们去市里参观或去附近的苏州游览。他甚至推测“这些文学家们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是想吃正宗的中国料理吧”[1]68。
武田泰淳本来也是个好酒的人,而且每喝必醉。他在《上海的萤火虫》 中写到自己喝醉酒后的特殊癖好:“我喝醉的样子与众不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一醉酒,我必然就想要登高。从椅子上爬到桌子上,再从桌子上爬到橱柜上,而且还大声说话。”[1]71-72而且,只要被周围的人一怂恿,他就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战场经历。从这里看来,武田泰淳似乎是大大咧咧的性格,甚至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在上海期间,他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喝醉了的武田泰淳会摆出端枪的姿势,给人讲他的开枪经历和血腥的战争场面。当时,他们所处的上海属于安全地带,不用担心子弹的威胁,粮食储备也很充足。从餐馆中那些有钱的上海居民的欢闹声中,感觉不出一点儿战争的气氛。可是,一旦走出上海,所到之处都严重缺粮。所以,上海人留在了上海,即使讨厌日本人,他们还是会通过与日本人交往来维持生计。作为一个旁观者,武田泰淳认为上海人是不幸的。他认为,“上海人真正的不幸,在于唯独他们自己可以远离全中国人所陷入的悲惨状态”[1]74。
1944 年11 月12 日至14 日,由 “日本文学报国会” 策划组织的第三届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在南京召开。大会给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石上玄一郎和小竹文夫发了邀请。小竹文夫不想去,让武田泰淳代为赴会。按照武田泰淳的说法,当时不少人是反对这个所谓的大会的,即便不反对,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武田泰淳没有办法,只好和石上玄一郎一起去了南京,和同样来自上海的佐藤俊子、池田克己一起作为 “大会来宾” 参加了会议。按照武田泰淳的话说,“因为我并没有参会的资格,只当享受一次假期了”。在南京期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是一位 “从北京来的诗人”,“虽然身份是大东亚省的职员,却是一个让人完全感觉不到战时的紧张状态的性格慢悠悠的男人”[1]115。据此推测,此人应该是同样以 “来宾” 身份赴会的土方定一。
大会前一天,传来了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的医院病亡的消息。对于这个作为叛国者将要永远背上汉奸骂名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武田泰淳有自己的看法:
我喜欢汪主席。他青年时代曾在大桥下安装炸弹,试图暗杀清政府的大官,是个勇敢的人。……就爱国心来说,他与抗战一方的人是没有丝毫区别的。总之,他是诚实的。他没有为贪图私利而挣扎。他热爱着祖国。比起此刻旅馆房间中,一蹲一立于厕所内外的日本的貌似文学者之辈,他是个出色得多的男人[1]116。
关于汪精卫的历史评价,这里暂且不论。武田泰淳在这里其实是要借汪精卫来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受日本当局支配的、成为日军占领政策助威者的懦弱的日本文人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作为转向者的悲哀和屈辱感。
按照《上海的萤火虫》 的记述,武田泰淳在上海分会担任了一年的出版部主任,期间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小泉八云的《一个日本女人的日记》,另一本是日本的一位自然科学家写的面向儿童的读物《我们的日常科学》,都是薄薄的小册子,与所谓的 “国策” 并不相符。原先设定的显示 “宣扬国威”“思想善导” 成果的目标也没能达到。
武田泰淳一年多看起来热闹而舒服的中日文化协会的生活,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结束了。他随后和其他日本人一样被收容到虹口的日侨集中区,开始了俘虏管理所的生活。从那时开始,他一边为日本侨民们代写文书,一边开始正式阅读《圣经》。他用代写文书挣来的钱买中国的酒喝,吃油腻的中华料理,还购买了中国的书籍杂志准备带回日本。
在中国迎来日本战败的武田泰淳,体验到了一种灭亡的感觉和精神的虚脱。他用廉价的酒菜来追求一时的 “满腹感”,“就像没有感觉的人偶,……没有耻辱,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块活着的看板。”[3]54-55在战后的上海,武田泰淳在幻灭感与罪恶感中承受着煎熬,直至1946 年2 月乘坐日侨遣返船 “高砂丸” 号离开了中国。
四、结语
本文对日本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的战时上海生活经历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1940 年代的上海作为战争中的孤岛,成为很多日本作家、文人逃离国内日益紧张和压抑的高压氛围的避难所。在这个中国、西洋和日本元素相互交织的世界里,他在参与占领当局的国策 “文化交流” 的同时,也在完成作为一个日本文人的内在思考和审视。这种多重交织的上海意象,也体现在武田泰淳后来以上海为舞台的多篇作品当中。上海经历、战败体验以及更早前的战场经历,成为作家武田泰淳思想和创作的原点。
战后,武田泰淳又分别于1961 年、1964 年和1967 年作为文学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中国各地进行访问,并与中国作家进行交流。这几次来华都分别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但对于60 年代的上海却没有多少描述。相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对30年前生活过的上海进行了细致的回顾。可见,这段上海生活经历不仅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他一生都无法割裂的中国因缘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土方定一(1904—1980),岐阜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战时曾任职兴亚院。
②小野忍(1906—1980),广岛县人,出生于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战争中曾任职于满铁调查部、民族研究所,战后任东京大学教授。
③林广吉(1898—1971),长野县人,明治大学毕业,1941 年来上海,参与创建“上海市政研究会”,1943 年10 月起,任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成为后期上海分会的实际负责人。
④增田涉(1903—1977),岛根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1931 年赴上海跟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1935 年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1937 年参与翻译《大鲁迅全集》,战后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教授。
⑤文中涉及的日文引文均为笔者翻译。
⑥石上玄一郎(1910—2009),岩手县人,出生于北海道札幌,小说家,高中起参加左翼运动,一度被捕,后专注于文学,1944 年4 月赴上海,1947 年1 月回国。代表作品有《绿地带》《精神病学教室》《黄金分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