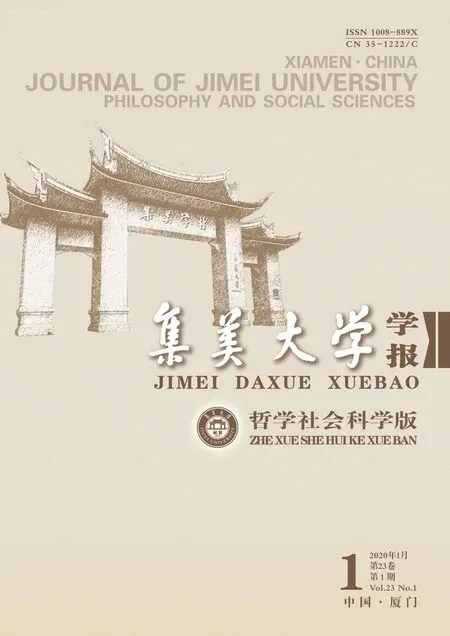“海洋国家”理念形成与华侨研究在近代兴起
陈绪石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2)
华侨研究在近代中国兴起,梁启超是第一人,在学界这应该是共识,如李安山指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光绪三十一年发表于《新民丛报》63期上,后以单行本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华侨研究的开始。”[1]1000再如,庄国土以为:“中国研究华侨事务的先驱者或可推梁启超先生。”[2]52但就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的起因和梁启超为何能成为华侨研究的第一人,则涉及不多,笔者主要从“海洋国家”理念角度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近代以前的华侨是被忽视的边缘群体
中华民族在古代重陆轻海,这是基本倾向,另一方面,移居海外的华侨并不少。侨居海外主要有三种类型:(1)受官方委派、担当一定使命的官员,如《史记》上所记载的徐福,他东渡日本以寻觅海外仙山。(2)逃避政治上的打击而亡命于海外的前朝移民,如蒙古灭宋,不少宋人定居东南亚。(3)东南沿海民众出海讨生活,他们是海外华人的主体。从海洋角度看,第一类中国海外移民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他们是古代中国人海外想象的产物,古人对海洋有误见,以为蓬莱山上有神仙居住,所以徐福奉命出海寻觅神仙,目的是满足秦始皇长生不死愿望。徐福最终的落脚点何在?目前无定论,所以,这个问题不好作进一步阐述。第二种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民,他们是政治避难群体。至于第三类,沿海民众出没海上,“帆船时代,中国海洋船上社会群体大致有:①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疍民;②以运输为生的船户、水手;③以经营海洋贸易为生的海商;④以海上抢劫为生的海盗;⑤以海上巡防和作战为职责的舟帅(水军、水师)。这里,着重讨论与早期海外华人来源有关的海商、海盗及船户、水手。”[3]这说明,从群体构成看,古代中国的华侨主要有海商、海盗、船户等,他们从陆地伸展到海外,在重陆轻海的古代,这属另类现象。从史书上看,定居在海外的沿海边民不是小数目,以明朝为例,在吕宋(菲律宾)一地,“闽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4]8370居住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数量堪称庞大,似乎商贩的人数居多,经商有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起而为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4]8409明清期间在东南亚雄霸一方的中国人不止梁道明,遗憾的是,这些海外割据政权很快衰败,原因甚多:它们遭遇西方劲敌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没有得到大陆中央政权的支持或甚至遭到中国皇权的压挤、打击;政权的建立者和支持者均出自沿海民间,整体素质不高。以上所论表明,古代中国人移民海外是常见现象,但与西方海洋国家的移民相比,中国人的整体表现黯淡。
古代南洋华侨数量不少,因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太平洋,沿海民间的经济有外向性。东亚大陆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所以,沿海中国人通过海道移居海外实为正常的人类活动。由于南洋的岛屿众多,且是中西文明交流的孔道,因此,古代沿海之民若移居的话就多集聚在东南亚。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处于东亚大陆,这里地域广大、土地肥沃,所以古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包容性和弹性,允许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在传统农业的大框架下,保留地方的经济特色,沿海地区因而存在海洋性的小传统。事实上,中国古代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始终没有被割断,只是表现时强时弱而已。”[5]也就是说,沿海民间向海上拓展的小传统在有的时段发展势头强劲,在有的时期,因中央王朝禁海,其空间被挤压,一旦海禁松懈或被取消,华侨人口迅速增多,海洋文化小传统就得以迅猛发展。“从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6]史书上的实例和数据证实了该观点,比如,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旅居在吕宋的华侨两万余人,“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4]8373华商的海洋商贸逐利心之强烈由此可见,他们飞蛾扑火一般涌向南洋,建构了一种在本质上与大陆农业文明不同的海洋商贸文明,但是,海洋商贸在中国毕竟是边缘性文明,而且华侨遭到西方殖民者打压,所以,南洋华商可谓在夹缝中寻求突围,实属不易。
综上文所论,与东亚大陆上的中华农业文明相比,沿海民间的海洋商贸文明在古代中国是次要文明,呈现局部性和民间性特征,亦被农业文明挤压,这就意味着,古代华侨是处于边缘的群体,他们往往是天朝“弃民”。宋元鼓励海商从事海外贸易,朝廷贪图的是税收,并不在意海外拓展,也由于中华农业文明在其鼎盛期,宋元时期的东亚和南亚海外华商基本不存在需要保护的问题,因此,华侨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不在政府的过问范围内。与宋元相比,明清王朝实则试图从海上退缩,但西方的大航海改变了世界进程,在全球化潮流中,当海禁松弛下来,中晚明至晚清以前,中国的在海外侨民人口未减反增。对中央集权的大陆王朝来说,由海商、海盗和政治难民等构成的庞大海外华人群体通常是麻烦,“‘逃民’、‘罪民’和‘潜在的汉奸’这些形象,与对商贸的传统偏见一起,构成了明代对海外华人敌视政策的基础。”[7]14这种说法很全面,首先明王朝以农耕立国,他们必然轻视海商,海盗的出没则进一步强化了明王朝禁海的决心,因此,海外华人是遭弃的边缘群体。试举一例。万历帝在阎应龙、张嶷的怂恿下准奏在吕宋开掘金矿,大臣纷纷劝谏,理由是:“昔年倭患,正缘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设计勒价,致倭贼愤恨,称兵犯顺。今以朝命行之,害当弥大。及乎兵连祸结,诸奸且效汪直、曾一本辈故智,负海称王,拥兵列寨,近可以规重利,远不失为尉佗。于诸亡命之计得矣,如国家大患何!乞急置于理,用消祸本。”[4]8372姑且不论菲律宾的机易山是否有金银可开采,从其性质看,阎应龙、张嶷的提议无非是经略海外之倡议,但儒家士大夫从守护大陆农业文明出发,将他们定位为奸民,并以为他们类似于汪直。士大夫无视史实,海盗汪直的出现与明王朝的海禁有一定关联,他们的上纲上线反映该群体鄙视海上经略的华商。因机易山事件,后来华人被大量屠杀,万历的回应是:“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4]8373明朝廷财政紧张,万历同意在吕宋开矿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不料此举却桶了大篓子,办事者张嶷被严惩表明,皇帝根本就无海外经略的意图,有名无实的罪檄无力震慑西班牙人,海外华侨得不到有效保护。大清朝继承明朝衣钵,对华侨鄙弃有加,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杀戮华人,乾隆得知后以为华人的惨剧是咎由自取。从不大过问到遭弃置,海外华人的地位低下,毫无疑问,只要天朝上国仍固守东亚大陆、守护大陆农业文明,朝廷就会视他们为草芥。
华侨在古代中国是边缘群体,反之,如果上层将国家发展的触角伸向海外、儒家士大夫致力于海上经略,那么勇于在海外实现人生价值的华人就是国家堪为大用的人才。状况的改变需要外力,因为东亚大陆够辽阔、中华农业文明很灿烂、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厚重,内部力量推动的转型难以发生。“大航海”力促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西方海洋文明在近代强势叩击国门,大变局在上演,华侨在国事中不再是沉默者,华侨问题由边缘进入舞台的中心。
二、华侨地位的提高和“海洋国家”理念的形成
华侨地位在近代有显著提升,这是在中西文明冲突背景下发生的。西方的海上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于明朝始就在经营南洋,虽然它们也曾试图打开明清王朝的国门,但收效不大。中西的冲撞基本出现在南洋,南洋华侨往往是西方殖民者屠杀的对象。然而,东南亚是朝廷并不重视的地域,中国统治者不会同情华侨的悲惨境遇。近代工业革命提高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品质,英国跃升为海上帝国,以英吉利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势登陆中国,晚清朝廷节节败退,中西文明的冲撞日益频繁,清王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成为日常外交事务,华侨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他们不再是“天朝上国”的弃民而是需保护的民众。
就晚清政府对华侨的保护,澳大利亚学者颜清煌有突出的研究成果。(1)他以为晚清政府对华侨华人做了力所能及的保护,与西方殖民者交涉海外华工的待遇问题是新起点。(2)他研究了大清朝态度转变的原因,如华工受虐损害了朝廷的形象、尊严等,同时,士大夫在其中的作用也被充分认识,“清政府对保护海外华人的态度大变。这一变化主要是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呼吁以及古巴调查团影响的结果。丁日昌便是这些官员中的一个,他显得对海外华人十分了解,并认识到利用他们可使中国得到好处”[7]149。(3)他研究晚清政府和官员在华侨保护方面作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问题。就上面所述的几方面,论者认为,清政府一改往日作风、重视华侨问题,这还须作进一步研究。如果在文明冲撞语境下综合研究清朝廷的转变,研究或许更深入、到位。在中西冲突背景下,中国溃败,所以,晚清政府才不得不与西方各国有外交关系,西方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刺激清朝廷,高层因而有意关心海外华人,再加上具海外工作经验的官员在推波助澜,华侨的“弃民”地位遂成为历史。
华侨地位的提高是近代华侨研究的先决条件,该群体成为研究对象,还需要其他前提。传统士大夫没有兴趣研究“弃民”,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农业文明精英,视海外旅居中国人为不务正业的不安分之徒。反之,若华侨的海外发展得到认可,他们可进入近代学者的研究视野。不过,华侨研究既需要民族主义热情,它也是一种理性的学术活动,如果学术探究潜入深层次,特定的学术语境和理论必不可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就是关键要素。
海洋国家是与大陆国家相对的学术概念,近代士大夫对它们做过学术界定。梁启超在《郑和传》《地理与年代》等作品里明确指出中国是大陆国家并从地理学角度阐述了理由,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诗文里,他认为活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等是海洋国家。海国、陆国一说非始自梁启超,近代中国被西方海上强国的力量所震慑,士大夫一直在探索海洋强国之路,魏源在《海国图志》就已初步提出该学说,“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8]鉴于晚清不断地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的冲击,加之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在士大夫已有的海国与陆国看法基础上,梁启超对两种类型的国家作了明晰的概念界定。综观梁启超等人的论述,笔者以为:中国作为大陆国家,(1)重陆轻海;(2)朝廷无意于海外扩张;(3)政府非但不扶持沿海民间的海外拓殖,还常常打压民间的海洋行为;(4)国家没有制海权。西方海国则相反:(1)海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翼;(2)国民勇于在海上冒险;(3)政府支持本国在海外的侨民;(4)近代以来的海国借助侨民之力谋求国家的海上权力。因此,民间与政府一致发力,视海洋为国家经略的重要场域,临海国家才是海洋国家。
海权对海洋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自大航海以来这是一个日益突出的主题。古希腊的许多城邦和古罗马是海洋国家,它们重视制海权,但是没有领海权意识,海权观念的全面形成不早于中世纪。“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国对土地的排他性领有权开始向海洋方面发展。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航海力量,对一些海域提出了权利主张。当时欧洲主要的沿海国家都相信,它们能够将自己的主权主张推广到公海的某些部分”。[9]根据此说推断,随着欧洲人在海上向全球扩张,海权意识也扩散至全球的许多地方,同时,海权观的含义日渐丰富,制海权、领海权、航路权等均是重要的组成。所以,单从海权角度看,海洋国家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在早期,地中海沿岸的海洋国家重视对海洋的控制,但不占有,近代以来,随着领海权观念的兴起,海洋成为海洋国家主权的历史在西方拉开大幕。近代中国的海权诉求始自魏源,他的海权意识还不够明晰,从国家主权角度全面论析海权的人是梁启超,因此,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国家的想法成熟于1900年前后。
近代中国人“海洋国家”理念之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重陆轻海的大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批有卓见的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他们无一例外地关注海上问题,魏源思想堪为代表。魏源所论涉及晚清海军建设、海上运输和贸易等问题,《海国图志》借鉴西方海国之长、推动中国向海上拓展的意图明显。魏源的海权意识初步觉醒,但他的思想非常复杂,他持有中国是天下中心的论调,并没有明确的打造中国为海国之理念,因此,“海国”方案是先锋魏源的模糊理想。近代中国人明晰的“海洋国家”理念生成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中国近邻岛国,它学习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也是一个封闭的农耕国家,在受西方海国欺侮之后,日本开启脱亚入欧历程。明治维新彻底改变了日本,其意义之一是:“它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0]日本发生巨变,如果从文明形态角度界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一个开放的海洋商贸国家。(1)儒家道统被西方启蒙主义取代,重商主义在日本形成。海洋商贸与大陆农耕是不同的文明,与儒家的重农抑商不同,勇闯海洋往往意味着海外贸易逐利,日本在近代确立富民强国之策,就是建立了新的海上谋利观念。(2)日本引进海洋学统,譬如,《海国图志》曾在中国遭受冷遇,日本人犹如久旱喜逢甘霖。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最有感受,“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11]324日本人最善于接受海洋方面的新知识,除了《海国图志》,《海权论》等也先在日本出版,它们是日本国家权力朝海上发展的教科书。(3)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具有强烈的海外扩张性。这个长期被“天朝大国”鄙视的小国战胜了大清国,中国人的尊严瞬间消失殆尽,认识、学习日本在近代中国成为风潮。近代中国人在甲午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海洋具有重要地位,但上层决策者通常以为以西方舰炮武装一支海军就足以保卫政权的安全,原因在于:“封建君主由于有稳定的土地收益,本身对海洋经济不感兴趣,甚至视其为专制皇权的洪水猛兽,因此缺乏发展海军的内在需求和动力。”[12]此说略有夸大,不过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为何难以像日本一样彻底转型,因为国家向海上发展的阻力太大。从借鉴、学习日本成为一时潮流来看,甲午之败促使朝廷和士大夫重新审视海洋与国家的关系,近代中国的革新向深度推进。
甲午战败促使近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变革国家的强烈内在冲动,而马汉的《海权论》则为他们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景,明晰的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在晚清民初形成。近代中国人在1900年前后接受《海权论》,途径有二:(1)《海权论》于1896年在日本出版,在日本学习、工作或流亡的中国人有机会阅读该著作;(2)在1900年之后《海权论》传入中国,更多的中国人受其影响。因为西方海国以及得西方真传的日本屡次击败大清朝,近代中国人丢失了农耕文化自信心,他们乐于接纳《海权论》。这本著作总结近代英国成为海上帝国的历史经验,目的是鼓动美国实施海上霸权战略,所以,马汉在著作中阐述了构成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六大要素:(1)地理位置;(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3)领土范围;(4)人口数量;(5)民众特征;(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13]29《海权论》其实就是一个建设“海洋国家”的路线图,应该说,在晚清民国,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将这种理论奉若神明,如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东方杂志》《海军杂志》《海军建设》里,不少中国人讨论如何建设强大海军以助力中国向海上拓展的问题。因此,接受《海权论》的一个重大意义是,非常多的士人和知识分子如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有了明确的海权观念,孙中山还有清晰的中国海权建设构想,统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理念形成。世纪之交的梁启超的海权思想最丰富,有一定深度,康有为不能与之相比;在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有《清议报》《新民晚报》,发表了不少畅论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文章,影响了孙中山、陈独秀,在“海洋国家”理念的形成中,梁最有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中西文明冲突背景下,华侨的地位逐步上升,同时,冲撞中的惨败也促使近代部分国人有了学习西方海国的想法,《海权论》是“海洋国家”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该理念的持有意味着华侨研究的条件完全具备。
“海洋国家”理念的形成之所以至关重要,在于海洋国家的海上经略需要民间力量,国民的海上拓展意愿是“海洋国家”的必备要素,对中国而言,华侨是民间的海外力量,所以,在“海洋国家”理念视野下,近代中国的海外侨民是备受关注的对象,相关研究兴起。马汉以为,西方绝大多数海洋国家规律性特征之一是国民须具有海上冒险的精神、经商致富的欲望和开拓殖民地的能力[13]50-58,这就意味着,一旦近代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有了“海洋国家”理念,而他本人具备研究条件与能力的话,那么,他极其有可能在该理念的驱动下研究华侨。梁启超有明晰的“海洋国家”理念,是晚清民初使命感强烈的文化巨人,也有很多机会接触、调研华侨,他的条件佳、能力强,在近代中国的华侨研究兴起之时,他是最有成就的研究者,其突出的学术地位有待于揭示。
三、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第一人
学术意义上的华侨研究始于晚清,一些讨论华侨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以为,西方殖民者的南洋华人研究为开山之作。有学者指出:“对华侨事务的学理性研究,可说肇始于南洋殖民政府的官员。较早时期,殖民南洋的荷属东印度政府为更有效地统治华侨,培养了第一批研究南洋华侨的专家。巴达维亚法院的高级翻译施莱格(G.Schlegel)在1866年出版了第一部研究华侨秘密会社的专著《天地会 》。1885年,另一位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翻译的高延(DeGroot)博士,完成了研究专著 《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19世纪末以后,英、美等国学者亦相继有研究华侨事务的专著问世。”[2]52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尽管明清期间确实有不少记述华侨的文章、著作,但它们仅有史料价值,学理性并不强。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及日本学者的海外华人研究,有的学者给予较高的评价,“西方学者的著述,重视从个别区域或国家入手,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理论,对海外华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诸如华侨社会结构、华人同化意识、秘密会党、华人信仰、华人教育、华人经济等方面,无一不纳入其研究课题之内,形成风格各异、内容充实的著述,覆盖了华侨华人社会的各个方面”。[14]西方学者的研究有较高学术水平,这无疑与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近代士大夫的学术理论与视野则受限。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兴趣研究华侨,其目的是服务于各国的殖民统治。
与外国学者华侨研究的服务于各国的海外殖民统治不同,士大夫的华侨研究基于中国问题,目的是推进中国向海外拓展,所以,近代士大夫的华侨研究才是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的起点。
晚清的中国士大夫关心海外华人华侨,他们的研究缘起固然是晚清朝廷不再将该群体视为“弃民”,实际上,如综合考察该问题,就会发现梁启超持有民族国家意识,这是研究华侨问题的重要前提。梁启超是士大夫,又是转变自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他有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他有关注海外华人问题的持久热心。早在1899年,他就写有《爱国论》以阐述模糊的爱国主义,由于在日本广为接纳西方学说,梁启超自觉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成,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里说:“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1]887这里姑且不论民族国家意识推动梁启超致力于打造一个现代中国,单论梁启超对他所接触的日本、北美、南洋等地华侨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爱之心,由于身处海外前后共计超过15年,梁启超所著广为涉及中国的各处海外侨民。梁以前的士大夫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民族主义感情和意识,就难有研究华侨华人的原动力。所以,梁启超之所以是近代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开创者,他个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功不可没。而且,从国家层面看华侨问题,研究更有高度和学术价值,就此而言,梁启超当是学术先驱。
梁启超有非常鲜明的“海洋国家”理念。由于甲午海战大清惨败于新兴海洋国家日本,加上《马关条约》的签订,借鉴日本的海洋兴国之路是近代士大夫的共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也不能免俗,他甚至比其他中国人更强烈地渴望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因而在《海权论》的启发下,梁启超有了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国家”的理念。梁启超在多篇文章里阐述过近代中国的“海洋国家”理念,《新大陆游记》则是综论之作,他从海军、海权、海洋贸易、海底电报等角度阐述了海洋新霸主美国的崛起,在警惕美国霸权之余,又渴望中国像美国一样利用太平洋、掌控太平洋,成为太平洋主人翁。因此,自魏源始,近代士大夫模糊的“海洋国家”理念在穿越李鸿章、黄遵宪等之后,在梁启超手里升华,变得十分明晰。
基于民族国家意识梁启超一直关注华侨问题,“海洋国家”理念更是他研究华侨问题的重要驱动力。梁启超有建设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却没有直接说过,因为有该理念,所以,他着手研究华侨问题,但二者间的关系在他的文章里有清晰可见的痕迹。作为民族主义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1899年著文如《爱国论》《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等研究海外中国侨民问题,十几年间,他一直关注华侨的生活、生存状况并探讨之;1918年他出游欧洲,途径南洋,华侨仍是他研究的对象。从梁启超关涉华侨问题的20多篇文章看,专论的著述不多,有《记华工禁约》《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这类论文自有其重要价值,非专论的附带论述也有一定意义,如《夏威夷游记》《新大陆游记》等。有人指出:“梁启超对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外交,还是历史、社会、经济问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15]最大的现实性是,推动中国向海上发展的理念驱使他研究华侨问题。梁启超的华侨研究并非就事论事,通常在国家的高度上,多与西方海洋国家的侨民对比中进行,下文略举两例分析。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研究华侨和大英帝国侨民,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新大陆成功殖民,建立美利坚新国,华侨在新大陆是没有希望的大陆乡土族民,尽管梁启超没有明确指出,但仍不难发现:对比一是批判近代华侨的缺陷,二是指出华侨没有殖民能力,该群体无助于中国成为英吉利式的海洋国家。再如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梁启超赞扬闽粤先民勇在海外殖民,指出:“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则彼两省人,其犹可用也。”[11]1368近代以来,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大都是海洋国家,中国向海外扩张是梁启超的理想,同时他在文章里还以海权发达的美国作为比较对象,这说明,梁启超华侨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推动中国向海洋拓展。从早期的《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至1919年的《欧游见闻录》,华侨殖民研究的落脚点往往是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因此,确实是“海洋国家”理念促使他研究华侨问题。
梁启超在华侨研究史上之所以卓有成就,在于他以海权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海外侨民。梁启超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学者,他的学术还处在世界前沿,这就决定了他的研究不会浮于现实表象。海权理论是将国家建设为海上强大国家的思想,由于梁启超流亡在新型海上强国日本,且他熟知西方的海权理论,所以,梁是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早期重要的构建者之一,在《新大陆游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文章里他明确传达中国的海权诉求,在《新大陆游记》里他还对马汉其人和思想做过评价。梁启超的海权思想融合有梁本人的民族感情与马汉的海权理论,是感性与理性合一、是梁启超华侨研究的理论资源。在华侨研究中以海权理论为指导思想,该理论强化了研究的学术性,也推动研究向深度开掘,如梁启超从海外华人身上探究国民的村落思想、保守个性和发掘中国人海外殖民的难点,这些均有深远的学术价值:(1)在国民性发掘方面,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发起者;(2)在华侨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如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揭示近代华侨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批判王朝打压华侨殖民,近代中国如欲践行海外扩张,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
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的起点是梁启超,这个学术起点很高,因为由“海洋国家”理念促成的华侨研究催生一种新学说。有学者在考察梁启超的意义时说:“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第 63期上首发《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尽管梁启超以西方殖民类比南洋华侨有些牵强附会,但却是第一次以比较研究的学理性思考,提出政府应当效仿西方国家,支持华侨的殖民事业。”[2]53虽然所论未指明,但这个判断触及梁启超华侨研究的核心,所谓的“西方殖民”其实就是西方海洋国家的海外扩张之论,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汉的《海权论》。庄国土先生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1)梁启超的华侨研究始于1899年;(2)梁的华侨海外“殖民论”以马汉的海权理论为基础,马汉以为,国民在海外的殖民才干构成了海权的一大要素,梁启超的学说亦不乏个人的思考,类比是其一,他阐述华侨殖民,就是寄望于华侨在海外为国家的扩张建立殖民地,使中国成为海洋国家。以《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例,梁启超讲述明清期间华侨在南洋短暂殖民成功的故事,该文的主题有二:(1)赞赏中国侨民的海上冒险精神和殖民能力;(2)批判明清朝廷,它们无意于向海外扩张,不支持甚至打压华侨的海外殖民,中国无法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再综合研究《新大陆游记》《记华工禁约》等文章,就能发现梁启超在研究中有几个基本学术观点:(1)中国应为海洋国家,政府须扶持华侨;(2)华侨须具有冒险开创之精神;(3)华侨在海外积极拓殖,国家借助民间力量向海外发展。这三个观点就是“华侨殖民论”的基本含义,即近代华侨或者像西方海洋国家的侨民或者如明清期间的殖民南洋华侨,他们须在海外建立殖民根据地;再进而言之,政府与华侨互相支持以服务于中国的海洋国家建设。
综上,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第一人,理由有:(1)“海洋国家”理念驱使他研究华侨问题,有高度;(2)他以海权理论为资源研究华侨问题,在华侨研究史上首次提出一种学说,有深度和影响力。
梁启超影响后来者,“殖民论”有“市场”,这表明“海洋国家”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华侨研究中具有普适性。李安山先生对梁启超的华侨研究有着客观的评价:“‘华侨殖民论’可以说是中国学者面对列强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可取,但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刘继宣和束世澂以及李长傅等)有相当大的影响。”[1]1002“华侨殖民论”在群雄逐鹿海洋的近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在当下,由于海洋霸权已不得人心,“华侨殖民论”当是历史的陈迹。至于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为何能得到后来研究者的认同,须追根溯源,“海洋国家”理念在近代中国是一股风潮,是华侨研究的基本语境和华侨言说的推动力。就此而言,“华侨殖民论”在学术界广有市场:(1)语境使然,梁启超是建设中国为强大海洋国家之时代语境的重要构造者;(2)先发者梁启超的研究有一定的高度与深度,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因此,探究梁启超华侨研究的学术影响,必须面对“海洋国家”理念,这也说明,该理念促成了近代中国华侨研究的全面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