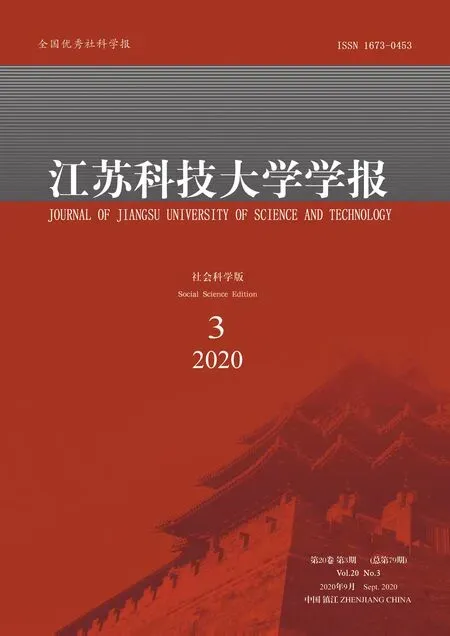外交庇护在近代中国
——以直皖战争后中日引渡安福党人交涉为例
陈甘霖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外交庇护是指一国以其驻外使领馆为场所,对违反驻在国法律并遭受通缉而申请庇护的驻在国人给予庇护。它既与在庇护国本国领土内进行的域内庇护相对,又与在国际法许可范围内使馆区所具有的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合法权益的外交保护不同,其本身是庇护制度的一种异变形态,虽然南美有少数国家通过签订公约的形式对其加以规定,但在一般国际法上并不承认这种庇护权,因而不具备普遍约束力。而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华列强却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将中国政府通缉犯庇护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列强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并扰乱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在与中国政府的交涉过程中,列强援引“治外法权” “政治犯不引渡”等国际法原则对自身行为加以粉饰,力图通过曲解国际法原则来为自己的庇护行为寻求合法依据,直皖战争后中日引渡安福党人的交涉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还缺乏专门研究,笔者一方面通过爬梳相关档案和史料揭示这一事件的史实,另一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在国际上较为常见的外交庇护权纠纷在近代中国呈现的真实图景。
一、引渡问题的源起
1920年7月19日,随着段祺瑞的辞职与东线皖军的崩溃,历时近一周的直皖战争以直系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如何收拾时局、重组政府、惩治已经失势的安福党人成为直奉联合控制的北京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大总统徐世昌于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次日便训令内务部缉拿安福党人,训令中称:“此次称兵构衅,情罪较重之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致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著步军统领督同京师警察厅一体严密缉拿,侯令办理。”[1]690这十人就是当时被下令缉拿的第一批安福党人,又被时人称之为“安福祸首”。
由于除段祺瑞自动辞职以外,其余需要引渡惩治的祸首已逃匿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单凭步军统领和警察厅的力量很难完成,政府只得派警察继续加强监视,同时“会商外交、司法两部,根据法理交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1]690。在司法部尚未将安福党羽的犯罪证据搜集完整的情况下,外交部先行照会驻北京外交团请求引渡,在致外交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的照会中称:“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并有勾煽土匪,侵挪公款情事,相应照请贵领衔公使查照,并请转达驻京各国公使查照,暂饬将上开各犯切实查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实纫睦谊。”[1]691
其实在北京政府向外交团发出引渡安福党人的请求之前,外交团已就此问题展开专门的讨论。在会上各国公使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英法美三国公使主张摈绝此辈,并根据和约以立论”[2]25。所谓和约即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馆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3]497条文中规定中国人不得在使馆界中居住,匿居在使馆界内的安福党人当然在可以引渡之列。但在会上日本公使小幡酋吉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如欲取一致行动,彼意今当认定日后如有同类之事,亦须照今日之办法。又东交民巷如摈绝亡客讬迹,则中国之外人租界,亦当照此办理。”[2]25由于在租界列强普遍享有司法特权,又有《苏报》案这样拒绝引渡的先例,日使将使馆区的案件与租界的案件相类比,其实也表明了愿意收纳安福党人的立场。由于日本公使强烈反对,再加上外交团内许多成员国并非《辛丑条约》签字国,所以依据和约立论的提议没有通过。英法美公使只得各自宣布知照其本国侨民,东交民巷不能容华人居住,有收留华人者,须令于四十八小时内出境[2]26。
日本和英法美公使立场的对立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有关。直皖战争后,亲日的皖系政权倒台,亲英美的直系入主中央,日本当局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立场上都会对失势的皖系安福党人抱以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且与曹吴执掌的北京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此时在远东,日本与英美在银行团问题、山东问题以及军备问题上多有龃龉,在一些议题上提出与英美完全相左的意见也不足为奇。在7月29日小幡酋吉致日本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的电文中就提到:“逮捕安福系首犯之明令,即将于今明两日公布,此乃英、法、美等国以攻击军阀主义而究追完全没落之安福系之结果。现安福系十凶既已全然来我方避难,在此情况下,本处尽管考虑其他种种避难方法,眼前殆无可能,本使完全穷于应付。”小幡酋吉虽然表明了希望收容十位被通缉的安福党人的立场,但还不敢自下决断,遂表示:“关于该等避难者我应所持态度之最后方针,究竟如何掌握,只有等待政府之决心,务请迅予电示为盼。”[1]1143
8月3日,小幡酋吉收到了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的回电:“关于庇护徐树铮以下安福系领袖一事,反对派方面虽将利用此事作种种排日宣传和进行抗议,然而,殊难认为由于此次动乱,日本之对华关系,会受到比此更大影响。但如拒绝为世人公认与日本有密切关系之段派于穷途末路之际所求之保护,即将丧失日本今后对中国政客之威信……若日本屈服于英、美方压力,始不能庇护政治犯。此在我对华关系上,将招致不体面后果。有鉴于此,对彼等亡命者,此际一律采取予以保护方针。”[1]1144直至此时,庇护安福党人的大致方针已经确定,引渡交涉对象已逐渐从外交团领衔公使柏卜变为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酋吉。
二、引渡问题的初步交涉
在确定了庇护安福党人的方针后,如何回应英美的质疑和中国的抗议,使自己的庇护行为变得合理成为日本当局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内田康哉在致小幡酋吉的训令中指出:“此事不管如何保密,终必泄露于外,而按目前事态,要彼等到别处避难已属不可能。因此莫如根据公使馆之庇护权,对彼等公然收容保护。关于公使馆庇护权,前例颇多,此事至少可以作为国际惯例主张之。”内田康哉将这种国际惯例解读为“根据使馆庇护权,对于亡命者不分政治派别,全予收容保护”[1]1146。根据内田康哉的授意,小幡酋吉于8月9日照会北京外交部,称在政府所通缉的十名安福党人中,除李思浩中途离开外,其余九人,“各自来本公使馆请求保护其生命,本公使顾念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许多之事例,认为出于不得已,决定对于以上诸人,予以相当保护,收容公使馆卫队营内。且对以上诸人严重告诫,在该收容所内不得干预一切政治,并使与外面交通完全断绝。本公使……深信贵国政府能十分谅解本公使馆此等之处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现在以上诸人所收之保护,并非因其所属政派之如何,予以特别待遇。虽以上诸人不属他之政派,在公使馆亦不能因此拒绝”[4]981。
在日使发出正式照会后,中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8月12日,新任外交总长颜惠庆表示对于日使保护祸首通牒,“决用最精法理驳复,要求引渡”[5]。至于引渡的具体办法,国务会议讨论后拟定了司法与外交部协同办理的方针,即“由司法部迅行调集各该犯等犯罪证据,并根据法理成立刑事罪名咨送到部,再与日使严切交涉引渡”[6]14。不过,司法部表示此案“尚无证凭书类可以抄送”,只得暂请“由外交部依据约章及国际惯例办理”[6]15。日使庇护祸首的消息传出后,一时物议沸腾,群情激愤,民众纷纷要求惩治,引渡祸首。《益世报》刊载了题名为《为引渡祸首敬告外交颜总长》的社论,其中写到:“以首都咫尺中外观瞻之地,坐视逆党逍遥法外,不能捕获,则我之国法何在?国权国体,至今堕落无遗,谁生厉接,至今为梗,吾不得不因强邻之跋扈,而欺我外交当局之无人矣。”[7]在各方的压力与请求下,外交部决定一面“咨催司法部照国务会议原案,迅速搜罗证据”,一面请日使监视诸祸首,为引渡做准备[6]17。
外交部遂于8月22日致文日使:“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抱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该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云。”[8]外交部长颜惠庆也对之前日使的照会提出驳复,其内容大致分为三点:“(一)各祸首非国事犯(政治犯)可由他国公使证明,当然不能保护;(二)就中日邦交上,亦应速度引渡,俾正典刑;(三)日对此案当与他国一致,免起国际争执。”[9]36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出现在对日本的正式照会中,但大体表明北京外交部当时的策略,在未掌握安福党人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先坚决否认安福党人为政治犯,并利用外交团中其余国家的不同意见给日本施加压力。
而日本方面担心中国报界对于日使馆庇护安福党人的报道会在民众中持续发酵,并酿成新一轮的排日风潮,所以于24日下午要求中国报馆禁止评论保护祸首一事[9]36。27日小幡酋吉对于中国方面的照会有了一个正式的答覆:“略谓贵总长本月二十二日答覆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明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4]983
日本公使反复强调安福党人为政治犯,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通过援引国际法上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来为自己的庇护行为寻求合法依据。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国际法上普遍承认并用于限制引渡活动的原则,其最早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法国应为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人给予政治保护,并将这部分人排除在引渡对象之外,法国大革命后这一内容更是以法国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833年比利时制订了《引渡法》,明确规定禁止引渡政治犯,在这之后这一原则相继被英美等国写入宪法,逐渐由一个区域性的规定变为国际公认的准则。政治犯不引渡虽然被国际社会遵守,但关于政治犯概念的界定却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受制于各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利益诉求的不同,不同国家往往会有不同的界定标准,国际法也始终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奥本海国际法》将其概括为“出于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而犯罪的人”[10]344,但具体何种动机和目的可称为政治性的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阐释。由于国际法对政治犯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使得被请求引渡国在具体案件执行中往往有较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被请求国可以将普通的刑事犯指认为政治犯而拒绝引渡,也可以将政治犯视为普通犯罪而引渡给请求国[11]。
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安福党人犯罪证据尚未搜集完全的情况下,将其随意纳入政治犯的范畴。不过,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并不是漫无限制的,政治犯不引渡必须建立在庇护权合法性基础之上[12]314。由于日本公使庇护安福党人的场所是日本驻华使馆而非日本国内,这样一种庇护行为属于外交庇护。由于请求庇护者往往身在犯罪行为发生国,这样对犯罪人进行庇护往往会损害驻在国的主权,所以国际法上只是规定驻外使馆本身拥有不可侵犯权,并没有规定驻外使馆拥有庇护权。即便南美地区国家普遍承认外交庇护权,但那仅仅是一种地区性的习惯,并非国际惯例,更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作为支撑[13]。《申报》转载英国《字林西报》关于庇护安福党人的社论中也提到:“此种保护行为从前确曾有之,但从未有人承认其为国际法之一部也。”该文同时也从法理的角度批判日本的庇护行为,认为“其所根据者,无非治外法权臆说之引申,但须知所谓治外法权者,乃虚构之词,近时其效力,已极有限制”。而所谓外交人员居处享有的特权,则“仅限于外使之独立与外使不可侵犯之尊严,及其公文案册不可侵犯之尊严”[14]。由于外交庇护本身没有合法依据,所以离开庇护权而援引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过北京政府也没有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条件与庇护权的法理依据作为自己的立论点,而是纠结于安福党人的犯罪性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三、徐树铮的出逃与中国抗议
在北京外交部向日本公使发出第一次正式抗议后,由于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党人涉案众多,司法检举程序较为繁杂,再加上北京政府对安福党人存款股份的调查被各大银行“以理由不充分,扰乱金融秩序相抵制”[15],所以调查取证进展较为缓慢,外交部官方也没有发出任何照会。不过此时北洋政府扩大了对安福党人的缉拿范围,在惩治第二批安福祸首的命令发出后,随即对曲同丰、光云锦、方枢等三十余人进行缉捕,并于8月26日在东交民巷外日本所开的扶桑旅馆处将光云锦抓获。日本认为此次行动侵犯了条约,对中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政府方面没有正面回应[9]37,但这一事件又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排日情绪。
事情到了11月16日又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小幡酋吉突然向外交部发出照会:“收容于本使馆护卫队兵营之徐树铮氏,近来再三请求本使停止其保护,撤退出本公使馆外,曾经本使切实努力促其反省。茲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该氏至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该兵营内,而十五日之朝即不见该氏之行迹。自系在十四日之夜,与十五日朝之间,单身逃出该所无疑等语。本使当日收容该使,系基于国际之通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该氏之事实照会贵国政府在案,茲复将该氏逃出本馆之事实,照请贵国政府查照可也。”[4]1004徐树铮是所通缉的十名安福党人中的头号要犯,他的出逃使得整个事件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关于徐树铮具体的出逃细节虽然没有在照会中说明,但在舆论界看来,日本协助徐树铮出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北京之日本人也盛传“十一月十四日,当徐树铮逃出使馆时,有日本兵士加以协助”一说[1]692。而各团体也电请政府向日本力争,并称:“彼既不能监守徐树铮,则其余诸人,亦难保不有逃逸事情,应将其余祸首,悉数引渡,以免再有疏虞。”[16]
北京政府虽然没有将安福党人的犯罪证据收集完备,但事态的发展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也不得不摆出强硬的姿态,于11月20日发出正式的书面照会并提出四项要求:“(一)贵使署担负看守之全责,今既听罪魁逃逸,是贵使自食前言,故请贵使向敝国政府用正式公文道歉。(二)贵署卫兵疏于防范,不能尽职,应请予以相当之惩罚。(三)小徐既在紧要关头逃走,则以后小徐如在敝国境内或境外贵国势力范围之内,犯有扰乱公安及破坏国际地位之行为,贵国政府应负其责。(四)贵使署不尽看守之责,致小徐逃逸。故其余祸首八人,不宜再逗留贵署兵营,而应请设法引渡,以应前请。”[17]
而日使小幡酋吉也于11月27日在致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的答文中逐条回应了中国政府的抗议,日使首先表示徐树铮寻求保护,公使馆将其收容纯粹基于国际惯例。其次,对于日使馆所应尽的义务,则仅限于“使敝署不能用为谋乱之机关,且不准徐等干涉政治,私通外间”。至于徐树铮的出逃则应由围守在使馆界外的中国军队负责,而日本政府对于徐树铮出逃后的行为更没有负责的理由。最后,日使表示对其余八人的政策并不受此次出逃事件的影响,“倘此八人欲收回前请,离去本署,本署亦不能拦阻之”。同时指出:“本署并非因贵政府之权而圈禁彼等,且本署亦无圈禁之权,此贵使所当注意者也。”[17]
从第二轮双方的交涉话语来看,双方争论的重点由安福党人的犯罪性质变为对徐树铮逃逸事件的问责。北京政府以徐树铮的逃逸为据,证明日使馆无能力看管剩余安福党人,并向日使陈明逃逸产生的恶果,希望日使改变原来的庇护政策,主张引渡。外交部虽然加强了外交攻势,措辞也更为严厉,却将论说的重点集中在对徐树铮出逃的责任上,而使馆看护能力不足更多是对庇护实际效力的质疑,仍没有从法理上对庇护权力的来源进行驳复。
四、中日引渡交涉的失败
进入12月份,总检察厅所检举的曾毓隽、丁士源、李思浩等人吞款渎职的犯罪证据大致搜集完备。12月1日,司法部通知外交部,请求以此为依据,再次照会日使,以普通刑事犯名义要求引渡[9]43。12月14日,外交部再次向日使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公使所持庇护逋客系国际习惯,在中国已成常例一说,并不成立。中国无此习惯,所可援为前例者,仅为荷使署庇护张勋一事,但中国并未认其合法,故不得视为正当之前例”。并再次重申徐等祸首为刑事犯,而非国事犯,现已证据确凿,请求引渡[9]44。
但日本再一次拒绝了北京政府的引渡要求,日使在24日再次答复外交部的电文中,一方面强调“日本政府只有希望中国政府平心静气,反复审查前次呈递于中国方面之说明书,此外不复再有他法”。除反复强调安福党人的政治犯性质之外,这一次日使还对其之前援引的国际惯例加以说明:“按公使馆收留保护,因政治上之理由,而恳求保护一身者,在西班牙及南美诸国先例颇多,不遑枚举。而在中国,则显著之实例甚多。如民国六年,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避难受保护,张勋在荷兰公使馆避难受保护,黎元洪在日本公使馆避难受保护,初不问其请求公使馆保护之不得已的政治动机原因如何,及避难人在政治上之地位如何也。因据上述种种情势,故被日本公使馆加以保护之诸君,既经明确,其避难实基于政治上之理由。则无论其是否为普通刑事犯,概不能允中国政府之要求而引渡也。”[9]44
在中国方面掌握安福党人的犯罪证据后,日本为论证其庇护行为的合理性,加强了对南美诸国与中国以往案例的分析,试图将个别案例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惯例,这显然是对国际法上“国际惯例”概念的滥用,《国际法规约》里规定了国际惯例所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首先是要被各国不断重复,其次是要被各国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18]10日本所称为国际惯例的域外庇护权只是出现在西班牙与南美,是一种地区性的实践,不具有普遍性。而张勋案例又不为中国政府承认,所以也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即便诉诸条约,也难以找到其法律效力。1896年中日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时曾在第24款对引渡问题有明确规定:“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或负债逃亡者,遁入中国臣民房屋或船舶上,一经领事照请,即将该犯交出。中国人在中国犯罪或负债逃亡等,藏于中国所住之日本臣民房屋或中国水面日本船上,一经中国官照请,日本领事即将该犯交出。”[19]274虽然该条约只是片面规定了在中国的犯罪情形,而没有对中日两国民众在日本犯罪的情形做出规定,属于不平等条约的范畴,但同样没有给予日本使馆以外交庇护的权利。
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便中国方面掌握了安福党人渎职贪污的证据,日本所称的国际惯例也并不被各国承认,但受制于《辛丑条约》第七条对于使馆区治外法权的规定,中国政府仍然无法采取相应的司法措施,更无法在未得到日本使馆许可下进入使馆馆舍进行搜查与缉捕,所以最终还是需要诉诸外交途径解决。日本依恃所享有的使馆馆舍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将治外法权扩大化,进一步引申为对安福党人的庇护权,且始终保持强硬态度,所以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处处受困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军警在东交民巷外长期的戒严与监视引起了各国公使的普遍不满,1921年7月15 日,外交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转告北京政府:“东交民巷系国际问题,与中日单纯关系不同,应将东交民巷之警探尽行撤退。”无奈之下,中国政府只得照办,1921年7月17日凌晨,东交民巷周围的警察全部撤回警局[20]。
而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又经历了新的一轮分化组合,奉直双方在关于内政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多有分歧,两派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竞相拉拢安福党人。此外总统徐世昌本身即由安福国会选出,与许多安福党人有着同根并蒂的关系,也主张对安福党人宽大处理。在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外交部再积极要求引渡安福党人已无实际意义。1922年1月2日,在奉系支持下的梁士诒组阁后随即发表公电,赦免了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六人[21]。而在11月28日,由于姚震、姚国桢、丁士源三人又效仿徐树铮逃出日本兵营,日本公使随即通告中国外交部,称安福党人已经尽数逃走,所以将看护设备一律撤除[22],这场旷日持久的引渡交涉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
五、结语
庇护权本是以国家属地优越权为基础,按国际法的相关要求在本国领土内实施,是一个主权国家行使正当权利的体现[20]。而依托于使馆界,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将驻在国的犯人藏匿于馆内的外交庇护则往往体现出对驻在国主权的损害。不过吊诡的是,这种违反国际公法、有损驻在国利益的行为却在近代中国屡屡发生。不得不说,列强在华权势的存在以及不平等条约体系为这样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提供了外部环境。就引渡安福党人事件来说,日使馆的外交庇护行为并非直接源于不平等条约,却是对不平等条约所产生的治外法权的扩大化,治外法权本身反过来又使得匿居于使馆界的安福党人免受司法惩罚。而一旦有类似行为发生,在华列强往往相互援引,并力图将不合法理的个案变成约定俗成的习惯。与之相关,许多所谓“国际惯例”与“通义”大都是列强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曲解国际法,并结合自身的行为捏造而成,这些内容也成为列强在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回顾这段历史,对此应有充分认识与把握。北京政府对于法理的认识不足与内部的派系政治也是造成最后引渡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拥有一个以国家实力作为后盾并具有良好法制环境的政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