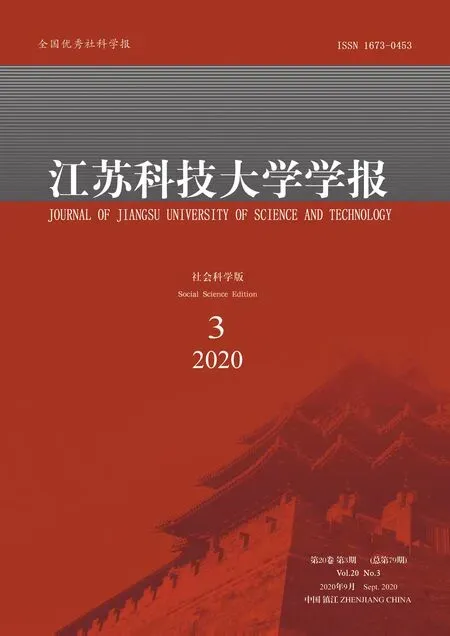论唐人岭南山水之二元审美
何婵娟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3)
在中国各地域中,岭南因其僻远,在唐代之前,岭南山水较少进入文人视野。唐代因岭南道成为安置贬官的重要场所,纷至沓来的北方士人以及本土士人的书写,使得岭南山水作为新的自然景观呈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
在方兴未艾的山水文学研究成果中,有关唐代岭南山水文学研究之作并不多。论文仅有户崎哲彦《惊恐的喻象——从韩愈、柳宗元笔下的岭南山水看其贬谪心态》《唐代诗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倡言》、黄斌《唐代桂林山水诗与桂林旅游审美的自觉》、汤静《唐代李渤桂林题刻与桂林山水》、宾妮《唐代桂林山水诗的文化底蕴特色》等。学位论文涉及唐代岭南文学研究的有陈凤谊《唐五代岭南诗歌研究 》、梁智谦《唐代岭南贬谪诗歌研究》、蔡勇《唐代岭南贬谪诗研究》、钟乃元《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已出版)等。这些学位论文重点关注唐代岭南诗歌,并未集中论述岭南山水文学。由于唐代岭南山水文学仍有较广的探索空间,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探讨唐人笔下岭南山水之不同面貌及其原因。
一、岭南山水的二元形象
因地域遥远,又因五岭阻隔,古代岭南与中原地区来往不便。在唐朝及之前的年代里,岭南都给当时人蛮荒、僻远、贫穷的印象。杜佑《通典·南蛮下》中言:“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之前是为荒服。”[1]5079不仅如此,唐代岭南成为安置贬谪官员的重要场所。户崎哲彦先生论述道:“隋朝规定‘流刑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到了唐代,改为‘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衡州距京两千九百五十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多是属五岭的北麓及其以南地区’。”[2]4“安史之乱时,许多文官逃难去江南等地,到了中晚唐官场政治斗争更为激化,流放频繁,其地多是南方,岭南是三千里之地,流放最多。”[2]4据尚永亮先生统计,唐五代岭南贬官人次,初唐97人,盛唐75人,中唐123人,晚唐134人,五代7人,共计436人[3]82。唐五代岭南道是安置贬官最多之地。
唐代贬谪来岭南的士大夫许多为著名文人,这之中有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张说、王昌龄、储光羲、李邕、刘长卿、卢肇、李绅、李德裕、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晦、李渤、李涉等人。另外王勃、萧颖士、元结、戴叔伦、王建、李翱、皇甫湜、许浑、李商隐、赵嘏、李群玉、张祜等人曾寓居两粤。纷至沓来的文人给蛮荒的岭南带来了中原文化气息,岭南独有的地域风情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唐朝以前“山水文学的舞台是江南地区,尤其以长江到洞庭湖周围的中游地区为中心。但到了唐朝,继续往南推移,从湖南的潇湘流域到五岭及其以南的广东、广西,后来岭南地区成为其中心”[2]5。岭南渐而成为唐代山水文学的创作中心,岭南山水也渐次进入唐代士大夫之眼帘。
唐代文人笔下的岭南第一印象多是“瘴雨蛮烟”,谈起岭南之瘴,唐人多惧怕。刘恂《岭表录异》中记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4]1又言及:“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4]22柳宗元《岭南江行》一诗佐证了岭南山水之恶:“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5]370山川如此,岭南民风更是彪悍,柳宗元《寄韦珩》一诗中言:“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5]366气候湿热、瘴气充斥、道路难行、民风彪悍等原因使得唐代士大夫视岭南为畏途。更何况来岭南的士大夫多是政治失意之人,多由繁华的京城贬谪而来,心理落差巨大,贬谪岭南期间他们的身家性命难保。宋之问因依附张易之、张昌宗以及武三思于景云元年(710)被流放钦州。先天元年(712)八月,唐玄宗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贬所。王无竞在中宗神龙元年(705)因依附张易之被贬岭南,在广州时被仇家矫制搒杀之。中唐著名宰相李德裕位高权重,唐宣宗继位后,五贬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850)十二月病逝于崖州。这些人的命运无不时刻警醒着贬谪岭南的士大夫。
因以上诸多原因,唐代士大夫视岭南为畏途,身不由己来之者则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岭南山水的各种看法,从而书写了特有的岭南山水文学形象。
(一)蛮荒、恐怖
初唐诗坛代表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均在神龙元年(705)遭贬。“在李武两党的激烈斗争中,由于武则天的逊位,中宗李显的复位,‘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旧唐书·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这便是初唐首次大规模地贬流诗人的事件。”[6]
由于武则天的退位,作为武后旧臣且依附二张的沈佺期被贬谪至驩州(今越南北部),沈佺期在驩州生活了五年。驩州的生活于沈佺期而言非常痛苦,他在《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一诗中倾诉:“遇坎即乘流,西南到火洲。鬼门应苦夜,瘴浦不宜秋……死生离骨肉,荣辱间朋游。弃置一身在,平生万事休。”[7]795炎热的天气、充斥的瘴气使得习惯于北方的沈佺期难以适应,更何况儿子、兄弟均因他牵连受罪,一想起这些事他不由得内心阵阵煎熬。归途无望,万事皆休,非常伤心。
沈佺期眼中的岭南是恐怖之地,如《入鬼门关》一诗中坦言:“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7]794此地在他看来:“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7]794鬼门关不是沈佺期一人害怕,“《太平御览》引《十道志》曰: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两石相对,状若关形,阔三十余步。昔马援讨林邑经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以)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故谚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人还。’”[8]28山路难行,水路难走,百蛮之地让沈佺期饱受考验。“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黄阁游鸾署,青缣御史香”(《答魑魅代书寄家人》)[7]795的京城生活成为他心中永恒的想念。
“神龙元年(705),随着武则天的逊位,李唐宗室的复位,结束了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武后的统治,也结束了宋之问三十年之久的‘称觞献寿’‘歌舞淹留’的宫廷诗人生活,把他从镐饮汾歌的中原掷向江南,掷向岭表,使他在七年三谪迁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道路:第一次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第二次贬越州(今浙江绍兴地区),第三次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灵山等地),最后赐死贬所。”[6]宋之问岭南生活期间之苦比沈佺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到泷州时,泷州山水让宋之问无比恐惧。“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躩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入泷州江》)[7]495晚上睡不安宁,白天一大早要赶路,瘴气充斥,天气炎热,山水险恶,处处让人惊怕,更兼民风刁蛮,诗人愁苦不堪。他在《早发大庾岭》中倾诉入岭南情怀:“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7]477他不仅思家,更恋朝廷,其《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诗:“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7]479令宋之问没有想到的是在端州驿站居然看到了昔日京城同僚们的笔迹,大家一道遭遇岭南之贬,同是天涯沦落人,内心伤感难以释怀。岭南风光虽别致,但他心里难过,越看越伤怀,“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7]488是他真实情怀的写照。
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十人被贬,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十年之后,柳宗元来到了柳州,岭南生活给他的文学创作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一诗写道:“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5]366柳州喀斯特地貌现今看来是非常美丽的,可在柳宗元眼中,这些山如剑铓,割断他百结的愁肠。登山远眺反而引起他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其《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写给他的四个朋友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他们也贬谪南方,分别出任漳州、汀州、封州、连州刺史。登柳州城楼,诗人想起了朋友们与自己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5]369一句欲言又止,诗歌尽抒愁绪, 结尾“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5]369无限伤情。户崎哲彦先生《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 一书分析了柳宗元对柳州山水的看法:“对柳州山水风土的恐惧感,除了用‘剑’比喻奇山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以外,还在《岭南江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寄韦珩》等寄人的诗歌中也流露得比较明显。”[2]106柳宗元笔下的柳州山水受其郁闷情绪影响,显得无比蛮荒惊悚。山水险恶,心情更差,“眼前的一石一木都成为他观照体味现实境况的参照,强化着他凄寂孤傲的自我意识,刺激着他一遍遍更苦涩地去咀嚼人生况味,更痛楚地去感觉内心不愈的伤口”[9]62。
沈佺期、宋之问、柳宗元等人均因政治失势贬谪岭南,心情抑郁凄怆,他们岭南生活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哀怨之气,其笔下的岭南山水多是蛮荒、恐怖、难受之形象。不过,唐代其他士人书写了岭南山水的另类特点。
(二)美丽、奇特
唐代文人笔下的岭南山水也呈现美丽、奇特的一面。著名书法家李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10]5042。开元十三年(725),“玄宗车驾东封回,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由是颇自矜炫,自云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甚恶之。俄而陈州赃污事发,下狱鞫讯,罪当死,许州人孔璋上书救邕”[10]5041。“疏奏,邕已会减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璋亦配流岭南而死。”[10]5042开元十五年(727),李邕途经端州(今肇庆),见到端州七星岩风景秀丽,多年宦海沉浮的他触景生情,挥笔创作了《端州石室记》这篇传世佳作。
《端州石室记》描写了七星岩美丽的风景,“薄人寰,腾物外,妙有特起,灵表秀开。绮田砥平,锦嶂壁立”[11]65。作者写了七星岩景区给人的整体印象:奇妙、锦绣、灵动。接着他详细描写了岩洞、水波、山峰的美丽姿态。“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涛海而洪波沸渭,叠杳窱而群峰嵯峨;飞动逼人,屹耸惊视;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风萧萧而一变天时;窦乳练于玉颜,石床列于仙座。”[11]65游玩其中,作者是“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营魄九升,嗜欲双遣”[11]65。朋友们一道游玩于斯,“避暑窟室,缔赏林峦;击石如钟,酌泉如醴”[11]65,不亦快哉!
《端州石室记》一文骈句与散句交错使用,骈句以单句对为主,行文严谨整饬,文辞凝练生动,手法多元,是篇漂亮的山水美文。其书法体方而笔圆,力劲而气舒,疏朗峻拔,纵横开阖,结构严谨,风采动人。
宝历元年(825)正月“壬申,以给事中李渤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10]513。李渤贬谪桂州,原因是上疏论救崔发。《新唐书·李渤传》记载了其原委:“五坊卒夜斗,伤县人,鄠令崔发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释之。帝大怒,收发送御史狱。会大赦、改元,发以囚坐鸡干下,俄而中人数十持梃乱击,发败面折齿,几死,吏哀请乃去。既而囚皆释,而发不得原。渤上疏曰:‘县令曳辱中人,中人殴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后, 不寘于法,臣恐四夷闻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诵言:‘前神策军在幔城,篡京兆进食牙盘,不时治,致宦人益横。’帝以问左右,皆曰‘无之’。帝谓渤有党,出为桂管观察使。”[12]4286
李渤虽贬谪广西,仍“正论不已,而谏官继论其屈”[10]4442。李渤到达桂林之后,“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13]191,宾主相得益彰,游山玩水,寻幽览胜。李渤游玩南溪山,发现其非一般之美。他在《南溪诗并序》中言:“溪左屏外崖巘,斗丽争高,其孕翠曳烟,逦迤如画。左连幽墅,园田鸡犬,疑非人间。”[14]525洞内钟乳石美丽无比,“其洞室并乳溜凝化,诡势奇状,俯而察之,如伞如盖,如栾栌支撑,如莲蔓藻井,左睨右瞰,似帘似帏,似松偃竹袅,似海荡云惊”[14]525。见到这番美景之后,李渤欣喜万分,赶紧命人对其进行开发营建,“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14]525。他经营南溪山心情无比畅快。李渤还发现了隐山之美,他为隐山六洞题名。李渤在桂林居住了两年,“风恙求代,罢归洛阳”[10]4442。离别之际,李渤对桂林山水依依不舍,其《留别隐山诗》云:“如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归。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15]19北归洛阳,这是唐代贬谪岭南士大夫的心中之梦,但李渤对桂林山水有了深情,依依不舍。其兄李涉贬谪康州(今肇庆),途经桂林时与他一道游玩桂林山水。李涉也非常喜爱桂林山水,其《南溪玄岩铭并序》中言:“桂之有山,潜灵亿年。拔地腾宵,戟列刀攒。岩之有洞,窈窕郁盘。虎挂龙悬,形状万端。”[15]18李涉感慨:“酒一卮兮琴一曲,嵁岩之下可以穷年。”[15]19
桂林山水之美,渐次引起唐代士大夫的关注。杜甫未到桂林,也闻说桂林之好,其《寄杨五桂州谭》一诗言道:“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上,雪片一冬深。”[16]145他想象着冬天桂林雪景之美,勉励朋友好自为政。
当我们整理唐人描写岭南山水的文学作品时,会发现他们笔下的岭南山水有着明显矛盾的二元形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矛盾的二元形象呢?这得从创作的主客观方面来寻找答案。
二、二元审美之因
(一)文人性情的差异
岭南山水形象与文人性情息息相关,不同文人个性不一样,同一文人不同时期心境不同,其笔下的山水风貌都不一样。
中唐著名文人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被一贬再贬,好不容易等到元和九年(814)奉诏还京,却没有想到结果是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当刺史,幸亏裴度、柳宗元等人救助,才改贬到连州当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居住了将近五年。在最初的贬谪时光里,刘禹锡也很难适应贬谪生活,其《谪居悼往二首》真切表达了他在朗州时的贬谪情怀。其二为:“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5]408他终日盼望归乡,在朗州等待了十年,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要踏入岭南的土地。按理说,刘禹锡心情应更为抑郁,但他生性豁达开朗,善于调节心理,“在被贬朗州、连州和夔州期间,刘禹锡不是走向荒僻的山林,而是积极地走进民间生活,了解民事民情,观察民风民俗,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具有浓郁异域情调的美,并以此转移自我注意力,调节愉悦其心灵”[17]。他很快适应了连州的生活,并且在连州积极为政,振兴文教,开启了连州的兴学之风。
连州山水在刘禹锡看来颇富佳趣,“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林富桂桧,土宜陶瓬,故侯居以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连州刺史厅记》)[11]92。从此文可以看出刘禹锡作为地方长官的拳拳之心,他关心连州史上的贤人,搜罗他们的事迹,以之为榜样,训导百姓。在连州积极为政的同时,刘禹锡将海阳湖疏浚修缮,建亭立榭,合为十二景,亲自为每处景点赋诗。《海阳十咏》引言曰:“元次山始作海阳湖。后之人或立庭榭,率无指名。及余而大备,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5]413《海阳十咏》组诗中将连州风景写得非常美丽,如《玄览亭》:“潇洒青林际,夤缘碧潭隈。淙流冒石下,轻波触砌回。香风逼人度,幽花覆水开。故令无四壁,晴夜月光来。”[5]413诗歌中的连州山水美丽清幽,连吹来的风都馥郁芬芳,月光照耀,水波微澜,非常美丽迷人。唐人眼中的“瘴雨蛮烟”地在“诗豪”的笔下绽放了另一种美。刘禹锡能挺过23年的贬谪生涯,晚年能与白居易在洛阳诗酒唱和,其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在贬谪之地历练出来的。
贬谪岭南对任何官员来说都是比较痛苦难受的,韩愈两次贬谪岭南,对他打击很大,但他“是一个感情炽烈、性格外倾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给自己定位很高,对自己的处境极度敏感,对目标的追求百折不挠”[9]2。因其百折不挠,韩愈很快适应了贬谪之地的生活,且积极振作,努力为政。
贞元十九年(803),京畿地区先旱后霜,灾情严重。京兆尹李实不仅不据实上报,反而照旧向百姓征税。朝野几乎无人敢言,作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上表为民请命,《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疏揭露了李实之过,文章对德宗皇帝也有所批判,表现出了韩愈常人所不及的社会责任感与非凡的勇气。德宗皇帝不仅没有听信韩愈之言,反而贬其为连州阳山令。
贬谪阳山对于风华正茂、满怀理想的韩愈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阳山之荒僻让韩愈吃惊,他在文学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此地山水的惊异、恐惧的感觉。“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送区册序》)[18]170在阳山生活期间,“韩愈写过南方山水的优美、自然地貌的奇异的诗文,但是从数量来说,还是极少,远远不及描述恶劣、危险的自然环境之多,因此诗文大多表现了惊异、恐惧交迫,惴惴不安的情绪”[19]159。但阳山之贬并没有挫败他的锐气,他个性阳刚,陈寅恪《论韩愈》中言韩愈:“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20]123
韩愈满怀理想,有很多的事要做。《次同冠峡》 一诗中言:“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5]293诗歌表露了韩愈在阳山的积极心态,他忙于为政,健全县衙编制,劝农桑,种树造田,兴学,忙得不亦乐乎。韩愈不仅不鄙薄阳山,不哀怨自身仕途,反而在阳山过出了滋味。《县斋读书》一诗颇显其心境:
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谪谴甘自守,滞留愧难任。投章类缟带,伫答逾兼金。[5]260
阳山山水别致,日子闲暇,读书不寂寞,有朋友喝酒,有青竹白云相伴,如果不想起家乡不眷恋仕途,此处日子倒也逍遥好过。一年二个月后,韩愈调离了阳山。
岂料15年后,韩愈再次来到了岭南。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而远贬潮州的他为再次踏上岭南之路而无比痛苦,对着远来送别的侄孙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5]306“韩愈在遭到阳山之贬后并没有内疚自责的情怀,而潮州之贬后,却在诗中一再地表示自己‘罪重’的懊悔心情。”[21]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一文中忏悔:“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18]233他希望得到宪宗的原谅,宪宗接到奏章之后,果真消气了:“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无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12]5262因得到了皇帝的宽宥,韩愈很快量移袁州,在潮州只呆了八个月。在潮州的八个月时间里,韩愈也没有闲下来,他关心农桑,发展文教,驱除鳄鱼,整顿潮州的社会秩序,促进了潮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赢得了潮州百姓的爱戴。千百年来韩愈成了潮州最有名望的官员,也成了潮人心目中的神。
阳山、潮州的两次贬谪对韩愈影响较大,“此期韩愈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扬弃险怪,趋向平易。贬潮期间的创作,乃是韩愈晚年创作嬗变的一个转折点”[22]。韩愈坎坷不平的仕途、跌宕起伏的心情在其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其笔下的岭南山水风貌各时期不一样。《柳州罗池庙诗》擅取典型的岭南物象来表现民众对柳侯的热爱,“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5]319。荔枝、香蕉都是岭南物产,且都在夏初成熟,以最新鲜的水果、新备的肴蔬来祭祀柳侯,表现柳州民众虔诚祭祀之状。“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5]319,将柳州山水写得极富情味,不同于柳宗元笔下大荒、惊悚的面貌。峨山美丽,柳江多情,桂树成林,山石莹洁,柳州因有柳侯山水更加动人。长庆二年(822),韩愈的朋友严谟以秘书监出为桂管观察使,离京上任前,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作《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一诗赠别: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5]310
诗人笔下的桂林山水美丽无比,“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一句高度概括了桂林山水秀美特征,千百年成为描摹桂林山水最出名的诗句。“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表现了当时桂林百姓生活的安居乐业,作者用颜色鲜艳的词,描摹了桂林山水之美,民风淳朴,物产丰饶,是个极佳之处。可以说,韩愈在这首诗中给予了桂林为代表的岭南山水极高的评价。
唐代士人中由贬谪来到岭南任职者,因个人性格不同,不同时期心情不同,想法各异,对岭南山水的感受不一样,这导致了他们笔下的岭南山水面貌不一。
(二)生活经历有别
翻阅《全唐诗》以及入岭南的唐人文集会发现,书写岭南的唐代文人可分为两类。
1.有岭南生活经历者
他们贬谪岭南为官,或因其他原因寓居岭南,或生长于岭南,较为熟悉岭南风土人情。他们笔下的岭南世界因个人创作心境不同,或蛮荒惊怖或美丽奇特,岭南山水在他们笔下有具体而细腻的呈现。前述沈佺期、宋之问、李邕、柳宗元、韩愈、刘禹锡、李渤等人均如此。南来岭南的士大夫又可分为贬官、任职或寓居等类型,这些人因其生活经历不一样,其笔下岭南山水面貌亦不相同。
“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12]5347的李绅亦为贬官岭南者。长庆四年(824)二月,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李绅此次被贬是因宰相李逢吉构陷,两人素不相睦,“宰相李逢吉与李绅不协,绅有时望,恐用为相”[10]503。趁着敬宗登基不久,李逢吉一党打击政敌不遗余力。
据卞孝萱先生《李绅年谱》可知:李绅于长庆四年(824)秋天抵达端州,于宝历元年(825)五月量移江州长史。李绅在端州实际生活时间不足一年。岭南期间他创作了《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红蕉花》《在端州知家累以九月九日发衡州因寄》《江亭》等诗。这些诗歌反映了他因贬谪心情郁闷,身体不适,但又顽强之心理。如《江亭》诗:“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今日病身悲状候,岂能埋骨向炎荒。”[14]618李绅的这种心理状态影响其审美体验,他笔下的岭南山水惊险、奇特而陌生。“千崖傍耸猿啸悲,丹蛇玄虺潜蜲蛇。泷夫拟楫劈高浪,瞥忽浮沉如电随。岭头刺竹蒙笼密,火拆红蕉焰烧日……阴森石路盘萦纡,雨寒日暖常斯须。瘴云暂卷火山外,苍茫海气穷番禺。鹧鸪猿鸟声相续,椎髻哓呼同戚促。百处谿滩异雨晴,四时雷电迷昏旭。”(《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14]594李绅在此诗中细致描写了岭南地区路途遥远、水路艰险、山林茂密、天气变化无常、动物出没、植被迥异,种种物象触发他贬谪之悲。亦如前人岭南之贬,担惊受怕、仕途苦闷之情倾泻于李绅笔下,其作品中岭南山水多蛮荒、惊怖之态。
人称“江南才子”的许浑于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因未能释褐入仕,故前往南海受辟于方镇幕府,希望获得幕主举荐而释褐做官,许浑可谓因任职而寓居岭南士人之代表。张红《许浑长安折桂与南海之行考》一文言:“其中入南海幕府的时间,当在其长安折桂之后、释褐做官之前。”[23]“今考许浑行迹,其当于大和九年初冬南行,开成二年春罢府北归润州。”[23]许浑在岭南东道节度使幕府任职一年多,与前述贬官们不一样,许浑来岭南是为了积极谋仕进,他进士及第七年后才得到官职。岭南幕府经历,让他得以熟悉岭南风土人情,其笔下的岭南风景时有秀丽之姿。《韶州韶阳楼夜宴》显现了其“字字清新句句奇”之风:“待月西楼卷翠罗,玉杯瑶瑟近星河。帘前碧树穷秋密,窗外青山薄暮多。鸜鹆未知狂客醉,鹧鸪先让美人歌。使君莫惜通宵饮,刀笔初从马伏波。”[24]114于诗中可见许浑入岭南时心境与贬谪岭南官员心境明显不同,他充满期待。其笔下岭南山水呈现出的更多为别样之姿、异样之美。《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其一曰:“未腊梅先实,经冬草自薰。树随山崦合,泉到石棱分。”[24]138其二曰:“鹭巢横卧柳,猿饮倒垂藤。水曲岩千叠,云重树百层。”[24]138其三曰:“海风闻鹤远,潭日见鱼深。松盖环清韵,榕根架绿阴。”[24]138这些诗歌表现了峡山寺周边生态丰富,风景优美,富有变化,生机勃勃,但因眷恋家乡,急于谋仕,许浑岭南诗又多带浓郁归情。
唐时岭南本土最著名的士人当属张九龄。张九龄为盛唐著名宰相,他深刻影响了其后千余年岭南本土文风。作为本土士人,张九龄眼中的岭南山水富有佳趣。《浈阳峡》:“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7]452张九龄笔下浈阳峡水窈窕、山峭拔,作者感叹世人不识其美。虽然仕途风波不定,但张九龄笔下的岭南山水多有俏丽、秀美之姿。如《自始兴溪夜上赴岭》中描写道:“日落青岩际,溪行绿筿边。去舟乘月后,归鸟息人前。”[7]465于张九龄而言,家乡的山水能抚慰他尘世牵累之心。
岭南本土士人韦敬辨撰文的《智城洞碑》是广西上林县保存的著名唐碑,该碑刊刻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在韦敬辨眼中,家乡智城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乃人间仙境。“疏藤引吹,声含中散之弦;密篠承风,影倾步兵之钵。灵芝挺秀,葛川所以登游;芳桂丛生,王孙以之忘返。珍禽瑞兽,接翼连踪;穴宅木栖,晨趣昏啸。歌莺啭响,绵蛮成玉管之声;舞蝶翻空,飖飏乱琼粧之粉。”[25]2
作为岭南土生土长的士人,他们眼中的家乡山水是美丽的,无论仕宦何方,他们对家乡的怀念都是真挚的。
2.没有到过岭南者
当前高校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纸质作业存在许多弊端[3];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大学生对网络依赖性的增加[4],医学院校加强了医学教学课程的网络学习平台的建设,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发布作业的网络考核逐渐被医学生接受。文章就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课程网络考核对本科生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认真体会,现总结如下。
唐人中书写岭南山水的另一类士人并没有到过岭南。他们没有岭南生活经历,他们的岭南印象多基于道听途说或者阅读经验,他们笔下的岭南形象较为笼统,大致可用“僻远、蛮荒、瘴疠、炎热、异样”等辞藻来概括。他们书写岭南的缘由不少是因为朋友去往岭南或者朋友在岭南任职,作为友人赠诗勉励表达牵挂之情,或者与朋友音书往来互诉衷肠。
卢纶《逢南中使因寄岭外故人》一诗反映了岭南炎热蛮荒:“巴路缘云出,蛮乡入洞深……炎方难久客,为尔一沾襟。”[16]649卢纶深切表达了对朋友的牵挂之情。元稹《送岭南崔侍御》一诗写岭南风土人情与北方迥异,其对岭南的描写明显带有想象夸张成分:“毒龙蜕骨轰雷鼓,野象埋牙斸石矶。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桄榔面碜槟榔涩,海气常昏海日微。蛟老变为妖妇女,舶来多卖假珠玑。”[5]843岑参《送杨瑗尉南海》亦基于想象:“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26]730贾岛《送张校书季霞》叙述容州遥远、气候不同:“从京去容州,马在船上多。容州几千里,直傍青天涯……南境异北候,风起无尘沙。”[24]476这些士人与有岭南生活经历的士人相比,其笔下的岭南物象明显较为笼统且带有想象虚构成分。
可见,唐代士人因其生活经历不同,其笔下的岭南风貌是不一样的。
于唐人而言,大部分岭南山水是陌生的,有待他们去发现书写,他们在不同情境下书写出了岭南山水之二元形象。另外岭南有部分地区的山水受到了唐人一致认可,这使得唐代岭南山水文学更呈现出地域性差异。
(三)地域性山水差异
唐诗中不乏歌颂桂林风景者,杨汉公《訾洲宴游》诗曰:“桂林云物画漫漫,雨里花开雨里残。惟有今朝好风景,樱桃含笑柳眉攒。”[27]3沈彬《阳朔碧莲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28]712两首诗均歌颂桂林山水之清幽美丽。前述李渤亲自经营桂林山水,北归时他对桂林依依不舍,其情可以理解。
如果说唐人眼中桂林乃胜地,岭南的罗浮山则是仙境。罗浮山是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又有“岭南第一山”之称。李白说:“余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26]529诗仙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连他都怀想罗浮,可见在唐人心目中罗浮山乃神往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髙三百六十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焉。”[29]839
罗浮山的出名与葛洪密切相关。东晋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之,洪乃止罗浮山炼丹。优游闲养,著述不倦,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30]361。葛洪在罗浮山炼丹,且笔耕不辍,赋予了罗浮山深厚的文化内涵。
唐宣宗时罗浮山道士轩辕集更为罗浮山增添了仙化色彩:“罗浮生轩辕集,莫知何许人,有道术。宣宗召至京师,初若偶然,后皆可验。舍于禁中。往往以竹桐叶满手,再三挼之,成铜钱。或散发箕踞,久之用气上攻,其发条直如植。”[31]卷七
于此可知,在唐人眼中罗浮山乃仙境。文丙《罗浮山》诗咏叹道:“罗浮多胜境,梦到固无因。知有长生药,谁为不死人。根虽盘地脉,势自倚天津。未便甘休去,须栖老此身。”[32]820曹唐《送羽人王锡归罗浮》表达了对罗浮山向往之情:“风前整顿紫荷巾,常向罗浮保养神……最爱葛洪寻药处,露苗烟蕊满山春。”[24]975李群玉在《广州重别方处士之封川》诗中期盼与友人一起登罗浮山:“愿回凌潮楫,且著登山屐。共期罗浮秋,与子醉海色。”[24]448吕岩《赠罗浮道士》赞美了罗浮山道士之自由生活:“罗浮道士谁同流,草衣木食轻王侯。世间甲子管不得,壶里乾坤只自由。”[32]607
从地域而言,岭南地区山水虽然均处于五岭以南,但山水又有差异性,高山、森林、河流、深洞、幽岩、大海、岛屿,这些本身就会给观赏者不同的审美体验。以此唐人笔下岭南山水又带有地域性差异。
综上所述,唐代岭南地区山水因自身面貌以及开发程度不一样,居于岭南的士大夫个人境遇与性情不同,他们在不同场景中面对各类山水而创作的岭南山水文学作品呈现出明显二元面貌。唐人岭南山水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贬谪文学色彩,在地域文学中呈现出别样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