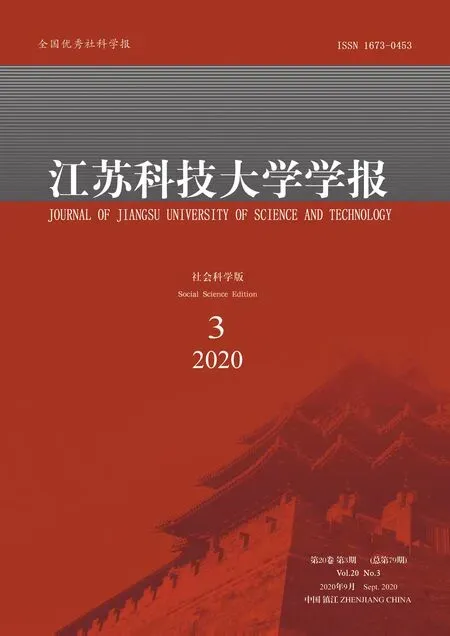视域融合:理解者主观性和历史性的泛滥
韩苏桐,余亚斐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目前,部分理解者由于在运用或追求以视域融合为方法或任务理解、创作文本时刻意放大自身的主观性和历史性,致使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进一步扩大、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这在社会上引起了质疑和嘲弄之声。基于此,为了正本清源,清除思想障碍,人们需认清伽达默尔(Hans-Gerog Gadamer)视域融合的内容、视域融合中存在的主观性和历史性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视域融合中的主观性和历史性问题。
一、作为理解任务和理解方法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视域融合,它是指在理解过程中,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它超出了原有视域的界限且包容理解者的自我意识。视域融合的产生,不仅明确了理解活动的任务,同时它也作为一种诠释学方法被人们所运用。
首先,伽达默尔明确把视域融合作为理解活动的任务。伽达默尔指出:“与历史意识一起进行的每一种与流传物的接触,本身都经验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理由,诠释学的活动就是筹划一种不同于现在视域的历史视域。”[1]396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理解者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隔阂,这种隔阂决定了理解者如何对待历史文本。理解者阅读历史文本,不是简单地理解文本当中的语言、文字、图画以及它们背后的东西,也不是回到文本所产生的历史时代,相反,“现代读者在观照历史流传物时,乃是基于自己的现代自我意识来理解历史上的他者所述说的东西”[2]。他们是从自身的前见和当下所处的情境出发,按照自身所处时代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文本,而前见、情境和现时代则为理解者提供了一种独特视域。这种视域具有历史性,却又充满现时代品格。当理解者开始理解文本时,属于理解者的视域就已经发挥作用,它与文本所展现的历史视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在此视域中,现时代的意识和过去正进行着紧密对话。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当代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文本进入当代其实是与理解者一同存在。换言之,与其说理解者理解历史文本,毋宁说是在理解的世界中理解者的思维与历史文本的思维在现时代中相互沟通、相互融合。视域融合就这样在开放的氛围中突破了原有视域的界限,扩大了理解者的视域,并使理解者的自我意识参与到新视域中,从而不断丰富理解者的理解方式与理解内容。新视域的产生,又将应用于之后理解活动中视域的融合。正如伽达默尔所强调的那样:“历史视域的筹划活动只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1]396-397因此,立足于历时性角度看,只要理解活动一直进行,视域融合就始终在发生,新的视域也会不断出现,由理解所组成的世界也就一直在动态变化。
其次,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具有生存论意义的一种诠释学方法。虽然伽达默尔曾明确指出,“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1]2,但从他提出视域融合概念起,视域融合就已经成为理解者在理解中发挥自我主观性的一种方法。彭启福教授明确了这一点。他写道:“像伽达默尔那样仅仅停留在对‘视域融合’的生存论事实的揭示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如何实现‘视域融合’作出一定的方法论反思和方法论澄明。”[3]他更是进一步强调:“伽达默尔在其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建构中,内在地蕴含着一种方法论的变革,即从传统的认识论意义的方法论走向当代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4]视域融合成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方法,其关键一点在于伽达默尔提出的“意义创生”。与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克服理解者的历史性去追寻文本原意的做法不同,伽达默尔承认前见的合法性地位,认为理解者的历史性不可克服,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是一定历史情境下文本意义的创生。伽达默尔指出:“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理解者所表现出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1]383为了详细阐述文本意义,伽达默尔进一步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383在他看来,在时间间距和前见的影响下,文本的原意难以把握,理解者所理解的文本的原意其实是在特殊情境下理解者所理解到的意义。这种意义由理解者所处的情境规定,因而也就是视域融合的产物。如果说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是理解者向文本客观性的追溯,那么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则是文本向着理解者的开放,也就是理解者主观意识的回归,它使得理解者总是从自身所处的情境和时代出发理解文本。视域融合也因此不断改变着前见,前见成为具有理解者自我意识或理解目的的理解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分隔开理解者和文本的时间间距就不再成为理解的阻碍,相反,时间间距对理解活动的发生起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在既定的时间间距下,理解者的视域融合不断丰富文本的意义,扩展文本的意义世界。时间间距就此成为文本意义的生长域。因此,从文本意义的发生层面讲,视域融合是理解者创生文本意义的手段,是一种诠释学方法。
简而言之,当视域融合作为理解的任务时,它是以自身为任务的单一的理解的循环。当视域融合作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方法时,它是具有目的和归宿的理解的循环。这种理解的循环表明理解对被理解存在的不断开放、理解所构成世界的不断扩大。但是,不论视域融合是作为理解方法还是作为理解任务,它都是理解者的主体性活动,是理解者获得在世存在的方式。
二、视域融合中的主观性和历史性问题
理解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归根结底是以理解者所处的现时代为主体、以历史为客体的融合,是理解者主观性的积极发挥,是理解者历史意识的张扬。从这一点看,视域融合乃是以理解者自身为中心的行为,它仍遵循了西方关于主客二分的单向关系模式[5]。这种模式在视域融合中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主体的自由化及最高权威话语弱化的问题,二是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对历史事实的轻视,即理解以现时代为主而轻视、否定历史的问题。
第一,视域融合彰显了理解活动的自由化,弱化了最高权威的话语。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者是不分层次、不分等级的,没有谁的理解更有优越性、更具说服力。他的视域融合就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肯定不同理解者不同的理解方式和理解内容。这种“肯定”有浓烈的个人自由化倾向。伽达默尔写道:“我们不熟悉其语言也不了解其内容的过去时代的本文的意思,只能用我们已描述的方式,用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往返运动才能表现出来。”[1]248这种“已描述的方式”就是理解者已熟悉的理解方式,它根植于理解者的历史性并与理解者的情境相联结。这就是说,在理解本体论的基础上,伽达默尔提倡尊重每一位理解者的主观性理解和创造性理解的发挥。然而,这样的理解会使理解者的主观性过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理解活动过度自由化,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进而弱化最高权威的话语。其一,由于理解者的前见和所处的情境各不相同,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方式、理解内容也各不相同。文本向理解者开放的程度、理解者视域与文本视域交融所产生的结果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理解者所有的理解只是在向着自我理解前进。换言之,只要现实生活中的理解者有所理解,或只要他们愿意,那么从各自的前见和情境而来的理解便“怎么都行”。这实际上已经造成了理解的过度自由化甚至是理解的混乱。其二,关于权威,“伽达默尔的观点是,批判的反思不能导致一种不依赖我们前见地合法消除权威。它其实导致一种独断地接受权威,因为它是建立在关于历史前见影响的洞见以及反对权威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一理解基础之上的”[6]。从这一点出发,理解者的批判、反思看似具有权威的根据——它立足于传统,但事实上,伽达默尔是以传统这一形式上的权威消解世界上一切事实权威者的话语。在理解过程中,理解者只要有所理解,他就是在接受传统,他的理解就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一旦泛滥,就会对事实中的最高权威产生影响甚至动摇事实权威的地位。可以说,理解者的自由化理解不仅在发挥主观性,同时也是对现有的、公认的思想和社会秩序的反抗。当自由化愈演愈烈,它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破坏也会更大。那时,人们的理解将不再是由自我主导,而是被另一种思想所驱使。
第二,视域融合作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方法,它肯定理解者的主观历史意识,轻视乃至否定客观的历史事实。关于历史意识,伽达默尔写道:“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所谓历史的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1]390在他看来,理解者是历史的繁衍,他们总处于一定的历史情境当中,历史情境为视域提供了立足点,理解者对历史的反思总是被自身视域的历史性所限制,因而历史意识不会真正认清理解者自身。伽达默尔的这句话似乎道出了理解者反思历史、认识自我的“当局者与旁观者各自迷糊”的状况。事实上,伽达默尔的历史意识“缺乏真实的历史实践性和彻底的辩证精神,仍无法正确理解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了用同一代替统一、用时间代替空间、用理论代替具体历史进程的倾向”[7]。在他那里,他所阐述的历史意识是与现时代发生效果关系的意识,是以现时代为主体、以历史为客体而非将二者置于同等地位的意识。这样的历史意识强行模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边界,以主观的历史意识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以理解者所理解的历史意义替换具体的历史进程,这导致理解者对历史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充满了主观性、片面性和模糊性。这在他对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批判中清晰可见。伽达默尔反对狄尔泰的观点,“即我们必须从某个时代自身来理解该时代,而不能按照某个对它来说是陌生的当代标准来衡量它”[1]300,他认为“历史意识就是某种自我认识方式”[1]305。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无法克服时空局限性去还原历史文本,因而他们的理解总是视域的融合。这种融合伴随意义的发生,意义连接起历史与现时代,消除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但是,理解者的视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理解者的实践活动不断变化。由于视域中包含历史意识[1]394,所以视域的不断变化促使历史意识也在不断变化。这样,历史意识对历史中真实事件的认识也就随之变化。在变化之中,客观的历史事实成为主观历史意识的附庸,只要理解者愿意,那么历史意识对历史的认识就具有“历史客观性”。这已经在根本上动摇了历史事实的根基,历史不再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而是被时间羁绊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意义的绵延。每一位理解者都可以把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当作“客观历史”,以其所领悟的历史意义抹去客观的、具体的历史进程,而公认的、具有权威的历史事实则被丢弃。如此,历史事实便“居无定所”。从这一点来讲,以理解者的历史意识为主导的视域融合,不仅会让理解者轻视历史,让历史成为“布娃娃”,而且它会进一步加深历史与现时代的矛盾,让历史遗留问题更复杂。
总而言之,伽达默尔对历史意识和自我理解的积极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使理解者过度发挥自我理解。这样的自我理解,不仅会弱化最高权威的地位,扰乱社会秩序,也会破坏历史的完整性,割裂历史的连续性,使理解者可能会用自身对历史的观感代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观感,导致理解者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自媒体获得快速发展、理解更具歪曲化倾向的今天,如何解决视域融合中存在的主观性和历史性问题,推动上下两方的客观性、有效性、一致性理解,促进思想的再开放、实践的再前进,这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应考虑的重要方面。
三、如何把握视域融合中主观性和历史性问题
视域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已经表明它对历史认同的消极影响。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抛弃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其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中国与其他各国以及国内上下两方视域交融、理解一致、勠力同心、共同应对;其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离不开视域融合方法[5];其三,国内正在进行的反腐工作、扫黑除恶工作、“四个全面”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环节,它们离不开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引导,人们的主观化理解与意义的创生在新时代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须辩证看待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思想,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引导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客观实际相契合。
首先,视域融合应坚持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这是视域融合必须遵从的前提条件。视域作为可视的区域,其中囊括了事物和事件。理解者在理解现在发生的事件时,不能首先把看到的事件判定为真实的经过,即事件的真实性不能依据理解者前见的判断。这与伽达默尔承认前见的合法性地位并将其应用于理解中存在明显区别。一般而言,视域融合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理解者坚持客观性,既恰当地描述了事件的客观过程,给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它又能修正其他理解者的前见;另一方面,理解者坚持主观性,对事件进行挖掘,能使原本隐藏的部分真相呈现出来,让事件进一步明朗。同样,理解者在阅读历史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时,也应该让历史内容客观呈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因自己的前见随意理解甚至曲解,以个人或部分人的历史观感或历史经历消解整个民族在某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否则理解者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应当看到,理解者是各个历史时代中现实存在的人,现时代与历史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二分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模式,各方都是相互作用、相生相成”[5],人们的历史意识不能跨越其所属时代,不能用现在的视域评论过去,也不能用过去的视域看待现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作为,完全脱离时代限制或超越时代的视域是不存在的。
视域融合应该把现时代和历史放在同等位置上。现时代作为历史的衍生,是过去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延续,它与历史中各个时代一样,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在不同时空中的总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现实事件的集合体,其中充满了客观性、实践性和现实性。理解者于现实世界中存在,是现时代和历史双方对他的认可,离开其中一方,理解者都不会存在。从这一点讲,理解者尊重现时代就是尊重历史,承认现时代就是承认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不仅将历史意识限定在其所属时代,而且能真正地在实践基础上而不是在历史意识基础上统一现时代和历史。现时代和历史在实践基础上发生、演变又使得视域中的事物和事件先于理解者的“目光”存在。这样,视域的融合就要在尊重客观性的基础上将历史事实与现时代进行交融。如此,理解者坚持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就是在树立理解的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理解者也只有树立理解的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才能使视域融合具有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才能真正促进视域恰当融合,为理解提供可靠保证。今天,我们在对待党史、国史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态度上更要明确这一点。
其次,视域融合应坚持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理解活动的环节。伽达默尔区分诠释学的真正问题并提倡在“提问-回答”的模式中进行开放性理解。不可否认,伽达默尔的“问题意识”扩大了理解的世界。但是,他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讨论并回答逻辑中困扰主观理解的问题,它仍停留在理解者坐而论道的层面上,没有落实在行动中,也没有“将问题与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自身蕴含的规律相联系”[8],它对解决现实中与人的实践和存在相联结的问题缺乏动力且浮于表面。因此,理解者在进行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不妨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理解活动的环节。原因有两点:
第一,解决现实问题是实现理解与时俱进的要求。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与问题相联结,理解也是如此。理解者是现实存在的人,他的视域中不仅有可视的事件,还有与事件相联结的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更重视问题和问题的解决。现时代和历史作为厚重的文本,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固定在某个时间点,更多的是“旧事重提”“旧事新提”以及“新事新提”。这些问题随理解者的生存发展一同产生,呈现出与时代同步、与理解者同在的特点。不解决这些问题,理解者的前见不能与时俱进;不反思这些问题,理解者就不能真正洞察时代特征,无法认清时代需要,更勿谈服务时代发展。只有解决好现实问题,辨析问题中的矛盾,反思解决问题的方案,各个阶层的理解者才能合理理解、明辨是非、达成共识、勠力同心,才能为之后的实践活动提供经验支撑,使实践走在恰当的道路上。
第二,解决现实问题有助于解决好人的自我存在问题,完善理想人格。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出现了“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者认为,“人身安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虽然必不可少,但相比而言,生活质量、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更为重要”[9]。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对人的存在的关怀也与此相关。
现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同样反映了这一点。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较之前大为丰富。但是,东西部、区域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十分显著,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收入差距依然明显,收入与支出不平衡甚至负相关,更遑论教育、食品安全、社会风气、医疗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历史遗留问题和新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些问题使人们面临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处理现实问题的矛盾,人们的生存、生活压力日渐增大,以致一些人在自媒体上对事物和事件态度的“泛娱乐”化、“精神胜利”化倾向日益严重。在他们看来,相关问题反复出现,暴露出某些因素对部分社会存在的默许和社会意识的纵容。更何况上下两方沟通不一致、视域未深度融合、解决问题“走过场”态度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在理解活动中,解决好现实问题是一个必要环节,它能够扭转人们已经形成的、固执的偏见,能有效推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舆论在社会监督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大大提高。各个阶层的理解者应该借助舆论认识处理现实问题,促进彼此视域深度融合,以此增强自身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理解者解决好现实问题,有助于解决好人的自我存在问题,才能在一次又一次视域融合中完善理想人格,匡正社会风气,实现理解的人文关怀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共生。但是,理解者解决问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注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更要适可而止,不能任由主观意识随意发挥甚至刻意对抗、侮辱最高权威。这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升级。
最后,视域融合应坚持在时代发展中实现理解者的自我价值。当今,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已然转变,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现实社会中紧张而网络中亲近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人对自然的予取予求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也在经历着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可预期的将来的比较和融合,具有怀念传统而敬畏现实、憧憬未来却又安于现状的特征。然而,理解者的存在是个性与社会性、自我与时代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理解者不单单是单个的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要求理解者必须立足于时代,在达成时代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理解者的自我价值。如果说坚持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解活动的底线和限制条件,而解决现实中与人的实践和存在相关联的问题是理解活动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时代中实现理解者的自我价值则是视域融合的最终朝向。没有不以时代处境为立足点的理解,也没有不以实现理解者自身价值、满足时代需要的理解。意义的最终朝向、理解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理解者所属的时代,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如今,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国与国间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民族与民族间的文明融合程度也稳步提升。但是,在中西方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极端政治等思潮也在兴起,它们的出现表明了全球治理的思想困境,扩大了不同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分歧[9]。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的混乱理解和诠释以及对时代发展形势的错误预估,更是脱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甚至是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对立面。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是普遍联系的整体,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应该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鼓励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在彼此视域的不断融合中“确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共识”[10]。文明因交流而多彩,理解因融合而深入,价值观因践行而达成共识。理解者只有立足于时代潮头,理解才有共同朝向,才能促进思想再开放、实践再前进;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视域才能不断扩大,容纳当代更多的美好事物;理解者只有将自我置于时代之中,顺势而为,才能真正做到自我与时代的融合,满足自我需要,实现自我价值。
在视域融合中,理解者一味地张扬自我意识、发挥自我诠释并不会使理解者获得更好的理解,相反,它会放大理解者的主观性,形成偏见。应当看到,真正的视域融合,它是在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和突出的社会新问题,是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共识。理解者也只有在其中才能更好地获得自我的在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