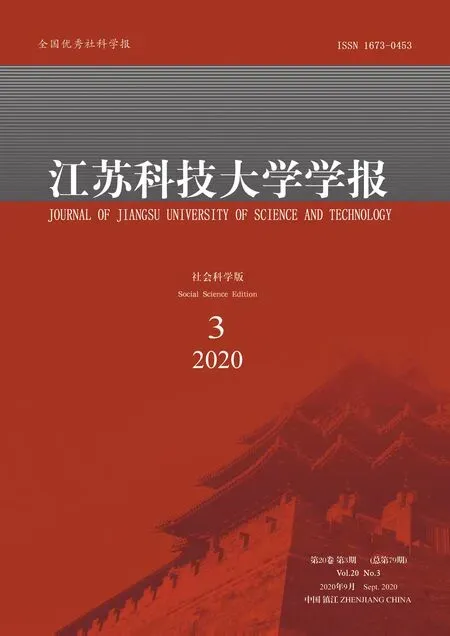天津法治文化历史渊源的运河维度
张红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 天津 300191)
从城市发展脉络的视角看,天津城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建城并不久远。近代已降,天津及其城市治理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跨越时空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以地方法律制度为物质基础,以法制观念为内核,以执法、司法为保障的法律文化的兴起更彰显了这种特色和意义。天津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的摹本,而且区域性的治理实践也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1],并为新时代法治天津的建设提供了城市法治文化的自信。天津与运河渊源颇深,天津城市的兴起、地域法律文化的确立、近代法治发展的标杆地位无不镌刻着运河基因。大运河是城市之根、地方文化之脉,因而笔者拟从运河维度考察天津法治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代,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正确道路选择的困惑与法治实践困难客观存在的现实。法治实践困难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显性层面的法律制度与隐形层面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之间的疏离,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文化。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2]。文化的价值在于以“文”化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融合了民族精神的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群有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法律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强调的是我国法律文化中新时代背景下的法治成分,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的判断。法律文化具有传承性,而充满价值判断的法治文化具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变革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要合理借鉴西方优秀法律文化,而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第一位的。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涵括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无形而内在的地域文化支配人们的活动,其中自然包括法治活动,并在区域文化和法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文化。根据文化模式论,文化要根据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建设天津地方法治文化,既要关注现下天津法治实践中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价值和法治习惯等,也要从城市发展的脉络探究法治文化的渊源,借鉴本地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
二、天津城市文化的运河基因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城市的兴起与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打开中国地图,天津版图像一匹骏马,身处华北平原的东北边缘,面向渤海,背靠冀中平原,马头伸向燕山山前平原,脚连接鲁西北平原。发源于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的河流都汇集于天津,注入渤海,形成著名的海河水系,故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是水上交通要冲。因临近渤海,6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的两次海水入侵,使得这片平原先后被海水淹没达数千年之久,人们因此被迫迁移,海侵以前的历史被湮没,以至于天津平原被认为是“滨海弃壤,无古可考”[3]。历史发展脉络呈现间断多、波动大的特点,这也成为天津建城较晚的重要因素。后来,运河的开凿改变了天津平原的水系,漕运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0多年,众河相汇之处的村落由“寨”成“镇”,随着区域行政级别的提升,天津逐渐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城市,所以有“天津是运河载来的城市”之说。运河是天津之根、城市文化之脉,天津城市文化所包括的法治文化自然镌刻了运河文化基因。
(一)“运渠”使天津初具航运枢纽地位
公元206年,曹操为北伐乌丸,在渤海湾西岸的滨海平原上开凿了运渠,以运粮饷。此举使得河北平原河流下游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天津历史带来了深远影响。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十余万户。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又从洵河口凿入潞河,以通海。”曹操开凿的运渠有两段:一段是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另一段是沟通洵河和潞河。沟通滹沱河和泒水段的是平虏渠,沟通洵河和潞水段的是泉州渠。曹操在沟通了滹沱河至鲍邱河之后,又自鲍邱河枝出一渠,一直向东延伸至滦河,名叫新河。曹操开凿的运渠,环绕渤海湾西、北两面,穿过整个天津平原,使偏居北方的滦河水系与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河系相联结,无疑是中国运河史上的一大创举。曹操凿渠虽然只是军事上的一时之需,却使河北平原上出现众流归一的局面。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此河道结构一经出现,便标志海河水系形成[3]35。海河水系的形成,使得位于众河汇合处的“天津”具有了成为航运枢纽的区位优势,对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漕运兴起开启天津向城市发展的历程
公元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壮丁百余万,开凿永济渠。永济渠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卫河)至“天津”附近,再经沽水(白河)和桑干河(永定河)到涿郡(北京)。金朝建都北京后,金章宗改凿运渠,大力发展以保障首都为目的的漕运,将“天津”作为南北运河的节点,为保护漕运和震慑地方而在此设“直沽寨”,“直沽寨”是可以追溯到的天津市区的最早聚落。元朝统一全国后,初期漕运由内河承担,隋炀帝开凿的隋唐大运河在多次疏通、改造之后,成为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直沽也随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河海航运枢纽和京畿门户。政治、军事的需求打破了九河下梢水患频发对“天津”发展的自然因素制约,以直沽为中心的“天津”经济日益发展,商业繁荣,人口激增,盐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元朝诗人张翥曾经写过“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诗句,描写了运河三岔河口处船桅如林的壮观景象。“直沽寨”升置为“海津镇”,“天津”开始了向城市发展的历程。
(三)漕运枢纽地位促使天津发展成为繁荣的都市
金、元时期的“直沽寨”和“海津镇”,主要发挥的是军事作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天津城的筑建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天津”这个名称也是在此时才出现的。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变”;建文四年(1402),燕王兵陷都城南京,次年于南京称帝,改年号为“永乐”。据李东阳《修造卫城旧记》载:“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可渡处也。”[4]天津置卫与筑城,使天津由“海津镇”发展为一个略具城市规模的军事堡垒,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并置于一城,但民刑庶政仍归所属的府、州、县管辖,卫所的职能范围仍然相当有限。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兵备道的建置,使天津卫城的管理体制由此初步得到统一。兵备道不只统辖三卫,其职能范围亦开始兼及民政和财政,天津已在军事重镇的基础上向手工业、商业发展。顺治九年(1652),基于清政府裁并卫所的举措,天津三卫合为一卫,统称“天津卫”。17世纪初期,随着巡抚一职成为定制,天津开始由军事重镇向行政区划的过渡。雍正三年(1725)三月,“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隶属于河间府,后由“天津州”升为“天津府”,天津由“卫”改“州”,标志着天津由军事城堡发展为封建城市。这个发展过程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大量的衙署、商贾和居民迁入天津。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记载,康熙皇帝认为“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盐政在历朝历代的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天津作为南北运河交汇处、河海运输中转站、京畿门户、漕运枢纽,长芦盐政署由北京迁到天津,长芦盐运使司署由沧州迁到天津,河道总督署由山东济宁府迁到天津,这些管理机构的相继迁入,使天津成为“盐政、漕政、河政”运行的中心。康熙四年(1665),漕运的重要税务机构——钞关,由临近北京的河西务移至天津,在南运河北岸的甘露寺旁设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天津钞关,百姓俗称“北大关”。钞关迁至天津,极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经运河由南方运来的粮食、丝绸、糖茶、百货等各种商品都要在北大关缴纳税款才可以放行。在漕运鼎盛时期,浮桥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大小商船,北大关一带的商业日益繁荣,一跃成为天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康乾盛世”,北大关一带的商业发展更是达至鼎盛。经雍正、乾隆年间的发展,天津的发展水平和地位已处于邻近的顺天、河间、济宁诸府之上,成为京畿地区最为瞩目的封建城市。
天津作为封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原因,固然与其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紧密相关,但经济基础仍是主要因素,大运河带来的漕运、盐业、渔业的发展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九河下梢的一个小村落,发展为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天津州、天津府,以至于成为近代北方重要的大都市,得益于运河的开凿与漕运之利。运河还是流动的文化载体,漕运的鼎盛不仅带来南方的商品,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奠定了天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勤恳务实、勇于创新的城市文化基调,形成了天津地方文化中的盐商文化、码头文化、戏曲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法律文化等内容。
三、天津法律文化的运河底色
法律文化分为以法律制度为表现的显性层面和以观念意识为表现的隐形层面。法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天津地域文化中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特征极大促进了天津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过程伴随着漕运的兴盛和衰落。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表现为由漕运制度及其执行奠定的集体主义、和合主义、实用主义的法律文化底色;后一个阶段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运河漕运的衰落以及海上漕运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天津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临近政治中心的区位优势,没有与其他运河城市一样走向沉寂,反而更加兴盛,并随着开埠而成为中国学习西方法治文明的窗口和推行新政的试验田。在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先行先试中,天津积淀了不同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法治文化。
(一)漕运积淀天津法律文化的基本底色
法治是规则之治,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规则文化。中国古代“以法治国”的文化内涵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文化内涵大为不同,但在形式上都强调规则的价值。大运河不同于自然河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价值,历朝历代都以举国之力进行开凿,目的是连接南北,保证国家统一和首都安全,保障首都和北方边疆的粮食供应,因而大运河的功能属性必然要求有一套需严格遵守并执行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天津城市发展主要经历了明清两朝,明朝和清朝与漕运相关的法律制度都十分完善。《明律》对漕运的规制主要是体现在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在治吏方面,主要是明确运河沿线各级官吏在河务、漕运方面的职责,并且规定了严苛的罚则;在治民方面,主要对破坏河防、漕河工程的行为进行规制。清代有关河漕的条文更加繁多复杂,后来为了便于执行,载龄等人编纂的《清代漕运全书》成为调整漕运事项法律规范的汇编。《清代漕运全书》包含了漕船规格制度、漕运兵丁制度、漕粮运输制度、漕粮缴纳办法和存储流程等。由此可见,清朝已经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完整的漕运法规体系。
基于漕运承载的国家职能,这些法规在运河沿线得到了严格遵守和执行。这必然会影响运河沿岸城市群众对规则的认知和遵守,对官员和百姓规则意识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天津法律文化中自然蕴含知晓规则、遵守规则的内容。漕运带来了天津商业的鼎盛,商业活动要求参与者既要遵守国法,还要遵守通行的商业规则,对商业规则的遵守同样成为天津法律文化的内容。运河及漕运为天津积淀了“集体主义、和合主义、实用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基本底色和遵守法律规则的基本内涵。
(二)开埠使蕴涵现代法治因素的法制文明在天津兴起
带有运河基因的古代天津法律文化是以“以法治国”为背景、以执行君主律法的意识和习惯为核心内容的。随着漕运衰落、天津被迫开埠,天津成为汲取西方法治文明的一扇窗口,带有现代法治因素的法制文明在天津兴起。
道光五年(1825),清政府任命琦善总办海上漕运,天津设收兑局负责验米交收,之后海上漕运中途停运;咸丰二年(1852),江浙漕粮又改为海运,运河运输逐渐名存实亡;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正式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运河漕运终于落下帷幕。作为封建城市的天津兴起于漕运,而作为开放型半殖民地城市的天津兴起则伴随着大运河漕运的衰落。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弄人之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天津的社会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城市经济也迅速由独立的封建经济转变为半殖民地经济,天津不再是封建的封闭型城市,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开放城市。外部因素的介入与天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勤恳务实、勇于创新的城市文化相结合,使得天津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的摹本,而且区域性的法治实践也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彼时,英、法、美、德、意、奥、俄、日、比利时九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各国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城市治理、公民社会架构等制度体系被复制到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天津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是全方位地引领风气之先,迅速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先驱、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口岸、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第一家公立医院、第一辆有轨电车、第一家机器铸币厂、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电报局等100多个“第一”。在这些物化“第一”的背后,是多项法律制度开创近代中国立法之先河,天津在法制文明架构上独领风骚,拥有辉煌的法制发展史,并形成了注重制度创新、追求现代法治精神的天津法治文化。
(三)天津创造了辉煌的法制文明
地方法制文明即一个地方实行法治的状态和所体现的文明程度,是在无形法治文化影响下有形法律制度创制及执行的成果和成就。近代以来,伴随清朝的衰落,中华民族饱经蹂躏,在改变“落后挨打”处境的探索中,天津作为试验田,在特殊历史环境之下顽强撑起法制创新的旗帜,以制度、机制创制为核心的天津地方法制文明的建构也因此兴盛于近代。仅以司法制度为例,天津就创制了审判制度、警察制度、监狱制度等。
司法审判是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关于司法活动、审判理念和审判制度的内容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审判观念和审判制度与现代审判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就审判制度而言,包括审判机构制度、审判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审判程序制度、复审与死刑复核制度、判决执行制度等内容,地方审判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一是其鲜明的特点。近代以来,西欧理性主义法律和司法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文明被动走上转型道路。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首先在天津府搞试点。1907年,天津府制定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庭章程》《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庭员弁职守》《审判研究所简章》等法规,改变了以往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合一的格局,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庭、天津县地方审判庭、乡谳局,并对民事、刑事审判程序和相关事项作了详细规定。
现代警察制度的创立对维护社会治安、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价值。中国的警察制度始于天津,1902年由袁世凯设立。自设立之日起,通过不断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较为缜密的警察制度体系逐渐形成。主要包括:警察组织法规,这方面的法规规定了警察机构的组织体系及各级警察机构之间的权限划分,官吏、警员的任用、奖惩以及服装、设备、警械规格和等级等;警察行为法规,这方面的法规规定了警察为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指导居民、保护居民及预防公共危害;司法警察法规,这方面的法规规定了警察侦查罪犯、搜集证据、逮捕犯人以及以辅助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为目的的警察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监狱在设立目的和管理上与现代监狱差别巨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代理巡抚赵尔巽设想效仿汉代输作制度,兼学东、西各国的禁系规制,采用惩罪、做工示罚的做法,建立了罪犯习艺所,将其作为专门安置和发遣充军、流刑以及徒刑罪犯之所在。1903年,清朝中央司法机关刑部议复了他的奏折,并且议准了《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章程》,规定罪犯经审明定罪后,即收入犯事所在地的习艺所,不以本省、外省以及年限来确定工役的轻重。天津作为推行司法改革的重要基地,袁世凯批复天津道采择日本的狱制,分缓急设立习艺所,制定了《天津罪犯习艺所章程》《天津游民习艺所章程》等,基本确立了近代监狱制度并在全国推广。清末天津监狱有天津府监狱、天津县监狱、总督衙门附属北洋大臣发审所监狱,以及南、北段巡警总局内的拘留所和新设立的天津习艺所。
清末至民国期间,天津除以上司法制度走在全国前列外,还在规划、教育、税务、海关、公共卫生、城市管理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新制度、新措施,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全方位地走在全国前列。此时的天津成为中国地方法制最完善、最复杂的城市之一,为现代城市法治文化的兴起奠定了深厚基础。
(四)天津为中国培育了大量法学人才
如前所述,文化的价值在于“人化”和“化人”,培育“法治人”是法治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近代天津的法学教育与世界接轨,走在了全国前列,形成了大学、专科、职校构成的具有特色的法学教育院校体系,为中国法治建设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的前身)于1895年创建。其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制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设有法科,开设了“律例学门”,初步具备了法律系的形态,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宗旨[5]。在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任课的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聘请了美、日、英、法、德、俄学者教授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培养了以王宠惠为代表的中国法学人才第一梯队(1)参见天津市教育局《教育志》编修办公室编《天津教育大事记》,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内部发行),1987年。。天津除了拥有培养高级法学人才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外,还拥有中国最早的法政学校之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该校被指定为全国各省同类学校的表率和样板,清政府曾于1906年7月颁布《北洋法政学堂章程》并通咨各省照办。中国最早的警察学校——北洋巡警学堂也诞生于天津。北洋巡警学堂类似于今天的职业教育院校,由日本警官三浦喜传任总教习,毕业生大都分配到巡警总局下的分局工作。此外,还有外国人独办的高等法学教育学校,如1900年英国人在天津设立的新学大书院,该书院的分科科目中有专门的法学。近代法学教育在天津的兴起,使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技术开始在天津社会逐渐发挥作用,为法治的推进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胥吏、讼师的专业法学人才[6]。
昔日的“滨海弃壤”因曹操首开运渠,众水归一,形成海河水系,天津由此初具漕运、海运枢纽的地理优势。伴随漕运兴起,历经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因明成祖置卫筑城而具有了城市的雏形。明清以来,天津逐渐开始了由城而市的发展过程,天津由卫变州,后升级为天津府,实现了由军事要地向封建城市的华丽转身。可以说,天津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也因漕运形成了遵守国法、遵守商业规则的地方法律文化。近代以来,随着漕运的衰败、海运的发展,作为海运枢纽、京畿门户的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设置租界,五方杂处,十国共管,不同法律文化、城市治理规则交融碰撞,融为一体,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机制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和转型,诸多具有开创性的法律制度在天津得以确立,并在执行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法治文化。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推进地方法治建设。梳理天津法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回顾璀璨的地方法制文明,有助于在全面依法治国、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下,提升地方法治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地方法治建设中的“化人”作用,以运河文化名城、法治文化名城的深切自豪感大力推进法治天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