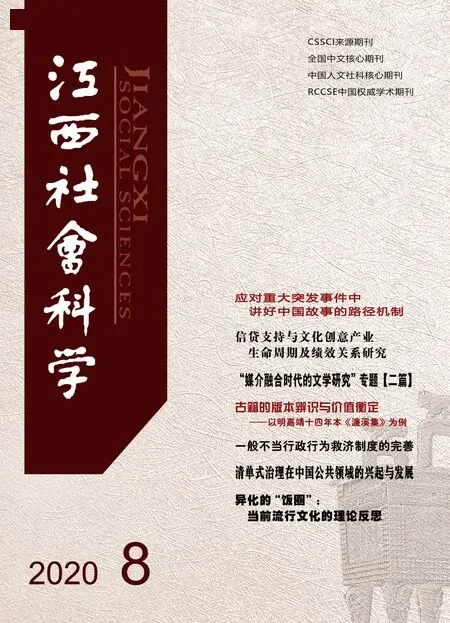泛娱乐化喜剧审美观的文化引导
■谢旭慧 程正野
在世界性娱乐文化风潮的影响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喜剧文化亦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娱民”优势,迅速走进国人的审美视野。但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喜剧审美观却呈现杂芜化、碎片化、功利化倾向,审美标准混乱、审美趣味低俗、审美取向媚外,导致正确的价值观严重缺失、理性价值诉求迷失。喜剧审美教育事关国民的灵魂塑造和时代的精神构建,因此,加强主流媒介的风向标作用,加大喜剧精品的示范引领,加大学校喜剧审美的教育力度,构建和优化喜剧传播的立体化体系,是构建和谐健康的喜剧审美观的必由之路。
“喜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美学上的一个范畴,是与优美、崇高、悲剧等范畴相对的美的表现形态。作为美学范畴的喜剧,其内部又包含一系列具体的样式,如滑稽、幽默、讽刺、机智、怪诞、荒诞等喜剧性范畴。“喜剧”的另一种含义是指艺术的形式。作为艺术形式的“喜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喜剧”仅指戏剧中的喜剧,即与悲剧、正剧相对的独立体裁。广义的“喜剧”则包括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本文讨论的喜剧,主要是美学范畴的喜剧,但在讨论过程中亦涉及其所代表的审美对象,即狭义的喜剧戏剧以及广义的喜剧艺术形式。
消费和娱乐是当今世界大众文化的核心,当下文化发展中的娱乐风潮是世界性的,它与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潮密切相关。早在90多年前,犹太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就曾说过:“这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视听的时代,机械复制的时代,灵光消逝的时代。”[1](P263)20世纪60年代,娱乐文化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提出了“我们终将娱乐至死”的预警[2](P161)。娱乐文化最活跃、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审美狂欢,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的复归和身体的快感。因为喜剧天生就是大众文化,喜剧所固有的快乐原则和游戏原则就具有瓦解崇高与消解神圣的功能,因此,喜剧便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并且渗透到文化消费的各个层面。大众娱乐文化的风行,极大开阔了喜剧的发展空间,丰富了世界喜剧文化的表现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喜剧的泛化和喜剧审美的碎片化、功利化与低俗化。
一、喜剧审美观重塑的必要性
中国虽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但国人可以通过各种“狂欢化”的喜剧审美行为,体验游戏和狂欢带来的快乐。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喜剧艺术市场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与制约,尚处于娱乐功能与宣教功能并峙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喜剧艺术的娱乐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扩张。21世纪以来,喜剧文化更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娱民”优势,迅速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中心。纵观当下中国的文化市场,在戏剧舞台上,开心麻花等团体的舞台喜剧迅速走红,而国产喜剧电影在票房榜上的霸主地位亦无人撼动;在电视荧屏上,脱口秀节目如火如荼,喜剧真人秀节目自2014年以来更如井喷般涌现。
在这个充滿喜剧元素、娱乐狂欢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喜剧艺术的受众及其审美观念、审美选择亦不可避免受到后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影响。当下中国的美学主调早已从推崇庄严的悲剧艺术转向嗜好滑稽幽默的喜剧艺术,从讽刺鞭挞的喜剧精神转向谑浪笑傲的游戏精神。国人的文化消费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娱乐元素被无限扩张、放大成为主导性元素,它跟从潮流,屈从市场,瓦解传统的审美标准。不在于意义、中心以及具体的人物形象,即“无理无本无根无绘无喻”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旨趣甚嚣尘上。
在喜剧影视方面,大量影视作品精神内涵简单,时尚性的浅层人生欲望及病态的慨叹方式,成为其审美观照的核心内涵,“大话”“无厘头”成为其典型风格。夸张、调侃、乖谬、癫狂、故作幼稚、胡搅蛮缠,以及各种粗俗的解构和语言游戏充斥影视剧。国产喜剧电影越来越趋向于娱乐化、浅表化,出现了叙事魅力缺失、意蕴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消解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张力。有的真人秀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以猎奇、猎艳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无聊的搞笑、庸俗的“隐私”暴露、生硬的竞技游戏,豪华的形式包装下是苍白的内容。还有喜剧小品中红色经典的戏说风,新闻节目中违背新闻真实性的说聊风,社教节目也热衷搞“情节演绎”。情色渲染、过度娱乐、恶性炒作已经成为当今媒体低俗化的重要表征。
审美观是人们对美的基本观点与看法,是审美观念的系统化,它包含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方面内容。审美观的背后体现的是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
当今时代,喜剧已然成为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刚需,崇尚个性解放、颠覆传统的青少年显然是喜剧文化的主要消费者。在笔者开展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喜剧小品受众的调查中,“你最喜爱央视春晚哪类节目”的选项中,4712人中有3243人选择了喜剧小品,占68.82%。而在为什么选择此类选项的回答中,选择“开心解闷”的占51.9%,其中男性占47.5%,女性高达54.6%。①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笑果文化发布《2018中国年轻态喜剧受众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年轻态喜剧成为综艺节目头部玩家,受众18-29岁为主。女性受众中的年轻人更多,并且大部分受众的职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有较多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和企业主,以及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除了电影消费,在线影视付费和在线音频付费在年轻态喜剧受众文娱消费中的渗透率也高达一半以上。”[3]可见,喜剧艺术已经成为青年人学习工作之余的重要娱乐消费形式。高强度的学习、快节奏的生活,使他们迫切需要解压放松的渠道,喜剧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需要正确喜剧审美观的引导,需要真正的思想舵手和艺术先锋引路,因为喜剧欣赏和创作的过程就是青少年构建审美心理结构的过程,对其素质结构的整体形成与提高,对促进其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喜剧具备宣泄功能,能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可以培养青少年清醒机敏的审美顿悟能力和乐观旷达的幽默态度。其次,喜剧提供社会镜子,具有警醒和预防功能。喜剧的审美教育方式是通过笑达到劝谕和警示效果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喜剧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增强客观自我意识,促进人的社会化。最后,喜剧审美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喜剧针砭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具有社会赏罚功能。
人的生命潜能的全面开发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只有经过审美教育的净化,才有可能实现。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对美的惊讶、赞赏和崇爱——这是人性态度的基础,舍此,人的文明素养的真正培育和形成便不可思议。”[4](P115)席勒也曾说过:“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导致社会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奠定了和谐。”[5](P83)当前,青少年喜剧审美观念错乱,喜剧精神严重缺失、理性价值诉求迷失,这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喜剧审美生态及喜剧审美观的偏误
当代中国媒介的“泛娱乐化”摈弃了娱乐游戏中的理性精神,抽空其人文蕴涵,不仅损害中国喜剧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国人的精神生活。
喜剧审美生态的恶化充分暴露了喜剧消费受众的审美观念的杂芜化和病态化。
(一)将喜剧性等同于可笑性
黑格尔曾说:“人们往往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淆起来了……笨拙或无意义的言行本身也没有多大喜剧性,尽管可以惹人笑。”[6](P142)“喜剧性”自诞生之日始,便与滑稽、可笑性诸概念混乱纠缠,迄今仍未厘清。英语中的comic,法语中的comigue,德语中的komik,作为表示性质的形容词,皆由名词comedy、comedic、komodic派生而成,而这些名词又都本源于古希腊酒神节中的komos(狂欢队伍)和komoidia(狂欢之歌),意指“喜剧”。因此,不论是词源生成还是词义演变,上述形容词都应该译成“喜剧性”。但是,由于语言转换与语言翻译的主观差异性,它们在中国化过程中常常被译成“滑稽”,遭遇误读。如柏格森的专著《笑:论滑稽的意义》中的comigue和黑格尔《美学》中的irony都被译作“滑稽”。[7](P64)从古希腊柏拉图探讨关于伦理学中的“可笑性”概念开始,到18世纪的菲尔丁,19世纪的黑格尔、里普斯、柏格森,再到20世纪的李斯托威尔、奈特、奥森、霍兰德、斯华贝、姚斯等,西方诸多美学家和哲学家都曾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对喜剧性和可笑性进行过见仁见智的理论分析。
简而言之,喜剧性是一个与可笑性既有深层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概念。喜剧性专指审美艺术世界中“有意义”的可笑性质。喜剧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其本质在于可笑性,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审美功能就是引人发笑。但笑作为一种人的本能的直接反应,自身不具备“审美价值”,只有通过诸如升华、纯化、反省等自我修行的演变,才能获得审美价值,成为喜剧性。因此,喜剧性是作为可笑性之净化或较高级的可笑性出现的。庸俗的噱头,神经质的笑,忽视了幽默内涵的滑稽,这些是没有喜剧性的。“喜剧性就是生命中的狂欢精神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反思中以智慧实现超越和自由的喜剧精神。”[8](P12)因此,喜剧的笑不是一般意义上笑,它的笑是含有价值判断的。
可是,不少受众却错误地认为,只要可笑的就是喜剧的。他们简单地将喜剧性与可笑性画上等号,模糊了喜剧与滑稽、游戏、闹剧、恶作剧的区别。生活就是为了开心,而不是为了承担责任,更不是为了承担痛苦,成为许多国人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人生观指导下的喜剧受众,很容易将玩世不恭的嬉笑怒骂当成诙谐幽默,把颠倒是非的信口雌黄当作艺术创新。当下的这种喜剧亚文化在青少年中很有市场,它们既有反传统的时尚性和创新性,也有背离主流价值导向的边缘性和消极性。
(二)将喜剧审美等同于“审丑”
作为喜剧审美客体的“丑”从来都是喜剧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学意义上的“丑”不同于伦理学范畴中与真善美相对立、与“假”和“恶”相一致的“丑”。西方正统的喜剧观点将“丑”定位于“美”的反面,同时将喜剧中的“丑角”定位于“否定性形象”。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9](P8),“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9](P16)。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影响了西方的喜剧理论和创作,喜剧文学描写的对象往往是“丑”“滑稽”“坏”和“缺点”,主题往往被限制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弱点上,所强调的往往是社会讽刺功能和惩罚功能。鲁迅也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喜剧与悲剧的区别:“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10](P297)但由此认定喜剧审美就是审丑并将之作为喜剧的经典定义显然是不适宜的,是片面的,这样就把许多正面喜剧形象拒绝于喜剧殿堂之外,既不符合喜剧艺术的创作实际,不符合中国的喜剧传统,也不利于喜剧艺术的健康发展。
从当今中国喜剧审美现状来看,不管是喜剧创作者还是喜剧受众,很多人混淆了喜剧美学范畴中的“丑”和伦理学范畴中的“丑”的概念,错误地将“丑角”等同于“丑”。当今文学领地中的丑陋意象如此之多,已互相呼应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动向。这种文学动向乃是对于审丑的强调。这些意象以其怪诞、畸形、病态、血腥、污秽、残酷给人以梦魇般的痛苦体验。这种文学动向已经波及一些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颠覆了一些正统的艺术法则。[11](P133)
还有不少受众直接将喜剧审美等同于“视角上”的审丑,这是导致审美扁平化、粗俗化的重要原因。审美层面的“丑”有两个层次,一是视觉层面上的“丑”角,即刻意追求外在装扮、言行举止滑稽可笑的人;一是精神层面的“丑”角,即道德、思想、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人们在嘲讽其行为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净化。一般来说,滑稽多偏重在揭示事物表现形态的缺陷,而幽默与讽刺则多针对对象的内在质性,所揭示的往往是由生命内蕴扭曲而产生的悖谬之丑。不少喜剧受众所刻意追求的只是外在可视的滑稽,满足于视角层面而非精神层面的“审丑”。他们错误地将“丑角”等同于“丑”,比如离奇的相貌、怪异的打扮、夸张的动作、出格的言谈,以及毫无逻辑的装疯卖傻等外在噱头;热衷于形式上的炫奇弄怪、翻新斗巧;热衷于对权威的揶揄“恶搞”,对一切具有经典性意味的人物、事件进行“恶作剧”式的调侃与戏弄。刘胡兰、董存瑞、《闪闪的红星》等都成了恶搞的对象。这些作品没有深层次地去发掘貌似“丑陋”或“丑恶”现象背后的内在缘由,从而进入真正的艺术“审丑”。
(三)将取法西方等同于创新
喜剧审美取向的媚外化是当代审美视野中的突出问题。受西方各种创作观念、艺术手法的影响,许多受众尤其青少年受众反叛中国喜剧传统,一味推崇西方的喜剧理论和创作方法,如时下正在流行的场地无界线,表演无脚本的沉浸式戏剧。这种追求即兴表演的偶发艺术,虽然使戏剧充满了无限可能性,但不少所谓的创新仅仅是把戏剧弱化为一次猎奇活动,而不是一次充满意义的精神之旅。还有上文提到的“审丑”现象,便是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精神主导的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史,实则就是丑日益升值、日益膨胀、日益成为主角的历史。譬如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那些被硬性移植的颇具黑色味道的喜剧,还有那些以极端怪诞的手法表达充满荒诞色彩哲学主题的“荒诞派戏剧”。着意强调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痛苦,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情绪的宣泄,一味追捧荒诞风格的“无厘头”,追求毫无节制的所谓“艺术自由”,而不是从揭示生活世界里所内蕴的根本性矛盾着眼,去分析构成怪诞或荒诞的审美基因,去领略荒诞所可能蕴含的深刻的哲理和美学内涵。这不但损害了时代审美气韵,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代社会应有的理性秩序。
三、喜剧审美的文化引导
喜剧受众的价值判断标准、审美观念以及审美取向都是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价值选择是需要导向的,互联网为喜剧审美的文化引领、喜剧审美教育提供了开放的园地和多元的途径。
(一)加强主流媒体喜剧审美的风向标作用
当今,媒介文化的影响大有超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趋势。主流媒体在现代文化危机治理中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它是喜剧审美的风向标,对国人的喜剧欣赏与创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加大喜剧精品的引领示范作用,多角度提升精细化制作水平。艺术的审美功能是通过艺术的感化作用实现的,优秀的喜剧作品具有较强的审美感化和教育作用。古罗马西塞罗曾说过:“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品性的模范,真理的反映。”[12](P575)全民娱乐时代的到来需要大量的喜剧创作,需要更多既具有文化感召力也具有市场占有力的喜剧精品。因此,要加强喜剧精品的创作,提升喜剧的正面价值和教育功能。今后的喜剧创作应该在主题立意上追求哲理化,努力把丰富的哲理内涵深蓄在风趣幽默的谈笑之中。在强调哲理性的前提下,追求更加完美的艺术化的表达。主流媒体应该对受众始终秉持理念落地、人情复归、文化濡化的传播策略。喜剧艺术可以描写丑,但描写丑只是创造艺术美的一个手段,“生活的丑”只有蕴藏了作家、艺术家的审美评价和审美态度,才能转化为“艺术的丑”。正如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所说:“否定性艺术形象只有具备社会认识价值、伦理教育价值和情感愉悦价值的高度完美统一,才能成为激发深刻美感的审美对象,转化为艺术美。”[13](P200)喜剧创作的着眼点应从人民的生活出发,更好地激发受众自身的“共情”心理;更好地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喜剧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广泛开展喜剧科普活动,澄清喜剧审美核心概念。主流媒体要通过开辟喜剧专栏、打造专业化的喜剧科普平台、举办喜剧知识竞赛等方式,帮助受众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幽默,什么才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笑。要让受众明白喜剧的滑稽和不严肃是表面的,它骨子里却是严肃的。只有使之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赋予其一定的社会伦理内容,可笑性才会具有喜剧性,才具有审美意义。运用多样化的生动的形式,帮助受众端正喜剧审美观,提升整体社会的审美情趣。如中央电视台小品大赛曾设置知识问答、专家解读和观察表演环节;喜剧真人秀节目《欢乐喜剧人》也曾通过访谈方式加入专家点评,不仅弥补了小品评价体系中专家缺席的不足,还极大地普及了喜剧理论知识和表演技巧,努力实现科普与娱乐化表现形式的融合,满足公众对官方主流媒体不断提高的现实期待。
(二)加强学校喜剧审美的教育力度
当前,方兴未艾的“恶搞”式喜剧潮流,把国人引向喜剧审美的歧途,而喜剧审美教育却严重缺位。不仅教材中缺少喜剧经典的美学示范,校园文化建设也缺少喜剧精神的深度涵养。从美学范畴来看,优美、崇高、悲剧和喜剧是美的四大范畴。事实上,我们的学校美育历来被习惯性地理解为美(优美)的教育,认为美育就是用优美、和谐来感化人的心灵,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亦多以优美为审美对象,如优美的风景画、动听的音乐、曼妙的舞姿等。崇高的教育则往往渗透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中。而悲剧,作为西方戏剧的经典范式,在中高等教育阶段亦多有涉及,唯有喜剧成了不同层次学校文化建设中的“零余者”。或者偶尔受到关注,但由于过分强调其教化功能,多采用说教式、灌输式的硬性教育,喜剧审美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学校则走向了反面,在举办活动时,错误地将流行文化等同于青少年主流文化,将平庸化逗笑取乐视为新潮、奉为时尚,将深刻而崇高的东西视为落伍而遭鄙弃,助长了学生庸俗的艺术审美价值观。今后学校的喜剧审美教育,需要着重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对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喜剧文化教育,树立文化自信。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说,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他认为诗、礼、乐三者是教化民众的载体与手段。而且“乐”应该是中正平和之“乐”,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喜剧艺术的基本审美倾向。这种“中和”准则也表现在喜剧手法上以诙谐幽默居多、浪漫和解为主。较之以“丑”为主要表现对象、以讽刺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西方喜剧,中国古代审美传统则是将爱美、求美当作审美活动的中心目标,“丑”通常处于辅助地位,美丑具有相对性和联通性。中国喜剧的审美传统还表现在积极干预生活,寓庄于谐,寓教于乐。中国的文艺理论注重表达情感或志向,讲究诗言志,注重文以载道,因此,传统喜剧艺术中亦有较多的伦理道德内容,强调的是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统一。这些喜剧审美传统在中国当代仍然没有过时,需要青少年继续传承,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当然,艺术鼓励创新,创新是艺术永恒的生命主题,但创新并非无源之水,创新亦不是猎奇,不是搞怪,不是全盘西化、以洋为尊为美。抛弃古老的喜剧传统,单凭追新鹜奇,不可能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喜剧文明。我们鼓励“拿来主义”,更鼓励拿来之后精心改造,使其适应中国水土。新时代中国喜剧审美必须契合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集体审美意识,喜剧创新也必须秉承艺术本身的发展脉络,延续中国喜剧文化传统的深厚血脉。
其次,创新喜剧审美教育方式,提高学校审美素质培养成效。喜剧审美教育“在于训练我们发现可笑的事物的本领;在各种热情和时尚的掩盖之下,在五花八门的恶劣的或者善良的本性之中,甚至在庄严肃穆之中,轻易而敏捷地发现可笑的事物”[14](P152)。喜剧引起的笑,不是基于生理本能的机械动作,而是包含着理性的内容,因此,训练人们发现可笑的人和事的能力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创作一个能使人发出“有意味的笑”的作品更不容易。教育工作者只有充分把握时代的文化症候,了解审美教育和受教育者的特点并加以运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审美心理差异和个性差异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以戏剧教育为例。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珂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他认为:6-15岁为戏剧教育的初级阶段,以“人格养成”为中心,着重于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塑造;15到18岁为戏剧教育的成长期或发展期,要以编导为主,以制作为辅,着重塑造学生“艺术”的人格;对18岁以后的成年人而言,戏剧教育主要以审美欣赏的方式开展,着重培养人的审美素养。[15]
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喜剧审美教育的形态特征,了解当下青少年的审美需求,从传统灌输型教育转向启发型、体验型教育。体验性、娱乐性、自发性和主动性是审美教育的形态特征,更是审美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显著特点。审美不是认识活动,而是情感的体验。喜剧审美教育同样重在“以情动人”。严肃的理性说教换成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活动,才会产生“寓教于乐”的审美效应。
学校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开展喜剧审美教育活动,如通过创办班级喜剧科普专栏(专刊)、举办幽默故事会、组织喜剧作品创作大赛、成立校园剧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带领学生参与喜剧欣赏与创作实践,使青少年积极主动融入其中并乐在其中,从而得到一种“自我实现”乃至“自我教育”的审美目的。
(三)构建和优化喜剧传播立体化体系
当今社会,人类艺术正在经历一次深远的变革。以连结性和互动性为特质、以“活动艺术”形式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艺术,使传统“受众”的概念完全被颠覆,受众既是接受者,也可以是创作者,他们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进行连结和交流。喜剧真人秀风潮就体现了这种互动性生产的过程。年轻的一代己经不习惯电视的单向点播,他们把目光更多转向互联网和剧场,他们需要更为灵活更加自由的操作空间和互动平台。
首先,建立移动网络喜剧资源共享平台。在群体性仪式传播已经逐渐让位于电子媒介仪式传播的今天,各级各类学校、城市社区、文化艺术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结合“互联网+”发展新形势,加强移动互联网中喜剧美育的内容和形式建设,扩大优质喜剧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如开辟校园喜剧网站,社区喜剧网,加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平台建设。同时要科学开展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的媒介批评意识。青少年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自觉地把网络和社交媒体作为喜剧创作实践的重要平台。我们在肯定社会微观权力互动对喜剧文化构建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一些“伪文化实践”对喜剧文化本身的冲击,引导学生端正媒介消费观,合理利用媒介资源,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其次,发挥剧场的磁场效应。就目前来看,网络视频、电影、电视媒体是喜剧节目的主要播放形式,除此之外,剧场也是喜剧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调查显示,目前剧场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一线城市中曲艺、戏剧的演出市场尚未成熟,二线三线城市尚未开发。而花不多的钱进剧场看一场喜剧演出是许多青年观众的理想选择。更有相当多的受众已不满足被动观看,他们希望有机会亲自参与表演和创作。根据笔者的调查问卷结果,“如有机会愿意花多少钱看一场纯喜剧的小品演出”这一问题,选择50元的受访者最多,占41.3%;其次是100元;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选择300元看一场小品演出的人数占14%。“如果有机会愿意亲自表演或创作喜剧小品吗”这一问题,受访者选择“愿意”和“非常愿意”的高达79.2%,而选择“非常愿意”的35岁以下青年尤其男性青年、大学生群体最高。②可见,提供舞台表演的剧场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相声、脱口秀、喜剧小品、二人转等语言类喜剧节目,其最佳生存空间不是荧屏而是剧场,因为剧场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舞台美术把剧场表演空间立体化,使观众置身于这个介于虚幻和真实的立体空间里。在这里,以演员为中心的动作空间、以角色为中心的审美空间、以观众为中心的知觉空间、以参与者为中心的交往空间构成了多层次的复杂网状结构。而这个网络关系运行的终极目标是演员通过角色表演,实现与观众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在当今时代,喜剧的舞台不能再是“我演你看”的“当众孤独”,所以,应当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少年的创造意识,让更多年轻受众直接参与演创过程,使他们在参与喜剧创作或表演的体验中,生发自由联想,启迪理性思考,收获人生感悟。
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梅瑞狄斯曾说过:“一国文明的最好考量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喜剧思想和喜剧发达与否,而真正喜剧的考验则在于它能否引起有深意的笑。”[16](P77)喜剧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作为当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尤其是作为青少年主动选择的流行艺术,理当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美育不可或缺甚至首选的艺术形式。青少年喜剧审美教育事关国民的灵魂塑造和时代精神构建,事关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媒体人、政府管理者都责无旁贷。
注释:
①②参见:谢旭慧《全国范围内喜剧小品受众问卷“我眼中的喜剧小品”调查数据》,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