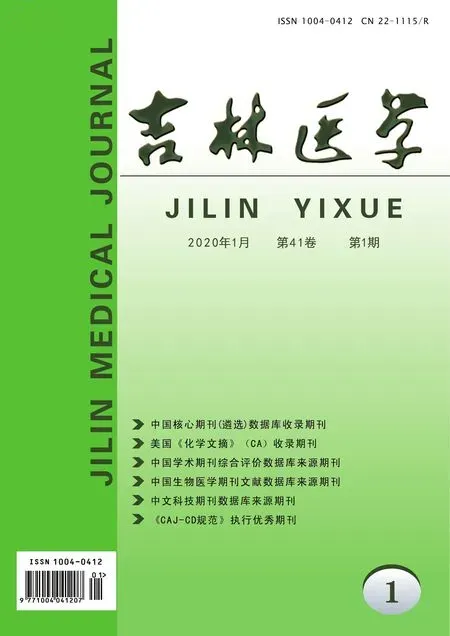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合并肺栓塞1例报告
曾祥雨,季 博,刘春梅
(1.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1;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 250011)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一种由免疫介导的血小板减少性、出血性疾病,但有文献报道ITP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风险反而高于正常人群[1]。目前对于血栓的预防及治疗尚未纳入ITP诊疗指南,怎样兼顾预防出血与抗凝治疗仍是一大难题。本文对我院周围血管病科收治的1例ITP合并肺栓塞患者进行回顾性报道,为此类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1 病历摘要
患者男,29岁,因“胸部憋闷1 d”于2017年12月26日疑为“肺栓塞”收入我院周围血管病科。既往2年前因扭伤致左下肢粗肿、胀痛,于外院治疗,当时未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好转后出院;6个月前因左踝处破溃于当地医院行左下肢静脉彩超检查,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于我院周围血管病科住院治疗,入院后查血小板(PLT):101×109/L,经系统治疗溃疡愈合后出院。2017年12月25日患者突感胸部憋闷,卧床时憋闷感消失,活动后加重,无肢体突发粗肿。门诊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未见新发血栓。查体:体温:36.2℃,脉搏:78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96/70 mmHg(1 mmHg=0.133 3 kPa),血氧饱和度:90%。双下肢皮色皮温可,无明显粗肿,腓肠肌松软无挤压痛。入院后急查心电图、心脏彩超、肺动脉CTA、血常规、凝血四项、D-二聚体、心肌酶谱、BNP、肌钙蛋白等。心电图示:①窦性心动过速;②V1 rSr's型,V3-4ST上抬;③SⅠ、QⅢ、TⅢ图形改变。心脏彩超示:①右室扩大;②三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肺动脉高压;③左室收缩功能正常(符合肺动脉血栓栓塞症超声改变)。肺动脉CTA示:①双侧肺动脉栓塞;②双肺炎性反应。附见:脂肪肝。APTT:68.6sec,D-二聚体:3.03 μg/ml,PLT:34×109/L,BNP:4 970.1 pg/ml,CK-MB:28 U/L,LDH:312 U/L。入院诊断:①肺栓塞;②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③脂肪肝;④PLT减少症。治疗上予持续低流量吸氧,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静滴尿激酶及活血化瘀类药物。2017年12月27日查PLT:30×109/L,停用低分子肝素、尿激酶,改为口服利伐沙班,20 mg,1次/d以抗凝。经血液科会诊后完善相关检查,并于2017年12月28日行骨髓穿刺+活检术,骨髓分析结论:原发血小板减少症。2017年12月29日复查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发现右股浅、腘静脉近端及右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右腘静脉远端、小腿深静脉血流缓滞。2017年12月31日查PLT:26×109/L。根据血液科会诊意见,予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40 mg,1次/d,连用4 d,皮下注射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15 000 U,1次/d,连用9 d,并明确诊断: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后PLT维持在39×109/L~55×109/L之间。期间复查彩超见右下肢深静脉血栓逐渐向上蔓延至股总静脉远端,2018年1月9日停用利伐沙班,改为静脉滴注阿加曲班10 mg,1次/d。2018年1月11日复查肺动脉CTA见双侧肺动脉部分血管内血栓较前减少。2018年1月19日复查彩超见右股浅静脉近端血栓延伸至股总静脉远端且多处与管壁游离,与患者沟通后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加用华法林钠片2.5 mg,1次/d。2018年1月22日查APTT:106.0sec,停用阿加曲班,继服华法林,根据国际标准化比值最终将华法林调整至4.375 mg,1次/d,2018年2月2日国际标准化比值示:2.05。2018年2月22日复查彩超,见滤器位置良好,游离血栓消失,患者无明显不适,行“下腔静脉滤器取出术”后患者出院。出院后患者继服华法林抗凝,定期门诊复诊,未见血栓进一步发展。
2 讨论
ITP作为一种常见的出血性疾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PLT破坏增多、PLT生成减少相关。研究表明抗体介导的PLT破坏以及细胞毒性T细胞介导的PLT溶解可能是PLT破坏增多的主要原因;巨核细胞成熟障碍和巨核细胞凋亡异常则可能导致PLT生成减少[2]。
VTE包括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成,年发病率为0.1%,美国每年约有60万人被诊断为深静脉血栓形成,且在住院患者中肺栓塞致死率约为5%~10%[3],严重威胁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早在1856年Virchow就提出了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血管内皮损伤、血流状态的改变、血液高凝。现代研究表明VTE是一种多基因多因素性疾病,凝血与纤溶的失衡会导致VTE的发生,其形成机制与炎性反应和血液高凝状态有关。静脉血栓虽然也包含PLT,但传统理论认为PLT在静脉血栓形成的过程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其对动脉血栓形成的影响远大于静脉血栓形成。但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PLT在静脉血栓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媒介为PLT胞内相关蛋白,通过增大PLT体积、促进PLT活化聚集等诱导静脉血栓形成,且PLT可通过其GP1bα受体、P选择素和早期炎性反应细胞共同促使白细胞募集及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形成来诱发VTE[3]。
虽然ITP患者PLT数量减少,临床表现多为出血症状,但有文献报道ITP患者患有VTE的风险较正常人群高出两倍[4]。ITP患者血栓形成的机制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在正常的血液循环中,PLT只有少量被活化,多数是处于静息状态,但ITP患者因PLT-白细胞聚集,内皮细胞受损激活抗PLT自身抗体,大量PLT活化,导致PLT微粒增多从而激活凝血瀑布,诱发血栓形成[5]。而PLT抗体异常活化同样可以造成PLT活化聚集,有研究推断Anti-GPⅨ抗体在体内可明显导致PLT减少,同时可诱发肺部微血栓形成,在体外却可引起PLT活化聚集;CD9抗体也可以诱导PLT减少并可能与肺部血栓形成相关;GPⅡb/Ⅲa抗体可使P选择素分泌增加,从而促进了PLT聚集[2]。以上这些PLT抗体的异常活化都可能与血栓形成风险增加相关。ITP患者的免疫力较正常人低下,因此更易受到细菌、病毒等感染,易导致血管内皮损伤,且革兰阴性菌产生的内毒素可引起组织因子、TNF、ⅠL-1b的释放,革兰阳性菌可以产生细菌黏多糖直接激活Ⅻ因子,加速血液凝固[6]。ITP患者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包括手术、恶性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高龄、肥胖、高血压、既往血栓史和抗心磷脂综合征等[7-8],且经过脾切除术、达那唑或丙种球蛋白等治疗后也有血栓事件的发生[2],这些与非ITP患者形成血栓的危险因素大致相同。因此,无论患者是否患有ITP,当存在以上危险因素时都应格外注意预防血栓形成。
本例患者通过监测PLT计数、凝血及血栓情况,权衡抗凝与预防出血的相互关系,在治疗上适当采取提升PLT措施并及时对抗凝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这提示我们在对于ITP合并VTE患者的治疗方案的制定上,医者应当平衡血栓形成与PLT减少的矛盾,评判患者的出血风险,寻求合适的抗凝方法,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目前ITP患者提升PLT的手段主要是减少PLT破坏及促进PLT生成,多数ITP的治疗如输注PLT、切脾、应用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等会加剧血栓形成的风险。本例患者发生肺栓塞入院前,因不了解自身病情,未进行任何ITP的相关治疗,住院期间患者PLT持续降低,因此使用地塞米松及重组人PLT生成素注射液以升高PLT,但PLT升高后发现血栓不断向上蔓延,一方面佐证了血栓易发生于ITP患者治疗过程中PLT上升阶段[8],另一方面也考虑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会使血液呈高凝状态[5],诱发了血栓形成及发展而导致。所以,若患者无明显出血倾向,应将PLT计数提高到足以安全地给予抗凝剂使用水平后,停止相关ITP治疗,给予充分抗凝并密切监测PLT计数和凝血状况,避免加剧出血风险及血栓进一步发展。
华法林是一种香豆素类抗凝药物,通过抑制维生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来阻断有活性的还原型维生素K的形成,从而干扰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的活化和蛋白C、蛋白S的合成而起到抗凝作用。华法林作为一种应用时间较长的口服抗凝药物,临床应用十分广泛,但华法林起效缓慢,且有治疗个体差异大,易受其他药物、食物影响及治疗窗窄、需要定期监测凝血状况等缺点。2010年后利伐沙班、阿哌沙班等新型抗凝药被美国FDA批准应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华法林的一些缺点,但新型抗凝药对于中重肝肾功能损伤患者需要禁用或者调整剂量,而且没有拮抗药、没有方便的监测血药浓度的手段限制了它们的作用范围[9],对于复杂病情引起的静脉血栓形成的抗凝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临床研究。通过本例患者证明华法林在病情复杂、需要多次调整抗凝方案时仍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华法林在抗凝血临床治疗中依然无法被新型抗凝药物完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