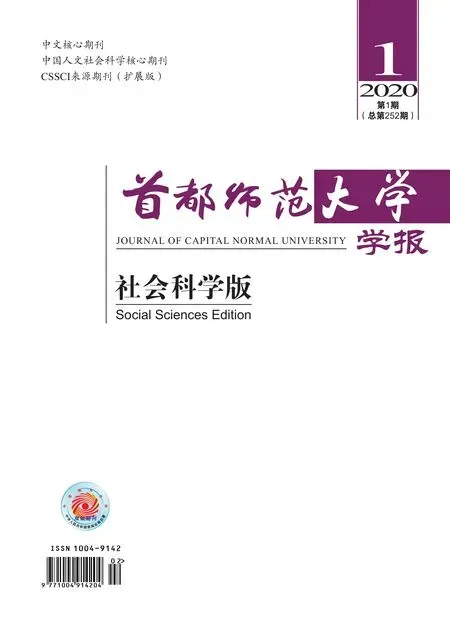现当代西方史学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张广智
戊戌秋日,我有幸先目睹了邓京力教授的大作《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读着,读着,“1990年代”“西方史学理论”“主体意识”等关键词一一向我们走来,疏凿源流,扶隐钩沉,辩证因果,探究真伪,终结硕果,成为当下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新作。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西方史学理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这种演变的理论研究就成为学界之要务。邓京力教授以一位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学贯西东,情思中外,对近二十年的西方史学理论,从后现代主义到新文化史,从语境解构到历史书写,从西方史学史到全球史学史,都进行了切中肯綮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家对该领域的卓越贡献。①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封底。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我想这一旨趣,应当是中国学人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以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立足点。上述笔者对《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评语,正切合这一主旨。唯其如此,21世纪的中国史学才能步入坦途,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一、反思于世纪之交
已亥再读,又有感悟。
本书著者所要探究的“近二十年”,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20世纪的最后十年,21世纪的最初十年。这一时间节点,稍知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便知,这个变化如作者所言,是“整体性变化”②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1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以及对这种“挑战”的“应战”,使得国际史坛一时风生水起、活跃非凡,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名家,行旅世界,随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就我个人而言,也曾不止一次遇见过伊格尔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大家,相聚浦江两岸,研讨在复旦园内,争辩在丽娃河畔(华东师范大学)……
确实如此。新旧世纪交替,时光容器变异,世人心绪纷繁,欢乐与惆怅同在,展望与回眸相伴,历史学家尤然。在这样的时刻,忧心忡忡的“史学危机”压得史界人士喘不过气来,史学的传统堤坝再一次被冲破了,乃至危及历史研究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史学现状,在这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而来的时候,反思过往,乃至追思到史学专业化以来所走过的路程,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史学,何去何从?上述这“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的生态,作为像我这样的过来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回顾历史,当人们把时空切换到一百二十多年前的1890年新旧史学之争的景况,也立刻唤醒我们的再思。
那次西方新旧史学之争,酝酿于19世纪下半叶,这是对占据当时史坛中心地位的兰克及其学派的挑战。它是从营垒内部揭竿而起的,兰克的弟子雅各布·布克哈特向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在西方史学的这次反思与革新的潮流中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1886年,兰克逝世了,卡尔·兰普勒希特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主要是在他同兰克学派之间的争论中进行的。1891年,兰普勒希特的代表作《德意志史》(共12卷)首卷出版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书迅即在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激烈争论。20世纪初,他的《文化史的方法论》问世,更把这场新旧史学之争推向高潮,在历史的对象、主题和方法等方面与兰克学派展开了一场大争论。略例一二: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囿于政治军事史,在他们那里,历史的主角总是少数精英人物,兰普勒希特与之不同,他认为历史应当包含更广阔的内容;前者之要务是记叙历史,以重建过去,孜孜于探究历史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后者则要探明事实发生与变化的理论依据;新派立意创新,致力于创建“新型的文化史学派”,阐发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文化史观念。在兰普勒希特的努力下,汇集成果有40卷的《兰普勒希特对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贡献》,如此等等。总之,以兰普勒希特为首的新史学派与兰克学派这场名为“历史方法论”的激烈争辩,实质上涉及历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这是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西方新旧史学之间全面抗衡的“前哨战”。对上述新旧史学世纪交替之际的争论,伊格尔斯在其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认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③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可见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大意义。
这场争论确实伴随20世纪西方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过程,没有停息过。此后,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于1900年成立了一个“国际综合中心”,同年创办《历史综合杂志》。他的史学要旨是挑战传统史学,反对兰克史学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倡导历史学的综合研究,也就是促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贝尔的史学思想,不仅被认为是一匹安置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而且更直接哺育了年鉴学派的诞生。
世纪之交的争论在大洋彼岸也激起了回应,鲁滨逊于1912年以其名作《新史学》,直接参与了西方史学世纪之交的反思浪潮,此后更有卡尔·贝克尔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推波助澜。贝克尔十分强调现在的决定意义和认识中的主观意志,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有助于当时批判传统史学的客观性理念,从而促进了从19世纪西方史学的客观主义向20世纪西方史学的相对主义转化。
考查这两次世纪之交的争论,确实表现出“某种相似性”①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33页。。就其总体而言,我以为皆显示出时代与社会进步对历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但史学的进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史学自身的反思(反省),前次的反思推动了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随后出现的新史学,邓京力在书中这样写道:它“为20世纪的历史学提供了取代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它以深层、大众、结构的历史超越了表层、精英、事件的历史,以可计量的、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超越了单纯定性的、个别性的分析方法,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视域超越了政治、外交、战争的狭隘性”②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33页。。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点染出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色彩绚烂,正如张耕华教授所指出的,是作者以深厚的专题个案研究为基础,对西方史学做出了综合性考查的结果。③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张耕华在封底的评论。
反思于世纪之交,不管是前次的大争论,还是今次的大论争,都为后世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后人的再出发创造了条件。
二、展望在新时代
怡人的春风拂面,我们生活在新时代,这就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歇息,唯有在前人业绩的基础上再出发,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这不由让我想起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最后说过的话:“史学史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应当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④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勒高夫这充满自信的话,多少年过去了仍没有过时,鼓舞我们对未来史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必将“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
展望在新时代。我们应当以敏锐的中国眼光观察西方史学近20年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⑤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2页。,跟上史学的前沿,努力与国际史学界相向而行,做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应有贡献。对此宏愿,当应聚众共议,借以群策群力,方能奋发有为。在这里,笔者仅就如何观察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性变化”,略陈管见。⑥笔者在《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6日“学术版”刊发的《从三个维度观察史学未来发展趋向》,于此略有小议,可参见。
(一)跨学科趋势地不断扩大
从西方史学史的视角言,西方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至19世纪的兰克大成矣。兰克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致力于近代早期欧洲诸国历史的编纂,兰克差不多为欧洲各国写就一部历史,这一史学编纂的国别史传统被20世纪的西方新史学突破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史学”伸出了双手,一只与自然科学牵手,另一只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它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束缚在单一的纯历史学研究模式中。从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新同盟军”的呐喊⑦参见鲁滨逊:《新史学》,他在书中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在他看来,西方史学需要充分利用“新同盟军”,充分“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页。,到年鉴学派的《〈年鉴〉创刊词》中的“打破学科之间围墙”的呼唤①参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其目的都在倡导跨学科研究,随之而来出现了现代史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比如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和影视史学等,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在中国,自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新史学浪潮也是一浪接一浪。综观中外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重新定向”;60年代以来,更发生了新变化。尽管变幻莫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跨学科、跨国研究的趋势锐不可当,观察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闪光的维度,不管是中国史学,也不管是域外史学。
(二)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兴旺
有道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未来史学的发展尤其如此,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互相了解之日。所以比较史学是一门值得提倡的新学问,将世界大同流派的史学,汇于一室,作比较研究,撷精取华,汰其糟粕,博大的新史学,将自此产生。”②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第2版,第7页。其实,中外史学交流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比如在中国史学的“青年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典在中土的翻译与流传,中国古代史学对日本、朝鲜和越南史学的影响;近世以降中外史学,尤其是19世纪末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与对话。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就其总体而言,是单向的输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及80年代后两次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高潮,都是如此。直至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时,中外史学交流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5年在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此可以这样说,我们说的中外史学交流再也不是域外史学的单向输入,而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史学的双向交流。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及影响的不断提升和深入,在中国正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桥梁的大好形势下,中外史学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必定出现新局面,呈现出不断兴旺的史学场景,终成为观察未来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一个亮丽的维度。但当下面对西方学术文化上的霸权,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比如,随着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当成为丰富史学史的内涵和促进该学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就有利于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引导中外史学交流的工作步入正确的轨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自2007年起,笔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集全国这一领域的精英之力,历十年之辛劳,终成《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不久即可奉献给学界。
(三)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增强
写下这个子题,我蓦然想起1992年春日,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E.P.汤普森已沉疴缠身,但仍抱病接受了中国学者刘为的访谈。刘为最后问:“您坚持什么?”答:“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③访谈全文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翌年8月28日,他就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句诤言,已越过时空,响遏行云,在历史的长空中久久回荡……
由此,我陷入了沉思。一位生活在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面临“二战”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空前信仰危机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环境,E.P.汤普森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笃信唯物史观,不只令我们肃然起敬,也激励我们在山河温润的新时代守望创新,砥砺奋进。
为此,以我们从事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而言,我以自己多年的实践证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确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我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历史观”,即指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于历史学研究,不啻是一场革命,开创了历史学的新篇章,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这包括它的历史理论(或历史观)和史学理论,但就其主要和基本的一面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或核心理念)①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学界见仁见智,自可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探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为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提供了原则性的理论根据。恩格斯的这一精辟论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下的著名的经典性定义,其文脉是联贯相通的。是常青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对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也自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又需对各方具有开放性,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墨守他们的个别论述而不放,这实在是疏离唯物史观的本意,当为我们所不取。在这里,我特别引出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放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同样的是,我们对待唯物史观也怎么可以“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众所周知,考察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是它的史学发展史),它总是在曲折坎坷中走来,无论是正本清源也好,还是回到原典也罢,其实质都是为在发展中求变,在变中得到发展,以寻求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唯其如此,也只有这样,唯物史观才能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邓京力教授的大作,当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相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显示,其成果亦丰,将成为我们观察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一个难以绕开的维度。
三、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人间最美四月天。此刻,让我想到了林徽因的名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轻风、云烟、星子、细雨、百花……,这些意象,缀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图画,让人们觉得人间四月,一切都那么美好。
正是在这个春和景明、万木竞秀的季节,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京华的春色点翠,为首都的春天增艳,为这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添上了最美的一笔。
我有幸与会,感慨良多,然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会议充满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活力,年轻一代正在茁壮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寄语青年一代时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同样,中国史学的未来也在青年。西方史学,中国眼光,一批年轻人可望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大显身手。进言之,他们也将在重绘世界史学版图中,在实现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做出重大的贡献。于此,我遐想不已,耳畔又传来了林徽因的天籁之音:“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想到这里,我发现在这人间最美的四月里,原来最美的却是这些个“年轻一代”,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