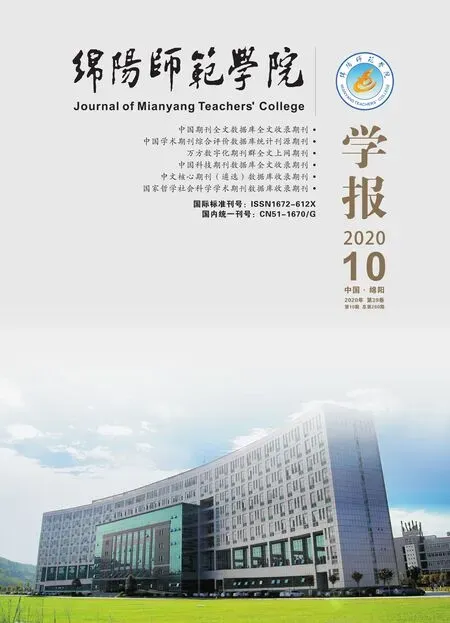朱熹“心统性情”说探析
所应洲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40)
“心统性情”一语最早可以考据的文字依据来自于张载,尽管张载本人没有对该学说有较大的展开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心统性情”说却得到朱熹极大的赞誉,将其和程伊川的“性即理”以及孟子的“四端学说”相提并论。《近思录》中有语,“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此话有大功”,朱熹也以此为框架来构建和完善了自己的心性理论。如此,该学说对朱熹哲学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9作为宋明时期第一个辨析心性关系的思想家,张载认为太虚和气的结合构成了性的名号,而心之名则来自性和知觉的结合。可见,在张载处就已经将心赋予了知觉能动的功能特点。
但是,在整个心性关系发展史上,张载还不是首开先河的人。孟子以“四端之说”来论述人性本善,第一次详细讨论了“性”的概念。由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为内在生而俱足的善性,在一定情景的促发之下可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地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个善心。朱熹“心统性情”说的提出和成型,就是基于前人性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当然,除却孟子和张载,作为道南学派的传承人,程伊川的“性即理”说更是为朱熹心性论注入了核心思想。朱熹云:“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五)两位前人的思想构成朱熹心性哲学体系形成的两大支柱。
朱熹对于心性关系的体验和认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李延平去世后的两次大悟——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在第一次大悟中朱熹体悟到“人之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大体莫非已发,殊其末发者为未尝发耳”[2]9。即是说,人生而为人,终其一生都只是活于已发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中,而内在之大体却依然敛蓄未发。显然,此时的朱熹将人的已发之情感和未发之性完全地隔离切分开。他此时修习的目的,即是在追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在第二次大悟,也就是己丑之悟中,在经过和张栻等湖湘学者的论辩之后,朱熹才对心性情关系有了深刻且完整的认识。未发之中是为性,为心之体;已发则为情,是为心之用;心统性情,贯通于已发未发之间。究其本体来说,性是纯良至善的,而究其发用来说,情有时善有时不善。“因此,要通达已发未发之旨、中和之道,心必以敬主性情,在日用处省察推明,这即是‘用敬’、‘致知’的为学工夫。”[3]74由此,朱熹的心性学说基本成熟,其后的研究也多是基于此思想而深入发展的。博前人之所长,而又融贯于自家之所得,方得朱子之心统性情说。
一、心论
心是朱熹心性论学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朱子语类》,卷二十)尽管朱熹多以理学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但是朱熹对心的作用和特点的体悟和认识更是超出常人。以至于钱穆有语:“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且一反常规,直接将朱学归于心学。相比于孟子将由人的道德情感而发出的四端为心,以此来揭示人性本善。朱熹将心视为人全身知觉运用的主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2]149也就是说人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心。这种主宰不仅仅局限于四肢感官的活动和认知,更是体现在道德修养上的引导。
朱熹早年师从李延平,学习道南指诀,体验未发之气象,即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也就是要将心保持于各种内在的情感知觉未发状态,从而悟得本体,由此可见心本身“可动”的特点。这种特点或言功能即是“虚灵知觉”,“虚”指的是心在没有接触或者感应外界之物时,呈现的状态是虚空澄净的,即是“心不可有一物”;而“灵”是指当外物被心所照见的时候,心会根据外物的状态作出相应的反映。就好似一面镜子,镜前什么也没有的时候,镜中亦是一片空无。而当有物时,镜子自然会反映出相应的影像。所以,当进入心中的物移开之后,心就又会回到原来的虚静状态。即是物来而随感顺应,物去则归于澄静,不着滞留。
这种“虚灵”的特点来自心的“知觉”功能。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书面意义上的知觉,朱熹的心之“知觉”表示心可以察觉感知的能力。这是一个“活的”能动的心,可以对存在与外的物作出反映。显然,这种“知觉”功能需要在外物的凸显之下才可以表现出来,但是作为心与生俱来的功能,“知觉”是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外物而独立存在的。即是没有外物照进,“知觉”也作为一种默而不发的能力保存于心中。由此可见,朱熹所要修达的未发之涵养之功,就是要让心之知觉不去接达外物,使心不被外物所扰,由此而保持心原本的虚静状态。
但人是活的,心是“活的”,知觉的功能接物而发。没有一定的修养工夫,心不可能一直保持虚静,而是会顺应不同的照进外物而作出不同的知觉。这样的知觉往往是良莠不齐的。故而,在没有操持的情况下,人心也就会有善有恶。而之所以会有人心和道心的区分,也就是因为心所知觉的对象不同导致的。人心知觉由形气所生之物事,故可善可恶,故“惟危”。道心知觉虚静之性,纯静明善,但亦受形气遮蔽而幽微难发,故而“惟微”。如此,道心和人心都只是一个心,不过是由于此心之知觉对象的差异而导致差异罢了。
那么心究竟为何物?朱熹并没有给心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从概念上来解释心的内涵。就如孔子从来没有统一而精准地定义过“仁”一样,朱熹之心,亦是在其辩说心性关系时显示心的特征和作用。为了方便理解,可以从逻辑层面将主宰之心以形而上之体和形而下之用以作区分。作为体用之统一体,心在未发时表现为寂然本体,是人之本心。在已发时则表现为感通之用,即是从作用层面来讲的知觉之用,其中自然也包括情。但就心本身的存在而言,心之体和心之用是混为一体的,心有体用。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叠加或者包容,而是一个有生命联动的结合,体在用中,而用即是体,既存在又流行。如此,就心本身而言,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形而上或者形而下其中的一端。既然心既具有主宰口鼻耳目等感官之作用和接事应物的知觉之功,又是虚灵澄明的本体,所以无论是从作用特点还是从其存在的角度而言,心都是贯彻形上形下之间的。
二、性论
要阐释朱熹心统性情说中的性,就要先了解程伊川的“性即理”说。前文已经论述过,“横渠之心统性情和伊川之性即理也是颠扑不破之理”,朱熹之性即是继承和发展了伊川的性理学说而得来。由字面意思得来,性即理表示性和理在本质上的某种一致性或言统一性。在宋明各家中,虽各有所得,各有侧重,但是理的意思大体一致。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讲,理是世间万千物事运行发展的规律和法则;就本体论而言,理则是所有事物生成的原因,是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这是一种外在的客观之理,作为所有物事存在运行的依据,理独立自足地存在。即这是一个没有具体形态的实体,需要借助形而下的器物来被人认知体验,但是理本身的存在则是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
如上,因为理是客观外在的,故而人想要认知理,想要贯通天人心理之间的阻隔,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办法。由于心具有知觉的功能,可以借助心来认识理,以心来统摄理之内容。然而由于理是形而上的,而作为知觉功用的心是形而下的,所以这样知觉所得依然是心理二分的结果。
朱熹为了贯通心理则另辟蹊径,在绝对形上的理和形下的心之间置放上性这一本体,将性赋予两重性质,从而融贯心理。所以,作为受形气肉体所困的人,认识性就是认识理的途径。由于要能够被心之知觉接应到,所以不同于理,性就不能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实体而独立存在。性一定要依存于具体的事物或者存在于一定的形气之中,如此,它才可以借该载体而存在。而根据程伊川的“性即是理”,下贯于人的性其实是完整地保存有理,而由于形而下的形气所遮蔽,故而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也缘于此,性才有了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区分。气质之性表示人最本始的情感欲望,它趋于中性,可善可不善取决于其被诱导的方向;而天地之性则表示了不被气质所蒙蔽的本性,也就是理本身。最早将性如此二分的是张横渠,在他看来,修习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本性”,而要达到该目的就要“变化气质”,将气质之性“变”为天地之性。而朱熹保持的则是趋于一种“性一元论”,无论是气质之性还是天地之性,性都只有一个,其所表现出的两种状态或者说差别,只是缘于性本身或者说下贯的理被形气所遮蔽的状态不同。
在展开论述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之前,还有必要厘清其心性论中心和性的关系。首先,从“性即理”也就是从性和理的一致性来看,性起着价值主体的作用。而在现实之中,由于性不可独立存在,必须依存于人,依存于人即是依存于人心。性对心实质上起着规定性的作用,所谓心性不离,正是性成为心之所以为心的依据。朱熹继承了孟子“明心见性”的观点,承认性和心之间的一致性,且正是通过心的发用,没有具体形态的性之价值本体才得以显现。但是作为人活动的绝对主宰,心起着“命物而不命于物”的绝对主体作用,这种作用绝对没有因为性的规定而有所减损。正如康德在论述绝对命令时认为,人并没有因为遵从绝对命令而使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受到压制,反而,正是由于绝对命令,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绝对自由。同样的,性规定心也在于确定了心主宰的自主性。如此说来,朱熹实质上也是一个隐藏的性善论者。他并没有像孟子一样直截了当地以童子坠井为契机直言先天的善之四端是如何在不加思虑的情况下发用为善之心而指导人做出善行,而是更加深究性和心之间的关系,以说明性之价值本体是如何通过心作用于人。由于先在的确认了理本体或者未经遮蔽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纯良的,再由于心性理之间的贯通,即可确认存有此心的世人皆有善的本性。或受气质蒙蔽的深浅,或自身涵养功夫的厚薄,从而显现出世人之善恶良莠不齐。但是无论怎么说,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总是会透漏出善的绪端。
同样,也正是因为有性作为内在规定,所以人所发之一切情感都是缘于性。由于性对心的作用是先在的,即是讲心对于性的作用是不自知的,故而由性所导致的心的发用往往是无虚假造作的。就如路人救坠井童子,整个行为的发生就在一瞬间,即是遵从了本性。当然,这种本性不同于野兽禽鸟的本性,人与动物不同正是由于人有心的主宰作用。理为万物之理,自然万物亦有性,然而鸟兽之性只知道服从于其生存所需的原始本能欲求,趋利避害完全都是趋于本能和生理欲求,故而可以说是盲目。实际上,也就是缺少了像人一样的心的知觉主宰作用,求得自身对性理的体认以及对外界事物的感悟。
三、情论
在《说文》中解释“情”字,谓其从心,青声。朱熹也讲,“情”字从心从青,性之动也。朱熹哲学中心、性、情三者是不相分离的,在论心的时候着重论述了心有知觉的功能,但是这个认知绝不仅是知识角度上对外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更是对已发之情流行发用的运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论证和理论实证,朱熹的心性理论是一种建立于道德实践之上的心灵哲学。虽然相对于先秦的儒学,宋代理学更加重视学理的分析和考究,但是归根到底朱熹的人性学说依然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以情感为人性的主要内容。故而,虽然有心为主宰,有性作为形而上的存在依据,但是要将心性道德落到实处,就要处理好情的发用。朱熹哲学中的情,包括四端道德情感和喜怒哀乐之情。他将在“心统性情”体系中作用的情层次分明地展开论述,由性发为情的过程、情的横向运用和道心、人心来说明道德情感对情欲的控制作用。在宋代朱熹理学成为官学之后,为了发挥人才选拔和社会规范的作用,朱熹的心性思想被发展得越发刻板和陈腐。“存天理,灭人欲”,多被后人口诛笔伐,但是在朱熹本人看来人心并不全是私欲,合理的欲望其实是正当的。人心都有向善的底,已发的情气质驳杂,但是在人心的主宰作用之下,始终是能够符合统一于性体的善情的。
心、性、情的统一,不仅是从性的价值本体作用和心的知觉主宰作用来看。心所知觉者,正是心体所发的情,情感就是知觉最真实的内容。这种体用关系即是由用以显体,也就是用情来显示性。作为本体的性虽然是有,但从实践层面讲,形而上的体是难以把握的,所以情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论性也要从喜怒哀乐之情上来讲,情即是性的真实内容。性不可见,情才是性的体现。而心的知觉作用,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性的途径,也就是用灵明知觉来显现其情感内容。所以说,在整个“心统性情”体系中,情的作用尤其体现于其现实意义上。心动是情,心、性、情三者有内在的一统关系,所以情也要在“心统性情”的体系之中才可以贯通心性,落到实处。而只有情得到了落实,性和理才能得以体现。朱熹重视情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在儒家哲学里情感道德和人的存在价值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其心性论的体系中,只有确定了情感在心灵中的地位,才可以说明理性道德的存在问题,因情见性,否则,所谓的性体都只是悬空之物,其存在和价值都可以体现言说的。
宋明时期,重视情用的哲学家不只朱熹一人,王夫之在其性情论中,对于情也有独到的见解。朱熹上承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是情,“四端”也是情。性和情是互相融通的,也就是说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之间是存在着互动的。在他看来,性是情得以发用的依据和根源,而情是性得以显现的存在。朱熹情之内容,可以将其视为是“四端”和“七情”。“四端”是由人心发出来的,仁义礼智是上天所赋予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故而,人心之中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不离不杂。而在王夫之看来,所谓“四端”和“七情”之间有严格的区分。道德情感即使是已发状态,但是它只能是性,而不能是情,同时他也驳斥了朱熹将“中和之情”视为善。王夫之以为性只能以天才能言,而情则可以为人所言。朱熹如此理论,不仅没有将天与人贯通,而且混淆了性、情的归属,从而犯了“以性为情”和“以情言性”的错误,从而导致情越过其适用范围而造成性的腐蚀。
无疑,王夫之如此理论割裂了性和情之间的关系,他没有像朱熹一样,将性和情统于在心之主宰之下的一个系统里面。王夫之这种将已发的道德情感视为性的理论,一方面在学理论证的层面缺少逻辑根据和说服力,同时也给人的道德实践增加了难度。他否定了人之本性的自然道德情感,将人心之所发都标榜为性,使得人性和理性相割裂。相比之下,根据朱熹之情的特性,现实之人进行道德实践要更具有可行性。
四、心统性情的内涵
除去对张横渠和程伊川思想的提取,朱熹的“心统性情”说还来源于朱熹本人对《中庸》的体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之中节,谓之和。”这种体悟缘于朱熹在体验未发之气象后,觉得道南指诀所要修达的体认未发之气象还未触及《中庸》中所追求的大境。这或许是由于朱熹早年曾经学于佛教的关系,他意识到体验于未发之间或许可以体识到性之本体,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将心性合一。但是这种体认无疑才达到体识性本体第一个层面,故而朱熹随之解释道:“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由此,朱熹将已发未发演变成了自己的心之体用说,实为对《中庸》的突破。
理解朱熹“心统性情”说的本质,关键在于对该问题中心、性、情以及与理的关系的充分理解,而在国内众多研究该领域的学者中,对于“心统性情”的理解各有千秋,甚至其中一些观点还存在较大分歧。钱穆认为,在“心统性情”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心,朱熹此处对心作用的强调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和发展,由此,钱穆进一步将朱熹的学说归于心学。与之不同,牟宗三认为“心统性情”中的心、性、情三者是相互分立的,朱熹之心不同于孟子之心,其统摄作用仅限于功夫论层面。进一步,牟宗三将“心统性情”阐释为横纵两说,即是从存有论和功夫论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冯友兰把朱熹学说的内核归结为“性即理”,将其整个学说界定为理学,并且与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对立区分开。关于“心统性情”,冯友兰认为情是具体的世间之物,必须要从心中发出,而性是存在于形而下的气中之理,所以它也是存于心中的。可见,冯友兰也是将心、性、情三者区分来界定的,并没有将“心统性情”学说与“性即理”联系起来阐释。张岱年亦赞同朱熹学说侧重于“性即理”的观点,同时,他提出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关键区分在于:朱熹的“心统性情”主张性含摄于心,但是却不等于心,性即理而心却非即理,而陆九渊的“心即理”则认为心、性、理甚至知觉都是同一的。蒙培元则认为钱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对朱熹学说中心的看法过于片面,他们都将心视为形而下的经验层次,其意义只体现在功夫作用上而非本体层面。进而,蒙培元提出“心灵(贯)上下也就是心兼上下,既不能仅仅理解为形而下者,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形而上者。可以从形而下的方面去说心,但不能说心就是形而下者”[4] 298。
从字面意思来看,“心统性情”,即心为主体,以其知觉主宰作用来统摄性和情。知觉为心的主要功能特征,也尤其为朱熹所重视。而知觉又可以分为所知觉者和能知觉者,所谓所知觉者即是指性之本体和心所发之情,这也就表明知觉最主要、最真实的内容即是人的情感。而所谓能知觉者,也就是指心能够应事接物的知觉功能。这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知觉,故而,在全面解释“心统性情”说的时候,也可以有两个方面——心兼性情(心统性情)和心主性情,也就是从性情结构和发用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心兼性情
心兼性情是从心的体用构成存在的角度来讲的,心作为体用不二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动与静、已发和未发。“心统性情,统,犹兼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以,此处的兼是指兼备皆含,而不是兼顾性情两者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说人之一心中就已经兼备人之本性和情感。心之未发时,即表现为性,是价值本体;当已发时,心又表现为人的情感。如此,心就综合和概括了动静、体用、已发和未发,而且也以它们为主要内容。
“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朱子语类》,卷二十)“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朱子语类》,卷五)在朱熹看来,由于心是兼含性情的,所以说心概括动静为一体也是来自性和情的特征。作为客观外在的理本体在心上的表现形式,作为价值本体的性也是寂然不动的,它需要虚灵明觉的心来表现。心之动,又具体表现为心之知觉。心动,也就引发出人一系列情感欲望的发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兼备于心的。当然,正如心之体用为一源,这里所讲的动静也不是绝对隔绝分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朱熹强调心静,则寂然不动;心动时,则要感而化通。这就表现出朱熹对道南指诀的突破和创新,不再刻意追求心静时去体验未发的本性气象,而在已发之时,即处于喜怒哀乐的情感体验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地操控来使情感之发动和性本体相统一。如此,对于心之不同状态,朱熹也就有了不同的对策。于静处,就要静心去体认心之本体,在各种情感未发之际,对心有所涵养。而于动处,就要利用好心的知觉作用,在情感的发用之中,体察认识心。最终是要结合动静,在心的任何状态之下都能保持中和之性。
心统性情之动静,也统其体用。“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讲心体用一源,但是心之体和心之用各有其界定清晰的含义,两者绝不可含糊混淆。朱熹将心之体用问题和《中庸》中的已发未发联系起来,心之体是心在未发用知觉之功能,所有思虑都没有萌动的时候。“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具段焉。”[2]89此时的心就是没有照映事物的镜子,有的只是空阔洁净的自己,也就是心之未发时的状态。而心之用,自然就是心之已发之时,心之所思虑、所欲求都有所发动。如此发动自然源于心自身的功能特征,由于心具有形而下的属性,故可以作用于禀受有形气之私的具体实物。而不管是发动或是未发动,表现为体或者是用,心的本质都是不变的。
(二)心主性情
心兼性情说明了心包含统摄已发、未发之性情,相对于心主性情来说,更像是一个静态的平列。而主性情,就更加彰显了心本体的灵明知觉和主宰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心为绝对主体对性和情都有全体作用。“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作为主宰的心,其对性情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就性而言,由于性本身属于形而上,是心处于静处的状态。故而落到实处,就需要心来照见本性,使得静态的心得以表现。对于情来说,人心发出的情感如果没有得到心的主宰统摄,原始的欲望和需求就会不加节制地发展,进而陷于混乱。心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使得喜怒哀乐之已发处于中节之和,对外显的情感进行调控掌握,使所有的情感、思虑、萌动都居于不偏不倚、适时适度、节制有序中,在和谐中发用。
就性来说,首先作为理本体在心上贯彻的体现,性于心而言是一个先在性的存在。但是,此处并不是因果关系,并非先有了性才有心。性和情都是出于心来讲的,心为两者的载体。那心要如何做到主宰性呢?“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和存养。”[2]55由于性本身是纯善的,所以当心为发用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和性相统一了。此时,心的主宰作用体现在要将静处的善心保持涵养住。因为形而上的性只能通过心来被人体认,所以修习者也只能借助静处的心来识得性体,从而将之贯通于日常践行之中。
但是,这种于静处体认对于常人来讲往往难以达到。或是难以跳脱出日常之中的欲求执念和己见偏私,而体识不到寂然不动的心之体;或是流于追逐形如槁木、面如死灰的静识表象而成“枯木禅”一般没有内灵的死静。情感发用和人的日常生活是不能割离的,由心发出的情才是心最基本、最真实的内容。心主宰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心内在地给出了一个标准来规定调整人发用的情感欲望。而这个所谓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心之体,即性之价值本体。“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2]23这就要求人在以心应事接物的过程中,要随时使自己的情感发用符合一定的道德情感标准。当然,心统性情所要求的心的主宰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规范,而是内在地实现心、性、情的统一,性还是那个性,心亦还是那个心,三者的本质是内在相通贯的。所以说,未发之性是寂然不动的善,是心善在本体层面的价值依据。而已发之情则体现于人日常实践之中的善,是性之本体在形而下层面的表现。朱熹的这种心性论不仅涉及到道德探究的学理层面,而且也包括伦理学上的实践层面。心主性情,也就是要在省察和存养之间、已发和未发之间使心主宰性情两端,实现道德理性和情感发用之间心、性、情三者内在的统一。
(三)涵养识察的修养方法
仅从理论层面讲清朱熹“心统性情”说中心、性、情三者的关系是不够的,心统性情的目的在于要继善成性、成善成德,在现实的日常生活践履中达到心性合一,使得由情感理智驱动的行为都符合道德准则。那么,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
首先在心之未发时,即要发居敬立己的涵养之功,让此心求定其本。在未发之时,心是没有任何情感思绪的萌发和展露的,完完全全是一个纯净的价值本性。而主敬,就是要主一无适合。从表面看就像是佛老的打坐一般,心态平和宁静,而内心处则是要治心、收心、养心,以避免心放外失驰,昏昧扰乱,从而保持心与理合一。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主敬立己的涵养之功也有使本体显现的作用。由于心是形而下的存在,是使贯通有性理,还是会受形气之私的蒙蔽而难以显现。只要是主敬,就自然会有顺应价值本体的倾向。朱熹相信人性本善,用沉于浊水之中的宝珠来象征人性。即使有污浊之水的遮蔽,宝珠仍然是明亮的。故而,天理和人性也只是需要有主敬的功夫来揭开其遮蔽,展露出其明亮的本性。虽然居敬立己之功用于未发之际,心为接物而于现实层面讲是空的,但是这种功夫并非是无意义的。正是由于涵养之功,给其后的道德修养以起点和根据,也使得心之道德主体得以显现和保持。
其次,从格物致知的功夫来修达。格物之说源于《礼记·大学》,朱熹继承并发展了格物之说。在朱熹理气论中,理是万物万事存在的依据,所以万物之中亦包含了理。结合心性论中心有知觉之功用和程伊川“即物穷理”的理论而发展成朱熹“即天下之物,穷已知之理”的格物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累功夫总能穷尽天理。这种由主体推及客体,将外在的事物纳入到自己的认识之中的功夫,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认知层面。朱熹所要格的物,不只是事物的名字,更是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理。即要穷尽事物外在的表象特征,直揭事物存在的依据和内核。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人才能够在现实世界里认识理。当然,日日格物的方法过于零碎,格物致知的工夫最终目的在于“豁然贯通”。当格物达到一定境界时,即可以豁然贯通,而此时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了。当然,格物穷理的工夫对应于“心统性情”说中,自然是要在心已发之时起作用。未发之时的心之体虽然有主观能力,但依然是作为价值本体的存在。只有在心发用之时,通过知觉主宰的作用,心才可以接应万物。然而心中本来就已经包含有理了,所以并不是说格物就是向外去寻一个理。人和外物皆来自一理,不过是因为人有心而理显。那么,向外格物其实也就是通过对外物的格致,使内在于心的理所明显。如果说居敬立己是由向内的路径来发明本性,那么格物致知就是从向外的路径到达心理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