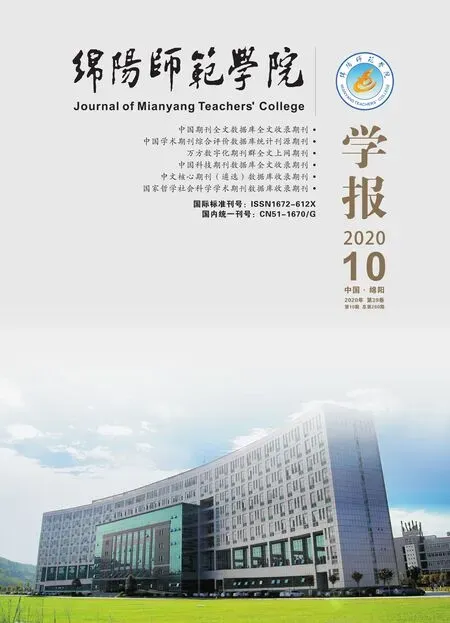论付秀莹《他乡》中知识女性的命运叙事
李翠青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二十一世纪以来,70后作家作为一股鲜活的力量在当代文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与6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专注于生活细部描写,以此来挖掘现实人生的真实困境。潘向黎小说呈现了都市欲望人生,盛可以对底层打工女性生活进行了深度剖析。付秀莹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作家,她的“芳村”叙事开启了新乡土描写的形式。付秀莹以清新细腻的语言赋予了小说诗性意味,将乡村隐秘之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自《爱情到处流传》开始,《旧院》《六月半》以及《陌上》,小说细致地探寻了乡村女性的精神世界,而《醉太平》《桃花误》《罗曼司》则转向了对于知识女性的关照,当知识女性从乡村走向城市,在陌生的异乡如何走出自身的命运。
付秀莹的新作《他乡》最初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2期,在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中位居第三。付秀莹一改过去的“芳村”叙事,而将笔触注目到了女性从乡村步入城市的生存境遇问题,可以说《他乡》比《陌上》更为成熟、厚重。小说聚焦新时期下知识女性的成长问题,女主人公翟小梨高考失利进入了普通学校,毕业后随男友进入省城,面对公婆嘲弄、男友不作为的态势,已为人母的她为了改变生存处境,毅然考取了北京的研究生,对于成功的极度渴望使得翟小梨游走在权谋利益之间,这是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充分显现。《他乡》是一部女性的精神成长史,翟小梨在与命运的不断博弈中走向了成功。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回顾了主人公二十多年的成长故事,在经历了世俗百态之后,翟小梨开始重新审视故乡厚土给予她内心的温暖,因而实现了精神归乡。在付秀莹看来,写小说是一种“控制的艺术”。这种控制力决定了小说是僵硬的还是丰满的,付秀莹认为写小说是一种补偿和安慰,个人的渺小无助可通过创作小说得到抚慰和平衡[1]。《他乡》中的翟小梨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体,她的成长可以唤起部分人的共情,对于70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青年时期急于逃离乡村,在命运的轨迹中顽强地成长,而身处异乡的荒凉唤起了他们对于故乡的怀念,小说最后的那句“难得糊涂。不是吗”,是知识女性在四处碰壁后的彻底顿悟,其中夹杂着忏悔与歉疚,还有对于命运的和解。
一、命运叙事
中国人讲命运,儒家文化中的“五十而知天命”,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都是将个人命运归于彼岸世界的掌控。命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描写由来已久,李泽厚解释“命”为“命运”“宿命”“命中注定”;“命”是偶然性,又具有神秘性,难以预测、把握、知晓、控制,超乎人们的知识和想象[2]213-214。对于命运,中国人怀着一种天然的敬畏之情,相信自己的一生将会循着既定的轨迹前行,也正是由于诸多因素导致了命运的不可捉摸。付秀莹的《他乡》以女主人公的视角回忆了二十多年来命运的跌宕起伏,小说在叙事空间上跨越了芳村、S省和北京三个场所。基于此,《他乡》描绘了主人公翟小梨在其内在性格以及外部环境共同驱使下的命运走向。
(一)性格决定命运
命运,在小说中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存在,它来源于多种因素的相互糅合,最后推动着小说人物前进。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人们对于命运的关照主要集中于神定命运、人定胜天、环境决定命运几个方面。宗教信仰者对于神灵世界的特殊力量显示出较大的权威性,在《他乡》中作者着重表现了人性与环境影响下命运的现实走向,而首先,翟小梨的命运与自身性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是在自身性格这一内在性的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的生命之道。
翟小梨的人生是靠她自己走出来的,“性格即命运,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3]6。敏感而又上进的个性使得她不甘平庸,在生活的打压下她从未放弃斗争。高考失利的她在大学中异常努力,毕业后以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奔走求职,自考本科,自考研究生,在男友章幼通冷漠的家庭中她依然凭着永不消减的热情努力生存着。她顽强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成为了一个年轻的母亲,却有着比父亲更坚强的臂膀,可以说翟小梨将农村人的质朴踏实、吃苦耐劳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本能,付秀莹将这种本能刻画进了翟小梨的性格里。“我眼睁睁看着,当年的那个天真幼稚的乡下女孩子,跌跌撞撞,一头撞进她梦想中的生活,而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只能听天命而已。”[3]38作者以多年后翟小梨的视角来回忆当初的场景,那时的翟小梨对未来报以巨大的希望,天真的乡下女孩终于进入了省城,这是改变人生的重大机遇,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即使撞破南墙也不回头。对于城市的无限向往,究其根源来看是城乡阶层的固化印象。就70后的人们而言,面对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成为了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而拥有城市户口是农村人最为成功的见证。翟小梨虽然成绩优异,但在面对章幼通的家人时,依然难掩内心的自卑。正是源于此,她迫切地想要在新环境中获取自身价值的认同,所以义无反顾地向前进,从S省最后到北京,成长为一名成功的女作家。出生在乡村的翟小梨,骨子里天然的敏感使她不断弥补自身缺憾,而乡村人的勤恳以及任劳任怨赋予她与生活博弈的强劲动力,这种淳朴天然的力量推动着她走出了自己的命运。
(二)环境影响命运
当代作家潘军坦言:“我就很崇尚一种宿命的东西,我觉得‘宿命’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对命运里的那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进行了一种高度的概括,概括成了一种比较美的形式。”[4]11-12这里的“宿命”被概括为命运的积极的美的形式,而这一形式源于构成命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小说《他乡》来看,付秀莹把翟小梨置身于三个不同的环境之下——芳村、S省、北京,环境的更迭也预示着主人公的成长历程,除了性格的内部因素之外,外部环境同样以强烈的感染力同化人的价值观念,推动命运的走向。
《他乡》讲述了主人公翟小梨自大学至研究生毕业后这一时期的成长故事,小说叙事空间从芳村开始。芳村是翟小梨的家乡,在这里她渡过了人生中的青少年时期。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价值观的养成、命运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翟小梨出生于农村,乡土中国的文明教授了她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认识,翟小梨对于家庭原初印象是一派父慈子孝的温暖气氛,芳村中的翟小梨单纯、质朴,对生活怀有美好期望。大学毕业后,翟小梨随着章幼通进入了S省,章幼通家庭的冷漠第一次让她对自己的农村身份感到自卑,寻找工作的艰难、意外怀孕使得这对二十来岁的小夫妻备受生活打击。在他们极度拮据之时,章幼通父母以冷漠的旁观者态度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未伸出援助之手。定居S省后翟小梨过早体验了婚姻的辛酸,她有幸见证了这个城市不同于芳村的冷漠,年纪轻轻便知晓了人世的冷暖炎凉: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拥有了过硬的学识能力才能真正改变命运,因此她考取了研究生,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小说上半部分描写了主人公心酸的成长历程,下半部分则讲述练就圆滑处世技巧的主人公如何游走在北京文化圈内。环境的再度改变使翟小梨跳出了原本的生活圈而投入到了众人仰望的帝都之中。她在学业以及事业上都节节高升,走出了知识女性的完满结局,成为了知名作家。由此看来,三次环境的变迁,推动着主人公人生目标的转变,主人公在追逐目标实现之时走出了自身的命运之路。
二、命运叙事的呈现
《他乡》中以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对翟小梨的一生进行了审视,而正文之外的其他人物篇则由五个相关人物展开叙述,多重人物视角的运用削减了故事因主人公独白而产生的主观性感知,异视角对峙下的人物心理更具真实性。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将主人公的内心进行了深刻剖析,多重叙事者的存在则是平行时空的再次审视,以此来揭示命运的必然。
(一)多重内聚焦的有机结合
热奈特在其著作《叙事话语》中将叙述视角分为三类:零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内聚焦是指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话语来呈现故事,小说《他乡》是以主人公翟小梨的意识展开叙述,文本多处涉及内心独白,翟小梨以一位成功女性的视角回顾二十多年来自身的命运转向。
《他乡》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讲述翟小梨与章幼通从大学到步入婚姻的故事,下部写翟小梨考取研究生后在北京的成长过程。小说由“我”独居北京的片段回忆而联想到高考,之后由母校中对未来充满期许的陌生女孩转场,闪回到高考结束后的自己。“我”由于高考失利考入专科院校,性格要强的“我”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一度成为学校的骄傲,然而“我”却和差等生章幼通谈起了恋爱。大学毕业后,面临工作危机,拥有城市户口的男友章幼通带“我”进入了他的家庭。面对男友家人的冷漠嘲讽,“我”只能低声下气忍耐,那时的“我”怀着对城市的向往,卑微地期盼着章幼通家人的接纳。小说以翟小梨的视角来聚焦外部环境,而叙述者“我”以拥有了近二十年的阅历来审视当年的自己。故事随着年轻翟小梨的视角不断推进,而来自二十多年后的翟小梨也在不时地阐释着宿命,透视结局。温情的芳村生活与冷漠的章幼通家庭的对峙,便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翟小梨对于家庭的逃离。城市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丢掉了乡村的古朴传统以及最本真的人性,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体。而这种矛盾,由宿命导引着,磨砺着人性,也让人不断成长。叙事者“我”亲眼看着当年懵懂的女孩变得成熟稳重,昂首自信地走在北京繁华大道之上,满怀欣慰而又心疼这一成长的代价。
小说的主体部分之外,还插入了七个番外叙述,插入部分包含五个人物叙述。这些人物同样以内聚焦视角对自身生命历程进行了补充性叙述,同时为故事主体情节提供了旁观者视角呈现。这种多重式人物的有限视角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故事情节,对于叙事者的心理进行补充。主人公翟小梨在某种机遇下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参与者,他们从自身不同的视角来审视翟小梨的人生,受邀作出评判。
章幼通是翟小梨的初恋,也是她的丈夫,家庭环境的压迫使得他懦弱、胆怯、不思进取,而翟小梨却是凭着一股劲不断向前行进的攀登者,她身上具有一种进步的现代性,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消极的不作为与主观能动性的对峙必然导致生活的龃龉;章幼通的父亲章大谋少年不得志,中年更是痛惜子女的无能,他嫉恨芳村的翟小梨那股拼搏干劲,而在翟小梨获得留京指标将孙女带走时,二者身份上的反差对调印证了命运的突转;同为知识女性,章幼宜的处境与翟小梨完全不同,她出身书香世家,却缺少家庭的温暖,她事事遵从父母意愿而不敢放手追求幸福,翟小梨的活泼张扬在她看来是如此粗鄙不屑,最终她却亲手造就了自己独孤无爱的一生;管淑人是翟小梨步入北京之后的情人,四十来岁的他离开妻女远赴北京读博,他要在帝都成就自我事业,翟小梨于她而言,充满新鲜热烈,他骨子里对女作家怀有天然的好感,从初遇翟小梨不自觉的倾慕开始,命运指向着他亲手培育了翟小梨这个女作家;郑大官人与翟小梨之间是纯粹的精神之恋,郑大官人出身不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帝都文化界占有了重要席位,而翟小梨的出现使他回溯多年前的自我,他照顾着这个小同乡,翟小梨最终的成功也昭示出二人近乎命运循环式的人生走向。五个人物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都参与了翟小梨的生命历程,来自二十多年后的“我”在回顾的过程中,深感命运的强大效力,而多重叙述者的存在为小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我”与故事人物有限视角有机结合,形成近乎全知性叙述,使得人物命运昭然若揭。博尔赫斯说:“小说应依照魔术的程序和逻辑,而不应按照科学与自然这种混乱的‘真实’世界的程序和逻辑。”[5]384因此,他主张小说用神秘隐喻现实,采用技巧性叙述来打破现实主义小说常规,付秀莹采用多重内聚焦的结构模式给小说以巨大的张力,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叙事的辩驳与和解中呈现小说的宿命观。
(二)叙事时间机制的有效控制
《他乡》根据主人公翟小梨的生活历程,以进入北京读研究生为结点,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转向。从芳村到S省,最终到北京,小说主要以倒叙展开,但在开篇即对主人公多年后的北京生活进行了场景式展现,在翟小梨面对大学以及毕业后的各种人生遭际之时,叙述者则预先对翟小梨的选择作出了现实性的印证。叙述者“我”以经验之身反观不成熟的自我,揭露理想与现实的强大落差,以此来呈现主人公陷于宿命的无力感,“我”在命运的推动下走出了人生之路。
小说主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阐释,故事前后两部分联系紧密,随着主人公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展开,在叙述过程中适时进行预叙,在叙述主人公心理推测之后随即给予现实印证。“我”在进入大学之前是没有信心的,干部子弟J鼓励“我”大学不错,“我”相信了他,“多年以后,当我和J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再次见面,已经时隔二十年了……她竟然成了作家”[3]15。小说叙事时间的转换,使得故事时间迅速省略,从而直抵主人公的命运呈现。小说在现实印证之外,更多的是对主人公所向往的未来进行反差性的预示。小说正文部分的内聚焦视角易于呈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剖析命运转向的必然性。主人公以独白的方式不断与过去的自我对话,随着意识的闪回冲破时间阻隔,预告命运。初尝爱情甜蜜时的翟小梨殊不知生活对于年轻人的磨砺如此狠辣;毕业后的意外怀孕使得翟小梨此后的婚姻生活充斥鄙视与冷眼,“这个红彤彤的结婚证,在多年之后,暗示的不是幸福、喜庆和百年好合,而是纠缠不清的疼痛,还有挣扎和彷徨”[3]84;进入北京后的翟小梨遇到了老管,她欣赏老管的干劲与雄心,作为一个异乡人,她把老管当成了唯一的依靠,对他无条件地容忍和付出,这种不对等的感情也必然预示了悲剧结局。翟小梨是以当代涓生的姿态审视了自我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如果说涓生对子君是一种忏悔心态,那么翟小梨则对自我进行全面审视后流露出的是复杂情感:她同情在冷眼嘲讽下受难的翟小梨,也自豪于翟小梨作为知识女性的成功,而她也忏悔自己的糊涂行径,最终与自身和解。
从时间向度上看,小说从主人公回忆性角度出发指向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时序超越了时差,实现了故事中过去与现在的密切衔接。小说整体延续着时间顺序进行,而时间向度主要借助于刻度来把握。作者多次使用清晰的时间刻度,使得文本在回溯与预示的过程中依然保有明确的时间脉络:“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点不对的呢?好像是毕业那年的暑假。那一年,是1996年,离著名的1998年大洪水,还有两年。离母亲辞世,还不到两年。”[3]39毕业的时间联系着生命中的重要事件;“2000年,这个看似不平凡的年份,跟任何一个年份一样平凡的,日常的,有一种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微微的倦怠,也有一点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淡淡的感慨”[3]108,以新世纪这一时间节点来预示生活的转向。此外,在小说的正文外附有一篇日记独白——《断章,或者浮云》,零散记录了主人公自1994年大学入学至2019年定居北京的二十五年生活经历,如此清晰明了的时间刻度使得故事产生一种似真性,唤起读者对于文本的现实认同感。作者选用了二十世纪末至新时期以来,人们所熟知的重要事件的时间刻度来显示命运的无常。在1998年相约九八的温暖歌声中“我”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在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新世纪到来之时,“我”却狠狠摔倒在生活的泥淖中。理想与现实的倒错以及极具讽刺的时间设置呈现出主人公无法摆脱的宿命。
三、命运叙事的价值阐释
《他乡》从知识女性翟小梨的视角出发,是主人公从芳村到北京二十多年生活纪实。农村姑娘翟小梨在婚姻中默默承受着命运的无常作弄,她的勤勉使得她不断丰富了自身知识储备,而学历的提升赋予了翟小梨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进入北京后她以强烈的抗争实现了命运突围,显现出新时期知识女性鲜明的进步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情节成为乡土小说的重要书写模式。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怀有美好童年回忆的新乡土作家对乡土进行了新的书写,乡土地母的宽容形象召唤者着知识分子的归乡。
(一)母性消隐下女性意识显现
在中国千百年的封建文化中,女性长期以来被视为男性的附庸,鲜有自我意识,由此也便造就了古代文学作品中批量化的温驯贤良女性形象的产出。近代以来,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接受了新时代思想的女性显现出了鲜明的进步意识。鲁迅率先为知识女性发声,一篇《伤逝》完成了对新时代知识女性子君那种勇于追求自我爱情精神的赞扬。在此之后,知识女性在小说中摆脱了柔弱的形象,具有了鲜明的个性意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性格张扬的莎菲、钱钟书《围城》里独立的孙柔嘉等都是对知识女性书写的延续。步入新时期后,众多女性作家在创作中融入了知识女性形象:谌容的《人到中年》写出了中年知识女性的惶惑;铁凝小说《大浴女》则书写了都市女性的成长历程;方方对笔下的知识女性给予深切同情,小说中呈现了知识女性逃不出的命运悲剧;徐坤《厨房》对新时期知识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选择出路进行了探析。70后女性作家付秀莹在新世纪之初正式步入文坛,其小说聚焦女性心灵世界,对城乡发展变化中女性价值观的转变进行了深度剖析。女性摆脱了“母性”的“利他主义”原则,展现出真我姿态。她们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女神,而真正活出了女人的模样。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到:“被压抑物的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6]6小说书写要强调七情六欲的回归,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挖掘更能揭露人性。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改造乡村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女性的婚姻爱情观念,而传统观念的转变源于物质欲望满足后产生的巨大精神愉悦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写道:“抽象权力不足以确定女人的具体处境,处境大半取决于她所起的经济作用。”[7]118女性爱情观的转变源于市场经济发展下更新的价值观,对于知识女性而言,她们凭借努力拥有高学位,也自然能谋得好的收入。经济权力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心理满足感也逐步提升。新时期的知识女性成为了成功的个体,不再卑微地承受着传统道德的束缚。付秀莹在新作《他乡》中塑造了一个新女性形象,翟小梨从传统的温良受难的女性最终转变为成功的女作家,她凭借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实现了人生完美蓝图。事业上的成功除满足了女性经济独立的欲望之外,也使得翟小梨敢于追求自我爱情。在得知老管有妻女的情况下,她依然希冀可以和老管相守终生。步入北京后的翟小梨对于章幼通只有逃避和失望,老管的优雅与干练以一种别样的长者魅力深深吸引了她。翟小梨在持久的黑暗中看到了希望,这是生的欲望连同爱的欲望促使她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女性在追求理想与爱情时更具主动性,而性格方面女性与男性地位的倒置则进一步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芳村中的女性打破了传统伦理观念的枷锁,她们不再一味地恪守相夫教子的职业素养,而真正为自己谋生路。如果说早期的《爱情到处流传》中母亲对于父亲与四婶子的“私情”持一种隐忍态度是传统妇女观的表现,那么香罗、望日莲、春米则是敢于追求自我的典范。她们周转在男人之间,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付秀莹在小说中塑造了强者女性形象,而在此之外,男性则以相对软弱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出走》中丈夫的出走以及《他乡》中章幼通的惰怠都与女主人公的积极向上形成对照。在《他乡》之中,章幼通的闲散、不知进取都使他落后于这个时代,翟小梨对于生活的强劲热情、对于命运的顽强抗争深深打击了章幼通,当翟小梨意识到永远无法改变章幼通时,她只能逃离家庭。翟小梨在北京的肆意放纵是知识女性以复仇者的姿态对于传统女性观的有力反抗,以此传达出新时期的女性意识形态。
(二)知识分子返乡情结的延续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的《故乡》开创了乡土小说模式,此后台静农的《地之子》、彭家煌的《怂恿》、王鲁彦的《柚子》等系列小说都对乡土愚昧文化进行了揭露,乡土是作为落后、批判文明而存在的;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则运用清新自然的语言对乡村生活进行了深切缅怀,知识分子返乡情结成为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以《山乡巨变》《暴风骤雨》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抒发了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返乡情感;八十年代后,文坛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返乡书写模式,汪曾祺的高邮风俗、路遥的陕北人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周系列小说等都是知识分子通过对故乡风俗人情的回望生发出别样的情感内蕴。二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使得乡村聚落日益缩减,对于新时期的部分小说家而言,他们在乡村经历了自由无虑的童年生活,因此他们的笔触也转向抒写乡村的诗意风韵,乡村人奔向了城市,在生活的压迫之下,他们最终返乡。付秀莹的《他乡》则是抒写了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历程,延续了以往乡土小说家对于返乡情结的揭露,并以命运这一因素作为重要推动力进行。
付秀莹幼年时在乡村生活,她以自身的经验性体悟造就了一代知识女性漂泊他乡的成长故事。翟小梨从芳村嫁到了S省,最终进入京城,多年的奔波让她收获了荣利,同时也失掉了自我。翟小梨是在传统乡村道德秩序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有着坚韧的自我约束力,她较早步入婚姻,但离开芳村后的生活一步步摧毁了她的期望。章幼通家庭的冷漠相处、血缘关系的淡薄都让她在新婚中备受艰辛。步入北京后她成了老管的情人,当她准备抛弃自己的家庭与老管在一起时,她才猛然发现自己只是被老管利用以晋升职位的对象。她在传统伦理与现实追求中备受挣扎,在命运的安排下陷入欲望的泥淖,因而她内心的撕裂疼痛才会如此深刻。进入城市后的女性,她们成为了城市里的“异乡人”,金钱欲望满足之后的空虚、城市的荒凉使得她们开始思索家园的美好。她们所产生的“乡村情感”意蕴更为深厚,故乡成为她们被城市“驱逐”之后为自己寻找的心灵归宿,也是她们疲惫的城市生活中的休憩点。
在《他乡》最后“致亲爱的某”那封信中,叙述者“我”深情地写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乡的逆子。我吃着她的乳汁长大,而后弃她而去。我一心离开故乡,到城里去。在别人的城市里,我吃尽了苦头。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在这个冠盖云集的京城,如一粒浮尘,风把我吹过来,吹过去。这是别人的城市。我的故乡在大平原上,在大平原的田野深处,在炊烟缓缓升起的村庄里。”[3]442乡村的孩子在年少时期都拼命想要离开家乡,为了求得功成名就,翟小梨在他乡备受冷眼,奴颜婢膝的讨好使得她的心灵麻木冷却,而故乡厚土的清新淳朴召唤着她的回归,翟小梨最终回到了章幼通身边。“当我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再一次回首的时候,透过时间的尘埃,透过多年前,那个春天的乱红和飞絮,泪水和伤痛,我再一次想到命运。”[3]383翟小梨回忆起乡土的温和,那片厚土具有广博的地母属性,它可以包容所有的灰暗,原谅一切污秽。翟小梨在与命运的博弈中,生活处境大为改观。她成为了一个女作家,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然而这些她曾一度向往的生活目标在实现之后内心却是如此空荡,远在他乡的知识女性失去了知心之交,命运的昭示让翟小梨再度精神返乡,精神返乡是怀着崇敬与感恩的心态再度回归故乡。翟小梨生长于芳村,也无法彻底与芳村脱节,在经历了多年的生活磨砺之后,在命运中重新认识了自我。
四、结语
付秀莹的《他乡》一改过去乡村风俗画的抒写模式,而过渡到了新时期知识女性的命运叙事。命运是中国人骨子里信奉的观念,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要素。翟小梨的一生奔波逃不开命运的推动力,从“芳村”到北京,环境的改变,捉摸不定的人性,在此之下,付秀莹写出了知识女性成长过程中对于命运态度的转变,从温情受难到进行命运突围,翟小梨最终走向成功。新时期以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普遍提高。知识女性在经济独立的同时开始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付秀莹作为新乡土小说的抒写者,延续了知识分子返乡情结的叙述,在经历了他乡之城的荒凉之后,翟小梨与命运握手言和,最后归入精神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