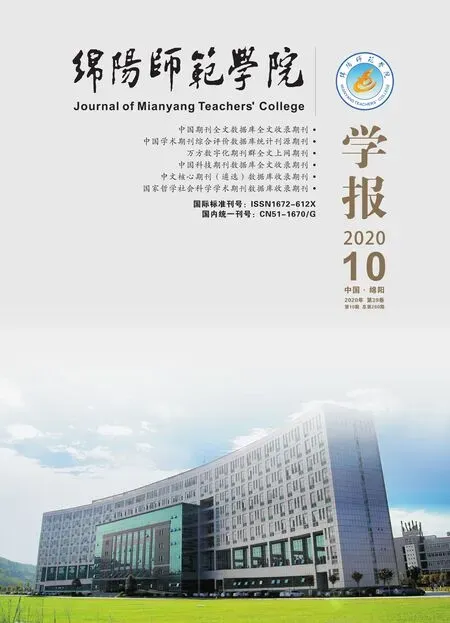《染血之室》的性别空间构建
王雅萱
(广州大学,广东广州 510006)
美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TheBloodyChamberandotherStories,1979)于1979年获得了切尔滕纳姆文化节文学奖(Cheltenham Literature Festival Prize),丹尼尔·米洛斯基(Daniel Marowski)认为该作品“迫使我们认真地思考人类和动物的天性”[1]117。国内学者多从女性主义切入,评价作品为“女性主义视角的女性形象变形”[2], 也有批评家从经验自我与叙事自我双重角度进行分析,视之为“少女时代历险故事”[3]261。21世纪国外评论界关于卡特“粗野”“低俗”的评论逐渐偃旗息鼓,转而关注卡特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倾向研究卡特作品解构经典文本及其互文性、表现形式、作者身份等方面,有批评家评价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家”[1]109。在空间叙事层面,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染血之室》的空间特征,学者伊莉莎·克劳蒂·亚非利蒙(Eliza Claudia Filimon)谈及卡特小说中城堡、监狱、岩洞等幻像,重点考察这些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接壤与碰撞。但此类论著忽视了空间自身的对立以及空间的叙事功能。在《染血之室》中,卡特聚焦空间叙事,关联不同性质的空间,以空间转变推进情节发展,以权力场域下的空间变动透视女性成长与斗争历程。卡特通过改写蓝胡子童话,将少女主人公放进对女性怀有极大恶意的传统古堡环境中,凸显女性个体成长的艰难,隐射女性通过斗争获取生存权力的苦难历史,由此显露卡特对女性成长与生存问题的独特理解。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来理解与梳理空间之间的对立或转换关系,辨明空间的表征与内涵,并以主人公在阈限空间的体验与成长,厘清小说空间叙事的现实指向。
一、空间对立:整体空间与个体空间
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生标志着空间不再是孤立的、单纯的背景,而进入了文学与人类生活的语境之中。在评论空间的作用时,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空间在文本中提供了“创造并再生产对特定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期待”[4]160。这种期待符合文学的模仿传统——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过程中,空间被赋予象征性外壳,以文本世界的权力关系再现现实权力网络,因此,空间的对立即特定社会关系的对立。《染血之室》中的空间以多层次对立揭示空间内涵性别维度,即性别空间。性别空间(gender space)不是指产权归属或只为男性或女性服务的物理空间,而是两性性别观念所塑造的差异化明显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阿曼达·弗莱特(Amanda Flather)认为:“不断强化的空间和社会的划分产生了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5]5他强调传统空间划分与父权制密不可分的联系,性别空间的提出点亮了空间层面的权力斗争,明确指出男性可以自由游走于各种类型的空间:蓝胡子可以随意出行,而“我”却困守在海上孤堡,家宅成为“女性监狱”。
《染血之室》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空间对立:整体空间的对立与个体空间的对立。整体空间为丈夫的家宅城堡——一天中有半天海陆都无法相接的“两栖神秘之地”[6]15以及母亲白色公寓所在的巴黎城市。整体空间中城堡与城市的空间对立,实质为囚禁女性与解放女性的文化对立,或理解为家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立,立足于是否剥夺女性公共空间的权力。城堡与城市的区隔也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所说,是一种“‘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割裂”[7]94。她认为正是妇女被生育与抚养子女所绑缚,所以生活更受“家庭领域”束缚。文本中城堡是 “我”婚后主要的生活区域——远离人烟且隔绝通讯——是一个典型的围困女性空间:公共空间的压制,禁止社交;私人空间的入侵,戕害生命。文本表现为男主人公借难以逃离的海上城堡使前任妻子们失声,方便他随意编写谎言,譬如“前任夫人才刚死三个月……在家宅翻船遇上意外,尸体始终没找到”[6]8。在此,城堡的封闭性展现了囚禁本质。相较而言,少女时期“我”所居住的城市巴黎如同女性建构的堡垒。正如阿曼达·弗莱特(Amanda Flather)所说:“空间不仅仅是消极地展现性别认同的被动背景,如何使用空间和经验反映了性别的建构和表达。”[5]75卡特主动设置巴黎城市空间,以户外游乐、社会联系等方式显露对主人公和公共空间的偏好,即便白色公寓自身狭窄,与城堡对比,也自然地被赋予城堡所不具有的公共空间属性。
个体空间的对立,具体表现为音乐室与其他主体空间及其边缘空间的对立,将家庭空间细分,完成自由与禁锢的多维度表达,又与整体空间对立相互对照、补充,使空间对立维度由单一变得多面。主体空间如卧室、禁区、图书室、办公室等封闭空间,边缘空间指封闭空间的联结场所,如堤道、走廊、楼梯、庭院。主体空间及其边缘空间是城堡的组成部分,即具体化的家庭空间,被塑造成禁锢女主人的空间。文本中通过大量的空间意象揭示“我”的内心恐慌,“黄金水龙头的个人专用浴室”“拥挤的穿衣间”“充满阴沉百合香味的卧室”,卡特借浮夸的装潢与性意味浓厚的意象,巧妙地将主人公的恐惧投射到空间之上。音乐室作为个体空间代指巴黎城市,或称之为公共空间的衍生品,因其面对大海,同阴郁神秘的城堡在意象层面做了鲜明的切割。并且,音乐室被“我”认为是城堡中唯一不会对“我”造成伤害的地方,这个房间不仅是物质性的空间,代表了自由、闲暇;也是精神性的空间,意味着舒适与欢愉,正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宣称的“一间自己的房间”[8]19的重要性。音乐室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其独特性,“我”在城堡中第一搜寻的就是音乐室,因为“音乐是我的第二天性,我只可能前往音乐室”[6]19。从禁区回来,“我”只敢待在音乐室,并且在遭受巨大打击后试图从音乐中寻求庇佑,在音乐中“创造一个五芒星保护我不受伤害”[6]46。音乐室与其他空间的对立是自由与禁锢空间的微观演绎,与巴黎城市和城堡的对立相对照,“我”的命运凸显女性灾厄来自于充满禁锢的家庭空间。
无论是整体空间的对立还是个体空间的对立,本质上都是性别空间对立,性别空间同时存在于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之中,所以二者之间时刻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冲突。从空间的角度观察,《染血之室》这一作品富有深度与价值,卡特没有将笔锋直指权力斗争,从单一维度探讨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认为二者不可协调,而是通过多层级的空间对立显露空间不平等。如果说整体空间的对立是公共空间与家庭空间的对立,那么个体空间对立就存在于家庭空间内部,因家庭空间内也存在部分脱离了传统划分、由女性观念塑造的差异化空间,因此再次形成对立。拆分家庭空间的做法首先为性别空间增添维度,不至于导致对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是简单性别对立的误解;其次为阈限仪式的产生提供可能,以表面的空间变化,暗喻阈限仪式进程,阈限仪式的更迭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促使主人公空间认知转变,构成女性成长与空间争夺意识萌芽的微妙隐喻。
二、空间转换:阈限仪式
“阈限仪式”是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按照时间顺序,将“通过仪式”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通过仪式”指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年龄发生改变时所举行的仪式[9] 95。作为成长仪式的初次受礼者,就阈限层面来说,“我”在城堡中完成了“通过仪式”,度过青春期的重要节点。如杰内普所说,这个仪式标志着“个体生命中的过渡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9]95。正如“我”在文本空间变化、阈限空间更替中逐步成长,进入成人世界。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我”对空间的认识也随着自身成长而变化,空间争夺意识萌芽。城堡作为梦想的家宅,随着工具关系发生变化,“我”发现其中蕴含着生存空间困境:一方面,紧随婚姻而来的物理空间限制是“我”面临的现实困境。“我”脱离了童年住所,走向婚姻,而自己并没有太多权力,只拥有阁楼的一间房,“但身处城堡我必须满足这种安排”[6]16。另一方面,现实与罗曼蒂克的婚后想象碰撞,阈限仪式的进程使空间争夺意识萌芽,加剧了“我”心理层面的不适,加深了“我”的精神痛苦。可见,阈限仪式在空间转换暗喻女性成长与点亮空间争夺意识中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依据卡特的安排,第一个通过仪式发生在图书馆、螺旋梯与卧室的更替中。“我”的年幼、顺从和沉默再次证明“我”是阈限阶段的初次受礼者——一块白板(tabula rasa),等待“所属群体的知识与智慧”在上面刻下痕迹。在《染血之室》中,这种“知识与智慧”是图书室中由《尤拉莉土耳其大王后宫历险记》和《苏丹妻妾作为献祭牲礼》显现的女性命运。据此,“我”的前通过仪式在图书室开始,在这一阶段,“我”认识到图书室中此类东方后宫为对象的绘画作品无疑流露出对“男性主宰性行为的迷恋和幻想”[4]86。蓝胡子对我宣扬,“我娶了一整个后宫的妻妾”,而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后宫是个与西方观念格格不入的地方。西方人表现后宫是要满足一个愿望,即揭示隐秘的东西。”[4]86这层隐秘愿望直指蓝胡子展现他表面蓬勃的男性欲望背后显露出对权力的渴望。度过前通过仪式时,“我”走出图书室,连结“前通过仪式”图书馆与“后通过仪式”卧室的是一道螺旋梯,走过螺旋梯意味着跨过了通往成人世界的一道“门槛”(threshold)。这道门槛中包含阈限空间的变化,“阈限”(liminality)一词来自拉丁文“limen”,它有“门槛”之义,即阈限的实体是模糊的,是“既不在此亦不在彼”的门槛般的过渡状态。从空间意义上来说,门槛同螺旋梯一样,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中间地带,不清晰也不确定。进入卧室是进入“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中的阈限阶段,情节发展中“我”失去童贞,完成了从少女到成人的过渡,这一阈限仪式宣告完成发生于“我”发现“我渴望他,而他令我作恶”[6]31。城堡个体空间(图书室、螺旋体、卧室)伴随阈限仪式进程而更迭,宣告“我”终于度过了“被碾压,被贬低,毫无怨言的接受专断惩罚”[9] 36的仪式——由阈限阶段的初次受礼者成长为掌握“知识与智慧”的成人。就情节而言,空间的转换促使“我”由少女变为女人,因此展开了“我”观察城堡与蓝胡子的新角度。因为贞操的破坏“不是持续演变逐渐造成的结果,而是与过去的突然断裂,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10]346。于是无论是阈限层面还是情节层面,都标志着“我”进入新周期,由向往婚姻生活到对城堡生活产生质疑。
文中还潜藏了另一个通过仪式,表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发生于办公室、走廊与禁区的转换中。前阈限仪式是在办公室进行的,“我”从卡住的小抽屉中找到了私人档案,这时被刻下的痕迹是丈夫与之前的妻子的情书,他们相爱的过往刺激年幼的“我”跨过门槛——一条漫长曲折且灯光不足的走廊。“门槛”之后是闩以黑铁的橡木门——蓝胡子所说的禁区(enfer)法文意为地狱,也有存放禁书的地方之义。在这一释义上,图书馆与禁区互为表里,共同建构了这个城堡的“知识”,禁区也意图以直观方式刻画“知识”于我这块白板之上。图书馆中陈列的书是《启蒙》《神秘之钥》《潘多拉盒子的秘密》此类,禁区门内则是各式刑具和被虐杀的前妻尸体,从精神到肉体,图书馆与禁区共同谱写了家庭空间的杀妻传统。死亡暗示在“我”意图逃离时进一步明晰,“我”打算逃向内陆的同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我看着圣瑟希里亚的眼神带有些许恐惧:她是怎么殉教的?”[6]44这一暗示不只来自圣瑟希里亚的画像,还有“我”在度过门槛仪式时遇见的《萨宾女子遇劫图》,阈限仪式之中众多绘画中显露女性死亡结局,暗示“我”的结局的同时也作出提醒。特纳指出此类象征指引极其重要,他说:“离群索居的女人之所以成长为一个女人,是因为她接受了箴言和象征方面的指导。”[9]104也正在此刻,“我”接受了图书室中《愚昧的处女》与墙上的《萨宾好遇劫图》象征意义的指导,度过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仪式,完成从家庭空间的内部争夺到意图逃离家庭空间,奔向公共空间的态度转变。
图书馆与禁区两个空间的特质微妙地与对方保持一致,二者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为阈限仪式首尾相衔提供可能。图书室舒适宁静,是“谋杀城堡”用以伪装自身的外壳;禁区血腥阴暗,则显示了城堡的真实面孔。两个空间并置形成冲突,藏而不露地表达出家庭空间的生存困境。“我”主动探索空间的行为,挑战了城堡的既有空间划分。从空间的角度看阈限仪式,仪式自图书馆开始到禁区结束,前一个串联了图书馆、螺旋梯、卧室,后一个将办公室、长廊、禁区并置,空间互为表里,阈限仪式首尾相衔。另一方面,图书馆与禁区共享空间意象,空间连接也由此显露。首先,压抑气氛贯穿两个空间。图书馆壁炉中烧着苹果木,“海涛传来催人欲眠的音乐”[6]20,沉郁压抑的气氛如同通往禁区的长廊,“我”在此处感到“愈来愈热,我额上冒出汗珠,也不再听见海的声音”[6]40。其次,颜色组合凸显空间连接。图书馆中“墙上的暗色镶板微微发亮”,“地上的地毯有的深蓝如搏动苍穹,有的艳红如心头鲜血”[6]20。与此相对照,禁区的墙壁如图书馆的墙面“光秃岩石,微微发光”[6]41,“我”用来打开禁区的钥匙形状古朴,是“黑铁做的巨大古董”[6]26。但钥匙掉进地上逐渐积起的血泊中,黑与红的颜色碰撞,宛如图书馆地毯。再比如,怪异气味创造空间联结。丈夫身上的“俄罗斯皮革味道”[6]20,应归结于书室陈列着大量包着小牛皮的书本,而在禁区中,堆放大量刑具的房间内点着香炉,四周“充满神职处所的怪味”[6]42。所以禁区正是图书馆的内核,不是蓝胡子所说的西塔楼底的小房间,而是城堡的“地底的私密空间”[6]40,“家宅中的阴暗存在,地下力量的一部分的存在”[11]17。在此前提下,“我”穿越向下蜿蜒且漫长曲折的走廊,无视逐渐消失的海浪声探索禁区的行为无疑是争夺空间。
三、空间变动:权力争夺
空间变动即意味着权力争夺这个概念隐含在文本中。无论是表面图书馆与禁区的设置,抑或是隐藏的家庭空间囚禁女性主题,都源于男性对空间的支配。社会空间并非中性,而是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来规训自身,最终演变为限制女性的工具。女性想要突破既定命运,必须争夺空间权力从而获得个体自由。卡特在《染血之室》设置了两层不同的空间变动:首先,“我”以取消空间功能的方式对抗既有家庭空间划分;其次,“我”计划逃离意为家庭空间的城堡,意在以挑战空间切割来维护自身安全、人格独立。看似简单的蓝胡子童话重写背后,存在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垒与颠覆,“我”对家庭空间的情感变化构成贯穿全文的权力争夺线索。
卡特以“我”的抗争历程证明,如果仅对抗既有空间划分,以取消空间功能来争夺空间权力收效甚微,唯有挑战既有空间切割,逃离名为城堡实为囚牢的家庭空间,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因城堡中女主人无法得到仆人的尊重,管家的态度“有礼但无心”[6]16,女主人更须遵守古堡的规矩,孤身盛装用餐,文本用一句自由间接引语揭示主人公内心想法,想要做城堡的主人,“我想的太美了!”[6]16“我”通过拒绝午餐晚餐、拒绝换装、要求在音乐室用餐等方式取消房间的功能性,抗拒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社会身份。这是不脱离家庭空间的常见对抗方式,但“我”心知,这样做并不能获得尊重,也不能获得实际权力。所以“我”进一步取消禁区的约束性,带走了那把禁忌的钥匙。“我”进入男性家长设置的禁区,争取自己的空间权力,最后方知这是一个陷阱,专门用来捕获意图空间变动的女性,我的对抗尝试只是顺应他的预设,“照着他预料的去做……就像夏娃”[6]58,终点等待我的是来自蓝胡子的判决——死亡。卡特以这种悲剧结局直白地指出在家庭空间中,意图以不彻底颠覆空间的形态获得空间权力是不可能的。
就挑战既有空间切割来说,“我”在得知禁区秘密——家庭空间的真相后,等待天亮,想在潮水退去后离开。这时“我”终于理解了蓝胡子的前妻们,她们不是“在家宅翻船遇上了意外”,而是计划夜深乘船逃离城堡,却未能成功。这种勇于跨越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藩篱做法,具有悲剧性的意义。女性在死亡警示前冲破桎梏,奔向象征自由的公共空间过程中,仍面对诸多阻拦。
四、结语
安吉拉·卡特通过着重描写“我”在空间的成长,展现空间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对家庭空间的逃离诉求。文本通过架构两层并行不悖的阈限空间的方式推动性别空间更迭,展示家庭空间对女性的囚禁,催生女性的空间斗争意识。文本中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并非简单分割,家庭空间中可以拆分出有公共空间内涵的个体空间,于是家庭空间内部时刻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冲突。“我”对城堡空间变动的挑战是权力的隐喻,是女性对空间决定权的宣言。空间对立主题也在卡特其他作品中多次出现,如《魔幻玩具铺》中的阶级空间对立、《新夏娃的激情》中的性别空间对立。《染血之室》中空间对立的独特之处源于卡特从空间角度展现了女性被圈禁在男性所规定的内部空间的现实,也表达了屈从于家庭空间,或从家庭空间内部寻求答案只能获得悲剧性结局,以颠覆家庭空间的方式才能在绝境中寻求解脱的观点。卡特不止简单描述女性权力斗争或家庭空间压抑女性,而是剑指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呼吁女性脱离桎梏,这也应和了她自身女权主义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