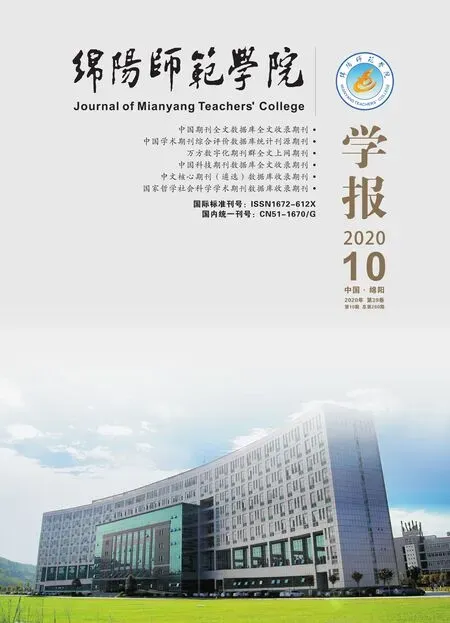舞剧《粉墨春秋》的舞蹈符号学分析
景晓文
(1.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2.绵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人类劳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肢体表达为主要沟通交流方式的文化传播载体。在发展过程中,个别达成共识的肢体动作逐渐被筛选下来成为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社会观念和人类认知。“舞蹈语言”就此产生,它同时承载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其符号意义逐渐凸显。“舞蹈语言是依靠身体动作进行表达的一种艺术性质交流工具。”[1]32其作为身体体现的典型现象,既是承载文化的客体媒介,同时也是人类生命情感、欲望等情态外化的文化主体。随着符号学概念的逐渐发展,我们发现被赋予了符号学意义的舞蹈语言更易于受众接受,比如傣族舞中的“孔雀手”,蒙古舞中的“走马步”等,都能使受众清晰准确地识别出舞蹈语言所传递的文化内涵。以符号学的方法研究舞蹈语言将进一步推动舞蹈学领域的学术创新和艺术实践,不断丰富舞蹈学跨学科研究体系。
一、舞蹈语言的内涵及其与符号学的关联
自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符号学概念以后,其在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已初见端倪。但在舞蹈学领域应用符号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却寥若晨星。作为人类外部形态和内在意义表达相结合的艺术概念,舞蹈语言与符号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运用符号学研究方法阐释舞蹈语言中的符号现象及其存在的符号意义,对于拓展舞蹈学理论研究、指导舞蹈艺术实践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舞蹈以人有节奏的肢体运动作为媒介,反映生活,表现人类升华了的思想感情。不同形式的肢体运动应运而生并以此进行交流,舞蹈语言的初始形态就此形成。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具有共识性、表意性的舞蹈语言在人类祭祀活动、部落纷争中起着重要的传情达意、托物言志功能。“舞蹈语言”一词最早由著名德国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于1963年在其著作《舞蹈的语言》中提出:“人之所以开始跳舞,是出自一种内在的动力。”她提出人的肢体动作本身具有语言表现的功能,人类可以将形体动作作为媒介以表现内心的情感和各种心理活动。她在学术实践中尝试用舞蹈语言表现超越个人之上的、带有普遍性的含义。胡尔岩先生将舞蹈语言界定为三个层级的认知:“舞蹈语言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动作、舞句、舞段三个层级。所谓三个层级,首先是指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级’,其次是指思维结果美学价值的‘级’,再次是指呈现于观众接受作品时所受到的美感冲击力的‘级’。”[2]174由此分析,舞蹈语言之于语言文字而言,舞蹈动作即为词语,舞句即为语句,舞段即为篇章,动作、舞句、舞段排列组成表意较为完整的舞蹈作品,以丰富的舞蹈语言展示创作者的精神世界并传递于受众。
符号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其本质是借助符号可感的形式以替代抽象内容并进行传递。其中,可感的形式就是索绪尔所提出的符号理论中的“能指”,而替代抽象内容所传递出的可理解的内容则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两者之间为二元关系。在艺术符号系统中,“所指”的不稳定性更加凸显,一个“能指”在观众的心中往往产生多个“所指”。著名符号学家雅格布·吉林泽尔曾说过:“符号学对填补舞蹈理论空白起了一定作用。舞蹈符号学的理论必须解释一个舞蹈是怎样表意的;舞蹈着的身体怎样才能用来表意;以及观众如何才能‘识读’舞蹈等问题。”[3]248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具有语言文字和非语言文字两种特性。舞蹈语言借助人类肢体这一可感的外化形式表达人类内在的抽象化情态内容,其实质就是符号学的表征现象,也蕴含着“能指”与“所指”。
舞蹈创作是基于对原汁原味的生活进行加工的过程,是对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艺术化再现的艺术手段。舞蹈依赖于舞者的身体动作律动,以其独特的舞蹈语言完成对生活的述说和情感的表达。要实现舞蹈作品的生动形象、独特个性以及饱满情感,就需要在舞蹈动作、舞句以及舞段上表达出精准、丰富、个性的舞蹈语言。舞蹈语言借助身体的律动来表现内容,并实现内容的传递和情境的塑造,其本质的构成是从展现生活本真到情感、思想升华的过程。舞蹈语言中的“能指”是指舞蹈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所指”则是指形式中所传达和表现出的情境和思想。舞蹈的过程就是舞者借助舞蹈语言与观者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实现互认。正是因为舞蹈是借助于肢体的律动表达,所以较之于声音语言、文字语言等具有明显标识的语言类别,舞蹈语言在“所指”上就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舞蹈在“所指”上可能带来的多重想象空间和抽象意境对舞蹈语言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只有准确、生动、鲜明的舞蹈语言,才能让观者准确把握舞蹈编创者的主旨,从而实现“能指”与“所指”的最广泛互认。
二、舞剧《粉墨春秋》的舞蹈符号学实践
舞剧是舞蹈动作、舞句、舞段的高层次集中与融合,其创编对舞蹈语言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和标准。舞蹈艺术由于受到肢体语言表达形式的局限,一般不易表达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但是,舞剧以“剧”为核心要义之一,就需要编创者在戏剧情节的支撑和指向下,以舞蹈语言刻画剧中人物的戏剧性格,推进情节发展,渲染戏剧场景。审视某个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势,须对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成果予以评估。下文以舞剧《粉墨春秋》为例,从符号学视阈深入阐述舞蹈语言所蕴含的符号现象及其意义。
经过16年的酝酿和积淀,8个月的创作与排练,舞剧《粉墨春秋》于2011年11月在北京保利剧场首演。观众及舆论对这部舞剧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在《粉墨春秋》专家研讨会上,总政歌舞团团长印青认为,《粉墨春秋》对“文化自信”作了最好的诠释,这部戏能够成为舞剧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作品;中国京剧研究所所长、北京戏曲家协会副主席赵景勃认为,《粉墨春秋》把戏曲训练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把戏曲中所谓的“土”“俗”变成了舞蹈的可赏之美[4]。早在1995年,编导邢时苗就已经在脑海中萌生出想要创作该舞剧的想法。漫长的创作历程,从收集材料、撰写剧本、确定主要演员、创编排演直至演出成功,《粉墨春秋》突破了传统舞剧的结构模式,实现了戏剧表演艺术与舞蹈语言的融合,创造了“以舞化戏”“寓戏于舞”的独特舞蹈语言符号。
舞剧《粉墨春秋》无疑在舞蹈语言与戏剧的情势互补、和谐共融方面作出了尝试和突破,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参照的经验与典范。剧中戏剧人物独特的“武生”角色定位,成为了“以舞化戏”“寓戏于舞”的重要背景和手段。编创者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中国优秀民间舞蹈艺术充分融合,以武行来强化舞蹈的形与色,以舞蹈来展现武行的力与美,创生出独具一格的崭新舞蹈符号。剧中通过生动形象、情绪饱满、新颖多样的舞蹈语言,刻画出个性鲜明的戏曲艺人形象。舞剧中的片段“马鞭”“髯口”“寸跷”,在戏曲与舞蹈相结合的基础上以现代艺术手法予以呈现,是中国舞剧史上的又一次创举,在舞蹈符号学研究领域具有典范价值和意义。
(一)性格化舞蹈语言实现精准“能指”
舞蹈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人的肢体语言反映现实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舞蹈语言都能成功地实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这一功能,只有精准、贴切、形象、生动的语言才能描绘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境,表现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特征,最终达到吸引人、感染人,进而影响人、教育人的目的[5]196。无疑,能反映生活、塑造人物的性格化舞蹈语言对于舞剧的编创具有核心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编创者与观者“能指”与“所指”的互认。舞剧《粉墨春秋》的编创者在对戏曲演员的动作特点及其所扮演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度揣摩与研究之后,既保留了戏曲塑造人物时“精”“气”“神”等形象特征要义,同时又将其动作提炼加工并舞蹈化。剧中舞蹈对于戏曲的提炼并不仅仅局限于戏剧形态呈现本身,而是在戏剧冲突的结构上,通过极具性格化的舞蹈语言来凸显人物性格,实现舞剧人物塑造的精准“能指”。例如第一幕中的舞蹈片段“马鞭”,是二徒弟短打武生武潘安的出场亮相舞段,时长仅30秒,却清晰地塑造了二徒弟的人物形象特征。二徒弟武潘安手持马鞭,以端腿亮相、飞脚片腿、点翻身、绕抡马鞭至留头亮相,一气呵成完成了出场的第一组动作。站在一旁的师傅指导其亮相后,二徒弟武潘安又以绕腕出鞭、拍腿踢旁、下腰俯身探海转、侧控旁腿拉马亮相完成了第二组动作,师傅在一旁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两组动作是将戏曲中武生常用的典型动作与中国古典舞蹈元素相结合凝练而成的,加上师傅的点头呼应,生动形象的舞蹈语言表明二徒弟武潘安技艺超群、能力出众,戏曲功底扎实、动作精干有力,师傅对其赞赏有加。同时,流畅成韵的性格化舞蹈语言也展现出二徒弟武潘安干练直爽、潇洒倜傥的人物性格特征。再如舞剧中“挑滑车”片段,三徒弟黑豆本身只是众多被“挑滑车”的“达子”之一。但是他在散戏以后,将“当车”之旗用作“扎靠”之旗,这一简单的舞蹈语言,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黑豆由“武行”变“大角”的追求,成功地塑造出该人物“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性格特征。
(二)情绪化舞蹈语言营造“所指”情境
舞蹈语言的表现形式与诗语言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师。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可见舞蹈语言是人的真情实感,在高度激动的情绪下的激情迸发,情绪化的舞蹈语言是渲染舞剧情境、推进情节铺陈发展的重要表现手法。例如舞剧《粉墨春秋》中的舞段“髯口”,又叫“口面”,意思是演员演出时戴在嘴上的“面具”,即剧中人物的胡须,它本是中国戏曲表演形式之一,在戏曲中通常由男子单人表演。“髯口”既能鲜明地标示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生活经历,又能突出地体现人物耿直、豪爽、急躁、机趣、鲁莽、怯懦、诡诈、多疑等各种人物个性[7]。编导巧妙地将“髯口”这一传统戏曲表演形式与中国优秀古典舞蹈艺术相结合,并以群舞的方式加以演绎,这是中国古典舞蹈表现手法的一次创新。演员们通过头部、手部、腿部、脚步的配合,用抖、甩、摆、移等动作将所饰演的角色通过生动且情绪饱满的舞蹈语言刻画出来。群舞演员起跳撩髯口,再落地张开双手于身体两侧,体现了人物的豪爽性情;左右扬撩髯口,使得舞台上胡须翻飞,传达出人物顽强与执着的精神状态;马步半蹲抖髯体现了人物急躁、纠结等情绪特点。再如,第二幕二徒弟武潘安由“天霸拜山”点化而来的那段“板腔体”表演。二徒弟顿挫有致的舞蹈在意识流中形成了与三姨太的呼应与对白,双方在意境中互诉衷肠的情境油然而生,实现了“寓戏于舞”的情绪宣叙效应。这一连串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情绪化舞蹈语言,使观者在享受视觉、听觉所带来的“能指”感官的同时,具有情感和意境的“所指”感官也随着舞蹈语汇的起承转合而跌宕起伏,构成了两者的交融与互认。
(三)多样化的舞蹈语言创新舞蹈符号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变化多端。舞蹈艺术要想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人生百态,仅仅依靠贫乏、单调的舞蹈语言和技巧是难以奏效的。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都十分注重舞蹈语言的求新求奇,通过艰苦的努力和训练,丰富和扩充舞蹈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加完整、生动,富于创造性。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正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与力量。优秀的舞蹈作品从来都需要编导从艺术的视角用心观察生活,并对其进行解构、加工,再发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多样化的舞蹈语言[8]。舞剧《粉墨春秋》中,不乏新颖多样的舞蹈语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舞段“寸跷”了。“寸跷”原是中国戏曲蒲剧艺术中男扮女装的单人表演。演出时演员需穿着木制的、仅前脚掌着地的高跟布鞋进行表演,脚从外观看起来就如同旧社会妇女裹的三寸金莲,属于戏曲艺术中的独门绝技。舞剧《粉墨春秋》编创者把戏曲中即将要失传的“寸跷”技艺与舞蹈相结合,用群舞的表演方式首次在舞剧中呈现。例如第一幕07分09秒时,六位男旦演员用水袖遮住脸颊,从舞台的左侧高台缓缓碎步上场成排而列,时而单脚站立,时而双脚交替,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舞蹈演员体态轻柔优雅,眼神妩媚动人,将女性的情态舞得惟妙惟肖,极具东方女性形色。又如15分04秒,在夜深人静时,原本该睡觉的众师兄弟透过窗户的影子,裹着厚厚的棉被偷学师傅给二徒弟传授技艺。众师兄弟时而蜷缩身体惊讶地探头张望,时而用被子挡住身体生怕被师傅发现。尤为活跃聪明的三徒弟黑豆学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旋子三百六”惊得众人接二连三地跃了起来,一会儿跳踢抱前腿,双手绕拉亮相,做出戏曲中拉马鞭的动作,一学就会的三徒弟赢得了众师兄弟的追捧,就这样他带着大家一起偷学动作直到被师傅发现。这段舞蹈加入了戏剧情节,通过巧妙利用道具“被子”,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舞蹈语言,塑造出了幽默乐观、求知欲强、执着果敢的梨园子弟形象。再如06分05秒,戏班晨练时利用空中道具吊绳训练腿功的舞蹈片段。舞台上空降下数根粗绳,演员将绳圈系在脚踝处,随着绳子升高将腿吊起来,由耗旁腿软度转换为耗正腿软度。黑豆强忍着痛苦坚持练习,在一旁的师傅见谁动作不标准就用刀背敲打鞭策,突出了戏曲梨园子弟们腿功训练的心酸与不易。这些新颖多样的动作语言是将戏曲题材的故事和戏曲动作语汇提炼加工成舞蹈语言呈现于舞剧舞台,既传承与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又极大丰富了中国民族舞蹈语言符号。
三、舞剧《粉墨春秋》对舞蹈符号学的启示
符号学家艾柯认为符号化有三步:一是思维主体确定某物的功能;二是归类为“用于什么目的”;三是由此命名为“叫做什么”[9]31。也就是说,将信息符号化的过程即是编码,将符号形式还原为信息的过程即是解码。由此衍生到舞蹈语言符号化的过程,则是舞蹈作品的创编过程即是编码,观众对于舞蹈作品的识别与理解过程是解码。观众对于舞蹈作品的解码可能是正解,也可能是别解、不解、误解、多解等情况。在解码过程中,受众成为主导,反作用于作品的编码过程和舞蹈语言创作。回归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舞蹈语言的一个“能指”可能产生多个“所指”。在舞蹈创作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变化决定着不同舞蹈语言的产生。那么,在舞蹈创编的编码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以创新的舞蹈语言符号实现精准的“能指”,同时也需要以观众在解码过程中的“所指”为主旨,依托多样、生动的舞蹈语言符号实现“能指”与“所指”的互认。本文从舞蹈符号学研究的视阈分析了舞剧《粉墨春秋》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舞蹈符号,正是这些生动形象、情绪饱满、新颖多样的舞蹈语言渲染了舞剧的主题与情境,塑造了人物形象的个性与特征,推进了“能指”与“所指”的互认。作为中国舞剧创作历程中的典范之作,《粉墨春秋》对我国舞蹈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舞蹈符号学研究的丰富与推动具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所谓“凡是艺术作品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惟其是旧材料,所以旁人可以了解;惟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家的创造”[10]。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已经成为新时期艺术表现形式的主流与趋势。跨界的融合与碰撞往往呈现出艺术表演的崭新形态和样式。舞蹈与戏曲的融合也是如此。早在此前,中国古典舞就借鉴戏曲的艺术技巧,并结合西方芭蕾舞的形体训练方法,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古典舞训练及表演体系。《粉墨春秋》将中国古典舞蹈与戏曲艺术相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典舞蹈语汇。舞剧中借助舞蹈语言提炼戏曲艺术中的经典动作,并非局限于戏曲形态表演本身,即所谓的“能指”,而是将提炼范畴拓展到舞蹈语言与戏曲艺术结合的“所指”,从而实现“以舞化戏”的价值定位。剧中不乏形象化、情绪化、多样化的舞蹈语言,它们对整个舞剧的主题渲染、人物刻画、情节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出,舞蹈语言的丰富与创新,不能局限于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简单整合,而应基于实现“能指”与“所指”互认的基础上,构建两者相互共融、情势互补的艺术生态格局。
另一方面,《粉墨春秋》不仅为我国传统舞剧的发展又增新气象,而且也对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发扬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舞蹈艺术而言,也应该反思:舞蹈艺术发展的瓶颈是否在于艺术想象力、创作力与观众审美能力和审美想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编码”和“解码”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否仍存芥蒂?持续创新丰富的舞蹈语汇无疑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源泉。我们既应该坚持和巩固已有的传统舞蹈语汇,同时更应该肩负起“守正创新”的时代使命。《粉墨春秋》运用了大量戏曲艺术中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舞蹈化的提炼与再现,使其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远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舞蹈艺术及其语汇要不断融合其他艺术形式的精髓,达成两者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和谐共生的艺术生态。
一部好的舞蹈作品能否成为精品,成为永久流传之经典,关键在于其所承载的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对人文精神与人文意义的不懈追求和极尽表达,更能彰显舞蹈作品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导向。作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舞剧《粉墨春秋》以其独特的结构样式和舞蹈语言符号,深刻阐释了“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的人生主题。其中舞蹈语言所展现出的强大表现力,既取决于编创者编码过程中以创新的舞蹈语言所表达的精准“能指”,也取决于观众在解码过程中对于舞蹈语言“所指”识别的高度互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