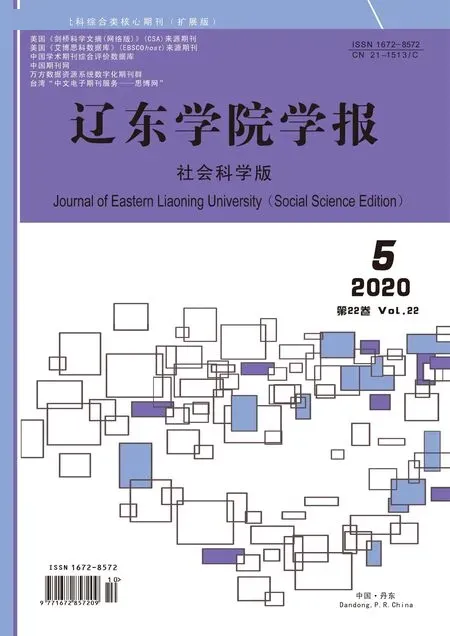金朝赠官制度述略
——以官民自身卒殁赠官为中心
高云霄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赠官是古代朝廷对卒殁官民的褒崇,是职官制度的重要一环,其与丧葬礼仪具有密切的联系。追溯赠官制度的渊源,其制雏形源于西汉时期的赠本官印绶现象。赠官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沉淀,至唐朝呈现制度化的趋势,于赵宋之世尤为完备,而同时期辽朝的赠官受历史背景与复杂官制的影响,且杂糅了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特色。金源王朝“奄有辽宋”,完颜氏双轨并举,一面沿中原王朝传统的轨道实行赠官,另一面沿北方游牧政权的轨道行之,二者融合发展,《金虏图经》云:“虏(金)之官品,本遵唐制。又以本朝(宋)之法并辽法参而用之。”[1]80张棣未讳言金朝之官制确以唐、宋官制为式,并参辅以辽法。本文探究的“赠官”,有必要在此略做说明。金朝“赠官”指朝廷对身故的官员、后妃的直系男性亲属、男性平民等赠与官职、爵位。赠官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官民因原有官爵达到一定标准或殁于王事死后而获赠官;另一类为在世官民的父祖赠官。本文重点考察官民的自身卒殁赠官。
比年来,赠官领域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有关金朝赠官制度的研究仍较为零散,李玉君在探究金朝宗室的任官和特权时,简要总结了宗室群体赠官的特点[2]。王新英在论述金代石刻对《金史》的补充与校正时,认为金代赠官制度应存在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可理解为赠官制度最终定型的时间[3]。王姝在探讨金朝后妃与本家关系时,总结了后妃的直系男性亲属的赠官特点[4]。孙红梅从“爵位”角度出发,阐述金代在封爵政策上,“死者”较“生者”享有更多的“优待”[5]。李鸣飞在探讨金朝官员“获得文散官的途径”时,指出如果子孙科举出身授文资,散官达到一定品级,父祖有可能获得封赠的文散官[6]。苗霖霖在阐明金朝官员赠谥问题时,认为有的官员逝世前虽未到三品,但赠官达到三品,同样获得了追谥的资格[7]。总起来看,当前学界尚未对金朝的赠官制度进行专题研究,这大致是缘于金朝赠官的史料较零散及其制度性规定过于简略造成的。笔者拟钩稽金朝史料及碑志文资料,兹仅就类别、模式、机构三个问题对金朝赠官制度进行梳理,请方家指正。
一、 金朝赠官的类别
全面爬梳《金史》《大金国志》《归潜志》等史籍,并佐以金源一朝的碑刻文,可知金朝赠官的类别繁多,大致有文阶官、武阶官、职事官、东宫官、地方官、三师、三公、使相、勋官、猛安、谋克、爵位等,被赋予赠官使命的各类官、爵在金朝的不同时期,显现出别样的发展特点。
(一)文、武阶官
官阶萌芽于北魏,延续至明清,“阶”“职”分离之制,以唐制最为典型,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8]18。宋初,寄禄官行阶官之权,元丰改制后又替换回原有的官阶体系,但其作用未发生根本变化。完颜氏既因袭唐、宋的赠官传统,又吸收和借鉴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官制特点,而辽朝的阶直接继承了唐代,是借用唐的文散官名称[9],其阶在辽官制里并不重要,已经失去了官品“标准衡量器”的作用[10]150-170。揆诸《辽史》纪、传,参检辽人的家族墓志等资料,笔者未发现辽朝存在以阶官为赠的确凿例证,也间接说明阶不能准确反映辽朝官员的身份和地位。熙宗颁行新官制前,金循辽法,未将阶官纳入赠官体系,据《完颜娄室神道碑》记载,“(娄室)天会十四年,追赠使相。官制行,改赠开府仪同三司,又追封莘王。”[11]52“天眷官制”实行后,像“开府仪同三司”类阶官渐被女真人吸收、认可,自此文、武阶官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文阶官自“天眷官制”颁行后,一直为官员生前加官及死后赠官的重要优赏。金朝赠文阶的比例总体较高,但在各时期存在不同特点。全面考索《金史》《归潜志》等金源文献,并参考墓志记载,兹就管见所及言之,作为赠官的文阶官如下: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特进、崇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荣)禄大夫、光禄大夫、荣禄大夫、资德大夫、资政大夫、资善大夫、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嘉议大夫、大中大夫、中顺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奉直大夫。此外正议大夫、中大夫、少中大夫、朝请大夫、奉训大夫、儒林郎等也常作为父祖赠官的内容,下文不作具体考察。总起来看,赠官上限始于从一品上阶的开府仪同三司,下限终于从六品上阶的奉直大夫,其涵盖范围较广,文阶六品为分水岭,六品以下的文阶官不作赠官。具体分析各朝文阶官的赠与情况,熙宗朝的文阶官多赠与宗室及女真族功臣,其品阶不低于从二品,呈高阶化特点,熙宗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依据宗室的血缘亲疏及生前功绩大小,大规模地追赠文阶官和爵位,其他部落的女真族首领也陆续得赠荣典,此外金初的契丹功臣萧庆得赠银青光禄大夫[12]1686,衍圣公孔璠也获赠荣禄大夫的褒崇[13]14。海陵朝文阶官的赠与对象以宗室及外族功臣为主,其品阶仍在从二品以上,高阶化得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已获赠官爵的宗室及各族功臣大多被改赠为二品以上的文阶官。世宗朝赠文阶官的比例较低,且集中赠与宗室和其他女真族显贵,如宗义受海陵迫害,“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孛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12]1741另有汉人医官祁宰因忠言被海陵诛杀,世宗“诏赠资政大夫,复其田宅。”[12]1874正三品中阶的资政大夫首次出现,二品以下的文阶官始被纳入赠官体系。章宗朝赠官的阶级进一步下移,嘉议大夫、大中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等四、五品文阶官开始发挥褒崇作用,但较低品级的文阶官多被授予汉族官员,宗室及女真族官员一般得赠二品以上的文阶官,而章宗夭折的子嗣,如洪靖、洪熙、洪衍更是得赠最高品阶的“开府仪同三司”[12]2059。金后期赠文阶官的占比仍较高,其品阶向下延伸至六品的奉直大夫(贾邦献)[12]2667,且获赠者以殁于王事的地方官为主,其中女真、汉族官员获赠数量未见显著差异。
金源一朝,作为赠官的武阶官如下: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昭义(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安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明威将军、信武将军、宣武将军、武节将军、修武校尉、忠翊校尉。总体而言,赠官上限始于正三品上阶的龙虎卫上将军,下限终于正八品下阶的忠翊校尉,其涵盖范围较文阶官更广泛,各级武阶官似皆可作为赠官内容,但武阶赠官的发展过程是曲折、动态的,各时期的变化需具体讨论。熙宗朝赠武阶官的数量较少,占比不高,获赠者基本为疏族或其他依附部落的女真首领,不赠与外族官员,且武阶官品级集中在三、四品,呈高阶化。囿于金朝史料的颟顸、粗率,在海陵朝官民自身卒殁的赠官内容中,未找到武阶官的蛛丝马迹。世宗朝的武阶官重获新生,获赠官员的数量激增,其中被海陵杀害的太宗、斜也、宗幹子孙集体获赠三品以上的武阶荣典,而契丹、汉族官员也被纳入武阶的赠官体系中,契丹官员生前均为品阶不高的地方官,因殁于王事,世宗恩赠武阶,如军士闰孙、史大及习马小底颇荅分别获赠八品的修武校尉和忠翊校尉[12]2640汉官仅世宗近臣张仅言于卒殁后得赠辅国上将军[12]2846,世宗朝赠武阶官的品级范围扩大至八品。章宗朝武阶官的数量回落,比例较低,除完颜宗道卒殁后得赠龙虎卫上将军外[12]1678,其余几位获赠者均为战殁的各族官兵,其品阶均在五品以上;金后期获赠武阶者不胜枚举,数量达到顶峰,其中获赠者多为战殁的地方官民,获赠者的品阶基本在五品以上。概言之,世宗朝和金后期为武阶赠官的黄金时期,获赠者多为战殁的地方官民。
(二)职事官
简言之,职事官即有具体职掌官员的统称。唐之官制,“有执掌者为职事官,无执掌者为散官。”[14]唐初,政府主要以文武散阶的体制封授官员,安史乱后,战事频仍、财政拮据,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衰败,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在唐末五代,甚至连一些使职本身也阶官化了[8]49,北宋元丰改制前,唐朝职事官衍生成为“寄禄官”,后神宗“以阶易官”,回到之前的官阶运行轨道上,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是时代的趋势。辽朝官制的复杂程度不下于赵宋,其官员的实职和虚衔不易区分,辽朝的官阶体系无北宋的“官”和“差遣”之分,皆可作“官”,其中中书令(政事令)、侍中及尚书令等所谓的“三省官”是辽朝赠官的重要内容,这类官职在辽初是有具体执掌的,但伴随职官制度的完善,逐渐沦为加官和赠官的虚衔,此外辽朝的尚书省为虚设机构,除尚书省六部官外,御史台官、卿监长官等也未被耶律氏应用到赠官体系中。王曾瑜先生认为,“金朝建立之初,落后的女真族根本没有整套官制,不过是首先逐步照抄辽制。”[15]太宗至熙宗天会年间(1123—1137)实行的赠官内容大体因袭辽朝,突显出辽的官制特色,后又逐步吸收唐、宋法,在“天眷官制”颁行后,“职”“阶”渐离,职事官几乎不作为赠官内容,但后期获赠职事官者数量“井喷”,其发展趋势呈阶官化。
金朝作为赠官的职事官大致如下: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省左丞相、尚书省右丞相、平章政事、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工部尚书、枢密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学士承旨。首先略论金初职事官的赠与情况,在天会七年(1129年),太宗集体对殁于“平州之变”的原辽汉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和康公弼赠官,其中虞仲文赠兼中书令,康公弼赠侍中[12]1725,太祖阿骨打入燕之初以辽官笼络二人,但虞、康不久卒于变乱,直至天会中方才获赠,是时金多因袭辽法,“中书令”和“侍中”应为完颜氏模仿辽官而赠,此二官虽在辽朝某段时间为虚衔或荣衔,但就总体情况言,二官属于职事官的探讨范畴。蒐罗《金史》《归潜志》及宋人语录等传统文献,未发现海陵朝有以职事官获赠者。世宗朝仅近支宗室完颜充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追降仪同三司、左丞相。”[12]1744然充生前官拜左丞相,死后追封郑王,世宗降赠充生前官职属于特例。降至章宗朝,死后赠职事官者依然是凤毛麟角,仅温迪罕缔达生前积官至翰林待制,“明昌五年(1194年),赠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成。”[12]2321是时似有其他获赠职事官的官民,限于史料的匮乏,其具体情况不明,但金中期的职事官未在赠官体系中获得重用,应是不争的事实。金后期赠职事官者数量剧增,由波谷跃至波峰,其中以尚书省官职为主,辅以御史台、枢密院、翰林院之职,且赠官均在三品以上,“职”“阶”多同时被应用于赠官,如《金史》云:“诏(女奚烈)斡出、(王)谨各赠官六阶、升职三等。”[12]2665后期职事官的滥授、滥赠推动了职事官的阶官化,省部寺监官组成的职位体系逐渐被架空。
(三)东宫官
东宫官即储君所属的官员。唐、宋两朝的东宫官为官员卒殁赠官的重要内容,且多赠东宫三师与东宫三少。检《辽史》及相关墓志的记载,发现辽朝在拥有一套汉制的官爵体系后,也对一些去世官员及其父祖赠与东宫官,其中官员自身卒殁赠官固定在三师、三少的范围,官员父祖赠官的范围则扩大至太子庶子、太子左翊卫校尉等品级较低的官职。值得注意的是辽之东宫官全部为虚衔,而金初的东宫官继承辽朝,仅作为官员生前加官及死后赠官的恩赏,直至海陵朝建立东宫制度,金之东宫官方有实际的职务。曾震宇在探析金初的东宫官时认为,“就官制的发展而言,金朝可说是辽、宋官制的汇合点,亦是辽、宋官制的源头——唐朝官制的再延续。”[16]曾先生的观点颇有见地,金初的东宫官确多因袭辽制,降至海陵朝,又在唐、宋的传统轨道上进一步发展。
有金一朝,仅见太子太师、太子少傅作为赠官内容。金初,完颜娄室和完颜谋演获此殊荣,娄室于天会十三年(1135年)赠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师[12]1653,谋演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赠太子少傅[12]1595,金初的东宫官仍沿辽朝的轨道运行,应用于本族功臣死后的赠官。自海陵王完颜亮建立东宫制度,东宫官几乎消失于赠官体系中,揆其缘由,似与该时期的东宫官确有辅佐皇储的实际职务有关。章宗朝以降的诸史料中,仅于元好问文集中发现一例,其云:“(孙)振之后入政府,迁尚书右丞,赠太子太师。”[17]942依托以上论述,可知晓金之东宫官非赠官的核心,其初期因袭辽制,后吸收唐、宋法,进一步发展自身特色,与唐、宋、辽有异。
(四)地方官
不论是实任还是遥领,地方官即专以地方政务为主的官员,而以“京朝官”为参照,其仍可称为“京外官”。唐朝赠与官员的地方官多为外州都督,且其总体趋势处于上升状态[18],宋朝赠地方官者多为武将,也有正任与遥郡官的分别,辽朝赠与官员及其父祖的地方官主要为节度使和刺史,且所赠多为遥领官,诸如防御使、团练使一类官职则不作赠官,金初因袭辽旧,至后期赠地方官的比例陡升,其特点较为鲜明。
纵观金朝,作为赠官的地方官如下:宣抚使、诸京留守、兵马都总管、遥镇节度使、节度使、节度副使、同知节度使事、知府事、同知府事、府判、防御使、同知防御使事、刺史、同知军州事、县令。金初地方官的赠与以遥领官为主,如完颜部人胡沙补与撒八殁于王事,天会中,俱赠遥镇节度使[12]2635,此外刺史也被赠与卒殁官员,据《孙伯英墓铭》载,“始祖坚,国初以军功赠龙虎卫上将军、陇州刺史。”[17]642辽、宋皆赠遥镇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官,金初亦仿效两朝旧法予以官员赠典。海陵与世宗朝未见赠地方官的例证,降至章宗朝,有东海县令完颜卞僧对宋战殁,赠海州刺史[12]277,东海县隶属海州,卞僧得赠比生前更高级的任官地官职,另有寿州死节军士魏全被赠宣武将军、蒙城令[12]280,魏全得赠寿州下属县的县令,二者生前为地方官民,均因战殁获赠。金后期赠地方官的比例陡增,以节度使官和刺史官为主,辅以诸京留守、兵马都总管、防御使、县令等官职,获赠者为地方官民,获赠缘由基本为殁于王事的推恩赠官,且官职多为生前任官地或居住地辖区的官职,如《读李状元朝宗禅林记》云:“李守济州,城破,不屈节死,赠乡郡刺史。”[17]240其中乡郡即指家乡所在之郡。金初因袭辽、宋旧制,赠官以遥镇节度使为主,但地方官在章宗朝前的赠官体系中未受重视,地方官仅代表官员生前官职的迁转,后期战乱频仍,官爵滥授,地方官也似职事官般呈“阶官化”趋势。
(五)三师、三公官
三师、三公在唐、宋、辽均作赠官,据《唐六典》载,“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近代多以为赠官。皇朝(唐)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但存其名耳。”[19]3三公官“亦但存其名位耳”[19]5,唐之三师自肃、代朝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比例和数量增加极为明显,三公官数量增加更快[18]。宋朝的三师、三公主要赠与近亲宗室和地位尊崇的文、武官员。参检《辽史》和墓志资料,发现辽朝也常以三师、三公赠与卒殁的契丹贵族和汉官显贵。金初,三师、三公多被应用于皇后父祖和近支宗室的赠官,此外卒于“平州之变”的原辽汉相左企弓获赠守太师[12]1724,曹勇义获赠守太保[12]1725。海陵、世宗、章宗朝赠与三师、三公的对象主要为近支宗室和后妃的父祖,此外海陵累以太师、太傅赠与渤海功臣挞不野[12]1809,章宗以太师褒赠降金的宋将吴曦[12]2180-2181。金后期赠三师、三公的比例不高,获赠者为宣宗皇后王氏的父祖与宗室完颜承晖。综上所述,金源一朝的三师、三公主要赠与对象为后妃的父祖和近支宗室,其他获赠者均为生前立有大功或地位尊贵的官员。
(六)使相、勋官
使相发端于唐朝,李氏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兼侍中、中书令为使相,但唐未以使相为赠,降至赵宋之世,使相的内涵丰富化,且被赠与地位显赫的官员。辽朝的使相也可作为赠官[20],且多赠与生前地位尊崇的官员或将使相作为官员父祖的赠官内容。金初使相的赠与大致和辽朝相似,如生前立有大功的女真将领完颜娄室赠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11],至后期,使相不再作为赠官内容,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勋官“止于服色、资荫,以驭崇贵,以甄功劳”[21]4921-4922,唐初之勋尚有尊崇的品阶地位,中期逐渐滥授,呈“阶官化”,李唐鲜有赠勋官者,赵宋之勋也非赠官的主力,辽朝因袭唐制,其勋官序列大致与唐朝、宋朝相同[9],爬梳辽朝碑志文资料,未见赠勋官的例证。唐、宋、辽的勋官地位较低,不足以褒赠身故的高级官员。有金一朝,世宗父(睿宗)完颜宗辅曾被海陵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12]410,在碑志文的记载中,也有少许官员的父祖得赠勋官,总体上,勋官并不受完颜氏的青睐。
(七)猛安、谋克官
猛安、谋克为女真的特色官职,《金史·兵制》云:“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2]992完颜氏将猛安、谋克纳入赠官体系乃赠官制度史上的一大创新。检索《金史》,发现金太祖阿骨打“变家为国”后,便对已身故的女真首领“追授”猛安、谋克,如乌延忽撒浑于“天辅初,追授猛安,亲管谋克。”[12]1919此外,大致在熙宗朝褒赠功臣时,乌延家族的另一人“思列,预平乌春、窝谋罕之乱,及伐辽、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赠银青光禄大夫。”[12]1919猛安、谋克不常授,但其为世袭官职,可荫补子孙后代,金廷为褒奖立功的女真贵族或优赏功臣的子孙,可能会予以“追授”。
(八)爵位
唐朝有九等爵,地位显赫的功臣和李唐宗室享有获赠的资格,宋的爵位体系大体因袭唐朝,其中身故的宗室和外戚为赠爵的主体,且内容以王爵、公爵、侯爵为主。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22]685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其封爵制度因袭中原汉法,爵位赠与的主体对象为契丹世家大族,具体为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少部分汉官也可得赠爵位,赠爵的内容大致为二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郡王及国公。金朝封爵制度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金太祖、太宗时期的封爵是对辽制的学习和模仿,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正式“颁行官制”,封爵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因此得以确立[5]。海陵颁行“正隆官制”后,调整封爵制度,削降大部分官员、宗室的爵位,世宗拨乱反正,对部分功臣和宗室予以“升爵”,但其制大体因袭不变,章宗严格控制王爵的封授,封爵制度基本完善。金后期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完颜氏为挽救危亡,滥授爵位,封爵制度走向衰落。
金朝赠爵的内容大致如下:二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郡王、国公、郡公。金初的封爵多袭辽旧,太宗朝的汉相刘彦宗为最早获赠者,《金史》云:“(彦宗)天会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郓王。”[12]1770熙宗确立封爵制度后,大规模地对身故的宗室、外戚及女真族功臣赠与爵位,其内容为二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和国公。海陵朝的用人政策“改变了祖宗以来依靠女真宗室贵族治国的用人政策,逐步大量启用普通女真人和外族封建士大夫”[23]115,天德、贞元年间主要对太祖系宗室、外戚及外族(汉、渤海)功臣赠与王级爵位,以拉拢人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正隆二年(1157年),“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12]107伴随封爵制度的改革,先前获赠爵封的宗室和各族功臣多被“降爵”,少数人被“削爵”而改赠阶官。世宗朝的赠爵者大体上为被海陵“降爵”“削爵”的宗室和女真族、汉族、渤海族功臣,赠爵内容为一字王、国公和金源郡王,郡王为新的内容,且“金源”与完颜氏的郡望有关,金人使用郡望作为封号,应是效法唐制的产物[24]98。章宗朝的赠爵对象为章宗早逝的叔辈、皇子及外戚,赠爵内容有一字王、国公、郡公,疏族和外族未获赠爵,可见至章宗朝,爵不滥授,封爵制度日臻完善。金后期出现爵授日滥的局面,但生前封爵与死后赠爵的数量相差较大,赠爵者的比例较低,且集中在外戚、宗室及战殁的高级军官上,其内容有郡王、国公、郡公,是时,爵位多在官员生前封授,阶官、地方官及职事官的追赠更受完颜氏的重视,赠爵比例的骤然下降也是金朝官爵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果。
二、 金朝赠官的模式
中原王朝唐、宋的赠官模式大体上分为单赠、双赠和多赠,其中单赠模式为官民自身卒殁赠官的核心,双赠模式中的组合形式繁多,多赠模式则以赠三官为主,也有赠四官、五官者。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赠官模式不似这般复杂,检《辽史》及墓志文资料,发现辽朝赠官仅单赠、双赠的模式,耶律氏应用多赠模式的例证并不充分。爬梳相关金源文献,基本的取向为《金史》《大金国志》《归潜志》等传统史料,并佐以金朝的墓志文资料,可知其赠官模式之梗概。总起而言,金朝的赠官模式以单赠、双赠为主,在赠官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完颜氏因袭唐、宋的中原汉法,将多赠模式应用在其官制中。
(一)单赠模式
金朝单赠的模式大致如下:单赠文阶官/武阶官/职事官/东宫官/地方官/三师/三公/爵。各类模式在金朝不同时期的特点迥异,仍需具体分析。金初以单赠文、武阶官和爵位为主,受赠群体为宗室和疏族功臣,另有些许殁于王事的女真将领被单赠以遥镇节度使,而卒于“平州之变”的四位原辽汉相分别被单赠三师和三省官。海陵朝的文阶官、爵位作为单赠内容,其中身故的宗室和各族功臣被“降爵”者颇多,少数被单赠文阶官。世宗朝的文、武阶官和爵位作为单赠,其中单赠文阶官者多为宗室,单赠武阶官者除宗室外,另有对外战殁的官民,单赠爵位者以近支宗室和开国功臣为主,爵位内容为一字王和金源郡王。章宗朝的文阶官为单赠核心,单赠武阶官、地方官、职事官、三师、爵位的数量较少,其中单赠文阶官者有宗室、宰相、衍圣公、地方三品大员,单赠武阶官和地方官者多为对外战殁的地方军官,单赠职事官者为翰林官温迪罕缔达[12]2321,单赠三师者为宋降将吴曦[12]2180-2181,单赠爵位者为皇叔和皇子,其制臻于完善。金后期的文阶官、武阶官、职事官、地方官、东宫官、爵位皆作为单赠内容,以单赠文阶官和地方官为主,受赠者基本为殁于王事的地方军官,但总体上,后期单赠模式的比例较低,双赠模式则更受青睐。
(二)双赠模式
金朝的双赠模式多应用于后妃、官员的父祖,本文重点考察官民自身卒殁赠官的双赠模式,其组合形式大致有:文阶官+爵/猛安/职事官/地方官、武阶官+地方官/职事官、三师/三公/职事官+爵、猛安+谋克。具体对各时期的双赠情况进行分析,金太祖、太宗朝无获双赠者,熙宗建立封爵制度后,多以“文阶官+爵”赠与宗室和疏族功臣,另有女真族首领获赠“猛安+谋克”的特色官职,总体上,金初以单赠为主,双赠的比例较低。海陵朝主要赠与疏族和外族功臣“文阶官+爵”,以“三师+爵”赠与太祖系宗室和亲信大臣,而以“三公+爵”得赠者鲜少,双赠的比例仍就不高。世宗朝赠“文阶官+爵”者集中在外戚群体,以“三师+爵”赠与太祖子宗杰[12]1604,完颜充以“文阶官+职事官”得赠[12]1744,世宗朝的外族官员未得双赠,双赠比例持续走低。章宗朝以“文阶官+爵”赠与早夭的皇子,均赠最高品阶的“开府仪同三司+一字王”[12]2059,“武阶官+地方官”始崭露头角,寿州死节军士魏全被赠“宣武将军+蒙城令”[12]280,该时期双赠的比例仍不见回升。金后期为双赠模式的重要转折点,其数量陡增,达到顶峰,以“武阶官+地方官”或是“文阶官+地方官”获赠者最多,此外以“职事官+文阶官/武阶官/爵”的模式获赠者亦有,其组合形式呈多样化的特点。
(三)多赠模式
金朝的多赠模式同双赠模式一样,多应用于后妃、官员的父祖。自身卒殁得赠两官以上者甚少,非立有大功的宗室不得多赠。例如,世宗父完颜宗辅从伐辽、宋,有大功于社稷,被海陵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12]410,“三师+勋官+一字王”的模式首见诸金朝史料。另有宣宗朝的宗室完颜承晖生前官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帅,封邹国公,金中都失守后自杀殉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12]2227,宣宗以“文阶官+三公+三省官+郡王”的四官模式褒赠承晖,以劝励职官精忠尽职。
三、 金朝赠官的主管机构
在金朝的不同时期,负责赠官的主管机构有所变更。金初因袭辽制,主管汉人赠官的机构似为枢密院,后都元帅府全权负责赠官事宜,尚书省六部设立后,金沿唐、宋法,以吏部主管赠官。金后期的行省、行枢密院及封建割据势力拥有“便宜”之权,往往可承制赠官,先斩后奏。
吴丽娱指出,唐代赠官主管机构为尚书省吏部的司封司[25]812。郭浩依据五代时期的相关诏令,认为五代沿袭唐制,赠官的主管机构仍为吏部司封司[26]。蒐罗墓志文资料,笔者推测辽朝中后期主管赠官的机构可能为南枢密院下属的吏房。金初多沿辽制,女真人以“因俗而治”的方针统治新占的汉地,枢密院应时而生,天辅七年(1123年),“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12]1002,金初枢密院“尚踵辽南院之旧”[12]1216,刘彦宗为知枢密院事时,金太宗“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进兵伐宋。”[12]1770据张喜丰考证,在刘彦宗主政枢密院时期,是枢密院职能与作用最盛时期[27],是时总领汉军的枢密院应为主管汉人的赠官机构,金亡北宋后,太宗诏元帅府曰:“将帅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迁赏之。其殒身行阵,没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赐赠官爵务从优厚。”[12]1697枢密院职能弱化的同时,都元帅府全权负责各色人等的赠官事宜,尚书省吏部设立后,渐收选官权于中央,《中兴小纪》载,“(金)六部初置吏、户、礼三部侍郎,后置三尚书,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书郎官,左、右司,及诸曹皆备。”[28]226田晓雷考证,金朝中央吏部的设立应在天会十二年(1134年)之后,天会十四年(1136年)之前机构基本健全[29],《金史》云:“(吏部)郎中掌文武选、流外迁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诰。一员掌勋级酬赏、承袭用荫、循迁、致仕、考课、议谥之事。”[12]1220金因袭唐、宋法设尚书省吏部,但未置司封司,吏部诸司机构的职掌被合并,“天眷官制”颁行后,吏部郎中为具体负责赠官的官员,中央尚书省吏部为赠官的主管机构。金后期战乱频仍,金廷在各地设立行省、行枢密院,“封建”各地割据势力,行羁縻统治,金廷多予地方军官“便宜”之权,如《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载,“其葬也,公(行台严公)感念平昔,赠以信武将军云。”[17]634但地方军官也仅是承制赠官,事后必须及时上奏中央,就大部分情况言,赠官的主管机构仍在中央尚书省,皇帝颁布赠官诏令后,有司方可执行。
四、金朝赠官发展阶段与特点
前文以类别、模式、主管机构分别梳理了金朝的赠官制度,就其发展和演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初期即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至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其特点如下:第一,以赠高品级阶官和一字王、公爵为主,以生前功勋显著者为赠与对象,其中宗室成员占较大比重,三师、三公赠与皇后的父祖和近支宗室,地方官以赠遥领官为多,使相、东宫官循辽、宋法,作为女真族功臣死后的荣赏,“追授”猛安、谋克为赠官制度上的创新;第二,以文、武阶官和爵位为主要单赠模式,双赠模式以“文阶官+爵”为主,受赠群体为宗室和疏族功臣,未应用多赠模式;第三,金初因辽制,主管汉人赠官的似为枢密院,后其权渐移于都元帅府,熙宗参唐、宋法,以中央的尚书省吏部为主管机构。
中期即海陵天德元年(1149年)至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有如下特点:第一,仍以赠阶官和爵位为主,阶官的品级逐渐下移,爵位的赠与内容丰富且赠与标准愈趋严格,此外该时期赠与职事官、地方官、东宫官的数量较少,三师、三公仍为后妃父祖及宗室的赠赏;第二,文、武阶官和爵位仍是单赠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双赠模式以“文阶官+爵”和“三师/三公+爵”为主,此外完颜宗辅得赠三官,总言之,双赠模式的比例较低,单赠仍为主角;第三,赠官的主管机构为尚书省吏部,机构内部职能渐趋完善,吏部郎中为具体负责赠官的官员。
后期即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至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有如下特点:第一,尽管赠文、武阶官者不胜枚举,但赠爵者较少,且集中于宗室和地方高级军官,该时期类似唐宋间职事官“阶”化的现象出现,省部寺监官组成的职位体系因职事官的滥授、滥赠逐渐被架空,地方官也滥赠不暇,似职事官般“阶”化,此外饶有趣味的是使相、猛安、谋克等官职未再出现于赠官体系中;第二,以单赠文阶官和地方官为主,双赠的组合形式繁多,尤以“阶官+地方官”更受完颜氏青睐,此外宗室承晖获赠四官,该时期双赠模式的数量达到顶峰,单赠数量较少;第三,出现地方部门承制赠官的现象,但中央吏部仍主其事。
明乎上述阶段特点,可知阶官、职事官、地方官、三师、三公、爵位被完颜氏应用于常态化的赠官体系中,东宫官、使相、猛安、谋克等官职渐淡出赠官的历史舞台,金源朝的赠官模式以单赠和双赠为主,鲜有多赠者,其赠官主管机构的更替顺序大致为“枢密院—元帅府—尚书省吏部”。金朝在因袭唐、宋、辽赠官制度的基础上,“参用请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循习。”[30]1198其制因袭与发展,成一代典章,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