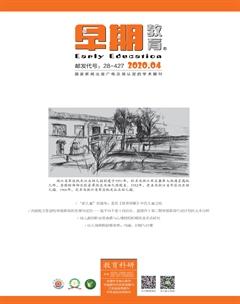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实践模型研究
王燕 刘国磊 张卫宇 钱雅文
【摘要】借鉴苏霍姆林斯基以义务感为核心进行家校(园)合作的教育经验,对当前家园合作工作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实践模型,其本质特征为以义务感为驱力与目标,义务感在家园合作的超循环系统中旋升。建立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实践模型就是以夫妻之爱提供儿童义务感生长的土壤,以父母子女之责滋养儿童义务感的幼苗,以家园合作成就义务感的快速生长,以幼儿园教育播撒义务感种子的活动过程。
【关键词】义务感;家园合作;实践模型;苏霍姆林斯基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20)04-0052-05
【作者简介】王燕(1984-),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硕士;刘国磊(1984-),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诊改办公室科长,讲师,硕士;张卫宇(1970-),女,河北秦皇岛人,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教授,硕士;钱雅文(1971-),女,河北秦皇岛人,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学生处心理咨询室科长,教授,硕士。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实践重视以家校(园)合作促进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的正面影响,其在教育实践中对家校(园)合作主体的人性、道德的凸显足以表明,以义务感为核心可以使家校(园)合作内部驱动、观念协调、方法适宜、循环提升。深入解读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借鉴以义务感为核心进行家校(园)合作的经验,提升家庭和幼儿园双方教育水平,对当前家园合作工作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实践模型的内涵
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义务感表现为:基于善的人性,个体通过关心、理解、同情、奉献他人,实现社会角色期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义务感体现在家园合作中,具有道德情感基础、教育方式、教育追求等多重属性,家园合作模型也应以义务感为核心,展现新的内涵。而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实践展现了以义务感为核心,以家园“互动”“协同教育”促进“儿童全面和谐发展”的有效模型。
(一)家园合作以义务感为驱力与目标
义务感是家庭和幼儿园两个教育集体之间、多个个体之间互动的驱力与目标。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义务感是促进多方主体各司其责的动力,是营造良性教育氛围的重要途径,是家园合作的重要追求。家园合作,顾名思义,主要由家庭与幼儿园两个集体在儿童教育中的互动构成。苏霍姆林斯基的家园合作教育实践,不仅关注两个集体之间的简单互动,还重点看到多个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家庭中,包括祖辈与父辈的互动、丈夫与妻子的互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兄弟姐妹的互动、祖辈与孙辈的互动;幼儿园中,包括师幼互动、师师互动、幼幼互动;第三类是幼儿园诸个体与家庭诸个体之间的互动,其中儿童在两个集体中均为重要角色。这决定了家园合作基于儿童发展、为了儿童发展的特性。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集体的爱抚和善良情感,集体的良好意愿,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它犹如汹涌的巨流把那些最不易动情的人也推动了”[1]。因此,要重视激发集体的义务感,以义务感为动力,发挥触动他人的教化能量。同时,也要看到儿童生活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中,要“使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要把与其他人的关系建立在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上” [2]。
家园合作以义务感为驱力与目标,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善的人性、主体间的信任、教育行为的一致性。其中,善的人性是家园合作的首要条件,主体间的信任是家园合作的必备基础,教育行为的一致性是家园合作的必要条件。
(二)义务感在家园合作的超循环系统中旋升
家园合作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家庭和幼儿园两方主体在儿童教育工作中的协同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关系是儿童成长的道德源泉,幼儿园集体的爱的唤醒力量是儿童成长的道德路径,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深化道德认识,促进知行合一以及道德的整体发展。这三者形成了依次提升的逻辑平台,在共生中形成了自循环的整生,即以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模型呈现旋升的超循环样态。个体家庭中的义务感以独特的表现形式为儿童扎下美德之根,儿童在幼儿园教育的引导下使美德之根显性化、泛化于集体生活,社会生活的义务感将善的人性放大、绵延,规约、推进了现实与未来的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这就在回环往复中形成了以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自循环形态的超循环,显示家园合作系统的整生规律。在这一超循环系统中,义务感在儿童个体、家庭、幼儿园、社会中增强、泛化。主要表现为:
1.“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家园合作的出发点
“对苏霍姆林斯基来说,所谓的道德,首先不是一套外在的规范或所谓的道德系统,而是指处于生命的核心,又流溢到生命的各个方面直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3]因此,基于善与仁爱的义务感可以净化儿童生长的气氛,滤出气氛中的疑虑、敌对、丑行、恶意。以基于善的人性的义务感促进教育的进行,不仅利于社会角色之间施加正确的教育力量,更可贵之处在于儿童因拥有幸福人生而保存、弘扬人性中的义务感。可见,以义务感为家园合作的核心,既能促进教育的有效开展,又有助于社会的正向绵续,而这皆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途径与目标。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和谐统一(即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公民和劳动者”[4]。
2. 自我教育是个体义务感旋升的基本路径
“严格地说,自我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让一个人去关心另一个人,力求看到自己身上的好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5]生活在民主的义务感而非强制制度下的儿童,会弘扬心中的仁爱与善良,并将这仁爱与善良以对他人的关心呈现出来,推广至周边的每一个人,不论富裕贫穷,不论亲疏远近,不论爱慕憎恶,甚至会推广至人类以外的动物、植物,哪怕没有“心灵”,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那纯净的孩童的民主是不顾宗法制度的……他不知道唯独人才有心灵”[6]。因此,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实践注重对儿童“关心他人”的情感和意识的激发,并認为义务感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的催化剂,同时在自我教育中旋升[7]。
3. 互动关系的良性环进是义务感的追求
公共生活中的人皆在大大小小、交叉变换的共同体中共处,并在共同体中承担一定角色:夫妻、子女、同事、朋友、合作伙伴等,每个个体都享有角色所带来的一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在关系中,每个人都具有双向性角色,服务与关照的给予者也是被给予的接受者,爱与善的情感的感受者也是同样感受的创造者,被他人义务感的包围者也是对他人义务的履行者。而这种双向的关系,不限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亦推广至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相互匹配关系中,这种匹配关系突破时空、代际限制。但人们普遍感受到,“生活的全部高尚寓于对义务的重视,生活的耻辱在于对义务的疏忽”[8]。义务感便在角色关系的匹配与发展中增强、泛化、绵延,并促进角色互动关系的良性环进。例如,夫妻之间的义务感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互相关心、善待,同时突破婚姻关系延续到孩子对待他人以及对待未来丈夫(妻子)的态度;父母教育孩子的义务感,除形成美好的亲子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促使孩子以亲子关系为“阵地”,与世界建立义务感,孩子也会成为有义务感的父母,重视对自己下一代的关爱;幼儿园对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表现出的义务感使孩子在学校感受快乐、智慧成长,同时创造欢乐,为集体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实践模型的建立途径
“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就是集中在他身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9] 每种社会关系都体现了个体身上承受的角色期待,实现这种期待则需要义务感的建立。在教育中,履行义务之后获取的成就感是激发义务感的关键因素:在家园合作教育中,促使个体义务感产生的关键是教育对于儿童成长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儿童作为家园共育对象的成长上,还体现在家庭、学校多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多重主体的和谐进步。
(一)夫妻之爱提供儿童义务感生长的土壤
家庭成员关系的融洽与和睦程度、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风格和效果。家庭关系中的基础和核心是夫妻关系与爱情关系,因此,苏霍姆林斯基对此作了专门阐述,“爱情的幸福,就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切责任感……爱情能最鲜明地反映每一个人对我们社会未来的责任感”[10]。“夫妇间的爱情、信任、相互的忠诚和帮助,这是向父母智慧之树提供营养的须根。”[11]可见,建立良好的爱情关系是承担为人父母责任的基础。父母“要在家庭中创造有利于教育子女的气氛”[12],“应首先以自己的相互关心的行为来教育孩子”[13]。
(二)父母子女之责滋养儿童义务感的幼苗
“义务感是家庭生活中人性美的核心,要让孩子成为有义务感的人,每个人都要对全家负责。”[14] 义务感在家庭教育生活中的表现应是主动承担家庭生活成本的意愿——如劳动,关心与服务其他家庭成员,承担教育事务等,是一种积极的生活与教育态度,也是家庭成员“在真正构成选择的情况下的内心对‘应当的认同,而不是‘被迫的服从”[15]。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家庭教育生活中,父母、子女应承担的职责分别为:
1. 父母的首要之责是正确表达父母之爱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爱与归属”需求得以满足是个体通向自我实现阶段的必要阶梯。父母对孩子出自本能的爱及父母之爱的正确表达能促进孩子的成长,是家庭教育的基础。苏霍姆林斯基在其教育著作中呈现了诸多收到良好效果的做法:万尼亚的母亲从饥饿与死亡中拯救并收养了四个孤儿,卡佳的父母将果园变成供孩子活动的俱乐部,萨达的父亲常常为孩子们组织即兴音乐会,等等。这些家庭教育的做法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父母对于孩子的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确保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义务感。“爱就意味着用心灵去体会别人最细微的精神需要。而这种心灵的感受能力是来自父母,但不是什么言语和解释而是榜样。”[16] 因此,父母的首要之责是正确表达父母之爱,这不仅使儿童“爱与归属”的需求得以满足,并为儿童提供了学习如何去爱的榜样。
2. 父母子女共同承担家庭生活的劳动之责
家庭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最初摇篮”[17]。在家庭中感受父母之爱并以爱回馈的同时,孩子耳濡目染父母对于社会的贡献,便会以家庭为基地,承担生活的职责和义务。劳动是激发儿童义务感的重要途径,家务劳动“实质上是学龄前儿童能够亲自参加为他人做事的唯一的活动形式”[18]。通过多种类型的家务劳动以及对父母工作的帮助,可以培植孩子对他人奉献的义务感,形成“心中有他人”、尊重他人、不妨碍他人、服务他人的习惯。
西塞罗说,“我们模仿每个人认为合适的人,并且遵循他们的志向和原则。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受父母教诲的影响,仿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性格” [19]。激发孩子从事家庭劳动的义务感之时,家长也要同时肩负家庭生活的责任。“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够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没有父亲的光辉榜样,一切有关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谈论都将变成空谈。”[20]
(三)家园合作成就义务感的快速生长
再高大的壁垒也无法把社会、家庭与学校(幼儿园)隔离开来[21]。“教师们只有和家长同心协力,才能赋予孩子们以巨大的、人的幸福。”[22]苏霍姆林斯基在其教育实践中以家长学校为中心,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家长工作,将增长家长的教育学知识与培养家庭教育实践技能并进。
1.“学校(幼儿园)领导家庭,与家长形成统一认识并进而形成教育合力”[23]
义务感具有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其认知内容愈明确,情感体验愈强烈,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定向作用就愈明显。然而,在家庭教育中常常出现两类截然不同的欲望倾向,一类是由对下一代的疼爱的欲望衍生出的过分溺爱,表现为不当的过分表扬、有求必应、包办代替等;另一类则相反,对于自己的爱的欲望远远胜于对子女教育的义务,因此,对子女的存在视而不见,对子女的教育消极怠惰。西塞罗说,“让欲望服从理智,对于遵守义务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合适的了”[24]。在西塞罗看来,知识是道德高尚性的重要元素之一。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家庭要有高度的教育学素养,这是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方面,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25]。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这个问题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为此,他专门编写了《家长教育学》,作为向家长教授教育学知识的教材,并开办了家长学校,使家长们在孩子入学以前,甚至在还只是想要成为父母的时候就可以接受家长教育,直至他们的孩子从中学畢业,从而以家长学校为中心增长家长的教育学知识,以知识与理性激发家校合作的义务感。
知识是道德高尚性的重要元素,但不直接指向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还需要经验和实践。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教育不仅停留于教育学知识的讲解,并且重视对于家长的教育实践的指导与督促,多种家长工作形式并进,包括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因此,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学校并不是孤立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机构设置,而是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桥梁。以家长学校为中心,家庭之间可以分享有益教育经验,吸取失败教训;通过家长学校,幼儿园可以教授正确的教育学知识、技能;家长学校还充当教育资源的“共享站”以及教育活动的举办地。例如,家长学校举办书籍展览会,帮助家长发现更多、更好的适合自己或孩子的书籍,以便让更多的书籍走进每一个孩子的家庭,从而推动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的家庭阅读活动;同时,家长学校通过举办多种节日庆贺或纪念活动,促进家长重视某些教育工作并集中完成。
2. 以儿童义务感为媒介催化家庭教育义务感
随着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儿童教育更加受到关注,儿童的主体地位更加得以彰显。儿童作为家庭中的重要主体,学习、教育、服务、享用家庭财富等多种权能更加突出。因此,在當今教育条件下,更应看到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实践中儿童的主体地位,他们可以通过幼儿园教育的道德泛化,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儿童进入幼儿园后,家庭与幼儿园二者成为儿童道德教育的主要源头。家庭与幼儿园在空间上相对分离,因儿童在其间往返,相对分离的空间又相互融合。对儿童而言,在两个场所中的感受是相互融合的,儿童也因为接受影响的更新而反作用于家庭与学校。以儿童为中心,形成了学生与教师、同学之间、儿童与家长之间的直接互动,并形成教师与家长的间接互动。苏霍姆林斯基说:“我竭力想使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要把与其他人的关系建立在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上。”[26] 事实证明,对于家庭、幼儿园两个道德“水源的清洁”,儿童是具有主动性的,“只有在儿童极力给家庭带来欢乐时,学校和家庭的努力才有可能统一起来”[27]。儿童生命整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可以催化家园合作教育的义务感,以义务感为核心的家园合作又进而成为滋养孩子心灵的涓涓细流[28]。
此外,幼儿园教育可以有意识地向家庭延伸。延伸的形式可以是幼儿园教育内容在家庭中的巩固与分享,可以是倡导幼儿园履行家庭生活义务等。延伸的重点不仅是幼儿的义务感得以践行,并且致力于调动家庭教育的义务感。以幼儿的家庭作业为例,“要求学龄前儿童在家里完成一定的任务和作业,是为了提高儿童的独立自主能力和创造精神,同时也可以调动家庭中成年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儿童学到的知识”[29]。
(四)幼儿园教育播撒义务感的种子
1. 充实儿童的“智慧、情感和意志”
“教育实践是以人的活动为中介,将人的本质力量内化于教育活动之中,以真善美为尺度,塑造理想的人。”[30]因此,“人在童年时期应当经历一个培养情感的学校——培养善良的学校”[31]。在“快乐学校”教育实践中,学校对儿童的成长负有明确的义务——使儿童在学校世界中享有幸福与快乐,每一天都得到“智慧、情感和意志”的充实。为了促使儿童达到这一目标,幼儿园教育需要在避免不良倾向上至少做到两点:一是“使认识活动不至于变为枯燥的教学”[32],二是“不能把上学变成没完没了的、表面热闹而实际空虚的玩乐”[33]。为了使儿童享有幸福快乐,“快乐学校”在实践中主要激发儿童通过童话、幻想和游戏以及儿童的独特创作,走进大自然中见、思、说,从而学会思考、学会探索,成为智慧充实、心灵高尚、意志坚强的人。西塞罗说,“应该做到使各种欲望服从理智,既不超越它,也不由于怠惰或懦弱而滞后,并使他们保持平静,不受各种心灵纷乱的干扰,这样全部坚定和全部节制才可能放射出光彩来”[34]。
2. 肯定儿童的“父母义务感”,并进行“未来父母”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集五种角色于一身,其中重要的一个角色即为“具有崇高道德基础的新家庭的建立者”。“高明的教育之道,就是善于把不懂事的孩子当作明天的父母来看待。”[35]为人父母与天职、人性相连,可以说教育、养育下一代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感。儿童从两三岁就开始玩“娃娃家”游戏,在游戏中有模有样地模仿生活中爸爸妈妈的一系列动作——喂饭、哄睡、唱童谣等,这正是“父母义务感”的早期显现。成人应首先尊重儿童在童年时期对于父母天职的探究,肯定其“父母义务感”,例如,尊重、赏识儿童的“娃娃家”游戏,认真对待儿童诸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之类的问题。而后,“我们不但培养孩子对待人诞生的那种高尚态度,我们还要培养未来的父亲和未来的母亲”[36]。“在学校高年级就要教育青年男女为尽父母的天职作准备……不是所有的人都将成为数学家、工程师、教育家、医生和设计师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要做父母……于是,苏霍姆林斯基首先带头在课外活动时间亲自对学生讲爱情问题,讲婚姻问题,讲怎样在精神上培养自己去履行做父母的义务,讲夫妻怎样共同生活,讲一个人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37]这样,“父母义务感”在“未来父母”那里萌生并建立起来,以期未来的孩子从降生便能感受到义务感的 “水源的清洁”,这对于人性的发扬、义务感的绵续具有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6][21][22][30][32][33]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唐其慈,毕淑芝,赵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26][31]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育人三部曲[M].毕淑芝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23][28] 魏智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4][10] [苏]塔尔塔科夫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生[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5][25]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7] 李镇西.追随苏霍姆林斯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19][24][3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M].张竹明,龙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18][29] [苏]马尔科娃.幼儿园和家庭[M].杭志高,王春明,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9][15] 薛洁,张丹竹.公民义务感:彰显文明的政治态度[J].江苏社会科学,2012(10).
[11][12][13][16][20]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家长教育学[M].林志英等,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2.
[14][17] 孙孔懿.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7][35][36]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第2卷[M].蔡汀,王义高,祖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7] 王天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自组织理论视角下,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资源共享模式研究”(课题编号:201803040153)、河北省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高职信息化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编号:JZY17084)的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刘国磊,beckham821@126.com
(助理编辑 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