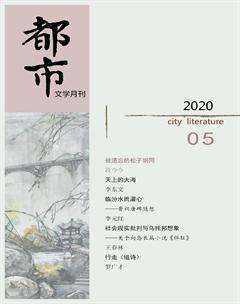临汾水而濯心
李元红
太原晋祠,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亦即那通天下闻名的唐碑,在这里安然地伫立了1300多年。在它的身旁,并排伫立着另一个外表看似一样的碑,那是清乾隆年间立的一块仿碑。有一个伴儿默默地在一旁陪伴着,唐碑或许并不孤独。
这个唐碑,看起来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大青石碑石,它的表面闪烁着清冷的光,如果用手抚摸,也一定是一股凉意沁透肌肤。遥想当年的唐太宗,回到他的龙兴之地晋阳,感慨系之,挥笔书之,于是便有了这块唐碑。1300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曾经辉煌的大唐也与我们渐行渐远。可是,这碑,今天依然坚实地伫立于此。它无时不在默默地叙说着当年的往事。它强大的信息流坚硬而执着地穿越历史时空,笼罩着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穿透全身,直逼心灵。这就是碑石的力量,它以自己强健的身体承载了遥远而厚重的历史,承载着不能承载之重。
我不由想起那年我曾站在贺兰山岩画面前,在冷峭的山风中,一种强大的信息场瞬时将我击中。相隔万年的古人在这些画面中忽然复活,我可以真实地感觉到来自远古的信息、生命的信息。如今,当我站在唐碑面前时,再一次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而且相对于岩画而言,唐碑带给我的信息更强烈,更真切,更历历在目。如果说那些岩画所传递的信息更多的是空灵与缥缈,给人以无限的想象与感触的话,那么唐碑则以高大威严的姿态、装饰华丽的碑碣和雄奇高贵的碑头螭首,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一种堂堂的皇家气象。
碑文以优美的行书和华丽的文字,详尽地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思想火花与内心世界。这文字,让我又一次走近大唐,走近唐太宗的内心,感受到他情绪的激昂炽烈,感受到他思想的温度与锐利,感受到他笔墨的灵动与气息的流淌。此刻,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到,历史很近,就在眼前。
大唐,从太原出发
辉煌的大唐王朝这趟列车,其始发站,就是太原。
太原这块土地历史悠久,底蕴极为深厚,尧时此地即属唐国。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桐叶封弟”,本是小帝王和弟弟唐叔虞的一个儿戏,可是,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一个儿戏,真的就把唐叔虞封于唐地,成为古唐国开国诸侯。因为此地晋水日夜流淌,福佑百姓。于是,唐渐而变成了“晋”。后人在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处建唐叔虞祠,供世代祭奉,这就是晋祠。
周王之亲,唐国之宗,晋国之祖。太原的唐叔虞祠,已不是简单的皇家家祠的概念,而是名副其实的国祠,其地位之显隆不言而喻。难怪李世民把太原这块宝地誉为“神邦”,这一定义明晰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这块土地的崇拜之意与深厚情感。
公元617年,民变频起,群雄起事,天下大乱,隋王朝岌岌可危。年仅19岁的李世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远见与胆略才干,极力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他们从太原府晋阳城起兵之后,半年时间便攻入长安,灭隋建唐。
“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发迹神邦。举风电以长驱,笼天地而遐卷。一戎大定,六合为家。”唐碑中,李世民这样娓娓道来,先皇李渊继承唐叔虞一千多年前唐之徽号,仿效周武王亲率八百诸侯讨伐商纣的历史担当,竭尽赤诚之心,祈求唐叔虞之神灵降福保佑。率军誓师,发迹于神邦太原。义军风驰电掣、席卷天地,于是很快天下大定,四方统一,建立了大唐王朝。
李世民父子为何执意立国号为“唐”呢?唐,唐叔虞之徽号,来自遥远的古唐国。可是,这个唐,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汉字,而是代表天意,代表着神灵,代表着鸿运当头、吉祥顺遂、江山永固……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之时,“爰初鞠旅”,曾在唐叔虞祠前叩拜,祈求唐叔虞的神灵保佑他们成功。他们一路征战,打入长安,当他们将要建立新的王朝之时,立国为唐,与其说是感恩神灵,不如说是秉承神灵的旨意更为贴切。“德乃民宗,望惟国范。故能协隆鼎祚,赞七百之洪基;光启维城,开一匡之霸业。”同时,他们也一定想到了唐叔虞以德治国,励精图治,开创了晋国兴盛七百年洪基伟业的丰功伟绩。唐叔虞德政的美名天下传扬,所以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是秉承神灵的旨意,不如说是继承唐叔虞的治国理念和德政传统更为贴切。此时,一个大大的“唐”字,冉冉升起,映耀天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王朝“大唐”从此诞生。显见,大唐王朝的建立,不仅仅是肇始地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厚文化血脉的传续与古风古韵的精神契合。
《说文》:唐,大言也。形声,从口,庚声。从遥远的古唐国走来的大唐王朝,让这个“唐”字从此响彻天下,彪炳千秋。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辉煌的一页。天朝盛世,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诗歌、书法、绘画登峰造极。无论当时的盛世景象,还是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唐,都发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是名副其实之“大言”。唐,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个身份鲜明的标签,一个深深刻于骨肉的烙印。唐人,唐装,唐人街,唐———朗朗弘音,亲切可人。这是一个让人思绪万千的字眼,一个令人情以系之的图案,一个发自丹田、洪亮而悠长的开口强音。
温煦的唐风,肇始太原,传扬天下。
“太原公子”的太原故事
太原,是李世民父子的发迹之地。李世民的青年时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对太原有着特殊的感情。公元615年,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是军政一把手。李世民随父来到太原,时年17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时人称之“太原公子”。这个称呼颇具深意,不是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也不是风流倜傥纨绔子弟,而是对李世民的赞誉和美称。事实上,青少年时期的李世民就已经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谋略、胆识与军事才干。《旧唐书》评价他:“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新唐书》评价他:“聪明英武,有大志。”
李世民生于多事之秋,长于戎马之间,在太原期间,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史载,在太原期间,从三件大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世民的“聪明英武,有大志”。第一件事是计救被突厥围困于雁门的隋炀帝。隋大业末年,隋炀帝北巡,被突厥十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募跟随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大军出发之际,他料敌于前,已经成竹在胸。他对云定兴将军说,一定要携带旗鼓以设疑兵。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促无援。我军要大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敌人一定认为救兵云集,就会望尘而逃。不然,敌众我寡,正面交锋,难以取胜。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依计而行。军队进驻崞县,突厥侦察兵急驰报告始毕可汗说:“王师大至!”可汗大惊,急命部队撤兵,于是解围而遁。隋炀帝在感激涕零之中,第一次见识了太原公子的軍事才能。不过,隋炀帝也万万不会想到,这个李世民也正是他日后杨家王朝的掘墓人。
第二件事是李世民为救父勇闯敌阵。高祖李渊镇守太原时,高阳有个叛乱的首领魏刀儿,自号“历山飞”,前来攻打太原,高祖在迎击战中,深入敌阵被困。危急时刻,李世民率领精锐骑兵突围而进,张弓射敌,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从万人之中救出高祖。这时步兵赶到,李渊父子奋力攻击,大败敌军。如果说上一个故事是以智取胜,那么这个故事则生动地表现了李世民的勇猛无畏。
第三件事是太原起兵前后,以至建立大唐王朝,李世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明辨天下大势,清醒地看到隋朝必亡,于是散财养士,广结天下豪杰,暗中积聚力量。在其父李渊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千方百计促使李渊做出决断,起兵晋阳。在起兵进军到灵石霍邑时,他们遇到隋将宋老生的强力阻截,恰逢久雨粮尽,战事不利。李渊此时计划“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关键时刻,李世民站了出来,力谏劝阻。这件事在史书记载中详尽生动,李世民力劝其父:本来兴起大义是为了拯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恐怕随从义举的人会一朝解体。退守太原一城之地,这不过是盗贼罢了,何以自全?父亲李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x是一意督促命令他引兵撤退。李世民急火攻心,在李渊的帐外大声哭号,声闻帐中。李渊召问其故,他回答说:如今是举大义之兵,进军奋战则必胜,退兵则必败。兵众离散在前,敌人进攻在后,死亡就在眼前,所以悲伤。李世民的一番话让李渊“乃悟而止”,立刻下令停止撤军,一鼓作气拿下了霍邑。随后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半年之后就打入长安。大唐建立之后,天下诸侯割据,各自称雄。李世民率部南征北战,先后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为唐朝的巩固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有学者怀疑,这段历史对李世民有篡改美化之嫌,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阔别28年重回太原
太原乃龙兴之地,王业所基。可是,从公元617年起兵晋阳,离开太原,28年过去了,李世民从未回过太原。经玄武门之变,从他登基之时算起,也过去19年了。没当上皇帝的时候,为巩固大唐江山南征北战,四面征讨,无暇顾及。特别是兄弟之间争夺皇位那阵子,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凶险异常,哪里还有闲情逸致重游故地。玄武门事件后,李世民御临天下,日理万机,也没有机会回来看看。故地重游,可能需要一个契机。
机会来了。
b
据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四月,唐太宗欲仿秦皇汉武,东封泰山,下诏定于次年二月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责令有关主管官员详细议定程序仪式。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在太原的老朋友们觉得机会来了。他们多年来也一直在期盼着太宗荣归故里,并且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十五年五月,并州的僧道名宿和故旧老友亲自赴京上表,表曰太原是王业的发基之地,皇帝明年登泰山封禅之后,恳请在返回长安途中,“愿时临幸”,顺道回太原看看。唐太宗亲切接见太原的故旧老友,在武成殿赐宴,叙旧聊天。太宗对侍臣和故旧老友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当时宴席上皇帝的故旧老友,一起回忆着大家在太原的往事,氛围融和,谈笑甚欢。太宗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谀。公等朕之故人,实以告朕,即日政教,于百姓何如?人间得无疾苦耶?”意思是说,都是自己人,说点大实话,国家政策如何,老百姓生活到底好不好。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欢乐,陛下力也。臣等余年,日惜一日,但眷恋圣化,不知疾苦。”这些故旧老友口才了得,而且是众口一词,“皆奏”是也。四海升平,百姓欢乐,这都是陛下您的功劳。我们能在有生之年欣逢盛世,真是无比珍惜这样的好日子。都想沐浴在您的阳光雨露下幸福生活,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疾苦。这一番话,不无奉承吹捧之嫌,但贞观盛世,天下太平,也不尽是虚言。大家这样说着,顺势坚请皇上回并州看看。太宗这时颇为感慨地说了一段话:“飞鸟过故乡,犹踯躅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岱礼若毕,或冀与公等相见。”于是赐给他们物品不等。可是事与愿违,刚刚过了一个月,就有星孛现于太微,冲犯郎位,因此皇帝只好取消到泰山封禅的计划,为此,他避开正殿反省过失,并且命令尚食减少膳食。这段故事,在《旧唐书·本纪三·太宗李世民》中有详细生动的记载。有的文章说,泰山封禅,乃魏征等人极力谏阻,故而取消,而且诸多网络文章也大多采用此说。经本人查阅新、旧唐书,魏征谏阻一说应属讹传。所以,网络上的东西可作参考,但不能为据。
3年后,机会终于又来了。
唐太宗贞观年间,高丽进攻大唐属国新罗,新罗王向中央告急。唐命高丽停战,遭到拒绝。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太宗决定东征高丽,令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任辽东道行军总管,从柳城(今辽宁锦州)出征。令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水军从莱州(今烟台莱州市)出发。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水陆并举,向平壤进发,征伐高丽。
3个月后,也就是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太宗决定御驾亲征,亲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三月到定州,四月誓师幽州,大飨六军,浩浩荡荡东进。四月,李勣攻打盖牟城(沈阳石台子山城),破之。五月,渡过辽水,皇帝亲率铁骑与李勣会围辽东城,战事十分惨烈,唐军借着劲风发射火弩,顷刻间,城中的房屋和城楼在一片汪洋火海之中化为灰烬,乃拔之。六月,师至安市城(营口),高丽将领高延寿率兵十五万人前来救援,以拒王师,被官军打得大败,死伤和俘虏不可胜记。高延寿等带着部下投降。因此皇上命名所临幸的这座山为驻跸山,并刻石以记功。
不过,攻打安市城似乎不太顺利,旧唐书载,“秋七月,李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冬十月,到达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注意,《旧唐书》选择了“班师”一词,其意为调回在外打仗的军队,也指出征军队胜利归来。关于安市城战事,史书可能另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说攻打安市城不顺利,没有攻克,但绝不是打了败仗。“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只是因气候不利而班师。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据说,唐军总共损失接近2000人,战马死了8000匹,唐军打下高句丽10座城,迁7万人入中国,还斩首4万多级,唐军还缴获大量马、牛、装备、物资。唐军多次大胜,其中单是在安市城外击败高延寿、高惠真的那次胜利,唐军不仅消灭了15万高丽军,还缴获马5万匹,牛5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其他大量装备。可以说,此战令高丽元气大伤。公元666年,唐将李勣攻占平壤,“裂其诸城,并为州县。”关于这次御驾亲征,也有文章讲到,好像李世民打了败仗,“不得不班师回朝”,回朝途中“再渡泥潦”,将士“死亡枕藉”,然后唐太宗“三十年未遭此惨局”,因而“气急患痈”。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未找到这些词语的出处,在新、旧唐书中都未見到这些记载。我在史书看到的记载只是,唐太宗“班师”。自然,征战近一年,可能疲惫是有的。
这次是真正的机会。返途中,于贞观十九年腊月,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幸临并州。故地重游,太宗可以好好休养一下身心了。正是年根岁尾,春节将近,唐太宗李世民回到了阔别28年之久的太原。此时,李世民也即将迎来他48岁的生日。48岁,按说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华。可是,未曾想,3年后,李世民就驾崩西去。据载,这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自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之后,李世民唯一一次回到龙兴之地太原。
回到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又值辞旧迎新之际,唐太宗李世民自然是倍觉亲切,感慨万千。《旧唐书》载:李世民在太原“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皇恩浩荡,回到发基之地,没有一点阳光雨露,肯定是不好意思。于是,特赦并州囚犯,设宴随从官员和在太原起义时有关随从的人员,并赏赐粟帛若干,颁布免除徭役命令,当年起义时户籍在编的百姓,免除徭役三年,后来附入户籍的免除徭役一年。《新唐书》记载:“曲赦并州,宴从官及起义元从,赐粟帛、给复有差。”可是,本文重点叙述的唐碑,在新旧唐书中均无半字记载,至少有一句“上御制御书《晋祠之铭并序》”也是应该的。史书就是史书,它就是这么任性,就这么惜墨如金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它有时确实过于简单,过于干瘪,了无趣味。好在,有结结实实的碑石竖在那里。这就是碑石的功劳,它屹立于史书之外,补充和还原着历史的生动与鲜活。还有,此事在北宋著名的四大部书之一的《册府元龟》中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今在祠中。”
这才似乎说到正题:唐碑
贞观二十年正月,晋阳城里,家家贴春联,户户放爆竹,年味十足。唐太宗李世民回到太原,首先有一件大事要做,那就是到唐叔虞祠还愿。当年,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之际,曾在晋祠唐叔虞祠祭拜盟誓,第二年攻取长安,平定中原,成就帝王之业。这个迟到的愿,直到28年后才来还。李世民带领群臣在唐叔虞肃穆庄严的塑像前,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祭拜仪式。此时此刻,在氤氲的香火之中,他的思绪也一定是随着这袅袅的烟云,蒸腾弥漫,缕缕不绝。往事如烟,往事也许并不如烟。28年,弹指一挥间,但想说的话却很多很多。于是,怀着感恩晋祠、感恩晋水、感恩唐叔虞的心情,欣然“树碑制文、亲书之石”,写下了这篇千古流传的文字:《晋祠之铭并序》。碑额上标明的时间是:“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晋祠之铭并序》全文共1203个字,分为序和铭两部分。序为骈文体,铭为四言句。它既是治国安邦的政论文,又是文采飞扬的散文(骈文),更是墨浓笔精的行书法帖。是一篇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辞藻华美、政论与抒情相结合的绝妙佳文,是一通集史学、文学、政治、书法为一体的丰碑,是一部研究、探讨盛唐时期政治、文化、文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珍贵的“石史”。从唐碑中,尽显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超凡的文学艺术才华以及书法家的风采,显示了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书法家。
唐太宗在这篇文章中,十多次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到“德”字。作者在强调什么,当然是强调德政的极端重要性。我个人觉得,德,是贯穿《晋祠之铭并序》全文的一条闪亮的红线,是此篇华丽文字中直击心灵的主题乐章,是恣意汪洋、铺排渲染背后的精神内核。
“夫兴邦建国,资懿亲以作辅;分圭锡社,实茂德之攸居”,序文首句,提纲挈领,开宗明义,阐明了“德”在兴邦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德政之核心地位。
“德乃民宗,望为国范”,唐叔虞正是品德高尚的榜样,他治理唐国“经仁纬义,履顺居贞”。他品德高尚,如一轮明月,光芒普照;他的胸襟度量,像浩瀚的大海,包容万类,润泽四方。他高洁的品德和德治受到百姓的崇敬和敬仰,他的崇高聲望和政绩也成为国家的表率和榜样。唐叔虞以德治国,励精图治,开创了晋国兴盛七百余年之洪基伟业,以至于后来成就晋国之霸业。千百年来,唐国古风,晋国遗烈,就在这块土地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基因中滋长、延续,续写着不朽的传奇。
唐叔虞是神灵,为这片美丽而肥沃的古唐晋地降临福祉;唐叔虞更是品德高尚的化身,他仁义治国的美好政声与优良传统光耀四方、润泽后世。在这里,李世民是在借神灵之名强调德政之实。诗经说,“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即施德于国,才可以使国家安宁,长治久安。唐叔虞的德明之光照亮了晋国的繁荣兴旺,更照亮了大唐的贞观盛世。
晋祠乃唐叔虞神居之处,李世民以饱满热烈之激情,华丽明亮之词汇,对晋祠的建筑之美、泉水之美、山川之美、草木之美、四季之美极尽铺陈渲染,并对晋祠施惠、至仁、刚节、大量之美德推崇备至,极尽赞美。“众美攸归,明祗是宅”,晋祠,不仅景色绝美,最厉害的是,还具有那么多美好的品德。天下名胜无数,谁听说过这些名胜还有美德?唯有晋祠,它景色美,品德更美,连神仙都羡慕不已,以此为家。悬瓮山“灵岳标奇”,因有灵性而更加雄奇不凡;日夜奔流不息的晋祠难老泉,“滋泉表异”,从而愈加与众不同,品行高贵。这正是:山水同日月共辉,神灵与美德同在。晋祠的山,晋祠的水,晋祠如诗如画的美景,晋祠高尚完美的品德,都令人赞叹。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唐叔虞———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伟岸身躯,他深沉而锐利的目光。此时此刻,李世民“仰神居之肃清,想徽音其如在”,怎能不感慨万千,心潮汹涌。
“惟贤是辅,非黍稷之为馨;唯德是依,岂筐篚之为惠?”感恩也好,祭祀也罢,不需要丰盛的祭品,而应是精神的继承,是德贤的修养。只有把唐叔虞以德治国的传统光大弘扬,让大唐王朝千秋万代、江山永固,才是目的所在。
唐太宗“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他要“竭丽水之金,勒芳猷于不朽;尽荆山之玉,镌美德于无穷。……俾洪威振于六幽,令誉光于千载”。
御制御书,刻碑勒石。千辛万苦,用心良苦。
“日月有穷,英声不匮。天地可极,神威靡坠。万代千龄,芳猷永嗣。”
品读唐碑,无数后人可否会有稍许启迪乎?
“南有兰亭序,北有晋祠铭”以及我眼中的唐碑书法
唐碑,其实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妙曼飞舞的书法,一种巨大的气场瞬间笼罩全身。从这些灵动的线条中,让人看到生命的张扬,血脉的流动,思绪的飘舞,旋律的跌宕。书法的力量,书法的魅力,就在这不知不觉之间,让你肃然起敬,让你深切地体会到文字的神圣。唐碑,其实,实乃唐太宗书法的一座丰碑,也因此奠定了唐太宗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世人素有“南有兰亭序,北有晋祠铭”之美誉,把其书法与天下第一行书相提并论,这是极高的评价,专业性的定位。《兰亭序》今天也只能看到摹本与临本,而真迹早已随葬昭陵,难见踪迹。而唐碑开创了我国行书止碑之先河,至今依然屹立在太原晋祠的“贞观宝翰”亭中,供后人观摩瞻仰,这就更加弥足珍贵。
细观唐碑之书法,飘飘洒洒,典雅清秀,疏朗健拔,气度非凡,可谓尽得王羲之之真传。众所周知,李世民极度推崇王羲之,据说其内府收集王羲之法帖居然有三千六百纸之多。其中,有一个“李世民计赚《兰亭序》”的传说,生动而风趣地描绘了藏于民间几百年的神品《兰亭序》再现世间、收入皇府的过程。李世民死后将《兰亭序》陪葬昭陵,以至后世陆游发出“蚕茧藏昭陵,千载不复见”的浩叹。可见,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李世民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喜爱来表达,而是真正发自骨子里的爱,深爱,酷爱,以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李世民的书法完全是王羲之的路子。清人王佑作诗评价李世民的书法:“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洲,虞褚欧柳俱拜倒。”
个人认为,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字已不是皇帝字,更不是江湖字,而是专业水准极高的书法艺术。可以想见,李世民虽在庙堂之高,日理万机,但在闲暇之时,对王羲之的法帖何止千遍万遍地欣赏、把玩、临摹。王羲之说,书法是玄妙之技,非通人达士,不可为也。同时,也不可否认,书法艺术也是动手能力极强的艺术,没有长时间的笔墨浸淫,心摹手追,不可能达到掌控自如且如此形神兼备的程度。历代善书的皇帝之中,李世民当之无愧居之榜首。自称“天下一人”的宋徽宗,其瘦金体虽自成一体,但我个人认为,不可与李世民之书法同日而语。康乾二帝,其圆润方正的皇家榜书,窃以为与李世民的书法也相去甚远。
以我观之,李世民唐碑的书法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性。一是典雅舒朗,结体端庄,气象雍容。其书法尽显王羲之之风骨和气韵,有御临天下之自信,有外圆内方之人生哲思,亦有笔墨运用控制之自如。二是法度严整,骨格雄奇,笔力遒劲。唐太宗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认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靠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把王羲之推崇于至高无上之地位,唐碑完全是堂堂皇皇的王羲之的风貌与法度。唐太宗在《论书》中还颇有体会地讲道,“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并在书法实践中总结出“虚拳直腕,指实掌虚”的理论。这些行家之语,绝非初学浅尝者可以道出,一定是长期修炼揣摩之后的有感而发。而且,李世民的这些书论在唐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三是飞逸洒脱,流畅自然,从容自如。唐碑洋洋洒洒千余字,字大如桃。从书法角度讲可谓鸿篇大作,书写应有相当难度。但整个碑文看起来高山流水,生动自然,堪称完美。碑文以行书为主,时有灵动之草书夹杂其间,使整个画面愈显生动。碑文中的39个“之”字,如兰亭然,书写风格各有不同,变化多姿。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书法功力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结体、笔法、线条、墨色、章法、韵味,随心所欲又尽得其妙,信笔由缰而尽在法度之中。
唐初之书法,已经形成严整瘦硬的唐楷体系。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是深得李世民赏识器重的大臣和名扬天下的书法大家。纵观四人書法,俨然已经奠定唐楷大厦之基石。中唐至颜真卿,书风为之一变,由瘦硬而为雄浑。到晚唐,柳公权又为之一变,将瘦硬与雄浑融合变通,成为一家。至此唐楷完美收官,彪炳史册。唐楷虽然都属“二王”一脉,但细论之,其楷书工整有余而韵味有所欠缺,这就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说“唐书尚工”,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到了宋的“苏黄米蔡”,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赞许的目光掠过繁华的盛唐,直接投射到更为久远的魏晋,去追寻书法的情趣与韵味,从而形成与唐相去甚远的书法风貌。这就是“宋书尚意”。话似乎有点扯远了,其实尚在题中。反观唐太宗之书法,还真没有丝毫唐楷之习气,完全是正宗的王羲之的味道。而且当年他千方百计地得到《兰亭序》,如获至宝,让身边的诸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一干大臣和书法大家们好好临摹。可惜的是,这些大臣和书法大家们却并未真正领会王羲之之真谛,或者说在传承和弘扬《兰亭序》这种代表魏晋风韵的书法精神方面,他们并没有比他们的皇帝做得更好。
不过,客观讲,与唐太宗极端推崇的老师王羲之相比,其书法还是稍有逊色,青出于蓝而未必都能胜于蓝。个人认为,王羲之的冷峻与硬朗,险拔与力道,在唐碑的墨迹中表现得还不够多。虽说“南有兰亭序,北有晋祠铭”,但唐碑之字与兰亭相似度并不大,与唐怀仁和尚用25年时间集字的《圣教序》可能更为接近。怀仁和尚千辛万苦地把《圣教序》完成之时,唐太宗已经驾崩24年了。但《圣教序》之字,大多是从内府所藏的王羲之墨迹中选用,曾是唐太宗在世时反复观赏临摹之法帖,所以,其字更接近《圣教序》,亦在情理之中。清人齐羽中评论:“其书气象涵盖,骨格雄奇,盖俨然开创规模也。其书结字用笔,颇似怀仁圣教序”(《三晋见闻录》)。唐太宗本人对此碑应是相当得意的,否则他也不会将《晋祠铭》拓片作为国宝赠送外国宾客。
回过头来,再说说晋祠之美
晋祠之美,似乎还没有说够。
在唐太宗眼中,晋祠的一花一木都是那么美,晋祠的一砖一瓦都是那么亲切。悬瓮山是神山,晋水是神水,晋祠是仙境。
“金阙九层,鄙蓬莱之已陋;玉楼千仞,耻昆阆之非奇。”晋祠的宫殿、晋祠的庙宇,如九天金阙辉煌壮丽,光彩照人,即使蓬莱胜境、昆仑阆苑,都粗鄙平淡,黯然失色,不值一提。想象一下,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晋祠已美到极致。
“悬崖百丈,蔽日亏红;绝岭万寻,横天耸翠。霞无机而散锦,峰非水而开莲。石镜流辉,孤岩宵朗;松萝曳影,重溪昼昏。碧雾紫烟,郁古今之色;玄霜绛雪,皎冬夏之光。”个人极欣赏“碧雾紫烟,玄霜绛雪”八个字。绿色的雾,紫色的烟,黑色的霜,红色的雪,顿时把我们带入一个奇异无比的梦幻世界。晋祠古今之色,冬夏之光,尽在其中。晋祠真的很美,可用这么神奇的笔触,凝练而传神地把晋祠的美写到这种极致,非常人可及。莫非唐叔虞给了唐太宗灵感,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神来之笔。
“其施惠也,则和风溽露是生,油云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则霓裳鹤盖息焉,飞禽走兽依焉。其刚节也,则治乱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万物而不倦,资四方而靡穷。”
它施惠于百姓,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则苗勃然兴之;它仁义高洁,天上飘飘飞舞的神仙都来这里憩息,飞禽走兽也归依到这里;它刚强坚定的意志和节操,无论天下大治还是大乱都不可改变它的崇高形象,无论寒冬腊月还是暑热蒸腾都不能动摇它的操守;它的胸怀大量,化育万物而从不知厌倦,扶助四方苍生而永无穷尽。晋祠,它乐善好施,仁义为怀,刚正不阿,胸襟宽广,天下的美德都集于它一身,是一个宽厚、善良、仁慈、坚强、执着、亲切的长者。他布云施雨、哺育万物、造福生灵,恩惠天下,是受人们爱戴崇敬的高尚完美的圣人。的确,晋祠已经不是晋祠,晋祠就是圣人。
“加以飞泉涌砌,激石分湍。萦氛雾而终清,有英俊之贞操;住方圆以成像,体圣贤之屈伸。日注不穷,类芳猷之无绝;年倾不溢,同上德之诫盈。阴涧怀冰,春留冬镜;阳岩引溜,冬结春苔。非疏勒之可方,岂瀑布之能拟。”晋祠泉水清澈飞涌,那是因为此水有俊逸超群、始终如一的贞操;水虽无形,流动的泉水分流入方、圆之池沼,体现了圣贤之人那种能屈能伸的高尚品格;日注不穷,犹如美妙的道行绵绵不绝;泉水长流不衰,却从不满溢于水渠之外,这就如同有高尚品德之人,告诫人们不能狂傲自满。
“故以众美攸归,明祗是宅。岂如罗浮之岛,拔岭南迁;舞阳之山,移基北转,以夫挺秀之质,而无居当之资。故知灵岳标奇,托神威而为固。”万德之美,皆从于已。这就是晋祠,它景色美,它品德高尚,它化育万物,谦逊低调,胸襟宽广,坚守如一。这样的美,天下无敌。
晋祠,是唐叔虞的神灵赋予了它非凡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品德。晋祠,其实正是唐叔虞的化身吧。
研读唐碑,让我对晋祠更加肃然起敬,对生我养我的三晋大地愈加崇拜景仰,对唐国晋地所孕育的深厚浓烈的唐风晋韵愈加如醉如痴。
“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后人览之,亦当共勉。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