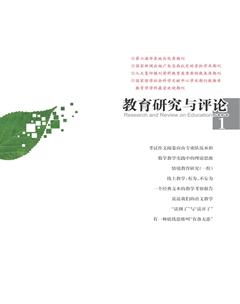境脉、社会与适应性存在
摘要:情境应该是一种由理解来定义、选择和建构的境脉,而且是一种适应性的存在。一切情境,除了让人置身其中,还有赖于人的存在、理解与创构。在教育之中,只有当情境作为人的适应性的存在时,它才真正存在。今天,教育的情境应有三种路向:从情境走向境脉,从师生走向社会,从适合走向适应。情境教育发展到今天,情境必然要从适合儿童走向适应儿童,适应儿童所在的境脉与社会;同时,儿童需要从事的是适应性学习,而不是用过去的方式和内容来培育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情境教育 情境 境脉 社会 适应性存在
【写在前面】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谈论情境教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李吉林情境教育。李吉林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探索、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情境教育②。遗憾的是,李吉林提出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情境课程与情境学习几十年来,理论界、实践界的关注者与研究者,大多拘囿于对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研究的研究。由于李吉林把重心放在了什么、何以和怎样才是“更好的情境教育”上,其他人往往也随之凝注于此。以至于直到今天,连何谓情境教育,都没有建立一个精确的并被普遍认同的定义,更不要说对情境、情境教学、情境课程等语词本身的自我理解与诠释了。事实上,无论情境教育,抑或是李吉林情境教育,都不应该以李吉林视界为限,到李吉林履痕为止。对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研究的研究,以及从自身出发,而非局限于李吉林立场与视角的情境教育研究,理应成为我们继续展开情境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两个必要选项。
如果把情境教育看作是完美的,那么,情境教育一定是残缺的;当我们把情境教育看作是进行中的和待完成的,情境教育却因此拥有了通向完美的可能。李吉林40多年探索情境教育的感同身受、亲力亲为,以矩阵般的叙事、论述及阐发,汇成了数十种皇皇大著,形成了事实和价值双重意义上的教育“富矿”,也基本构成了一个实践性理论的“闭环”。“富矿”值得更深的挖掘和更好的提炼,“闭环”有待更新的打开和更广的拓展,李吉林通过情境教育的探索与建构,打开了儿童教育的崭新空间,而不只是提供了儿童教育实践与研究的若干成果。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从儿童出发,从教师出发,从自身实际、需求与研究出发,每一次披荊斩棘的前行,都可能是情境教育的新路。正如李吉林乐为“长大的儿童”①,聚焦“大写的儿童”②那样,情境教育追求的是“儿童飞得更高、更远,且能飞、能呜”,唱响儿童喜欢、向往的“云雀之歌”③。而每一个儿童都有自己的方向,每一只云雀都有独特的歌唱。
由此观之,情境教育不是某一种教育的定式,而是在拓展“每一个人”的存在与表现,启发着理解的境脉、可能的生活与身体的转向。作为新的情境教育学的源泉,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研究、实践乃至整个生活,展现出了巨大的实证性和丰富性。
情境教育的核心是“情境”。李吉林指出,“‘隋境教育之‘情境是‘有情之境,是‘活动之境,是一个有情有趣的网络式的师生之间的广阔空间。它将教育、教学内容镶嵌在一个多姿多彩的大背景中。这是促使儿童能动地活动于其中的环境”④。然而,这里的“情”是谁的情,“境”又是谁的境呢?在情境教育的体系设计中,情境是创造出来的,是“根据教育目标”“人为优化的”⑤。显然,在这里,情境的创造者与优化者,首先和主要的是怀有“教育目标”的教师,而非儿童。这也意味着,此情未必是儿童之情,需要经过注入、迁移和转化,才有可能成为儿童的内在,却并不必然成为儿童的内在。至此,教育的情境未必是儿童的情境。
从境脉学习理论的角度,情境教育的情境,起码对于儿童而言是不完整的。虽然李吉林的视野没有被“情境”限定,她强调拓展“教育的空间”“儿童活动的生活空间”,使之“宽阔”“开放”“适宜他们成长”⑥,尤其是,“一切境界无不为我、为儿童所设”⑦,但问题也正在这里:情境教育追求“充分利用环境、控制环境,最终使儿童生活的各个区域以统一的目标求得和谐”⑧,这种万人同情、天下一统的传统意蕴,这种对儿童及其生活区域的系统控制,难免带有诱使甚至强迫的色彩,形成了显在与隐性的多重压迫,并可能导致儿童思想向度的偏狭。对此,李吉林时有自警,始终坚持主张儿童的“主体意识”“主动发展”,但来自学校(教师)、环境、社会的体制性力量汹涌澎湃,教育很难一直自觉地作为引领和可能,相反,稍不留意就化作隐性的压迫与暴力,造成教育“发出者”和执行者无意之中的“人为恶化”。
教育的情境,当然要从教育目标出发,也需要“人为优化”。但是,儿童的认知、交往、成长绝不限于被“优化”的情境,“情境”应该作为一种源泉与启迪,让儿童走向境脉,走向生活,走向他所在和可能的全部情境,进行自主的选择与导向、自我的理解与创构。在笔者看来,情境应该是一种由理解来定义、选择和建构的境脉,而且是一种适应性的存在。一切情境,除了让人置身其中,还有赖于人的存在、理解与创构。在教育之中,只有当情境作为人的适应性的存在时,它才真正存在。
一、从情境走向境脉
对于“情境”,《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情景,境地;《韦伯斯特词典》解释为:与某一事件相关的整个情景、背景或环境;《教育大辞典》则将情境作为象征互动论,是分析人际互动过程时使用的概念。这三种解释,都指涉人的情感、处境与“人情境”的关系。进一步细分,又有人与人、人与情、人与境、情与情、情与境、境与境等多种关系及其交叉与叠加。但再往深处看,情境又是混沌的、多样的、易变的,它没有那么多指标和道理要讲。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确的规定性和指向性,教育的情境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明示、固化的样态。
在中国,最早提出“情境”一词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他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李吉林情境教育的共同研究者李庆明注意到“情境”与“意境”的区别,却又说“情境”与“意境”基本同义①。李吉林则一再强调情境教学受到外语情景教学、中国古典文论“意境说”的影响②,这就难免让人诧异:情境教育的“意境”源头与“情境”本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李吉林在情境教育立论时是否曾有过“意境教育”的选项?在她心中,“意境”是否基本等于“情境”?
然而,意境与情境终究不同。情,有感情、情面、爱情、情欲、情形(情况)、情理(道理)等义项;意,则有意思、愿望、料想、事物流露的情态等义。有情大抵有意,有意却未必有情。“情境”与“意境”的可能混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表明,情境教育有时关切的并不一定是情,而是客体、客观?
情境“促使儿童能动地活动于其中”,那么,在情境中,儿童是作为主体,还是作为客体?儿童的能动是主体的能动,还是客体的能动?在中小学的教育实践中,将情境作为一种客体,将儿童作为另一种客体,并不鲜见。笔者曾经提出“客观能动性”:“客观能动性,也即客体的能动性。这种客体的能动性,是就客体对客体的关系而言。”将儿童视为有待优化的“物”,视为“人的实践的延伸,或者人的实践的衍生物,又或是人的意识(认识)的对应物”。③这样的倾向与做法,至今仍在中小学教育界普遍存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深刻反省和彻底改正。
谈及情境,李吉林激情洋溢:“这种根据教育目标优化的环境,这种充满美感与智慧的环境氛围,与儿童对知识、对审美、对情感的要求是相吻合的。进入这样的情境,儿童的情感、心理必然会发生共鸣而契合,促使儿童在现实环境与活动的交互作用的统一和谐中,获得全面发展。这种人为优化的情境,促使主体的能动活动与现实环境优化的统一,激发儿童潜能与培养塑造的统一,最终达到素质的全面提高与个性充分发展的统一。”④相对于前述对环境的“控制”,这段论说表现出了较大的弹性,较多地关注“现实环境与活动的交互作用”,却仍是在凸显“好的情境教育”的育人价值,并不足以证明一般性的教育情境“与儿童对知识、对审美、对情感的要求是相吻合的”。须知,每一个儿童都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任何一种教育范式,都不可能与所有儿童的不同要求切合。
情境是对环境的人化和人为优化,问题在于,谁来优化?谁为谁优化?谁为谁进行谁需要、认可和喜欢的优化?如果预期的受体不需要、不认可、不喜欢,教育应该怎么办,又可以怎么办?如果“人为优化的环境”并非人人认为优化的环境(事实往往如此),这个“环境”由谁来进一步优化?又以怎样的预期与标准来优化?进而,优化者和被动接受优化者如果在對待“人为优化的环境”时产生了异议、矛盾甚至冲突,两者何以自处、何以待人?
情境“根据教育目标优化”,是对教育宗旨的秉持、对教育任务的重视、对教育对象的改造,也是情境教育的自我修炼、自我设限与自我建构。情境是将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简化后的精神/物质存在,是静态的、固定的、现实的和美化的;这也意味着情境往往是虚拟的、代人的、即时的和预构的。
与情境不同,境脉隐含着学习的真正意义、生活的事实理解、存在的价值诠释,因此,更是动态的、变化的、现实而又淡泊的和素净的,从而意味着境脉通常是真实的、实在的、连续的和生活化的,同时又是想象的、心理的、理解的。
境脉是自然的境域,还是生命的脉络,兼具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性,这就为学习、认知和成长提供了普适、泛在的交互性。相对于情境的规定性、指向性而言,境脉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与不可测性。如果说情境是由教师来发动对知识意义的认知与理解,那么境脉就是在期待儿童主动去展开系统性的学习,不仅从外源性知识系统,也从自身的认知结构,进行关联的、具身的学习,丰富、壮大和延展境脉。
从情境教育的角度来看,境脉就是一连串隐在和动态的情境,是立体的、网络的、绵延的、多元化的情境。在境脉中,每个人总是在本能地寻找、选择和构建情境,这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规划与调控,学习成为主体的需要和主动的行为,人(儿童)因此表现出兼为人和学习者、存在者和发展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境脉又在持续地消解不断出现的情境,这些情形源自人(儿童)对新信息、新知识、新意义和新处境的理解,“教师教”的情境终究会让位于“学生(自我决定是否、怎样)学”的境脉。
从根本上说,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师生权力逐步转移,儿童身份日益明确,情境的意义将逐渐退隐,而境脉的意义自然凸显。随着儿童的长大,教育情境的创设必将让位于真实问题的提出,教育问题与生存/发展问题日益增强的一致性,让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情境沦为人的境脉之中闪过的某种桥段。
情境是境脉定向的选择性再构,境脉是情境开放的交互性召唤。从情境转向境脉,是学习认知的应然路向,也是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
出于一种智慧的应对,李吉林提出了“儿童知识社会”的架构,将情境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致力于拓展儿童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向家庭、社会延伸开去①。这是教育情境的知止②,也是情境教育的转型。从此开始,情境不再是教师的创构,也不再是限制性的师生二元创构,而是儿童理解的自由漫步,走向生命曾在、正在和将在的境脉,走向儿童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经验与无数可能的主体性再构。
二、从师生走向社会
观察情境教育展示活动中呈现的许多精彩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师生、情境与教学任务相得益彰。教师带领学生穿行在一个个精心创设的情境中,学习知识,培养能力,表达丰富感受,仿若行云流水,又如飞鸟入林,令人叹为观止。
但这一切美妙的情境,就其完整和美好程度而言,仅限于公开演示的时刻。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对于类似的任务,绝大多数教师都不具备独力的完全胜任的愿景、能力和资源。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其人力、物力与技术资源,也不足以支撑每一个教师个体对每一处教育情境的完美创造,而是需要教师个体自行解决问题或协调资源同创共享。
况且,即使这些美妙的情境能够普遍、充分地展开,它们对儿童将来要走进的社会而言,也只是某种可有可无的乌托邦,一些略有情调的教育戏剧。比起波澜壮阔、情节奇异的社会大戏,甚至关于衣食住行的生活小品,教育的情境也只是成长旅程中的旧日记忆。
教育学者高文指出,理解情境有三个“置身于”:“一是学习者所置身于的物质、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二是知识被产生和创造出来时所置身于的情境;三是知识所置身于的整个知识体系,也就是知识在知识结构中的位置及其脉络。”③
物质化、关系化的社会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情境,是非常必要的;社会还是知识被产生和创造出来时所置身于的情境之一,而且一般都是最为关键的情境;同时,社会至少有相当多和相当重要的部分,是知识应在的位置及其脉络,或者说,社会直接对应着知识所置身的那个知识体系,相互作为对价和交换。
编辑家夏征农认为,“情境是指一个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人们社会行为产生的具体条件”①。如果换一个方向,让社会环境作为教育情境和情境的创构者,就相当于将社会作为教育的源头,产生、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场域,催生一个人本应通过教育培养和成就的社会行为。
教师是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教学者,但“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不能保证他就能教会别人学习。事实上,专业知识有时对教学是有害的,因为许多专家忘却了学生学习的难易”②。知识爆炸、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要求学习跨界进行,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能仅对相应块面的认知有用,这种勉为其难的认知往往显得浅显而低效。实际上,师生置身其中的境脉也许更能影响甚至决定教与学的成败,比如背景知识、周边信息,又如信息技术、在线教学,再如社会心理、经济生活,这些看似缺少充分必要性的识知需求,都有可能成为教育教学的短板,或高效学习的阶梯。这还只是技术方面的分野,在更为广大的领域,教师的境脉与学生的境脉往往阴差阳错,动如参商。因此,让社会而不是教师作为教育情境更重要的创构者,可能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
在英汉词典中,“境脉(conlext)”的语义是指“上下文”,或指“人或事存在于其中的各种有关情况”、来龙去脉、背景、情境等,任何事物都可以理解为一种与其当前和历史境脉不可分割的正在进行的行为。③经由对上下、来去、内外的追索,境脉甚至可以延展到事物的全部情境及其整体。这时,我们可以发现,是“上下文”成就了情境,而不只是情境照亮了“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包括处于其中的情境,由社会和(人置身于和观察着的)自然来充当,也许更为恰切。
李吉林情境学习作为“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的范式”,“其内容概括为: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④我们需要厘清,情境是教师基于选择的构建,由此,情境才有可能变得“美”、干净而有力。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我们在选择得到的同时,还意味着失去了“得到之外”的一切。教育的情境所需要和能容纳的“美”是如此精致,以至于情境是完整的、值得珍视的,而境脉却是残损的、受到忽略的。
这就使得教师创设的情境往往容易变成单向度的空间,失去了“上下文”的语境和“上下游”的环境。学生被动或主动的参与,会让情境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但时间、空间与交往的有限性,仍然妨碍了情境进一步的开放与丰盈。单向度的思想令人更加浅薄而功利,教育的“发出者”、课程的编制者和教学的执行者系统地推进教育,创造情境,然而其理论、规划、制度与材料之中“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⑤。
但是,儿童一旦从教师为主的师生二元创构关系中挣脱,走向社会,会发现世界变得天宽地阔。一方面,师生一同置身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教师不再是学生心中的主要权威,二者关系由隐性的对立转向显在的同盟;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包含并可以容纳儿童求索事物的全部情境,包括儿童原有的記忆、经验、经历、本能反应和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自然构成的内部世界,以及按照他者秩序安排提供的学习内容、发展标准、所在环境,以及因这些潜在部署引来儿童反抗的外部世界。
李吉林指出,“社会是儿童知识建构不可替代的情境”,“为儿童对世界的感悟,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起着奠基的作用”,认为“这也是教材,而且是更为活生生的‘文本”。①这就让儿童对情境创构的参与达到了主导的程度,具有了相当的自由和自主权。儿童的学习的意义不再单方面由教师“给定”,而是在学习过程中建构和生成,通过儿童自身的学习现实,与周围世界中的学习要素的相遇、交互和表现,不断碰撞、联结、集聚、融合,以尝试、协商、互动的形式存在。
这时,既是儿童在认识周围世界,发展个体生命自身,包括所在的情境与境脉;也是周围世界在认识儿童,丰富世界本身,包括儿童所在、不在和可能存在的全部情境。
从师生创构走向儿童与社会同构,是情境教育的必然,也是情境生长的必然。情境一开始提供的,是生命特写、交互平台与一触即发的机会。走向社会,就通向了情境的无限创生,而人(儿童)“在社会世界中的认知和交往以及与社会世界的认知与交往”就置身于“正在进行中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中”,②个体与社会的真实的发展性交互关系,逐渐让社会成为个体的相关、密切甚至属己的存在。至少,在情境教育的发展意义上,或者说教育情境的生长意义上,人(儿童)与社会可以互洽地共在,甚至是同一性的“共同此在”。
三、从适合走向适应
在教育体系中,儿童为了更加安全、舒适和愉快(而不是为了更好地成长),而服从和依赖规训他们如何思考、表达和行事的班主任、科任教师、试卷、校长、警察和检票员,“社会必然性迫使人们把‘物(包括他们的身体、心灵和感情)同其功能等同起来”③。这样的思想惯性,让儿童在意义的认知和应用过程中“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呈现出“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④由此,教育及其情境就成了一种“技术的中介”,人和自然在其中“变成可以替换的组织对象”。⑤人通过学习成为更好的人,如果教育让人变成“可以替换的组织对象”,无论这种“物”或“工具”有多精妙、多强大,教与学都没有意义。
李吉林着力创设“趣、美、智的情境,实际上就是把知识还原到或者是镶嵌到产生知识的那个情境中”。她举例说,语文是再现作家创作时所经历的那个情境,“情境教育就是把学生带到那个特定的、优化的或完美的情境中去,因为,一切知识都是在情境中产生的”⑥。然而,“那个特定的、优化的或完美的情境”并不足以支持儿童持续、充分和自由的认知,“特定”带来了局促,“优化”产生了伪饰,“完美”导致了终结,让儿童语词(意义)的输入与输出,与他本身失去了生命性、生态性的联系。从语文认知的角度,李吉林的情境还原或知识植入并无不妥。不过,在这里,教育体现为儿童认知对“那个特定的、优化的或完美的情境”的适应,而不是情境对儿童认知的主动适应。在教育实践中,或许后者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推行。
哲学家赵汀阳指出:“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并且,每种生活都有各自的道理,因此,某条真理总是可选择的或可放弃的,一种真理如果不好就可以不要。”⑦认知是这样,情境也是这样。由于存在代沟,教师(成人)认为适合儿童的,其实往往并不适合儿童,或者说,儿童认为不适合。对于并无充分自觉性和足够自控力的儿童而言,学习有何意义、价值与必要,情境有多生动、精美与有趣,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认为不够好、不属己、不适切甚至仅仅是不想要的,“就可以不要”。
情境教育发展到今天,情境必然要从适合儿童走向适应儿童,适应儿童所在的境脉与社会,否则,其路向必将被儿童对认知的假性适合阻断。
如果今天和此后的教育情境,仍然被设定为某种“特定的、优化的或完美的情境”,并一成不变,就一定是“不适合”的,更是“不适应”(儿童发展与社会变化)的。一方面,我们认为适合儿童认知的,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想要和自身需要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进而表达的,“不只表达他们自身、他们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愿望,而且也表达不同于他们自身的某种东西”①。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伪圣”场景一许多儿童自觉地向老师、“三道杠”或其他各类权威、偶像靠拢,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表演和描述的并不是与他们年龄、经历、见识、格局相匹配的事情,而仿佛是从那个特定的場域灌注到他们身体里,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输出的。可怕的是,他们有时竟然真的做如是想、如是感。
没有一种活动不是情境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儿童的变化,教育的情境必须具有充分的儿童性,从着眼于学习,转向李吉林所说的“为儿童的学习”②,进而走向“儿童的自我学习”。儿童在情境中的自我学习,“重点是涵盖完整的人的全面充分的理解,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大量有关世界的事实性知识;它强调与世界的交互活动;强调主动行动者(agent)、活动和彼此相互构成的世界”③。换言之,儿童的自身、自我与自由,即境脉,即情境,即教育,即他们“想要的生活”。
情境必须从适合走向适应,还在于,儿童需要从事的是适应性学习,而不是用过去的方式和内容来培育现在与未来。毕竟,在一个充满复杂性、变革性、自我创造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世界上,谁能说清自己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谁又能预料自己将在不断嬗变的世界中真正需要和用到哪些知识与技能?教育学者王美认为,教师要着眼于明天,培养“适应性专长”,“通常表现为深度的概念性理解、在新情境中的适应性改变、学习新知乃至创建新知的倾向、元认知”。④
在笔者看来,“在新情境中的适应性改变”,应该成为情境教育的一种重要路向。一切情境都是在自我的理解中创造的,一切理解都是在与情境的交互中生产的,适应性改变包括境脉学习、相关认知、属己建构、意义协商、困境驱动,从而使教育的过程能够“把人类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美好事物的欲求转化成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个体内心之中对美好事物的生动欲求”,“给予个体美好事物的经历”。⑤情境因此成为一种适应性的存在,适应人(儿童)的实际与需求,适应儿童个体的境脉及其学习,适应知识在真实情境和社会场景中的认知与应用,在多个向度与可能之中适应以上一切适应领域的交互与协商。
情境作为一种适应性的存在,是人化的,也是属己的,具有主客观一体化的能动性一它是儿童本身,是儿童所在的境脉,是社会的场景与要求,是“自我在世界中的绽出”,是自我所在的自在世界。
情境要能在儿童“需要的时候积极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安静地回退到成人的世界之中,始终守住自己行动的边界”⑥。毕竟,教育不是儿童的独角戏,而是成人与儿童的共谋和协商,是儿童和“长大的儿童”的适应性交往和发展性生产。
(邢晔,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科员。南通大学情境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江苏省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李吉林情境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教育研究与评论》特约主编。)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以儿童学习为中心的中国情境教育范式的建构与国际比较研究”(编号:BHAl70132)、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三期重点课题“基于跨界融合的‘玩美童年综合活动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编号:2019JKl3-ZB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吴康宁.“李吉林情境教育探索”再理解[J].课程·教材·教法.2018(3):4。
①李吉林.我,长大的儿童[J].人民教育,2003(17):39。
②③李吉林.美的彼岸(诠释:情境课程的建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自序3。
④⑤李吉林.情境教育的诗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1, 191。
⑥⑧李吉林.云雀之歌(纪实:情境教育的拓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28 - 129,127。
⑦李吉林.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7(3):97。
①李庆明.儿童教育诗:李吉林与她的情境教育[M].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69。
②④李吉林.情境教育的涛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6-19,191。
③邢晔.作为客观的能动——课程的实践特性、客观能动性与底层逻辑[J].教育视界,2019(5):59-60。
①李吉林.情境教育:促进“儿童-知识-社会”的完美建构[J].全球教育展望,2003(4):39。
②提出“儿童-知识-社会”架构,是李吉林有关情境设计的主动止步。
③转引自:顾泠沅.儿童·情境·学习[C]//顾明远.李吉林和情境教育学派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127。
①王文静.中外情境教育的发展与比较[C]//顾明远.李吉林和情境教育学派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413。
②约翰.D.布兰思福特,等.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扩展版)[M].程可拉,孙亚玲,王旭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9。
③ J. Michael Spector,M.David Merrill, Jeroen vanMerrienboer.等.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M].任友群,焦建利,刘美凤,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6.
④李吉林.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7(3):98。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13。
①李吉林.情境教育:促进“儿童-知识-社会”的完美建构[J].全球教育展望,2003(4):39。
②J.莱夫.E.温格.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③④⑤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54.28,134。
⑥李吉林.云雀之歌(纪实:情境教育的拓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33。
⑦赵汀阳.知识,命运和幸福[J-哲学研究,2001(8):40。
①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54。
②李吉林.为儿童的学习——情境课程的实验与建构[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③J.莱夫,E.温格.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④王美.适应性专长与教师学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⑤⑥刘铁芳.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