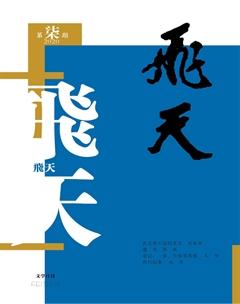风景、史诗与寻根的意义
杨毅
内容提要:叶舟的《敦煌本纪》以史诗般的长篇巨制为敦煌立传。叶舟“发明”了一座敦煌,也重新发现了敦煌的风景。《敦煌本纪》在认识论层面上颠倒了审美对象的认知过程,这源于“内面的人”面对崇高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也暗合了经济全球化以来对于“风景”的新的想象。再者,《敦煌本纪》延续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在史诗性的写作中塑造典型,歌颂英雄主义,将人物塑造寓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之中,开启了当代小说叙史的新路径。最后,《敦煌本纪》以文化寻根的姿态重新发现文学之根、民族之根和精神之根,延续了寻根文学的传统,但也因其处于新的社会思潮和时代语境之下,呈现出“后寻根”时代的文化想象与主体焦虑。但无论如何,《敦煌本纪》在全新的意义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的版图,作家叶舟的努力同样值得肯定。
从构思到写作,叶舟历时十六年完成的《敦煌本纪》以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为敦煌立传,回应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冲动”①,显示出作家非凡的勇气和文学抱负。小说出版后很快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并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叶舟尽管此前已有长篇小说写作的经验,但却近乎偏执地将《敦煌本纪》称作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与其说是小说本身在作家心目中的重要性,倒不如说是“敦煌”二字具备的某种“魔力”带给作家强烈的写作冲动,以致书写敦煌成了叶舟写作的宿命、人生的宿命。
近二十年来,尽管叶舟有多种题材的小说问世,但他的创作始终围绕“敦煌”展开。从诗文集《大敦煌》(2000年)到诗集《敦煌诗经》(2015年)和《丝绸之路》(2017年),再到短篇小说《蓝色的敦煌》(2017年)和最新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他用诗歌、散文、小说、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敦煌景观,如同莫高窟上的匠人不厌其烦而又妙笔生花地彩绘出石窟的壮美。不妨说,这是一个作家与其精神领地相互成全的故事。一方面,敦煌奠定乃至孕育了诗人兼小说家叶舟的精神资源和文学版图,成为作家写作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叶舟也在数十年间用文字供养敦煌,试图重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来自西部的精神价值,并由此开启他的寻根之旅。从这个意义上说,叶舟书写《敦煌本纪》就不仅是为敦煌树碑立传,更是为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的血脉和记忆。那里汇聚着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的古旧中国,却也氤氲着被世风打磨却初心不改的精良纯明的少年中国气。
敦煌:风景的发现
在中外文学史上,将某个实在或想象的地域作为作家构筑自己文学地标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鲜。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还有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皆是如此。作家们凭借经验与想象自由地书写它们的历史与现实,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王国,开拓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当然,这些伟大王国的建立也留给作家在叙事上的不小难题。作家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充分调动已有知识和想象,编织起令人信服的历史的形式,从而在讲述中建立期人与地域/世界的有效关联。在阅读这些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遇到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拼接成的故事也足够曲折动人;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遥远而纷至沓来的地貌、建筑、民俗,借此呈现出历史的在场感;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那些古老而灵异的仪式、神话和传说,经由它们窥见埋藏着的整个民族的秘史。然而,《敦煌本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敦煌视作亟待被发现的风景,在“风景”与“发现”的双重意义上熔铸敦煌本身。
这里所说的“风景的发现”,正是源于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论述。作为一种认识论装置,“风景”并不是自然山水风光本身,而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②。“风景的发现”作为日本现代文学发生的关键节点,还意味着有关审美主体、审美知觉的形态、构成和结构的错位乃至反转,是“把曾经不存在的东西变成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③。柄谷行人举了写实主义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通常认为,风景画或者写生乃是对自然的一种模仿,是“一种平板的写实主义”。然而在柄谷行人看来,“所谓‘描写是与单纯地描写外界有着某种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必须去发现这个‘外界本身”④。换言之,对于画家(也包括作家)而言,他们所要描写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外在于主体本身而存在,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却又亟待被发现的“风景”。这样一来,在审美主体新的视角下形成的审美对象作为“风景的发现”,就从根本上反转了审美主体的认识过程。柄谷行人总结道:“这并不是视觉问题。使知觉形态发生改变的这个颠倒并不在于‘内或‘外的颠倒,而是符号论式的认识装置的颠倒。”⑤
之所以将叶舟书写敦煌视作“风景的发现”,不仅源于小说对敦煌地理、文化所做的传记式的探寻与钩沉,更是因为敦煌从根本上颠倒了作家叶舟与其审美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叶舟坦言:“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唯有她,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⑥叶舟用文字供养敦煌,与其说他感悟到了敦煌之美,倒不如说他重新发现了内在的人。如同柄谷行人所说:“风景的被发现并非源自对外在对象的关心,反而是通过无视外在对象之内面的人而发现的。”⑦应该说,这种“认知装置的颠倒”和“内面的人的发现”发生在作家创作前的长期酝酿期,也植根于《敦煌本纪》这一作品的精神内涵之中。
如果说作家叶舟与审美对象在文本的外部建立起“风景”与“发现”之间的关系,那么《敦煌本纪》中歌颂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少年,则是在文本中发现了他们独特的“风景”。有趣的是,这种“风景”的发现同样“是对无视外界存在的内面优越地位的确立”⑧,这是因为小说将之归因为少年的精良纯明,而非外在环境的驱使。小说借李豆灯的视角写道:“这敦煌的土地上,竟然呼啦啦地冒出了这么一茬子人。如此英勇慷慨的一群俊朗少年,明晰地站在了自己面前,仿佛横空出世一般……此乃一股异己的势力、野生的呼啸,他们没有任何的服属,天不惧、地不怕,犹如一把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需要淬火、需要开刃,才可以一试风霜,有所报偿。”⑨此番预测可谓精彩而准确,这充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为河西走廊开路。深处西部边陲的沙州城及关外三县,因道路不通、消息闭塞而早已沦为无人问津的锈带。当梵义催问:“如何除锈?”梵同给出的答案是“开路,开一条生路”;“做当世护法,去开一条生路。”胡家坊的梵义、梵同带领众多快马游击,成立了日后叱咤于河西走廊一带的急递社,为的就是“替这一条长路、替整个河西走廊除了锈、灌足了生气,让它气血两旺、筋脉舒展”⑩。这群精良纯明的少年用脚开路,驰骋河西一带,凭借青春、热血和勇敢为锈迹斑斑的河西走廊打开了一条崭新的生路,更隐喻了为近代中國开辟一条崭新体制的道路;开路在敦煌乃至西部的意义自不待言。小说写了他们开路的壮志义举、写了他们在岁月与世道的磨砺中不断成长,也写了他们面对顽固势力的坚守和落寞。其二是为莫高窟和千佛灵岩存留佛经、文书和卷子。自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大量卷子和文书外流于世,这无疑给莫高窟和敦煌造成巨大伤害。正如梵同所说,“莫高窟丢了佛经、千佛灵岩丢了文书与卷子,这就等于整个敦煌丢了魂、抽掉了主心骨、丧失了精气神”{11}。在孔执臣的带领下,梵义等人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截留并仿造了大量文书和卷子,在伽蓝密室中为敦煌存留住一笔最为珍贵的财富。以梵义为代表的一群少年既有急递社开路的“明修栈道”,又有伽蓝密室藏经的“暗度陈仓”。精良纯明的少年践行着他们内心的正信,守护住敦煌的佛龛。同样,敦煌锈带也因这群少年的存在而显得熠熠生辉。
叶舟在《何谓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例》一文中描绘了河西走廊上“一群奔跑而壮美的少年”:“自秦至汉,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便拉开了帷幕。幸运的是,登上这个少年舞台的恰巧是一帮天纵之才,他们好奇、奔跑、血勇,孤独求败,渴望征服,每一块肌肉上都充满了力量与雄性荷尔蒙。他們一心想看遍世上的所有风景,想去追逐落日,去触摸地平线的尽头。那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旧约年代,没有废话、没有陈词,也没有羁绊。她碰巧遇上了南下的敌手,不免怒发冲冠,引刀一试。”{12}
无论叶舟如何赞美和歌颂少年英气,我们都不能忽略这种内面的人出现的根本原因:“简言之,这种内在的人是经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而产生的。”当然,“内在性并非反讽或逃避,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持续进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以‘想象世界来与现实世界对抗”{13}。叶舟在接受东方卫视采访时谈到《敦煌本纪》的隐喻:“随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经济活动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面临的是情义危机。我尤其强调的义是义气、义士、义举,这几个‘义,其实我们已经变得不认识这个词;我们也缺少去践约、去一诺千金、去慷慨执义。我们连这种本能都没有,我们连这种冲动都没有。”{14}这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为何高举“义”字大旗,写义庄的由来、繁盛和落魄。小说开篇即交代:索门六辈子爷孙,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有索门在,这敦煌就有了主心骨。”{15}然而,被誉为敦煌义人的索敞却没能守住祖上积累下来的荫德,反而很快因私欲卸掉了义庄的分量;索门也由盛转衰,从此渐渐败落。但是,“义”字本身却丝毫无损于它的存在,已然悄悄转移到河西司马梵义的身上。梵义秉承父亲的教诲,为兑现父辈的承诺,坚持要为索门开一座义窟……应该说,《敦煌本纪》所要彰显和呼唤的正是“义”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不只属于某个人或家族,而是敦煌数千年来孕育的正信,或者说是叶舟借敦煌发现的风景。只不过,恰恰因为它在今天已经被以利益为中心的交换原则所取代,才反而显得弥足珍贵。由此,《敦煌本纪》通过反讽建立起“新的风景”,并以去政治化的形式呈现。这也暗合了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对“风景”的想象。正如作家本人所言:
有人说小说家其实是一种“发明家”,如今回过头来看《敦煌本纪》就是我重新“发明”了一座敦煌。这部小说穿了那个年代的外衣,其实就是写的现代。所有的艺术都是指向现代的,都是指向此时此刻的。我借了历史的外衣,去表达我对敦煌的认知。{16}
按照康德著名的“美与崇高”的定义,《敦煌本纪》中的风景显然属于崇高的范畴。如果说自然之美要求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依据,那么崇高则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崇高来自不能引起快感的对象之中,而将此转化为快感的是主观能动性。”{17}小说中的风景已经超出了想象力的界限,而是要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发现其合目的性所获得的一种快感。小说没有过多描写西部的壮美,因为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部在小说中首先是作为锈带出现的。小说也没有刻意描写西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一切都显得如此自然。只不过,《敦煌本纪》激活了西部的历史传承、文化意蕴乃至民族精神——这些是长期缺席于当代文学的异质经验,也是小说所要传达的意蕴所在。
本纪:史传传统与史诗风格
本纪的体例为叶舟的才能和野心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的写作功底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体例中得到了较好的接纳。本纪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以来,历代修史者只用于记述帝王家世和丰功伟绩。《史记索隐》云:“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18}作家叶舟选择本纪的形式为敦煌立传,这本身就暗含了作家对自身及表现对象的认知。“唯有敦煌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一部本纪是历史精华的压缩、是时代光阴的自由穿梭,更是民族文化的追根溯源。本纪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储存方式,隐藏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秘史。
当然,本纪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归传统的努力。《敦煌本纪》承接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并开启了当代小说如何写史的新路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纪传体例,扭转了正史在宏大叙事方面对微观细节和个人经验的遮蔽,对此前编年体史书的不足做了有益的补充。班固的《汉书》沿袭《史记》的编排,将“本纪”简略为“纪”,但并未改变其内容和写法,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记事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唐代对于史传文学的发展,表现为正史修撰的繁荣有序和传记文学的发达,以及唐传奇的勃兴。后者突破了史传文学立足历史本身的特点而极富文学性的表达。宋元以降,正史、传记文学、历史演义等各种文体全面繁荣。明清小说虽然以文学性为主要特征,但也离不开史传文学的影响。《红楼梦》不仅有着丰厚的历史背景,还有着极强的人文底蕴,且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的肌理和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之中。小说中的时代影射、家族叙事都带有史传文学的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传统异常发达且连续不断,不仅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础,还深刻影响着叙事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当代,这个传统不再确定。当代一些文学作品里,人物并不重要,变得面目模糊,有些甚至成了符号。深入地描写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所受到的挤压,人物充满无措感,无奈、颓丧或抱怨,甚至扭曲变形,都有着貌似理所当然的借口,放弃为人的高贵感。这当然不单单是人物塑造的问题,我们对高贵不再确信,‘高贵这个词甚至包含了难以言说的嘲讽意味。”{19}——事实上,这同样适用于《敦煌本纪》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回归。
晚清以来,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文学文体的类型也在从统一走向分化。中国传统的文史合一逐渐让位于文史分立——历史以追求真实为己任,而文学越来越朝着虚构的方向发展。在文学的内部,叙事文学脱离了史传文学的传统而追求故事本身的讲法。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七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为达到既定的目的,必须在既定的要求之下生产既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种极具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彻底颠覆了宏大叙事——“村庄史”、“家族史”、“民间史”和“个人史”构成与“民族国家”相对的“小历史”,成为历史叙事的常见主题。现如今,经过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的涤荡,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已经演变为对于个体记忆的回溯与呈现。它们将历史看作极度晦暗不明之物而无法认知,只能依靠记忆拼接出无数支离破碎的片段。正是在这种后现代思潮占据历史叙事的哲学基础的前提下,《敦煌本纪》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回归就显得尤其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叶舟在《敦煌本纪》的写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材料,并获得了自如的伸展。叶舟为小说的写作查阅了大量的旧书、地方志、油印小册子等文史资料,还直接找到当地农民聊天;这些都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敦煌本纪》中,考证、引用、阐发比比皆是,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场景的设置和细节的处理都透露出作家扎实的功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敦煌本纪》都堪称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三大家族的兴衰、上百号人物的命运,再加上朝代体制间的更迭,共同熔铸于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之中。《敦煌本纪》从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写到1938年的近代中国,将人物置于动荡年代中去塑造,以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把恢宏的历史事件作为家族叙事和人物塑造的背景,将人物与故事融合成为有机整体,从而在内容与结构上实现其美学价值。
《敦煌本纪》截取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进行叙述,尽管跨越的时间不长,但却抓住了中国从古代君主体制向近代共和体制转型的关键期,以及国共双方对峙的三十年代。在此基础上,作家根据小说的结构、主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选取典型的背景材料勾勒出中国二十世纪前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敦煌本纪》卷十中,“普天共和”在少年们的欢呼声、炮仗的爆炸声和漫天飘散的传单中得到了宣布。小说借胡恩可元神的视角写道梵义的感受:“胡恩可的元神随风摇曳着,诧异地瞭见梵义呼吸急促、面色煞白,好像他手中攥着一桩恶讯似的。”“胡恩可骤然发现,梵义的表情一紧,尻子也坐不稳了。胡恩可差一点失笑了出来,因为他瞧见梵义吓尿了,尿在了裤裆里、尿在了马背上,湿漉漉一片。梵义自己也浑身悚然,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这改朝换代的一天所降赐的礼物,慌忙扔掉了传单,埋下了身子,生怕被别的少年讥笑。”{20}从叶舟选取的时间节点与历史事件来看,宏大叙事显然并非作家的本意,因为它们大多用于服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换言之,叶舟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因此,小说中的那些一个个的鲜活生命,无一不打上了叶舟独特的印记,成为迥异于其他作品中的具有时代和现实意义的典型形象。
在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中,梵义无疑是整部小说中的核心人物,而且起到线索性的作用。之所以说梵义是叶舟苦心经营反复酝酿出的一个独特的形象,是因为这个生长在敦煌沙州城的少年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之后依旧不改其精良纯明的本心,坚守住内心笃定的正信。梵义取名为“义”,显然寄寓了作家所要传达的理念。正如梵义所说:“结社邑义,义字当先,这一颗字浩大如天,也重于祁连山。这是生而为人的正信,更是一个儿子娃娃应有的本分。”{21}梵义从不谙世事的财东家的儿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河西司马,为家族更为敦煌守护住了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个从宗法社会走出来的年轻人,他的头脑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观念。他在时代巨变中的所作所为,正是源于其内心坚守的真善美与外界种种的假丑恶之间的强烈冲突。从这个角度说,他与索朗、丁荣猫、连公子等人的矛盾就不只是家族之间的矛盾,而是“义”与“利”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丁荣猫为牟取暴利,将罂粟花引进了沙州城,开始疯狂地种植鸦片。但却因为河西走廊的贸易通道完全掌握在急递社的手中而导致销路受阻,双方为此冲突不断甚至势同水火。直到丁荣猫与索乘沆瀣一气,企图借助县政府的力量为鸦片贸易打开方便之门。但即便如此,梵义依旧没有屈服,而是牢牢遏制住西北边陲的每一条道路,最终未能输出任何一枝邪恶之花。《敦煌本纪》彰显一个大写的“义”字,甚至可以说是重义轻利。
《敦煌本纪》最为惊心动魄之处,莫过于酒泉洪门对梵义等急递社成员展开的追杀。洪门不顾昔日情面而大兵压境,在鸦片贸易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也来向梵义借一条“罂粟之路”。梵义自然不为所动,但却因无意间透露了众多游击的行踪而酿成大祸。洪门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了酒泉驻防团,导致梵义的同伴悉数被枪杀;一群闯荡天地的少年英雄竟以悲剧的方式草草收场。小说写了少年英雄的勇敢无畏、写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坚决果敢、写了他们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不屈不挠,也写出了这些英雄走向末路时的落寞与孤独。然而,这一切都因小说笼罩在英雄主义的巨大光环之下而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英雄主义自然是史诗性作品不可缺少的内涵。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体现在时代和体制转型过程中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尽管共和体制已经确立,但于敦煌而言,它似乎只是远处刮来的风而并未真正改变这里的一切。因为说到底,敦煌本纪只能由敦煌人自己书写。梵义为河西走廊开路,孔执臣抢救莫高窟和千佛灵岩,包括从敦煌走出而投身革命的索乘、梵同,他们凭信念和理想在敦煌开出的灿烂之花足够美丽而动人。他们孤身犯险,用脚开路,践行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顺应了时代大势;少年英雄的壮举显然构成了《敦煌本纪》史诗性风格的重要一环。
“后寻根”时代的文化想象
考察《敦煌本纪》的地方性书写,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这一普遍被认为是“回归传统”的文学思潮,其实“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本质上说,寻根文学乃是主体遭遇世界后的自我焦虑与想象突围。正如陈思和指出,由于早期寻根文学的作家大多为知青身份,他们这群刚刚走上文坛的年轻人急需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但他们又不像前代作家那样有着强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理想失落之后,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表面上看,他们寻找到的是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充分建立在作家对现代派接受的基础之上。“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地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22}“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本原性(事物的‘根)构成,将能为民族精神的修复、为‘现代化的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23}
李丹梦指出:“寻根宣扬的‘以文化反拨政治,并非是要对抗或超脱政治;毋宁说它是一种和平迂回、欲进且退的集体改良态度。一言以蔽之,经由文化‘寻根的言说阐释,无足轻重的知青俨然成了民族/历史的主体,他们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上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甚至上升为在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民族代言人。”{24}
叶舟虽然并未被归入寻根作家之列,但却毫无疑问地将文化寻根融入到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写作生涯之中。不可否认的是,叶舟对敦煌的歌颂与书写带有明显的寻根意味。叶舟说:“事实上,敦煌是几种文化的总枢,是古代西部中国的首都;无论从历史、地理、军事、贸易、宗教、民族和风俗,还是从我们这个民族的缘起与精神气象上讲,她都有一种奠基和启示的意义。”{25}叶舟渴望从西部找寻到我们民族失落已久的文化之根、精神之根,这显然与1985年前后寻根文学的宣言不谋而合。韩少功在著名的《文学的“根”》中认为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26}。韩少功文中所举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还有乌热尔图探寻鄂温克族文化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色彩,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寻根文学思潮虽然早已过去,与之相关的特定历史背景与主体身份也不复存在,但它对地域、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再造与想象却作为寻根文学乃至八十年代的文学遗产而被保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舟的敦煌书写流露出昔日寻根文学的余韵,乃至成为“后寻根”时代的文化证言。显然,《敦煌本纪》不仅要为西部或敦煌的文化进行申辩和张扬,更蕴含了作家叶舟更大的志向、抱负和野心。在一次访谈中,叶舟谈到自己创作的历程:
我前面说过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大部队”,我不想被悬浮,也不想虚妄地写作,更不愿意随大流。我有两个榜样:一个是张承志老师,一个是杨显惠老师。礼失求诸野,他们的双脚扎扎实实地踏勘在西北的大地上,每一次告别,他们倔强的背影都让我潸然,也都像是一次警告或启示,催促我上路。
后来,我自己也照样学样,一次次地上路,深入到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褶皱深处;在黄河上游飘摇,也在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黄土文化之中穿行,在丝绸之路上漫游。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和他们一点儿隔阂都没有,我其实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27}
由此看来,叶舟以一种“在地性”的写作回馈并供养脚下的土地和文明。《敦煌本纪》回到风云激荡的年代,回到年久失修的“锈带”,所要寻找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少年时代的气概。叶舟多次表示他对清代诗人黄仲则诗句的喜爱:“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在叶舟看来,“‘幽燕之气就是《史记》的气概,就是项羽的气概,就是荆轲、高渐离的气概,就是中国古代春秋的性格,就是一诺千金、兄弟联手其利断金,就是十步杀一人。”{28}叶舟坚信,《敦煌本纪》所要找寻的精神文化之根并未消失殆尽,还保留在未被全面开垦的边疆。从时间的维度上说,这种精神气概还在史前史的意义上存留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在小说中,长子梵义在胡恩可病倒后第一次出门远行,领略到如此壮烈残败的风景,也感受到孤单一人在外的落寞。这时,他忽然想到父亲从前对自己说的:“我们没别的命,我们的命就在河西一带,在敦煌一线。我们也没有另外的大光阴,我们的光阴,就是活在这一条长路上,生做马,死当车,一辈子走下去。”{29}“但是,苍天有眼,国家有幸,整个西北至今锈而不死,僵而不化,一直掩藏着大好筋骨,保存着中国的最后一份元气。”{30}——这是梵同面对敦煌乃至整个西北锈带所做的慷慨陈词,也可看成小说旗帜鲜明的“寻根宣言”。事实上,胡恩可一语成谶,因为梵义的结局何尝不应验了父亲的教诲。拖音因梵义而死,梵义最终也成了拖音,他永远留在了开元寺默默守护着敦煌。
“惟有一愿在,能呼观世音。”这是《敦煌本纪》反复出现的谶语,也是作家最想传达的观点。叶舟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人的精神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足够令人安身立命,甚至气吞山河。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博大与卑微的不同层面,这注定了他们或为“利”而生,或为“义”而死。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同样熔铸于寻根思潮的血脉之中,只不过它被推演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敦煌本紀》对于精神世界的探寻由人心直抵神性。沙州城与莫高窟在小说中分别象征了世俗与神性两个世界。平日里,敦煌二十三坊由文武和事老协会把持,呈现出一种民间的显像。尽管沙州城中上演着一出出血淋淋的算计与争斗,但这些阴谋决不被允许在莫高窟这样一个神明之地作祟;即便再凶悍的土匪到了这里也只得放下屠刀潜心忏悔。只有在莫高窟,敦煌人的内心才是平静安稳的。莫高窟的佛龛预示着关外乃至整个国家的兴衰,正如梵义所说:“敦煌板荡,罂粟遍地,关外三县一派消沉,国家也是满目疮痍。这在我看来,只因为我们民族头顶上的佛龛空了,供养丧失了、无信无义,就像千佛灵岩上的藏经洞一旦流失,整个莫高窟也就失了三魂、丢了六魄似的。”{31}
简言之,叶舟在《敦煌本纪》中的寻根,是要通过对古旧中国西部边陲人性的张扬,为当下中国片面发展的现代实践找寻到一个合法的基础乃至良方。无疑,叶舟找到了地方性这一基础用来连接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并将之推演到当下的中国,使之以连续体的形式有效回应着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将历史带入地方性的书写,令叶舟暂时摆脱了他对现实抱有的怀疑与游移,使其得以沉浸在对民族文化的寻根之中。虽然叶舟并未真正解决当下的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敦煌本纪》由此凸显“后寻根”时代的文化想象与主体焦虑。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是打着“回归传统”的旗号,“曲线救国”地实现对现代派/化的接受,那么“后寻根”时代的文学则是在现代派/化成为一种集体感召与动员结构之后的今天,借“传统”和“地域”之名重新反思现代逻辑,回归世道人心。进一步说,《敦煌本纪》通过地方文化寻根,试图找回人性中最为深沉古朴的东西,用来抵抗现代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制和阉割。叶舟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将自我不断丰富与历史化,另辟蹊径地反思现代逻辑。《敦煌本纪》借由地方性的书写转向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想象,这是小说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所在。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说,叶舟对于敦煌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毫无疑问,《敦煌本纪》动摇了长期以来内陆文明从属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相反是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视角重塑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世界文明,这也符合当下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所体现的文明观。小说中的少年英雄为西部“锈带”开路,如同叶舟以一部《敦煌本纪》为西部“除锈”。应该说,《敦煌本纪》深入到民族血脉之中、挖掘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也打通了一条东西方文明彼此借鉴互通之路,使之在十十一世纪成为一条焕发生机的生命带。
总之,《敦煌本纪》不仅在全新的意义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的版图,还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文明的发展,作家叶舟的努力同样值得肯定。
注释:
①有研究者指出,一些作家在刚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怀有一种经典思维和经典意识,表现之一是作家们在进行文本书写的时候,往往刻意瞄准经典文本,以此为准绳。参见刘小波:《“经典冲动”与当前长篇小说书写》,《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
②⑦⑧[日]柄谷行人:《中文版再版作者序(2013)》,《日本現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7、5页。
③[日]柄谷行人:《英文版作者序(1991)》,《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④⑤[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1页。
⑥张海龙、雷媛:《唯有敦煌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叶舟接受兰州晨报·掌上兰州专访》,《兰州晨报》2019年8月28日。
⑨⑩{11}{15}{20}{21}{29}{30}{31}叶舟:《敦煌本纪》,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395、295、61、218、1157、193、396、1081页。
{12}叶舟:《西北纪》,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14}{28}2019年10月31日21:00,叶舟做客东方卫视中心艺术人文频道《今晚我们读书》,视频见微信公众号“叶舟的北方”2019年11月3日推送。
{16}《叶舟:书写敦煌是我一生的宿命》(专访),见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19年9月4日推送。
{17}转引自[日]柄谷行人:《中文版再版作者序(2003)》,《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18}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19}王哲珠:《史传文学的开阔性》,《文艺报》2017年4月14日。
{2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2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4}李丹梦:《新中国道德构建的地方契机——论李佩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25}{27}周新民:《叶舟:大敦煌之鹰——六〇后作家访谈录之十九》,《芳草》2016年第1期。
{26}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