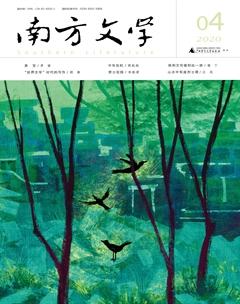一篇被法镭搅了局的诗论
杨小滨
我最近常常被那个叫作法镭的家伙搞得六神无主。比如,当我现在要下笔写一篇严肃的诗论时,法镭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这篇文章应当这样开头: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各种辉煌的理念毁灭成正义的幻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以这个时代的精英兄弟们而自豪。我本来想写的是另外一句话:在这个主流话语仍然以宏大的虚假希望主导着我们语言体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诗人从空洞洪亮的合唱队中毅然撤离,发出自己异质的声音,这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希望所在。
我听见了法镭在远处的窃笑声。呃,好吧。的确,从百年前新诗的开端,经过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喧闹,一直到今天依旧强劲的诗歌主潮,诗人们对自我的确信也建立起了另一种神话:主体的神话。那些自我中心的抒情主体占据了诗歌写作的核心,仿佛主体的声音是全然自足的、绝对可信的。法镭,这是你想说的吧?那我就顺着你的思路继续。
这个主体从整一化自我的声音出发,致力表达情感和观念,无论是郭沫若式的天狗、徐志摩式的雪花,还是郭路生式的知青、王家新式的受难者;无论是朝向大海和天空,还是面对历史和社会。这在五四时代和后“文革”时代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文学必须从伦常社会或集体狂热中解放出来,回到自我的“真诚”表达。但事实是,抒情的“小我”总是不自觉地靠向作为他者的“大我”,并且依賴于“大我”的宏大理念:因为唯有“大我”才能保证“小我”的合法性。在我们当今的文学话语里,从来不缺“大我”的旗帜。当然,“大我”总是代表了正义,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呢?
法镭从手机里探出头来打断我:其实,徐志摩还写过《变与不变》这样——用你们理论家常喜欢引用的巴赫金的行话来说——“众声喧哗”的诗。诗中除了树叶和星星,抒情主体甚至分裂成“答话”的“心”和“插话”的“灵魂”。就像你和我,他补充说。甚至,郭沫若的那首《天狗》里的“我”,就真的是一以贯之的单一自我吗?就算是,他好歹还要剥自己的皮,吃自己的肉呢,比你们这些自恋者强多了。
我吃了一惊,法镭知道的太多了。静下来一想,我更感兴趣的,却是鲁迅的那首《我的失恋》。虽说自称为打油诗,却一举消灭了所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新诗。是吗,法镭问道,为什么?我想了想,应该是因为诗中的“我”和鲁迅没有半点关系,鲁迅创造了一个面具化的荒诞主体,从而消解了那个可能会表达伟大爱情观念的现代主体。鲁迅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早的后现代主义者。写到这里,恰好看到张枣的一句话:“作为新诗现代性的写作者,胡适毫无意义,也无需被重写的文学史提及。我们新诗之父是鲁迅,新诗的现代性其实有着深远的鲁迅精神……”我想也许可以把“现代性”看作是“后现代性”,反正利奥塔认为现代必须首先是后现代的。在《狗的驳诘》里,鲁迅塑造了一个连狗都辩驳不了的贫乏主体。在《野草》的许多篇章里,鲁迅也应和了超现实主义对梦境的迷恋。
那么,也可以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梦境的。因为梦里超现实的我不必是现实的我。梦里的我不过是法镭罢了。刚说罢,法镭突然破窗而入,露出狰狞的牙齿,让我心惊胆战:那你呢?你无非是拿我当挡箭牌,仿佛你可以逃脱自我审视!我问:你到底是谁?法镭哈哈大笑:你臆造了我,居然不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