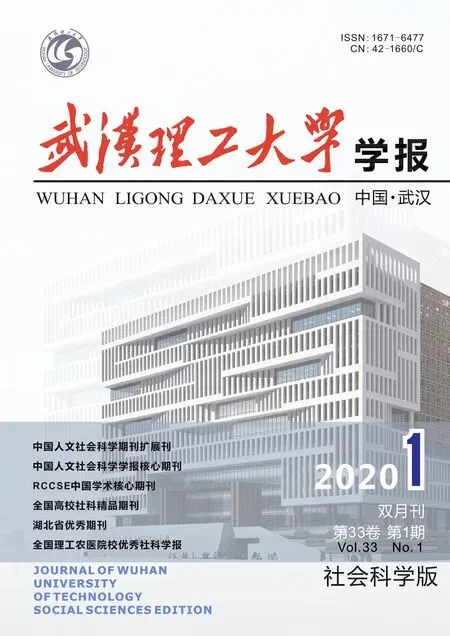论斯图亚特·霍尔的阶级思想*
陈美灵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1932.2-2014.2)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有机知识分子”、“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等。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曾指出:“不管是谁想要写一篇关于不列颠左派知识分子的小说,当他开始四处找寻一些典范的虚构角色来连接不同的趋势和阶段时,他一定会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在重新创造斯图亚特·霍尔。……他可以说是行走的编年史,他知道一切事物……”[1]232。
霍尔先后以《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新左派评论》杂志、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今日马克思主义》为平台,发表了众多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针对性的文章,论述了英国战后社会变化及其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形成了其视域独特、视角广阔、体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点的阶级思想。本文以霍尔散落的文本或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为参照,提取“霍尔的阶级思想”为主线,力图从霍尔阶级思想的研究视域、发展进程、理论渊源、成因探究、总体评价五个方面全景式呈现和分析霍尔的阶级思想。
一、 霍尔阶级思想的研究视域
“大众文化”是霍尔阶级思想的研究视域,即霍尔的阶级思想与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霍尔阶级思想的大众文化视域体现在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当中:霍尔将大众文化视为撕开僵化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切入点,他将大众文化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主体、阶级斗争的方式、阶级斗争的结果等)和社会主义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具有政治的维度:他认为大众文化是阶级斗争的场域,为构建社会主义提供了空间。
第一,大众文化是阶级斗争的场域。霍尔对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简单化处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而对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重视应该提上新左派理论建设的日程。霍尔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具有重要的关系,大众文化具有政治的维度,与阶级斗争相关联,他坚信大众文化研究的落脚点在于阶级的视角或阶级斗争。早在《大学与左派评论》发表的《无阶级感》中,霍尔就强调文化的政治内涵,他曾不无遗憾地讲到:“我们的文化本身就以某种方法转化为政治,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遭到我们贬低的政治理论中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事实”[2]80。他在《解构“大众”笔记》中指出,大众文化与阶级斗争是关系复杂的统一体,大众文化与阶级具有紧密而复杂的联系:阶级与阶级斗争要深入大众文化领域,大众文化同样不可忽视阶级的维度;否则,只有大众文化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不能忽视他所分析的“大众”与阶级的复杂关系[3]55。霍尔认为,不能被“大众文化”这一具有包容性的术语掩盖其与工人阶级文化、工人阶级的关联;如果忽略或缺失阶级的视角,漠视阶级斗争,谈论“大众文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大众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提供了空间。历史地看,“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在霍尔看来并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恒定的,它既包含同质性的工人阶级文化,也包含异质性、复杂的工人阶级文化,还包括以种族、性别等为基础的非阶级文化。这与霍尔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份相符,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是: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简约论观点。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变动不居,“大众文化”的着眼点是形式和活动,其基础是特定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因而对“大众文化”的定义应该注重其持续变动的张力。霍尔不无讽刺地讲到:“文化形式本身不含有内在确定性,而且不能因为它在某一时期曾与一场相关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就保证它将永远成为阶级的活标志,以至每次使用它,它都会‘说着社会主义的语言’”[3]55。霍尔在指出大众文化的物质性、多层次性、与统治文化关系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认为,大众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的斗争领域,为构建社会主义提供了空间:“大众文化……不是已经完全成熟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被简单地‘表达’出来的场所。不过它是社会主义可以在那里得以建立的领域之一。这是为什么‘大众文化’具有重要性:否则,实话说,我根本不会去理睬它”[3]57。但霍尔也指出,这需要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来实现。
大众文化作为霍尔阶级思想的研究视域,体现在他对媒体、青年亚文化、道德恐慌、“新时代”等的研究中,正是在对“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批判性的动态分析研究中,霍尔挖掘了“大众文化”的物质性、异质性、结构性或抵抗性,他的目的在于发掘大众文化的抵制潜能,发现新的抵抗力量,构建新的社会主义。霍尔对于大众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成功研究,使大众文化实现了一种阶级、政治介入,提升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地位。
二、 霍尔阶级思想的发展进程
霍尔的阶级思想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域,既体现了英国新左派的立场,又体现出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特色。他以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为依托,对大众文化在不同阶段和领域内的形式和内容(媒体、青年亚文化、撒切尔主义、“新时代”等)进行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对当代工人阶级、阶级意识进行了文化建构,提出了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性质问题的批判性理解。随着霍尔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式的转变,其阶级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不断流变的景观,难怪有学者评价道:“但是不管怎么样,霍尔像变色龙一样的职业生涯,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一贯的”[1]233。以霍尔阶级思想的具体立场、研究背景、研究内容来看,他的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新左派时期、伯明翰时期以及后伯明翰时期。
第一,早期新左派时期:同质性无产阶级的虚假的无阶级感。20世纪50-60年代,霍尔在新左派运动早期,或称前伯明翰时期,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是否使得工人阶级发生了改变。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和传媒这一大众文化的研究、对工人阶级的研究,霍尔指出,虽然工人阶级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到来发生了改变,但是它仍然存在,不过工人阶级的体验与构成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虚假意识:“无阶级感”(a sense of classlessness),视自己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伪装的、虚假的“人民资本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阶级、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工人阶级在“人民资本主义”的虚假现实与工人阶级“无阶级感”的虚假意识中以一种新的奴役方式“解放”了自己[4]164-167。对此,霍尔倡议社会主义者要找到介入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战略方法,要进行积极的政治介入。霍尔关注统一、同质性的无产阶级,开启了将文化介入政治的研究,并在日后的研究中铺展开来。前伯明翰时期霍尔的阶级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文化的政治介入,此时霍尔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体,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生活经历,是同质性的;他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抵抗的潜力,新左派要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指出这是理论和现实的策略需求;霍尔将社会主义信仰纳入阶级和意识等感觉领域重新思考。
第二,伯明翰时期:异质性无产阶级的霸权—抵抗模式。霍尔阶级思想的第二阶段大致与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相对应。20世纪60-70年代,霍尔阐述了对“复杂统一体”,即“媒体—亚文化—国家”的思考。这一时期霍尔的阶级观具体体现在——期间霍尔对媒体、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道德恐慌的研究中,其阶级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阵地,其中工人阶级文化是复杂的而不是同质的,具有抵抗的方面而不只是霸权的方面。与上一阶段相比,霍尔的文化介入的理论取向和现实关切是一致的,但此时霍尔将工人阶级看作是复杂的、异质性的。由于经验等因素,工人阶级是异质的、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既是能动的场域,又是被动的结构,霍尔从大众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寻求抵抗的主体,他认为大众文化表现为媒体、亚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等形式,其中既蕴含工人阶级结构性的被动地被统治或被领导,又蕴含工人阶级主动的积极的抵抗或抵抗潜力,同时由于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不同等因素,工人阶级发挥能动性进行抵抗的潜能和抵抗程度各有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霍尔的阶级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争相合,实现了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葛兰西转向”的范式转换[5]。
第三,后伯明翰时期:异质性的多元化主体社会。20世纪80-90年代与21世纪的后伯明翰时期,霍尔的阶级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发现多元主体的过程中,从阶级淡漠走向了去阶级。这与其早期新左派时期、伯明翰时期所具有的鲜明而坚定的阶级立场具有很大不同。首先,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分析了当时盛行的撒切尔主义,分析了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指出这正是左派所欠缺的,主张学习撒切尔主义:为社会主义信仰辩护;实行非阶级指向的政策;联合其他的阶级和阶层。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学习的代价是消解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主体性地位。在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阶段,霍尔将他本来就不看重的阶级推向了更加边缘的地位,这为霍尔在对“新时代”的研究中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20世纪90年代后,霍尔在对“新时代”的分析研究中转向身份政治,背离了阶级的文化政治,将其思想推向了极端,彻底地取消了无产阶级的优先地位。霍尔在关于新时代的论争中,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将阶级主体碎片化之后,他用多元主体取代了阶级主体,认为社会主义政治不再根据共同经验而被思考,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种族、性别等在社会结构中的综合影响。遗憾的是,霍尔逐渐走向身份政治这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尔都是著名的新左派成员”[6]44,言外之意令人唏嘘不已。
三、 霍尔阶级思想的理论渊源
以上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纵向分析了霍尔的阶级思想,那么片段式、节点式地分析其阶级思想是否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霍尔称其为“不做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喜鹊”。诚然,他在研究中继承发展了英文文化马克思主义,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霸权思想等。要具体了解、认知霍尔的阶级思想,其关键是理解文化唯物主义、葛兰西霸权思想、接合理论,因为它们是霍尔阶级思想立论的理论基础,是影响霍尔阶级思想的理论视域、发展进程或观点立场的重要原因。
第一,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它由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代表性人物雷蒙德·威廉斯所阐释,强调文化本身的过程性和物质性。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直接推进物质的范畴之中,提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文化唯物主义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肯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肯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反对将文化定义为纯粹的精神范畴,又反对把文化看做是经济基础的直观反映。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开阔的社会视野,体现了政治介入的自觉的政治意识。霍尔受此影响,坚持了一种文化介入的、积极的政治观,将“大众文化”看作是积极的能动的场域,是阶级抵抗的方式、社会变革的阵地、社会前进的动力。霍尔反对英国传统的利维斯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是霍尔阶级思想的基本点,其现在他对多样的、具体的大众文化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及其阶级思想的大众文化视域。
第二,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霍尔的阶级思想深受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7]。该理论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8]37,并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葛兰西区分了东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指出了文化霸权这种社会统治方式,即社会统治集团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统治,而是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等文化手段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赞同,进而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和领导。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谈判和斗争是复杂的,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形成“共同意识”的复杂历史过程。葛兰西对领导权、领导权的获取方式进行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阐释。霍尔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理解大众文化,因此他在媒体传播中肯定了积极受众的方面、在青年亚文化中看到了青年对主导性资本主义文化的政治性抵制、将“撒切尔主义”解读为“威权平民主义”。霍尔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政治等的斗争领域,既有“同意”,也有霸权。
第三,接合(articulation)理论。该理论强调偶然性、非必然性、非决定性,认为社会力量、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非必然的、非一一对应的。在霍看来尔,拉克劳、墨菲的接合理论实现了与僵化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论、还原论的决裂。霍尔指出,Articulation具有关系的连接、话语的表达的含义。他借鉴这个概念的含义与语义阐释了自己的接合理论。其一,不同要素的链接形成统一体,而要素之间的接合不是预设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持久的、非绝对的;其二,不仅强调关系或结构的链接、连接或接合,而且强调话语的表达;其三,强调接合的未完成性,认为不同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8]552。20世纪80年代后,霍尔在“撒切尔主义”、“新时代”的研究中对一系列问题有了更深的或崭新的认识——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大众文化与阶级地位是不对等的;阶级意识形态或大众文化是多样性;种族、身份、性别等是影响阶级意识或大众文化的重要因素——他强调阶级与经济地位、种族、性别等身份的链接,强调政党对主张的理论的阐释和宣传(表达)[9]。霍尔在与接合理论的相遇中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四、 霍尔阶级思想的成因分析
霍尔阶级思想的文化视域、流变发展、借鉴理论与他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英国具体国情、个人成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霍尔的阶级思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战后英国具体的文化环境、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的发展状态、霍尔始终“不在中心”的个人经历等。
第一,英国社会文化研究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相对薄弱、新左派学者对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是霍尔阶级思想形成、变化的时代背景。首先,战后英国新左派立足本土研究特色,进行了积极的理论研究,形成了颇具英国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抵制了苏联政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界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形成了人本主义的重要原则。受此影响,霍尔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僵化片面理解,同时积极实现一种文化的积极政治介入。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薄弱,这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更易于冲破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更加容易背离马克思主义。霍尔的阶级思想的立足点、理论取向、思想流变、丰富内涵就是这一松散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产物和表征。同时,大量欧洲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战后被左派学者译介。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宽广的理论视域和热切的政治诉求客观上推动了新左派理论的繁荣,也为霍尔的阶级思想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这体现在霍尔对符号学、霸权理论、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的借鉴发展方面。
第二,战后英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发生的剧烈变化是霍尔阶级思想形成、变化的社会原因,是现实背景。霍尔的阶级思想起源、发展和形成于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中以及英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他以战后英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为具体研究对象,力图从折射二者关系的大众文化中发掘阶级抵抗。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英国资本主义在战后繁荣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其吸引力将工人阶级整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似乎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现实解释力和改造力,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霍尔揭示了这种无阶级感的虚假性,提出了积极的政治介入规划。20世纪60-7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历经繁荣发展与危机转变,处在“共识政治”之下。在霍尔看来,阶级文化、阶级关系、阶级斗争随之有了新变化,他通过对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非同一性、意识形态性、斗争性。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资本主义富裕神话的破灭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由衰及盛的发展,在危机中华丽转变,英国社会中新的变化由此接踵而至,因此霍尔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新变化进行了研究并进而强调身份政治。
第三,霍尔的移民身份、成长历程对其阶级思想的形成和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多数出生在英国工人阶级家庭,在二战中成长,多为英共党员,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保持了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他们自觉地反对苏联的教条主义,将英国的具体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较好地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霍尔在身份、种族与成长经历方面与第一代新左派有很大不同。霍尔出生于英国的殖民地——牙买加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岁时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是成长和生活于英国的黑人,这使他在英国与牙买加、白人与黑人间始终处于“边缘”的地位,关注对边缘群体、身份、性别、种族的研究;霍尔延续了儿时对文学的热爱,大学专业为颇具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这使他对大众文化内容及其变化情有独钟,因而他强调文化政治,强调从文化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独特的学术视角、种族身份、成长经历、学术旨趣使得霍尔更容易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转向身份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
五、 对霍尔阶级思想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可见霍尔的阶级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政治,他本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甄别与解构,进而发掘了不同形式、内容的大众文化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意蕴,所具有的阶级抵制潜能,他力图在文化中发现和塑造新的社会抵抗力量,构建新的社会主义。霍尔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和建构,提升了大众文化的地位,使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介入方式。霍尔的阶级思想是个流变的过程,是复杂的统一体,既有始终一贯的文化介入和政治介入立场,也有对工人阶级整体性及中心地位的无意识瓦解,因而霍尔的阶级思想既具有借鉴意义也具有警示意义。
(一) 霍尔阶级思想的积极因素
霍尔阶级思想的积极部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其二是对自觉的政治意识的践行。首先,霍尔敢于突破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窠臼,并且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以英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为基础,自觉地、创造性地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虽然后期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但他前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是具有学习借鉴意义的。其次,霍尔始终坚持自觉的政治介入意识,发掘大众文化的政治意义,力图激活其中的阶级抵抗力量。第一,霍尔阶级思想的深层原因(社会主义的整体式微)体现其自觉的政治意识。第二,霍尔将大众文化解读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认为文化是政治的。第三,霍尔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其阶级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体现其自觉的政治意识。最后,霍尔正确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始终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力图用理论解释工人阶级的新变化、构建新的社会主义主体。
(二) 霍尔阶级思想的消极因素
诚然,霍尔的阶级思想在思想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我们的学生研究和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霍尔的阶级思想忽视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极易导致泛政治化。在霍尔看来,文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文化是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因而他强调文化的政治介入,后期霍尔阶级思想的流变过程就是泛政治化问题的显现过程。霍尔在解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简单关系的过程中,亦构建了一种看似复杂的简单政治学——抛弃了阶级观,过分强调文化的政治功效。霍尔的阶级思想是一种文化政治,对文化作用的过分夸大、矫枉过正的直接后果就是,他在后期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对文化的过分强调以至忽略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泛政治化。
第二,霍尔的阶级思想是一种折衷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强调、平民主义的情怀为民粹主义埋下了隐患。因而,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贬低,指责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同化和腐蚀,反思英国传统的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观,霍尔赞扬大众文化的抵抗功能、对主体的塑造功能。这反映了霍尔对资本主义下的大众文化的乐观、对工人阶级抵抗的创造性的乐观,但这种乐观可能导致低估社会结构对于民众的制约;对于肤浅文化的不假思索的肯定,造成一种盲目的平民乐观主义、一种不加甄别的民粹主义。
第三,霍尔的阶级思想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轻视文化分析中经济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济地位来确定阶级,其与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它不单单是个经济的范畴。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错误理解之上,霍尔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的理解失之偏颇,使其走上了片面强调文化政治的道路。
第四,霍尔的阶级思想从文化切入,将社会主义建立在了缝合差异的不断连接的基础上,强调差异的统一体和去政治化,使得社会主义的实现如空中阁楼,可望而不可及。霍尔取消阶级分析的去政治化做法,具有一种泛政治化的倾向,他对抵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持一种宽容的乐观主义,将社会主义建立在信念一致之上的现实乐观主义。另外,霍尔对社会主义持悲观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使得社会主义失去了现实的根基。从短期看,文化政治的确能够使大众某方面的利益得到满足,但从长远看,这实际上消减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战斗力。多中心实际就是无中心,多主体就是无主体。
(三) 对霍尔阶级思想局限的扬弃
霍尔的阶级思想的局限性的根源在于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走向了偏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在矫枉过正中走向了民粹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泛政治化。霍尔偏离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走向民粹主义与身份政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其泛政治化和民粹主义取向和身份政治转向表现为对于文化活动中经济力量的否定。霍尔的阶级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对立起来,这是建立在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之上的。事实上,坚持积极的、文化的政治介入,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划,必须在进行文化研究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否则,只会消解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注释:
①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也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或“伯明翰学派”而著名,在文化研究的发展中曾占据重要位置。中心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于1964年首先在英语系创立,在2002年6月被校方关闭。霍加特是中心的第一位主任,当时斯图亚特·霍尔则是他的助理。1968年当霍加特离开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霍尔成为中心的主任,在1979年离开前,霍尔带领中心度过了作为多产的时期。霍尔的副手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接替了他的位置。一般认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初的三个关键性人物,属于第一代新左派,具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霍尔、大卫·莫利、多萝西·霍柏森、迪克·海布迪基等则是第二代新左派,与第一代相反,他们偏重于对文化意义作不带感情色彩的符号学分析,文化不再囿于文本,而同社会实践和制度结构密切联系起来,阶级、性别、种族问题便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心在霍尔的领导下变得更加理论化、学术化、政治化,形成了重要的文化研究重镇。
② 麦克罗比语,她将霍尔对“复杂的统一体”的探讨称为“一种微观政治学分析”。参见(英)麦克罗比的《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编译)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和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