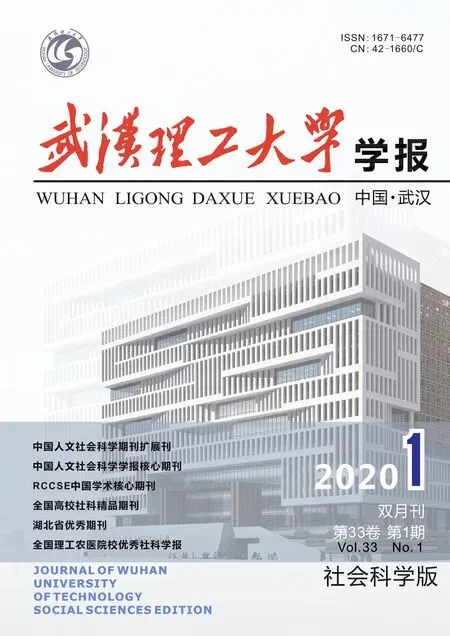被颠覆的隐喻:麻风主题的当代阐释*
——以希斯洛普的《岛》为核心
陈 倩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当代英国作家希斯洛普(Victoria Hislop,1959—)的代表作《岛》(The Island,2005)讲述了一个家族与麻风病抗争的故事,引发人们对麻风的再度重视和探讨。这一人类历史上古老的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最初起源于《圣经》中关于“不洁”、“异类”、“罪与罚”的原型表述。后世文艺作品不断重复着麻风主题,由于受强大宗教阐释学影响,麻风病人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呈现出负面的形象。比如,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贝姨》(La cousine bette,1848)里描绘麻风病人的惨状:“手简直不能看,长了许多惨绿的小脓疱……四肢的尽头都在烂,都是脓血”。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1831)中善良、忠诚的加西莫多被麻风病折磨得面貌丑陋,身体畸形。法国作家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给麻风病人的吻》(Le Baiser Au Lepreux,1922)中,尽管主人公并非死于麻风,但妻子给这个丑陋丈夫的“给麻风病人似的吻”令其万念俱灰,这个比喻悲哀却真实地刻画出人们对麻风病根深蒂固的嫌恶。
可见,麻风病长期以来被视为异类对正常社会的入侵以及秩序和理性的失控,形成了渗透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神话”[1]。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指出,社会对疾病的恐惧和排斥会滋生出种种关于疾病的“隐喻”。比如“橡胶手套”隐喻艾滋病[2]2;肺结核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相联[2]17;癌症则指腐败的生活方式[2]72。麻风病同样成为极具象征性的文化符码。然而,随着西方当代思想对“他者”、“他性”、“他异性”等范畴的再认识,文艺作品中的麻风隐喻经历了巨大转变:从极端否定的象征符到被正视,再到成为超越和批判成见的有力武器。《岛》正是一部典型的反思之作。它立足于二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以独到的叙述方式、深切的人道关怀,颠覆了几千年来的麻风隐喻,重塑了健康与疾病、理性与非理性、“罪”与“赎”、“自我”与“他者”等一系列二元关系,展现出当代西方文学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转向。以往对该作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的反讽手法及其对战争、人性的批判,极少关注与之相关的“身体”、“特异性”、疾病所引发的伦理危机,由此往往将其局限为一部畅销小说而不是文学社会学文本来解读。本文试从麻风病的原初宗教寓义入手,梳理它在西方观念中的发展;继而引出希斯洛普如何颠覆了麻风的传统隐喻,在当代背景中重审这一文学主题;进一步将《岛》放置到西方的疾病写作史、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语境中考察,结合西方思想的转向,分析这部作品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
一、 古老的放逐:麻风“神话”的宗教之源
上世纪抗生素被广泛运用之前,麻风病固然是不治之症。但是,相对于许多同时期的恶性传染病,比如肺痨、疟疾、霍乱而言,麻风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不少麻风病人患病后能活几十年,在较长潜伏期内与正常人一样,看不出区别。因此,麻风的负面隐喻体系之建立并不完全在于疾病本身,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形成的关于它的种种社会观念。这些观念源于宗教经典,它们主导了传统时代的文艺作品,也成为希斯洛普创作《岛》时的文化前语境。
皮肉上长有麻风的,他是麻风病人,他是不洁净的……得麻风病的人,他的衣服要撕裂,头发要剃光,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旧约·利未记》
“洁净”是《圣经》的终极表述之一。《利未记》第11章到15章都在谈论不洁之物,强调献祭品必须没有瑕疵,妇女生育后必须洁净身体,麻风病患必须被隔离,痊愈后经过洁净仪式方可进入圣殿……后世的教义据此建立起寓意化诠释的传统。比如公元1世纪,写给犹太人的巴拿巴(Barnabus)书信指出,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象征着不同类别的人,因此麻风病代表着罪恶。20世纪初,夏隆纳主教(Bishop Challoner,1691-1781)在关于威斯敏斯特圣经的笔记中也写到:“是否分蹄及倒嚼是直接区分善与恶的界限。如果鱼没有鳞和鳍,就被认为是不洁净的。”[3]可见,“洁净”在基督教中实际上是个关乎道德判断的词。由于麻风这种最古老的皮肤病被认为是典型的“不洁之症”,从而成为“异类”、罪恶和惩罚的象征[4]。染上麻风病的人,头发、汗毛和眉毛均脱落,面部畸形,皮肤出现斑块甚至腐烂,四肢很可能会残缺,从而外表邋遢、恐怖。在《旧约》里,表面的洁净与否对应着内心的纯洁程度,约伯的皮肤病变已暗示了皮相与灵魂之间的表里关系。之后,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嫉妒、毁谤摩西,神让她得了大麻风(民12:10-15);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贪财,谎以主人之名收受了乃缦的银子,患上大麻风(王下5:21-27);乃缦本人也曾因骄傲长过大麻风(王下5:1-19);乌西雅越职,非要在圣殿烧香,也得了大麻风(王下26:18-20)……总之,宗教经典对于麻风的阐释使之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寓意。
既然“不洁净”同罪与罚相联,那么最初的治疗途径并非医学而必须通过赎与恕。在《旧约》中,耶稣曾不止一次拯救了向他忏悔的麻风病人(太8:2-3,路17:11-19)。甚至麻风病人的存在本身亦成为上帝恩宠的表征。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写着:“你蒙受着主的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主不会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脱离他的陪伴。”[5]9因此,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对麻风病束手无策,但据研究,从罗马帝国开始,它实际上间接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6]142。
中世纪,随着十字军东征,麻风病在欧洲迅速蔓延。西方世界对麻风的恐惧与日俱增,麻风病院多达一万九千个[5]7。此疾不仅迎合了基督教对异教之地肮脏与落后的想象;而且教会认定它暗示了不洁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德败坏,它甚至成为一个形容词,法语中描绘被腐蚀的石头表面时,会用“像患麻风病似的”[2]53。教会对于其内部的麻风患者,一律无情地划归为“异类”。比如在2005年上映的以中世纪耶路撒冷王国历史为底本的电影《天国王朝》(Baldwin IV of Jerusalem,2005)中,鲍德温四世谦谨沉稳、雄才伟略,在其统治下耶路撒冷国打败外族入侵、平定国内分裂势力。然而,这位君主短暂的一生一直生活在面具的阴影之下,罗马教廷也多次对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只因他不幸是位麻风病患者。同样,在佛教里,麻风即“癞”也是最严重的疾病,被认为是对今生、前世或病人亲属或祖先所犯下的最深重罪孽的报应。肌骨腐烂程度似乎对应着病人内在道德败坏的程度。五种特殊疾症,包括癞和白癞,甚至被禁止出家受戒[7]。
人们对麻风的厌恶逐渐演变成疯狂的屠杀、放逐和隔离。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常常用船把大批麻风病人运到海上,再投入海中溺死。自12世纪末,“愚人船”载着患有麻风、天花、霍乱、精神病的患者漫无目的地在水中飘荡,于是海中的孤岛被建成最理想的麻风病囚禁区[8]。它们虽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但也生成了文明社会的坏疽,映照出人性的冷漠、怯懦和自私。多少家庭宁可为亲人办完葬礼后将他们永远弃置在隔离岛,也不愿给他们任何治疗和关爱。正如桑塔格发现,“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但令人恐惧的还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惟恐避之不及,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的公民权的剥夺,是将人逐出社会……”[2]100-101麻风患者成了“活死人”,人类社群中的“他者”。尽管19世纪中期,英国皇家医学会建议取消中古以来对麻风患者的各项法律限制,但源于宗教的麻风隐喻以及社会对它的恐惧,隔离却始终被保留着[9]。希斯洛普的《岛》出版以前,麻风病人的可憎面目同麻风隔离区肮脏、凄苦的形象一起,被历代相关主题的文艺作品定格下来。
二、 从“愚人船”到“诺亚方舟”:被颠覆的隐喻
麻风传统寓义的生成以及对它的极端处理方式既呈现出人们的无知,也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所有难以控制的因素被划为“异类”和“他者”,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岛》的作者希斯洛普曾多年从事记者工作,接触过很多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这促使她力图打破社会成见,从更多维的角度来诠释社会和人性。针对麻风寓义的深刻宗教渊源,希斯洛普关于这一隐喻体系的全新阐释同样集中在宗教和伦理方面。
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克里特海岸以北的斯皮纳龙格岛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麻风病隔离区。渔夫吉奥吉斯的妻子伊莲妮本是村里最受人敬仰的教师,她不避讳患有麻风的学生而染上麻风。她在斯皮纳龙格岛死去不久,二女儿玛丽亚也不幸患上麻风,被引渡到隔离岛。吉奥吉斯于是成为几十年如一日、唯一往返孤岛与大陆之间运送货物和人员的船工。小说至此,似乎与此前的麻风主题文学并无不同,都在叙述麻风病人如何被文明社会遗弃。然而这艘神秘“愚人船”上的情景是“正常”社会难以想象的,它比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温暖、宁静、民主、自由。领袖由全体岛民定期公选出来,与大陆上的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比。被“正常”社会歧视、得不到关爱的麻风患者在此互相帮助,相爱相守。当法西斯的血腥席卷欧洲之时,他们甚至可以在此每天悠闲地欣赏落日、聚在一起看电影、办报纸。尽管岛上设施十分简陋,一切却井然有序。“这座小小的岛屿不是个等死的地方”——“斯皮纳龙格是许多好人的家”。
复活节是斯皮纳龙格岛最重要、也极具象征意味的节庆。人们相信复活节后,一个个病躯可能会变成全新的、没有斑点的、复苏的身体。实际上,来到斯皮纳龙格岛对于这些麻风患者来说已然获得了重生。在那个血腥残暴的年代,只有这里的居民才真正相信基督会复活。二战的硝烟逐渐燃至与斯皮纳龙格仅一水之隔的布拉卡,整个欧洲充满末世的恐怖,像艘随时将沉没的船。反讽的是,一位麻风病人偷偷离岛想回家与妻儿团聚,就在他好不容易游过海峡踏上大陆的那一刻即被纳粹兵射杀。这一事件之后,斯皮纳龙格的人们都不再想离开这个避难所。更荒谬的是,斯皮纳龙格岛居然得到纳粹的特别“优待”。他们害怕麻风病人因饥饿离开孤岛,只好不断往那里运送补给品。难怪布拉卡的人们总是自嘲:“我们的国家被残暴的德国人占领,年轻人受到镇压,老人被烧死。他们(斯皮纳龙格居民)才是自由的!”
在此,《旧约》流传下来的麻风病隐喻被彻底颠覆,健康与疾病、理性与非理性、地狱与天堂、“罪”与“赎”的逻辑完全置换过来。麻风岛由让人闻之色变的“愚人船”变成乱世里的“诺亚方舟”。
在人物设置上,《岛》明显具有反传统宗教寓义的意图。作品中几位重要人物都得过麻风。首先是这个家族的曾祖母、吉奥吉斯的妻子伊莲妮。她是典型的“好人”,作者在圣徒日的狂欢活动时,借安娜之口将伊莲妮比喻成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圣康斯坦丁诺斯不也和他妻子圣伊莲妮共同享受这个日子吗?圣伊莲妮这个名字让她片刻之间想起了母亲。”圣伊莲妮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康斯坦丁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最终皈依基督。传说康斯坦丁大帝也曾罹患麻风,异教祭司告之杀戮儿童,取血沐浴可治病,但康斯坦丁大帝以仁慈之心拒绝了。于是圣徒保罗和彼得向他显现,指点他找到西尔维斯特主教寻求医治,麻风病从他身上奇特地消失。《岛》安排一位与圣伊莲妮同名的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感染麻风,深含寓意。
伊莲妮的二女儿玛丽亚正像康斯坦丁那样患过麻风,最终因她的善良而被治愈。她很会调配草药,在斯皮纳龙格岛医治了很多人,与丈夫克里提斯医生成为这个麻风世界的救世主。作者曾借马诺里之口,称之为“圣母玛丽亚”。在克里提斯看来,她是爱与美的化身:“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玛丽亚强烈地唤起他对该画的印象。”玛丽亚的善良和圣洁完全颠覆了麻风病人在《圣经》里的形象,她实际上是“复活的耶稣”。她和姐姐安娜全然不同,一个是天使,另一个是魔鬼;一个在麻风病的考验中成长、重生,另一个在优裕的生活中堕入地狱。麻风不再是不洁净和惩罚的象征,相反,它成为走向圣洁与救赎的阶梯。
第三位值得关注的麻风病人是伊莲妮的学生迪米特里,人们认为是他将麻风病传染给了伊莲妮。在希腊语中,“迪米特里”又称“迪米特里奥斯”,希腊有一位同名的圣徒,为保卫自己的城市,被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处死。作者笔下迪米特里的亲生父母有很多孩子,他从小不得重视,患麻风病后更遭家人遗弃。在隔离岛,伊莲妮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医生关注他的健康,他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成年后也成为教师。对他而言,充满温情的隔离岛是伊甸园,以至于当他被医治好而释放回大陆时反而变得无所适从,“每天隔海相望的村庄不过是海市蜃楼”。迪米特里就像圣徒迪米特里奥斯,最终为守护自己的伊甸园殉难了。
与斯皮纳龙格的温馨宁静相比,大陆上却上演着一幕幕悲剧。伊莲妮的大女儿安娜天生丽质,但从小虚荣、自私。嫁入豪门后,和丈夫的堂弟偷情,且疏远嫌弃父亲和妹妹。安娜犯下傲慢、懒惰、色欲等恶行,和妹妹玛丽亚形成鲜明对比。同安娜偷情的马诺里是地道的花花公子,他一度迷恋纯真的玛丽亚,但在知晓她患上麻风的第一时间便抛弃了对方。玛丽亚将他比作犹大,“会背叛自己的家庭,会亵渎对他的仁慈和盛情”。与犹大不同,他直到最后都不曾有一丝愧悔之心,尽管玛丽亚的爱曾几乎将他拯救,但他终究是撒旦,向地狱最深处走去。安娜的丈夫安德烈斯是整部作品中最具悲剧性的角色。他生活简朴,为经营家族产业每天早出晚归。心地单纯的他热情迎接多年未归的堂弟并为其安排生计;周围人都知道他妻子和堂弟的私情,他也不愿多加怀疑,以至于真相大白后觉得大受欺骗而杀妻,在监狱里孤苦死去。安德烈斯虽然无辜,但他犯下暴怒和杀人罪,成为畸形社会的牺牲品。
三、 “身体”、“他性”与“现代性”:《岛》的启示
如果说“身体”是人类伦理的始基,那么如何对待疾病这种“身体”的存在方式则成为考验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身体”、作为“他性”的疾病与“现代性”在文化隐喻系统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正视和反思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希斯洛普将《岛》的故事安排在二战时期颇具历史寓意。在传统与现代之交,正值医学终于可以治愈麻风之时,这些曾经的“活死人”回到“文明”大陆和各自的“故乡”后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恐怖的“屠场”和“废墟”。在传统社会,人类面临的多是来自外部的挑战;而现代世界,弥漫在西方的绝望、颓废和“末世”情结却大多源于人类自身。因此,包括麻风在内的各种“疾病”书写所承载的隐喻体系成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主题、叙述策略及文化症候[10]。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鼠疫》(La Peste,1947),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癌症楼》(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1968),法瑞尔(J.G.Farrell,1935-1979)的《克里希纳普之围》(The Siege of Krishnapur,1973),斯拉夫尼科娃(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1957-)《脑残》(Лёгкая голова,2003)等作品,以各种疾病意象反映了在启蒙理性、工业机械主义、政治官僚化、民族国家体系、审美媚俗等一系列全球“现代性”发展中,人们遭遇的各种困境:荒诞、恐怖、混乱、颓废、失去爱与信仰……“斯皮纳龙格”为代表的麻风岛反而成了逃避灾难的乌托邦。何处才是人类真正的“故乡”?
1976年,美国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的代表作《瘟疫与人》,详细分析了传染病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他将传染病的生物传播称为“微寄生模式”,而其赖以形成的文化心态、权力意志和以城市为核心的全球化扩散渠道则为“巨寄生模式”[6]63。麦克尼尔发现,在“巨寄生模式”影响下,“微寄生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单纯的生理现象转化为具有隐喻作用的社会现象。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也曾将传染病的防控体系与权力话语联系起来,总结出“麻风病模式”和“鼠疫模式”。前者是排斥的模式,后者是容纳的模式。福柯发现,中世纪以来,人们将麻风病人驱逐出社会共同体,而对待鼠疫则不同,他们在鼠疫肆虐的城市实行严格的临时管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疾病本身的性质造成: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容易短期内爆发,且存活率极低,对于这种“毁灭性”的疫情,隔离变得极其困难且意义不大。麻风则是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有相当久的寿命。由此,权力机制、道德舆论、文化语境必须有效对其实施管控[11]。
进一步说,与鼠疫等烈症相比,人们对麻风的厌弃已经不只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奈。麻风和癌症一样,就像从自体之中生出的“另类”,这种“他性”与“自体”如影随形、难以区分,使人们备感尴尬。当皮肤的破损、触觉的麻木、躯干的畸形缓慢地侵蚀着患者的身体,患者不得不重新认识并逐渐接受另一个“自己”。正如《岛》的主人公玛丽亚,她害怕的并非麻风病本身,毕竟“亲爱的妈妈”也是麻风患者。她害怕的是样貌的改变,“不认识自己”;害怕被遗弃在隔离岛,永远失去至亲挚友。一旦到达斯皮纳龙格,发现这里竟比大陆上更井然有序、充满温情,还能逃过战争;父亲常往来于陆岛之间;最好的朋友不但没有疏远,反而偷偷来探望……她觉得自己甚至“更幸福”了。可见,麻风隐喻及其代表的社会歧见比疾病本身可怕得多,它反映了人类社群对于内部“异已”的冷酷和残忍。
自古希腊以来,尤其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哲学一直试图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更深入地认识人类自身,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传统关于“主体”的言说总强调“同一”化,认为解决冲突的最终方法即将“他者”还原为“同一”。直至黑格尔打破单纯的“同一论”和“总体论”,认识到差异的重要性,为重审“他者”(The Other)开辟了空间。后来者延伸了黑格尔哲学这个未及展开的维度。比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1905-1995)通过反思犹太种族大屠杀及文明的冲突,试图超越现象学而转向伦理学,强调应该尊重“他者”的绝对地位[12]。在他看来,全球化、殖民主义、权力意志乃至暴力和战争都是“同一性”在现实中的投射。西方现代性危机,尤其主客体的紧张关系即源于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片面理解[13]。但是,列维纳斯要坚持的“他者”是“不能还原为自我”的“另类”,而现实中,“自我”与“他者”是很难相互区分的。病患、侏儒、残疾人、智障者都因为在社群中的“他者”身份而饱受屈辱。“自我”总习惯以“非我族类”的思维去对待“他者”,却忽略了“他者”可能是主体自身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真正的“他者”,只有“自我”无法被全然化约的“他性”(The Alterity)。诚如英国学者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所言:“他性是所有社会身份中的基本要素……他性就在我们之中,当一种文化、社会或团体把某个个体排斥为他者时,它试图排除或压制的实际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14]。
正因为麻风患者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存在于“自体”之内的“他性”,“正常”社会才急切地要将这些隐藏的“他者”硬性隔离出去。在此,麻风隐喻已由古老的关于“不洁”、罪与罚的传说转化为文明社会如何面对“自我”之“他性”的问题。《岛》中安娜和玛丽亚两姐妹、马诺里和安德烈斯两兄弟、索菲娅和阿丽克西丝两母女……撒旦和上帝,实则互为另一个自己。换言之,“主体性”本身暗含着根本的“他性”维度。对麻风的绝然拒斥反映现代人处理“他性”的态度:对身体异质性发展的恐惧和无奈,以及人们对自身创造的“现代性”的失控和绝望。
四、 结 语
在文学中,疾病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现象,“身体”往往包含着多重寓涵。希斯洛普的《岛》严肃探讨了西方文学中长期受到忽视却又被高度“神话化”、“妖魔化”的麻风主题。以往虽有大量作品涉及麻风现象,但大多只是整个文本的插曲。它们即使对麻风病人怀有同情,但总体而言,并未摆脱传统社会形成的偏见式麻风隐喻。对《岛》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忽略了它包含着一条隐含的暗线,即有意批判基督教历史上的麻风典故和麻风事件。基于《圣经》中“不洁”、“异类”、罪与罚等表述,麻风病患者一直被“边缘化”和“异化”,人们习惯用嫌恶、恐惧、排斥来对待这些人类社群中的“少数派”和“他者”。
在麻风隐喻被高度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广泛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岛》极具象征性地彻底颠覆甚至倒置了传统关于健康与疾病、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失序、罪恶与救赎、丑陋与美好的既成逻辑和等级秩序,将被社会遗弃的隔离岛想象成能幸存于种种“现代性”劫难的乌托邦……它典型印证了当代西方文学价值和人文关切的转向,即对弱者和他者的重审与“涵纳式”认同。它说明人类最可怕的挑战并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疾病所指涉的人性弱点、社会偏见和时代困厄。
“他者”的“发明”与当代文化语境中主体与外在的紧张关系以及自我的封闭性焦虑紧密相联。疾病与健康如影随形,前者时时潜伏在每个人身体内部,实为“身体”日常存在方式的一种。《岛》展现出在整个人类社群里,病患并非真正的“他者”,只是“自我”的“他性”而已。当“他者”与“自我”不再以割离的二元模式存在,而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中作为“自体”的“他性”之一而呈现时,两者便有可能互相注视、包容和诠解。对麻风的隔离表现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恐惧和不明,对麻风隐喻的颠覆实为人类对自身认识局限的反思和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