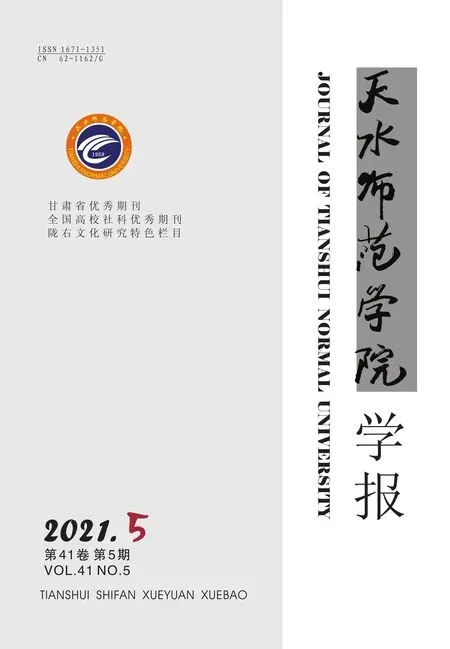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重理论建构
闫强乐
(西北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博大庞杂,自成体系。法律文本方面,律、令、例等多种法律文本并存;法律部门方面,宪法、民法、刑法、诉讼、行政等多方面法律部门并存;法律空间方面,中央立法与地区立法并存,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重学术图景。[1]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法律文本、法律内容、法律空间、官僚体制等不同角度建构不同的法律体系认知,形成了律令法体系、部门法体系、“国家—民间”二元法体系、“六事法体系”等不同理论学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重理论图景。但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依循自身的政法逻辑演化,具有独特的法律文献、法律内容、法律精神。本文梳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多重理论图景的建构历程,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价值理论基础,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各种理论的利弊得失,期望为建构一套适应中国本土文化自觉的法律体系提供一定的学术思考。
一、文本视域下的“律令”体系
中国古代“律令”体系的理论建构受到日本法律史学者研究范式的影响,学界重点从中国古代法律文本的辑录、考释研究,参考日本古代的法律图景,以法典文本为中心,建构出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通论“律令”体系的学术研究现状,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大体沿袭中田薰最早的提法,或是进一步明确法律体系的概念,或是进一步充实律令法体系的内涵,或是根据时代的变迁、历代法律形式的演变,修正律令法体系的认知,形成律令、律令格式、敕令格式、律例、典例等多重图景的法律体系论说。
(一)律令体系:日本学者的学术建构
日本历史学家在总结日本大化革新的历史之后,认为“大化革新时建立,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的日本古代国家,以律令为基本法典,故称律令国家”。基于隋唐时期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日本法律史学者中田薰提出了“律令”体系的学术概念,其根据唐代法律律、令、格、式的基本文本,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律令”法律体系的沿革,明确“律令”体系的概念,“所谓律令法系,是指由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组成之国家统治的基本法的中国独特的法律体系”,[2]并且认为律、令、格、式完备的唐代法律是律令法系发展的顶峰。在此之后,经过日本大师级学者大庭脩、小口彦太、菊池英夫、堀敏一、梅原郁、渡边信一郎、池田温、冨谷至等的不断“加持”与细致研究,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似为不刊之论,成为日本学界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基础概念与理论前提。
(二)律令体系:中国学者的不断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欧美、日本的学术理论、学术概念又一次漂洋过海,对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于中国法律史而言,“律令”体系的学术概念成为建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学理基础。张建国基于“概括作为两千年来帝制时代法律的体系”的意愿,将律令法体系的学术概念引入中国,认为“律令法体系是指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的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律令法体系是一种基本由公法构成的成文法体系,历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3]经由张建国先生的学术概念引进,“律令”体系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学术概念,不同时段的法律史学者基于中国古代史的不同文献材料,详细论述律令体系的内容、区别、嬗变与特征,形成基于律令学说的多重学术图景。
1.秦汉魏晋“律令”体系
以晚清律学家薛允升、沈家本、程树德为代表的早期辑佚、考证、复原研究,为秦汉法律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史料与学术基础。[4]之后的研究成果,对秦汉时各种法源的不同作用、地位、性质给予了定义和解说,进一步揭示了汉律令体系的内部结构,从而开启了“律令”体系的滥觞。而伴随着晚近简牍法律的出土,丰富了秦汉法律体系研究的新材料,尤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主,其中大量的秦令史料,大力推进了秦汉法律体系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法律体系研究,学界基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以及“违令有罪则入于律”“律以正名,令以存事制”的史料,关注于“律令分野”的学术问题,为进一步认识律令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参考。
2.唐宋“律(敕)令格式”体系
唐代法制史学者基于《唐六典》律令格式内容的文献记载,通过考证、辑佚、复原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法典编撰的角度,为隋唐“律令格式法律体系”提供了学术厚度。周东平通过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归纳而指出“唐代是中国律令制的完成时期,其律令较之以往,作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尤其如此。它们凝结着汉民族法制发展与成熟的智慧,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这在八世纪中叶的开元末达到了顶点”。[5]宋代法律体系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自宋神宗开始,在继承唐代“律令格式”体系的基础之上,编敕成为新的法律形式,逐渐地“以敕代律”,形成“敕令格式”法律体系。
3.明清“律例”体系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逐渐增多,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需要更为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因时制宜,因事定例”的创例活动成为明清立法的主要特点。在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例”的修订、“会典”的编撰、“令典”的式微,对之前的“律令法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例与律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尤为凸显,逐渐形成“以律、例为主体,包括众多的法形式的法律体系”,[6]即“律例法体系”。杨一凡强调《会典》“大经大法”的作用与地位,认为明清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会典》为纲、以律例为主要形式、以例为立法核心”的框架构建,可称之为“典例法体系”。[7]在基于律例学说的多重学术图景中,一些学者亦对明清律例法律体系进行了学术修订,提出“律令—祖制”[8]“律例—礼仪”[9]“律令—礼法”[10]等不同的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博大庞杂,以上基于律令体系的多重学术研究,多从法典文本角度进行认识,重点关注国家制定法、国家成文法,主要区分刑事法和行政法,根据不同时代法典文本的变化,建构不同的法律体系认知,为认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但在法律体系问题上,“律令体系”鲜有从中国古代法律自身规律出发予以归纳,虽然沿用了传统法律术语概括,在内容涵盖面上难以容纳中国古代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对外关系方面天下之法,只得其一端,难以真正认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全部面相。
二、内容视域下的“部门法体系”
(一)近代大陆法系“部门法体系”的形成
相较其他法系而言,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独具特色,形成了以六大法典为核心的六法全书式的法律体系,徐爱国认为“在法律制度(规范)的表现形式上,大陆法系的六法全书式的体系是非常经典的,是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之一”。大陆法系“部门法体系”以宪法为指导,以私法(民法、商法) 为基础,包含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主要法律内容,编纂相关成文法典,构建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法律体系。
大陆法系“部门法体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期的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划分,罗马法以民法为主体内容,六法中的其他法典某种程度上承接了民法典中没有规制的内容。直至拿破仑时代,1799年颁布《法国宪法》,1804年制定《民法典》,1806年制定《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制定《商法典》,1808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典》,1810年制定《刑法典》,陆续完成了六法法典的编纂,创造了大陆法系成文法典的传统,建构了完整的大陆法系“部门法体系”。[11]之后,德国于1871年完成国家统一,制定《宪法》《刑法典》《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典》《商法典》。日本于1889年开始明治维新,学习德国法治建设,编纂法典,亦形成“部门法体系”。通过大陆法系的世界传播,“部门法体系”成为大陆法系独具特色的标识,影响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其他法系的法律变革与社会革命。
(二)“部门法体系”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殖民化,西方法律观念和政治观念被建构为一种“文明”的秩序观念,从而被赋予普适主义的正当性和规范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的军事、政治入侵,面对西方的法律殖民主义,“西法东渐”成为中国近代法律史的主旋律。
1884年,法国人毕利干翻译了《法国律例》一书,将近代法国的六法全书翻译到中国,亦将大陆法系的“部门法”体系介绍到中国。1901年,清末变法修律开始,以德国、日本法律体系为参考,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典与著作,修订《大清新刑律》(1911)、《大清民律草案》(1911)、《刑事诉讼草案》(1911)、《民事诉讼草案》(1911)、《钦定行政纲目》(1910),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部门法律体系。北洋政府时期在继承清末变法修律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近代中国的部门法法律体系。南京民国政府的立法者总结清末法制改革以来历朝政府在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律,包括《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中华民国民法(总则编)》(1929)《中华民国刑法》(1928)、《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1928)、《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1931),中国近代法律的典型形态——六法体系基本形成,亦宣告中国法律近代化基本完成。[12]
(三)中国古代“部门法体系”的学术建构
伴随着“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浪潮,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隐含的但又“坚实”的假定之上的:以欧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代表的西方法治文明与以中国(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华法治文明形成的巨大反差。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完全遮蔽在西方法学概念、理论、框架的解构之下。西方社会历史类型、法学学科分类体系、法学概念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基础。我们一直以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律价值取向和法律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古代法,以至出现了所谓“外国法律史就是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史反倒成了外国法律史”[13]的局面。
在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问题研究上,现有研究成果是“大陆法系(部门法体系)视野中的中国法制史”。[14]中国法律史的开山鼻祖梁启超首先利用西方近代法学体系、法学理论和法学概念、术语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上从刑法、民法、行政法、司法角度进行论述,开启“大陆法系视野中的中国法制史”的滥觞。梁启超的法制史研究继承者杨鸿烈,进一步建构了“部门法体系”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发达史》以中国历史朝代顺序为经,以西方部门法划分为纬,按照大陆法系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部门法知识分类体系,阐述中国法制自先秦至清末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建立起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西方部门法特征,之后持续影响着中国法律史叙述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法律史叙述延续着西方部门法的分类体系,这一时期,法律史著作、教材纷纷受到西方部门法知识分类的影响,产生了许多研究中国古代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的专题著作。法律史的教材全都采用西方部门法的分类,通过搜寻资料,填补衔接,建构起了中国古代“部门法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至今仍对学界产生重大学术指导的教材,即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该书汇集了21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贤人时彦,以中国历史朝代为经,以西方部门法为纬,“究五千年法制轨迹,集一百年学术大成”,全面建构了中国古代法律世界的辉煌图景,为梳理悠久灿烂的中华法治文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借鉴与学术参考。在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问题上,第一卷的编纂者已经认识到“以部门法总结归纳各代法律内容与制度是西方法律及法学传入中国以后才出现的”,张晋藩先生亦指出“必须明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由若干部门法,如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所构成的,是诸法并存的,也是民刑有分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说在法律的内容上更接近古代的事实,但在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上仍有叙述空间”。[15]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国家的法律体系建构受到西方法律体系的影响巨大,似乎,只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叙述,才能发掘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辉煌成就。
其实这些研究背后都隐隐约约地受到西方费正清“挑战—回应”范式的影响,主观建构式地形成中西法律文明的冲突。如前文所述,西方法律制度只是在17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在欧洲核心区域形成,其中具有典型代表的部门法概念与制度体系,直至拿破仑时代才创建完整的“六法体系”(部门法体系),1799—1810年拿破仑的法典编撰事业确立了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基本模式,而这距今只有短短的200年,这200多年逐渐形成的东西,被19世纪以来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想当然的当作东西方社会永久的鸿沟,由此催生的“部门法学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成为百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从而整体抹杀了中国本土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
三、空间视域下的“国家—民间”二元法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人类学思潮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概念,大传统是代表国家的,是指上层人士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代表乡村的,指在乡村中农民所代表的文化。[16]这一理论概念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梁治平为代表的学者借鉴西方人类学概念、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再阐释,提出了“用文化阐释法律”的学术命题。
国内学者潜移默化地受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古代“二元”甚至“多元”的法律体系框架。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最早回应了西方人类学的中国认知,基于清代宗法族规的实证研究,对比分析西欧庄园法、印度村社法、中国宗族法的异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格局框架中,超越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了宗族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张力,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建构出“国家—宗族”二元的法律图景,为之后法律人类学研究、民间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梁治平在民间法概念的基础上,从民族、宗教、宗族、行会等不同角度论述法律渊源,勾勒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多元体系格局。之后,历史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开展轰轰烈烈的民间法研究运动。尤以中南大学谢晖教授主编《民间法》期刊,每年组织召开“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为深入研究民间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在上述学者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根基“国家—民间”二元理论,在基层乡村、民族宗教等不同背景下,形成“国家—民间”二元法律体系图景,对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以及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学术视角。但我们隐约可以辨识出,这是一个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它区分国家与民间的二元性,强调国家—公共,私人—民间二者之间的分界,本质上是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解说中国历史,[17]建构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
四、官制视域下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其自有的特点与问题,自秦汉帝制伊始,中国便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府体制,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官僚制度。[18]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秦汉创立的“超稳定结构”习惯于官僚体制,是按照官僚脉络组织起来的高度集权化的等级制政府,于法典而言,律典是皇帝告诫官吏如何准确运用刑罚手段对公共职能的行使加之控制的指示。于中国法律史研究而言,“官法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帝国逻辑,法律史学研究必须与行政结构及行政规章结合,方能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真实面貌。
美国学者昂格尔“官僚制的法”,罗威廉“中华法律制度的官僚特征”,李贵连“‘治吏’是中国历代法治的‘宗旨’”,皆以学理阐释了中华法系“行政化”法体系的特征,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基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学术研究而言,“六事法体系”理论[19]以古代官僚体制建构古代法律体系,基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模式,沿着“因事设官、依官制法”的社会管理发展脉络,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从而展现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方式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内部取向”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于中国自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具有独立于其他文明的“中国性”。“六事法体系”理论解构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帝国逻辑——官法同构,认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制度设计方面,“以‘治官’为切入点,通过‘治官’,兼顾‘治民’,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官法同构”摒弃了西方“国家—民间(公私区分)”的市民社会理论,直面中国古代“大一统”集权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官法同构”的制度体系之下,履行管理职责的官僚体系得到法律强制力的支撑,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统治意志通过官僚体系逐级延伸,遍及版图疆域每一角落。同时,同样体现皇权、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法律,则通过复杂的官僚体系网络,覆盖社会生活各领域,实施于州县地方。“官法同构”的国家治理结构,基于官本位的社会关系,使得中国古代国家与百姓之间,通过官僚体制,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大一统”集权的社会理论真正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社会关系问题。
(二)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文本构成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政权采取不同方式处理法律文本与法律内容的关系问题,近代欧洲国家建构了内容与文本相统一的法律体系,以部门法为划分依据,制定了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典等法律文本。“律令”法律体系多从法典文本角度出发,根据不同时代法典文本的变化,建构不同的法律体系认知,但这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内容面相。
“六事法体系”理论将法律文本视为法律内容的载体,认为中国区别于西方,“采取文本结构与内容体系既相互分离、又交叉对应的独特方式”。以清朝乾隆时期的“六事法体系”为例,《会典》《会典则例》、部院《则例》、《大清律例》成为主体法律文本结构。其中《会典》《会典则例》为国家法,具有“大经大法”的性质,全面规定国家的基本性制度与根本性事务。部院《则例》、《大清律例》为部院法,根据国家法的根本规制,细化落实国家法的各项规定。
在法律功能作用的问题上,“立规设禁”成为处理法律文本关系的另一个标准。《会典》《会典则例》、部院《则例》在法律体系中主要“立规”,就所涉及的社会法律关系做出制度性的规定,确定法律行为准则,规定法律运行程序。《大清律例》在法律体系中主要“设禁”,对于违反上述法律行为准则、法律运行程序的行为,进行处罚性规定。“六事法体系”理论以法律位阶、法律功能的分析角度,回应了国内外学者“律令”“律例”“典例”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文本关系问题,为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
(三)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
在以西方部门内容建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划分标准的合理性与妥适性。或许可以做这样一种假设,当我们穿越中国古代任意一个历史时段,跨时空地与古人进行对话,诸如民法、行政法的知识认知,必定难以与古人做到有效的价值沟通。
西方部门法体系下的法律部门划分大体上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为主要标准,分为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法等不同类别。“六事法体系”一改部门法体系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属性,以中国古代职官部门的设置为划分依据,按照中国古代法律调整对象所属社会事项的类型或者领域分类,“理解之同情”,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进行部门分类,形成了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六事法体系”按照中国古代法律对象所属的法律类别,适应当时的政府官僚管理体制,覆盖中国古代文武百官、士农工商全部社会主体,调整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家庭、婚姻等各类社会关系,基本实现了对于中国古代主要法律关系的全面调整与全面覆盖,从而提高了国家治理和法律应用的效率。
总而言之,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六事法体系”理论建构,立足中国语境(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传统),贴合中国观念(中国官本位的价值标准),发掘国家治理的“官法同构”的帝国逻辑,以官僚体系建构法律体系,更加符合中国古代法律的真实状态,也展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鲜明特色。[20]
五、余论
百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无数先贤学人基于不同的知识认知,在西方法典编纂论、西方部门法理论、西方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建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重理论图景,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借鉴历史传统实现法律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学术积累。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乃是依循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演化而成的,具有独特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形式。21世纪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需要学者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中国法律史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需要摆脱作为西方学术投影的存在形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踏上一条艰苦的原创之旅。“六事法体系”理论,基于中国国家治理“官法同构”的制度模式,为创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一定能成功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是我们中国法律史学人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