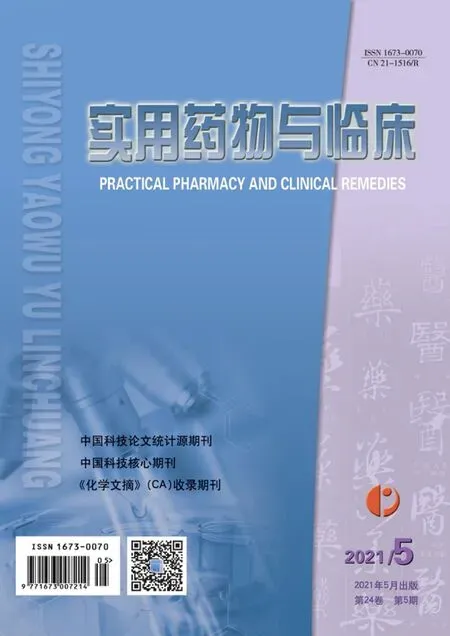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炎症性肠病失应答的研究进展
贺小露,周 青,黄晓晖
0 引言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2种疾病类型。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IFX)是首个用于治疗IBD的生物制剂,能有效促进肠道黏膜的愈合,减少或避免激素的使用,降低手术风险和住院率。然而,临床中部分患者出现对药物的失应答(Loss of Response,LOR),表现为疗效欠佳甚至无疗效。研究显示,10%~30%患者对IFX起始治疗无应答,称为“原发性失应答”,起始应答较好而随着时间推移又失去疗效的称之为“继发性失应答”,据报道在治疗期间出现继发性失应答的患者高达50%[1]。LOR导致疾病复发、手术率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加重,是IFX实际应用中的难题。目前LOR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本文主要就LOR的产生机制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
1 LOR的可能机制
1.1 血清药物谷浓度 英夫利昔单抗LOR的发生与血清药物浓度不足相关。Seow等[2]的研究发现,IFX治疗的患者血清中,可测得血清谷浓度的患者与无法测得血清谷浓度的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69%和15%,内镜缓解率分别为76%和28%,结肠切除风险分别为55%和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项研究表明,无论是诱导期,还是缓解期,更高的IFX血药浓度与较好的临床结局密切相关[3]。一项研究分析了728例中到重度UC患者IFX血药浓度与临床结局的关系,结果显示,临床应答更好的患者的IFX血药浓度显著高于未应答的患者,诱导期(8周)血药浓度大于>41 μg/ml的患者达到临床应答的可能性低于此血药浓度患者的2倍,而维持缓解期血药浓度>3.7 μg/ml可使UC患者获得满意的临床结果。Bortlik等[4]认为,在维持治疗前达到3 μg/ml的血药浓度有助于维持缓解,部分研究则将此临界值设为2 μg/ml。需要注意的是,“达标治疗”的目标不同,所需的血药浓度也不同,例如黏膜愈合需要更高的血药浓度来维持。Ungar等[5]根据回顾性分析将6~10 μg/ml设为达到黏膜愈合的浓度窗口。另一项单中心的横断面研究发现,使肛周病变型CD患者的瘘管愈合的IFX血药浓度至少应大于10.1 μg/ml。IFX血药浓度不足的原因是个体药代动力学过程存在差异,如男性、高体重、低白蛋白水平等因素均可加速药物清除,使血药浓度降低。也有文献报道,在UC患者用药1 d后的粪便中检测出IFX,推测药物可能经受损黏膜丢失,导致药物清除过快[6]。
1.2 抗药抗体 IFX属于人鼠嵌合的IgG1单克隆抗体,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可使机体产生抗IFX抗体(Antibodies to infliximab,ATI)。研究发现,不规律地使用IFX的患者中近60%出现ATI,ATI可导致输液反应以及对IFX的失应答[7]。一方面产生的ATI与英夫利昔单抗结合而抑制英夫利昔单抗的生物活性,另一方面,二者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加速IFX的自身清除[8]。文献报道,ATI的形成使IFX的清除增加2.5倍[9]。目前认为,ATI阳性与较低的谷浓度有显著关系,一项研究发现,77%的患者中IFX浓度在0.00~2.31 μg/ml能检测到ATI阳性,相反谷浓度在14.98~39.59 μg/ml则测不到ATI[10]。需要注意的是,有一部分ATI的产生是一过性的,称为短暂性抗药抗体。短暂性ATI可自行消失且不会导致患者继发性失应答[11],而持续性ATI与药物的临床疗效有关,会引起LOR。
1.3 其他因素 疾病本身对IFX的应答是有影响的,孤立性肠道病变及既往无腹部手术史患者更易对IFX产生治疗应答,狭窄性病变患者应答率较低[12]。一项纳入3 187例CD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使用IFX维持治疗一年内LOR的发生率为36%,伴有肛周病变、发病年龄小、结肠受累是导致LOR的危险因素[13]。另外,炎症程度也会影响药物的应答,Olsen等[14]发现抗肿瘤坏死因子-α(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较高的UC患者达到临床或内镜的缓解率更低,原因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药物去阻断血清和组织中大量的TNF-α,因此,炎症程度高以及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更高的剂量才能达到临床疗效。目前已明确吸烟是CD独立危险因素之一,相对于吸烟的CD患者,不吸烟者对于生物治疗显示出更好的应答[15]。
2 LOR应对策略
2.1 治疗药物监测与ATI检测
2.1.1 治疗药物监测 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在探究药物失应答的机制以及评估IFX的疗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与经验性调整治疗策略相比,以TDM为基础的IFX的剂量优化更具成本/效益比,同时血药浓度监测可预测患者临床结局,与患者生物学、内镜和组织学缓解密切相关[16]。目前临床中多为被动的TDM监测,即患者发生失应答后再进行监测,而主动的TDM监测则是对缓解期患者按计划进行TDM监测。考虑到经济压力和远期的效果,对所有人群进行主动TDM监测目前还存在争议。也有研究认为,与被动TDM相比,主动TDM可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如TAXIT研究显示,根据主动TDM监测的结果,调整IFX用量,可提高患者临床缓解率,或节省治疗费用[17]。目前多数的研究显示,IFX有效的谷浓度为3~7 μg/ml,TAXIT研究对于谷浓度不足3 μg/ml的患者进行了优化治疗,经过优化治疗,患者的临床缓解率从65%提高至88%(P=0.02)[4,17]。在有效的谷浓度范围内,浓度越高临床结局越好。有文献建议IFX的谷浓度≥5 μg/ml能获得较好的临床结局[18]。So等[19]报道了在儿童IBD患者中,IFX的血药浓度应>1.58 μg/ml。
2.1.2 ATI检测 ATI的形成是导致IFX血药浓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监测TDM的同时也需监测ATI的水平。ATI可能是一过性的,一般应根据2次的检查结果进行判断。此外,抗药抗体一般于IFX输注4次后出现,检测时间不应早于14周[20-21]。对于ATI的检测值,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试剂盒的结果有差异。有研究报道了ATI水平为8.0 μg/ml可以作为ATI阳性或阴性的临界值[22]。
2.1.3 治疗策略调整 目前越来越推荐对于IFX失应答的患者采取TDM评估后进行分类处理。IFX谷浓度不足(<3 μg/ml)、ATI阳性,表明患者对IFX产生抵抗,可换用其他的TNF-α抑制剂;无法换用其他TNF-α抑制剂时考虑尝试强化剂量。IFX谷浓度不足(<3 μg/ml)、ATI阴性,可考虑强化药物治疗(增加IFX剂量、缩短给药间隔以及联合免疫抑制剂)。研究显示,提高IFX剂量至10 mg/kg,或缩短输液间隔至4周或6周是缓解LOR有效的方法[23]。另外联用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能通过降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减轻炎症负担等提高IFX的血药浓度,因为炎症负担重和较高水平的CRP均可以加速IFX在体内清除,从而导致其血药浓度过低[24]。IFX谷浓度足够(>3 μg/ml)、ATI阳性,提示患者的炎症过程可能非TNF相关的机制介导,可以考虑换用非TNF-α抑制剂的药物,如硫唑嘌呤或其他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或进行外科手术治疗。IFX谷浓度足够(>3 μg/ml)、ATI阴性,提示治疗失败可能与药物无关,需要寻找其他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
2.1.4 转换为其他抗TNF-α药物 IFX谷浓度不足且ATI阳性的患者,转换为其他抗TNF-α药物时,可重新获得临床应答。GAIN试验发现,对IFX失应答的中重度CD患者在换用阿达木单抗(首剂160 mg,随后80 mg/2周)后,在第4周约21%的患者获得缓解,而使用安慰剂组仅为7%(P<0.001)[25]。随后,ADHERE试验(GAIN的延伸试验)报道了长期应用阿达木单抗96周的缓解率(活动度指数CDAI较基线下降≥100、CDAI<150)分别为39%、26.5%[26]。另一项试验研究IFX失应答的中重度CD患者换用赛妥珠单抗(400 mg/2周)作为二线治疗,在第6周有61%患者获得临床应答(CDAI下降>100分),39%患者得到缓解[27]。多项国际多中心研究均已证实,对于抗TNF-α治疗失败的患者,改用其他作用机制的生物制剂如乌司奴单抗(IL-12/IL-23抑制剂)和维多珠单抗(抗α4β7整合素抗体)均有很好的疗效[28],但我国目前只有抗TNF-α制剂被批准用于IBD的治疗。
2.2 预测LOR的生物标志物 有学者认为,CRP水平能反应IBD患者炎症的负荷程度,同时高的炎症负荷能加速TNF-α抑制剂的清除,因此,CRP可能是潜在的预测LOR的生物标志物。Song等[29]发现,基线CRP水平>1 mg/dl与药物原发性无应答显著相关(P=0.042),另外在Cox风险比例模型中就多个因素对LOR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CRP水平>1 mg/dl同时CRP较基线下降>70%与1年的LOR显著相关(P=0.001)。肠道微生物参与IBD的发病及治疗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及数量的改变可能与IFX失应答密切相关。有研究对维多珠单抗治疗反应不同的IBD患者粪便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维多珠单抗治疗反应良好的CD患者在治疗前携带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其肠道内的罗斯菌和伯克霍尔德菌明显高于治疗失败患者[30]。国内研究发现,中国人群IBD患者肠道菌群的改变模式与西方人群相似,并且分析了中国人群CD患者使用IFX前后的粪便样本,结果发现梭菌目相对较多的患者对IFX反应较好,与单独使用活动指数CDAI预测IFX疗效相比,与CDAI一起可将准确性由58.7%提高至86.5%,因此,作者认为梭菌目可能可以作为预测IFX疗效的生物标志物[31]。Nishida等[32]研究了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率对UC患者使用IFX的疗效预测,结果发现,IFX失应答的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率显著高于持续应答的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率为4.488可以作为预测IFX药物失应答的临界值。可能的机制是中性粒细胞参与IFX细胞膜受体Fc-γ介导的吞噬过程,高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率导致IFX的清除增加,血药浓度降低。
3 结语
IFX在临床应用广泛,但药物失应答是面临的巨大挑战。开展IFX治疗药物监测和ATI的检测尤为重要,通过优化治疗方案尤其是调整谷浓度水平,可使大多数患者重新获得应答,相较与经验性的调整用药剂量或换用二线、三线的抗TNF-α治疗药物更合理,更有利于实现个体化用药。近年来的研究进展提示,一些指标如CRP、特定的肠道菌群、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可作为潜在的预测IFX疗效的生物标志物,但仍需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