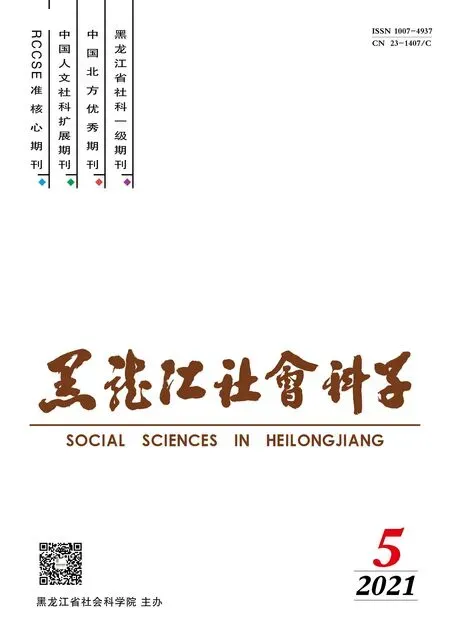从“平一九州”至创建“大业”:隋朝的“大一统”经略
史 话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跨境研究学院,美国亚利桑那 菲尼克斯 85257)
“大一统”一词,始见载于战国人纂述的《公羊传》[1],其思想则可上溯至西周[2]。这一思想经过长久而深厚的积淀,成为指导性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与民族凝聚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学界围绕大一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先秦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形成[3]、秦汉等时代的大一统实践等方面[4]。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观念,大一统思想从初萌到形成完善的体系并具体指导王朝实践,其过程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文明史,其中隋朝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
隋朝成功地践行了大一统理念,终结了三国以来持续三百余年的动荡与分裂,使中国进入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隋唐时代;隋朝两代君主在强化思想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多维度地践行了大一统思想[5]。隋文帝先后废除及平灭了后梁与南陈,结束了中原数百年的乱离状态,实现了“平一九州”;隋炀帝在创建“大业”的过程中,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以及南征东伐,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劳役过繁、穷兵黩武以及奢侈靡费等危害政权良性运转的负面现象(《隋书》给隋炀帝的定位是“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历来史家鲜有质疑)[6],但同时也体现出其对国家整体规划的用心筹谋,显示了政治才能与军事韬略[7]。杨广的施政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与“炫耀性的想象力”,曾被誉为“政治美学家”,他的这种素质使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于野心勃勃的计划”[8]。杨氏父子在经略国家的过程中,无论是固土开疆还是攘外安内,都带有明显的大一统思想特质,对唐及后代的政治观有着深刻影响。然而,学界的相关研究还很有限[9],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隋朝两代君臣的大一统思想
有隋一代,朝中人才萃集:颇具卓识且敢于上疏言事的裴矩、长于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长孙晟、善战多谋的杨素等,皆为践行大一统理念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撑;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作为消弭了南北互不统属、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等多重影响国家一统、四海归附的阻碍因素,底定了隋的天下体系。杨坚在重建统一王朝的同时,也逐渐完善了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格局的思想;在其当政期间,大一统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具备了从认识体系到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入的可行性。杨广不仅承袭了其父留下的治世,也继承了其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全方位体现于天下秩序的构筑之中。
(一)隋文帝君臣的大一统思想
隋朝君臣自建国伊始便尝试构筑大一统的解释体系。开皇四年(584),散骑常侍薛道衡提出“平一九州”“责以称藩”[10]1406的构想:“《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10]1407认为隋文帝圣德天挺,有能力一统中原,并从历史循环论的角度为天下统一寻求依据。梁睿则指出:“拓土开疆,王者所务。”[10]1127君臣理念的高度契合,为隋朝提供了考量天下格局的理论支持。而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提出“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理论,则催动了隋炀帝践行大一统理念的雄心,遂“甘心将通西域”,倾全国之力东征高丽,北通突厥,东南经略台湾,积极扩张隋王朝版图。
隋文帝反复强调自己“受明命为天下君”[11]“受命于天”[10]1843,肩负着维护天下和合为一的使命与责任,有意识地将天命与皇权相联结,并在施政之中体现出来。比如称讨伐南陈是“天诛”[12]307“去华夷之乱”[10]1278,对周边民族实施经略是禀承“天命”[10]1774,海隅的诸藩王则应遵从朝廷的政教和风化。为了维护天下一体,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经略方式:四夷若无离心之意,则卧鼓息烽、戒奢崇俭、轻徭薄赋,“求风化之宜”[10]1278;四夷若有离心之举,或觊觎中原繁华,则必行惩罚——所谓“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开皇十八年,隋发兵攻打强盛但不受节制的高丽,即表达了维护一统的决心。同时,认为“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12]3188,强调天下万民都是皇帝的臣民,而子育万民则是皇帝的本分。基于这种天下共主的自判,隋文帝时期结束了中原三百年以来隔长江对峙的局面,实现率土大同,完成了一统基业。
(二)隋炀帝君臣的大一统思想
隋炀帝在前朝的基础上,矢志于巩固并拓展大一统的基业,年号“大业”即强势折射出了这一理念。
首先,构筑辐射范围更广的天下秩序,自我认同为实现中原万世一统局面的明君圣主之属。隋炀帝将自己与周文武王、汉武帝等贤能君主并列,自认为承担了“永监前载”的历史使命。大一统基业的取得往往是先兵后礼,所谓“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10]78,这种战略思路影响了杨广的天下治理理念。年号“大业”,典出《周易·系辞上传》“富有之谓大业”,也即“什么都有”[13]。隋炀帝的这种自我定位与其个人性格有关。唐太宗曾与魏征探讨隋炀帝,认为其即使不能称为尧舜,也绝非桀纣,魏征则认为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10]95。不过,这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贤明之君应有的品德,却可能是构筑大一统国家所需要的素质。隋炀帝本非嫡长子,系运用权谋使先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成为皇储,得以纂承鸿业。为达到其预设的贤君圣主之目标,杨广紧锣密鼓地实施了全方位的大一统经略。
其次,具有开放的民族思想,希望“戎”与“夏”融为一家、“华”与“夷”没有隔阂。隋文帝时代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国力富庶,然而政局并不安稳,四方之民并没有完全臣服:北方边疆民族的骚动、南方士族态度的摇摆以及东部高丽存怀的不臣之心,皆可谓暗流涌动,故至隋炀帝时期放弃了“息烽收戈”的怀柔性治理政策,转而操戈以统。不同于隋文帝的“用夏变夷”,隋炀帝时期的民族政策气魄上更为宏大,主张“无隔华夷”“混一戎夏”,希望摒弃民族间的隔阂,进而消除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敌意和觊觎,将之纳入到自己的天下秩序之中,最终成就“天之所覆,孰非我臣”的大一统格局。这种跨越华夷畛域的大一统思想,在其后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再次,相比于隋文帝所谓的“天下”即“四海”的理念,隋炀帝的相关视野要更开阔。在他的诏书中,较为频繁地出现了“宇宙”一词,诸如“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方今宇宙平一”[10]64等等。不过单纯依靠文教往往很难实现一统,需要武功作为佐助:对于强悍的边鄙四夷以及叛乱,只有兴兵征讨才能彻底改变四海交争的局面。因此他震慑已经归降的突厥启民可汗,联络西迁的西突厥,安抚在隋和突厥间左右摇摆的契丹,并举国兴兵征讨有不臣之心的高丽、吐谷浑,遣使东南进行探索,力图全面压制周边民族政权,保障隋王朝的东亚中心地位。
隋炀帝受到做“宏放之君”理想的鼓励,在前人一统观的理念之上,形成了其自身对于天下格局的认识与理解。依托富足的国力,他期望超越前代,构建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新秩序,实现“六合为家”的宏阔愿景。
二、隋朝的大一统实践
隋得国于统一北方的北周。杨坚通过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治策略,使东突厥归顺,之后废除、平灭梁、陈,实现了继秦汉之后的再一次统一。隋文帝巩固统一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设立三省六部制、改革府兵制、创立科举制、编制《开皇律》等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推行均田制、“大索貌阅”以及兴修水利、广置粮仓等以发展生产。隋文帝时代,府库盈溢,天下累积的财富足可以应付五六十年的消费[14]。至杨广登基时,隋朝的财政实力已居历代之冠,兼之推行躬节俭、平徭赋等举措,使天下达到了仓廪充实、人物殷阜、士马全盛之佳境。大业四年(608),隋朝有郡190、县1255,户8907546、口46019956,垦田55854040顷。后人对隋朝之富多有评议,如王夫之认为隋的富庶超过了汉唐的盛世时代,钱穆也认为“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15]。这种局面孕育并激发了隋炀帝企望比肩于秦皇、汉武的雄心,也为其开创一统大业提供了优渥的物质基础。隋炀帝时代的大一统实践有着严密的逻辑链。一是固本,“本”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直辖区域,具体表现为:迁都洛阳,可喻为更换并维护心脏;开凿大运河,相当于贯通动脉;三下江南巡视,以笼络人心并保持整体协调。二是安边,并致力于“边疆内地化”,对强盛不受节制的边疆势力不惜动用武力,进行讨伐。通过上述全方位的措施,意图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一)迁都洛阳,通过对政权“心脏”的置换,意图确立更为稳固的天下格局
“国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天子统治天命所定的疆域的中心。”[8]79隋朝前期都城大兴城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曾历经长久的战乱,由于灌溉设施废毁失修,故而农业生产每况愈下,造成当地物资匮乏。因此当地粮食的来源主要是关东,即使皇帝也需要就食于洛阳,粮食“偶然也从巴蜀运输过来”[16]。捉襟见肘的关中经济严重限制了隋朝的发展。仁寿四年(604),杨广登邙山眺望洛阳时说:“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17]回到大兴城后即颁布《营建东都诏》,详论洛阳作为国都的优势:洛阳具有“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赋税等”的地理优势,如果这里成为天下中心,会方便四方诸侯缴纳贡职,符合历史上的王都所具有的“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的共性特征;洛阳是先皇隋文帝乃至古来君王的理想定都地点,只是囿于“九州未一”“困其府库”等因素而未能成行。并且指出,大兴城虽然是隋文帝登基后新建,投入使用尚不足二十年,但地理位置不佳、关河悬远,若有战事,则军队彼此之间难以接应,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一与稳定。此诏从舆论上为迁都做足了准备。
营建东都是隋炀帝在后人的品评中饱受诟病的开始。据《隋书》卷24《食货志》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10]668单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触目惊心,然而仔细分析则并非如此。隋朝的“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如果每个月服役者有200万,以施工时间10个月计,则共有约3000万人参与了洛阳城的修筑,其中死亡者即大约为1200万~1500 万。需要指出的是,杨广即位之初,老幼妇女和特权阶级是不服徭役的,因而殁于营建东都的基本都是青壮年劳动力(《隋书》卷24《食货志》载:“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据《资治通鉴》载,隋文帝末年总户数超过890万,“以口户比五点一七乘之,当有户籍人口四千六百万以上”[18]。如果《隋书》的记载是准确的,则营建洛阳时累死了全国1/3的人口,青壮年人口几乎悉数殁于此役。若果然如此,则隋朝自此无丁可征,隋炀帝后续的诸多重大举措都无法成行。显然,《隋书》的数据有夸大之嫌。而据《北史》所载,为营建北魏京师所征役丁约有5.5万人,筑京师320坊,约40天而罢。北魏京师占地,东西20里、南北15里,面积仅为隋朝东都的一半。又据《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所建之东都并无外城,外城系由唐朝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因而,隋炀帝修筑的仅有短垣的东都,工程量并不大,完全在隋朝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迁都洛阳,更便于对天下的治理,体现了大一统帝国对四方臣民抚之如一的理念。虽然大兴土木不可避免地给百姓带来了巨大困扰,但此举对后世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开凿大运河,疏通南北交通动脉
在为帝国置换新的“心脏”的同时,隋朝君臣还搭建并疏通配套的“动脉”,以保持帝国活力——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应运而生。历史上,往往将隋朝开凿运河的主要动机说成方便隋炀帝观赏江南的琼花与搜罗美女。虽然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毕竟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前揭张昆河文)[7]。改革开放以来,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渐趋公允,认为此举意在巡历淮海、安辑河北(前揭李筑文)[6],改变“关河重阻,无由自达”的状况,以达到“协同归心”的政治目的[19]。
文献中没有关于隋运河修建方式和过程的翔实记载,仅提及先完成南段,再贯通于北。从后世治淤的情况判断,大运河的修凿耗费人力物力巨大。元朝时期,为解决通惠河旧址淤塞的情况,“不用一亩泉旧原,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20]疏通仅164里长的通惠河便如此大费周章,隋朝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起来,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途经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8省市,全长约2700公里,其修造之曲折艰难可以想见。
综合来看,隋朝修凿大运河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认为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则纯属后人忖度。大运河通航之后,中原王朝实现了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一体化经营的目标。一方面,以洛阳为中心,将历代所修沟渠和运河连通,并使其与自然地理固有水系相互交织,从而将中原连为一体,促进了南北方人口的流动与融合,南方人口由此迅速增长。到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的人口数量已几乎持平;唐末宋初,北方与南方人口比例逆转为2∶3,之后南方长时段维持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21]。另一方面,大运河的通航使南北得以贯通,促进了地域的均衡发展。唐末以降,中原王朝呈现出经济重心在南、政治军事重心在北的态势,而大运河则是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运河盛衰与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可以说,修建大运河是隋炀帝围绕大一统理念所做的直观白描,也是他践行大一统理念的重要一环。
(三)巡行南方,巩固统一
杨广即位之后,意识到江东诸帝没有遵循天子巡狩之古礼、耽于后宫欢娱是导致王朝不能享祚长久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把巡行作为控制庞大帝国的手段之一,在位期间东巡西幸,靡有定居。最值得关注的是其数下江南,这其中自然蕴含着他的江南情结:13岁受封晋王,19岁出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20岁率军平灭南陈,实现南北统一,坐镇江南直至35岁登基;他在南方屡立战功,且结好于江南士族,并通过受戒等举措获得南方佛教徒的拥戴,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隋炀帝南下巡行共计三次,每一次都有其政治背景。大业元年八月至次年春三月,是其登基后的首次南行,意在安抚并凝聚民心。秋冬的江都,气候阴冷潮湿,并不舒适,也并非景致美丽的季节。单纯从时间上判断,此行定然不是为“胜游”[秦韬玉《隋堤》:“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阴埋野色万条思,翠束寒声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苑,东波终不反龙舟。远山应见繁华事,不语青青对水流”(《全唐诗》卷 670)],抑或满足游幸之私意。大业六年三月,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的大运河北段永济渠竣工,在议定亲征高丽之前,杨广第二次南行,期间宴请江淮父老与百僚,意在稳定南方民心。次年二月,来到涿郡并颁诏声称将欲问罪于辽左。从江南归来以及出兵辽东,这二者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关联,而运河则是有机连接二者的关键所在。隋征高丽的1103800大军以及大量辎重皆在短时间内集结于涿郡,永济渠承担了重要的运输通道的作用。大业十二年七月,隋炀帝第三次巡行至江都。是时义军蜂起、天下危困,隋炀帝驻跸江都系意欲保全隋的半壁江山、再图霸业。
尽管隋朝结束了中原地区自东晋以来的分崩局面,实现了国家一统,但民族隔阂与对立的状况依然存在。隋炀帝意在通过横向迁都、纵向疏河以及动态巡行等方式,使大一统的局面得到巩固,胡汉之间趋于凝聚,“非我族类”的意识弱化并走向消弭。
(四)以武力经略周边蛮夷,致力于“边疆内地化”
隋朝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实施行政干预和军事打压并用的手段,有效地扩展了周边领土的缓冲区,确保了边疆地区的安全。
其一,东征高丽。隋炀帝的四夷经略理念承袭自隋文帝,体现出明确的四海之主的大一统意识。其经略对象包含突厥、契丹等,着力最大的则是高丽。在存国的7个世纪中,高丽大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友好关系[22],虽然期间多次尝试性挣脱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但总会旋即重新朝贡,尤其是对南北朝时期的各政权皆事以臣礼,体现了其多面逢源的周边关系协调能力。而在中原政局离乱之时,其趁势向朝鲜半岛拓展疆土,势力越来越强。隋初,高丽频繁遣使,行臣礼甚恭。但在陈被隋灭亡之后,高丽则起兔死狐悲之意,进行战略准备以免蹈陈的旧辙。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给高丽,强调“天子”与“人臣”的差别,指责高丽作为“藩附”却“心在不宾”,明确警告其如果不守臣职,则隋朝会施以武力。至杨广登基,态度便更加明朗。
在隋朝君臣的视域中,高丽的属性有三个考察层面[23]:从地域的角度,自商周起至汉晋止,其所在皆是郡县之地,属于华壤及“冠带之乡”;从政权的角度,高丽是中原王朝的“藩附”,有朝贡的义务;从华夷的角度,高丽与中原王朝是“列星”与“太阳”的关系,其附属地位是由传统理念所决定的。尽管高丽势力渐趋强大,但无论其偏居浑江流域,还是拓展至大同江流域,其势力范围始终未超出周汉以来大一统版图,而且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当高丽诱纳中原亡叛之徒、拥兵边垂、阻塞朝鲜半岛部族假道朝贡之路,并侵犯靺鞨、契丹等民族,甚至与突厥暗中勾连抗隋等事件频繁发生后,隋炀帝遂决定兴兵以维护一统:大业七年、九年、十年,三次亲征高丽。不过由于耗费巨大,导致中原呈现乱局,且军中将士逃亡者络绎于道。而高丽虽然没有被隋军攻破,然而民生愈发艰难,甚至出现野无青草的惨状。这场战争对隋与高丽都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创伤,隋的国祚短促与其有直接关系,而高丽也自此一蹶不振。
其二,对契丹与突厥等北方民族的治理。契丹自北魏显宗时起,便向中原王朝贡献名马文皮,并渐成制度。隋开皇三年,契丹与靺鞨等族共同兴兵反隋,没有取胜,契丹诸莫贺弗率部4000家归降隋朝。杨广初年,契丹寇抄营州,遭遇隋将韦云起所率包括突厥启民可汗部众在内军队的打击而惨败,隋朝获契丹“男女四万,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男子悉杀之,以余众还”[24]。不过,无虏而还表明隋炀帝政策存在失误,周边民族入寇说明隋朝的控制能力还有不足。而在唐朝的怀柔与羁縻政策下,契丹各级首领不仅是世袭的都督、刺史,同时也有一定的自主权。不过据《资治通鉴》载,唐玄宗天宝四年(745)九月,契丹也曾杀害和亲公主反叛。因此,杨广恩威并施经略四夷的手法有其高明之处,但限于时代等因素,失败也在所难免。
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中的突厥兴起,并逐渐成为威胁最大的外族[25],颇有轻慢中国之意。隋文帝时期,曾扶持相对顺服的启民可汗以制衡他部;在与启民可汗联合击溃契丹之后,还将契丹人畜赐给启民可汗,以提升其实力及威望。大业二年,启民可汗赴洛阳朝觐隋炀帝,隋方则大陈文物以耀威于戎狄之间。大业三年,启民可汗带领臣僚入朝,上表“请袭冠冕”,表达了易华服的文化认同与永为藩属的政治态度[26]。而隋炀帝为巩固一统,也陈兵耀武,北巡突厥。启民可汗遣子觐见隋炀帝,并奏请奉迎舆驾。针对突厥骑兵行军灵活的特点,隋炀帝放弃传统的长阵,转而采用机动的方阵,起到了震慑突厥的效果。隋炀帝肯定了启民可汗“受正朔,袭冠解辫”的态度[27],不过却以“夷夏殊风,不求变俗”、应“各尚所宜”为由,没有同意其更易蛮服的奏请:“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10]1874
7世纪初,东突厥兵强国富,西突厥则强势不受节制,在周边部族之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吐谷浑唯突厥马首是瞻,契丹亦服属突厥,高丽则与突厥暗通款曲,从而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压力。为阻止突厥进一步壮大,进而与他族联合威胁隋朝,隋炀帝遂沿袭其父“离强合弱”的战略以稳固北方。
其三,西向恢复丝绸之路。魏晋以降,西汉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西域诸国互相吞灭,与中原的交往一度弱化。大业元年,隋炀帝派裴矩赴张掖经略西域诸蕃,裴矩“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28]的说法也激发了隋炀帝开远夷、通绝域的热情。为了复通西域,隋炀帝先后四次派裴矩到张掖、敦煌等地,以促进西部诸蕃同中原展开贸易,并给以厚利,高昌、伊吾、龟兹等国由此也纷纷遣使朝贡。同时,隋炀帝也多次亲巡西域。大业五年,隋炀帝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隋朝版图由此扩大了方圆数千里。尽管隋与30多个西域政治势力明确了朝贡关系,同时建立了使者往来机制,但隋炀帝对于天竺、拂菻等未能宾服尚感遗憾。
其四,关注东南。大业三年,隋炀帝派遣羽骑尉硃宽出使流求(今台湾岛),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大业六年,隋炀帝派武贲郎将陈棱等率兵万余人,前往流求,但言谈不睦以致兵戎相向,数千名当地居民随隋军返回大陆;在今海南岛设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遣人到安南、占婆等地探查,加强了隋与今东南亚地区的往来。
隋炀帝即位前,曾坐镇江南十余年,竭力安抚士人,消弭南方的离心倾向。即位后,他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经略西域,向西北拓土千里;三征辽左,意图恢复汉代旧疆……在其努力经营下,当时西域朝贡者多达30余国,南荒也有10余国,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期间也曾数次遣使入隋。虽然唐太宗认为隋炀帝“骄暴”,但对其功绩也是充分认可的。
三、对隋朝两代君臣大一统建构的反思
隋朝享国37年,其中,以8年之功结束了南北朝的乱离状态,实现了全国统一,而为完善大一统建构所进行的努力,则可谓从始至终。
首先,隋朝在“统”的过程中,致力于“一”。隋朝在“统”的实践中可谓付出甚多,所建构的大一统思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终隋一朝,大一统局面并未真正实现,相反在民心与国力方面都受到了致命损耗,故而在后人的品评中,隋文帝有“仁”称,而隋炀帝则往往被定位为“苛、急、暴”。这样的评价有客观的一面,但也包含有唐代官修《隋书》的主观刻意。事实上,不能否认隋朝君臣围绕大一统理念在“思”与“行”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虽然由于隋炀帝急于事功以致民力疲敝,但其根本的出发点则是为了践行大一统理念。大业十三年,黄河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水患,造成社会动荡,以致“人相啖食,十而四五”[10]673,可谓使隋朝雪上加霜。由于诸多宏大工程及举措皆在短期内难以看到效益,而操之过急却使得负面效应凸显,遂导至天下动荡、民心尽失,政权走向覆灭。
其次,隋朝消泯了南北隔离,促进了天下一体以及民族融合。西晋之后,中原地区进入了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政局分裂时代,期间胡人南下,汉人则为躲避战乱而纷纷南渡,造成南北之间从民族到政权的全方位对立。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原之后,杨广承接父业,努力将一统的基业扩而大之:开凿大运河,使中原得以被南北贯通的动脉所凝聚;三下江南,聚拢当地人心,使其对隋政权保持诚服;重通西域、用兵辽东,意在恢复汉代旧疆。
再次,隋朝的大一统实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承上启下之功,给后世的天下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隋朝消灭了其前人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8]53综合来看,隋朝从构筑起“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要荒咸暨,尉候无警”[10]55的强大帝国,直到气数耗尽、德运终结,可称“细节丰富、过程丰满”,但时间上未免过于短暂。不过有学者指出,即便隋的动乱与早亡祸起于隋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于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29],而隋朝君臣的功业以及所绘制的帝国蓝图,“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于慎行:《谷山笔麈》)
最后,杨广被“炀”这一谥号污名化了,应该正确评价这一历史人物。杨广即位时立国不久,不同于西汉初期经济凋敝,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方有武帝行大有为之政的状况;隋朝社会财富积累过程较快,给予了杨广实现大一统功业的可能性。但立意做新一代秦皇汉武的杨广过于急功近利,频繁兴兵、大兴土木,反致“大业”未成。杨广去世之后,其孙杨侗曾谥其为“世祖明皇帝”,而据《逸周书·谥法解》,谥为“明”,或指“照临四方”,或指“谮诉不行”,其孙当取前者之意。也就是说,隋朝人对于杨广的认识还是正面的,肯定了他的大一统之功。至唐朝,方改谥其为“炀”。所谓“炀”,谥法上指“去礼远众”“好内远礼”“好内怠政”,对应杨广的行止,可谓都不恰当。值得注意的是,杨广本人曾谥陈后主为“炀”,而“……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30]的陈后主则的确可当此谥。因而,唐人恶谥前朝末帝,未尝不包含别样情愫,并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此举却有误导后人千余年之嫌。
出身关陇集团的杨氏,结束了自三国历经两晋五胡十六国以迄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分裂,实现了“平一九州”。为巩固并完善一统“大业”,隋朝从文治到武功、从中心到边缘,进行了全方位的经营:营建东都以固本、征讨高丽以靖边,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南北……隋朝也由此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磅礴气象。不过,由于杨广障目于大一统的宏图,忽视了诸多客观现实,从而使“大业”中折,原本“天下丰乐”[31]的杨隋一朝也在烽火相连中大大消耗了国力,最终由李唐王朝所取代。始自唐朝的对隋炀帝的恶评,使得后世在考察其一生功过时多集中于挞伐其荒淫与奢靡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大一统探索在民族凝聚与疆域底定过程中的贡献。无论是从思想体系层面,还是从具体实践角度来看,隋朝的大一统建构都直接影响了唐朝,为唐朝成为古代东亚世界凝聚力和辐射力最强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