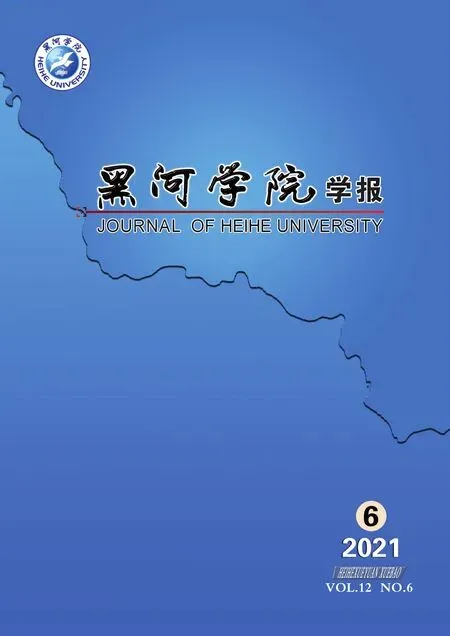伪满洲国时期李乔话剧的创作背景及特点
任金凤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东北戏剧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此时东北戏剧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随着日伪占领东北,东北沦陷,很多有识之士以笔为刀,对侵略者的暴行和底层大众的悲惨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话剧作为一种贴近现实、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形式,在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东北沦陷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一大批优秀的话剧创作者应运而生,李乔便是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话剧创作者之一。李乔1919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原名李公越,李乔则是他的笔名。在创作初期,李乔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写作,到了1937年,李乔逐渐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并与当时小有名气的话剧作家田菲、成雪竹、徐百灵、安犀成立了“协和剧团”,成为当时满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李乔自称为“戏剧的信徒”,其话剧创作注重实践。1939—1942年的3年时间里,李乔相继创作了《下等人》《大年初一》《不良青年》《团圆年》等多部话剧作品,这些作品经编导后都进行了舞台演出。纵观李乔创作的话剧作品,大多反映了现实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或是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东北沦陷后,李乔的话剧创作开始倾向于对伪满众生相的描写,表达了其对侵略者统治的不满,因此,研究李乔的话剧也能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东北沦陷区文学创作,尤其是话剧创作的初衷、特点和目的。
一直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东北作家的关注度并不高,尤其是对东北话剧创作者缺乏重视,沦陷区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汉奸文学”,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民众、启发民智、渴望沦陷区民众能够获得思想解放和觉醒的话剧创作者无疑是不公平的。李乔是一个演员,是一个导演,同时也是一名编剧,其所创作的戏剧既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又充满了矛盾与纠结,其中的很多内容既饱含了自己勇于反抗殖民统治的家国情怀,又有迷茫、无奈的迎合,但无论如何,李乔话剧对东北沦陷区生活场景的刻画,以及对殖民统治下东北沦陷区“众生相”的描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些话剧进行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了解东北沦陷区的实际情况,也能够了解当时话剧作家复杂的精神状态和无奈的文化选择。
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话剧创作初期,李乔的话剧大多是批判社会不良风气,以及人们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希望能够通过话剧来达到教化的目的,形成敦风化俗的效果。《黑白线》是一场独幕剧,该剧对社会上那些为了攫取金钱、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颠倒黑白的投机者进行了批判。剧作《谁是谁非》则是讽刺了那些道貌岸然、两面三刀的伪君子,揭开了“假绅士”的虚伪面具。独幕剧《时代儿女》则是告诫现代青年男女要敢于突破封建思想的枷锁,改正封建文化中的陈规陋习。独幕剧《大年初一》和《团圆年》则着重刻画了底层贫困人民在新年到来之时,虽然已是家徒四壁,无隔日之粮,却还要想方设法地“摆一摆”,象征性地过个团圆年的悲惨境遇。通过这些剧作可以看出,李乔的话剧创作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渴望能够利用话剧这种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来达到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作用。
后期的创作,李乔的作品创作技巧更为圆熟,并非总是直接与殖民者进行抗争,也常常会用某些意向来喻指殖民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而“夜”便是最常用的意象之一。在李乔的作品中,“夜”反复出现,这种灰暗的笔调让人感到无助和苦闷。正如当时的社会一样,只要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东北人,都像被无尽的夜的黑暗包围着,看不到光明未来,能感受到的只有生存的压抑。李乔自己也说过“在笔上生活的人十有八九生活是暗淡的”。因此,李乔的很多话剧标题都是与“夜”相关,如《夜歌》《夜路》《荒村雪夜》《夜深沉》等。而这些话剧的故事也基本都是在夜里展开的。《夜火》的故事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展开的,黑暗的天空挂着有着微弱光亮的月,昏暗的街道亮着孤独的街灯,这种巨大的黑暗和渺小的光亮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一种压抑的、令人窒息的凝重氛围与话剧的戏剧情节交相辉映。《夜火》的主人公是年轻的一男一女,男主人公赵勤,女主人公小铃,这两个人都是具有独立和反抗意识的青年,两个人互相帮助,共同走上了逃亡之路,通过描写两个人的坎坷命运来揭露殖民者统治下东北地区的本质——充满剥削、压迫与迫害的社会,有力地揭穿了殖民者竭力宣传和营造的“王道乐土”的假象,让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暗如黑夜、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光明的社会中。在《夜火》的结尾处,作者通过燃起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来照亮黑暗的夜空,寓意着广大民众可以通过觉醒和反抗来获得重生的希望。
在李乔的话剧中,“夜”不仅仅代表了黑暗的社会,更代表着人心中的黑暗面,因此,在李乔的话剧中也有很多表现人性之恶的情节。例如,在《欢乐之门》中,妓女雪玲在黑暗的夜色中接待嫖客,《团圆年》中的刘四因为活不下去只能到村里打家劫舍,《荒村月夜》中的张士诚为了抢女人而杀人,《夜歌》中的周先生染上了毒品,为了能够吸上吗啡,竟然将自己的母亲活活气死。这些故事情节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夜幕里的点点星光无法驱散黑暗,给人以一种想要反抗却又深感无力的窒息之感,这既是作者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呈现,又是当时东北民众生活境况的缩影。
二、对摧残“善”与“美”的控诉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在李乔的戏剧中,这样的“毁灭”随处可见,在殖民统治下的东北,黑暗的社会将所有善与美的事物打碎,越是善良的人、越是恪守道德的人,越会受到压迫和剥削,而那些蝇营狗苟、不择手段的人,则能够平步青云,这种好人受难、坏人当道的社会让人感到悲哀。
在李乔的话剧中,善良、勤劳的劳动人民常常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导致自己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而当他们想要伸张正义时,却又困难重重,或是官官相护,对他们不管不问,或是遭遇当权者的镇压,不让他们反抗,而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却始终可以逍遥法外,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悲惨境遇下,那些本来勤劳、善良的底层人民只能凄凉地死去。在话剧《黑白线》中,文化月刊的经营者士敏是一个勤劳肯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于书籍、报纸的接受度不高,因此,文化月刊的经济效益并不好,为了能够让文化月刊继续经营下去,不至于倒闭,士敏不得不四处奔波,还要向自己的父亲借钱,而父亲却把钱给了老何,一起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结果老何携款潜逃,留下了一大笔债务,而老何的妻子、士敏、士敏的父亲这些没有作恶的人,却不得不背上了还债的负担,他们的生活变得愈发困苦了。
在话剧《下等人》中,方志平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兢兢业业地在杂志社工作,希望能用自己的才华把杂志社做大做强,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胡二爷利用自己妹妹美林将方志平的全部家当都骗个干净,又不断挑拨方志平与杂志社社长的关系,最终胡二爷成为杂志社的编剧,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来骗钱,正直的方志平无法容忍这种行为,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辞职。
无论是《黑白线》中的士敏,还是《下等人》中的方志平,他们都是有文化、有理想、正直善良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和谐、充满正义的社会,他们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美好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遭受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苦难,而老何、胡二爷这些投机钻营、内心邪恶的人却都混得顺风顺水,这种不合理的人物命运的设定恰恰是李乔对殖民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细心观察的反映。
除了善良与邪恶之间的冲突之外,李乔在话剧中还善于通过善良与邪恶之间的转换来展现人性,通过暴力、仇恨的悲惨事件来描写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展现了特殊情况下扭曲的人性,这无疑也是一种悲剧。例如,在《荒村月夜》中,农民张士诚在充分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中无法生存,于是铤而走险成为匪徒,甚至不惜杀人害命。原本老实本分的农民最终却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这种从善到恶的转变既是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刻画,也是对现实社会扭曲人性的控诉。
三、对伪满国策的附逆创作
李乔的话剧创作大多是着眼于殖民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生活现状,以及社会问题的,这对于针砭时弊、开启民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日本殖民者对文化施压是无法逃避的,因此,李乔在话剧创作过程中,也无奈地创作了少量迎合伪满国策的内容以求自保,体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主要是由作者在爱国情怀与时局现状之间的游离所导致的。正如李乔所说:“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在沦陷地区的特殊环境中写作,唯其特殊,我才想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抑郁情怀;唯其特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受着许多制约,难免粗糙,难免形成一些畸形儿”。
在李乔的附逆话剧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克尼》和《协和魂》。该话剧的主要内容是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为了能够完成该发明,使无线电早日问世而终日忙于工作,甚至因此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长达七年的科研工作,最终实现了远距离无线电传播。无线电是日本殖民者对东北人民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工具,也是殖民者来体现科学进步的载体之一,这一点在《马克尼》中也体现得比较明显,例如,该剧有这样一段对话:
梅茵雅弗丽:“听说满洲不是很落后吗?”
孔耶尔士:“以前是很落伍的,自从建国之后,他们的进化非常快,只拿无线电说,几年之间,差不多全国普遍了”。
从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马克尼》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日本殖民者统治和改造的“优越性”。
如在《协和魂》中这样表达:在秋汛即将到来的时候,全村都有可能被洪水淹没,想要避免出现这一毁灭性的灾难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拉闸泄洪,但是如果闸被拉开了,洪水就会迅速倾泻而出,那么拉闸的人就会瞬间被洪水卷走,生存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没有人愿意去承担拉闸的责任。在这关键时刻,常常被村民排挤的朝鲜人——老韩主动请缨,将闸门拉了下来,挽救了全村人的财产和生命。这部话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十分鲜明的,但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本村本族的人,常常是自私的、排外的、胆小怕事的,而深受全村青年喜爱的女性蓉子和勇敢拉闸的老韩都是异族人,这其实是在向观众传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异族人常常是优秀的、上等的,他们理所应当受到他人的爱戴和尊重,这种观点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政策遥相呼应,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殖民叙事。而在这部话剧的结尾,作者借刘村长的一番话将这一观点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
刘村长:“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总看不起外来人,更排斥不同的民族,可是一旦大家遇到了危急,遇到了正事,就没有谁肯出头去办,更没有谁肯牺牲,现在倒是人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把我们大家救了,拍拍良心,我们不惭愧吗?”[2]
从这两部话剧可以看出,李乔所创作的附逆话剧,一个主要的逻辑便是:东北地区是蛮荒的、落后的,生活在这里的民众是愚昧的、野蛮的,而异族则是进步的,异族人是勇敢的、文明的[3],因此,东北需要接受异族人的改造,这实际上就是迎合了殖民者的殖民叙事需要。
然而,作为有良知且具有丰富经验的话剧创作者,李乔的附逆话剧与为殖民者歌功颂德、宣扬战争和改造合理性的话剧作品也有明显区别,李乔的话剧对日伪政策的宣传是极尽隐晦的,常常是通过点染的方式来完成,在“应命”创作话剧时,也常常会用生活化的方式来淡化作品的政治化色彩,冲淡作品的政治意图,以此来拉开与殖民者意志的距离。例如,作品《夜歌》《大地的呼唤》等。
作为扎根于人民群众的话剧作家,李乔的话剧体现出了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作品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人们展现了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的黑暗社会;二是对殖民者摧残“真”与“善”,包庇“恶”与“臭”的丑陋行径进行无情控诉;三是迫于压力,创作了部分附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日本殖民者的国策,为伪满官方宣传“日满协和”的理念提供了载体。总而言之,通过李乔的话剧,人们既能够看到当时话剧创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殖民者统治的憎恨,又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政治夹缝中的迷茫与挣扎,这不仅是李乔一个人的精神矛盾,同时也是许许多多东北沦陷区文人的无奈却又现实的生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