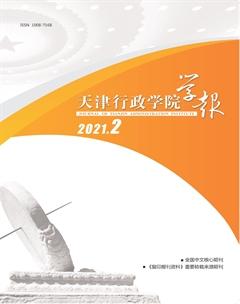国家兴衰、包容性制度与全球平等
高景柱
摘 要: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论是一种用于分析国家兴衰之源的重要视角。这种制度论认为制度可以被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繁荣,汲取性制度应该转向包容性制度。该制度论存在一些解释的限度问题以及一种循环论证的倾向,在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全球正义,是一种解决全球不平等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关键词:
国家兴衰;包容性制度;包容性发展;全球正义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2-0003-08
在关于国家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些国家走向兴盛而有些国家走向衰落?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这种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有不少观点被用于解释国家兴衰的根源,地理環境决定论就是一种较早出现的观点,孟德斯鸠是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强调寒带的国家热爱自由,热带的国家热爱专制,“当我们看到,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异。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1](p.273)。地理环境决定论还通常主张,寒冷的气候会刺激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国家也会因此发展较快,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会抑制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国家也会因此发展较慢。同样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国家兴衰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不认可这种观点,而是强调“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2](p.15)。实际上,在戴蒙德看来,地理环境仍然对国家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国家的兴衰,例如,马克斯·韦伯曾在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探讨了新教伦理在西欧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心态的担纲者,不但绝不仅止于、或者主要是身为商贸贵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毋宁大多是力争上游的产业界的中产阶层”[3](p.40)。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从分利集团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兴衰,从分利集团的发达程度和国家活力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影响国家兴衰的因素[4](p.56)。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强调了制度对国家发展和兴衰的重要意义,“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5](p.3)。在诺斯的推动下,用于分析国家兴衰的制度视角愈发具有影响力,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继承诺斯的观点以及批判上述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论等观点的基础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将制度视角发扬光大,提出了解释国家兴衰的“制度决定论”,他们将制度区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和“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国家兴衰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兴衰的制度阐述的内在逻辑、缺陷以及发展趋向,将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兴衰与制度类型
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用于解释国家兴衰之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赞同,他们主要通过一个例子进行反驳。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诺加利斯城被一道栅栏分为两部分,栅栏北部的、位于美国境内的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居民拥有的生活水准,要明显高于栅栏南部的、位于墨西哥境内的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居民拥有的生活水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两块地方起初就属于同一个城市,有着相同的地理环境、气候以及疾病,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可是它们之间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其中的原因归结为制度,“诺加利斯属于美国的部分实行的是美国制度,能从这些制度激励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商业中受益,而诺加利斯南部则缺少这些”[6]。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炼出了一个关于国家兴衰的重要命题,即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采取的制度通常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二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同时强调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决定一国兴衰的关键影响因素,“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我们就把这种制度称作汲取性政治制度”[7](p.56)。换言之,包容性政治制度应当满足国家要足够集权以及多元化这两个必要条件。我们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言说的“足够集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制政体下的集权”是不同的,他们在这个地方采纳了韦伯的国家概念,即“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性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8](pp.52-53)。那些没有合法垄断国内暴力的国家(如索马里),便不可能维护国内秩序、提供公共物品,更不可能发展经济。对这种国家来说,实现国家的兴盛只能是一种奢望。包容性政治制度应当满足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多元化,多元化指的是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政治权力受到其他权力机关、社会团体等组织的监督和制约,民众拥有政治权利。与包容性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制度是汲取性政治制度,诸如索马里这样没有合法垄断国内暴力的国家制度只是一种汲取性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民众既缺乏投票权,又缺乏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途径。
经济制度可以被分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前者“必须具有保护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性,能够为人们交易和签约提供基础;它还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7](p.52)。换句话说,安全的私人财产权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核心,在此制度之下,人们拥有投资和努力工作的激励机制,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阶层)都可以获得可靠的财产权,都可以获得成功的机会。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逻辑,汲取性经济制度处于经济制度的另一个端点,当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时,私人财产权就得不到有效保护,民众没有投资和扩大生产的动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不存在,少数精英人物通过垄断机制,将经济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虽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明确说明他们采取何种标准将制度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但是通过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之间的主要差异是,政治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以及政治权力是为了少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了广大民众谋利益。在包容性制度下,政治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制约,政治权力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而在汲取性制度下,政治权力通常得不到有效制约,其主要目的是剥夺广大民众的财富,使得少数精英阶层从中获益。
如果我们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获得四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组合形式,也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非常推崇的一种组合形式。以包容性政治制度为基础,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篡权和破坏包容性制度的基础更加困难。控制政治权力者也不能够轻易运用这种权力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同样,包容性经济制度使资源分配更加平等,有利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续”[7](p.57)。易言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局面。一方面,以包容性政治制度为根基,包容性经济制度被建立起来的难度并不大。其中的缘由在于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之下,政治权力是较为分散的,不可能被哪个人或哪个组织单独掌握,民众享有政治参与等政治权利,民众、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等可以一起监督政治权力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不利于广大民众利益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是较为困难的。另一方面,当包容性经济制度被建立起来后,民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就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较为充足,民众反过来也愿意为包容性政治制度提供某些支持。
与第一种理想的组合形式相对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是一种最不理想的组合形式,这两种类型的制度很容易相伴而生,这也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最不赞成的一种组合形式。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少数精英既掌控着所有的政治权力,又掌控着选择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的权力,能够挑战这种权力的力量几乎是不存在的,“汲取性经济制度使这些精英阶层致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又帮助巩固他们的政治优势”[7](p.57)。同时,少数权力精英在这种经济制度中通过不当手段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以及资源,自己掌控的政治权力也会因此在短期内变得更加牢固。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相互支持一样,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之间也会相互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民众的利益通常得不到任何保障,国家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是一种介于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之间的组合形式。虽然汲取性政治制度整体而言倾向于设立一种汲取性经济制度,但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情况,在某些國家确实出现过,比如,一些仅仅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国家或者一些政治改革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步伐的国家。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包容性经济制度之所以没有完全绝迹,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包容性经济制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进步,当权者需要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资源,倘若本国经济非常落后,也就意味着当权者可以掠夺的资源非常少。二是从事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难度,肯定要远远小于将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变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政治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难度。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有一种减少精英阶层从改革中获取利益的倾向,在这种组合形式中,一旦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掌控者不能在实际意义上控制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后果,包容性经济制度便会走向终结,在这种组合形式中,国家的发展是不稳定的。
第四种是在现实的国家生活中难以出现的组合形式,即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该组合形式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因为一旦政治制度是包容性的,政治权力被广泛分散,受到有效监督,不会被滥用,此时建立一种只为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的汲取性经济制度已经大体上没有任何可能性。如果这种经济制度出现了,那么它所谓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便不是真正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二、国家繁荣之路:从汲取性制度到包容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解释国家兴衰时极为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制度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诺斯以前的一些思想家,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等。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先驱,斯密等人关注制度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斯密强调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发挥的作用,弗格森关注制度的演化,休谟关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立足的制度怎样被置入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之中[9](p.40)。与休谟、斯密、弗格森以及诺斯等人的研究进路相比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兴衰的制度解释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从制度这个单一因素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兴衰,强调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着力探讨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对国家的不同影响。
虽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分析国家兴衰的过程中不断申述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汲取性制度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排除汲取性制度下经济出现增长的可能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汲取性制度下经济有可能出现增长,甚至在某个时间段内会有较高速度的增长,然而,这种增长难以持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存在着两种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汲取性经济制度下,当精英阶层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将资源直接配置到为精英阶层掌控的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中时,增长就会出现。例如,在17至18世纪的海地和牙买加就曾出现过这种增长,这些地方当时盛产食糖,奴隶是主要的劳动力,少数大农场精英掌控着所有的政治权力,奴隶的生活条件恶劣,这并没有妨碍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食糖被销往世界各地。然而,这些地方缺乏创新,奴隶没有劳动的积极性,当新经济出现时,这些地方的经济也就出现了停滞。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增长的苏联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增长迅速,工业化飞速发展,在军工等领域中,苏联可以同美国抗衡,当时无论苏联的政治制度,抑或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汲取性的,虽然国家可以动用自己手中掌控的专断力量,通过人为的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将资源从一些使用效率很低的领域(如农业领域)转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的领域(如工业领域),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无法持续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苏联的高速增长就基本上停止了。为什么汲取性制度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大体上给出了两种原因。一是在汲取性制度下,创造性破坏并不存在,激励民众进行工作和投资的动力也不存在。在汲取性制度下,精英阶层通常不愿意采用新技术,因为新技术会带来创造性破坏,会威胁到精英阶层自身的统治地位,会暂时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以及影响社会安定,对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担心使得精英阶层不愿意采用包容性制度。二是那些存在于汲取性政治制度之下的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从本质上而言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汲取性制度自身产生的内讧摧毁[7](pp.64-66)。由上可见,那些幸存于汲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通常难以持续下去,容易出现夭折的情况。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互影响的情况也受到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重点关注,其中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就是这种相互影响情况的一种主要体现形式。依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之见,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一种负反馈的情况,它们之间有一种恶性循环关系,即汲取性政治制度倾向于千方百计地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而汲取性经济制度也通常会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存在和维续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当然,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对国家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因此被称为一种负反馈。例如,塞拉利昂的发展情况就非常鲜明地凸显了这种负反馈的情况。英国殖民者在对塞拉利昂进行殖民期间,为了从塞拉利昂获取很多利益,很自然地在塞拉利昂建立了汲取性制度。当塞拉利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后,塞拉利昂的权力握有者只顾获取个人私利,没有动机改变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是继续维持着这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易言之,塞拉利昂的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存在巩固了汲取性经济制度,同时那些从汲取性经济制度中获益良多的人会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收买法官以及操纵选举等,从而为业已存在的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持续存在提供资源和支持。对于这种负反馈背后的内在逻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曾总结道,“汲取性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构成对权力行使的约束,因此推翻之前的独裁者并控制国家的那些人根本不受任何制度的限制,可以随便使用权力,滥用权力;汲取性经济制度意味着仅仅通过控制权力、征用他人财产和建立垄断就有大量的利润和财富可赚”[7](p.273)。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国家繁荣,汲取性制度应该过渡到包容性制度。
与汲取性制度下难以为继的增长相比,包容性制度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国家的兴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英国为例分析了包容性制度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光荣革命在很多方面对英王及其官员的权力做出了有效的限制,议会获得了極大的权力。例如,它拥有财政权,可以决定采取何种经济制度,同时,英国的政治体系并不局限于精英阶层,它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这些阶层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换言之,光荣革命成为英国社会走向多元社会的一个关键节点,英国也因而成为创建世界上第一套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当英国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被建立起来之后,英国的经济制度也开始不断走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光荣革命之前存在的垄断、任意征税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在光荣革命之后都开始慢慢消退了,“政府采用了一系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激励的经济制度。它稳定地实施产权,包括给想法也赋予产权的专利制度,这提供了创新的重要激励。它保护法律和秩序”[7](p.73)。光荣革命是英国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契机,多元主义政治制度的出现是光荣革命的重要成果,乡绅、制造者、商人和贵族等群体一起推翻了专制主义制度,“使财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保障,因为人民不再惧怕国家的掠夺行为”[7](p.4)。在光荣革命爆发之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出现并非偶然,这与从英国包容性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来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关联性。在包容性经济制度建立后,私有产权获得明确的保护,金融市场得以改善,国内的垄断被逐渐消除,工业扩张的壁垒也消除了,在此之后,英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英国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与上述负反馈关系不同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正反馈的情况,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种良性循环关系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机制发挥作用[7](p.248)。其一,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以及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多元分配的基础之上的。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权力的分散状况使得某些人想垄断某些权力已经变得不可能,这也使得法治观念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成为一条不容背离的理念,这种原则也使得英国自19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选举权。其二,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支持,这种相互支持可以真正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包容性经济制度清除了诸如奴隶制和农奴制等最恶劣的汲取性经济关系,降低了垄断的重要性,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政治竞争环境更加公正,这些都弱化了人们试图通过篡夺政治权力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其三,包容性政治制度基本上不会对媒体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当它表露出滥用权力的做法时,这种现象肯定会遭到媒体的严厉批评。
三、趋向全球平等:包容性发展与全球正义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制度的视角对国家兴衰以及全球不平等的原因做出了一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分析,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提炼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这两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兴衰以及由此出现的全球不平等,对政治发展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还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情况,尤其将分析的重心置于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之间的负反馈关系以及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之上,这些做法都很有启发意义。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解释仍存在一定限度。第一,在制度经济学的传统中,休谟、斯密、弗格森以及诺斯等人只是强调制度是解释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这种解释路径推向了极致,只是从制度这个单一角度解释国家兴衰,但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只是强调这是由一些偶然因素和制度漂移造成的。实际上,国家兴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通常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例如,中东一些盛产石油的国家和缺少石油的国家通常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也有着很大的差别。第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选择较小样本的基础上试图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并试图将其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的发展,这其中的解释效力令人怀疑。他们将英国作为采取包容性制度的典型国家,英国确实在工业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飞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20世纪以来,英国基本上就处于衰落状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论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第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论证方法上有时存在循环论证的倾向。例如,按照他们的观点,英国和西班牙分别对北美洲和南美洲采取不同的殖民模式以及不同的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方式,这导致英国和西班牙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并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力分配方式,致使英国和西班牙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制度。然而,在为什么英国和西班牙会对北美洲和南美洲分别采取不同的殖民模式以及在大西洋贸易中采取不同的模式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与英国和西班牙以前拥有的制度存在某种关联性,这种论证方法使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论有循环论证的嫌疑。
在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这种现象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又是全球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当今世界上各国贫富差距巨大、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大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被有效应对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在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实现全球正义,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应对方式。国际层面上的包容性发展主要侧重于促进发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减少全球不平等和推动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当下,包容性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基本共识之一,这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不平等逐渐扩大有很大的关联性。
国家间不平等的日益扩大,与国家自身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诚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反复强调的那样,各个国家采取的不同制度肯定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兴衰,有些国家采取了包容性制度,而有些国家恰恰采取了汲取性制度。汲取性制度是导致一些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某些国家采取汲取性制度呢?这是因为有些国家在历史上长期被他国殖民,殖民者为了从殖民地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就在殖民地建立汲取性制度,虽然这些殖民地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有些殖民地中新的领导者并没有将汲取性制度转化为包容性制度,而是为了自身获取更大的利益,仍然延续着先前的汲取性制度。历史上以种族灭绝、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等为代表的一些非正义行为恰恰是当下某些国家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同时,“当前的贫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过去的非正义的担忧。对过去的事情缺乏关注可能表现出缺乏想象力;对现在的贫困缺乏关注表现出道德冷漠。例如,不关心古代斯巴达的奴隶阶级当然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中有更多的实际迫切诉求,而对非洲奴隶制及其当前后果缺乏关注则是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能力。因此,‘历史上的非正义不可否认地对当前的非正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0]。目前一些富裕国家也正是这些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的受益者,因此,这些富裕国家必须对因其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而致贫的国家进行赔偿。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矫正历史上的某些非正义现象就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赔偿就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它既包括战争赔款等经济形式的赔偿,也包括公开道歉、真诚忏悔、恢复名誉和反省战争等非经济形式的赔偿。
全球不平等的日益扩大与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发言权,各种规则往往不利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国际秩序通常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深刻影响着一些贫困国家的发展,是全球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例如,国际借贷特权是目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形式,它是指任何国家(无论专制的抑或民主的)的统治者都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向国际机构或他国借贷,这种特权也使得借贷国在国际上不得不承担一些义务。如果其继任的政府拒绝偿还,那么该国将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严厉制裁,至少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丧失了借贷资格。现行国际法不加区别地对国际借贷特权的承认和保护会带来何种结果呢?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认为,它使得那些专断的统治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很容易获得贷款,并用贷款去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借贷国的民众被迫承担了大量的负担,同时它也会强化某些人通过政变攫取政权的动机[11](p.114)。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中,新政府不能拒绝偿还旧政府欠下的债务,也不能拒绝履行将要担负的义务。倘若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不能得到规制,势必会阻碍包容性发展的实现。
实现全球正义是包容性发展的主要目标。什么是全球正义?全球正义是一种超越目前国家边界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論,主张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分配正义,强调不管人们属于哪个国家,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强调个人是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研究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视角,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和人权则是全球正义理论的三种主要分析路径①。博格、查尔斯·贝兹(Charles R. Beitz)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等人是全球正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②。一方面,全球正义要求富国及其公民援助穷国及全球贫困者。例如,当某些国家发生地震、洪水或者海啸等自然灾害时,有援助能力的国家要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款、物资或医疗救助等援助。另一方面,全球正义要求尽力消除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例如,抵制某些国家对他国主权的任意侵犯等行径,改革目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高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主要机构(比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发言权,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决策等。
怎样实现全球正义?大体上而言,公平的全球治理有助于全球正义的实现。公平的全球治理应当以一些核心价值为依托。全球治理应当以哪些核心价值为根基呢?全球治理的价值对于确保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以及对于全球治理能否取得积极的效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进行过一种富有影响力的论说,“一切人都能信守尊重生活、自由、正义和平等、互相尊重、关心别人和正直等核心价值。这就会提供一个基础,把建立在经济交流和信息进步之上的全球友邻关系,改造成为一个一统的道义社会”[12](p.47)。当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已经不断清晰和明朗起来,总体上来说,平等、正义、人权和民主等价值是公平的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价值业已成为全球治理不应当违背的核心价值。如果全球治理能够真正奠基于这些价值的基石之上,那么全球治理就是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否则,全球治理将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公平的全球治理将推动包容性发展的逐步实现,将有利于全球正义的逐步落实。例如,公平的全球治理有利于在全球层面上建构一种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能够逐步减少目前全球很多领域中业已存在的民主赤字,能够在全球层面上逐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上所载的各项权利,能够使某些国家承担对其他国家的赔偿义务。因此,通过公平的全球治理,全球不平等程度也能够逐渐得以缓解,全球正义也能够逐渐落实。
注释:
①关于全球正义理论的三种主要分析路径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拙文:《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例》,《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9期;《全球正义的契约主义分析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论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②相關研究参见Thomas W. Pogge. 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94(3); Charles R. Beitz. 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 Justice. The Journal of the Ethics,2005(9); Peter Singer. Famine,Affluence,and Mora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2(3).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M].谢延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吕应中,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美]达伦·阿西莫格鲁,詹斯·罗伯茨,王维平,何欣.一体化世界中的国家间贫富差距——达伦·阿西莫格鲁访谈录[J].国外理论动态,2012,(7).
[7][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李增刚.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9][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Richard Vernon.Intergenerational Rights[J].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Review,2009(1).
[11]Thomas W. Pogge.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ies and Reform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
[12][瑞典]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M].赵仲强,李正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责任编辑:贾双跃]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Inclusive System and Global Equality
Gao Jingzhu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but some countries are poor? What are the root causes of global inequality? Daron Acemoglus and James Robinsons institution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sourc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untry. According to thi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stitu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inclusive and assimilative systems. Inclus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prosperity, assimilative systems should be turned into inclusive system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 tendency of circular argument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global inequality to realize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inclusive system.
Key words: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inclusive system, inclusive development, global justice